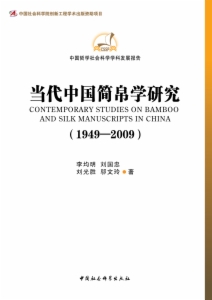第一章 帛书的发现
|
来 源
:
|
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0 \ 下编 帛书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 | ||
|
摘 要
:
|
同简册相比,帛书具有许多优点,帛书可以免除简册容易散断错混的弊病,同时帛质柔软平滑,易于运笔及舒卷,分量又很轻,便于携带。到目前为止,真正属于书籍的帛书总共出土了两批,它们都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附近,一批是40年代出土的楚帛书,还有一批是70年代出土的马王堆帛书。由于三号墓的下葬时间是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前168年),这就为该墓所出帛书的断代提供了一个下限,即它们的抄写时间都不会晚于这一年。 | ||||||
|
关键词
:
|
帛书 概说 汉墓 马王堆 文物 简牍 缣帛 马王堆帛书 墓葬 漆器 封土 |
||||||
在线阅读
第一章 帛书的发现
字体:大中小
一 帛书概说
帛,或称缣帛,系丝织物的总称。帛书也叫缯书,是中国古代用来书写文字的丝织品,因为帛一般是白色,所以又有素书之称。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丝织技术的国家。关于养蚕织帛,在中国曾经流传着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其中有两个故事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一是伏羲氏化蚕桑为绵帛;二是西陵氏之女、黄帝的元妃嫘祖始教民育蚕缫丝以供衣服。这些神话传说展现了中国丝织历史的久远。
20世纪以来的考古成果也充分印证了中国养蚕织帛的漫长历史。1926年春,清华学校(即清华大学的前身)在李济的主持下,曾组织了一个考古团赴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考古发掘,这是中国人自己进行的第一次成功的田野考古工作。当时李济他们所挖掘的是一处距今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遗址。在出土的众多遗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经锐器切割成一半的蚕茧壳,茧壳长约1.36厘米,宽约1.04厘米,上部被锐利刀刃切去。这个茧壳虽然已经有些腐坏,但是仍旧发光。后来李济将它带到美国化验,证实确是蚕茧。该遗址同时还出土了一些陶制的或石制的纺轮残片。这些遗物轰动了当时的学术界,也为人们研究丝绸起源提供了具体物证[※注]。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出土了一批距今4700多年的丝织品,其中有平纹残绸片,蚕丝编的丝带,以及用蚕丝纺捻而成的丝线[※注]。另外,1984年在河南荥阳还出土过我国北方丝麻织品的最早实物——一些平纹组织物和组织稀疏的浅绛色丝织罗[※注]。这些发现充分证明,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开始养蚕织帛,而且当时生产丝绸的地区已经比较广阔,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均有所分布。
不过,虽然中国养蚕织帛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很显然是将之作为衣物使用,中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帛来书写文字,至今仍是一个不易说清的问题。

丝帛什么时候用作书写材料,目前尚难考订。不过,从文献记载来看,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帛书。《晏子》外篇卷七云:“景公谓晏子曰:‘昔吾先君予管仲狐与穀,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以为其子孙赏邑’。”我们知道,齐景公和晏子是公元前5至6世纪的人物,而齐桓公、管仲则是春秋早期的活跃人物,本篇文字中称齐桓公赐给管仲两块地一事曾经“著之于帛”,如果此言可信的话,那么在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已经出现帛书。另外,《论语·卫灵公》中有“子张书诸绅”的记载,而《周礼》卷三十《司勋》中则说:“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这里的绅、太常皆为缣帛之类的织物。又,《士丧礼》言“为铭各以其物(郑注:杂帛为物),亡则以缁”,《国语·越语》则曰“越王以册书帛”[※注],也可证明春秋时期帛书的存在。《墨子·明鬼》篇说:“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墨子是战国早期的思想家,成语“书于竹帛”即源自他的这篇论述,它反映了当时简册和帛书并行的情况。又如《韩非子·安危篇》亦有“先王致理于竹帛”之语。有鉴于此,王国维曾指出:“帛书之古见于载籍者,亦不甚后于简牍。……以帛写书,至迟亦当在周季。”[※注]应该说王氏的这一见解是很有见地的。
到了秦汉时代,用帛书写文字的记载材料就更为丰富,仅以《汉书》为例,从中即可见到秦汉时代有关帛书的众多记述:
陈胜、吴广起义时,为了在众人中树立威信,“乃丹书帛曰:‘陈胜王’”(《汉书·陈涉传》)。
刘邦起义时,为了策动沛县城中百姓,“乃书帛射城上”(《汉书·高帝纪》)。
秦始皇焚书坑儒,但《诗》却未遭损失,究其原因,《汉书》谓为“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书·艺文志》。又,《汉志》历谱类载《耿昌月行帛图》232卷)。
匈奴拘扣苏武,向汉使诡称苏武已死,汉使遂以“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帛书”加以斥责,匈奴信以为真,只好释放苏武(《汉书·苏武传》)。
……
根据学者们的意见,汉成帝时,刘向、歆父子为皇室进行图书整理工作,往往是先把文字的初稿写在竹简上,改定以后,再写上缣帛[※注]。西汉末年,扬雄调查各地方言,也是把调查来的材料先记录在“油素”(光滑的白绢)上,便于涂抹改动,修改妥当后,再写上缣帛的[※注]。
很可惜的是,汉代的书籍在西汉末的王莽之祸和东汉末的董卓之乱中遭到了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在董卓之乱中,皇室图书遭到董卓士兵的大肆抢掠,“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后汉书·儒林传上》),这些帛书遭到这样的践踏,实在是令人痛心。
帛书在先秦秦汉时期的使用情况大致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用帛来书写,是与帛的特点密切相关。同简册相比,帛书具有许多优点,帛书可以免除简册容易散断错混的弊病,同时帛质柔软平滑,易于运笔及舒卷,分量又很轻,便于携带。帛的另外一项用途,是用来画图。这些方面都是简册所不可企及的。不过用帛书写,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帛上面的文字一经写定,就不好像简牍那样随意删改。更为重要的是,帛是很贵重的丝织品,价格较高,不易获得,从而限制了它的使用[※注]。总的来说,帛要比简册方便,但帛价也比竹木贵重,从而不能像简册那样普遍使用。
自从在汉代发明造纸术之后,纸逐渐取代了简册和帛书而成为更为流行的书写材料。帛书虽然在魏晋时期还间或在使用[※注],但已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帛书和其他丝织品一样,在地下不易保存,因而历史上并未见到有确切记载。帛书的情况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个不解之谜。只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我们才有幸看到了历史上的帛书原物。
1908年,英国人斯坦因(A.Stein)第二次到中国西部进行探险活动时,曾在敦煌发现两封帛书信件,这两封信件保存还较为完好。两封信都发自一人,可能是驻山西北部成乐地方的官员致书敦煌边关某人的信,其内容主要抱怨通信困难。其一约9厘米见方,另一长15厘米,宽6.5厘米。另外,斯坦因在敦煌附近还发现一件未经染色的素帛,一面载有1行28字,文云“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廿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另一面印有黑墨印章。这些材料后来都收录在罗振玉与王国维所编的《流沙坠简》一书中,罗、王二氏还对它们作了考释,如对前两封书信的考释云:
对于后一件载有零星文字的素帛,《流沙坠简》考释云:
除了上述材料外,解放前所发现的敦煌文物中还有2片织造精致的素帛,其一上有深黑色梵文铭,可证明古时中国与印度和中亚有丝帛贸易。1930年,在罗布淖尔古墓中也发现一件丝帛残片,乃公元2世纪之物,右角有10个Kharosthi文字[※注]。
1973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发现棨信一件,这件棨信为红色织物,长21厘米,宽16厘米,上边有系,正面墨书“张掖都尉棨信”六字,原件保存良好,字迹清晰,据简报应为西汉晚期遗物。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棨信即信幡,是一种旌旗,其作用是作为符信,用来传令启闭关门[※注]。
1979年,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还出土了一件帛书,据报道,帛作长条形,长43.4厘米,宽1.8厘米。它的左侧是毛边,右侧则边缘较整齐,上端作半弧形,下端平直。帛上有墨书一行,是绢帛染成红色后再写上去的,其内容是:“尹逢深,中殽左长传一,帛一匹,四百卅乙株币,十月丁酉,亭长延寿,都吏稚,釳”[※注]。
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甘肃甜水井附近的汉代悬泉置遗址进行了全面清理发掘,获得了以简牍文书为主的大量文物。其中帛书有10件,均为私人信札,用黄、褐二色绢作为书写材料。其中编号为II90DXT01143∶611的帛书信件为黄色,长34.5厘米,宽10厘米,保存最为完整。整件帛书竖行隶书,共10行,322字。信中除问候祝福语外,也有诉说边塞辛苦的内容和从内地代为买物寄与敦煌的日常小事,通过这些信件可以了解当时敦煌与内地的交往以及居住边塞人们的生活状况[※注]。
不过,总的来说,上述这些帛书材料显得比较零散,另外,如果从内容上来看,它们也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籍。到目前为止,真正属于书籍的帛书总共出土了两批,它们都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附近,一批是40年代出土的楚帛书,还有一批是70年代出土的马王堆帛书。
二 楚帛书的发现与流传
楚帛书是我国近代以来最早出土的真正可以称得上是简帛书籍的一批重要文献。楚帛书的发现距离现在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对于楚帛书本身在海内外曾流传着种种不同的说法,楚帛书实物则在长时间里收藏于美国的博物馆中,秘不示人,这些情况都给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外交流的深入,有关楚帛书的种种问题才逐渐得以澄清。
1942年9月[※注],一群“土夫子”(解放前长沙人对于盗墓者的称呼)来到当时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南郊一个名叫子弹库的地方(位于现在湖南省林业勘查设计院内),挖开了这里的一座古墓。这座墓葬是属于长沙特有的所谓“火洞子”墓,据说在盗掘时,曾有大量带硫黄气味的气体冒出,用火柴点燃,火焰曾高达数尺。盗墓者进入墓中后,从墓中取走了漆盘、铜剑、木剑鞘、木龙、陶鼎、陶壶、陶簋等物品,另外还取走了一个竹篾编成的书箧,关于这件竹箧(或称竹笈)的情况,蔡季襄在《晚周缯书考证》中曾附有插图,并作了详细的描述[※注]。陈梦家曾经将之概括为:
陈梦家这里所说的盛放在竹笈内的“缯书”及残缯断片,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楚帛书。
帛书出土时,是存放在竹箧里面[※注],这与后来出土的马王堆帛书的情况非常相似。关于帛书在竹箧中的存放情况,商承祚后来也根据“土夫子”的回忆作了描述[※注]:
帛书由于系盗掘出土,盗墓者为了隐瞒真情,故玄其说,曾有意隐瞒真实的出土时间和出土地点,在很长的时间内曾给帛书的出土时间、出土地点等问题造成了很大的混乱。30多年后,为了进一步了解该墓的情况,湖南省博物馆在当年参加盗墓的“土夫子”带领下,于1973年5月重新发掘了这座墓葬,从而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材料[※注],澄清了过去关于此墓葬的种种传闻。
这座墓葬为一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穴墓,墓中棺椁共三层,即椁、外棺、内棺。椁与外棺之间在头端和北边各有一个边箱,随葬器物大多放在边箱里。因曾被盗掘,有的被盗走,有的被遗弃在盗洞近椁盖板处,其余均被移动了位置。在墓中残存的文物中,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一幅“人物御龙帛画”,另外还发现了鼎、敦、壶等陶器,竹木漆器,玉璧,丝麻织物等文物。
由于该墓为一椁二棺的结构,根据《庄子·天下》及《荀子·礼论》记载“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两重”,而且此墓不含青铜礼器,规格较低,再结合帛画上的男子肖像及其装束来看,墓主人估计是士大夫一级的贵族。
至于该墓葬的年代,此墓出土的鼎、敦、壶等陶器是战国中期常见的器物组合,但陶敦器形扁圆,子母口又很明显,具有向后递变的一种形制。另外,据1942年参加盗掘的“土夫子”所言,头箱内曾出土了泥金版,而长沙楚墓出土泥金版仅见于战国晚期的墓葬中。根据这些情况,考古工作者认为此墓的年代约相当于战国中晚期之交,楚帛书的年代下限亦可因此而得以确定。
楚帛书被盗掘出土后,不久就为古董商人唐鉴泉所得。唐鉴泉原做上门裁缝,1927年正式开店营业,招牌为“唐茂盛”。并辟屋之半兼营古玩。从1931年起他专营古玩,人皆呼之为“唐裁缝”。唐鉴泉得到帛书后,曾写信给著名学者商承祚,以帛书求售。商先生接到信后,托友人沈筠苍前往了解情况。沈筠苍给商先生回信中说:“唐裁缝出视之时,是在白纸之外再用报纸将之松松卷起,大块的不多,小块的累累,将来拼复原样恐不可能。”正当商承祚与唐鉴泉反复议价之时,长沙地区的文物收藏家蔡季襄回到长沙,帛书遂为他所得。
蔡季襄得到帛书后,请有经验的裱工将帛书加以拼复和装裱,并命长男蔡修涣按原本临绘帛书图文,蔡季襄亲作考释,写成《晚周缯书考证》一书,该书写于1944年的抗战炮火之中,1945年春印行。此书出版后,楚帛书及其内容的情况才传播开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蔡季襄携带楚帛书来到上海,寻求将帛书出手。1946年,他在上海遇到了柯强(John Hadley Cox)。柯强是美国人。1935—1937年曾任教于长沙的雅礼中学,并在长沙大肆收购中国文物。抗战爆发后他返回美国,至抗战结束后又从美国来到上海。蔡季襄与柯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二人以10000美元将帛书成交,议定帛书由柯强在美国代为兜售,柯强留下押金1000元,余款待付,帛书及其他绝大部分帛书碎片及装帛书的竹箧等物都因此全部流入美国。
关于帛书的上述这些情况,据陈松长公布的蔡氏自述材料[※注],我们可以得到更为明确的了解。
蔡季襄在他的自述材料中说,1943年,他在从上海逃回长沙后,花了数千元的代价,在东站路唐茂盛古玩店买到战国时代出土的缯书一幅和其他陶铜器物。然后,长沙于1944年4月沦陷,蔡季襄携带楚帛书避难至安化。在安化城北租房住了一段时间,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于1944年8月份以前写成了《晚周缯书考证》,同年在蓝田付印,第一次对楚帛书的形制、文字和图像进行了研究和介绍。1945年抗战胜利,蔡氏从安化回到长沙,因生计清淡,即于1946年携带楚帛书前往上海,想通过上海的古董商金才记卖一个好价钱。但金才记出价太低,蔡氏转而找了另一位早已认识的古董商叶三。叶氏认为在当时上海帛书漆器等文物的销路不好,不愿接手。后经傅佩鹤从中牵线,与正在上海的柯强联系上了。见面后,柯强看到了蔡氏所写的《晚周缯书考证》一书,如获至宝,索要了一册带回他的寓所。后在柯强的寓所里,柯氏介绍说美国有红外线照相机,可以显示缯书上不清楚的文字,提高和增加缯书的价值。这样,在傅佩鹤的怂恿和柯强的一再要求下,蔡氏既为了脱手卖个好价钱,又为了多解决一些文字的释读问题,答应将帛书借给柯强研究照相,结果却被柯氏连哄带骗地将帛书转手带到了美国。关于帛书的被骗经过,据蔡氏自己所述,其详细情况是:
帛书流入美国之后的情况,长期以来国内的学者一直不太了解,经过李零的精心调查[※注],现在我们对于帛书在美国的流传情况已经比较清楚。
柯强把帛书带到美国后,曾到各大博物馆兜售。然而,尽管柯强把价钱一直压到了7500美元,并且反复强调说此物如何重要,声称如果无人购买,就得归还中国,或者到伦敦和斯德哥尔摩去卖,然而始终没有一家博物馆愿意购买[※注]。因此,到了1949年,柯强把比较完整的这件帛书寄存于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留供检验。至于其他帛书残片及存放帛书的竹箧,柯强则将之送到福格博物馆(the Fogg Art Museum)检验。因此,在1964年之前,帛书始终处于“无主”的状态。
1964年,柯强把存放在大都会博物馆的那件比较完整的楚帛书取出,售给纽约的古董商戴润斋(F.T.Tai),到了1966年,戴润斋又把从柯氏手中购得的文物转售给美国著名的文物收藏家赛克勒医生(Dr.Arthur M.Sackler),据说当时戴氏本想留下那张楚帛书,但因美国著名古物收藏家辛格医生(Dr. Paul Singer)偶然发现并大力推崇,力劝赛氏购进此物[※注],这样,楚帛书才归赛氏收藏,楚帛书亦从此声名大噪。
1966年之后,楚帛书一直是赛克勒的藏品,并于1987年赛克勒美术馆建成后从纽约移到该馆收藏。赛克勒本人现在已经去世,但他生前曾表示,总有一天他会把此物归还中国。
1992年,柯强将其他帛书残片连同书笈也一起售给了赛克勒美术馆。至此,流入美国的所有帛书材料都被赛克勒美术馆所收藏。现在这些帛书残片正在整理之中。
楚帛书被柯强带到美国去后,只有极少的一些帛书碎片还留在国内,据说这些帛书残片是蔡季襄送给徐桢立的,徐桢立又将它们转送给商承祚,它们总共由14片残帛组成,残帛中最大的一片最长处4.6厘米,最宽处2.7厘米,很可惜的是除了这一大片残帛之外,其余的13片残帛现在都已不知下落,只剩下在1964年由文物出版社史敬如为之拍摄的照片及商氏自己的摹本。1992年,《文物》和《文物天地》同时公布了这批珍贵材料[※注]。1996年,商承祚的后人将现存的那片残帛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这片残帛也是国内目前仅存的唯一一片子弹库帛书的残片。
三 马王堆帛书的发现
马王堆帛书是马王堆汉墓发掘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是新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史上一次重要的考古发掘。对于马王堆汉墓发掘的意义及其重要地位,李学勤曾经形象地指出:“真正的重大发现当然包括相当数量的珍品,但其根本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此。重大的考古发现应当对人们认识古代历史文化起重要影响,改变大家心目中一个时代、一种文化以至一个民族的历史面貌。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必须载入考古史册的重大发现。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就是这样意义的重大发现。……发现中有完好无损的女尸,有成组成套的物品,还有内容珍秘的帛书、竹木简。这三项有其一,已可说是重要发现,如今三者兼有,在中国考古史上尚没有其他例子。”[※注]
马王堆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五里牌外,距长沙市中心4公里,这里的周围地势平坦,交通方便,中间有一个方圆约半里的土丘,土丘的中部残留着两个高约16米的土冢。土冢一东一西,紧相邻接,底径各约40米,顶部圆平,直径各约30米。两冢平地兀立,中间接连,从远处看,形状很像一个马鞍。
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工作队曾对马王堆这两个土冢作过调查,根据封土及有关情况,断定这里是一个汉墓群。1972年,考古工作者正式发掘东土冢,整个发掘工作至4月底结束。因为这是一座汉墓,故被定名为马王堆一号汉墓。马王堆一号汉墓由封土、墓道、墓坑和墓室(即墓坑下部)组成,形制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斜坡墓道在墓坑北边正中,上宽下窄。墓坑在封土下,墓口南北长20米,东西宽17.9米,从墓口至墓底深16米。墓坑中填“五花土”,并经夯打,木椁四周及上部填塞木炭,木炭外面又用白膏泥填塞封固。可能主要是由于木炭和白膏泥的防潮防腐作用,使尸体、葬具以及大量随葬器物得以保存完整。
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墓中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另外还发现了T形帛画、素纱蝉衣、漆器、乐器、木俑等一千余件珍贵的文物,一些器物上还写有“轪侯家”等文字。一号墓的材料一经公布,立即轰动了世界。
因为马王堆东土冢被定名为一号汉墓,相应地,西土冢就被定名为马王堆二号汉墓。另外,在发掘一号汉墓的过程中,又在它的南面发现了一座汉墓,考古工作者将之命名为马王堆三号汉墓。三号汉墓在一号汉墓南4.3米,由于三号汉墓的封土堆几乎全部被一号汉墓的封土所覆盖,外表上很少露出痕迹,所以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这里只有两座墓葬。
为了更全面地认识马王堆汉墓的总体情况,1973年,考古工作者继续对马王堆二、三号汉墓进行了发掘。其中三号墓墓坑是带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墓口南北长16.3米,东西宽15.45米。墓道位于墓坑北端的中部,坡度为19度,这座墓墓口的西、北两壁和墓道,在构筑一号墓南壁时被部分破坏,表明三号墓是早于一号墓的。
马王堆三号墓共出土了一千余件随葬器物,包括帛画、帛书、简牍、兵器、乐器、漆器、木俑、丝织品、博局等。其中帛书全部出土于东边箱的57号长方形漆奁。这个漆奁长59.8厘米,宽37厘米,高21.2厘米,内有五格,大部分帛书放在漆奁中间较大的一个格子里,少部分放在边上那个较窄的通格里,上面还压着两卷医书竹简[※注],由于年久粘连,有残损。
三号墓出土的简牍从内容上看可分为遣策和医书两种,其中的木牍记有该墓的下葬年代,时间是“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另外,墓中还出土了带有“轪侯家”铭文的漆器。西汉初期纪年中超过十二年的,仅汉高祖有十二年和汉文帝初元有十六年。“轪侯”系汉惠帝时封给长沙相利苍的爵位,自然可以排除汉高祖时代的可能性,而汉文帝初元十二年二月恰好是乙巳朔。这样三号墓的年代就得以确定,为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前168年)。
随后考古工作者又对马王堆二号墓进行了发掘。二号墓的封土被一号墓的西壁打破,由此证明二号墓的年代也是早于一号墓。二号墓也是带墓道的坚穴,二号墓由于密封不好,再加上历史上多次被盗,所以保存情况较差。在墓内残存的随葬品中,最重要的是三颗印章。一颗是玉质私印,刻阴文篆体“利苍”二字,另两颗是铜质明器,分别刻阴文篆文“轪侯之印”和“长沙丞相”,从而为判断二号墓的墓主身份提供了证据。
通过对马王堆三座汉墓的全部发掘,这三座汉墓的年代、墓主身份等问题也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二号墓出土的“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和“利苍”三颗印章,是马王堆为利苍一家墓地的确证,从而纠正了过去将之说成长沙王刘发等人墓地的说法。据《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和《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的记载,利苍是汉惠帝二年(前193年)被封为轪侯的,死于吕后二年(前186年),由此可知二号墓的时间即应当在此年。
三号墓出土的一件木牍上有明确的纪年,据此而推定它的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其情况已如前述。
至于一号墓的年代,由于它分别打破了二、三号墓,从地层关系上看是晚于二、三号墓的。但是,一号墓和三号墓的随葬器物,无论是漆器的形制、花纹和铭文,还是丝织品的图案,或者简牍文字的书体、风格都非常接近,往往如出一人之手;而一号墓出土的泥“半两”和三号墓填土所出“半两”钱,又同样都是文帝时期的四铢半两,因此,两墓的年代应该相当接近,可能相距仅数年而已。
弄清楚了马王堆三座墓的年代,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一号墓与二号墓东西并列,都是正北方向,两墓中心点的连接线又是正东西向,封土也几乎同大,由此推断这是两座不同穴的夫妇合葬墓。男西女东,正符合“古时尊右”的习俗。可见二号墓是第一代轪侯利苍之墓,一号墓应是利苍妻子的墓,她比利苍晚死20余年。
三号墓紧靠一号墓的南方,即利苍妻子之墓的脚下,两墓墓口相距仅4.3米。据鉴定,一号墓女尸的年龄为50岁左右,三号墓墓主的遗骸为30多岁的男性,二者相差20来岁,当是母子关系。因此,三号墓墓主应是利苍夫妇的儿子。
由于三号墓的下葬时间是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前168年),这就为该墓所出帛书的断代提供了一个下限,即它们的抄写时间都不会晚于这一年。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