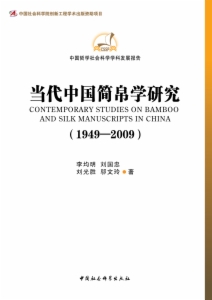八 简牍典籍与先秦、秦汉学术史的重建
|
来 源
:
|
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0 \ 上编 简牍典籍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 | ||
|
摘 要
:
|
简牍典籍所处的时代主要在战国、秦汉时期,虽只处于学术史的前段,但前段与后段源流相连,是一个整体,如阜阳汉简证明《孔子家语》并非伪书,而有清之际盛行一时的王肃伪造说自然得以平息,因此对简牍时代学术史的考察,是整个学术史重写的前提和基点。阜阳汉简《诗经》中有“后妃献”、“风(讽)君”等3片残简,整理者认为应是阜阳汉简《诗经》的《诗序》残文, 《毛诗序》的成书年代有战国、汉代、三国等不同说法,阜阳《诗经》的下限是汉文帝十五年,这为解决《毛诗序》的学术公案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佐证。必然会引起我们对学术理论的重构,简牍对考据与义理的双重作用,站在21世纪末尾,或许会看得更加清楚。 | ||||||
|
关键词
:
|
简牍 诗经 学术 周易 老子 汉简 宇宙 归藏 典籍 太一生水 古书 |
||||||
在线阅读
八 简牍典籍与先秦、秦汉学术史的重建
字体:大中小
顾炎武指出,周贞定王二年(公元前467年)至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凡一百三十三年间,“史籍阙轶,考古者谓之茫昧”(《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造成这一学术困境的原因:一是当时统治者对古书的人为破坏;二是对古书成书年代的人为后置,使战国学术史后置为秦汉学术史。前者的破坏是无法弥补的,而后者的影响是可以挽回的,大量简牍典籍的出土不仅扩充了古书的内涵,而且作为断代标尺,使一大批古书的成书年代得以重现确立,在学术史上确立了若干可以贯串起来的坐标点,因此将某一类型的古书(包括简帛本),如易学、诗学等,按照时间先后排列起来研究,就能大体上重现构建学术史的发展链环,重写早期学术史的新篇章。
大量简帛典籍的出土,直接影响是使学术史的重写成为可能。简牍典籍所处的时代主要在战国、秦汉时期,虽只处于学术史的前段,但前段与后段源流相连,是一个整体,如阜阳汉简证明《孔子家语》并非伪书,而有清之际盛行一时的王肃伪造说自然得以平息,因此对简牍时代学术史的考察,是整个学术史重写的前提和基点。
《周易》是一部古老的典籍,从汉代开始,被尊为五经之首,六经之中,《史记》对易学传承的记载最为详尽,上博简《周易》、王家台秦简《归藏》、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阜阳《周易》及楚简中“卜筮祭祷简”的出土,使易学研究的空间得以大大拓展,通过文本比勘,可使久思无解的经文获得新知。上博简《周易》有经无传,证明了易学中的“九六”之称,在先秦已经存在。夏有《连山》,商有《归藏》,西周有《周易》,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出土,证明了辑本《归藏》的可信。马王堆帛书卦序与今本《周易》不同,卦名“钦”、“林”与《归藏》有关,但帛书《系辞》却与今本相近,呈现出《归藏》与《周易》复杂交融的状态,因此将不同时期的易学著作重新排队,考释《周易》经传的文本内涵,梳理《归藏》、《周易》传流脉络,就成为易学研究中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汉代诗学以毛、鲁、齐、韩四家最为有名,但出土简牍却与四家诗学并不相同。阜阳汉简《诗经》多通假字、假借字,与《毛诗》不是一个系统,也不是鲁、齐、韩三家《诗》中的任何一家,可能是流传于楚地的诗学流派。《汉书·艺文志》说:“《诗》凡六家,四百一十六卷。”《汉书·儒林传》又提到“《鲁诗》有韦氏学”、“《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阜阳汉简《诗经》的出土使我们看到了汉代诗学蔚为大观的兴盛面貌。郭店简的出土,只是让我们看到了《缁衣》、《五行》等篇中引《诗》、论《诗》的部分章句,而上博简《诗论》作为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诗学理论著作,它的出土把《诗经》学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阜阳汉简《诗经》中有“后妃献”、“风(讽)君”等3片残简,整理者认为应是阜阳汉简《诗经》的《诗序》残文,《毛诗序》的成书年代有战国、汉代、三国等不同说法,阜阳《诗经》的下限是汉文帝十五年,这为解决《毛诗序》的学术公案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佐证。汉代解诗,大都是从政治方面阐发《诗经》的道德教化作用,而上博简《诗论》中孔子首先对《诗经》作整体论说,再依次对邦风、大夏(雅)、小夏(雅)各篇思想内容、特点逐一解说,并无《毛诗》的政治教化色彩,因此我们将上博简《诗论》、阜阳汉简《诗经》残本、《毛诗》及《孔丛子》中孔子论诗结合起来,考释今本《诗经》文句的本义,就会大大丰富我们对早期儒家论《诗》传《诗》的认识,廓清早期诗学传播的脉络,推动和深化当前的《诗经》研究。
先秦儒学的三大坐标为孔、孟、荀,虽然彼此的思想框架基本相同,但从孔子到孟子,从孟子到荀子,儒学却有很大发展变化,其间的变化轨迹,特别是孔孟之间的一百七十年,由于资料缺乏,一直晦暗不清。按《先秦诸子系年》,我们将孔孟之间重要谱系人物的生卒年代排列如下[※注]: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
曾子约公元前505年—前436年
子思约公元前483年—前402年
子上约公元前429年—前383年
孟子约公元前390年—前305年
孔子殁后,儒学继续向前发展,曾子、子夏、子游等为第一代,子思为第二代,子上为第三代,孟子为第四代,孔孟之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代。郭店儒简出土于湖北荆州市郭店1号楚墓,考古学界利用类型学的方法,推定此墓的下葬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末,即不晚于公元前300年,郭店儒简中有《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缁衣》等明确可以肯定属于子思学派,郭店儒简除《语丛》外的其他篇章,反映的是孔孟之间子思及其弟子生活时代的思想世界,代表了当时儒家心性之学所达到的水平与高度。
我们知道,孔孟之间长达一百三十多年,只靠郭店简“一个驿站”并不能填平孔孟之间的思想“沟壑”,上博简《内礼》的出土,证明前人关于《曾子》十篇晚出的种种怀疑均不能成立,《曾子》十篇的成书时间和曾子及其二、三代弟子的生活年代相当,因此我们将《曾子》十篇与郭店简串联起来,就能进一步把孔孟之间的研究推向深入。
孔子去世后,曾子成为早期儒家学说的主要传播者,《韩非子·显学篇》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家八派中有四派与曾子有密切关联(李学勤先生语),因此《曾子》十篇和郭店儒简同处孔孟之间,是先后相承的两个学术枢纽,把握了《曾子十篇》与郭店简的内容关联,实际就是把握了孔孟之间思想演变的主线。
《荀子·非十二子》指责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杨注:“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荀子也是儒家,笃信仁义,没有批判仁义礼智信的理由,因此近人多不信杨说。也有学者怀疑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但却在思孟著作中找不到踪迹,以致思孟“五行”竟成为学界千年不解之谜。简帛本《五行》的出土,始知思孟“五行”乃是指“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而非“木、火、土、金、水”阴阳五行,五行之谜涣然冰释,为研究由子思五行到孟子四行的哲理提升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学证据。
朱熹对《大学》格物致知的解释是:“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四书章句集注》)朱熹训格为至,认为自己必须切近外物才能穷尽事物之理,训致为推极,训知为识,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今日穷一理,明日穷一理,日积月累,瞬间自会豁然开朗,穷尽万物之理。王阳明青年时代,为求得圣人之道,依朱子“致物穷理”之说,去亭前格竹子之理,到七日,“劳思致疾”,遂叹曰“圣贤是做不得的”[※注]。
《性自命出》和《大学》同处孔孟之间,内容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结合《性自命出》对《大学》“格物致知”章进行新的诠释。《性自命出》说:“凡见者之谓物”,“格”应按照郑玄注,训为来,“物格”就是物或事出现。《性自命出》的“性”是会意字,从生从目,性生而具有视物的能力,“致知”的意思是外物出现就会被人发现,被性感知[※注]。这里的关键是对诚意的理解,明白了诚分为圣人之诚和人之诚两种。在哲理上,人可以通过圣人上达天道,实现天人贯通。在实际生活中,人能在圣人《诗》、《书》、《礼》乐经典中感悟到成贤成圣的真理,不会再犯王阳明“格竹子”的错误了。
郭店儒简的出土,使孔孟之间一时成为学术的热点,但不要忘记,出土文献是使整个早期儒学浮出水面,荀子的性恶论与郭店简《性自命出》“好恶,性也”有一定关联,荀子的天人相分理论可以在郭店简《穷达以时》中找到渊源,荀子对思孟的批判可以在郭店简《五行》中找到支点,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中的韵文八首格式、用韵都与《荀子·成相篇》非常相似,证明《荀子·成相篇》与民间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郭店简的出现,不仅孔孟之间,而且孔荀之间,也不再遥远。
《老子》以道作为自己的哲学本体,不少地方讲“一”,却不讲“太一”,不以太一作为自己的学说本体。《老子》说“上善若水”,推崇水之德,却从不以水作为化生万物的载体,也不讲“太一藏于水”。《太一生水》以太一为本体,以水、天地、阴阳、四时等的相辅相成作为宇宙生成的途径,描绘了宇宙从无到有的创生过程,战国道家宇宙生成论重视气化学说,《太一生水》的问世,使我们得知在“尚气”理论外,还有一个尚水的理论体系[※注]。作为重要的道家佚文,《太一生水》宇宙生成模式与《老子》的理路迥异,也不见于其他传世文献,因此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太一生水》“水生”不同,《亘先》重“气化”,以亘先为人事名言建构的最初,不强调母子关系,重视宇宙演进先后。《太一生水》与《亘先》反映了战国时期道家的宇宙生成理论上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郭店简《老子》没有反儒倾向,到马王堆帛书《老子》反儒倾向的强化,因此老学自身的演变就很值得探究。郭店简《老子》的出土,证明《老子》成书在《庄子》之前,李学勤先生《孔孟与老庄之间》指出《亘先》的一串术语“大全”见《田子方》,“太清”见《天运》,“太虚”见《知北游》,因此《亘先》可以看做《老子》到庄学的桥梁。
马王堆帛书的问世,使我们看到了黄老之学的真实面貌,黄老学派将老子与黄帝之学结合起来,其在政治上的有为与庄子一派迥然有别,并在汉初政治舞台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黄老之学的形成与发展是战国时期道家思想的重要转变。楚简《太一生水》、《恒先》、《三德》为早期道家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而《慎子》、《鹖冠子》、《尹文子》、《文子》等文献本来面目的重现,使早期道学史也面临重写的问题。
《史记》记载庞涓兵败,自杀于马陵,《孙膑兵法·禽庞涓》记载孙膑擒庞涓于桂陵,为考证庞涓的军事经历提供了新的文献依据。银雀山汉简的出土,使吴《孙子》、齐《孙子》、《尉缭子》及《六韬》等书的本来面貌得以恢复。战国时期,车战已逐渐退出军事舞台,而上博简《曹沫之阵》仍以车战为主,且主要人物是曹刿与鲁庄公,因此上博简《曹沫之阵》实际是反映了春秋早期兵法谋略,而《孙子兵法》为春秋末期,《孙膑兵法》、《尉缭子》为战国时期,张家山汉简《盖庐》为亡佚已久的兵阴阳家的著作,《六韬》的成书时间则相对晚些,因此将不同时期的兵学文献联系起来,就为研究先秦、秦汉时期兵家军事思想及战略、战术的转变开辟了新的境界。
过去我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精英阶层文化,即《汉书·艺文志》中前三类——六艺、诸子、诗赋,而忽略后三类——兵书、术数、方技。出土简牍、帛书文献却有相当大的部分恰恰是“兵书”、“术数”、“方技”,天象星占、择日龟筮、医方养生、兵家阴阳的知识在古代随葬文献中的数量,表明它在实际生活中占了很大的分量,也常常是古代思想的背景;比如占卜中所依据很大的分量,也常常是古代思想的背景:比如占卜中所依据的阴阳五行的技术操作方法,与古代中国人对大宇宙和小宇宙的观念有关;医药学中的很多知识,也与古代中国人的感觉体验有关;而天象地理之学,更是古代中国思想合理性的基本依据。可以说,考古发现的大量术数、方技类简帛文献,促进了对于中国古代一般知识与思想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思想史的注意焦点[※注]。
大、小传统是美国人类学家雷斐德(Robert Redfield)1956年首先提出的概念,他在《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一书中说,“大传统”(great tradition)是指社会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是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即“雅文化”,而“小传统”(1ittle tradition)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也称“俗文化”。相互依存而相互影响,是大小传统的基本规律。我们这里借用雷斐德的概念,所谓“大传统”是指《汉书·艺文志》中前四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即流行于社会上层的经典文化。所谓“小传统”是指《汉志》的后两类——术数、方技。所谓“小传统”是指流行于社会下层的民间文化。
小传统的特点是实用性、稳定性、隐蔽性,实用性是指和民生紧密相关,稳定性是指民间是其扎根的土壤,长时间在民间流传,隐蔽性是指在《汉志》之后,正史的记载逐渐减少,甚至在正史中不见其生存的痕迹。简牍帛书中出土大量的数术、方技类古籍,促使我们对“小传统”价值进行重新的审视,李零《中国方术考》、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都是成功的例证。
今天我们所说的重构,不是单指大、小传统的研究,是指通过简牍来研究大、小传统之间的互动,古代数术、方技,保存了较多原始的资料和信息,是精英文化的渊薮,大传统的宇宙论、人性论等哲学命题,往往来自对这些小传统的继承与归纳。民间流行的数术、方技,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大传统的影响与改造,今天主流意识排斥数术、方技的态度已有所改变,但问题是如何从学术层面来研究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吸收、相互影响,这才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任务与方向。
大量简牍典籍的出土,使20世纪的学术面貌获得巨大改观,简牍材料的大量出现,固然令人惊喜,但我们的“消化”能力却非常有限,真正“吃透”这些出土典籍,恐怕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因此21世纪必定是一个简帛时代。出土文献也是文献,我们处于21世纪的开端,现在的研究,多是字词、版本、源流等方面一个个小问题的考证,以至于后来的学者可能认为今天的学问主要是“小学”,今天的学者只是“小学家”,但我们相信,随着简牍研究的深入,对学术基本认识的改变,必然会引起我们对学术理论的重构,简牍对考据与义理的双重作用,站在21世纪末尾,或许会看得更加清楚。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