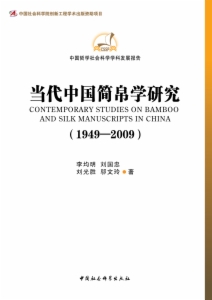一 文字之隶变、草化与符号
|
来 源
:
|
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0 \ 中编 简牍文书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3 | ||
|
摘 要
:
|
关于战国文字,见于各地出土楚简,涉及文献数量不甚多,其大部存属楚简典籍,所以关于战国简牍文书文字的情况可参见本书上编简牍典籍第二章第二节关于战国文字的论述。与简牍典籍文字之追求规正不尽相同,简牍文书更多的是追求快速与效率,正是这点使它在促进隶变与草化中起着更大的作用。必须注意的是隶草阶段的草书自由度较大,故异体甚多,常用字尤甚,如:而实际上,草化的过程就是不断简化的过程,以简牍书信常见的敬语“再拜”的“拜”字为例,可看到如下演变轨迹:此类字皆为简牍文书释读的难点,但它们的生命力脆弱,其中多数后世未见普及。 | ||||||
|
关键词
:
|
简牍 文书 隶书 典籍 篆书 新简 战国时期 提示符 偏旁 斜线 研究对象 |
||||||
在线阅读
一 文字之隶变、草化与符号
字体:大中小
(一)文字的隶变、草化与简化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简牍时代正值汉字发生激烈变化的时期。此时,汉字由战国时期的多国异形,至秦趋于统一,同时字体由篆而隶,平行发展的还有草体,汉末又产生楷体之萌芽,展现了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过程,此后汉字的结构没有太大的变化。李学勤先生认为:“战国、秦、汉文字粗略地可以划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是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第二是战国时期秦国以至秦代文字,第三是汉代的文字。”[※注]这是从文字体系划分的,如再加上三国至魏晋已呈楷化趋势的汉字,则构成了整个简牍时代文字发展的四大阶段。简牍文书文字即包含这四大部分。关于战国文字,见于各地出土楚简,涉及文献数量不甚多,其大部存属楚简典籍,所以关于战国简牍文书文字的情况可参见本书上编简牍典籍第二章第二节关于战国文字的论述。
简牍文书所见最具特色的文字现象是其隶变与草化。与简牍典籍文字之追求规正不尽相同,简牍文书更多的是追求快速与效率,正是这点使它在促进隶变与草化中起着更大的作用。隶书即相对于篆书而言,它是由篆书的草率写法演变而来,《说文·叙》:“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繁,初有隶书。”《汉书·艺文志》:“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徒隶也。”早期的隶书是篆书的辅助,行政之需要促使其被大量应用,而后才逐渐占据主体地位,其过程当然是渐进的,裘锡圭先生认为:“就各种日常使用的字体来说,一种新字体总是孕育于旧字体内部的,并且孕育期不会很短。如果新字体包含过多的新成分,那它是不大可能得到社会上一般人的承认的。隶书和小篆都形成于秦始皇时代,隶书应该是从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中逐渐发展出来的。”[※注]
隶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赵平安先生《隶变研究》一书对隶变的现象、性质、规律、意义等做了系统的论述,梁东汉先生为其作《序》云:“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古汉字演变成现代汉字的起点。有隶变,才有今天的汉字,可见研究隶变不但对一个文字学者来说非常重要的,对研究汉族文化的人也非常重要。只有了解隶变,才能真正认识汉字,特别是现代汉字;只有了解隶变的起因、经过、现象、规律和影响,才能比较清楚地认识汉族文化以及它在隶变阶段中取得的种种成就。”这是对隶变意义作用的阐述,又云:“前人研究隶变,寥寥无几,成就不大。赵平安先生全面研究隶变,把重点放在战国中期到汉武帝以前,目光锐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摒弃了用《说文》的小篆和汉碑隶或部分简书帛书的文字进行比较的陈旧方法,用丰富的出土材料诸如西周、秦、汉金文,秦至汉初的简帛文字,秦陶文,秦汉印文,秦汉石刻文字,秦货币文等来论证隶书产生在战国中期,还分析了隶变的外因、内因,阐述了隶变的现象和规律,多有发明,富于新意。无论在深度或广度方面都超过了前人,是这项研究的一次突破。”是对《隶变研究》一书的充分肯定。[※注]
尤值一提的是《隶变研究》一书中对隶变的必然性和可能性、隶变的现象和规律、隶变的性质做了充分的阐述,对研究简牍文字有借鉴意义。其中关于“隶变的性质”陈述了四点:第一,隶变不是质变,即隶变并没有改变汉字的根本性质,所以隶变不是质变。第二,隶变不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或转折点,即它没有改变汉字发展的方向,而与古今汉字发展的总的方向一致。第三,隶变不是突变,即隶变继承了古文字的形变方法,其过程连绵数百年,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不是突变而是渐变。第四,隶变是对汉字书写性能的改革,即在隶变的不同阶段,汉字的书写性能处在不断的改进之中。后一阶段的汉字比前一阶段的汉字更为简化,更便于书写,这说明隶变的过程是汉字书写性能不断改进的过程。这四点在简牍文书中都可以得到印证。但形变之后果常常是激烈的,也会使人产生变了之后已面目全非的感觉,故对于形变也应予足够的重视。其中通过隶变而造成的偏旁混同多少已有质变的意味。


以上五字下半偏旁隶变皆作“大”。
可见偏旁的混同确实是对汉字的一次重大的改革。
今见楚简以外的简牍文书大多以隶书写就,所以比较容易看懂。但西汉中后期之后的一些文书已见以草书写成的,而这些草书的写法与今天看到的草书不尽相同,释读起来就会感到有些困难,于是它也成为简牍文书基础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必须注意的是隶草阶段的草书自由度较大,故异体甚多,常用字尤甚,如:


而实际上,草化的过程就是不断简化的过程,以简牍书信常见的敬语“再拜”的“拜”字为例,可看到如下演变轨迹:

此类字皆为简牍文书释读的难点,但它们的生命力脆弱,其中多数后世未见普及,极少字竟然与今简体相似,如上引“为”字。
由于隶变与草化过程常采用矫枉过正的办法,西汉中后期也产生一些容易混淆的同形字与形近字。前者如“土”、“士”、“出”形皆作“土”;“夫”、“矢”、“先”、“失”形皆如“夫”等,所见较普遍。后者如以下所引:
此外,“功、虏、男、劾”;“王、玉、壬”;“莫、箕、筭”;“传、傅”;“愿、顷”;“吏、夬”;“文、交、丈、支”;“己、已、巳、乙”;“欲、数”;“来、求”;“高、亭、事、守”;“天、与”等字组,同组字之字形亦相似。
隶、草的简化过程大致沿着以下省略与替代方式进行:
省略偏旁或笔画。
“雷”字篆书从三个“田”旁,隶书只从一个“田”,省了两个。
“香”字篆书从“禾”、从“水”、从“曰”,隶书省去中间的“水”,作“香”。
此类字只要利用工具书即可辨认,但其中也有省略过甚而未见于后世者,如:
以点、画代替复杂部件。
以上三例所见是以横短画或竖短画替代文字的中部结构。
以上三例所见是以圆点替代原文字的“田”旁、以斜短划替代原文字的“口”旁。

总言之,简化是简牍文字发展的大趋势,但也有个别的逆反——繁化,如:
三国吴简所见官员签名中之繁化较多见,如:


上述签名方法屡见于走马楼三国吴简,所书字不仅增笔画,往往也将直线扭曲,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体现个性,当无文字学意义。
相对于简牍典籍来说,简牍文书所见假借字与通假字都要少一些,此或由行政运作的严肃性及时代较晚所决定。骈宇骞先生认为假借字与通假字是有区别的,主要采用孔德明的观点:“假借字与通假字虽然都属于文字的同音替代现象,但它们的外延是不相同的。假借是造字时历时的同音替代,而通假则是用字时共时的同音替代。这两个概念的外延是一种不兼容的并列关系。假借字与通假字这两个概念的外延相互排斥,各自独立,是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假借字是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即传统六书说中的假借;而通假字则是训诂学的研究对象,即通过识别通假字来训解疑难之处。”[※注]就此分别而言,则简牍文书所见通假字更多见,如:
“以”通“已”,见《新简》EPT5·111
“必”通“毕”,见《合校》262·16、273·12
“功”通“攻”,见《敦》3257
“汗”通“寒”,见《新简》ESC·24
“风”通“讽”,见《新简》EPT50·1A
“河”通“苛”,见《新简》EPF22·698
“责”通“积”,见《敦》3257
“环”通“还”,见《合校》557·4
此类字皆本有其字,即其本字亦屡见于简文中,今借用其他同音字表示,故为通假而非严格意义的假借,当然习惯上是把这两种都通称假借字。
合文即二字或多字连书,多见于早期战国简、秦简,西汉中期以后的简牍则少见。
(二)符号
本文所谓符号指文字以外的其他标识,犹今各式标点、编辑符号,对文字的表达功能起辅助与强化作用。骈宇骞先生将此类符号归入“题记”类。[※注]符号的形态多样,它除了有与简牍典籍相同的部分,还有许多是简牍典籍没有的。由于名册及账簿的大量使用,对其进行核算时(包括账账、账实核对,人员见存增减之核对等)便要用更多的符号,这些符号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为便于辨别,所引简文不加现代标点),列如下:
1.句读符

此例所见符号犹今逗号。但句读之符号不完整,可见当时句读符的使用还没有形成严密的体系,大多只在当时人认为容易误读处才使用。


句读符通常书于文字右下角,其形态小于字体。
2.重叠符



多字重文通常先连读所有带重叠符的文字,然后再重读,而不是单字重读。陈盘先生曾注意史籍中重文的这种用法,纠正了前人的错误,云:“《毛诗·魏风·硕鼠》:‘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俞樾曰:‘樾谨案《韩诗外传》两引此文,并作:适彼乐国。适彼乐国。爰得我直。当以《韩诗》为正。《诗》中叠句成文者甚多,如《中谷有蓷》篇迭嘅其叹矣、嘅其叹矣两句;《丘中有麻》篇迭彼留子嗟、留子嗟两句;《东方之日》篇迭在我室矣、在我室矣两句;《汾沮洳》篇迭美无度、美无两句,皆是也。毛与韩,本当不异。因古人遇迭句,皆省不书,止于字下加二画以识之,《宋书·礼乐志》所载《乐府词》皆如是,如《秋胡行》迭愿登泰华山、神人共遨游二句,则书作愿=登=泰=华=山=,神=人=共=遨=游=,是其例也,此诗亦当作适=彼=乐=土=,传写误作乐土乐土耳。下二章同此。’案俞说是。”[※注]
战国时期的数字廿、卅之类常加重叠符作廿=、卅=表示合文,到汉代就不加了。
3.界隔符
界隔符通常用以隔断文句,避免混淆。早期的界隔符是一条横线,后来改成斜线。以横线表示隔断尚见于战国简、秦简及汉初简牍。但用横线表示隔断有其弊端,故逐渐被斜线所取代,陆锡兴先生云:“斜划号是战国秦汉常见的横划号发展演变而来的,无论是符号形式还是用法都显示了这种密切的渊源关系。”又云“横划号是横的一笔,形状与数字‘一’相似,所以极易相混而误。如人们把仰天湖楚简的横划号释成数字‘一’就是例子。西汉中期以后,横划号已经基本废止,或者以斜划号的形式保留下来。”界隔符在简牍文书中的界隔作用如:
界隔文书责任人与起草人,如《新简》EPT50·16:“五月丙寅居延都尉德库守丞常乐兼行丞事谓甲渠塞候写移书到如大守府书律令/掾定卒史奉亲”,此例中斜线前所见人名为发件与收件直接当事人;斜线后人名则为起草人。但加斜线的做法不是绝对的,有时仅以空格不书字表示界隔。
界隔事件当事人与见证人,如《新简》EPT51·234:“出二月三月奉钱八千□百……建昭三年五月丁亥朔己丑尉史弘付不侵候长政/候君临”,此例所见界隔符前文字为凭证文件主体,而其后仅为监督见证人,故以界隔符分隔之。

起首语单书一行是当时书信的正规写法,但这样写占版面多,为了能在一牍之中书写更多文字,致信人便将起首语与正文在一行中连写,其间以界隔符隔开。
4.提示符

提示主题,如:
此例所见三简为一册书。首简为主体词,概括档内容,犹今内容提要,故文首加提示符提示;“移大将军莫府书曰……四时言犯者名状”为上级指示内容;“谨案部吏毋犯者敢言之”才是文件的核心,故亦以提示符“●”冠于文前,使之醒目易辨。
提示条款起首,如:
此例所见原为由十六简组成的《烽火品约》册书,今仅录其中三简,每简皆为品约之一条款,故文首以提示符“●”表示。
提示章节者多见于简牍典籍。
提示小结与合计,如:
“右爰书”指其右侧文书的内容为司法文书“爰书”,是对文书性质的小结,故其前加提示符“●”提示。
第十七队:
“凡迹积卅日”是对戍卒日迹天数的合计,故其前加提示符“●”提示。
提示特殊事项,如:
“●候君诣府”乃后书,为声明当政之甲沟候官候到都尉府去了,故候长代行其文书事,文首加“●”易引人注目。
5.钩校符
钩校符,校对符号。账账、账物及文字核对古时皆称“钩校”,简文多写作“拘校”,对簿籍而言通常指账账核对及账物盘点,《汉书·陈万年传》:“(陈汤)后竟征入为少府。少府多宝物,属官咸皆钩校,发其奸臧,没入辜榷财物。”此钩校即盘点行为。钩校之结果可以文字表示,亦可以符号表示,常用符号有乚、—、〇、∠、卩、︱等,皆为钩校后写上的,因此有别于正文,无论文字还是符号都是第二次写上的。钩校符的每一种形态在特定的簿籍中都有特定的含义,但它的寓意不像文字那么稳定,常常因事而异。钩校符多用于以下实践:
实物、人物是否见存,常见三种情形。
第一种是以文字表明钩校结果,如:
此例所见以文字表示钩校结果,意义明确。衣,衣着,或指衣物等被当事人穿在身上。
第二种是文字与符号并用表明钩校结果,如:
此例以文字“见”说明人物之见存,而以符号“∠”与文字“已”表示衣物之见存与否,其中或以“∠”表示衣物尚存于原处,而以“已”表示衣物已被处理(或领走)。
第三种单纯以符号表明钩校结果,如:
此例以符号“∠”表示人物之见存与否。
行为是否已施行之钩校,亦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亦以文字表明钩校结果,如:
毕,指钱已收或付毕。
第二种亦以文字与符号并用表明钩校结果,如:
此例所见钩校结果以文字与符号并用来表现比较复杂的过程,以符号“卩”先后表示领取与支付行为已完成,用文字“九月戊辰阁”来说明这笔钱又被存回藏阁中。
第三种亦单纯以符号表明钩校结果,如: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