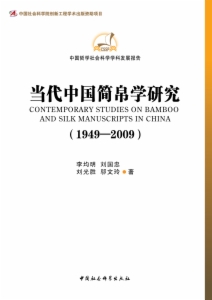二 楚帛书的发现与流传
|
来 源
:
|
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0 \ 下编 帛书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 | ||
|
摘 要
:
|
关于帛书在竹箧中的存放情况,商承祚后来也根据“土夫子”的回忆作了描述[※注]:帛书由于系盗掘出土,盗墓者为了隐瞒真情,故玄其说,曾有意隐瞒真实的出土时间和出土地点,在很长的时间内曾给帛书的出土时间、出土地点等问题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蔡季襄与柯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二人以10000美元将帛书成交,议定帛书由柯强在美国代为兜售,柯强留下押金1000元,余款待付,帛书及其他绝大部分帛书碎片及装帛书的竹箧等物都因此全部流入美国。至此,流入美国的所有帛书材料都被赛克勒美术馆所收藏。1996年,商承祚的后人将现存的那片残帛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这片残帛也是国内目前仅存的唯一一片子弹库帛书的残片。 | ||||||
|
关键词
:
|
帛书 墓葬 文物 晚周缯书考证 土夫子 古玩 古董 泥金 大都会博物馆 文物收藏家 帛画 |
||||||
在线阅读
二 楚帛书的发现与流传
字体:大中小
楚帛书是我国近代以来最早出土的真正可以称得上是简帛书籍的一批重要文献。楚帛书的发现距离现在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对于楚帛书本身在海内外曾流传着种种不同的说法,楚帛书实物则在长时间里收藏于美国的博物馆中,秘不示人,这些情况都给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外交流的深入,有关楚帛书的种种问题才逐渐得以澄清。
1942年9月[※注],一群“土夫子”(解放前长沙人对于盗墓者的称呼)来到当时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南郊一个名叫子弹库的地方(位于现在湖南省林业勘查设计院内),挖开了这里的一座古墓。这座墓葬是属于长沙特有的所谓“火洞子”墓,据说在盗掘时,曾有大量带硫黄气味的气体冒出,用火柴点燃,火焰曾高达数尺。盗墓者进入墓中后,从墓中取走了漆盘、铜剑、木剑鞘、木龙、陶鼎、陶壶、陶簋等物品,另外还取走了一个竹篾编成的书箧,关于这件竹箧(或称竹笈)的情况,蔡季襄在《晚周缯书考证》中曾附有插图,并作了详细的描述[※注]。陈梦家曾经将之概括为:
陈梦家这里所说的盛放在竹笈内的“缯书”及残缯断片,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楚帛书。
帛书出土时,是存放在竹箧里面[※注],这与后来出土的马王堆帛书的情况非常相似。关于帛书在竹箧中的存放情况,商承祚后来也根据“土夫子”的回忆作了描述[※注]:
帛书由于系盗掘出土,盗墓者为了隐瞒真情,故玄其说,曾有意隐瞒真实的出土时间和出土地点,在很长的时间内曾给帛书的出土时间、出土地点等问题造成了很大的混乱。30多年后,为了进一步了解该墓的情况,湖南省博物馆在当年参加盗墓的“土夫子”带领下,于1973年5月重新发掘了这座墓葬,从而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材料[※注],澄清了过去关于此墓葬的种种传闻。
这座墓葬为一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穴墓,墓中棺椁共三层,即椁、外棺、内棺。椁与外棺之间在头端和北边各有一个边箱,随葬器物大多放在边箱里。因曾被盗掘,有的被盗走,有的被遗弃在盗洞近椁盖板处,其余均被移动了位置。在墓中残存的文物中,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一幅“人物御龙帛画”,另外还发现了鼎、敦、壶等陶器,竹木漆器,玉璧,丝麻织物等文物。
由于该墓为一椁二棺的结构,根据《庄子·天下》及《荀子·礼论》记载“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两重”,而且此墓不含青铜礼器,规格较低,再结合帛画上的男子肖像及其装束来看,墓主人估计是士大夫一级的贵族。
至于该墓葬的年代,此墓出土的鼎、敦、壶等陶器是战国中期常见的器物组合,但陶敦器形扁圆,子母口又很明显,具有向后递变的一种形制。另外,据1942年参加盗掘的“土夫子”所言,头箱内曾出土了泥金版,而长沙楚墓出土泥金版仅见于战国晚期的墓葬中。根据这些情况,考古工作者认为此墓的年代约相当于战国中晚期之交,楚帛书的年代下限亦可因此而得以确定。
楚帛书被盗掘出土后,不久就为古董商人唐鉴泉所得。唐鉴泉原做上门裁缝,1927年正式开店营业,招牌为“唐茂盛”。并辟屋之半兼营古玩。从1931年起他专营古玩,人皆呼之为“唐裁缝”。唐鉴泉得到帛书后,曾写信给著名学者商承祚,以帛书求售。商先生接到信后,托友人沈筠苍前往了解情况。沈筠苍给商先生回信中说:“唐裁缝出视之时,是在白纸之外再用报纸将之松松卷起,大块的不多,小块的累累,将来拼复原样恐不可能。”正当商承祚与唐鉴泉反复议价之时,长沙地区的文物收藏家蔡季襄回到长沙,帛书遂为他所得。
蔡季襄得到帛书后,请有经验的裱工将帛书加以拼复和装裱,并命长男蔡修涣按原本临绘帛书图文,蔡季襄亲作考释,写成《晚周缯书考证》一书,该书写于1944年的抗战炮火之中,1945年春印行。此书出版后,楚帛书及其内容的情况才传播开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蔡季襄携带楚帛书来到上海,寻求将帛书出手。1946年,他在上海遇到了柯强(John Hadley Cox)。柯强是美国人。1935—1937年曾任教于长沙的雅礼中学,并在长沙大肆收购中国文物。抗战爆发后他返回美国,至抗战结束后又从美国来到上海。蔡季襄与柯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二人以10000美元将帛书成交,议定帛书由柯强在美国代为兜售,柯强留下押金1000元,余款待付,帛书及其他绝大部分帛书碎片及装帛书的竹箧等物都因此全部流入美国。
关于帛书的上述这些情况,据陈松长公布的蔡氏自述材料[※注],我们可以得到更为明确的了解。
蔡季襄在他的自述材料中说,1943年,他在从上海逃回长沙后,花了数千元的代价,在东站路唐茂盛古玩店买到战国时代出土的缯书一幅和其他陶铜器物。然后,长沙于1944年4月沦陷,蔡季襄携带楚帛书避难至安化。在安化城北租房住了一段时间,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于1944年8月份以前写成了《晚周缯书考证》,同年在蓝田付印,第一次对楚帛书的形制、文字和图像进行了研究和介绍。1945年抗战胜利,蔡氏从安化回到长沙,因生计清淡,即于1946年携带楚帛书前往上海,想通过上海的古董商金才记卖一个好价钱。但金才记出价太低,蔡氏转而找了另一位早已认识的古董商叶三。叶氏认为在当时上海帛书漆器等文物的销路不好,不愿接手。后经傅佩鹤从中牵线,与正在上海的柯强联系上了。见面后,柯强看到了蔡氏所写的《晚周缯书考证》一书,如获至宝,索要了一册带回他的寓所。后在柯强的寓所里,柯氏介绍说美国有红外线照相机,可以显示缯书上不清楚的文字,提高和增加缯书的价值。这样,在傅佩鹤的怂恿和柯强的一再要求下,蔡氏既为了脱手卖个好价钱,又为了多解决一些文字的释读问题,答应将帛书借给柯强研究照相,结果却被柯氏连哄带骗地将帛书转手带到了美国。关于帛书的被骗经过,据蔡氏自己所述,其详细情况是:
帛书流入美国之后的情况,长期以来国内的学者一直不太了解,经过李零的精心调查[※注],现在我们对于帛书在美国的流传情况已经比较清楚。
柯强把帛书带到美国后,曾到各大博物馆兜售。然而,尽管柯强把价钱一直压到了7500美元,并且反复强调说此物如何重要,声称如果无人购买,就得归还中国,或者到伦敦和斯德哥尔摩去卖,然而始终没有一家博物馆愿意购买[※注]。因此,到了1949年,柯强把比较完整的这件帛书寄存于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留供检验。至于其他帛书残片及存放帛书的竹箧,柯强则将之送到福格博物馆(the Fogg Art Museum)检验。因此,在1964年之前,帛书始终处于“无主”的状态。
1964年,柯强把存放在大都会博物馆的那件比较完整的楚帛书取出,售给纽约的古董商戴润斋(F.T.Tai),到了1966年,戴润斋又把从柯氏手中购得的文物转售给美国著名的文物收藏家赛克勒医生(Dr.Arthur M.Sackler),据说当时戴氏本想留下那张楚帛书,但因美国著名古物收藏家辛格医生(Dr. Paul Singer)偶然发现并大力推崇,力劝赛氏购进此物[※注],这样,楚帛书才归赛氏收藏,楚帛书亦从此声名大噪。
1966年之后,楚帛书一直是赛克勒的藏品,并于1987年赛克勒美术馆建成后从纽约移到该馆收藏。赛克勒本人现在已经去世,但他生前曾表示,总有一天他会把此物归还中国。
1992年,柯强将其他帛书残片连同书笈也一起售给了赛克勒美术馆。至此,流入美国的所有帛书材料都被赛克勒美术馆所收藏。现在这些帛书残片正在整理之中。
楚帛书被柯强带到美国去后,只有极少的一些帛书碎片还留在国内,据说这些帛书残片是蔡季襄送给徐桢立的,徐桢立又将它们转送给商承祚,它们总共由14片残帛组成,残帛中最大的一片最长处4.6厘米,最宽处2.7厘米,很可惜的是除了这一大片残帛之外,其余的13片残帛现在都已不知下落,只剩下在1964年由文物出版社史敬如为之拍摄的照片及商氏自己的摹本。1992年,《文物》和《文物天地》同时公布了这批珍贵材料[※注]。1996年,商承祚的后人将现存的那片残帛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这片残帛也是国内目前仅存的唯一一片子弹库帛书的残片。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