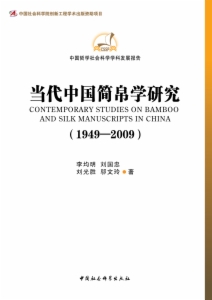一 楚帛书的内容与基础研究
|
来 源
:
|
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0 \ 下编 帛书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 | ||
|
摘 要
:
|
这一时期最有突破性的研究是, 1960年,李学勤第一次论定帛书边文的十二月名即《尔雅·释天》所述的十二月名[※注],另外, 1962年,陈梦家的《战国帛书考》一文以帛书与传世文献进行系统比较,指出帛书与月令类文献最为接近[※注],也是对楚帛书认识的一个进步。本书分《楚帛书研究概况》、《楚帛书的结构、内容与性质》、《释文考证》三部分,对楚帛书已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根据用红外线照片重新对楚帛书进行了探讨,颇多新获。大约在《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发表前后,大陆学者利用楚帛书的红外照片来研究楚帛书的情况骤然增多,从而在大陆掀起了楚帛书研究的新热潮。 | ||||||
|
关键词
:
|
帛书 释文 红外线 论著 大陆学者 神像 学者 研究成果 天象 Noel Barnard 大都会博物馆 |
||||||
在线阅读
一 楚帛书的内容与基础研究
字体:大中小
楚帛书写在一幅宽度略大于高度(47×38.7厘米)的方形丝织物上。整个幅面分为内外两层,内层是书写方向互相颠倒的两大段文字,一段13行,一段8行;外层绘有12个神像,上下左右,每边各3个,为一至十二月之神,其中除标有“易曰义”的神像是侧置外,其余头皆朝内,每个神像皆有题记,作左旋排列,依次转圈读;四方交角还有用青、赤、白、黑四色画成的树木;青木与白木的树冠相对,赤木与黑木的树冠上下相对,树根皆朝外。全书既无书题也无篇题,但外层12段文字,每段结尾都有一个分章的符号(用朱色的方块表示),后面另外书写含有神像名称的章题;内层两段文字也各有三个分章的符号(形式与边文相同)。织物原是折叠存放于竹箧内,留下两套折痕,一套年代较早,包括纵向的折断痕迹三道和横向的折断痕迹一道,痕迹较深,分帛书为8块;另一套年代较晚,包括纵向的折断痕迹五道和横向的折断痕迹一道,痕迹较浅,分帛书为12块(“纵”指窄面,“横”指宽面)。左右边缘还比较整齐,但上下边缘残破,装裱时有若干部位发生错位,幅面原为浅灰色,年久变为深褐色,使图像文字难以辨认。
李学勤曾建议称内层八行的那段文字为《四时》,十三行那段文字为《天象》,外层四周的文字为《月忌》[※注],许多学者都对这三部分文字作过考释,下面我们就按照李零在《中国方术考》中的释文及介绍讲述这三部分文字的内容(尽量用通行字)。
帛书《天象》的释文是:
以上三章主要是讲顺令和知岁的重要性。第一章是讲月行固有度数,如果过快过慢,不得其当,就会造成春、夏、秋、冬节令失常,日月星辰运行混乱,以至造成各种凶咎,如草木无常、天棓星降灾于下,山陵崩堕,泉水上涌,雷鸣电闪,下霜雨土,云霓傍日,兵祸四起。第二章是讲岁有德匿,天有赏罚。民人知岁,天则降福,民人不知岁,天则降祸。第三章是讲民人应对天地山川诸神虔诚恭敬,以时奉享。如果民人不知岁,祭祀不周,天帝便会降以上述凶咎,使农事不顺。
《四时》篇的文字是:

《月忌》篇的释文是:
以上十二章是讲帛书十二神所主的各月宜忌,顺序是按正月到十二月排列。每章开头“曰”字后的第一字是月名,后面是各月宜忌之事,最后三字是各章的章题,第一字是月名,第二、三字,或隐括该章内容(如女月得出师,题作“女此武”),或表示季节(如春季的最后一月作“秉司春”)
整篇帛书的三个部分文字是一个整体,《天象》侧重于“岁”,《四时》侧重于“时”(四时),《月忌》侧重于“月”,彼此呼应。
楚帛书因属盗掘出土,中间又经过多次转手,最后流落海外,从而使帛书的完整性及材料的及时公布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帛书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临写本和照片,这些材料的精确程度直接影响到了研究成果的正确性。根据帛书材料的公布情况,我们可以大致把研究过程分成三个阶段(其中大陆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因与国外联系较少,因此从国外获得材料的时间相对要晚一些):
(1)楚帛书研究的草创期(40—50年代中期)
楚帛书出土并归蔡季襄所有后,蔡季襄本人即令其子蔡修涣临摹,蔡季襄本人作了释文,并附有简短的考证,成《晚周缯书考证》一书,1945年春印行,这是最早发表和研究楚帛书的论著。书中对于帛书出土情况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并附有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的插图,是研究帛书出土情况的主要原始材料之一。蒋玄佁在《长沙(楚民族及其艺术)》一书重新加以临摹,当时许多学者研究楚帛书时,多据蔡氏本或蒋氏本而复制,并积极进行研究,这时期的主要研究论著有陈槃《先秦两汉帛书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4本,1953年)、饶宗颐《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考释》(《东方文化》1卷1期,1954年)、董作宾《论长沙出土之缯书》(《大陆杂志》10卷6期,1955年)、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下)(《文物》1959年第9期)等。这些文章涉及帛书的阅读顺序、图像理解、释文等重要内容,但是因蔡氏临摹本缺字和误摹较多,整个研究还难以深入。
(2)楚帛书研究的发展期(50年代中期—1965年)
柯强把楚帛书带到美国后,曾由弗利尔美术馆将帛书拍成全色照片,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兜售帛书,同时也提供了一些副本供某些学者研究,借助这一照片,许多研究者先后做有临写本和摹写本,如日本学者梅原末治《近时出现的文字资料》、饶宗颐《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澳大利亚学者巴纳(Noel Barnard)《楚帛书初探——新复原本》、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等文都做了临摹工作,并作了有益的研究,从而将帛书的研究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最有突破性的研究是,1960年,李学勤第一次论定帛书边文的十二月名即《尔雅·释天》所述的十二月名[※注],另外,1962年,陈梦家的《战国帛书考》一文以帛书与传世文献进行系统比较,指出帛书与月令类文献最为接近[※注],也是对楚帛书认识的一个进步。
(3)楚帛书研究的繁荣期(1966年—)
1966年,楚帛书归赛克勒所有。1966年1月,存放帛书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延请澳大利亚的巴纳博士(Dr.Noel Barnard)为指导,委托阿克托科学实验公司(Acto Scientific Photographic Laboratory Inc.)开始试验用航空摄影的红外线胶片摄制帛书照片,历时数月,终于找到合适的摄影方法,摄制出了黑白和彩色两种照片,字迹图画异常清晰,使许多肉眼看不见的字迹和图案显现出来,其效果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摹写本和照片,从而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967年8月21—25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及考古系在赛克勒基金会的出资赞助下,举办了题为“古代中国艺术及其在太平洋地区之影响”的学术座谈会,这是帛书新照片的第一次“亮相”,会上发表了巴纳、梅莱(Fean E.Mailey,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纺织研究室副主任)、饶宗颐、林巳奈夫等的论文。本次座谈会的论文由巴纳博士主编,于1972年结集出版,书名即为《古代中国艺术及其在太平洋地区之影响》。巴纳本人还撰有一系列的论著讨论帛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帛书红外线照片的公布,立即在海外掀起了楚帛书研究的热潮,港台学者严一萍、金祥恒、饶宗颐等都参加了讨论。其中严一萍、金祥恒两位考证帛书所述传说人物的头一位是“伏羲”,现在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因此大陆学者没有能够参加这一讨论热潮,也很少有人知道国外有新的帛书照片和各种摹本的发表。
楚帛书的红外线照片为国内学者所知大约是在70年代末,据曾宪通说,他最早见到楚帛书的红外线照片是70年代末在商承祚家。到了1980年,当时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的李零有感于国内对于海外楚帛书研究信息的隔绝,开始搜集国内外的有关论著,对楚帛书作重新研究,写成了《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1985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本书分《楚帛书研究概况》、《楚帛书的结构、内容与性质》、《释文考证》三部分,对楚帛书已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根据用红外线照片重新对楚帛书进行了探讨,颇多新获。本书是大陆学者第一部以红外线照片为依据研究楚帛书的论著,并荣获北京大学首届青年优秀成果二等奖。
大约在《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发表前后,大陆学者利用楚帛书的红外照片来研究楚帛书的情况骤然增多,从而在大陆掀起了楚帛书研究的新热潮。成果不断问世,如李学勤写了系列论文[※注],此外,曹锦炎、高明、何琳仪、曾宪通、朱德熙等也参加了讨论。
到目前为止,楚帛书的出土和研究工作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已发表的有关楚帛书的论著已超过了150多种。笔者见到的最近一篇研究成果是李学勤的《释楚帛书中的女娲》(收入《文物中的古文明》一书,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尽管人们曾多次试图对楚帛书研究作最后总结,但是,正如李零所说:“帛书研究却远没有‘山穷水尽’,反而显得好像初被开发,还有许多‘不毛之地’。”[※注]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