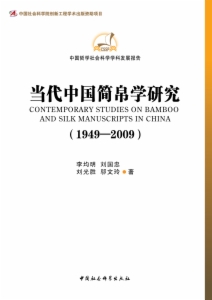二 马王堆帛书的内容与基础研究
|
来 源
:
|
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0 \ 下编 帛书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 | ||
|
摘 要
:
|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马王堆三号墓东边箱的57号长方形漆奁中出土了大批帛书。马王堆帛书很多都没有篇名,不少帛书是由帛书整理小组根据其内容而加以定名的,由于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工作至今都没有全部完成,很多帛书尚未正式发表。帛书《经法》、《经》、《称》、《道原》(或合称为《〈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黄帝四经》、《黄帝书》、《黄老帛书》)帛书《经法》和《经》、《称》、《道原》一起抄录在帛书《老子》乙种本之前,全文用较规范的汉隶抄写,行与行之间有“乌丝栏”界格。 | ||||||
|
关键词
:
|
帛书 老子 小组 马王堆帛书 阴阳五行 缪和 经脉 阴阳十一脉灸经 周易 五行 足臂十一脉灸经 |
||||||
在线阅读
二 马王堆帛书的内容与基础研究
字体:大中小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马王堆三号墓东边箱的57号长方形漆奁中出土了大批帛书。这些帛书由于长期卷压折叠,已经残破断损。因此这些帛书出土后,立即由湖南省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进行了精心的修复工作,妥善保存起来。随后,在1974年3月,国家文物局正式成立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对帛书进行精心的复原、整理、释文和注释工作。
这些帛书质地是生丝织成的细绢。帛的高度大致有两种:一种48厘米左右,一种24厘米左右,即分别用整幅和半幅的帛横放直写。画表和图的帛,幅面大小看需要而定。出土时,整幅的帛书折叠成长方形,半幅的卷在二三厘米宽的竹、木条上,一同放在漆奁中。
帛书一般都是横摊着从右端开始直行写下去的,有的先用墨或朱砂画好上下栏,再用朱砂画出7—8毫米宽的直行格(即后来所说的“乌丝栏”或“朱丝栏”),这种行格很像后世的信笺,实际上是模仿了竹、木简的样子;有的则不画行格。整幅的帛书每行70字左右,半幅的每行写30余字。除了个别的字用朱砂书写之外,都是用墨书写。墨的原料是用松枝等烧成的烟炱。
帛书的长短也很不一致。短的,一段帛上只写一种书或画一幅图。长的就不同了,写完一种书或画了一幅图后,也不剪断,就另起一行接着写下一种书,或者画另外的图。所以一幅长帛上常常有好几种帛书。
帛书的体例也不一致。有的帛书在第一行顶上涂一黑色小方块作标记,表示书从这里开始。有的帛书则没有行首的标记。有些书是通篇连抄,不分章节;有的则用墨点记号分章;有的则提行另起章节。大部分帛书都没有书名,有标题的一般都写在文章的末尾,并记明字数。这种篇章题记的表示方法,在古籍中是常见的。
总起来看,帛书的样式与简册非常相似。根据文献记载,汉代书籍所用的简大致有长、短两种。长简为汉尺二尺四寸,用来书写经典;短简为一尺二寸或一尺,也有八寸的,用来抄写诸子、传记等[※注]。帛书也有整幅和半幅两种尺度,与简册大体相同,至于帛书尺度与内容的关系,则似乎没有东汉那么严格。
帛书的字体大致有三种:一是篆书;二是隶书;三是处于篆隶之间的草篆,又称秦隶。书写的字迹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有的工整秀丽,有的洒脱,显得潦草,显然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这些迹象表明,帛书抄写的年代正处于汉字急剧变化演变的时期。我们知道,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各国文字差别很大。秦统一全国后,进行了“书同文字”的工作,把秦的篆书向全国推广。秦代除了篆书作为全国的标准字体外,还以民间流行的隶书作为日用文字。隶书也是从周秦篆书来,字体已经接近楷书。由于隶书结构简省,书写方便,所以在汉初隶书已经逐渐取代篆书。从帛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秦代到汉初汉字的这种演变趋势,从而给我们留下了秦汉之间汉字的演变轨迹。另外,有一些帛书从字体上看显然出自同一人之手,学者们根据这些帛书的抄写情况,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了职业抄手,比如用隶书抄写的一些帛书,其抄写时间应该在文帝初年,都是出自一位职业抄手之手[※注]。
马王堆帛书的种类十分丰富。如果我们按照《汉书·艺文志》“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的这种分类方法对马王堆帛书试作分类的话,可以发现它们涵盖了除诗赋类之外其他的五类图书。
马王堆帛书很多都没有篇名,不少帛书是由帛书整理小组根据其内容而加以定名的,由于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工作至今都没有全部完成,很多帛书尚未正式发表。目前对于马王堆帛书数量的统计有不同的说法。其中陈松长曾以单篇作为计数单位,将马王堆帛书分成以下6大类44种[※注]:
一、六艺类
1.《周易·六十四卦》
2.《易传·系辞》
3.《易传·三子问》
4.《易传·易之义》
5.《易传·要》
6.《易传·缪和》
7.《易传·昭力》
8.《春秋事语》
9.《战国纵横家书》
10.《丧服图》
二、诸子类
1.《老子》甲本
2.《老子》乙本
3.《五行》篇(或称《德行》篇)
4.《九主》篇(或称《伊尹·九主》)
5.《明君》篇
6.《德圣》篇(或称《四行》篇)
7.《经法》
8.《经》(或称《十六经》、《十大经》)
9.《称》
10.《道原》
三、术数类
1.《五星占》
2.《天文气象杂占》
3.《阴阳五行》甲篇
4.《阴阳五行》乙篇
5.《出行占》
6.《木人占》
7.《相马经》
8.《“太一将行”图》(或称《社神图》、《神祇图》、《避兵图》)
四、兵书类
1.《刑德》甲篇
2.《刑德》乙篇
3.《刑德》丙篇
五、方技类
1.《足臂十一脉灸经》
2.《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
3.《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
4.《脉法》
5.《阴阳脉死候》
6.《五十二病方》
7.《却谷食气》
8.《导引图》
9.《养生方》
10.《杂疗方》
11.《胎产书》
六、其他
1.《长沙国南部地形图》
2.《驻军图》
下面我们根据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的整理报告和有关学者的论述,对于这44篇帛书的情况作一个介绍。
一、六艺类帛书
1.《周易·六十四卦》
帛书《周易》原无篇题,或称之为帛书《六十四卦》。它抄写在一幅宽48厘米,长约85厘米的丝帛上。横幅界画朱栏,字以墨书。每行字数不等,满行为64—81字,总共93行,合4900余字。从字体上看,抄写年代应在文帝初年。
帛书《周易》的六十四卦每卦均有卦图,除个别字有残损外,六十四卦完备无缺。与通行本相比,帛书本《周易》的最大差异之处是卦序不同。通行本分上、下经,上经三十卦,始于乾,终于离;下经三十四卦,始于咸,终于未济。帛书本则不分上、下经,始于键(乾),终于益,其排列顺序亦有规律可寻,即将八卦按照阴阳关系,排成键(乾)川(坤)、根(艮)夺(兑)、赣(坎)罗(离)、辰(震)算(巽),然后以键、根、赣、辰、川、夺、罗、算等为上卦,以上述阴阳组合的键、川、根、夺、赣、罗、辰、算为下卦,再以上卦的每一卦分别与下卦的八卦组合而形成六十四卦。这种排列方法与汉石经、通行本完全不同,因此,帛书本《周易》显然是《周易》别一系统的传本。

2.帛书《系辞》
帛书《系辞》和另几篇易传古佚书同抄在一幅48厘米宽的整幅帛上,开篇处有长条形墨丁,帛中有朱丝栏界格,文字是规范的汉隶,共47行,3000余字[※注]。
与通行本相校,帛书《系辞》的主要不同是:不分上下篇;缺通行本《系辞上》的第八章和《系辞下》的第五、六、八章和第七章的一部分。
帛书《系辞》与通行本的不同,还表现在许多文字的不同上,两相校勘,帛书本多有优胜处。例如通行本《系辞》中有:“乾坤,其《易》之缊邪?”其中的“缊”字很费解。韩康伯注:“缊,渊奥也。”虞翻注:“缊,藏也。”孔颖达疏曰:“乾坤是易道之所蕴积之根源也,是与易为川府奥藏。”这一解释总觉得比较费解。对比帛书本,我们不禁豁然明白,原来此处是作“键(乾)川(坤),其《易》之经与(欤)?”“经”意为纲领,此句是说“乾坤”二卦是易的纲领,所以下文说:“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矣”。两相比较,帛书的“易之经”显较今本“易之缊”为胜。但是也有些文字帛书本不如今本。如今本《系辞》言:“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察终,故知死生之说。”在帛书本中,“察”、“原”两字都作“观”,连用三个“观”字,便显然不及今本[※注]。
3.帛书《二三子问》(或作《二三子》)
帛书《二三子问》与帛书《六十四卦》同抄在一幅幅宽48厘米的帛上,紧接在帛书《六十四卦》之后。帛上画有朱丝栏界格,字体是比较规范的汉隶。首有墨丁,文中以圆点分为三十二节。全篇共36行,2500余字。原件已断作4块高24厘米,宽约10厘米的长方形残片,由于这件帛书的首句为“二三子问曰”,张政烺据古书命名通例,将之称为《二三子问》,已故的于豪亮则将其分为2篇来分析(张、于二文均见《文物》1984年第3期)。
《二三子问》的原文尽管多有残缺,但其文字大致可读。文中以圆点分为三十二节,第一节文字较长,论述“龙之德”,第二至第四节、第九至第十七节论述乾、坤两卦的爻辞,第五至第八节依次论述了蹇、鼎、晋三卦的卦爻辞,第十八至第三十二节末尾依次论述了屯、同人、大有、谦、豫、中孚、小过、恒、解、艮、丰、未济十二卦的卦爻辞。于豪亮认为自“二三子问曰”至“夕沂若历,无咎”止为一篇,其后至“小人之贞也”又另为一篇,事实上,尽管“夕沂若历,无咎”这一句后还剩三字的空位,书写者就另起一行了,但这并不能说明这是两篇帛书。相反,从其文字内容本身来看,这2500余字确实是首尾相贯的一篇《易传》著作,不好将之分开。另外,如果以帛书多以篇首墨丁作为分篇标志的这个特征来看,将之分为两篇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注]。因此,后来的学者多依从张政烺的意见,将其视为一篇帛书。
《二三子问》解《易》有一明显的特色,就是只谈德义,罕言卦象、爻位和筮数,尤其是大部分解说都冠以“孔子曰”,更使之具有很浓厚的儒家学说色彩。例如:“《易》曰:‘杭(亢)龙有悔。’孔子曰:此言为上而骄下,骄下而不殆者,未之有也。圣人之立正(政)也,若遁(循)木,俞(愈)高俞(愈)畏下,故曰‘杭(亢)龙有悔’。”又如“《易》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孔子曰:‘此言大人之宝德而施教民也,夫文之孝,采物暴存者,其唯龙乎?德义广大,法物备具者,〔其唯〕圣人乎?’‘龙战于野’者,言大人之广德而下接于民也;‘其血玄黄’者,见文也。圣人出法教以道(导)民,亦犹龙之文也,可谓‘玄黄’矣,故曰‘龙’。见龙而称莫大焉。”很显然,这是一篇儒家《易传》的古佚书之一。
帛书《二三子问》虽无传世之本可供参照,但其与许多卦爻辞的文字不同,特别有助于今人对通行本《周易》卦爻辞的理解和重新认识。例如通行本中未济的卦辞作:“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其中的“小狐汔济”就很费解。帛书《二三子问》正好有对此段卦辞进行了解释。帛书作:“小狐涉川,几济,濡其尾,无逌利。”两相对勘,原来通行本在传抄过程中漏掉了“涉川”两字,而将“几”字又讹成了“汔”,这样,本来是很明白的一句话,就变得很难理解了。由此可见帛书《二三子问》对易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注]。
4.帛书《易之义》(或作《衷》)
帛书《易之义》篇紧接在帛书《系辞》之后,抄写在一幅48厘米宽的帛上,开篇的顶端有墨丁为记,帛书有朱丝栏,文字形体和《系辞》一样,是规范的汉隶。
这篇帛书尽管断为两截,但开头四五行尚清楚,尔后便有几行残缺,到十四五行以后便趋于完整,至最后一行又有残缺。据估计全篇共约有45行,约3000字。
这篇佚书的定名较为复杂。这篇古佚书由于和《系辞》抄在一起,加之其中又包含有今本《系辞》下的第六章、第七章的一部分、第八章以及今本《说卦》的前三章,因此,先前学者往往将其视为帛书《系辞》的下篇。后来韩仲民提出不同意见,从墨丁作为分篇的标志出发,认为它显系另一篇佚书,张立文则据其首句“子曰易之义”将其定为《易之义》,也有学者称之为“子曰”篇[※注]。廖名春曾怀疑该佚书也可能和其他几篇易传一样,也有它的原名,只是因为最后一行残缺而失落了。后来廖名春又从帛书照片中找出一残片,认为此残片正好可接于此件帛书的最后,其中的“衷”字则是这件帛书的篇名,因此径以《衷》命名此篇。
《易之义》文中以圆点隔开为若干章节,但由于帛书本身残缺较多,其确切章节无法确定。据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部分:(1)第一至第二行说阴阳和谐相济,乃是《易》之要义,即所谓“易之义,唯阴与阳,六画而成章”,这大概也是此篇所着重阐述的主要内容。(2)从第三行至第十行是对《周易》的许多卦义进行陈说。(3)从第十三行至第十五行左右,为今本《说卦》的前三章,内容较为完整,但“天地定立(位)”四句,则根据帛书卦序对《说卦》文进行了改造。(4)第十六行至第二十一行左右,阐述乾、坤之“参说”。自第二十二行至第三十四行,分别阐述乾坤之“羊(详)说”。从第三十四行至第四十五行,为今本《系辞下》的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依朱熹《周易本义》所分)。

5.帛书《要》
帛书《要》篇和帛书《系辞》、《易之义》同写在一幅宽48厘米的帛上,它紧接着《易之义》篇。本篇篇首有残存的墨丁,篇尾有标题:“《要》,千六百四十八”,可知此篇原本就以《要》名篇。全文用比较规范的汉隶书写,行与行之间有朱丝栏界格。
帛书《要》篇的开头几行已残,根据其所记的实际字数和每行所写的大致字数推断,篇首残了6行左右。而全文大约是24行,共1648字。《要》篇文中亦有圆点作为章节区分的标志,由于篇首部分残缺过多,故具体章节数目无法统计,但自第九行起,分章情况就鲜明了。从其内容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部分:(1)从第九行(包括第八行的一部分)至第十二行“此之胃也”可能属一章,其内容主要是今本《系辞》下篇第五章的后半部分(依朱熹《周易本义》所分)。(2)从第十二行“夫子老而好《易》”至第十八行“祝巫卜筮其后乎”,主要是记载孔子晚年与子赣(贡)论《易》之事,着重叙述了孔子晚年好《易》的原因。(3)从第十八行最后两字至第二十四行末为一章,主要记叙孔子对其门人弟子讲述损益两卦的内容和哲理。
帛书《要》篇的学术价值,也许当以后二部分最为重要,因为这是对孔子晚年与《易》的关系的最好说明。孔子与《周易》及《易传》的关系问题,过去一直存在着争议。而在《要》篇中说:“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这与《史记·孔子世家》、《田敬仲完世家》、《论语·述而》的记载可以印证,而孔子对损、益二卦的赞赏也与《淮南子·人间》、《说苑·敬慎》、《孔子家语·六本》的记载相互支持。可见至少在汉代初年,人们是知道孔子晚年不仅好《易》,而且传《易》的。这对一直存在争议的关于孔子与《易传》的关系的研究,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和证明。
6.帛书《缪和》和帛书《昭力》
帛书《缪和》紧接着帛书《要》篇,另起一行,抄在同一幅48厘米宽的帛上,篇首有墨丁,首句为“缪和问于先生曰”,以“观国之光,明达矣”作结,篇末空一字格,有标题《缪和》二字,但无字数统计。帛书间有残缺,现存约70行,共5000余字,帛书格式和字体与上述诸篇相同。
帛书《昭力》紧接着帛书《缪和》篇,也另起一行抄写。该篇帛书篇首没有墨丁,首句为“昭力问曰”,以“良月几望,处女之义也”作结,最后空一字格,有标题“昭力”二字,故一般仍将其视为单独的一篇来处理。这篇帛书篇幅较短,共14行,有930余字。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仅900余字的帛书在篇题“昭力”之后又空一字格,记字数“六千”。于豪亮曾经指出,这个字数应是《缪和》、《昭力》两篇字数的总和,甚确。
帛书《缪和》、《昭力》虽然各自名篇,但从内容来说,它们实如一体,犹如一篇文章的上下两篇。《昭力》篇首没有墨丁标志,而最后所记字数“六千”,实又包括了《缪和》在内,可能与此有关。
与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一样,《缪和》、《昭力》大体上也是以问答的形式解《易》。两篇共约二十七段,段与段之间用黑色的小圆点断开。其中《缪和》约二十四段,第一至第五段是缪和向先生问《易》,讨论了涣卦九二爻辞、困卦卦辞、□卦、谦卦九三爻辞、丰卦九四爻辞之义。第六至第八段是吕昌向先生问《易》,讨论了屯卦九五爻辞、涣卦六四爻辞、蒙卦卦辞之义。第九段是吴孟向先生问《易》,讨论了中孚卦九二爻辞之义。第十段是庄但向先生问《易》,讨论了谦卦卦辞义,第十一段是张身向先生问《易》,也是讨论谦卦的卦辞之义。第十二段是李羊向先生问《易》,讨论了归妹卦上六爻辞之义。第十二段至第二十四段解《易》的形式为之一变。它们不再是问答体,而是直接以“子曰”解《易》和以历史故事证《易》。其中第十二至第十八段每段皆以“子曰”开头,依次阐发了复卦六二爻辞、讼卦六三爻辞、恒卦初六爻辞、恒卦九三爻辞、恒卦九五爻辞、坤卦六二爻辞之义。第十九段至第二十四段则先叙述一个历史故事,再引《易》为证,这种形式,与《韩诗外传》解《诗》如出一辙。这种大量用历史故事来解说《周易》卦爻辞之旨的方法,可以说开了以史证《易》的先河。
帛书《昭力》共三段,都是以昭力问《易》,先生作答的形式出现的。第一段是阐发师卦六四爻辞、大畜卦九三爻辞及六五爻辞的“君卿大夫之义”,第二段是阐发师卦九二爻辞、比卦九五爻辞、泰卦上六爻辞的“国君之义”,第三段是阐述“四勿之义”。与《缪和》等比较,《昭力》解《易》综合性强,《缪和》与《二三子问》等,一般是就具体的一卦一爻之义进行讨论,而《昭力》则揉合数卦数爻之辞,阐发它们的共同意义。
《缪和》解《易》,不言数,只有一处分析了明夷卦的上下卦之象,其余都是直接阐发卦爻辞的德义。《昭力》则全是谈卦爻辞的政治思想。这种倾向,与帛书《二三子问》等篇也是比较一致的。
帛书《缪和》、《昭力》所载《周易》经文,与通行本也有一些不同,可以用之校正通行本的一些错误。如蒙卦卦辞今本作:“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而《缪和》第八段称引和解释此条卦辞,“告”字皆作“吉”,与帛书《六十四卦》、汉石经本相同。看来今本之“告”当属“吉”字形近而讹[※注]。
帛书《缪和》还有一个很有价值的方面,就是第十九至第二十四段记载了六个历史故事,这些历史故事虽然大多见于《吕氏春秋》、《新书》、《说苑》、《新序》、《韩诗外传》、《大戴礼记》等书,但仍提供了许多新的信息。如第十九段记汤网开三面,德及禽兽,感化的诸侯有“四十余国”,而《吕氏春秋·孟冬纪·异实》和《新序·杂事》都说是“四十国”,《新书·论诚》则只说“士民闻之”“于是下亲其上”,比较而言,《缪和》所载最详。第二十段记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式(轼)事,《新序·杂事》、《史记·魏世家》、《艺文类聚》所引《庄子》都有类似记载。但《缪和》点出了“其仆李义”之名,而其他文献都只云“其仆”,可见《缪和》的作者更清楚、更接近于史事,不然的话,它就不会保留下这些细节的真实。又如第二十一段记吴舟师大败楚人,“袭其郢,居其君室,徙其祭器”,与《左传》、《史记》所述相同,但“太子辰归(馈)冰八管”,吴王夫差置之江中,与士同饮,因而使士气大振之事,却为史籍所无。总起来看,这些历史故事都为历史记述提供了新的材料,值得加以重视。
7.帛书《春秋事语》
帛书《春秋事语》抄写在宽约24厘米、长约74厘米的半幅帛上,帛书的前部残缺较严重,不知道到底缺几行。后面部分比较完整,尚有余帛没有写字。这件帛书原来卷在一块约3厘米宽的木片上,约十二三周,由于帛质腐朽,加之棺液的浸泡,出土时已分裂成大小不等的200多个碎片。经过整理,全篇现存16章,每章都提行另起,多用墨点作为分章符号,但没有篇题,也没有书名。全篇共约97行,上有直界乌丝栏,字体由篆变隶,不避汉高祖刘邦的讳,抄写年代大致在秦末汉初(前200年左右)。
帛书《春秋事语》各章中所记史实最早的是鲁隐公被杀,最晚的是韩、赵、魏三家灭智伯,其记事年代略与《左传》相近。每章所记之事,彼此不相连贯,既不分国别,也不分年代先后,每章所记,凡记事都比较简略,但记言论则比较多,可见此书重点不在记事而在记言,是先秦书籍中一种比较常见的“语”式体裁,因此,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将其定名为《春秋事语》。
8.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或作《战国策》)
《战国纵横家书》是用半幅帛抄写而成,帛长1.92米,宽24厘米,每行三四十字不等,首尾基本完整,后面尚有余帛没有写字。全篇帛书共325行,11000余字。本篇帛书的字体在篆隶之间,避汉高祖刘邦之讳,当是公元前195年前后的写本。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共分为27章,每章用小圆点隔开,不提行。27章中见于司马迁《史记》和刘向所编《战国策》的,只有11章,此外的16章都不见于现存的传世古籍。这27章根据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面14章,都和苏秦有关,只有第五章见于《史记》和《战国策》;第四章的一部分,《战国策》有而脱误很多。其中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苏秦给燕昭王的信和游说辞;从第八到第十四章则是苏秦等人给齐湣王的信和游说辞。第二部分是第十五章至第十九章,这几章在每章末尾都有字数统计,并在第十九章末尾有这几章字数的总计,所以显然是另一个来源,其内容主要是战国游说故事的记录,除第17章外,都见于《战国策》或《史记》。第三部分是最后8章,根据其中有关苏氏游说的资料不和首十四章有关苏秦的资料编在一起来判断,这应该是另一种辑录战国游说故事和纵横家游说言论的本子。最后3章也都不见于传世古籍中。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战国后期的历史资料,弥足珍贵。尤其是第一部分十四章有关苏秦活动的原始新材料,极大地充实了战国史研究的内容。司马迁等人对于苏秦活动的年代和有关的史实的叙述有不少错乱之处,如《史记》中称苏秦与张仪是同学,根据帛书则可以知道:公元前312年,当苏秦在楚游说陈轸门下的时候,还是初露头角的年轻人,而此时的张仪已是“烈士暮年”的长者了,可见《史记》乃至《战国策》中的记载,至少把苏秦的卒年提前了30年。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亦为有关的历史文献的整理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例如《战国策·韩策三》有“韩人攻宋”章,经与帛书对勘,乃知“韩”字是“齐”字之误。而《战国策·齐策四》中的“苏秦自燕之齐”章在《史记》中就误将“苏秦”写作了“苏代”。更典型的一个例证是:今本《战国策·赵策四》的《赵太后新用事》章中,有“左师触詟愿见太后”一语,《史记》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两种本子孰是孰非,颇难公断。今帛书所记与《史记》相同,这就证明了《史记》本的正确,因而也就澄清了这个久疑未释的历史之谜。
9.《丧服图》(或称《丧制图》)
《丧服图》绘于一幅长26.2厘米、宽48厘米的整幅帛上,全图由1个朱色的伞盖和19个正方形色块(加上残缺部分应是24块)组成,从上到下有部分方块中间有墨线相连,其中左侧一线有五块朱色,其他均为黑色。这种图形或许是轪侯家族的表示亲疏关系的族系示意图,朱色也许意味着嫡传的关系。该图中有6行56个字的丧服制度记载,主要记叙汉初人服丧的有关规定,其中提到了三年之丧、期年、九月、七月等服丧期,但没有言及三月或更短之丧期者,这与汉文帝遗诏短丧的规定似乎不太吻合,与传统的丧服记载亦有区别,因此,这或许是轪侯家族自己所奉行的丧服制度的一种图文式的记载[※注]。
二、诸子类帛书
1.帛书《老子》甲、乙本

帛书《老子》甲、乙本各有特点,诸如经文句型、文字等均有区别,如甲本“此之谓玄德”,乙本则作“是谓玄德”,甲本“故曰为道者非以明民也”,乙本作“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也”,甲本“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乙本作“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诸如此类差别不下二百余处,贯穿全书始末,足以说明帛书《老子》甲、乙本来源不同,代表汉初两种不同古本。
如果把帛书《老子》甲乙本与传世的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和傅奕校定本相比较,它们与传世本《老子》也有较大的差别。
(1)传世诸本《老子》都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而帛书本则正好相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2)传世诸本《老子》分为81章,而帛书本则不分章节(甲本部分加一些圆点,有些似乎是分章符号,但无法确定)。但从其行文来看,今本各章的次序有些应当加以调整。如今本第四十章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一章:“上士闻道而勤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而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善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三章顺序,看上去似乎没有问题,但用帛书本一校,就发现它的错误了。帛书本是不分章的,甲本同于今本第四十一章的那段文字因残泐太甚,仅存二字;乙本比较完整,但列在第四十章那段文字之前。可以肯定,乙本的这一顺序比今本更为合理。因为第四十章是讲宇宙本体的“道”,第四十二章亦同,两段文字紧密相连,当是《老子》书的原样,今本把第四十一章那段文字插入这两段中间,则文义隔断,可见是错误的。

不过,帛书《老子》甲、乙两本在当时只不过是一般的学习读本,皆非善本,书中不仅有衍文、脱字、误字、误句,而且使用假借字亦不够慎重,因而在许多方面也并不如今本。
2.帛书《五行》(或称《德行》)
帛书《五行》紧接着《老子》甲本抄写,全篇共180多行,约5400字,全篇原无篇名,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根据其内容而名之为《五行》,后来魏启鹏根据周秦古书名篇的通例,并考其全文主旨,径取首句的“德行”二字名篇。但是湖北省荆门郭店也出土了该书的竹简本,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全书以“五行”两字开头,故仍应以“五行”名篇为是。
帛书《五行》篇由两部分组成,自第1行至第44行为第一部分,主要提出了若干儒学命题和基本原理。自第45行至篇末为第二部分,其内容是分别对第一部分所提出的命题和原理进行论述和解说。按照古文的惯例,第一部分是“经”,第二部分则是“说”,或者说是“传”。
帛书《五行》篇本身没有标题,其内容主要是围绕“聪”、“圣”、“义”、“明”“智”、“仁”、“礼”、“乐”等道德规范进行论述并解释。据研究所知,这是失传已久的关于“思孟五行”理论的重要的古文献,它的发现,证实了当时思孟学派的存在,使人们对思孟学派的一些基本观点有了清楚的认识。
在第一部分所提出的诸多儒学命题和道德规范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的“五行”说,它为解开二千多年来学术界不得其解的“思孟五行”之谜找到了一把钥匙。篇中提出了“仁”、“义”、“礼”“智”、“圣”的“五行”说,其中不少地方袭用《孟子》的话,应是思孟学派的著作。我们知道,《荀子·非十二子》说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过去一直未得确解,帛书《五行》篇的发现,有助于我们弄清思孟学派“五行”说的真相,进一步深入研究先秦的儒家思想。
3.帛书《九主》
帛书《九主》篇是紧接在《老子》甲本、帛书《五行》之后所抄写的第二种古佚书,全篇共52行,约1500字。该书原无篇名,马王堆汉墓帛书小组根据其内容将之命名为《九主》。也有学者称其为《伊尹·九主》。
《九主》篇的主要内容是记载伊尹论九主的言论。《汉书·艺文志》道家有《伊尹》31篇,小说家有《伊尹说》27篇,但这些书很早就亡佚了,南朝刘宋时裴骃作《史记集解》,只引《别录》,不能以原文纠正误字。到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对“九主”也只是望文生义,说“九主者,三皇五帝及禹也;或曰:九主谓九皇也”,甚至将“法君”理解为“用法严急之君”。可见,唐人已对“九主”的本义茫然无知。帛书的出土,使我们重新认识到,所谓“九主”,原来是“法君、专授之君、劳君、半君、寄主、破邦之主二、灭社之主二”。这样,也就足以使我们重新订正《史记集解》所引《别录》的错误。例如《别录》将“专授之君”就误拆成了“专君”和“授君”,其实“专授”的原意在《管子·明法解》中有着明确的解释:“授”就是付与,所谓“专以其威势予人”、“专以其法制予人”就是“专授”,所谓“专授之君”,就如《史记·范雎列传》中所说:“且夫三代所以亡国者,君专授政,纵酒驰骋弋猎,不听政事,其所授者妒贤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为主计,而主不觉悟,故失其国。”简言之,也就是专授政事于人而失国之君,根本就不能断裂成“专君”和“授君”,而“专君”、“授君”也实在不好理解,现在帛书的出土,终于解开了这个死结。
4.帛书《明君》
帛书《明君》是紧接在帛书《老子》甲本、《五行》、《九主》之后所抄写的第三篇古佚书,全文48行,1500余字。本篇原无篇题,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根据其内容,将之命名为《明君》。
本篇帛书似乎是一篇给国君的奏书,作者以“先王”的情况为例,阐述贤明君主的几大要务,用帛书的原话就是:

5.帛书《德圣》(或称《四行》)
帛书《德圣》篇是抄在帛书《老子》甲本、《五行》、《九主》、《明君》之后的另一篇古佚书。本篇后面部分文字残缺较为严重,不能属读,也不知原篇是否有自己的篇名。全文现存13行,约400字。《德圣》一名是帛书整理小组所加。
帛书整理小组认为,这篇帛书也讲到“五行”,与抄在前面的第一篇古佚书《五行》有关,但又有一些道家的语汇。魏启鹏曾依据先秦古籍篇章署名的通例,求证于本篇的内容,改称其为《四行》篇。
6.帛书《经法》、《经》、《称》、《道原》(或合称为《〈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黄帝四经》、《黄帝书》、《黄老帛书》)
帛书《经法》和《经》、《称》、《道原》一起抄录在帛书《老子》乙种本之前,全文用较规范的汉隶抄写,行与行之间有“乌丝栏”界格,抄写时间可能在文帝初年。帛书幅宽48厘米,出土时因折叠而断裂成多块24厘米宽的帛片,帛书除断裂处外,保存得比较完整。
帛书《经法》是这四篇佚书的第1篇,共77行,凡5000余字,它一共由9个小章节组成,即道法、国次、君正、大分(或作“六分”)、四度、论、亡论、论约、名理等,末尾有《经法》的总篇题。按其内容,这是一篇讲法治、讲农战、讲君主治国之道的文章,其中《道法》又是《经法》篇的总论,以“道生法”开篇,主要阐述道与法的关系,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而最后的《名理》则是对《经法》篇的总结,主要概述“道”的本质和循道生法,依法治国,国无危亡的原理。
帛书《经》是这四篇古佚书的第2篇,共65行,分15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有题名,它们分别是:立命、观、五正、果童、正乱、姓争、雌雄节、兵容、成法、三禁、本伐、前道、行守、顺道、十大。据其篇末题字,全文4600余字,其书写款式和抄写字体和《经法》篇完全相同,显系同一抄手、同一时期所抄成。
对于帛书《经》篇名的确定曾经过了很长的探索。该篇最初被定名为“十大经”,后经帛书整理小组经过对帛书“六”、“大”二字的字形作了仔细对比,认为应是“六”字,所以在1980年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一)中,将其定名为“十六经”。但由于帛书本身只有15章,而且最后一章(帛书整理小组认为只是半章)没有章名,故帛书整理小组认为原文可能编排有所错乱,或者曾有亡佚。也有学者主张应把篇名改称为“十四经”[※注]。参与帛书整理工作的裘锡圭后来又指出“细按字形,恐仍当释为‘十大经’”。李学勤在《马王堆帛书(经法·大分)及其他》[※注]也认为此处应是“大“字,但对篇名问题提出了崭新的见解。李先生认为,应该将“十六”和“经”分开来读,“十大”是本篇最后一个小章节的章名,因为第15章正可划为十句互有联系,又各成格言的话,而且能以韵脚来判断,所谓“十大”,就是指这十句重要的话,“大”字应按《荀子·性恶》注所释:“大,重也”。“经”则是这一篇的总名。李先生的这一解释既解决了这篇帛书篇末一章独缺标题的困惑,又解决了该篇帛书章数方面的疑问,可谓独具慧眼,因此,本篇帛书的篇名应按李先生所言为《经》。
帛书《经》各章大多通过叙述黄帝君臣的故事来叙述治国之道和用兵策略,例如《果童》一章中就提出了贵贱、贫富均等的民本思想,《前道》一章中则强调“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才能长利国家、世利百姓。《本伐》章则对战争的性质进行了分析,认为“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兵容》一章则认为用兵要法天、法地、法人才能作出正确的决断,取得胜利,不然,必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总的说来,帛书《经》是一篇用黄老刑名思想以阐述治国用兵之道的古佚书,其思路与《经法》篇的治国用道理论完全相同。
帛书《称》是这四篇古佚书的第3篇,共25行,约1600字。全篇帛书不分章节,主要是汇集一些类似格言的话,所反映的思想大体与《经法》、《经》一致。
帛书《道原》是这四篇古佚书的第4篇,其篇幅最短,只有7行,共464字。本篇帛书虽短,但其内容却很重要,它主要是推究阐释“道”的本原、性质和作用,其内涵和思想,与《老子》、《文子》、《淮南子》的“道”论有密切的关系。帛书《道原》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通篇基本上押韵,这和以韵语成篇的《老子》亦非常相似。
三、数术类帛书
1.帛书《五星占》
帛书《五星占》抄写在一块幅宽48厘米的整幅帛上,通篇用很规范的汉隶抄写。全文共146行,约8000字。本篇帛书原无篇题,帛书整理小组根据其内容将之命名为《五星占》。由于帛书中的天象记录一直到汉文帝三年(前177年)为止,可以断定帛书的写成年代是在汉文帝初年,帛书整理小组认为可能是在公元前170年左右。
帛书整理小组曾据帛书《五星占》的内容,将之分为九章,即:木星、金星、火星、土星、水星、五星总论、木星行度、土星行度、金星行度。这九章内容可大体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前六章,其内容是对木星(岁星)、金星(大白)、火星(荧惑)、土星(填星)、水星(辰星)的运行规律和星占规定的描述和记录,属于天文星占类的古佚书。第二部分即后三章,主要是用图表的形式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前246年)到汉文帝三年(前177年)共70年间木星、土星、金星的运行位置,并描述了这3颗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动态。
帛书《五星占》的出土,对于我国天文学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价值。根据记载,我国讲天文的专门书籍,最早的当推战国时代甘德所写的《天文星占》八卷和石申所写的《天文》八卷,这两部书的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370年到前270年之间。可惜它们都早已失传,仅有一些佚文存世。帛书《五星占》的出土,使我们得以直接看到了秦汉时代星占书籍的原貌,尤其是后三章对木星、土星、金星的位置及在一个会合周期内动态的叙述,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利用速度乘时间等于距离这个公式,把行星动态的研究和位置的推算工作有机地联系起来,这就比战国时代甘、石等人零星的探讨前进了一步,而成为后代历法中“步五星”工作的先声。学者们发现,帛书《五星占》所载的金星会合周期为584.4日,比我们今天所测值583.92日仅大0.48日;土星的会合周期为377日,比我们今天所测值只小1.09日;恒星周期为30年,比我们今天所测值29.46年只大0.54年,这些数据都远较后来的《淮南子·天文》及《史记·天官书》更为精确,可见当时中国的天文观测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2.帛书《天文气象杂占》
帛书《天文气象杂占》抄在一幅长150厘米、宽48厘米的帛上,字体是隶书,但篆书意味相当浓厚。出土时已经碎成大大小小的几十片残帛,并有一小部分已经腐烂,但还可以基本上恢复原来的面貌。这篇帛书原无篇题,帛书整理小组根据其内容将之命名为《天文气象杂占》。
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图文并茂,除了下半幅末尾的一段之外,从上到下可分为六列,每列又从右到左分成若干行。占书每条上面是墨或朱,也有用朱墨二色画成的图,下面是名称、解释及占文。也有些只有名称,或只有解释;还有一大部分只有占文,而没有其他。每列多的有五十几条,少的残存二十余条,全幅包括完整或残缺的共约三百条。下半幅末尾的一段,是墨写的占书,有文而没有图,从上而下分为三列,每列多的二十六条,少的残存十三条,合计尚存五十七条。该篇帛书的内容,如果从占文所根据的对象来划分,大体上可分为云、气、星、彗星等内容。下半幅末尾有文无图的一段,其内容基本上和前面的文字相似,可能是同一性质的另一本占书。
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占文,除了“贤人动”、“邦有女丧”、“有使至”等一小部分之外,其余大多是‘客胜”、“主败”、“攻城胜”、“城拔”、“不可以战”、“益地”、“失地”、“军乃大出”、“战得方者胜”等有关军事的占语。因此,该书应与兵阴阳之说密切相关,并可与《淮南子·天文》、《史记·天官书》、《乙巳占》、《开元占经》、《通典·风云气候杂占》等书所记载的兵家所用天文气象占验的内容互相参证。
从天文学史的角度看,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彗星的部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观测和记录彗星的国家,《左传》中就有三次相当具体的记载。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对于彗星的观测已经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画有各式各样的彗星,除最后一条翟星外,其余都分彗头彗尾两个部分。彗头画成一个圆圈或圆形的点,有的圆圈中心又有一个小的圆圈或小圆点,这表明,当时人们很可能已经见到在一团彗发的中心有一个很小的彗核。所画的彗尾则有宽有狭,有长有短,多种多样,可见当时人们对于彗尾的观测也已经相当仔细。这些材料足以说明,在两千多年前,我国观测彗星已经有了出乎意料的成就。帛书所绘的彗星图,是世界上最早的彗星形态记录,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
3.《阴阳五行》甲、乙篇(或称《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或称《篆书阴阳五行》为《式法》)
帛书《阴阳五行》共有两篇写本,甲篇写本抄写年代较早,系用篆意很浓的篆隶抄写而成,乙篇稍晚,系用规范的八分隶抄写。这两篇帛书都是既无标题,又不分章节,帛书整理小组根据其内容暂称之为《阴阳五行》,甲篇也被称为《篆书阴阳五行》,乙篇则被称为《隶书阴阳五行》。2000年出版的《文物》第7期以《马王堆汉墓帛书〈式法〉摘要》为题,将过去被称为《篆书阴阳五行》的该件帛书正式改名为《式法》,并公布了其中的一部分材料。

帛书《阴阳五行》的乙篇“长约l.23米,上有文、图表。大致分为十个单元”(见周世荣《略谈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竹简》)。相对而言,这个本子比甲本要完整得多,有些图表相当完好,成段的文字也比较好读,例如:
这一段文字前有“十二日宫军”五字,这或许是这一段文字的标目,从该段文字所记十二日辰的所占内容来看,这显然是择吉日良辰的既定占语。
乙篇类似这样完整的段落还比较多,又如:“丙寅、丁酉、壬申、癸卯是胃(谓)臽,而不□其乡(向),毋逆以行。行水,不有大丧,必亡。”这段话的上面,用墨线横断的上部单独题有一个“臽”字,显而易见,这是该行文字的一个标题,所谓“臽”,原本是“丙寅、丁酉、壬申、癸卯”这四个干支相配的日子。凡“臽”日,不可逆行,否则,不有大丧,就有家亡之灾。此外,帛书还记有刑德运行的规律,记有择顺逆灾样的占语,记有“文日”、“武丑”、“阴铁”、“不足”等阴阳五行的特有名称和解释,特别是那好几幅图表式的文字,尤其醒目,确是研究阴阳五行学说在汉初本来面目的极好资料。[※注]
4.帛书《木人占》(或称《杂占图》)
帛书《木人占》抄于幅宽48厘米的整幅帛上。据介绍,该篇帛书“绘方形、梯形、三角形,及婢女举木人作占验的图形”(见周世荣《略谈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竹简》,载《长沙马王堆医书研究专刊》)。不过陈松长说他曾对帛书原物作过认真的验对,并未在这篇绘有“方形、梯形、三角形”的帛书上找到“婢女举木人作占验的图形”,却有“举木人作占验”的文字[※注]。这卷帛书相对比较完整,除文字因经浸泡而字迹较虚外,整块帛书由99个不规则的图形及大约59行文字组成。因此,许多学者径称其为《木人占》,本篇帛书的字体与《老子》甲本、《刑德》甲篇较为相近,是一种篆意较浓的古隶,其抄写年代亦当与《老子》甲本、《刑德》甲篇相近,即应抄成于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前后。
这篇帛书的内容分上下两块排列,上面一块开篇就给有9行99个不规则的图形,这些图形以方形为主,间有变形的匡形、梯形、三角形、井字形、十字形等,每个图形内都有少则1字,多则8个字的文字注释,大多是“吉”、“大吉”、“大凶”、“小凶”、“不吉”等有关吉凶的一般占测语,但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占语。如:“食女子力”、“食长子力”、“以善为恶”、“有罪后至”、“空徒”,这些图形和这些文字的关系到底如何?其所占测的对象到底是什么?现在还没有真正破译,仍有待学林时贤的研究。
在这些图形的左侧和下面,分别写有五十九行占语,因为文字字迹较虚,颇难认准其字形,仅就其依稀可辨的那些文字来句读,可知其占语大都是占测方位吉凶的,例如开篇就有一行:
此外,在图形的下方,列有二十多行关于方位占测的诠释语,例如: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件帛书中还有好几行相人的记录,如:
除这些较完整的几行文字外,残破处还多有“贵人恐,贱人缌”,及“人鼻”、“人口”、“人北(背)”等有关人体部位的相面用语,由是可知帛书《木人占》亦有部分相人术的内容,而这恐怕也是我国现存相人术最早的文献抄本之一。
5.帛书《相马经》(或作《相马经·大光破章故训传》)
帛书《相马经》抄写在幅宽48厘米的整幅帛上,全文共77行,约5200字,除略有残损外,大部分字迹清晰。字体为隶书,抄写相当工整。帛书整理小组根据其内容将之命名为《相马经》,也有学者认为这篇帛书更准确的名称应是《相马经·大光破章故训传》。
帛书《相马经》是一篇谈相马的辞赋体古佚书。全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第1行至22行)是“经”,即《相马经》的《大光破章》这一部分;第二部分(从第23行至44行的“处之,多气”)是“传”,它是对“经”的大意、精要进行综合归纳,寻绎发挥的文字;第三部分(从第44行至77行)则是“故训”,也就是对经文的训解。
帛书的第一部分,主要是讲相马眼的学问。因此开篇就称“大光破章”。“大光”可能即指眼而言,而“破”可能是解析之义,所谓“大光破章”,意为相眼之章,它应是这一篇经文的章名。帛书的第三部分主要是对第一部分的训解。例如帛书第一部分开头言:
第三部分的文字中则对此明确加以解释:
通过这一段训释,我们才知道,原来经文中所说,都是对良马眼睛的一种颇具文学色彩的形容和要求。
帛书的第二部分则是对第一部分加以阐发和归纳讲解。不过,这一部分内容并未依照经文的次序逐一来阐述,而只是就其中的几点加以发挥而已,这种发挥,有的是对经文的总结,有的则是对经文的阐发[※注]。
6.《“太一将行”图》(或称《社神图》、《神祇图》、《避兵图》、《太一避兵图》)[※注]
帛书《“太一将行”图》现存原物幅长43.5厘米、宽45厘米,本是一件具有神秘色彩和艺术价值的帛画,但因这幅帛画有多达百余字的题记文字,故亦可以视为一种帛书。
该图彩绘,虽有残破和互相因折叠浸染的印痕,但图像和题记文字基本清楚。图像正中上部彩绘一位主神,他头戴鹿角,双眼圆睁,巨口大开,舌头前吐,双手下垂,上身着红装,下着齐膝青色短裤,赤足,两腿分开,双膝外曲,作骑马欲行之势。他的右侧腋下单独墨书一个“社”字,而头部左侧则有题记:
“以”字以下残泐,不知究竟缺几字。由题记文字可知,这位主神就是楚汉人心目中极有权威的太一神。
“太一”神的左右两上侧残破较为严重,但仍存有两个依稀可辨的图像和一些题记文字,其中右上侧是以墨线勾勒的云气和一个半边的侧面人像,该像的左边墨书题记文字为:
“太一”神的左上侧则以朱色为主,绘有一些云气和一个正侧面的头像,它双目浑圆,怒视前方,它的右侧亦有题记,现仅存一个“雷”字,由这些题记可以知道,这两个图像乃是雨师和雷公,这和《楚辞·远游》中“左雨师使径侍兮,右雷公以为卫”的描写可以对应。
在“太一”神的两臂之下,左右两侧共排有神人四个,按照“东行为顺”的次序,右起第一个头戴青色三山冠,身着青色短袖衣,红色短裙,右手下垂,左手高举,似举一利器,但因帛画已残,已不知为何物。他双目圆鼓,巨口大开,长舌前吐,髭须斜飘,脸色赤红,一副神武而狰狞的面孔。右边有一行题记:
右起第二位亦头戴三山冠,修眉大眼,张口伸舌,左手举一剑状物,右手下垂,身着红色短衣,下穿红墨相间的条纹短裙,赤足。其右侧亦有一行题记:
右起第三位,即“太一”神左侧的第一位则头作侧面,头上有角状形冠,左手上扬,手掌作兽爪状,右手下垂,圆眼鸟喙,身着红装,上加半截墨色短袖衣,其左臂下侧墨书题记一行:
最后一位则头顶中间下凹,两端异骨突起,上顶双重鹿角,黄脸上怪眼斜睨,双目圆张,两须分扬如剑戟,脖子细长,肩部耸一怪骨,双手侧握一殳,惜其题记文字已残。
这四个神像也许正是楚帛书所言的“祝融以四神降”的四神,它们是掌管四方,护卫“太一出行”的神灵。
在“太一”神的胯下,绘有一条头顶圆圈的黄身青龙。在这条黄首青龙的下边,左右还各绘一龙,其右边之龙朱首黄身,龙头上扬,龙身曲动,前持一红色瓶状物,龙头下题有“黄龙持炉”四字。而左边之龙则黄首青身,与黄龙成对峙状,前亦捧一青色瓶状物,龙首下题有“青龙奉容”四字。
在帛画的右侧,还有一段总题记,文意都是太一出行时的祝语,文字不长,仅存44个字,但其中反复出现了“先行”、“径行毋顾”、“某今日且〔行〕”等语词,可见这幅帛画应是以“太一”出行为主旨的一幅作品。
四、兵书类帛书
帛书《刑德》甲、乙、丙篇
帛书《刑德》共有甲、乙、丙三种抄本,甲、乙两篇保存得比较完整,丙篇则残破太甚,已很难拼合和句读。甲篇的抄写字体是比较放逸的古隶,行与行之间没有乌丝栏界格,篇中有“乙巳,今皇帝十一年”的话语,系指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可见《刑德》甲篇是汉高祖在位时抄写的。乙篇长84厘米,宽44厘米,字体是比较规范的汉隶,行与行之间有很规整的乌丝栏,看上去比甲篇要精工得多,篇中有“丁未,孝惠元”的话语,可见乙本的抄写时间在孝惠元年(前194年)以后。丙篇现存原物共揭裱为18块残片,从残存的片断文字看,其内容与甲、乙两篇大致相同,只是该篇全部用朱文书写,间有很粗重的墨线边框,这种较为奇特的形式是否别有含义,尚待研究。
帛书《刑德》甲、乙、丙篇是现存秦汉时期兵阴阳的著作之一。甲篇和乙篇的内容基本相同,都由“刑德九宫图”、“刑德运行干支表”和关于刑德运行规律及星占、气占等兵阴阳的文献三个部分组成,所不同的是,甲篇的“刑德九宫图”绘在帛书的左上角,排在干支表的后边,而乙篇的“刑德九宫图”则绘在开篇的右上部,列在干支表的前边。
五、方技类帛书
1.《足臂十一脉灸经》
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同抄在一幅长帛上,帛的幅宽为24厘米。该篇帛书全文共34行,字体为篆意较浓的古隶。全文没有标题,帛书整理小组根据其内容将之称为《足臂十一脉灸经》。
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古的一部经脉学著作。文中有“足”、“臂”二字高出正文一格书写,可知此篇可分为“足”脉和“臂”脉两部分。其中“足”脉包括足太阳脉、足少阳脉、足阳明脉、足少阴脉、足太阴脉、足厥阴脉及死与不死候一节。“臂”脉则包括臂太阴脉、臂少阴脉、臂太阳脉、臂少阳脉、臂阳明脉五节,每一节中均较简要而完整地记载了其脉的名称、循行径路、生理病态和灸法疗法。其特点是,这十一脉的循行方向全是由下而上,向心循行的,而其治疗方法则全是灸法,并都只说灸其脉,而没有穴位名称,也没有针治记载。至于病候的描述也简单而原始,没有多少理论和治则上的讨论,这反映了帛书所记经脉理论的原始性。
2.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
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共有两种抄本,甲本紧接在《足臂十一脉灸经》后面抄写,共有37行,保存得相对比较完整;乙本则和《却谷食气》、《导引图》抄在一幅帛上,中间残缺较多,仅存18行。帛书本无篇名,帛书整理小组根据其内容将之命名为《阴阳十一脉灸经》。
这两卷帛书是继《足臂十一脉灸经》之后,而在《黄帝内经·经脉篇》之前撰写的另一种古经脉学著作。与《足臂十一脉灸经》相比较,《阴阳十一脉灸经》则显然要进步得多,例如:
(1)关于十一脉的排列次序,是以阳脉在前,阴脉在后,不再是以足臂分先后。
(2)关于十一脉的循行径路、病理症候和灸法的描述,也比《足臂十一脉灸经》进步和丰富得多。
《阴阳十一脉灸经》的内容可分为足巨(太)阳脉、足少阳脉、足阳明脉、肩脉、耳脉、齿脉、足巨(太)阴脉、足少阴脉、足厥阴脉、臂巨(太)阴脉、臂少阴脉等十一节。有趣的是,这两篇和《足臂十一脉灸经》一样,都无“经脉”之称,而只有“脉”字作为“经脉”的统称,而且其治疗也很单一,全是采用灸法,这说明这两卷经脉学著作仍是比较原始的著作之一,但是很显然它已发展、丰富了《足臂十一脉灸经》的理论,为后来的《黄帝内经》中的经脉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帛书《脉法》
帛书《脉法》抄录在《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之后,出土时已严重残损。全文仅300余字,帛书整理小组根据原文首句的“以脉法明教下”,将之命名为《脉法》。
帛书《脉法》的内容也是论述根据脉法来判断疾病的症候,这里所说的“脉”,与《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的“脉”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它既有后世医书中的“经脉”之义,也有血脉(血管)之义。帛书《脉法》中还特别提到用灸法和砭石治疗的问题。西汉初期名医淳于意曾有“故古圣人为之《脉法》”之语,但《史记》所引《脉法》佚文似较帛书更为具体详细。
4.帛书《阴阳脉死候》
帛书《阴阳脉死候》抄录在《脉法》之后,全文一共才一百来字,是马王堆帛书中篇幅最短的一篇。该篇原无篇名,帛书整理小组根据其内容命名为《阴阳脉死候》。
帛书《阴阳脉死候》主要论述在三阳脉与三阴脉疾病中所呈现的死亡症候及有关理论。文中认为三阳脉属天气,一般不至于死,只有折骨裂肤,才有死的可能性,故其死候只有一种。三阴脉则属地气,其病多是腐脏烂肠,常易引起死亡,故其死候有五种之多。因此,本篇和《脉法》一样,也是一篇古代的诊断学著作。其内容同《灵枢·经脉篇》中关于“五死”的一段相近,但有一些重要出入,而且没有《经脉篇》所具有的五行学说色彩。因此其著作年代应早于《黄帝内经》的成书。
5.帛书《五十二病方》
帛书《五十二病方》抄写在《阴阳脉死候》之后,全篇帛书共计有462行,原无篇题,但卷首有目录,目录之末有“凡五十二”的记载,正文每种疾病都有抬头标题,共五十二题,与卷首题字互相一致,因此帛书整理小组将其命名为“五十二病方”。
帛书《五十二病方》是一篇迄今所知我国最古的医学方书。书中记载了各种疾病的方剂和疗法,少则一二方,多则二三十方不等。疾病种类包括了内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等科的病名,尤以外科病名为多。治疗方法主要是用药物,也有灸法、砭石及外科手术割治,还有若干祝由方。书中药名多达二百四十余种,有一些不见于现存古本草学文献,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西汉初期以前的临床医学和方药学发展的水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篇帛书和前面四种古医书中,都没有针法出现,而《黄帝内经》书中不但有针法,而且详述有九种形制、用途不同的医针。由此可见《五十二病方》的著成较早,在我国医药学史研究上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帛书《五十二病方》末尾还附有几条古医方的佚文,而且字体亦有所区别,整理者曾认为这是在全书抄录后,另经他人续增的,故称其为《五十二病方》卷末佚文。这部分佚文由于多残缺不全,故很难句读。这种缀续佚文的现象有待进一步研究以揭示其真正的原因。
6.帛书《却谷食气》
帛书《却谷食气》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导引图》共同抄写在一幅宽约为50厘米的整幅帛上。帛长150厘米。该篇文字出土时已成残片。由于残破严重,行数和字数颇难确定。现存可辨识的字计272个,缺损字数也在200余字。从字体上看,这篇帛书当为汉初写本。本篇帛书原无篇题,帛书整理小组根据其内容将之命名为《却谷食气》。
帛书《却谷食气》的内容大致包括却谷和食气两部分。却谷也叫辟谷、断谷或绝谷,是指停食五谷而服食代用品。食气是古代气功的一种,它是一种结合呼吸导引以求却病养身的方法。尽管本篇内容残缺不少,但其所录,反映了我国汉代以前气功导引方面的成就,现在看来也有许多临床实践的参考价值。
7.《导引图》
《导引图》抄写在帛书《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之后,出土时亦大部破损。该篇帛书亦原无篇名,帛书整理小组根据其内容将之命名为《导引图》。严格地说,它应属帛画,不应划在帛书内讨论,但该图的每个图式原都有题记,而且又是和《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同抄在一幅帛上,故言及马王堆医书者,都自然要论到它。因此,我们亦将其和其他方技类帛书一起作一介绍。
《导引图》是一幅彩绘的导引练功图。经过帛书整理小组的多方缀合拼复,得知帛上共有44幅人物全身的导引招式,它分为上下4行排列,每行各绘11幅小图,人像高9—12厘米。所绘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人物姿态动作各异,有坐式者,有站式者,有徒手导引者,亦有持器械发功者。人物形象则多戴头巾或绾发,仅3人戴冠,身上多着夹袍、穿布履,但亦有赤膊、赤足者,可见其导引锻炼时并不讲究服饰。每个导引图侧都有文字题记,但因残缺太多,现能看出有字迹者约30余处,而清晰可辨者则20余处。
《导引图》虽然残破严重,题记亦很简略,但其内容却十分丰富。《导引图》的题记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导引动作的固定名称,如“折阴”、“熊经”;一类是治疗某种病症的动作,如“引温病”、“引颓”、“引聋”、“引膝痛”。还有两者兼有的,如“沐猴讙,引热中”。它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中时代最早的一件健身图谱[※注],它和帛书《却谷食气》篇一样,为研究我国特有的气功疗法的源流和发展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
8.帛书《养生方》
帛书《养生方》单独抄在一幅帛上,前面是正文,最末是目录,全文估计应有6000余字,但因缺损严重,现仅存3000余字。字体是介于篆隶之间的古隶体,其抄写年代大致在秦汉之际。帛书原无篇题,帛书整理小组据其内容命名为《养生方》。
从帛书《养生方》篇末的目录来看,该篇帛书共分32种医方,由于帛书残损,实际只有27种保存下来,根据其内容可以分为五类:
(1)用于男性治疗或保养。包括《老不起》、《不起》、《加》、《洒男》、《用少》、《食引》篇部分。
(2)用于女性治疗或保养。包括《勺(约)》、《益甘》、《去毛》等部分。
(3)用于行房,包括《戏》、《便近内》等部分内容。
(4)一般的养生补益。包括《为醴》、《治》、《麦卵》等部分内容。
另外,卷末还附有女性生殖器的平面图,上面标有表示其部位的术语。
从这些内容来看,帛书《养生方》与房中术有密切关系。古人所说的“养生”,概念很宽泛,不但包括一般的养生补益,也包括各种性治疗和保养。本篇帛书对于我们了解古代的养生学具有重要的价值。
9.帛书《杂疗方》
帛书《杂疗方》单独抄在一幅帛上,由于出土时已严重残损,其行数和字数都无法统计,据帛书整理小组公布的整理结果,现存文字约79行,而这79行中的行数,文字残缺也很厉害,因此内容识读相当困难。原篇无标题,帛书整理小组据其内容命名为《杂疗方》。
帛书《杂疗方》也是一篇古医方书。现据残帛的有限内容来看,其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1)益气补益医方,共2条。
(2)壮阳、壮阴的诸医方,共20条。
(3)产后埋胞衣方,共2条。
(4)“益内利中”的补药方,约有3条。
(5)治疗“蜮”虫及蛇、蜂所伤医方,共8条。
(6)主治不详的若干残缺处方,共7条。
由于这些内容涉及面较多,故帛书整理小组将其定名为《杂疗方》,其内容亦仍以房中术为主。另外,这卷帛书中所记的“禹臧狸(埋)包(胞)图法”有文无图,而帛书《胎产书》中则有图无文,这两卷帛书正好可以参校互补。
10.帛书《胎产书》
帛书《胎产书》抄在一幅正方形的帛上,上部是二幅彩图,其中右上部为“人字图”,左上部为“禹臧(藏)图”。帛书《胎产书》的文字全部抄写在帛的下部,现存约34行。字体接近云梦睡虎地秦简,估计写成较早。全篇原无篇题,帛书整理小组据其内容命名为《胎产书》。
帛书《胎产书》是一篇有关胎产的方技类古籍,正文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第1行至第13行,是“禹问幼频”养胎方法的记录,它论述了十月胚胎的形成及产妇调摄法,其内容与六朝、隋唐时流传的“十月养胎法”大致相同,但其文字和叙述更为古朴简要,显然是比较早的祖本。第二部分是第14行至第34行,主要是集录的21个医方、记载胞衣的处理和埋藏及求子等方法。帛书上部的《禹藏图》、《人字图》在这卷帛书都没有文字说明,但上述《杂疗方》中有一篇“禹臧理(埋)包(胞)图法”可作“埋胞图”的注解。“人字图”虽在帛书中没有文字说明,但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人字”图的研究可知,这是一种根据胎儿产日预卜命运的测算图。
六、其他帛书
1.《驻军图》(或称为《守备图》)
《驻军图》是一幅长98厘米、宽78厘米的军用地图,用黑、红、青三色绘制。所谓军事地图,是在地形图上根据作战意图、计划,按照地理条件、标定兵力、武器等配置、作战态势等情况的地图,通常有进攻和防御(包括守备)之分。这幅地图上只表示长沙自己方面的军队,而没有敌方南越国的军队和军事内容,说明它是一幅重在防御的军事地图。严格来说,本篇帛书亦为一幅帛画,但由于图中所记文字较多,故亦放在帛书中加以介绍。
《驻军图》的左、上方,分别标有东、南二字,因而其方位是上南下北,与现在地图的方向正好相反。图中所绘的区域大致在今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沱江流域一带,方圆约五百里,其比例大致为八万分之一至十万分之一。图上用深颜色把驻军营地、防区界线等要素突出表示在第一层平面,而把河流、山脉等地理基础用浅色表示于第二层平面。这与现代专用地图的两层平面表示法是一致的。
《驻军图》上详细标注有城堡、障塞和营垒等军事要塞的位置和文字,并特别用丁形、方形或不规整的框格注明了驻扎军队的所在位置,从图上可以看到,驻守此地的有4支军队,大部分驻扎在诸水系的上游,分成9个营垒,其中主力军驻守于大深水一带,居中有“周都尉军”、“周都尉别军”,右翼则有“徐都尉军”和“徐都尉别军”,左翼则有“司马得军”、“桂阳□军”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图中间的三角形堡垒式的“箭道”,它的三面都绘有岗楼式的城垛和箭楼,并有一条“复道”靠近水系,隔水又有“周都尉军”驻防,很显然它是这个防区的最高统帅所在地。
《驻军图》中除一些军事要塞都有图注外,还绘有两个方形的城邑:一处是“深平城”,它大致位于今江华县瑶族自治县的沱江;还有一处是“故官”,它或许是候馆的旧址。此外,图上圈注最多的里名,经统计共有41个里名。“里”本是最基层行政组织机构,但图上所注似乎并不注重“里”这个行政单位的大小,而主要是详注各里的户籍情况,如:
很明显,这种记载,都是为驻军征集兵力,调集民力作注脚的,这种记录,也客观地记录了当时因战争而人口锐减的实际情况。
根据史料记载,公元前181年南越王赵伦曾“发兵攻边,为寇不止”,吕后曾派将军隆虑侯周灶将兵击之,后因暑疫罢兵。结合《驻军图》中所绘的军事防区图及所注文字推论,这幅帛图应绘制于高后七年(前181年)南越王攻打长沙国边境之时到汉文帝元年(前179年)罢兵以前,这幅《驻军图》之所以随三号墓墓主人下葬,意味着这位墓主人亦是当时参加抗击南越、戍守边郡的长沙国军事长官之一。
2.《地形图》(或称《长沙国南部舆地图》、《西汉初期长沙国深水防区图》)
《地形图》画在一幅长宽各96厘米的帛上。与《驻军图》一样,该图亦应属于帛画,但因该图中所记文字较多,故亦放在帛书中加以介绍。该图原无题名,帛书整理小组根据其内容称其为《地形图》。
《地形图》上绘有河流、山脉和城镇、乡里、便道等各种地理要素,其所绘区域以“深平城”为主,西向大致包括桂林地区的大滨江以东的灵渠;东向大致包括珠江口一带的九龙和香港;北向则大致止于湖南零陵地区的阳明山以南的双簰附近。地跨今湖南、广东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部分。在东经111度至112度30分和北纬23度至26度之间。
与《驻军图》一样,《地形图》的方位也是上南下北,其比例尺约为十八万分之一,以现代地图制作理论来衡量,这幅图亦已达到了相当准确、精密的程度。例如图中用闭合曲线勾画的山脉,其轮廓、走向和峰峦起伏的地形特征都绘得十分准确,而用方块表示城镇、用圆圈表示“里”等行政单位都井然有序,不相杂乱。至于其比例的准确性,亦不能不使人们为之惊叹。
这幅地图所绘大致可以分为主区和邻区两大部分,主区以今湖南道县及潇水流域为中心,邻区则以今全县、灌阳和钟水一带为主,广东南海一带则为远邻区。图中除了绘制深水(今潇水)这一主要水系外,共绘有30多条支流。这些水系的描绘多用粗墨线勾填主干道,用细墨线描绘大小支流,河流的大小宽窄,清楚明白,很便于查检。如果把图上深水水系的主要部分同现代地图作一比较,可以看出河流骨架、流向等都基本相似,有些区域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有些河流名称如泠水等一直沿用到现在,也可谓是“源远流长”了。
这幅地图除详绘有水系、山脉外,还标有8个城邑,57个乡里,其中8个城邑都是汉代所置县名,经考古调查,这8个城邑均找到了当时相应的古城遗址。
这幅地图还有一种用特殊图例表示山脉的方法,在该图的左侧下方,画有9个并列的柱状物,柱头涂有山形线墨体,而且旁边还加注“帝舜”二字。相传帝舜曾巡游江南,死后葬于九嶷山。从该图所绘方位和文注,可知这九个柱状物即用来表示九嶷山的9峰。这种特殊的表示法无疑是现代地图绘制中用形象图示地理位置的最早范例。
上述就是马王堆44篇帛书的大致情况。按照计划,马王堆帛书总共要出版6册的整理报告,但是至今由帛书整理小组正式整理出版的整理报告只有第一、三、四这三本,其他的三册至今未能出版。有鉴于此,2008年,湖南省博物馆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合作,准备重启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工作。如果这一项目进展顺利的话,我们有望在不远的将来看到这六册整理报告的全部出版。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