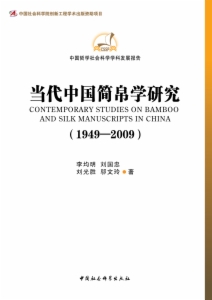十三 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研究
|
来 源
:
|
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0 \ 下编 帛书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 | ||
|
摘 要
:
|
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材料公布后,许多学者纷纷撰文加以讨论[※注],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命名问题。陈松长、刘绍刚、王树全合写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释文再补》一文[※注]根据帛书照片及原件,依据帛书残片的图文内容、字体风格、污痕情况、反印文字及图形等特点将一些帛书残片补入,在帛书拼接缀合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文中还附有修订后的释文内容。王树全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列国云占”探考》一文[※注]则结合古籍中有关列国云气的描述,对于《天文气象杂占》中的云图与占语进行了讨论,颇多收获。 | ||||||
|
关键词
:
|
帛书 天文气象 天文气象杂占 彗星 天文 成书 战国时期 气象 考释 学者 列国 |
||||||
在线阅读
十三 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研究
字体:大中小
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材料公布后,许多学者纷纷撰文加以讨论[※注],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命名问题。顾铁符指出,这幅帛书的内容包括云、气(包括蜃气、晕、虹等)、星、彗等方面。总的看来,以占气的篇幅最大,其次是云,第三是彗,而星的分量最小。我国古代的天文学,一般说,一是研究日月五星,用以制历法;二是研究二十八宿、中宫、外宫,用以定节气;三是研究气象(古代对天文和气象并没有严格区分,气象亦归入天文),用以观察天气。这幅帛书是以气象占为主,穿插了天文范围内的彗,以及个别的星,因此称它为《天文气象杂占》可能比较妥当。
(2)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性质。顾铁符指出:“《天文气象杂占》的占文,除了‘贤人动’、‘邦有女丧’、‘有使至’等一小部分占文之外,其余的都是‘客胜’、‘主败’、‘兵兴’、‘军疲’、‘城拨’、‘邦亡’、‘益地’、‘失地’等关系军事方面的。这和一同出土的《刑德》等一样,都是属于兵家阴阳,亦即军事迷信的书。”魏启鹏也说:“通过对《杂占》的整体观察和分析,可以肯定它是兵家所用的天文气象占验之书。”李学勤则言:《天文气象杂占》这种书,“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法,应当划归数术类的天文家”,这一见解在具体分类上虽与顾先生小有差异,但实质是一样的。因为该书从内容上看,既可划归兵阴阳类,也可划归天文类。
(3)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成书时代及作者。对于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抄写时代,顾铁符指出,“这幅帛书的字体,虽然已是隶书,但篆书的意味还相当浓厚。同时出土的许多帛书中,只有《老子》甲本和《战国纵横家书》和它比较接近。书中称所有国为邦,国君为邦君,不避汉高祖刘邦的讳。由此可见,这幅帛书的传抄,至迟不晚于西汉最初的几年;但亦不排除更早的可能。”对于这一看法,学者们没有太多的分歧。
至于帛书的成书年代,顾铁符指出:“《天文气象杂占》中最有时代关系的,是101条至114条十四个国、族的云。其中有赵云、韩云、魏云,说明成书是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之后。其次如越、中山、宋,都是战国时期被灭掉的国(楚灭越在公元前345年,赵灭中山在公元前301年,齐灭宋在公元前286年),而各国云中还有这三个国。不过,古代人对地理名称的使用常有连续性,国亡后仍可能把国名作地名用”,“《天文气象杂占》成书的年代和《周礼》相去不远”。从这些论述来看,顾先生认为《天文气象杂占》是成书于公元前403年之后的战国时期。席泽宗也认为《天文气象杂占》的成书时间应在三家分晋和越灭亡这两个年代之间或稍后。
魏启鹏则认为,“古代天文学的观测、推算、占验,是需要若干代人接力进行的事业。帛书《杂占》集录的天文气象占验乃多家之言,上至战国之前,下至秦楚之际。”魏先生认为帛书中的“天出荧惑,天下相惑,甲兵尽出”、“鱼(渔)阳亡”等占辞具有秦楚之际的特征,其纂辑年代当为司马迁所称的秦楚之际。
至于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作者,顾铁符指出,帛书中对于各国云的论述亦可见于一些典籍,但是排列顺序却有很大差别:“《开元占经》、《晋书·天文志》、《太平御览》引《兵书》等,都是从韩云开始,楚云排在第三,《乙巳占》中甚至没有楚云。独有这幅《天文气象杂占》以楚云排在最前面,这决不是无缘无故的事。总的来看,《天文气象杂占》提到的历史事件很少,但四一六条提到吴伐楚的柏举之战,并且是以楚人的口气说的。”此外帛书中还有一些含有地域性的词语,因此很可能是出自楚人之手。席泽宗和李学勤也持同样的观点。
魏启鹏认为,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天文气象占验是若干代人接力进行的事业,文中所引材料的作者,也绝不限于帛书注明的任氏、北宫、赵□等人,而纂辑为《杂占》当为楚人。这又把帛书作者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区分。不过魏先生仍然肯定这件帛书最后成于楚人之手。
(4)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学术价值。顾铁符指出:“《天文气象杂占》里的云、气、星、彗四个部分,分量有多有少,论科学价值亦有很大悬殊。据我们初步研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天文中的彗,其次是气象中晕的部分。”“《天文气象杂占》中关于彗星的二十九条,重点是在表示出各种彗星的形态。除了最后一条彗星之外,其余都分彗头、彗尾两个部分。彗头画成一个圆圈或圆形的点;在六一九、六二○、六二三、六二八等图中,圆圈的中心又有一个小的圆圈或小圆点。这个小圆圈或小圆点,是否说明在当时已经见到在一团彗发的中心,有一个很小的彗核,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另外,帛书所画的彗尾有直有弯,且有大小不同的弧度,可见当时观测彗星已经注意到了彗尾的形态差异。总之,“这二十九条彗星,很足以说明二千几百年前我国观测彗星已经有了出乎意料的成就。这一部分彗星图,是我国古代研究彗星的里程碑”。
席泽宗也从科技史的角度论述了帛书彗星内容的重大价值。陈奇猷则对帛书彗星图占作了新的考释,随后王胜利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这些学者的工作使得对帛书中彗星内容的研究继续深入。
学者们对于帛书中彗星等部分内容特别重视,主要是从中国科技史的角度加以认识的,实际上如果从中国古代的数术传统及古文献研究的角度考虑,帛书《天文气象杂占》还有更多的意义。这方面李学勤的文章给人们很多的启示。李先生主要讨论了《天文气象杂占》中有关白虹的占语“白虹出,邦君死之”,将之与荆轲刺秦王时“白虹贯日”联系起来并加以解释,还进而对《燕丹子》一书的情况作了讨论,这是对《天文气象杂占》研究思路与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开拓。
近些年来关于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如刘乐贤在《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中对于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篇也作了详尽的校注和考释,并对篇中的“北宫”的含义及楚地彗星占测传统作了讨论[※注];陈松长也撰有多篇研究《天文气象杂占》的论文[※注];陈松长、刘绍刚、王树全合写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释文再补》一文[※注]根据帛书照片及原件,依据帛书残片的图文内容、字体风格、污痕情况、反印文字及图形等特点将一些帛书残片补入,在帛书拼接缀合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文中还附有修订后的释文内容。王树全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列国云占”探考》一文[※注]则结合古籍中有关列国云气的描述,对于《天文气象杂占》中的云图与占语进行了讨论,颇多收获。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