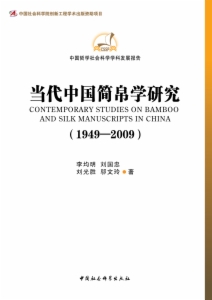十六 帛书古地图研究
|
来 源
:
|
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0 \ 下编 帛书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2 | ||
|
摘 要
:
|
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共出土了三幅帛质古地图,即“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或称“园寝图”),由于“城邑图”上没有文字,因此我们不过多予以讨论。对于第一幅地图,谭其骧认为就是汉代通常所谓的舆地图,根据地图内容,谭先生建议定名为“西汉初期长沙国深平防区图”(《二千一百多年前的古地图》, 《文物》1975年第2期),吴承国则认为“马王堆地形图系秦代江图”[※注]。对古地图内容的认识和研究对古地图内容的认识和研究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古地图上所标出的特殊地理名称及古代区域地名的考释,一方面则是对古地图绘制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价。很显然,这些对比研究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马王堆古地图具有重要作用。 | ||||||
|
关键词
:
|
古地图 地形图 驻军图 地图 马王堆 帛书 马王堆汉墓 学者 防区 要素 河流 |
||||||
在线阅读
十六 帛书古地图研究
字体:大中小
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共出土了三幅帛质古地图,即“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或称“园寝图”),由于“城邑图”上没有文字,因此我们不过多予以讨论。
地形图和驻军图出土时,折叠的边缘已经断裂破碎,专家们经过精心努力,终于将它们修补复原。其具体情况在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发表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的整理》(《文物》1975年第2期)及《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驻军图整理简报》(《文物》1976年第1期)中有详细的论述。
“地形图”和“驻军图”发表之后,学者们对其作了很多的研究,综观这些研究论文,主要是围绕下列主要问题展开讨论的。
(1)关于古地图的定名问题
“地形图”和“驻军图”本身并没有题名。帛书整理小组发表这两幅古地图时,指出前者“属于地形图”,后者为“驻军图”,随后学者们对这两幅地图的准确命名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于第一幅地图,谭其骧认为就是汉代通常所谓的舆地图,根据地图内容,谭先生建议定名为“西汉初期长沙国深平防区图”(《二千一百多年前的古地图》,《文物》1975年第2期),吴承国则认为“马王堆地形图系秦代江图”[※注],周世荣等人则支持帛书整理小组的命名(《马王堆帛书古地图不是秦代江图》,收入《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
至于《驻军图》的命名,学者们也存在一些分歧。詹立波认为,这幅地图“反映了汉初长沙诸侯国军队守备作战的兵力部署情况,属于军事要图,可称为‘守备图’”(《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守备图探讨》),不过,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称“驻军图”或“守备图”并没有质的区别[※注],称“驻军”,比较侧重在其军队的建制和防区的分布,称“守备”则强调防守装备布局方面。不过学术界一般都认同“驻军图”的定名。
(2)关于古地图的绘制年代
马王堆古地图发表之后,对古地图绘制年代的意见一直是众说纷纭。对于“驻军图”,有的学者认为可以早到汉高祖或惠帝初年[※注],有的学者认为定在高后末年为宜[※注],也有的学者认为应是文帝初年[※注],还有一些学者则将“驻军图”的绘制时期笼统地定在高后七年(前181年)至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之间[※注]。
至于“地形图”的绘制年代,进行讨论的学者相对比较少。曹学群在《论马王堆三地图的绘制年代》一文中将“驻军图”与“地形图”的内容加以比较,认为“地形图”的绘制年代应相对早于“驻军图”,可以确定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至高后七年(前181年)之间,而很可能是在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以后至高后七年这段时期之内[※注]。
(3)对古地图内容的认识和研究
对古地图内容的认识和研究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古地图上所标出的特殊地理名称及古代区域地名的考释,一方面则是对古地图绘制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价。
在对古地图地名的研究方面,周世荣做了很多工作。周先生曾运用出土的汉印资料,将之与古地图进行了对比研究,还亲自对古地图上所绘的城邑要塞进行了实地调查[※注]。《地形图》中标明的八个大城,除桂阳可能被近代建筑湮没外,其余七个古城遗址周先生都发现了眉目,从而使两千年前神奇古老地图中的奥秘终于略见端倪。
对于古地图绘制方面的情况,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已经作了很好的说明。如关于“地形图”,帛书整理小组指出,这幅地图所包括的范围大致为:东经111度至112度30分,北纬23度至26度之间,地跨今湖南、广东两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部分。地图的主区包括当时长沙国的南部,即今湘江上游第一大支流潇水流域、南岭、九嶷山及其附近地区。其邻区为西汉诸侯南越王赵佗的辖地。地图主区部分内容比较详细,邻区比较粗略。这件帛书的主区有一个大致的比例,在1/17万—1/19万之间,如按当时的度量制,约相当于一寸折十里地图。地图上表示的主要内容既包括作为自然地理要素的山脉、河流,又表示了作为社会经济要素的居民地、道路等,而地貌、水系、居民地、交通网四大要素,正是现代地形图的基本要素。因此可以说,这是一幅相当于现代的大比例尺的地形图。从地图内容要素的表示来看,该图绘制技术也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例如河流的粗细变化,自然弯曲表示得相当生动,河口处没有通常易于错绘的倒流现象,道路的绘画几乎是一笔绘成,看不出有换笔的接头,描绘居民地的圈形符号的圆度很好(如深平),显示出该图较高的绘制技术水平。在绘制方面,看来当时已经有了初步的“制图原则”,例如:对地图内容的分类分级、化简取舍,地图符号的设计,以及“主区详邻区略”等,有些至今还在应用。因此,该图的出土确是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一大发现,表明了我国两千一百多年以前地图科学的蓬勃发展和测绘技术的高度水平,由此说明了晋朝的裴秀关于“汉代舆地及括地诸杂图……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的说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注]。至于“驻军图”,帛书整理小组指出,这幅地图的主区为大深水流域,在今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潇水流域,方圆约五百里,它所包括的范围,仅仅是同它一起出土的“地形图”中的部分地区。主区北部绘得比较详细,而南部地带比较简略。其主区的比例大致是1/8万—1/10万,图上东西方向与南北方向的比例不太一致,较“地形图”约大一倍。“驻军图”的基本内容不只一般地表示山脉、河流等普通地图要素,而且根据它的专门用途而突出表示了九支驻军的布防和防区界线、指挥城堡等。该图把驻军内容突出表示于第一层平面,而把河流等地理基础用浅色表示于第二层平面,这与现代专门地图的两层平面表示法是一致的。这幅“驻军图”是用三色彩绘的军事要图,主题鲜明,层次清楚,表现了我国古代高度的地图测绘水平。总览全貌,大多数河流和一些与驻军有关的山头均注有具体名称,居民地有的还旁注户数,尤其突出地表示了各支军队的名称、驻地,显示出各军事要素与周围地形的关系。所有这些都说明了“驻军图”必定是在实地勘测的基础上绘制的。同时,由于它真实地记录了当时长沙诸侯国在军事上的驻防备战形势,所以它又为研究西汉初期的军事、历史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佐证[※注]。后来谭其骧、张修桂等还继续就这两幅古地图的绘制特点及所反映的历史地理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注]。
对于马王堆古地图的研究,近年来有一些学者从新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李均明在《关于〈驻军图〉军事要素的比较研究》(收入《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一文中,运用丰富的汉简资料,将《驻军图》所示防区与居延防区进行了很有意义的对比;王子今则将“地形图”和“驻军图”与甘肃放马滩秦墓古地图进行对比研究,指出它们之间在突出标示交通路线方面有某种继承关系,而其内容又可补充史籍对于南楚交通记载之不足,因而有助于对汉代交通史的认识[※注];刘晓路的《从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地图看墓主官职》(《文物》1994年第6期)则综合考察了“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的内容,认为墓主人生前的官职应是长沙相。很显然,这些对比研究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马王堆古地图具有重要作用。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