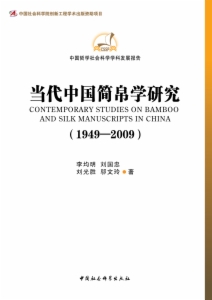隶臣妾及刑期问题
|
来 源
:
|
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0 \ 中编 简牍文书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 | ||
|
摘 要
:
|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云梦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包山楚简、江陵张家山汉简等大批法律简牍资料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战国秦汉法制史料。罗鸿瑛主编《简牍文书法制研究》[※注],孙家洲主编《秦汉法律文化研究》[※注],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刘海年、杨升南、吴九龙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一册《甲骨文金文简牍法律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文集》[※注],李力《张家山247号墓汉简法律文献研究及其述评》(1985.1—2008.12)[※注],等等。这里仅就学界讨论比较集中的隶臣妾及刑期问题、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年代问题、秦汉律令体系、刑罚体系、司法诉讼制度等略作综述。 | ||||||
|
关键词
:
|
律令 臣妾 隶臣妾 二年律令 汉简 文书 刑期 法律 刑罚 劳役 简牍 |
||||||
在线阅读
隶臣妾及刑期问题
字体:大中小
1975年,睡虎地秦简出土之后,其中所见“隶臣妾”的身份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形成了睡虎地秦简“隶臣妾”身份问题研究的热潮。2001年张家山汉简公布之后,引起学界对这一论题的再次关注。学者们相继提出了如下观点:
第一,刑徒隶臣妾官奴婢说。1977年,高恒发表《秦律中的“隶臣妾”问题的探讨》一文,提出睡虎地秦简中“隶臣妾”的身份问题,从秦“隶臣妾”的身份及秦律中有关隶臣妾免为庶人的规定、隶臣妾从事的劳役及其生活待遇、秦律中的隶臣妾与奴隶制社会中的奴隶之间的区别,以及隶臣妾的反抗斗争等方面,对秦“隶臣妾”的身份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秦律中的“隶臣妾”是一种刑徒名称,汉律中所用的刑徒隶臣妾名称也是因袭秦制;从刑徒隶臣妾服刑期限问题、隶臣妾的来源问题、隶臣妾在法律上的地位问题来看,“秦时的隶臣妾实际上就是一种官奴婢”,将罪犯当作奴隶,是奴隶制的残余。秦律沿用了古已有之的制度。“隶臣妾”的来源,除了本身犯罪被判刑外,还有因亲属犯罪而籍没的人及投降了的敌人。秦时的刑徒是没有刑期的,所以“隶臣妾”实际上是一种服刑没有期限的官奴婢。“隶臣妾”在法律地位上虽与奴隶制时代的奴隶有所区别,但仍然是没有人格的工具物品。[※注]唐赞功[※注]、李裕民[※注]、陈连庆[※注]亦持此说。
第二,官奴隶说。高敏主张秦“隶臣妾”是官奴隶,认为“秦时奴隶的名称,按官府奴隶与私家奴隶而区分为两大类别。官府奴隶大多谓之‘隶’,其中男性谓之‘隶臣’,女性谓之‘隶妾’,总称为‘隶臣妾’。而私家奴隶,则多称之为‘人奴’、‘人奴妾’或‘臣妾’。另外,还按年龄与服役种类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注]他在读了高恒的论文之后,从秦“隶臣妾”与刑徒的区别、秦的刑徒有无刑期、“隶臣妾”有无私有财产、“隶臣妾”的法律保护及奴隶制残余对社会生产的桎梏问题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秦“隶臣妾”的官奴隶身份,对高恒的讨论作了补充。[※注]后来为回应林剑鸣《“隶臣妾”辨》一文,高敏、刘汉东合作发表《秦简“隶臣妾”确为奴隶说》[※注];为答复林剑鸣《三辨“隶臣妾”》一文,刘汉东独自发表《再说秦简“隶臣妾”确为奴隶说》[※注],重申秦“隶臣妾”为“官奴隶”之说。
黄展岳支持“官奴隶”说,并明确指出隶臣妾与刑徒最重要的区别在于:“隶臣妾”是终身性的服役,刑徒则有一定的服役期限。他还对高恒、高敏的观点进行了评述,认为高恒“混淆了隶臣妾与刑徒的性质区别:把隶臣妾当成刑徒,又把刑徒说成终身服刑。”因此,“高恒同志举汉文帝十三年减刑诏令作为秦时刑徒是无服刑期限的依据是站不住脚的,高敏同志在指出这一问题时,又陷入另一矛盾中。他说,文帝减刑诏令中的‘有年而免’是指‘隶臣妾’,‘要把秦的隶臣妾的终身服役,改为有刑期的刑徒,使之刑期满后便可免为庶人。’高敏同志既然承认文帝十三年以前的隶臣妾是终身服役的奴隶,则何来‘有年而免’?这就是矛盾所在。”[※注]此外,宋敏[※注]、于豪亮[※注]、苏诚鉴[※注]、宫长为[※注]、杨巨中[※注]、蔡葵[※注]、孙仲奎[※注]等人也持“官奴隶”说。
第三,刑徒说。林剑鸣为主张此说的代表人物。他发表多篇论文,反对“官奴隶”说的主张,强调“隶臣妾”仅仅是一种刑徒,他们并不是“官奴隶”,也不相当于奴婢。认为“隶臣妾”不能与“臣妾”同日而语。“臣妾”是奴婢的称呼,“隶臣妾”则是刑徒的专用名称,而且“隶臣妾”只是一种十分普通的刑徒。秦简中提到“隶臣妾”与提到“臣妾”的均有十分明确的区别,所以不能把有“隶”的均与奴隶相连。秦到战国时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也起了较大变化,许多名称含义也有了变化。战国以后人们使用的“隶”有“一般”、“平常”、“卑下”之意。“隶臣妾”不光有私有财产,还允许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对于役使“隶臣妾”致死者,还要追究法律责任,这与奴隶有明显的区别。总而言之,秦简中反映的“隶臣妾”不是“官奴婢”,也不是奴隶,只是一种刑徒。“隶臣妾”同其他刑徒的区别,仅在于被刑轻重不等,这不仅不能说明“隶臣妾”不是刑徒,而只能说明他们是一种被刑较轻的刑徒;但“隶臣妾”同“臣妾”的区别,则在于能否屠杀、买卖和有无独立经济地位,这种区别不仅说明“隶臣妾”同“臣妾”有本质的不同,而且证明“隶臣妾”决不是奴隶。“隶臣妾”不是奴隶,也不是严重的罪犯,只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刑徒,这也就是他们被称之为“隶臣妾”的原因。[※注]他在《三辨“隶臣妾”——兼论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对“官奴隶”说的持论者进行全面回应,并从方法论上作了检讨。他认为,断定“隶臣妾”是奴隶的一些论著,大多是从其法律地位、来源、待遇、服役期限等方面去论证其阶级属性。这对研究“隶臣妾”无疑是有益的。但是,往往忽略对其本质的探讨,而夸大其次要的、附属的形态,至少是主次不分。这样得出的结论,往往似是而非。“隶臣妾”是刑徒还是奴隶,这本来属于两个范畴的问题:前者属法律范畴,后者属阶级范畴,这两个范畴并不完全一致。当然也不排除在某种情况下二者的一致性。现在的问题是讨论“隶臣妾”是否为奴隶,这就需要用划分阶级的标准来衡量,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弄清“隶臣妾”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在弄清他们不是奴隶,不具有奴隶的属性之后,我们还必须清楚意识到,他们作为刑徒又是多种成分的混合物,它的成员分属于不同的阶级。[※注]
张金光亦反对秦“隶臣妾”为“官奴隶”说,认为“隶臣妾”与刑徒无本质区别,实属于刑徒的范畴。他从来源与有无附加肉刑、刑具、衣服号色等,服劳役类别、繁重程度及社会地位,口粮标准,刑期,犯罪判刑升级六个方面,论述了秦“隶臣妾”的刑徒身份。[※注]钱大群认为秦“隶臣妾”是具有终身奴隶身份的刑徒。他在《谈“隶臣妾”与秦代的刑罚制度》一文中指出,“秦代刑罚复合使用上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肉刑或徒刑和终身罪隶身份刑的复合使用,而‘隶臣妾’就是刑徒和身份刑复合使用的表现形式之一。”“《秦简》中的隶臣妾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那就是因为犯罪而被判为奴隶,同时还有一定期限的徒刑。作为刑徒并有终身奴隶身份的‘隶臣妾’,首先是重于‘候’和‘司寇’的一个刑罚等级。”[※注]王占通、栗劲主张秦“隶臣妾”是“带有奴隶残余属性的刑徒”,认为“隶臣妾基本上是刑徒,但保留某些官奴隶的残余属性。它是奴隶社会的‘罪隶’演化而来的,具有很大的过渡性。”因此,在它身上就不能不保留国家奴隶即官奴婢的残余属性。[※注]栗劲在《秦律通论》一书中进一步阐述说:秦是由奴隶社会刚刚转变而来的早期封建国家,奴隶制的残余还相当严重,在隶臣妾这个刑徒的身上也有明显的表现。其一,隶臣妾是终身刑,具有社会身份的形制。其二,隶臣的妻子虽然可以是平民,但是,他们的子女必须是隶臣或隶妾,如果试图改变这种关系,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基于上述两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隶臣妾这种刑徒身上,还保留有奴隶即官奴隶的残余属性。但是,从本质上看来,隶臣妾仍然是法定的刑徒。[※注]张传汉认为“隶臣妾是服刑罪人,其服刑方式是,在不受监禁下,为官府服劳役。隶臣妾有独立的家庭经济,又有一定的人身自由,部分时间服劳役,部分时间从事公和不从事公,轮番更替,是秦代适用于轻罪的一种较轻的刑罚手段。”[※注]张颉慧[※注]认为“隶臣妾”是一种刑徒,刑期有限,同时具有官奴隶身份,但又不同于奴隶社会的奴隶。
第四,秦“隶臣妾”由“刑徒和官奴隶两部分组成”之说。主张此说的学者有刘海年、陈玉璟、杨剑虹、施伟青、杨升南、李力等。刘海年在《秦律刑罚考析》一文中指出,“秦律中的隶臣妾,要比其他徒刑,如城旦舂、鬼薪白粲等的情况复杂。城旦舂、鬼薪白粲,都是因其本人触犯封建法律被判处徒刑的。而隶臣妾,可以是被籍没的犯罪人家属;也可以是战争中投降的敌人;还可以是封建国家掌握的官奴婢隶臣妾的后代。”[※注]后来他又撰文专门探讨秦“隶臣妾”的身份问题,认为秦的隶臣妾既包括官奴隶,也包括一部分刑徒。[※注]陈玉璟早先提出,战国秦汉时代“隶臣妾”既用为奴隶名,也逐渐用为刑徒名。[※注]后来又撰文详细阐述这一看法,指出:“隶臣妾”作为奴隶的名称,它是古代社会的产物。伴随着长期的奴隶阶级的反抗斗争,在春秋时代,其本意可能已发生了转移。在《秦律》中,“隶臣妾”的身份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人:刑徒和奴隶。秦统一以后,官私奴隶统称为“人奴”、“臣奴”,“隶臣妾”便成为刑徒专名的一种。“汉承秦制”,“隶臣妾”在西汉为二岁刑。至东汉时代,“隶臣妾”在文献中不见刊载,作为一种名物制度,它可能是在历史上消失了。[※注]杨剑虹认为“隶臣妾应该区分为两类,一是刑徒中的隶臣妾,二是国有奴隶。”[※注]施伟青指出“隶臣妾”的身份十分复杂,包含了刑徒“隶臣妾”与官奴隶“隶臣妾”。[※注]李力[※注]、杨升南[※注]亦赞同秦“隶臣妾”由“刑徒和官奴隶两部分人组成”之说。
2007年,李力撰写《“隶臣妾”身份再研究》一书,从法制史的角度,重新对“隶臣妾”身份问题进行研究。书中对以往学界关于“隶臣妾”身份问题的研究作了全面梳理和评述;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对“隶臣妾”一词的流传、使用期限、结构及含义作了详细的考辨;系统整理睡虎地、龙岗、里耶秦简以及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和《奏谳书》等简文中有关“隶臣妾”的史料,逐一进行分析解读,分别考察秦简所见“隶臣妾”的身份和张家山汉简所见“隶臣妾”的身份,勾画出战国、秦汉时期“隶臣妾”产生、发展演变的基本轨迹,认为:“隶臣妾”一词,是秦律中的专有法律术语,不仅指官奴隶,而且也指刑徒,经过战国时期、秦朝的发展,在西汉时期的法律中演变为一个纯粹的徒刑刑名。[※注]
秦代徒刑的刑期问题,历来根据东汉卫宏《汉旧仪》的说法,认为是一至五岁的有期刑,但秦简出土之后,这一传统的看法引起了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无刑期说,二是有刑期说。
1977年高恒《秦律中“隶臣妾”问题探讨》提出了秦时的刑徒无服刑期限的看法,认为在汉文帝发布减刑诏令之前,各种刑徒都是无刑期的,刑徒隶臣、妾当然也没有服刑期限。在秦律中因犯罪而判为隶臣、妾者,不是后世有人认为的服一岁或二岁刑的一般刑徒。秦律中的刑徒隶臣、妾,实质上是因犯罪被确定的一种官奴婢身份。[※注]1983年,他又在《秦律中的刑徒及其刑期问题》中作了进一步的论析,认为作为主要刑罚的城旦舂、隶臣妾、鬼薪白粲等徒刑无刑期,他们既是刑徒,也是终身服劳役的官奴隶,只有赀徭、赀居边、赀戍和“居赀、赎、债”等几类刑徒有服劳役期限。卫宏《汉旧仪》中有关刑徒的记载并不全是秦制,因而不可据之认定秦时的城旦舂、鬼薪白粲等刑徒有固定的服刑期限。[※注]栗劲、霍存福《试论秦的徒刑是无期刑——兼论汉初有期徒刑的改革》也认为秦的徒刑皆为无期刑。理由有二:一是按秦律内容抄录的秦简不著刑期,证明秦的徒刑是无期刑。二是在秦的各类徒刑中,隶臣妾是具有奴隶和刑徒的双重身份的。它具有赎替的旁延和世袭接续的特征。因此,隶臣妾是无期的。在秦律中,隶臣妾同其他刑徒是能够互相转换比较轻重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其他刑徒也是无期刑。同时也指出,秦的无期徒刑并不绝对地是终身刑。秦的严刑峻法,使大量的自由农民转为刑徒,但同时也有另一种流转,这就是由徒刑向自由农民的转化。就秦简来看,刑徒的流转,基本上有两种方式,其一是隶臣妾的以人赎替,包括爵赎、戍边赎罪及以人替换,但不能以钱赎刑;其二是赦。此外还有“免臣”,即刑徒与奴隶的双重身份一同豁除。秦简中有“系城旦六岁”、“城旦三岁免为司寇”,以及赀、赎、债有劳役抵偿期间等律文,均有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皆不能以之作为有期刑的根据。汉代真正实行有期徒刑,是从汉文帝十三年的刑法改革开始的。[※注]苏诚鉴《秦“隶臣妾”为官奴隶说——兼论战国历史上“岁刑制”的起源》认为秦代的“隶”系受肉刑不死的罪犯,连同其家属,终身供官府役使。古代法律无岁刑,即无今之所谓的有期徒刑。[※注]
高敏、黄展岳不赞同高恒的意见,认为“隶臣妾”和刑徒有别,“隶臣妾”是终身服役,而刑徒是有服役期限的。[※注]刘海年亦主有刑期说,他在《秦律刑罚考析》中指出,从法律规定看,秦的刑徒是有刑期的,有期徒刑不是始自汉文帝改革。并根据秦简的记载、卫宏对秦刑制的叙述和《汉书·刑法志》等几个方面的材料,考析出秦代各类徒刑的具体刑期:城旦舂五至六岁;鬼薪白粲四岁;隶臣妾三岁;司寇二岁;候一岁。这几种徒刑除服劳役的时间长短不同之外,在服刑时受的约束和管制也有很大区别。[※注]后来他在《关于中国岁刑的起源——兼谈秦刑徒的刑期和隶臣妾的身份》中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的有期刑不是始自汉文帝改制,在此之前战国时代业已大量适用了,不仅秦的刑徒是有期刑,齐国等关东诸国的刑徒也有刑期的。而秦的隶臣妾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官奴隶,另一部分是刑徒,二者来源不同,性质也不同,不能等同视之。作为刑徒的隶臣妾有一定的刑期。[※注]
张建国《西汉刑制改革新探》[※注]全面检讨了以往各家关于汉代劳役刑的刑期问题的看法,结论认为有关这方面的形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1)汉文帝十三年以前,从秦继承下来的劳役刑是不定期刑(特定意义上的无期苦役),这一时期的各种劳役刑的轻重(除去肉刑等附加刑造成的区别外),是以刑名所代表的劳役的苦累程度来加以区别的。(2)汉文帝十三年开始,至汉武帝太初元年为止,各种劳役刑基本成为有期刑,最高刑期是六年,以下依次递减。其轻重的区分,是以刑期的长短和劳役的苦累程度(较高的几种有定期递减,形成较复杂的结构)这二者的混合形式为标准(附件刑造成的区别除外)。(3)从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刑罚制度进一步作了调整,从秦继承过来的隶臣妾这一刑名被取消,刑罚等级在其上的各劳役刑的刑期顺序减少一年,也就是最高刑期是五年,以下依次递减。经过整合后的各劳役刑内部不再存在复杂的劳役结构,从此劳役刑的刑名基本用来表示刑期的长短(附加刑造成的区别除外),从这时开始,才和《汉旧仪》中说的刑期一致起来。
近年随着张家山汉简资料的公布,学者们倾向于从动态演变的角度来考察刑期制的问题。籾山明《秦汉刑罚史的研究现状——以刑期的争论为中心》[※注]认为①从战国秦到汉初的劳役刑,没有固定的刑期;除通过赎身或者恩赦之外,没有释放的途径。②对各种劳役刑设定刑期的,是文帝十三年的改革。③规定刑期的罚劳动,自文帝改革以前就已经存在,其改革的意义就在于将这种形式扩大到所有的劳役刑。邢义田《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重论秦汉的刑期问题》[※注]认为刑期制并不是文帝改革时突然出现的。从刑无刑期到刑而有期,从不定期到定期应是一个十分漫长而且复杂的发展和调整过程。刑期很可能是从偶然、权宜、局部和非常态,逐步变成一种原则,走向常态化、全面化和系统化。睡虎地秦律和张家山汉律其实刚好见证了文帝以前刑期已以某些形式存在,却尚未系统化和全面化的状态。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之法及汉所承的秦法中无疑已有有期刑,唯刑期见于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刑期非必一定,也不成体系。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