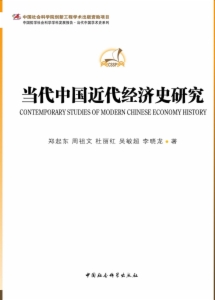第二节 经济史研究的重镇形成
|
来 源
:
|
当代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7 | ||
|
摘 要
:
|
这一年,在陶孟和的支持下,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7年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创刊。他们在实践中建立起一定的研究程序和学术规范:选定课题后,熟悉前人研究成果、掌握大量一手史料,然后细心整理,用统计学、经济学的方法排比与分析史料,从历史现象中得出结论。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所改组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正是因为承继了如此深厚的学术资源与优秀的学术传统,它继续保持国内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镇地位。 | ||||||
|
关键词
:
|
棉纺织 外资 学术 集刊 原始资料 史学 内资 史料 马克思主义学说 研究会 棉纺织工业 |
||||||
在线阅读
第二节 经济史研究的重镇形成
字体:大中小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治趋于稳定,经济有所发展,学术研究也有了较大进展。这一时期出版业的繁荣和期刊的蓬勃发展,为学术成果的发表和传播提供了载体。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亦获得较快发展,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至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近代经济史领域专业研究队伍的形成、专业期刊的创办、一批高质量专业著作的出版,以及近代经济史研究方法、理论的规范等,标志着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的正式诞生。
当时,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镇是陶孟和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1935年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这一小节将专门予以探讨。
1932年,北平社会调查所正式成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组,汤象龙担任组长,组员有罗玉东、刘隽、梁方仲等人。这是中国第一个从事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专业研究机构。当然,当时的近代经济史研究,对所谓的“近代”界定较为模糊,研究时段并不严格限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研究组的重要成员梁方仲,研究的即为明代财政史。汤象龙、罗玉东和刘隽等人主要研究晚清至民国经济史,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研究组成员正在集中整理清宫档资料有关。
这一年,在陶孟和的支持下,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7年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创刊。这是一份半年刊,自1932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按时出版5卷共10期,此后因战乱陆续出版3卷共6期,至1949年总计出版8卷共16期。近代经济史组成员的重要研究成果即发表在这份刊物上。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是一份学术水平很高的杂志,论文篇幅较长,以扎实的材料和严谨的学术规范著称。它对自己的定位是:“本刊以讨论中国近代各种经济问题及现象,并介绍各种重要经济史料书籍为宗旨;而以根据充分的正确事实,原始资料兼用严格的方法为讨论的基础。此种刊物的发行为中国学术界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创举。”[※注]寥寥数语,指出了这份刊物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发刊词强调了研究经济史的重要性:“在我们认识经济在人类生活上的支配力,并且现代经济生活占据个人、民族、国际的重要地位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历史的大部分应为经济史的领域。”[※注]“历史的大部分应为经济史的领域”,这是何等的胸襟与气魄!这句话道出了经济史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经济史研究的任重而道远。“我们认为整理经济史最应注意的事有两点:一是方法,二是资料。关于前者,我们以为一切经济史的叙述必须根据事实,不可凭空臆度,所采用的方法应与研究其他的严格的科学无异。关于后者,我们认为最可宝贵的要为原始的资料,尤其是量的资料,有了这种资料才可以将经济的真实意义表达出来。”[※注]可见,《集刊》推崇的研究方法,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法,强调原始资料的挖掘和利用,一份材料说一分话。根据经济史的特点,特别注重原始材料中数据部分的计量运用。
在陶孟和的大力支持下,经济史组同人当时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清宫档历时7年的大规模整理,这也是他们重视资料收集的切实践行。1930年至1937年,共抄录清宫档中的财政经济史料12万件,其中一半以上形成了可以直接利用的表格,同时收集专业书籍1000多种,形成了研究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的宝贵资料库。[※注]这批资料至今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镇所之宝。在抄录整理资料的同时,经济史组成员的实证研究逐步开展,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源源不断地产生。
汤象龙的重要论文,有《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 《咸丰朝的货币》《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注]等。其中,《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是汤象龙发表的学术处女作。他认为外国鸦片输入中国后导致中国白银流出,是清政府禁止鸦片的根本原因。这是我国第一篇从经济角度研究鸦片战争发生背景的专题论文。当时,汤象龙选定“中国近代海关税收”作为长期研究课题。他收集军机处档案各海关监督报销册共6000件,大胆采用统计方法,将其中一些定期的、系统的、计量的政府报告和报销册进行摘录,制作表格。这些工作先后花费四年时间,四位经过一定训练的人员摘录和校对史料,两位统计员帮助制作表格,可见其繁难之程度。恰在表格制作完成之时,抗战爆发,进一步的分析撰述工作无法进行。1942年,汤象龙离开研究所。世事变迁,直至1978年,他才重新着手这一研究课题,以年老病弱之躯、惊人的毅力,于1992年84岁高龄时出版《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
经济史组的另一名成员罗玉东,当时主攻厘金史研究。厘金制度,是我国近代财政史上一项特殊而重要的制度,1853年创立,1930年废止。厘金虽然对国家财政多所补益,但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罗玉东花费三年时间,遍阅清宫档军机处所藏各省厘金报告3000余件,并参阅各种史籍,写成《中国厘金史》。[※注]在书中,罗玉东对厘金制度的起源和推行经过、政府相关管理政策、厘金收入和支出状况,以及各省厘金的具体状况等,开展了系统的研究。这部书充分利用统计学方法,正文各种类型的表格达138个,是研究中国厘金史的优秀著作。
刘隽当时进行的是中国近代盐政史研究,论文有《道光朝两淮废引改票始末》《清代云南的盐务》《咸丰以后两淮之票法》等。[※注]他是1934年全国盐政研究会论文比赛一等奖获得者。罗玉东和刘隽都为近代经济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可惜均在抗战时期英年早逝,后辈学者已很少记得他们。梁方仲于1933年冬进入经济史组,从事明代田赋史研究。他关于一条鞭法的研究享誉海内外。因本研究主要涉及近代经济史,故对梁方仲的研究不予详细评介。
1934年5月,汤象龙、吴晗发起成立“史学研究会”,参加者还有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夏鼐、罗玉东等近十位年轻人。这个研究会办了两个史学副刊,一个在天津《益世报》,一个在南京《中央日报》,一直坚持到抗战爆发,造成了很大影响。史学研究会的成员后来几乎都成为经济史领域和历史领域的著名学者。
汤象龙领衔的近代经济史组的学术活动和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意义:第一,组织收集、整理清宫档,为近代经济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和资料基础。第二,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发表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这些成果重视原始资料,倡导科学方法,树立了近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规范。汤象龙本科阶段在清华国学院学习,研究生时主攻经济史;梁方仲本科就读于清华经济系,研究生在经济学部,两人均具有较强的文史功底和西方社会科学基础。他们在实践中建立起一定的研究程序和学术规范:选定课题后,熟悉前人研究成果、掌握大量一手史料,然后细心整理,用统计学、经济学的方法排比与分析史料,从历史现象中得出结论。这样,经济史研究不再止步于现象描述,而成长为西方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影响下的新式学科。他们主导的史学研究会,在天津《益世报·史学副刊》的“发刊词”中说:“中国史上的问题太多了,我们愿意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就个人的兴趣和所学,就每一个问题做广博深湛的探究。”[※注]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做广博深湛的研究,若细细品味,这句话蕴含无限,不仅概括了近代经济史学的研究特色,也是其他学科的治学门径。将近80年过去,在宏观视野与微观研究之间游刃有余——我们今天的研究何尝不是在追寻这样的境界!第三,践行了梁启超提倡的新史学从君史转向国史、民史的目标。1935年,汤象龙在为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所作的序言中写道:“现在我们要叙述文化的进步、经济的变动、社会的变迁等等”,“以往的历史是以帝王朝代为联系,目的只在记载与帝王有关的言行,此后的历史应以整个民族或各民族的发展为主体,记载他们多方面的活动”。[※注]也就是说,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学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这本身与现实历史发展中清王朝的陨落、民国的开创有关,也与经济史研究内容和关怀的变化有关。
陶孟和领导的研究所的风格,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精神一致。社会所是一个自由研究学术、探求真理的乐园。所内当时主要流行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说,但也允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讨论。[※注]严中平的《中国棉业之发展(1289—1937)》[※注],即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也是抗战时期近代经济史领域的重要著作,获得1942年第一届“杨铨纪念奖金”。严中平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随即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中国棉业之发展(1289—1937)》的内容,涉及鸦片战争前中国棉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特点、洋货入侵后机器棉纺织工业的建立、国内机器棉纺织先驱者的创业经验、民族棉纺织业畸形繁荣和萧条的原因与过程、英日等国瓜分中国棉货市场和确立对华投资霸权的过程。这本书的副标题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过程之个案分析”,作者是要以棉业为样本,指出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近百年经济上的根本变迁是资本主义的发生。当然,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是外力造成的结果。中国民族工业,包括棉业的发展,处在外国商品的倾销和外国资本的压迫下,所以必然不能顺利前行。
严中平的著作出版后,陈振汉在《图书评论》上发表书评[※注],后来又转载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上。陈振汉于1939年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美国棉纺织工业的区位:1880—1910》后,1940年回到国内,在何廉、方显廷领导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这篇书评以及严中平后来的回应文章,可以视为棉纺织史研究领域的强强对话,极具探讨意义。
陈振汉在书评中,肯定了严著的两个优点:一是取材丰富,论断精当。原始资料旁征博引,发现了很多新史实。二是过去的棉业著作,只以罗列材料、铺陈事实为能事。严著从个别史实的始末中,发现一般性,或者说发现较之棉业的兴衰过程本身更广泛的意义、更重大的价值,实现了棉纺织研究史上的重要突破。他还指出,全书能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展开,以这个问题为线索收集和排比材料,自成体系。事实上,这一评价与汤象龙等倡导的“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是一致的。也可理解为,当时研究经济史的优秀学者,已经注意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有机结合。当然,陈振汉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商榷意见:在清季国内资金山穷水尽的情况下,直接借用外资或是外人来华设厂,可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增加国民收入,是值得欢迎和鼓励的。严中平对外人来华设厂或外资竞争的恐惧与危疑态度,令人不解。陈振汉认为,内资与外资之间是相辅而不相悖的,因为外资的利用增强了本国人民的生产能力,增加本国人民之所得,也就增加了内资积聚的机会。外人来华设厂,增加的所得自然有一部分归诸他们享受,然而大部分是在中国雇用或购买各项生产元素或劳务,作为税捐纳给中国政府,变成中国人民与政府的所得。另外,外资工厂的技术示范效应、先进管理经验和对国内商民的刺激作用,也颇为有益。陈振汉进而提出:“民族资本”的概念,除了可以激励民族感情外,并不值得重视。
严中平很快发表《论外资外厂问题并答陈振汉先生》,予以回应。[※注]他根据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史实,指出华籍纱厂的发展异常困难,而外籍纱厂却很顺利。其中的原因,即为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和外资企业在经济上、技术上的优势。所以他坚持认为内资与外资是冲突的,外资侵入与发展的结果,内资便绝无蓄积的机会。不过,针对抗战胜利后中国需要借助大量外资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严中平也予以肯定。不过他主张的是间接投资,而不是外国人的直接投资——在华设厂。
此处之所以较为细致地展示严中平与陈振汉之间的交锋,是想揭示当时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几个关键点。严中平与陈振汉都是训练有素的棉纺织史专家,都明了需要突破传统的孤立地描述历史现象的研究方式,引入一定的方法、理论来指导经济史研究,以小见大,提高研究水准。但两人在学术背景上存在很大差异,严中平在中学和大学阶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陈振汉则是在西方经济学熏陶下成长的。他们对外资外厂性质、民族资本概念、华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关系、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命运等问题,存在根本分歧。他们之间的争论,反映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民国时期的对立;相对和缓的交锋方式,则显示了当时社会有着求同存异的宽松的学术氛围。两人在新中国的际遇,则反映出1949年后学术态势与格局的彻底改变。严中平是1949年后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界的领军人物。1955年,严著改名为《中国棉纺织史稿》,修订后再版发行。1961年,高教部把这本书列为高等院校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指定参考书。而陈振汉在1957年因与其他五位教授一起发表《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而被划为极右分子,剥夺了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
总体而言,1927—1937年是社会所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时期。1937年至1949年的抗战与内战,对社会所的经济史研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除了严中平的棉纺织史研究外,所内同人巫宝三从事处于世界学术前沿的国民收入研究,1947年出版《中国国民所得(1933)》一书,将该所研究经济史的学术路向予以延续、升华。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所改组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正是因为承继了如此深厚的学术资源与优秀的学术传统,它继续保持国内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镇地位。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