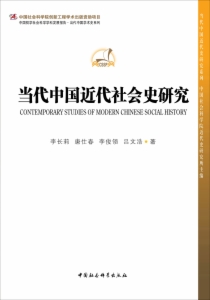三 女性生活及其社会角色
|
来 源
:
|
当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7 | ||
|
摘 要
:
|
近代中国女性的活动既有密切关联政治的解放运动与参政斗争,也有不同于政治活动的社会生活。学界对近代女性的社会生活、权利意识与犯罪活动、女性的社会形象与角色以及女性与社会的互动等问题进行了越来越细致的讨论。姚霏借助晚清上海画报和图册所刊载的大量女性与城市空间的图像,勾勒出女性的活动空间和她们在生产、消费领域的身份特征。针对图像在历史研究上的运用,她指出,尽管图像史料的运用仍处在探索阶段,即使西方历史学界也不曾实践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解读图像的手段,但不应因噎废食。潘大礼提出,从竹枝词透视近代女性的日常生活。 | ||||||
|
关键词
:
|
女性 中国女性 妇女 角色 学界 画报 学生 生活方式 女性权利 中国妇女 图像 |
||||||
在线阅读
三 女性生活及其社会角色
字体:大中小
近代中国女性的活动既有密切关联政治的解放运动与参政斗争,也有不同于政治活动的社会生活。学界对近代女性的社会生活、权利意识与犯罪活动、女性的社会形象与角色以及女性与社会的互动等问题进行了越来越细致的讨论。
(一)女性生活
20世纪80年代,学界在继续讨论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同时,开始关注近代女性生活。迄今为止,女性生活一直是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的重要问题。这期间,郑永福、吕美颐《近代中国妇女生活》一书引人注目。该书视野开阔,以宏观与微观、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多角度、多层次地描绘了近代妇女生活的缠足、婚嫁、服饰、信仰、娱乐与职业等方面的变迁。两位作者将此书视为其所著《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一书的姊妹篇。他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妇女运动时,深切感觉到应该深入了解妇女运动的前提与基础,即妇女的日常生活。因此,他们着重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审视。在《近代中国妇女生活》一书前言中,作者们慎重考虑了“生活方式”的概念问题,认为“生活方式”“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它包括人们对衣食住行、劳动工作、休息娱乐、社会交往、待人接物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以及与这些观念相适应的行为方式”[※注]。虽然在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及行为科学中,生活方式有特定的含义,人们对它的理解见仁见智,但“它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人们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和一定的价值观念支配下,为满足自身的物质要求和精神要求所采取的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注]。可以说,“生活方式”是分析社会生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由于在国内学界较早且充分运用了“生活方式”的分析视角,《近代中国妇女生活》一书在近代女性生活史研究上具有开拓性意义,有学者称赞说:“(该书)是近年来妇女史研究中难得的好书。”[※注]
2006年至今,学界对近代女性生活中的交往、生育、自杀、生计等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
其一,关于近代女性交往。魏中林、花宏艳认为,晚清女诗人的文学与交际网络除了以血缘与亲缘为主的家族网络之外,还不断拓展出以报刊为平台的媒介传播网络、以学校为核心的私谊网络和以社团为载体的社会网络。凭借这些现代交际网络,她们不断地寻求身份认同,应对政治变迁,传播自我形象。[※注]赵凤玲讨论了五四时期社会媒体上关于男女社交公开的论争,认为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享有社交权利。但当时整个社会氛围对女性的日常社交还是形成了一定的限制,能够走到时代前列的女性毕竟还是少数。[※注]
其二,关于近代女性生育。张晓艳、王俊斌以山西省保德县百人口述调查资料为中心,考察了民国时期晋西北妇女的生育状况,认为当时该地区妇女的生育状况极为落后,其主要体现在早婚盛行、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并存、不注重产妇的健康等方面,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保守的生育习俗与当地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注]杨剑利从生育观念的角度讨论了民国时期乡土妇女在生育方面存在的种种不幸。[※注]
其三,关于近代女性自杀。李书源、杨晓军以1912—1921年《盛京时报》刊载的女性自杀案例为中心,解读了民国初年东北地区女性的自杀现象,认为该现象呈现出自杀年龄年轻化、自杀方式多样化等特征,其当事人原因在于人际冲突、生存与生活压力、纲常名教引起的殉情及受虐等问题,而社会原因在于民初东北地区发展的迟滞与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注]杨齐福、汪炜炜考察了民国时期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惠安女集体自杀现象,认为这种现象难以防控的主要原因在于性别的职业流动与两性关系的失衡,传统的婚姻制度与特殊的社会习俗,尤其是普遍存在的“金兰盟”。[※注]
其四,弱势女性群体的生计与处境。赵赟考察了近代苏北佣妇在上海的规模与处境,认为她们处在社会的底层,备受歧视;江南人为了自身利益或自身认同的确立,突出她们与这个阶层的区别,因而使对苏北佣妇应有的同情与帮助被歧视与偏见所取代,由此强化她们的优越感。[※注]池子华、吕晓玲注意到,近代长三角地区的打工妹群体虽然来自四面八方,籍贯构成复杂而多元,不同行业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但以长三角本区域人为主体,显示出打工妹空间运动鲜明的区域内部流动的特征。[※注]郭卫东考察了民国时期广州瞽姬的生活遭遇,分析称20世纪30年代部分盲女退出“瞽姬”行当,但由于官方善后安置举措的失当,她们的生计仍然没有着落,甚至更为艰难。[※注]孙丽萍、宋丽莉、张舒主要依据口述史料,呈现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山西女性的生存状况,认为她们不仅亲历了心灵与肉体的双重苦难,而且许多人的人生轨迹因此转变。[※注]艾晶认为,清末民初的一些女性意识到在婚姻家庭中的不平等地位,并进行了一定的抗争;而这一时期女性因为自私、好妒等因素,造成以女性为中心的婚姻家庭矛盾较为突出。[※注]
此外,吴小玮注意到,民国时期广州政府则率先掀起了禁革女子束胸的“天乳运动”,有力遏制了束胸之风,促进了“健康美”的审美观念的传播。运动中尚有性别话语、国族精神和政党意图的交织,可见民国时期女性解放的多面性。[※注]
(二)新女性的社会形象与角色
学界对女学生的角色、形象与观念的讨论,成为2006年来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的一个亮点。张莉认为,晚清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发现和对妇女问题的发现是女学生出现必不可少的条件。他们关于现代意义上的新妇女形象的理想逐渐在女学生身上落实,其关于民族国家的设想也是在女学生从历史地表浮现并进入历史舞台的过程中一步步变成现实。[※注]宋少鹏从社会性别的角度考察了五四运动时期的女学生,认为这些女学生以国民意识和国民责任为号召,以“女学生”的身份参与到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运动之中,体现了女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自身也成为推动政治发展进程的主体。[※注]周东华不同意学术界关于近代教会女生政治意识问题的惯常看法,即认为她们不爱国。他提出,近代江南教会女生之“爱国”有“负责任之爱国”与“理性爱国”两种,前者凸显国民品性,后者赞扬知识水准,而她们更相信“理性爱国”的有效性。[※注]民国时期女学生在社会传媒中的形象不断被建构。曾越注意到,从民初到20世纪40年代,大众媒体绘画图像通过视觉符号置换,建构了一条女学生从清纯少女走向摩登女郎的衍化路径,在视觉上营造出女学生物欲渐强而内涵渐弱、“分利”色彩渐浓而“生利”意义渐淡的形象特征。图像形象的“沦陷”将女学生的进步意义消解殆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女学生以及女性解放的现实困境与社会文明发展的艰难曲折。[※注]
学界对近代其他新女性形象的讨论也较为深入。杨联芬讨论了五四新女性在身份认同上处于新伦理与旧角色相矛盾之困境的问题。其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女性处于社会道德变革的涡流中心,她们因文化身份而分属意识形态的“新”与“旧”两端。作为新文化共同体的一员,新女性认同正义伦理,肯定个人权利,追求恋爱自由;但作为女性,她们的性别认同与关怀伦理心理,却使之往往对“旧”的一方充满同情而在权利问题上做出妥协。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体现了“五四”正义伦理的道德局限。[※注]赵凤玲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沿海一些大都市的新女性、摩登女郎,认为她们以特有的女性身体形象,既诠释了新式女性思想解放、身体解放在社会中所扮演的与传统女性不一样的角色,又说明在消费文化盛行的时期,女性的身体形象也被打上了商品的符号。这一方面显示了新式女性独立的人格得到社会承认;另一方面也说明女性的身体形象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摆脱不了被欣赏、被阅读的歧视地位。[※注]冯剑侠讨论了民国时期女记者的出现及其形象的建构,认为女记者的职业性质对传统性别规范的挑战引发了男性文人对重新定义性别角色的担忧和焦虑,而她们采取“去性别化”的话语策略,强调自身的职业素养和社会功能,则是为了建构起性别中立的职业认同。女记者们的“中性化”和“职业化”究竟是对这一“男性的视角”的纠偏还是强化,仍是一个值得继续反思和探寻的问题。[※注]
有学者对宋庆龄、康同璧与胡彬夏等近代女性人物的身份建构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刘俊凤通过对宋庆龄“私人书信”的分析,试图从一个侧面展示“一个更加真实、丰满的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宋庆龄”,认为“她的生活历程不仅诠释了20世纪中国女性自我解放的路径,也成为中国女性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典范”。[※注]张朋认为,康同璧成年后自觉参与并领导了清末民初的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当时新女性的代表,从而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不断“生产”自我的社会身份。[※注]此外,张朋还分析了清末民初女报人胡彬夏的办报活动与身份认同,认为其主持的《妇女杂志》前后基调的变化反映出胡彬夏在自我身份塑造与社会舆论认可之间寻求平衡,进而避免社会身份“焦虑感”的努力。[※注]
此外,李颖以三门塘碑刻为中心,讨论了清至民国清水江流域侗族妇女参与公益事务的范围和方式。[※注]
(三)女性权利与违法犯罪
近代女性社会地位上升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女性权利的确立。向仁富着力探讨了20世纪20—30年代中期广东妇女的权利问题。他认为,当时广东妇女积极争取受教育权、经济平等权、参政权等权利,但她们争取来的权利,但是同实际权利相比较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此争取过程中,国共两党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至于广东妇女争取权利的运动有相当突出的“男性特色”,也有很强的从属于民族民主战争的工具性价值。[※注]财产权是女性权利中的核心部分之一。郑全红在《民国时期女子财产继承权变迁研究:传统向现代的嬗变》一书中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民国时期女子财产继承权变迁的脉络,透视了民国时期法律制度变革对女性社会地位的价值取向。[※注]王新宇认为,女子财产继承权是近代法律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种性别权利的突破。但女子财产继承权体现的仅仅是一种权利能力,而不是行为能力,甚至在债务继承时家境贫寒之女反受继承权之害。近代关于女性权利的立法实则利弊各半,原因在于这项法律变革基于一场政治运动,而不是社会变迁的结果。[※注]徐静莉分析称,民初女性在婚姻与继承方面的权利“仅仅停留在文本上”,大理院在涉及女性权利的婚姻、继承案件的司法裁判中既有对传统的妥协,也有顺应潮流的灵活与变通。[※注]
谢开键、肖耀依据民国时期贵州省天柱县妇女买卖土地的文书,分析妇女在土地买卖过程中扮演的卖主、买主、凭中等角色,认为是当时该地区的女性拥有了较大的财产支配权利,但她们依然缺少争取法律保护的主动权益诉求,其权利和地位仍受到各种或隐或现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注]张启龙、徐哲通过考察清末广州南城高第街房地产交易的契约文书,发现以寡母(寡妻)为主的一些女性参与了买卖过程,她们在家庭大宗交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注]此外,海日古丽·牙合甫探讨了近代维吾尔妇女在喀什贸易事业中的地位。[※注]
寡妇、妾与婢女是民国时期的女性弱势群体。曹婷婷注意到,晚清江浙地区在存在妇人改嫁携去妆奁的习惯。不过,也有因此争讼的案例。寡妇享有的财产权并不稳固,对于夫家财产并没有擅自处分的权利,受到族人的监督。[※注]李刚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在立法上虽确立男女平等原则,而法律条文对妾制并无禁止性规定,因此终无法根除“妾”之风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事实。[※注]张晓霞、顾东明依据清末民初《申报》的寻婢广告,认为婢女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十分低下,经常出现逃跑的情况,但她们已经产生了脱离依附男性的传统而自立的觉醒意识。[※注]
小田、张帆认为平民的地位更宜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进行确认,而这种地位可称为“日常地位”。以民国时期苏州轿妇为案例的考察表明,在影响日常地位的诸多变量中,所谓声望是特定共同体中体现“妇道”的村妇名声;所谓财富是村妇兼任多种劳作而获得的家庭收入;所谓特权主要是在家庭关系中村妇决定自身权利、义务的主体资格(或称为人格),其决定着村妇的日常地位。[※注]
近代女性犯罪是学界相对陌生的社会现象。艾晶在此问题上用力甚多,揭示了清末民初女性犯罪的特点与官方、民间的应对措施。她依据民初司法统计和案例资料,分析认为民国初年女性犯罪的动机多因为经济因素。女性犯罪人多为处在经济底层的人们,在无法解决自身的困难时,只有铤而走险。[※注]艾晶还集中考察了清末民初官方对女犯的宽宥与监禁。她注意到,清末民初,女性犯罪的数量和类型都有所增多,但统治者在加强控制的同时,也对犯罪女性进行了一定的宽宥处理。清末修律之时,更是减轻了对女性犯罪的惩罚。[※注]但在实际执行中,清末监狱对女犯的看管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便是官媒的虐待、勒索。加之当时大部分监狱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部分女犯因而愤恨自杀。[※注]近代民间的家法族规对女性的性越轨进行了一定的制约和惩治,这让很多女性苦不堪言。艾晶认为,近代虽有部分家法族规对性越轨女性的惩罚有所减轻,但却未能真正去除女性的性禁锢;在民国时期性解放的思潮中,女性在与传统贞操观念束缚做斗争的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明显的表现便是此时期性犯罪女性的数量和类型都出现了一定的增长趋势。[※注]
(四)女性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近代社会变迁促进了女性的觉醒,而女性觉醒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的变迁。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从社会性别的角度,讨论了女性这一性别群体在近代中国文明演进过程中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向,这种变化作为一个中间环节与近代以前的女性相比有什么不同,对当代中国女性群体的发展产生何种制约,进而寻找女性群体变化与不同区域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女性群体的变化中揭示影响社会变迁的某些动力和机制。其认为,女性在近代中国社会中所经历的变化是迈出了从女人到人的第一步。[※注]吕美颐分析了近代妇女运动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认为妇女运动的直接与间接成果一般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与提高,两性关系的错位逐步得到纠正,性别群体利益不断得到调整。二是妇女运动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强大冲击波,对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着重大影响,使人们逐步接受某些新事物,产生某种新共识”,推动了“正向”社会变迁。妇女运动的影响,往往从局部展开,由点向面扩散,从量变发展到质变。这是一个社会重新整合的过程,也是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注]
相对于前述学者概论女性与社会的关系,夏晓虹从个案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刻剖析。她通过惠兴、胡仿兰与秋瑾之死及其引发的社会风潮三个个案,分层解读晚清女性解放与民间社会力量崛起之间的关系。[※注]马军细致考察了1948年的上海舞潮案,认为这一起女子集体暴力事件是民主意识对抗极权专制的一起政治事件,也是一场无预谋、无组织、无纪律的极端行为,并且从头至尾掺杂着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色彩。案件结束后,许多当时的骨干或被动或主动地向进步组织靠拢,因而使该案有了一个最好的结局。[※注]
此外,范若兰考察了近代中国女性人口的国际迁移情况。其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女性国际迁移的总规模应在230万人左右,主要流向东南亚地区,流向美洲、欧洲、澳洲和非洲的女性移民很少。这种国际迁移可分为三种类型,即依附迁移型、主动迁移型和被动迁移型。[※注]
(五)社会传媒与女性生活
图像比文字更能直观地反映社会现象,一些学者从画报等图像资料透视近代社会传媒与女性的关联,颇有新意。秦方以晚清时期天津的几份画报为例,探讨了近代女学视觉展现的议题。其认为,观者对于女学的凝视,不仅限于男性对女性的性别凝视,也有社会阶层和身份认同的差异,甚或也会成为中外权力关系的表现方式。而画图中存在的“内外有别”的空间,使得近代女学和传统社会性别规范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注]田梅英、张云英分析了《点石斋画报》与晚清女性角色变迁的关系,认为这一时期社会急遽变化,男外女内的性别角色分工开始松动,沪上女性因得风气之先,率先迈开了由家庭到社会的步伐。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既是社会变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元素。[※注]陈艳考察了《北洋画报》,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起,较之以前的名媛闺秀,越来越多的普通城市女性出现在该画报封面上,她们的穿着打扮乃至生活方式都生动诠释了从“时尚”到“流行”的日常大众文化的变迁。而其中的普通职业封面女郎不仅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天津女子职业传统与现代纠缠的复杂面貌,也显示了现代城市职业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之间的现实处境。[※注]她还注意到,《北洋画报》封面自20世纪30年代起转向对爱国女学生及女运动员的热衷,她们作为“新女性”的代表,显示了《北洋画报》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时代审美趣味变动下的积极选择。但是,这些女学生形象表面的现代化并不能消解其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其表述具有调和现代与传统的特殊功能。[※注]韩红星也分析了《北洋画报》,认为近代女性角色从身体、社会、观念等方面都接受了新的解构与重塑,新时代的女性则在与传统角色的博弈中寻求自己的新定位,但她们无法抛弃已经进入她们血脉的固有的文化根髓,因而融入了一个新旧并存、传统与现代共立的角色重塑过程。这相较于传统女性而言,她们已经被时代赋予了新的使命与新的角色。[※注]姚霏借助晚清上海画报和图册所刊载的大量女性与城市空间的图像,勾勒出女性的活动空间和她们在生产、消费领域的身份特征。针对图像在历史研究上的运用,她指出,尽管图像史料的运用仍处在探索阶段,即使西方历史学界也不曾实践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解读图像的手段,但不应因噎废食。[※注]
不只是社会传媒的图像可以反映出近代女性生活的独特面相,歌谣和竹枝词也是值得女性史研究关注的对象。有学者提出,要积极拓宽近代女性研究的史料范围。小田主张进行史学与艺术的跨学科对话,运用近代歌谣讨论近代女性的生活。在具体运用时,“一方面需要从歌谣中析出相关元素,解构原有歌谣,滤化艺术情感,抽象民众观念,进行‘去艺术化’处理;另一方面,依据歌谣的内容和歌谣的存在环境及其存在方式对其进行时代性确认”。[※注]潘大礼提出,从竹枝词透视近代女性的日常生活。[※注]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