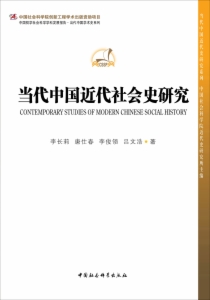四 秘密社会
|
来 源
:
|
当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4 | ||
|
摘 要
:
|
一般说来,秘密社会是指那些具有秘密宗旨或教义、按照严格的秘密仪规从事地下活动的下层民间团体,由于各种秘密结社通常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活动,因而构成了一个外人不易了解、官方不易控制、正常社会秩序难以容忍的群体,人们通常称之为“秘密社会”。秘密社会中通常有会党与教门之分。会党以天地会为主体,活跃于福建、台湾、两广和长江流域一些省份,小刀会、三点会、三合会、仁义会、江湖会等名目是它的支派。城市化、移民、游民、传统文化、区域社会文化环境与秘密社会兴起、发展的关系,秘密社会与近代政治、社会变迁的关系等内容被纳入研究的范围。 | ||||||
|
关键词
:
|
秘密社会 会党 天地会 教门 社会史 会道门 哥老会 帮会 洪门 起源 史料 |
||||||
在线阅读
四 秘密社会
字体:大中小
一般说来,秘密社会是指那些具有秘密宗旨或教义、按照严格的秘密仪规从事地下活动的下层民间团体,由于各种秘密结社通常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活动,因而构成了一个外人不易了解、官方不易控制、正常社会秩序难以容忍的群体,人们通常称之为“秘密社会”。
秘密社会中通常有会党与教门之分。会党以天地会为主体,活跃于福建、台湾、两广和长江流域一些省份,小刀会、三点会、三合会、仁义会、江湖会等名目是它的支派。教门主要流行于中国北方各省,例如白莲教、天理教、一贯道、八卦教、义和拳、大刀会、红枪会等。
秘密社会史的探讨从清末一直延续到现在,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搜集整理了一批海内外珍贵文献,并就天地会的起源等问题展开讨论。五六十年代,这一讨论又与明清易代史、农民战争史研究相结合。80年代以来,除原有问题展开新的争论外,并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来分析会党的形成与发展,注重档案资料、秘密会社内部文献的发掘与利用,研究议题已扩大到各种秘密会社组织的形成、内部结构及其影响。已有数篇综述涉及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研究。[※注]本节在借鉴上述成果的基础上,对该领域研究成果进行补充并重新梳理。
(一)研究历程
远在辛亥革命时期,陶成章就著有《浙案纪略》,专附一篇《教会源流考》,概括了白莲教、天地会两大秘密团体的源流和派别,这是中国较早研究会党史的著作。五四运动之后,尤其是三四十年代,出现了数部有关会党的论著和资料集。首先,发现并出版了一批秘密社会的内部文件,例如1934年发表的广西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1935年出版的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注],1937年发表的《守先阁天地会文件》以及一批记述天地会的历史、组织、规条、口号等内容的《海底》《天地会文献录》,[※注]这些史料为展开会党的研究提供了依据。第二,罗尔纲、萧一山、周贻白、王重民等学者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出版了戴魏光的《洪门史》、朱琳的《洪门志》等著作。[※注]这些书大都以介绍会党的内部组织、帮会分布、信仰、礼节、堂规、旗帜等方面的内容为主,基本属资料性图书,但也有一些分析和考订,有些记述颇为珍贵。如《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一书是萧一山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抄来的天地会秘密传世文件,附有图像、碑亭、腰凭、旗帜、洪门会场图等,另有联络、传帖、符咒、隐语等,史料价值很高。罗尔纲在1943年整理出版了《天地会文献录》,并结合清朝刑法的制定和人口增加与土地兼并问题阐述天地会的起源,富有启发性。
解放以后,在革命史观的指导下,大陆的农民战争史研究蓬勃兴起,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五朵金花”之一。秘密社会作为下层群众的组织,得到了较高的评价。在基本肯定秘密社会革命性的同时,学者们也尝试着分析秘密社会的起源、成分和性质。秘密社会史研究已经起步,但尚未充分展开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基本上仍为革命史观的“注脚”。
这一阶段出版的资料有《天地会诗歌选》《上海小刀会起义》《金钱会资料》《南通军山农民起义史料》等。[※注]发表的专著有《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论晚清两广的天地会政权》《苏松太会党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等。[※注]值得注意的是,60年代初,大陆学者就会党问题展开了学术争鸣。参加讨论的有荣孟源、俞澄寰、郭毅生、戴逸、魏建猷、袁定中、邵循正、陈守实等人。争论问题主要集中在会党的成分、会党的性质两个方面,其中出现了许多非常好的见解,例如荣孟源、魏建猷、邵循正对天地会成分和性质的分析,陈守实对明末遗老创立天地会的传统观点的批判。这期间,蔡少卿于1964年发表的《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一文,在吸取这些学术观点的基础上,他力排众议,独辟蹊径对天地会的起源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探索,主要表现在:(l)确定天地会创始人是福建漳浦万提喜(即洪二和尚);(2)提出了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二十六年的新观点;(3)在研究方法上,把注意力集中在档案资料方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秘密社会史逐渐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受到了更多学者的重视,并且取得了空前的成果。除了以往比较关注的天地会、白莲教以外,其他各种民间教派、会党组织也纷纷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整体研究和微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80年代,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关于秘密社会的史料和工具书。如《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自立会史料集》《广西会党资料汇编》《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联合编辑出版的《天地会》是内容十分丰富的天地会资料书,共计七册,240余万字。[※注]魏建猷主编的《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和《中国会党史论著综录》对1983年以前发表的论著作了提要说明。[※注]这些工作是一项重大的基础工程,为中外学者的研究工作带来极大便利。
80年代起召开了几次秘密社会史方面的学术会议,起到了整合人才队伍、营造专业氛围、沟通学术信息、推进深入研究的作用。1984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中国会党史讨论会,这次会议讨论了会党的起源、性质、地位、作用等问题,会后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关于会党史研究的专题论文集。这次会议还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会党史研究会,这标志着中国秘密社会史已经形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1988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届中国会党史讨论会,会议讨论了会党的阶级结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民国时期的帮会以及会党与其他民间结社的关系问题。1993年,在南京召开了秘密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80年代前期,一些学者就秘密社会史相关问题撰写文章,展开争鸣。到80年代后期,蔡少卿出版了《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和《中国秘密社会》等专著。90年代,濮文起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马西沙、韩秉方的《中国民间宗教史》,周育民、邵雍的《中国帮会史》,秦宝琦的《中国地下社会》第二卷《晚清秘密社会》,胡珠生的《清代洪门史》等专著相继出版,掀起秘密社会史研究的小高潮。进入21世纪,路遥的《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彭先国的《湖南近代秘密社会研究》,刘平的《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谭松林主编的《中国秘密社会》,吴善中的《晚清哥老会研究》,欧阳恩良的《形异神同:中国秘密社会两大系统比较研究》,梁景之的《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雷冬文的《近代广东会党——关于其在近代广东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秦宝琦的《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和《中国地下社会》第三卷《民国会道门与黑社会》,秦宝琦、孟超的《秘密结社与清代社会》,邵雍的《中国近代会党史》,刘平的《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邵雍的《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邵雍编著的《中国近代会道门史》,高鹏程的《红卍字会及其社会救助事业研究(1892—1949)》,刘平主编的《洪门与辛亥革命丛书》等专著比较集中地在十年间出版,将秘密社会史研究推向高潮。[※注]
80年代至今的三十来年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一些研究团队和研究骨干。比较大的研究团队有上海师范大学的魏建猷及其弟子;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蔡少卿及其弟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秦宝琦及其弟子。他们或是对秘密社会史各专门领域展开论述,或是集中力量撰写秘密社会通史性著作。山东大学的路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西沙、韩秉方和天津社会科学院李世瑜、濮文起等主要致力于中国民间宗教的文献和田野研究。胡珠生、赫治清等在这一领域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经过一百年的积累,秘密社会史研究领域所取得了丰硕成果,梳理出了秘密社会的基本系统、内部结构和组织文化、大致的发展历程,以及秘密社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活动。
(二)主要议题
1.天地会的起源与性质
90年代之前,天地会的起源与性质是秘密社会史研究的中心内容。关于天地会创立时间有十多种看法,影响较大的是“康熙甲寅说”(1674)和“乾隆二十六年说”(1761)两种观点。
“康熙甲寅说”的首倡者罗尔纲。1932年,广西贵县修志局在搜集当地史料的过程中,发出了一批天地会秘密文件,罗尔纲将这批文件抄录下来,后来,他先后发表《〈水浒传〉与天地会》等文,提出天地会是在康熙十三年由汉族反清志士创立的。[※注]20世纪80年代,赫治清发表了《略论天地会的性质》等文,多方面地论证了“康熙甲寅说”,他的主要依据是“西鲁传说”和“严烟供词”。[※注]
1964年,蔡少卿提出了乾隆二十六年说,他在《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一文中认为,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地区,乾隆二十六年由漳浦和尚万提喜创立。蔡的根据是清朝大使汪志伊上奏的《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注]20世纪80年代,胡珠生、赫治清、张兴伯、陈旭麓等纷纷提出异议,他们指出:不应置大量天地会传说史料于不顾;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档案大都散失,不能排斥目前未发现但能证明天地会出现早于乾隆时期的档案;汪志伊的说法缺乏根据;洪二和尚和洪二房和尚不是同一个人,也许洪二房和尚是天地会一批创始人的总代称;涂喜与朱鼎元、李姓及马九龙之间的关系不清楚。20世纪80年代,秦宝琦连续发表文章支持“乾隆二十六年”说,他依靠新发现的档案资料指出:涂喜就是提喜,也就是洪二和尚;汪志伊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其根据就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接任闽浙总督的伍拉纳与巡抚徐嗣曾审讯行义和陈彪之后向清政府上报的奏折。
在天地会的性质问题上,影响最大的是“反清复明说”与“团结互助说”。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对“反清复明”观点进行了广泛渲染,产生了很大影响。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一文中指出,洪门是因明太祖年号而取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20世纪三四十年代,罗尔纲、萧一山、周贻白分别写了《〈水浒传〉与天地会》《天地会起源考》《洪门起源考》等文,都认为天地会是明朝遗民或郑成功创立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团体。[※注]罗尔纲的“反清复明”说和陶成章等人是有区别的,他通过对史料的研究来得出结论,故这种观点有许多支持者。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学界对天地会的性质展开了讨论。荣孟源等人拥护天地会创于康熙十三年的说法,认为反清复明是它的政治纲领。[※注]戴逸曾试图打破这个传统观点,把它的出现和该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从而提出天地会较多地反映了城市平民阶层的要求。魏建猷指出天地会的成分大多为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注]邵循正指出天地会的阶级成分仍然以破产农民、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和流氓无产者为主要成分,因此,把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起来是不妥当的。[※注]
70年代末以来关于天地会的性质又起争论。秦宝琦指出:天地会系明朝遗老为“反清复明”而创立的论点,并无确凿的史料根据;在现存史料中,未见有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的记载;这个口号只是在嘉庆初年才在天地会逐渐出现。这些关于天地会性质的讨论,注意使用计量统计的方法,如蔡少卿分别对乾隆、嘉庆、咸丰年间和辛亥革命时期天地、江湖会成员身份的统计,秦宝琦对天地会创立初期漳浦卢茂起义成员的身份统计,更加实证地揭示了会党的阶级结构。陈旭麓指出:天地会是基于政治上的抗清要求而产生的,但是经济上的互助要求才是它长期活动和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有学者指出,天地会起初主要为了互助,后来了为适应组织发展和反抗清统治者镇压的斗争需要,提出了“反清复明”一类口号,逐渐带上了政治色彩。[※注]
2.秘密社会的变迁
中国近代秘密社会本身的演变,最主要的成果为2002年谭松林主编的《中国秘密社会丛书》。[※注]曹新宇、宋军和鲍齐撰写的第三卷《清代教门》和仲伟撰写的第五卷《民国会道门》论述了教门的演变。《清代教门》指出,清代是秘密教门充分发展的时期,不仅名目繁多,信徒剧增,而且有些是新出现的,如九宫道、在理教、大刀会等。作者认为在晚清,随着民主革命的兴起,秘密教门逐渐开始向会道门转化。《民国会道门》论述了民国时期有关会道门组织内幕、戒规、活动以及发展演变过程。欧阳恩良和潮龙起撰写的第四卷《清代会党》和邵雍撰写的第六卷《民国帮会》论述了会党向帮会转化,帮会向黑社会转变的过程。《清代会党》讨论了哥老会与近代湘军的关系,也指出,咸同年间粮船水手中的罗教信徒正式形成了青帮,辛亥革命时期秘密会党急剧分化,除少数会党首领接受革命党人的引导,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外,大多数会党仍然从事打家劫舍或杀人越货的活动,有些还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开始向黑社会转化。《民国帮会》指出,民国时期的秘密会党,大多衍化为黑社会,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许多帮会首领成了军阀或外国侵略势力的鹰犬,有些本身就成了军阀、官僚,后来又与国民党相勾结反对共产党,一些帮会头子成了国民党的“党国要人”,大多数帮会组织变成了黑社会。
秦宝琦的《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系统论述了清末民初秘密教门如何从以下层群众为主的结社组织蜕变为以官僚、地主、商人为主的会道门;部分秘密会党如何从下层群众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的结社组织蜕变为黑社会组织。[※注]秦宝琦的《中国地下社会》第三卷《民国会道门与黑社会》认为,民国年间的洪门,来源于清代的天地会与哥老会,青帮也来源于清代漕运水手中的行帮组织——安清道友等。不过,民国年间的洪门或青帮,均已经不再是下层群众的互助和抗暴性质的组织。有的蜕变为军阀、官僚的工具,有的蜕变为黑社会组织,只有从海外洪门衍化来的中国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民国年间的会道门也是同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不仅表现在两者大多有组织方面的渊源关系,而且会道门歪理邪说也大多来源于秘密教门的基本教义。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所处的历史背景有所不同,因此,其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也就必然有所区别。民国初年的会道门,则成为官僚、军阀聚集实力,角逐政坛的工具,或成为具有政治野心的教主企图建立神权统治的工具,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会道门中大多数投靠日本侵略者,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注]
郑永华、赵志的《近代以来的会道门》一书概论了民国时期多种形式的会道门,说明会道门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具体环境下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功能。认为会道门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多种矛盾交互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极其深刻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也有其自身的文化根源和悠久的历史传承。[※注]
吴善中的《晚清哥老会研究》认为,哥老会起源于川黔等地,并无明确的政治主张或种族意识的嘓噜。该书认为在从嘓噜向哥老会的演变过程中,边钱会、青莲教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湘军内部早就存在的盟誓结拜、结为“兄弟兵”的风气对哥老会的迅速发展有重要意义;在同治年间哥老会已经首先在两湖地区崛起;而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迅速蔓延与扩张是在同治、光绪年间,其中游兵散勇、客民、盐枭等势力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注]
刘平的《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主要从文化角度着眼来研究清代的秘密会党与秘密教门。从哥老会自身的体制、经典文献、隐语传播、偶像崇拜以及举行仪式的地点等问题入手,分析了哥老会所载的《十条》和《十款》的内容以及象征意义。刘平认为,包括哥老会在内的会党与秘密教门一样,也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会党分子尤其是头目更多的是一些流氓无产者,他们以江湖义气相标榜,以巫术、宗教等手段固结人心。大多数秘密社会的叛乱,尽管其思想信仰中包含明显的反政府倾向,但一般都旨在敛钱、抢劫,因而也应归类于反社会类型。[※注]
刘平的《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从宏观层面探讨中国秘密宗教的基本内涵,认为,民国时期,民间教派演变为会道门,并形成自身武装(如大刀会、红枪会),与各种政治势力折冲樽俎,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扫除旧的社会势力,取缔会道门成为一场运动。然而会道门旧势力并没有真正消失。[※注]
梁景之的《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关注清代民间宗教的结构性研究,力图在信仰体系构成、宗教群体构成、宗教修持和体验、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关系四方面,勾勒出清代民间宗教实况。[※注]
欧阳恩良的《形异神同》比较了教门与秘密会党的共性与个性,考察了秘密社会成员的入教(会)心态、情感意识与伦理价值取向;以数据明确了秘密社会成员的构成以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组织发展状况;比较了教门与会党之间的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机制;探究了秘密社会与民间文化、民俗事象的解释。[※注]
3.秘密社会与近代政治
中国秘密社会与中国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很长时间都是在革命史、政治史视角下展开,因此秘密社会与近代政治是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会党与太平天国。许多学者认为,会党起义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党的积极作用主要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会党活动掩护了拜上帝会的活动,鼓舞了太平天国起义领导人的信心,为太平天国起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二是会党通过发动起义和直接加入太平军,减轻了清军对太平军的军事压力,壮大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声势。不过,1978年,蔡少卿撰文指出,太平天国后期,在处理与天地会的关系方面没有统一的政策,双方合作的好坏取决于各地将领和当地天地会的态度。
会党与教案。20世纪50年代,李时岳撰文指出,在1884—1894年,会党成了反洋教运动的核心力量或主导力量。有学者在研究了1891年长江流域的反洋教斗争后,认为哥老会在传递、散发反洋教宣传品、预谋申连、组织发动长江中下游地区群众反洋教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82年胡汉生撰文指出:哥老会是余栋臣发动武装反洋教斗争的桥梁和纽带,也是起义军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余栋臣提出的“扶清灭洋”口号中的“扶清”很难被致力于反清复明的哥老会所接受;大量流氓无产者涌进哥老会,不断腐蚀和破坏着起义军的队伍;余栋臣有效地利用了哥老会组织,又被这个组织束缚住手脚,最终导致了起义的失败。
会党与辛亥革命。许多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开始与资产阶级革命派互相联合、互相渗透,其反抗封建统治的积极作用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联络会党不断发动起义为武昌起义做了准备,武昌起义的胜利,不只是取决于新军士兵的发难,同时也是会党群众和响应的结果。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在肯定会党在辛亥革命的积极作用时,还要看到它的许多消极面。有人认为会党的种种弱点在辛亥革命时期表现得很充分,实际上起了降低革命派组织的政治水平、扰乱社会治安、为旧势力所利用等消极作用。1982年,杜德凤撰文指出,会党这种落后性的组织又往往容易被地主豪绅势力所操纵,加上他们带有盲目的破坏性,因此有的会党变成了反动力量。
由刘平主编的《洪门与辛亥革命丛书》对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证。该丛书包括李恭忠、黄云龙的《发现底层:孙中山与清末会党起义》,孙昉、刘旭华的《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外一种:辛亥革命时期洪门人物传稿》,孙昉的《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与欧阳恩良的《西南袍哥与辛亥革命》。[※注]《发现底层:孙中山与清末会党起义》重点描述了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起义、自立军起义、1906年萍浏醴起义与1907—1908年粤桂滇大起义中会党与革命的关系。《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主要说明了哥老会在西北地区拓展空间的过程以及同盟会与西北哥老会关系的演变过程。《西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认为:西南袍哥的生存发展与这一地区传统的社会组织习俗紧密相关。《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认为海外洪门对辛亥革命做出了极大的奉献,却未能得到应有的政治回报和待遇。
《民国会道门》认为民国初年,秘密教门仍坚持维护和要求复辟君主专制,反对共和政体,许多教门首领还与清朝遗老的宗社党相勾结,企图推翻民国政府,复辟清朝统治;“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教门首领们又大肆诋毁民主与科学,宣扬迷信和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并且迎合失意军阀官僚的需求;抗日战争时期,会道门头子又与日本侵略势力相勾结,充当汉奸;解放战争时期,会道门头子与国民党特务相勾结,反对人民革命。
邵雍所著《中国近代会党史》,从横向上来说,作者借助会党在近代中国产生、发展、消亡这一主线,勾勒出会党在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与历届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将会党的兴起、分化及流变都投放于区域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是该书的重要特色。为了凸显太平天国时期会党运动的区域化特征,作者特意精选闽南小刀会、上海小刀会、两广天地会、湖南“征义堂”、江西“边钱会”、浙江“金钱会”、台湾“八卦会”等区域性的会党起义为研究个案,如此安排既反映了整个会党群体的共性,也展示出这些组织的地域不同时期存在的较大差异。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会党群众一贫如洗、一无所有,往往比其他人更倾向于使用非法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同盟会联络会党进行武装起义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会党在与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斗争中有过比较积极的表现,也有不光彩的阴暗面。会党毕竟是少数人的利益集团,其政治的责任感与方向感比较模糊,这就注定了它具有极强的游离性和善变性。”[※注]
邵雍编著的《中国近代会道门史》重点探讨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会道门在中国近代各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表现,用较多的篇幅重点论述了各种会道门的组织结构、社会功能以及政府、会道门群体、民众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潜在紧张和社会矛盾。作者注重史料挖掘,力求展开细密的实证研究。[※注]
邵雍的《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共分“秘密社会与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时期的秘密社会”“中国共产党与城乡秘密社会”“秘密社会与土地革命”“秘密社会与抗日战争”“秘密社会与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秘密社会走向没落的“最后的较量”七章,将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一直下延到现当代。作者充分注意到秘密社会中帮会与教门两大部分的平衡,加强了对后者的研究,其中关于悟善社、宗教哲学研究社等内容在其他学术著作中多语焉不详,大同民主党则未被提及。本书的亮点是关于中共与秘密社会关系的论述。作者利用新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相关档案资料,第一次较为完整地介绍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对秘密社会的观点及其策略的变化。作者认为秘密社会对中国革命从组织、过程到结果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作者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秘密社会工作上的一些失误,认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和红军对加入革命队伍的帮会警惕不够、改造不及时还只是个别地区局部存在的问题。在全局上,党组织和红军在帮会工作方面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左”倾偏见,犯了“左”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中共在处理与秘密社会的关系上,从最初的缺乏经验到后期的游刃有余,也为其政权的稳固奠定了基础。[※注]
4.秘密社会的区域性
秘密社会在空间上总是与某些特定空间相联系,秘密社会史研究或多或少都具有区域性,加之史学领域内宏观论述逐渐走向微观史学,越来越多的学者注重从区域性视角探讨秘密社会史。两湖哥老会、抗战时期山东秘密社会、山东秘密教门、福建秘密社会、湖南秘密会党、广东秘密会党等,都有学者进行专门探讨。
彭先国的《湖南近代秘密社会研究》较系统地阐释、解读了湖南会党百余年的发展历史,探寻湖南会党在近代历史上发生、发展的基本特点与规律。该书交代了天地会与哥老会在湖南的交替以及湖南哥老会的组织特点与活动规律,指出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湖南哥老会占山据地,开始向集团化方向发展,成员结构也趋于本地化。该书分析了士绅与会党、近代型知识分子与会党相联络合作的历史动因、成败得失。[※注]
雷冬文的《近代广东会党——关于其在近代广东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分析了咸丰年间广东天地会的反清起义、广东天地会与外国侵略者及广东士绅的关系,以及广东天地会与太平天国的关系。该书还论述了广东会党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反清斗争,民初广东会党与革命党冲突的原因、特性与功能,并探讨了广东会党的匪化问题及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广东会党与孙中山的进一步合作及会党与工农运动的关系,抗战中广东会党的分化,解放战争时期广东会党的极端化发展变化。[※注]
路遥的《山东民间秘密教门》既是一部详尽的调研报告,也是一部严密的学术著作。其中以大量的调查资料对一炷香、八卦教及其分支离卦教、九宫道、一贯道、一心天龙华圣教会、红枪会等九个重要教门的历史做了深入的分析。该书勾勒了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历史与概况轮廓,解读了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制定的许多灵文、咒语或法语。[※注]
梁家贵的《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秘密社会研究1937—1945》认为,国民党为了巩固其一党专政、排斥打击其他政治势力尤其是中共力量而拉拢利用秘密社会,中共从全民抗战的立场出发,积极团结、争取它们抗日,并在斗争中改造它们,而日本侵略者则利用、操纵山东一些教门、帮会势力,充当汉奸鹰犬,残害民众,围剿抗日力量。
邵雍的《近代江南秘密社会》梳理了近代江南的秘密社会的变迁脉络,认为上海是秘密社会聚集的城市,根源在于其发达的商品经济为贫民提供了生存的机遇。江南多种多样的会道门平等相处,其在江南社会的工业化转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该书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学界的认识,即近代江南的秘密社会主要扎根在城市,而非贫苦的乡村。[※注]
近代秘密社会史研究最初主要依据秘密社会本身留下的会簿宝卷等文件从内部着手研究秘密社会本身变迁的历史。秘密社会内部流传下来的文本,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流变,其中的一些内容已变得不很准确,也不能准确反映时代特征。
20世纪60年代初,从社会等因素分析秘密社会的研究路径开始兴起。这种研究路径使秘密社会史研究发生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跳出秘密社会内部的文本和传说,以社会经济变迁为背景,从外部各方面对秘密社会的记录、观察和评论入手,来研究秘密社会本身的变化,二是研究秘密社会与外在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蔡少卿的《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一文,从档案入手,兼顾地方志、时人的文集和笔记、报刊、回忆录、外文记载,还亲自访问一些健在的当事人,进行社会学式的分析,即反映了上述趋向。受时局的影响,这种趋向深受革命史观的影响。比较关注秘密社会的性质和历史地位,多强调其作为下层阶级的互助组织,突出其在“反封建斗争”中的积极作用。
80年代,社会史复兴的大背景下,才真正实现从社会等因素分析秘密社会。城市化、移民、游民、传统文化、区域社会文化环境与秘密社会兴起、发展的关系,秘密社会与近代政治、社会变迁的关系等内容被纳入研究的范围。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