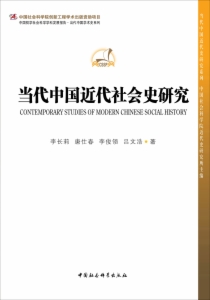三 交通方式
|
来 源
:
|
当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4 | ||
|
摘 要
:
|
交通工具由西方引进机械动力而取代中国传统自然动力的过程,带来了中国近代交通革命,深刻影响了人们出行流动方式与范围,改变了人们社会生活节奏与内容,成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近代交通变革及其与社会生活关系受到较多关注,出现了较多研究成果。张伟指出,抗战前重庆市内交通以小轿、滑竿、人力车、木渡等交通工具为主,抗战时期是重庆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黄金时期,主要表现在公共交通线路、公共交通工具数量的增加和城区道路的修建、改造以及轮渡码头等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关于近代交通发展已经有了一批研究成果,但对交通与社会生活变迁的关系尚缺乏较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 | ||||||
|
关键词
:
|
公共汽车 公共交通 人力车 交通工具 交通 城市公共交通 电车 城市交通 国民政府 事业 铁路 |
||||||
在线阅读
三 交通方式
字体:大中小
交通工具由西方引进机械动力而取代中国传统自然动力的过程,带来了中国近代交通革命,深刻影响了人们出行流动方式与范围,改变了人们社会生活节奏与内容,成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近代交通变革及其与社会生活关系受到较多关注,出现了较多研究成果。
已有对近代交通的综合研究,苏生文《中国早期的交通近代化研究》一书,对船舶航运、铁路火车、公路汽车等交通近代化变迁作了综合考察,并对城市交通近代化过程中乡与城、私与公、旧与新、弱与强、华与洋等几类矛盾作了分析。[※注]刘莉指出,近代人们的出行生活经历了从传统旅行交通到新式旅行交通的演变,在经济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交通客运业、人口迁移及旅游业等方面;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则体现在提高了生活质量、改变了生活观念,并与社会风气的变迁紧密相连。另外,旅行交通的演变在以新代旧的主流趋势之上,呈现出艰难性、地域差别性以及新旧并陈、中西并存的独特而显著的特点。[※注]李长莉认为,近代交通工具的革命产生了多方面的社会文化效应:人们的出行更加快捷、舒适、方便,对人们认识并接受近代工业科技起到了一定的启蒙和先导作用;人们的出行频率更高,人数更多,社会流动增大,扩大了公共活动空间,促进了公共活动,为近代公民社会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人们的出行方式商业化程度大增,因而也更趋于平等化、大众化,以往的等级色彩趋于淡化,促进了人们的平等意识;交通工具发展的不平衡也拉大了城乡出行方式的差别,形成城乡新旧二元化的出行方式及城乡人眼界和观念的差别。[※注]
关于具体交通工具新旧交替对人们生活产生的影响,如铁路,阚晨霞指出,1906—1915年的《申报》有大量报道铁路“反日常”现象,事故、犯罪等“不安全”,售票、开行制度等“不便利”,设施和管理的“不舒适”,是三个基本因素。铁路“反日常”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铁路建设过程中损坏民众利益的恶政以及战争、匪患等,自然灾害与疾病也会造成“反日常”现象增多,而铁路系统自身存在的管理弊端、技术水平低下也是影响因素之一。[※注]徐涛考察了近代自行车的进口状况与传播过程,讨论了各时段中国人对自行车的反应,对引入初期“自行车技术源自中国说”的成因史料作了考辨,揭示东西方文明在器物层面上的碰撞痕迹,中国人面对全新技术的应对策略和认知水平。[※注]
交通近代化最为明显的是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这是城市生活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因此受到较多关注,出现了较多研究成果。鲍成志认为,19世纪晚期,新式公共交通在中国城市兴起以后,不断嬗递变更,成为推动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衡量城市兴衰发展的重要尺度。[※注]邱国盛认为近代中国城市的“交通革命”从人力车开始,由于它的机械构造,廉价、快捷、方便、省力的特征使人力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轿子等旧式交通工具的超越,从而推动了城市公共交通向前发展。但人力车的存在和它与电车、公共汽车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毕竟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阻碍了城市公共交通早期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注]
除了上述对交通变革的综合性研究之外,还有不少对于特定城市或地域交通变迁进行考察。如交通近代化发展最早也最显著的上海,引起较多关注。陈文彬《1908—1937年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研究》一书,考察了清末民国时期上海中外公共交通企业的经营与管理,认为近代上海城市公共交通事业是在各种社会力量、利益主体的相互博弈中向前发展的。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构成了公共交通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变量,决定了上海公共交通近代化的路径和样式。他还对近代上海公共交通的结构与城市节奏变迁、上海公共交通与市民生活关系作了研究。[※注]何兰萍指出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为了维护交通秩序,通过强化交通管理人员的职能分工,健全交通管理机构,加强交通法规的颁布与执行等一系列措施对交通问题加以防范和解决,构建出一套具有近代意义的城市交通管理体系,控制并减少了交通意外带来的危害,创建了相对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租界当局在实施城市交通管理的过程中,传统的中国人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这种不适应性在文化、利益、民族矛盾等因素的交织作用下,逐渐上升为中西之间的碰撞与冲突,但最终还是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租界当局实施交通管理的过程,影响了辖区内乃至整个上海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性,培养了他们的规则意识和交通安全意识,促进上海及中国其他城市的近代化。[※注]
天津是继上海之后新式交通发展的城市,杜希英指出,天津随着新式马路、铁路的修筑和港口海运的发展,人力车、电车、汽车、火车等新式交通工具的传入,城市交通体系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对城市结构、人口流动、经济发展及市民生活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力地带动了天津城市的近代化。[※注]刘海岩认为,20世纪初天津引入电车,引发激烈的社会抗议,反映了演变中的城市社会接受外来事物的矛盾心态,以及对打破现存空间秩序的恐惧。最终,电车为市民所普遍接受,通车路线覆盖了五国租界和老城区,成为近代公共交通网络的中心,成为大众化的交通工具,加快了城市人口和资本的空间流动,促进了近代城市空间的重构。[※注]韩鹏考察了民国时期天津人力车业的兴起、发展、衰落以及所涉及的相关同业公会,探讨人力车业在天津近代交通中的价值与地位和对天津社会生活及城市近代化的意义。[※注]
北京虽然交通变革开始较晚,但由于其首都的优势,后来发展较快。李志红考察了北京公共交通发展的历史轨迹,公共汽车事业的经营状况,分析民国时期北京城市公共汽车事业的经营组织形式。指出北京城市近代化发展迟缓导致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滞后,制约了公共汽车事业的发展;政府公用事业经营模式上的弊端,策略失当,垄断经营公共汽车事业,限制了融资渠道,公共汽车事业的发展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同时指出尽管发展不足,公共汽车还是为北京城市旅游业和近代意识带来了一些影响。[※注]李玉梅考察了北京的市政建设、北京电车公司的创办过程、发展变化、经营状况、职工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兼营公共汽车以及电车与人力车的矛盾等方面,探讨北京电车公司在北京城市公共交通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并分析北京电车公司惨淡经营、缓慢发展的原因,从而透视出旧中国北京城市交通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注]
南京是北伐后国民政府首都,交通市政也有较大发展。吴本荣指出,清末以后伴随西式马车、人力车、火车、汽车等新式交通工具先后传入南京,新式马路、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相继修建,近代南京公共交通应运而生。近代公共交通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空间、城市管理、人口流动、市民生活等诸方面的改变,对南京的城市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注]李沛霖考察了清末至抗战前南京公共汽车、出租汽车、人力车业等公共交通业的票制、车辆、营业情况,观点如下:南京公共交通满足人口需求、均衡人口分布及促进人口流动,与城市人口产生良性互动;以公共交通业所缴纳的车捐为战前南京城市财政收入做出巨大贡献;订立交通法规、加强车辆管理、强化人员训练及改进交通设备,促进了城市管理;公共交通发展使时间观念的强化、城市意识的推进及生活质量的提升等,改变了城市生活。[※注]邢利丽考察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到南京解放前,南京城市公共汽车事业兴起的背景、发展情况、经营状况、管理情况和影响。[※注]李沛霖通过考察抗战前南京公共交通与生活空间、日常流动、时间观念和市民意识等城市生活方式的各方面交互联系,管窥两者间的交相作用,进而检视南京城市自近代向现代嬗变的真实场景。[※注]
重庆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交通状况也受到关注。薛圣坤指出,1933年重庆公共汽车公司成立,公共汽车作为一种新颖先进的交通工具开始在重庆市区运行,但发展缓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城市的工矿企业及大量人口纷纷迁入重庆,促使公共汽车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也存在一些局限。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由于缺少了中央政府财政支持,重庆城市公共汽车事业经营状况日趋恶化,到重庆解放前夕,公共汽车事业到了几乎无法正常经营的状况。作者指出重庆城市公共汽车事业的发展壮大是国民政府中央管理扶持的结果。[※注]张伟指出,抗战前重庆市内交通以小轿、滑竿、人力车、木渡等交通工具为主,抗战时期是重庆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黄金时期,主要表现在公共交通线路、公共交通工具数量的增加和城区道路的修建、改造以及轮渡码头等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注]
除了上述全国性重要城市之外,还有关于其他多个城市交通近代化的研究。李韬认为,民国初年广州市政建设的主要内容是电车事业,从创办之始的电车承办权风波,继而是十多年的惨淡经营,到30年代这种当时先进的公共交通方式最终与广州擦肩而过。广州电车事业的这段经历反映出在民国初年动荡与分裂的社会政治局势下市政体制的不断完善与前进。[※注]艾智科认为,清末民初,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的市政建设运动后,汉口城市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由于一批市政专家的合理经营与管理,汉口公共汽车在创办初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与此同时也隐藏着一些潜在的困难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凸显出来,抑制甚至摧毁了汉口公共汽车的进一步发展。尽管汉口公共汽车的初步兴办是一个简短的过程,但它却是市政建设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它促进了城市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公共汽车也与当时城市居民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联系,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联系也愈加紧密。[※注]朱君认为清代的成都交通处于由传统的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过渡转型时期,以人力为主的轿子逐渐向半机械的交通工具——人力车、自行车和全机械的交通工具——汽车转变,川汉铁路也在这个时期得到倡筑和动工。作者指出清代成都的陆路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并向四方呈放射性状的四条交通干路。19世纪末,从日本引进的人力车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在成都得到普及,传统的轿子在城市公共交通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该文也分析了交通对成都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包括对城市人口、物质、信息流动等方面的影响。[※注]余晓峰考察了民国时期成都公共汽车的经营状况、管理体制、道路建设以及影响作用等问题,认为公共汽车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城市居民的出门远行,促进了近代城市生活节奏和社会风气的转变。[※注]还有作者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审视近代徐州城市化进程。[※注]
另外,对区域交通发展与社会状况也有所研究。余建明考察了湖南近代交通发展的过程,并从经济变迁、政治变迁、社会生活变迁、思想观念变迁四个方面分析了交通进步对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广泛影响,论证了交通发展在湖南从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促进作用。[※注]章建指出,安徽自1912年津浦铁路首通,到20世纪30年代淮南铁路、江南铁路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初步形成了一个铁路运输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中安徽交通格局仅以东西向的水运为主,而缺乏连通南北重要孔道的局面。在铁路以及水运等交通方式的共同努力之下,近代安徽的运输局面为之一新,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变迁步伐。[※注]苏玉欣介绍了胶济铁路在德日占领下和北洋政府管理时期的营运情况及工人境遇,认为收归国有以后,胶济铁路的命运并无根本好转,考察了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状况和艰难发展历程。[※注]靳婷婷指出,河北地区1918—1937年的公路建设,经历了初步发展和快速发展两个阶段,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筑路方式,即商人修办、官方修办和以工代赈。全省公路建设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取得了一定成就,初步完善了公路管理体制,民营汽车运输业务和官办汽车运输业务得到拓展。公路建设不仅加强了河北省内外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还有效地带动了沿线地区商业的繁荣,给普通民众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带来新的变化,对社会风气和居住条件也产生一定影响。[※注]东北在近代是具有一定特殊性的区域,刘莉有三篇文章讨论近代东北交通演变与社会生活关系,指出近代东北,人们的“出行”生活经历了从旧式、传统的路、车、轿、马、舟,向新式、近代化行旅交通道路及工具的转变。这一演变极大地震撼和冲击着东北古老的生活方式,不仅改变着东北社会物质生活的内容和质量,同时也使民众的精神生活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变化。城市交通由步行为主的交通方式向集中的大众化公共交通转变。长期封禁之东北地区,因这一转变而产生的影响是十分鲜明而剧烈的。近代东北城市中公共交通体系的建构,对民众生活的物质层面及精神层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提升了民众的生活质量,推动了民众生活观念诸多方面的转变。[※注]
与交通发展相关的旅馆业也开始有研究者关注。龚敏考察了1912—1937年旅馆业的发展脉络,以典型企业经营实际和管理规则为样本,分析近代旅馆经营与管理特征及类型、等级和行业管理相关内容,试图比较清晰地勾勒近代旅馆行业发展的全貌。该文认为近代旅馆业在西式饭店的刺激带动下和中西式旅馆的探索中完成了传统旅馆业向近代旅馆业的转变过程。[※注]刘杨认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繁荣兴盛,旅馆业也已具备相当程度的现代化特征;另外,上海纸醉金迷的都市消费文化又与新式旅馆业互相影响,旅馆提供了除传统食宿服务外的越来越多的娱乐和享受,刺激并扩张了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消费,而这同时又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力之一。作为第三方的同业公会和市政府则在尽力维持行业的环境以及明细行业竞争的规则,试图以制度来控制这个行业的良性发展。正是得益于三方良好的互动,共同造就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独特的旅馆文化。[※注]
关于近代交通发展已经有了一批研究成果,但对交通与社会生活变迁的关系尚缺乏较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