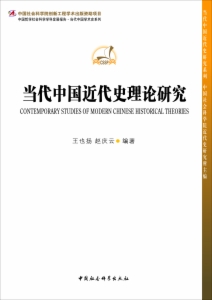二 “三次革命高潮”说解析
|
来 源
:
|
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 | ||
|
摘 要
:
|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叙事框架,深切地反映社会巨变。1954—1957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吸引了众多近代史学人参与,最终大体确定以“三次革命高潮”说作为叙事脉络,并以此构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关于这一讨论的学术背景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随着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中国近代史获得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前编纂的“单元式”或“专题式”的著作已无法满足教学科研之需,建立和完善近代史学科体系成为史学界的当务之急。 | ||||||
|
关键词
:
|
近代史 革命高潮 三次革命高潮 太平天国 学科体系 学术 学科 帝国主义 学界 时限 内因 |
||||||
在线阅读
二 “三次革命高潮”说解析
字体:大中小
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自1954年始,至1957年告一段落,历时三年。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将各方论文及情况介绍结集成《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出版。
历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进行历史分期实质上是人们为了“使自己的知识得到一种更简单的从而更有说服力的表述而把连续的历史内容依照从某种特定的角度选择的事实和一定的观念体系分为段落”。[※注]分期方式本身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解答,这种讨论存在分歧应在情理之中。同时应该看到,对于当时隐含于分期问题的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取得了一定共识,讨论者对于胡绳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概念普遍表示接受与认同。“三次革命高潮”说遂成为20世纪50年代所形成的唯物史观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核心话语和标志,其简单明了而又确实体现了胡绳所构建近代史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因“三次革命高潮”说写入了1956年高等院校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注],进而影响到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近代史通论性著作的编写框架。
在唯物史观学习如火如荼展开之际,阶级斗争观点及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观点被视为唯物史观的要义。翦伯赞明确提出:“把中国的历史贯穿在一条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主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主流上。”[※注]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胡绳提出以阶级斗争作为分期依据最后获得较多认同自在情理之中。胡明确表示:中国近代史著作就是要“通过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来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各个阶级间的关系发生了些什么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怎样地发展的”。[※注]
在胡绳构建的近代史“三次革命高潮”概念中[※注],所谓革命高潮,“乃是社会力量的配备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充分地表露出来的时期”。提出这一概念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注]。胡绳定义的“三次革命高潮”,具体表述是这样的:(1)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此时“中国社会内部还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历史的推动力量仍只能是农民这一个阶级”;(2)甲午战争以后,以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为标志,农民革命与资本主义思想虽然并存,但是彼此隔膜,互不相关;(3)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实行革命,在一定程度内进行了对工人、农民力量的发动。因此,历史发展的动力在这时期是集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注]
胡绳以“三次革命高潮”概念考察近代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低落,潮来潮去,在三个革命高潮的前后划分出四个低潮,从而具体分为七个段落:1840—1850年;1851—1864年;1864—1895年;1895—1900年;1901—1905年;1905—1912年;1912—1919年。毋庸讳言,“革命高潮”一词具有相当强的意识形态属性,胡绳将之引入学术领域,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概念。这也是本书前述所谓近代史研究与执政党意识形态“共用一套话语”的具体表现。
有学者注意到“三次革命高潮”说与其所本依的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的内在矛盾之处。将二者做一对比,可以看出“三次高潮”说实际上淡化处理了19世纪三个重大涉外事件——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其更多地呼应了“半封建”的一面,而较少涉及“半殖民地”因素,体现出以中国本土事件为核心的取向,与后来柯文所归纳的“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有某种契应。[※注]从接续学统的角度而论,研究“三次革命高潮”说与“中国中心观”在取向上具共通性,自有其启发意义。但有两点必须看到:其一,由美国学者柯文归纳的“中国中心观”(China Centered Approach)有其特定的指谓和语境,将“三次革命高潮”说与之简单对应难免似是而非;其二,胡绳对其理论诠释体系之凸显中国本土因素的倾向有明确的理论自觉。事实上,1954—1957年的分期讨论中,以西方侵略为主线还是以中国历史发展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诠释框架,曾引起激烈论争。“三次革命高潮”说是在政治与学术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由胡绳系统归纳而成,其提出并被广泛接受并非偶然,具有深层社会思想基础。
重视重大政治事件是20世纪50年代近代史研究者的共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即所谓的“八大事件”[※注]作为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当时无论怎样讨论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框架、基本线索、基本内容、基本走向,都不能脱离于此。但是,如果将此“八大事件”等量齐观、平均用力,则与新中国成立前蒋廷黻、陈恭禄、范文澜等人以事件史为中心的编纂体例类似,在胡绳看来,这种结构模式无疑缺乏系统性,不能突出近代历史的本质与主流。“三次革命高潮”说实际上从阶级斗争角度突出了“八大事件”中表征着人民反抗过程的几次事件。这种凸显中国本土因素的研究倾向,确乎与此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倾向有所不同。
为进行反帝爱国动员以救亡图存,因而1949年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多以中外关系为论述中心,侵华史、外患史、国难史、近代外交史之类著述,粗略统计,著作不下130部,文章约300余篇。[※注]当时大学的课程设置中,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外交史往往合而为一。蒋廷黻受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影响,视外交史为“中国近代史的最重要方面”[※注],内政兴革仅为外交的反映,其《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可以看作“外交史大纲”[※注]。金毓黻认为,“近百年内,中国内政鲜有可述,对外关系,实居主位”。[※注]即以胡绳而论,他虽力图兼顾列强侵略与人民反抗这“两个过程”,但其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仍以中西关系为研究对象,且偏重于“侵略”的一面。
随着1949年真正意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国人心底激荡着扬眉吐气的民族自豪感,凸显“中国”在近代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成为学人的潜在预设。追溯近代以来人民革命斗争历程,构建革命的谱系,论证新政权的历史合法性,成为意识形态层面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进而被有着浓厚“以史经世”情结的学人在某种程度内化为不言自明的共识。对于胡绳所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新中国成立初即有评论,批评其正面论述近代中国革命思想发展的梗概不够清晰,“使近代史中的革命思想的主流不够突出”。[※注]1958年5月,由近代史所学人撰著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学界一些人对此书进行了抨击甚至否定,批判这是一本中华民族“挨打受气史”,解放了的中国人民需要的是“扬眉吐气史”,此书有严重的方向性错误云云。[※注]
总之,在1954—1957年学科体系的构建中,从近代中国内部寻求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逐渐成为包括胡绳在内相当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共同倾向,而且他们对此是有相当的理性认识的。
首先,在侵略—革命的整体观照中,胡绳此时更为强调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一面,而有意淡化处理了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与毛泽东的思路吻合。毛泽东所云“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注],即蕴含了在中国社会内部寻求中国近代历史的主导因素之意。孙守任同样以毛泽东“两个过程”论为立论基础,但他的解读显然与胡绳有别。他明确提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使中国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并竭力保存其封建基础的过程在近代史中往往居于主导地位,“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外国侵略势力”,“外国侵略势力本身性质的变化及其对中国侵略性质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的变化”。他以“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性质、形势和深度的变化”为分期依据。[※注]范文澜则明确表示,“帝国主义拥有极大的优势,在民族战争成为主要矛盾时,它总是处于矛盾的主要面”,而“在国内战争成为主要矛盾时,封建主义也总是处于矛盾的主要面”。[※注]范、孙二人均将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最重要的界标,在他们看来,甲午中日战争标志着列强侵略方式的根本转变。孙守任的观点受到金冲及、戴逸[※注]、章开沅、黄一良等人批评;而以范文澜在学界的崇高地位,连续发表三篇关于分期问题的文章,应者寥寥,仅有李新赞同其意见。[※注]
其次,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说理论体系最终获得更多学者的认同[※注],也缘于对“劳动人民是历史主人”的认同。1949年5月范文澜先后在北京大学做《谁是历史的主人》[※注]、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室做《再谈谁是历史的主人》的讲话,均强调“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翦伯赞则说:“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史观,具体就是“研究劳动人民的生产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注]
基于此种思想,胡绳一再表示:“中国近代史是以中国人民为主体的。它不是以外国帝国主义者为主体的历史”,“也不是某些反动人物的历史”[※注];“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地看清楚中国近代史中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注]。他的“人民”定义,即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列: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清政府自身的兴革及其领导的几次中外民族战争,自然很难进入其关注的中心。孙守任强调列强侵略,黄一良问道:“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究竟应该是什么?究竟谁应该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角?”不难看出,“三次革命高潮”说突出了“人民”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尤其突出了劳动人民的革命作用,这成为它能够在当时获得广泛认同的基础。如邵循正所言:给予太平天国等劳动人民反抗斗争“以足够的地位和分量”,就可以阐明“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读者清楚地看出在凶悍的国外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封建统治势力双重压迫之下,中国人民并不是一味挨打的。这样,读者就不会感到中国近代中只是漆黑一团,而是处处有使人志气奋发的生动斗争的局面和可歌可泣的史实”。[※注]
最后,外因与内因的哲学关系也是当时学者考虑分期问题的一个重要依据。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注],这一哲学认知对参与论争的史家无疑有相当大的影响。而苏联历史学者德鲁任林明确表示:“并不是外力入侵本身,而是该民族对外力入侵的反应,而是历史过程之内的运动在此类条件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应在划分历史时期时被当作复杂的(但究属次要的)因素予以注意。”[※注]几乎所有批评者都认为孙守任过于强调外力影响:金冲及认为孙守任“以外来因素的演变发展代替了内在历史规律的分析,而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来”[※注];戴逸认为孙守任抛弃了毛泽东《矛盾论》中“关于外因内因相互关系的论点”,而“我们不能把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不加区别地等同看待”[※注];毛健予认为孙的观点“令人感到有强调外因论的浓厚的色彩”[※注];李荣华虽然提出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加深、崩溃为分期标志,对西方的因素比“三次革命高潮”说稍多重视,但亦认为孙守任“强调了外因作用相对冲淡了内因的作用”[※注];章开沅指出,孙守任“忽视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必须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的规律而发生作用”[※注]。可见当时学者在外因内因的辨析下,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已然形成相当一致的倾向。到1958年“史学革命”兴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争被归结为“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孙守任的分期观点则被批判为“厚帝国主义薄中国人民”的“外因决定论”,走上了“客观上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的道路”[※注]。
概而言之,20世纪50年代的论争者均秉持革命史观,均以马列经典著作为自己立论的理论支撑及批驳他人的理论武器,却因着眼点差异而说法不同。近代中国的西方因素应置于什么样的位置这一问题,隐含于分歧之中。胡绳以“三次革命高潮”说来审视中国近代史全局,突出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反抗斗争,将之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根本推动力量。封建统治者与列强的矛盾则被淡化处理,二者“相勾结”的一面得到更多注意,而由清朝统治者主导的几次对外民族战争自然难与太平天国、义和团相提并论[※注];歌颂人民革命的主体伟力,使得外力的影响只能居于次要的地位。
“三次革命高潮”说当然远远无法涵盖近代史的丰富内容,与此前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架构相较,这一理论架构系统性得到加强,阶级斗争色彩愈加浓郁,阶级革命所占分量更重,农民的历史地位与主体价值进一步突出。胡绳提出分期问题,其初衷是想改变既有近代史叙述“政治史内容占了极大的比重,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这一偏颇。但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近代史诠释体系由于过分突出阶级革命,势必导致“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的历史成了一元化的线性公式”。[※注]总体来说,胡绳欲丰富、扩充近代史论述内容这一初衷并未达成。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曾号召对近百年史先分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进行专门研究,在此基础上再做综合研究。而“三次革命高潮”说只突出了阶级革命,近代史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无从落实。
正是现实中居于强势的阶级斗争理论及实践,使得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最终胜出,以至在后来近代史通论性著作编撰及研究中将之奉为圭臬。在“三次革命高潮”说诠释体系规范下的近代史研究,基本忽视统治阶级为应对危局的自身变革,如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等历史内容完全被摒弃于研究者的视野之外。其歌颂革命的价值取向,亦导致对于暴力革命的过分揄扬和对于改良运动的过度贬抑(尽管胡绳曾把戊戌维新列为第二次革命高潮的一个特征,但改良作为革命的对立物实在难有肯定之处)。其与意识形态绾合过于紧密,也必然影响甚至制约科学研究的学术性质。而当不同的学术观点受到政治批判,“三次革命高潮”说被综合大学、高等师范文史教学大纲采纳并在教科书中加以贯彻之后,中国近代史的诠释体系日益定于一尊。
1956年由邵循正执笔拟定的高等院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注],大体依照近80年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之间矛盾的交相演变,以及由此导致的近代人民革命三大高潮——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将中国近代史分为三个时期:1840—1864年、1864—1901年、1901—1919年。此后,高等院校历史系所编撰的中国近代史讲义及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专著,都以《大纲》为依据,以三个时期安排篇章论述史事,同时或多或少增添了一些近代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内容。
平心而论,5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新兴学科,整体水平尚低,对纷繁的近代史事有所优先侧重,集中有限的研究力量重点突破,亦无可厚非。但是,其所有理论构想几乎都难逃被僵化、教条化的宿命。从后来近代史学界的学术专题研究来看,绝大部分的研究著述均集中于“三次革命高潮”,近代史领域的三个专题学会分别为太平天国学会、义和团学会、辛亥革命学会。在现代学术体制里,学会对学术研究的引导与推动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体制化的影响之下,其他史事,甚至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都未能获得应有的重视。[※注]据姜涛统计的《历史研究》所载论文情况分析表,不难发现50—60年代学界对“三次革命高潮”(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与辛亥革命)的热衷及对其他史事的相对忽视。[※注]“文化大革命”前出现的几部影响较大的近代史通论性著作,“虽然都有自己的学术特色,但是就编撰的基本思路以及编撰体例和编撰内容来说,都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学科理论的影响”。[※注]“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成为中国近代史著述不变的叙事公式。
这种具有“范式”意味的近代史叙事和诠释体系,成为“社会环境等外界因素影响历史学家个人的中介”,并“借助学术发展机制自身的力量顽强存在”。[※注]以辛亥革命史研究为例,革命史研究模式的基本理论预设,一方面使辛亥革命史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同时也带来视角、方法的极大局限,使研究者难以放眼四顾、能动钻研。扬下层民众、抑资产阶级的价值尺度,使得对资产阶级的研究与其在辛亥革命中所处的位置并不相称。至于立宪派及立宪运动,虽然范文澜曾指出,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具有两面性,既“参加革命同时又破坏革命”,并明确表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共同的行动”。[※注]但由于革命史研究模式中将革命与改良片面对立,立宪派和立宪运动在当时的诠释体系中基本上被定性为“反动”,难有细加探讨的余地,自然少人问津。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