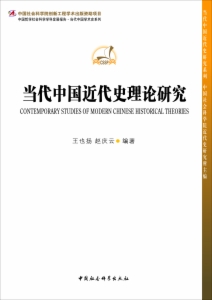一 关于太平天国研究
|
来 源
:
|
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2 | ||
|
摘 要
:
|
近代史之于当代史学理论,因为“近”而关系密切。而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却作为两次革命高潮而给予完全的肯定,这实际上是把农民运动当成了近代史的主流。在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起义已是旧式农民战争的尾声。洋务运动作为太平天国起义的反动,是统治集团的部分人企图采用西方技术挽救垂死的封建制度所作的努力,但是它在客观上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陈旭麓分析了洋务派在引进、学习西学时的口号“中体西用”,指出“这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在中西文化两极相逢的矛盾中第一阶段的结合形式,是以以新卫旧的形式来推动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口号。 | ||||||
|
关键词
:
|
太平天国 资本主义 平均主义 近代史 资产阶级 洋务派 民主主义 农民 资产阶级革命 田亩 地主 |
||||||
在线阅读
一 关于太平天国研究
字体:大中小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方面,然而在阶级斗争极端化的政治氛围下,农民起义被任意拔高,洪秀全也被说得神乎其神,太平天国历史的本来面目受到严重歪曲。进入新时期,学者们终于能够把虚悬的“天国”重新拉回到历史的真实中来。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造反不等于革命,农民起义,包括太平天国起义,也不能称为革命,因为旧式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旧式农民起义不可能实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他们既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上层建筑,也不可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上层建筑。[※注]这样来看太平天国运动性质的意见,给人以崭新的理论视角。在除去“神”的外衣后,对洪秀全的评价就比较一致了。人们看到,洪秀全的确是太平天国的领袖,在太平天国前期,可以说没有洪就没有太平天国。但定都天京以后,他的帝王思想、保守思想、享乐思想急剧发展,很快变成高高在上、居于深宫的封建帝王,政治上陷入权力之争和内讧,组织上搞严重的宗派主义,军事上表现了僵化和保守,思想上则完全沉溺于宗教迷信,导致太平天国由盛到衰,最后失败。人们还特别强调要正视洪秀全的错误,从中吸取有益的历史教训,起到知往鉴来的作用。[※注]
李泽厚是“文化大革命”后最早对太平天国问题“再思考”的学者之一,他发表在《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的论文《太平天国思想散论》影响较大。关于“太平天国与拜上帝教”,他认为“从意识形态看,太平天国有其非常鲜明的特色,它穿着宗教外衣,表现了农民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地主阶级进行空前的思想反抗和暴力冲击。然而,太平天国思想却无法挣脱封建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局限,缺乏近代资产阶级基于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所产生的民主主义等重要内容。相反,象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宗教迷信等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占据了重要地位。它们违反社会发展的规律,不符合现实生活的要求,起了导致革命失败的作用。洪秀全的思想突出地表现了农民阶级意识形态这种革命反抗与封建落后的两重性”。关于“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反孔”,他指出,不应把它形而上学化,要看到它的两重性。洪秀全固然因考场失败对孔孟教义怀有不满,但他主要是在起义后,才日益坚决反孔。尊孔与反孔,剥削有理的儒家理论与反剥削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剧烈斗争,正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尖锐表现。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基础作为依靠,也就提不出新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来替代封建主义,以孔孟为集中代表的传统封建思想就并没有、也不可能被真正打倒或清除。它们又以各种形式在太平天国意识形态内渗透、保留和表现出来。对所谓太平天国冲击“四大绳索”,他指出,从永安到天京,从《天命诏旨书》到《太平礼制》,它的制度是等级异常确定,尊卑十分分明,弟兄称呼纯为形式,君臣秩序备极森严,不仅有等级制,而且有世袭制……完全是封建主义那一套,并无任何近代民主主义。对旧有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冲击破坏,主要是表现在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和军队中,而不是表现在广大社会和和平环境里,前者毕竟是少数人和为时短暂的,在革命冲击过去后,很快又退回到原处。所以,太平天国并没有也不能使整个社会从这“四条极大的绳索”下真正解放出来。《天朝田亩制度》是公认的太平天国革命思想的总纲,李泽厚认为,该纲领的特征恰恰是上述革命反抗与封建落后这种双重性的最典型的表现。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在早期发动组织群众和作为军队风纪,的确能起巨大作用,但把它们作为整个社会长期或普遍的规范、准则和要求,则必然失败。所以我们在强调这个纲领的反剥削、代表农民的理想和要求的伟大革命性的同时,也不能无视、掩盖或否定这种小生产者的封建落后性质。不建立在工业大生产的基础上,纯粹从消费、分配着眼,搞平均主义、禁欲主义的共产主义,把“五母鸡二母彘”之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强制推行一种单一化的社会集体生活,在事实上是行不通,搞不长,挫伤群众(包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阻碍社会的前进发展的。尽管想得如何平等美妙,终于只是乌托邦。李泽厚对《资政新篇》的价值却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它在近代条件下,给农民革命指示了一条摆脱封建羁绊、甩开落后空想、继续前进的方向和道路。这是当时符合历史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的方向和道路。尽管由于军事局势,根本没能实行,但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正是由于《资政新篇》,太平天国才具有指向“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的近代民主主义的气息。如果说,《天朝田亩制度》的重点在于打破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那么《资政新篇》的重点就在于建立和发展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再是“五母鸡二母彘”之类的农业小生产的狭隘眼界,而是建立近代工业、全面开发资源的宏大计划。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克服前者的封建性、落后性和空想性。《资政新篇》的作者洪仁玕把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提出了“与番人并雄之法”,要与外国竞存。他的好些主张和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差不多,但洪仁玕这个方案,比后来改良派陆续提出的发展工商业的主张,不但早二三十年,而且也更为全面和彻底。
对于无限拔高太平天国,说它有一个“革命哲学思想体系”,黄彦提出了质疑,认为“对洪秀全等人的宗教唯心论加以抹杀或美化成别的样子。所谓太平天国有一个‘泛神论的思想体系’云云,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而“所谓太平天国‘进步历史观’和儒家唯心史观的‘根本对立’,看来似乎很注意划清革命派与反动派的阶级界限,实际上是抹杀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原则界限”。[※注]
董楚平从平均主义的历史功过角度评价太平天国。他说:“在二千多年的农民战争史上,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发展到最高水平。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的准备和初起阶段,对革命所起的积极作用,莫过于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特别是永安突围以后,到定都天京,革命形势发展之迅猛,不仅超出清政府的意料之外,而且也是洪秀全等人始料所不及的。究其原因,不能不归功于‘天国’理想的宣传和在太平军内部军事共产主义的严格实行。但是,平均主义思想制度的作用是不可能持久的。它只能兴奋于一时,不能持续到最后。革命进入高潮以后,扔得愈快愈好。”他进而分析道:“当革命初起,平均主义用来对付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它有‘破’的功用,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当革命进入高潮,平均主义用于人民内部,解决社会生产时,它就比封建主义为害更甚。太平天国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宁受比较正常、相对减轻的封建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而不要平均主义。因为平均主义违反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违背经济规律,只能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历史上有‘罪恶’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没有‘理想’的平均主义社会的道理。”董楚平的结论是:“判断一个政策是否正确,不能只看它的条文具有多少‘理想的光辉’,今天读起来有多少动听之处,而要联系当时的具体条件和实践后果。《天朝田亩制度》如果颁行于金田起义前后,倒不失为一个革命的文件。但它是颁行于定都天京、革命进入高潮以后,不是用来‘破’,而是用来‘立’。此其一;其次,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是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最发达的地区,这种先进的经济因素与平均主义的矛盾更大,它更加容不得平均主义的破坏。此时此地,颁行《天朝田亩制度》,与其说是革命的,毋宁说是反动的。从实践后果来看,它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今天,我们把《天朝田亩制度》捧上了天,而对拜上帝教倒还有所批判。当然,顽固地坚持拜上帝教是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拜上帝教创立于革命以前,没有拜上帝教,哪来的太平天国革命?它对革命是立过汗马功劳的。而《天朝田亩制度》颁行于定都天京以后,它对这场革命哪里起过拜上帝教曾经起过的作用呢?但由于我们看问题脱离具体的时空条件,故扬此而抑彼,弄得褒贬失当。”[※注]
林增平对“太平天国革命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提出商榷,认为这有待进一步研究。他指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自耕农的增加和永佃制的扩大并不符合资本原始积累的定义,因而不能推导出它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一结论。近代资本主义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兴起,都有它的历史的准备,即都经历过期限长短不一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但太平天国后自耕农的增多,大多数是无地少地的农民重新得到土地的户、口的增多,这种现象,显然是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间原先存在过的统一遭到破坏后又归于统一。而永佃制,既然是“佃农对其所耕种的土地有绝对使用权和支配权”,那么这种租佃制度的扩大,也就意味着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间某种程度的结合的扩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耕农的增多和永佃制的扩大,就不是分离封建经济的因素,而恰好成为已经破裂了的封建经济的黏合剂。这同原始积累的规律和内涵相比较,真说得上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了。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料和论据证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不曾经历原始积累阶段的,或中国的原始积累不是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的分离,而是更归于结合的过程,那么,就不可能用自耕农的增多及其分化和永佃制的扩大来解答太平天国革命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兴起的课题。林增平还认为:“永佃制并不是在长江中下游各省普遍地实行和扩大,而只是在部分地区有所发展。在实行永佃制的地区,情况也有很大差别。有的地区,佃户确曾借助永佃权不同程度地遏制了地主的贪得无厌的剥削,有的地区,则永佃权反成了地主豪强加重盘剥的手段。因此,似乎不宜不加区别地说永佃制‘使地主与佃农之间土地依附关系遭到破坏’,笼统地作出‘永佃制成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有力工具’的评价。”“更需要提出,即使是在农民利用永佃制使地主的贪欲遭到压抑,感到‘深受其制’的地区,也缺乏确凿可靠的史实足以说明,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是因此而转向投资新式企业的。”[※注]
在摈弃政治性抬捧之后,对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不管是肯定的多些还是否定的多些,研究者们开始尝试用一种客观历史发展和联系的观点来看问题了。刘大年说:“太平天国是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前进,我以为从直接的结果来看,很难找到它推动生产力前进的有说服力的论据。它的重要意义是很明显的。它把广大分散的人民反抗斗争集中起来,对封建宗法社会的全部权力、秩序加以扫荡,极大地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崩溃,此其一。它对外国侵略者展开大规模武装斗争,打破了西方资产阶级迅速把中国殖民地化的企图,此其二。太平天国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比过去许多次农民战争发展得更高些,对于后来的人民群众斗争具有显著影响,此其三。但这些都不属于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内容。如果我们的眼光看得远一点,情形就不一样了。把太平天国放在中国整个民主主义革命,即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过程中加以考察,把它看做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有重要意义的一步,有了它,然后才出现义和团运劫、辛亥革命,而后才有五四运动,而后才有新民主主义各个阶段的斗争,而后才有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后才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大发展,就可以说它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前进。”[※注]章开沅也同意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中的重要环节。他说,太平天国的主要历史功勋并不在于建设新制度,而是在于破坏旧制度,破坏旧制度就是为新制度的产生开辟道路。尽管“反满”(“讨胡”)不是太平天国农民战歌的主旋律,但是太平军以国内战争的形式公开而广泛地声讨满洲贵族统治的罪恶,并在所到之处扫荡其各级官僚机构。清王朝虽然借助外国侵略者的援助扑灭了农民战争的烈火,但是它再也不能恢复原有的相对稳定的政治态势,“外重内轻”已成必然的趋向。如果说,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主要受益者是各地诸侯,那么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受益者则是地主阶级的地方实力派。湘军、淮军的崛起及各派洋务集团的产生,都说明封建专制主义“大一统”的局面已经暗藏着分崩离析的危机。[※注]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