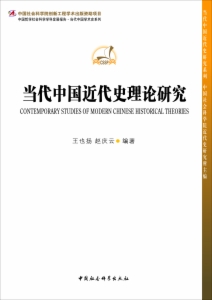一 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续论
|
来 源
:
|
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 | ||
|
摘 要
:
|
1954—1957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因“对1919年后的历史作自由的学术研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碍难之处”[※注],讨论者形成以1840—1919年为中国近代史学科时限的基本共识。近代史时限的确定,虽可看作学科成熟的标志,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时限是具有相对性和开放性的, “所有历史分界线都是人为的,都是以重大政治事件为标志的,这种划分是为了使历史研究更好地彰显不同时段的特点,掌握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是如果过分坚守。大陆学界对近代史上限问题的反思,总体来说影响较为有限, 1840年为近代史开端仍是主流意见,且通过高校学科设置予以强化。 | ||||||
|
关键词
:
|
近代史 时限 现代化范式 学者 半封建社会 革命史范式 社会性质 学界 开端 学科 中国历史 |
||||||
在线阅读
一 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续论
字体:大中小
1954—1957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因“对1919年后的历史作自由的学术研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碍难之处”[※注],讨论者形成以1840—1919年为中国近代史学科时限的基本共识。[※注]但如前所述,当时不少学者是将这一界定作为权宜之计而接受的;将这一学科时限写入高校历史系教学大纲,也主要是基于实际操作的考量。因为,社会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居于相当重要的位置,以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的转变来标示“近代史”,相较于以新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变化来标示“近代史”,实际上具有更为有力的理论依据。既然1840—1949年的社会形态被界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么以此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时限,显得更有理论底气。
随着时间推移,中国近代史实际研究工作频频突破1919年的下限。全国近代史研究重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改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72年成立民国史研究组,这就从学科建制上打破了1919年的学科界限;1979年近代史所创办《近代史研究》杂志,明确表示:“本刊欢迎下列有关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的稿件。”这种“破界”现象,后来在近代经济史、政治史、法制史、教育史、社会史等专门史领域,以及近代通史性著作写作领域,渐趋普遍。[※注]
当年首倡1919年下限说的胡绳在1981年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中提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30周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注]陈旭麓在讨论近代史线索时也指出,应着眼于历史社会形态将1840—1949年的110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注]这样,以1949年为近代史下限似乎达成了共识。[※注]
不过,对于高校教学来说,1919年为近代史下限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涉及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和师资准备,甚至从业者的饭碗等一系列实际操作的问题。许多从事党史、革命史或从党史、革命史转入现代史教学的教师一直反对1949年近代史下限说。[※注]1983年9月中国现代史学会和北京市历史学会召开现代史科学体系专题讨论会,与会的有全国高等院校教“中国现代史”教师四十余人,多数人仍主张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彭明发言:“一般说来,社会科学研究机关的同志,大都同意中国现代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的意见,而从事高等院校教学的同志,则从教学实际出发,反对这一意见。根据作者所接触的教师来看,讲现代史多年的同志认为再往上去教‘五四’以前的历史,或者专门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的历史,都有困难。长期从事近代史教学的同志,认为让他们去从事五四以后历史的教学,也有困难。由此看来,双方意见的统一,还要有一个过程。”[※注]
1997年胡绳在祝贺《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时,再次提出:“把1919年以前的80年和这以后的30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注]随后,张海鹏继续多次呼吁打通中国近代史学科中的1919年这一壁垒[※注],并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者的认同。[※注]2007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张海鹏主编10卷本《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均将近代史学科时限定为1840—1949年。2012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近代史专家编写的高校历史专业教材《中国近代史》出版,将此学科时限进一步予以确认。
近代史时限的确定,虽可看作学科成熟的标志,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时限是具有相对性和开放性的,“所有历史分界线都是人为的,都是以重大政治事件为标志的,这种划分是为了使历史研究更好地彰显不同时段的特点,掌握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是如果过分坚守,画地为牢,可能适得其反”。[※注]步平明确明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对时代特征的认识的加深,‘近代’时限的演进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注]朱宗震亦提出:“迟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会被后人合并到中国近代史的范畴中去。”[※注]胡锦涛在2008年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提出“三次革命”:辛亥革命、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注],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结合作为第二次革命,就从时间上跨越了1949年这一近代史下限。拉长历史的视界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下限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其继续向下延伸的趋势应当是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能够预料的”,“如果将近代史研究的下限严格限制在1949年,显然已经禁锢了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注]也有学者对以社会形态来作为分期的标准质疑:社会形态的含义相对稳定不变,而各种历史时期则是相对而言的,“近代史应是距当代人不太久远但又非绝大多数当代人所能亲身经历的社会历史,现代史则是与当代人密切关联的社会历史。……确定‘古代’、‘近代’和‘现代’这些概念的关键因素是时间,而且都不可缺少‘当代人’这一参照系”。[※注]姜涛则对中国近代史时限提出了新的看法。他指出,近代是指距离自身所处不远的年代,其本质上是相对史,它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与特定的绝对历史年代重合或分离。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绝对的中国史的角度看,实际上只是指从清王朝前中期的“治”走向晚清民国时期的“乱”,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走向“治”这么一个过渡时期或中间环节。相对于研究者而言,近代史活的灵魂就是“近”,它必须回答现实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因而根本不必拘泥于1840—1919年或1840—1949年的所谓近代史的上下限的划分,这些年限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近”也不是无限逼近,而是应该与“眼下”保持一定距离。他认为保持30年左右的距离较为合适。因此,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下限应该后延。在目前,中国近代史至少应当包括整个清史、中华民国史和(与眼下保持一定距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注]换言之,他认为近代史下限在当前至少可以延至改革开放之初。
事实上,继近代史研究重心从晚清下移至民国后,一些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已开始逾越1949年这一学科时限,而将目光投向20世纪50年代。近年来,不少学者从“革命”的角度倾向于将中国革命的下限延伸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49年的‘解放’,只是国家政权的更替,并非中国革命的终结。1949年以后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仍在继续。”[※注]随着研究者“破界”愈趋普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时限似乎并不必限。严亚明认为,近代史的时段只是历史时间框架,是构筑史学体系所必需的思维工具,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不能作僵化理解,应根据具体研究对象来确定研究的时空范围。[※注]
至于中国近代史的上限,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上限长期以来似成不容置疑的定论,并无多少学术探讨的余地。2000年高翔所著《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还被人警示曰“将18世纪和近代扯在一起,是不是要回到尚钺的老路上去?”[※注]
还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50年代来新夏提出:1840年英国大量派遣军队入侵不过是1839年军事进攻的继续和扩大,因此应以183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注]来新夏在20世纪80年代仍坚持1839年开端说。并提出,以1839年为近代开端,表明中国人民是以抗击侵略者为自己近代历史的开端,而非以英国入侵为开端。[※注]牟安世于1987年明确提出应以1839九龙之战为中国近代史开端。[※注]对1839年开端说,李少军、杨卫东,以及徐立亭撰文提出批评。[※注]笔者以为,1839年开端说同1840年开端说所争只是鸦片战争爆发时间,二者并无实质差别。此外,还有将近代史开端置于1840年以后的诸如1861年开端说[※注]、1905年开端说[※注]、1911年开端说[※注]、1898年开端说[※注]。但这些观点的影响均较为有限。
而美国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除最老式和最激进的以外”,都放弃了把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总的分期标界”。“认为‘中国社会以外的力量’(孔飞力语)入侵中国与中国近代史开端之间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这种假设本身已被宣告无效。”而“美国史家可能认为自己日益抛弃1840年,随而更多地从内部考察中国近世史是成熟的标志,是美国史学进入成年期的标志,说明我们终于超越了旧模式的‘思想上的帝国主义’,并以中国自身为基地,从中国的情况出发来对待中国历史”。[※注]这一被柯文总结为“中国中心观”的美国中国学研究取向,也影响到大陆学界对近代史开端问题的认识。
2003年,许苏民接续侯外庐“早期启蒙说”并加以发挥,提出中国近代化之路的“内发原生”模式,将明万历九年(1581)确定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是年推行“一条鞭法”,且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华[※注];晁中辰则明确将明隆庆元年(1567)开放东南海禁作为中国近代史之起点。[※注]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应打通明清史与近代史的樊篱。如赵世瑜认为,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明清史与中国近代史之间的连续性,导致将社会变革的多面性与复杂性简化。近代的历史不仅是东南沿海的历史,近代的主题也不仅是帝国主义侵略和近代化。如晚清时期大规模的西部移民以及由此而来的“边村社会”的形成,这一重大历史变化如果不从明朝、至少是清雍正以后的移民浪潮去把握,则看不到其在19世纪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刘志伟亦提出,尽管在具体内容上存在历史脉络的断裂,但问题的逻辑从来都是贯通的,近代史的研究者不必要事先划定一个时间断限,而要依研究的问题伸延时间上的视野。如农业经济史研究中,赋税问题和租佃问题自明清至民国时期始终是一脉相承的,要弄清这类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变化的逻辑,就必须贯通起来进行研究。[※注]
大陆学界对近代史上限问题的反思,总体来说影响较为有限,1840年为近代史开端仍是主流意见,且通过高校学科设置予以强化。有学者力图回避“近代史”分期之牵扯,如桑兵以民国学人使用的“晚近历史”代之。其所谓“晚近历史”,“大体指清代至民国时期,偶及晚明”。他明确表示:用“晚近”一词,方便之处“一则避开近代史开端的分歧;二则防止将清史截然分为两橛,不相连贯;三则避免治近代中国史上不出嘉道之讥”。[※注]
不少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学者,从现代化的角度观察问题,认为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的演进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姜义华赞成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社会从古代向现代的迈进,以20世纪最后20年成绩最为辉煌,值得大书特书。[※注]而胡绳晚年对近代史的再思考,也是延伸到了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论述,这说明历史研究不宜设限。王也扬总结说,“近代史”一词的英文,即“Modern History”,本就含有近代、现代与当代之意。历史是一条斩不断的长河,把时间界限当作研究界限,人为竖立藩篱的做法,不利于学者思考和研究问题,这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历史研究了。[※注]
而对于中国近代史时段内的具体分期,朱宗震认为,从1840—1949年,应以1901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后期又各分为两期。共分四期,即1840—1869,1869—1901,1901—1927,1927—1949。其值得注意者,是他将1901年作为近代史前后期的界标。他的主要理由是:其一,辛丑条约后,列强在华使节成了中国政府的太上皇,从而完成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其二,1901年后,列强对清政府的压力和中国社会内部的自觉的变革运动,形成某种合力,构成了对“中学”体制的突破。此后开始了对传统政治体制的冲击和更新。他特别强调:“以1901年为界,不仅仅是因为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而是因为中国社会在列强侵略局面下,经过长期的积累,到这时发生了局部质的变化。”[※注]另一种更具影响力的观点,则是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作为关键的分期界标。李良玉提出,作为中国近代通史,不应再考虑以1919年划分为上下两编,而应以1912年民国初创作为分期界标。他将近代110年分为五个阶段:1840—1861,1861—1894,1894—1912,1912—1927,1927—1949。[※注]房德邻也认为,以1919年划界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统称民主革命史,这是专门史,而不是作为通史的中国近代史。1919年作为文化史的标志性年代是合适的,但是对于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专门史,1919年不能作为标志性年代;若从通史的视角看,1919年五四运动自然并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而应以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为界标,将中国近代史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在他看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的意义远远超过1919年五四运动,中华民国的成立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在整个中国通史上有划时代意义;1840—1912年的近代史其实只是“前近代”,1912—1949年才是“近代”,因为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才建立了一个近代的国家政体。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晚清史和中华民国史实际上是晚清政府史与民国政府史,二者简单相加并不等于中国近代史。[※注]
相较于大陆学界,台湾学界对近代史时限持更为开放的看法。如近代史研究重镇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就将研究范围上探明清之际,并注意引进人才以开拓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的研究。据张玉法先生所言,这也是郭廷以的理念。[※注]同时他们对中国近代史下限也并无明确的界定,对于1950年代以后亦多有关注。
自20世纪初中国学界将“近代”概念用于历史编纂以来,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时限问题讨论甚多,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梁启超曾指出:“历史是不可分的,分期是勉强的”[※注];“时代与时代之相嬗,界限常不能分明,非特学术思想有然,即政治史亦莫不然也。一时代中或含有过去时代之余波,与未来时代之萌蘖”。[※注]罗家伦也强调:“时间空间的本质,原来是不可以割裂的”;“近代史名称,也不过是就研究便利而划分的一个段落”。[※注]此后学者在讨论近代史断限问题时,不断表述此意。马克思主义学者戴逸1956年强调“近代”、“现代”概念的相对性与含混性,随着时代变迁必将被赋予不同的内涵[※注];刘大年也明确表示:近代、现代这些沿用已久的历史学术语本系相对而言,并非严格的科学术语。[※注]
“近代”概念的相对性,意味着对中国近代史的时限问题须持更开放的看法。章开沅呼吁走出“80年或110年”的中国近代史,“在基础知识与学术视野两方面至少要向上延伸到清史乃至明史,而尤其需要重视明清之际经济、文化的内在变迁。同时也要向下延伸到1949年以后”。[※注]彭南生指出:“所有历史分界线都是人为的,都是以重大政治事件为标志的,这种划分是为了使历史研究更好地彰显不同时段的特点,掌握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是如果过分坚守,画地为牢,可能适得其反。”[※注]桑兵亦认为:历史断限本为研究便利,若变成安放史事的框架,“虽有整齐划一之便,若不能灵活把握,反而削足适履,不免割裂史事的联系,一定程度妨碍了对历史的认识,则有本末倒置之嫌”。[※注]
还须看到,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的时限问题时,学者实际上面临两难:一方面承认“近代”时限为相对而言,不宜也难以作特别分明的分割;同时中国近代史学科建置又要求有确定的学科时限。张海鹏提出,对于近代史断限的问题,应该区分个人研究与学科建设:个人研究可以“不受时空限制”,而学科建制则还须寻求近代史时限的共识。[※注]虞和平也提出“学科时限”与“研究时限”的区分:所谓“学科时限”,指“获得学界基本共识,并形成制度性确认,被全国相关研究和教育机构统一规定采用的时限”。所谓“研究时限”,指“既缺少学界基本共识,又没有形成制度性确认,只是学者们在自己研究中自行采用的时限”。个人“研究时限”的破界是正常的,但在不断“破界”中又会逐渐凝聚新的共识,形成新的“学科时限”。[※注]
“近代”只是相对而言,朝代的界线则是确定不移。早在20世纪30年代,周谷城即指出朝代分期意识之根深蒂固:“……现在治史的人,虽认为朝代为不甚重要了,然为旧习所拘,叙述的对象仍限于朝代之内,仍未由朝代之内移到朝与朝之间。”[※注]近年来1912年民国建立作为分期界标的意义日益凸显,反映出中国传统史学中朝代史的潜在影响。中国近代史所包含的“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段,在断代史观念之下,前者作为清史的固有部分、后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朝”得到强化。原来力图超越“断代”而求“断世”的中国近代史,也不得不面临被弱化甚至分解的危机。未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如何演化,仍需有识之士慎重酌量。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