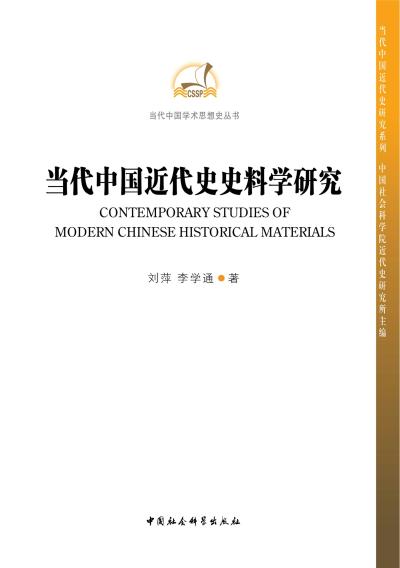第四节 口述史资料的采集与出版
|
来 源
:
|
当代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5 | ||
|
摘 要
:
|
在从事口述史料搜集整理的实践中,学术界围绕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关系、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的价值、口述史料的局限、口述史料实际操作的技术与手段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针对对口述史料真实性的质疑,也有学者认为,可以采取多次访谈的方式, “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注]。由于口述史学的共通性,中国学者对西方口述史学理论的引入和介绍,对规范中国口述史学,促进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还是有所裨益。 | ||||||
|
关键词
:
|
史料 口述历史 文献资料 史学 回忆录 学者 文献史料 受访者 日军 中国学者 研究方法 |
||||||
在线阅读
第四节 口述史资料的采集与出版
字体:大中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西方史观及研究方法的影响,口述历史研究逐渐受到中国学界的青睐和重视,被引入多学科的研究中,而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并呈现出“火爆”的趋势。口述史学的兴起,不仅促进了传统史学观念的变革,相应地,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口述史资料的挖掘和整理,使传统史料学中的口碑史料,成为独立的史料门类,拓展了史料的范围和类别,也扩大了史料学研究的范畴。作为一种新型的史料类别,口述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的手段、方法及形式,都与传统的文献资料有较大的不同。在从事口述史料搜集整理的实践中,学术界围绕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关系、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的价值、口述史料的局限、口述史料实际操作的技术与手段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由于口述历史强调的是“活”的历史,要求必须具备一定量的受访者的存在,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口述历史研究只能在近代史和当代史领域展开。二者相较,当代史成果又略胜于近代史。在近代史领域,改革开放后口述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妇女史、抗战史以及中共党史研究中,以至于有人以“口述妇女史”“口述抗战史”称之。虽然众多的出版物均以“口述历史”命名,但是考量这一时期的出版成果,尚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著作,只能算是口述史料,至今,也仍未脱离这一局限。而在史料学意义上的口述史料研究中,实践早于理论,有关口述史料的理论研究略显滞后。
(一)口述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在传统的史学研究中,口述历史主要被看成是一种搜集和保存原始资料的手段。口述史料(又称口碑史料),在中西方传统史学研究中均有运用。尤其在反映文字出现前的古史中,口碑史料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太史公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即大量采用了口碑史料。新中国成立后,延续了这种史学传统。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界围绕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在全国各地展开社会调查活动,以文献考证和口碑史料相结合,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先后出版了《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天津义和团调查》(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兄弟会资料选辑》(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1961年,内部印行)、《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同一时期,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的《近代史资料》创刊号上登载了《三元里平英团史实调查会记录》,随后各期也刊发了不少有关辛亥革命的访谈及口述资料。在全国政协主持的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中,以亲历、亲见、亲闻为特色,汇集了大量的口述史料。而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系列丛书,20世纪80年代初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和出版的《革命回忆录》等,也是以口述史料为特色。
虽然上述口述史料方面的实践,由于史料搜集观念及技术手段的落后,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料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却抢救了大量“活”的史料,也为以后口述史料的搜集与口述历史研究积累了经验。
20世纪80年代,一些中国学者翻译介绍了有关西方口述历史的著述,西方口述历史的理论和实践开始传入中国,并为中国学者所接受。台湾学者郭廷以主持的口述历史项目及出版的大量成果,也对大陆口述历史的开展起到一定推动和借鉴作用。同时,一些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从事口述史料的搜集,开展口述历史研究。如美国康涅狄克大学布鲁斯·斯蒂文在北大开展“中国城市历史和发展的口述史研究的计划”。1986年美国哈佛大学何海诗与北京社会科学院的钟少华共同合作,采访中国早期的留学生,从而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研究的实践。1996年,钟少华整理出版了《早年留日者谈日本》(山东画报出版社),书中搜集了100位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留日经历。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本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及方法进行口述史料搜集及口述历史研究的著作。
口述历史研究方法较早在中国妇女史研究中运用,这与口述历史注重个人体验、个人感受有关,而妇女史研究恰恰需要关注妇女的内心世界及情感,而这又是正史记载所缺乏的。1992年,陕西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教师李小江开展“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课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妇女口述资料搜集,并出版了《让女人自己说话——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三联书店2003年版)。该丛书拟通过女性的声音,讲述女人的历史感受,记录女人的历史记忆;以女性的视角,考量历史的足迹。书中纳入访谈的女性范围较广,有知识女性、红军女战士、战争中的农村妇女、“慰安妇”中的幸存者、东北抗联的女兵等,使长期被传统正史所忽略的妇女声音、妇女形象,得以生动的呈现。1997年,由贵州社会科学院张晓编著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同样把视角转向了长期不被关注的少数民族妇女身上。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抗战史研究的兴起,为了弥补文献资料的缺乏,抗战史研究领域也开始运用口述历史研究方法,对相关口述资料进行发掘和采集。这一时期,口述史料的搜集较多地集中在日军暴行方面,如南京大屠杀、日军掳掠劳工、日军殖民统治以及“慰安妇”问题等方面,其关注的视角从重要历史人物向普通民众转移,多方面、多层次呈现战争的个体体验,也有力地揭露了日军的残暴罪行。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
由孙邦主编的《伪满史料丛书》(10 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选用了1200多篇口述资料和回忆录。
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原国民党将领口述抗战回忆录》丛书(2005年版),系从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征集到的文史资料中选编而成,包括《我所亲历的淞沪会战》《我所亲历的台儿庄会战》《我所亲历的南京保卫战》《我所亲历的武汉会战》《我所亲历的南京保卫战》《我所亲历的常德、长衡会战》《我所亲历的桂南、桂柳会战》和《我所亲历的印缅会战》,从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角度,全方位地反映了中国正面战场的作战情况。
日军南京大屠杀口述资料是口述史工作者着力挖掘的重点。由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搜集了315位亲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揭露了当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长达6周的集体屠杀、零散屠杀、性暴力、抢劫焚烧破坏,对南京城狂轰滥炸等惨绝人寰的血腥暴行以及当时的各慈善团体收埋被害者尸体的情况。张连红、张生等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调查口述》(上、中、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收录了20世纪80年代至今南京市有关部门、学校、个人对日军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目击者的调查资料1600 余份,共130万字,按照调查时间以及调查者的不同分为九个部分。此外,还收录了当时新闻报刊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访问报道、目击者的日记,以及幸存者在南京事件后撰写的回忆录。
何天义用十年时间,走访征集战俘劳工口述资料1000 多件,整理访谈资料400万字,并选取600多人的访谈资料,结集成《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出版(齐鲁书社2005年版)。随后又整理出版了《日军侵华集中营——中国受害者口述》(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从受害者的角度真实地反映了二战期间日本残酷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
张成德、孙丽萍主编的《山西抗战口述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从1500名亲身经历山西抗战的受访者中,选取辑录了665人的口述资料,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风俗、生态、卫生、宗教、妇女、灾荒、瘟疫、市场、伦理道德等方面,反映1937—1945年山西各地的社会状况,特别是普通百姓在战争状态下的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书中有大量的细节性描述和写实性记录。
由齐红深主持的“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研究”课题,搜集到1280位亲历者的口述史料和3000多件历史图片和教科书等实物,先后出版了《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流亡——抗战期间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历史》(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从青年学生的视角,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殖民教育和奴化教育的历史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2011年,齐红深又编辑出版了《黑暗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当事人口述》(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星火”是东北沦陷时期的一个青少年文学团体和读书会组织,活动范围主要在辽宁省盖州、营口、沈阳、本溪、大连和长春一带。成员主要是中小学生。他们抵制日本奴化教育,秘密阅读进步书籍,开展读书、写作活动,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创作了一批爱国诗歌、散文、杂文、小说作品。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惨遭日军镇压,是东北沦陷时期日军制造的最后一个大惨案。本书通过42位“星火”成员和中日两国当事人的回忆和200余幅历史照片,从不同角度还原了“星火”组织的兴起、活动形式,以及惨遭日军镇压的历史。
抗战时期,浙江是最早沦陷的地区之一,在被日军占领的八年时间内,浙江人民遭受了日军残酷的蹂躏和迫害。200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学生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口述历史调查活动,搜集了120 余份幸存者口述,编辑成《烽火岁月中的记忆:浙江抗日战争口述访谈》(袁成毅、丁贤勇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揭露了日军在浙江的暴行,反映了浙江人民的抗日斗争。
近年来,为了抢救抗战史料,江西省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对抗战史料的搜集发掘工作,编辑出版了《永远的惨痛:江西省抢救抗战时期遭受日军侵害史料·口述实录》(尹世洪、傅修延主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以市县为单位,收录了大量的口述史料。为有助于更完整地反映日军侵略罪行,还编有简要概述,并附少量地方文献。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而产生的大量难民,是抗战时期严重的社会问题,以往学界一直关注不多。杨圣清《苦痛的记忆:中条山战役难民口述历史实录》(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以难民口述的形式,真实再现了1941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条山制造的惨案,揭露了日军在中条山所犯下的种种暴行及当地难民的惨状,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缺失。
除以上列举的口述史料外,近年来,各出版社推出的以口述历史命名的图书。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口述自传”丛书,包括《黄药眠口述自传》(2000年版)、《舒芜口述自传》(2002年版)、《文强口述自传》(2003年版)等。该社编辑出版的《口述历史》集刊,以及各媒体、杂志开设的“口述历史”专栏等,都收录刊载了相当部分与近代历史相关的口述史料内容。
近代以来,中国党史口述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是一个热点,大多以单篇的形式发表于各刊物的“口述历史”专栏中,对于弥补文献资料的缺失,以及历史的细节方面均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资料。对中共高级领导人的亲属及后人的口述史料的追寻也成为口述史料的新方向。比如周海滨的《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通过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闻天、胡耀邦的亲人的口述,展现出家庭生活里质朴与真实的领袖形象,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其中包括陈独秀的修墓始末、瞿秋白的平反始末、李立三的异国情缘、秦宪邦(博古)的坠机细节、张闻天的最后岁月等。
上述出版物,均以专题或事件为主,虽然大多以“口述历史”命名,但如果按照口述历史的定义衡量,尚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著作,称为口述史料或更为恰当。虽然,其形式大都以访谈为主,但正如有学者直言的那样,“一切口述史固然都是访谈,但不是一切访谈都是口述史”。尽管一些口述资料采集者对口述资料也进行了分类编排,对当中的人名、地名、时间,甚至史实错讹也进行了考订,但这些工作,仍然属于史料学的范畴。一些史料集以综述、序言等形式对口述史料中涉及的内容进行了说明,但都属于史实性甚至于常识性的说明。有的资料集虽然附录了部分文献资料,如《日军侵华集中营——中国受害者口述》,为了证实口述史的真实可信性,选编了同一时期同一问题的档案资料、报刊资料,特别是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时获得的口供、笔供和调查、揭发、检举加害者的供词和见证者的证词,但这些材料也仅是对口述史料的补充,尚未达到将文献史料与口述史料相结合,对所涉及的历史进行解读的程度。
此外,在目前出版的各种口述史料中,水平也参差不齐,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学术目的和学术意义,为口述而口述的现象比较突出。同时学术眼光较窄,部分选题较为集中。比如有关抗战史口述史料的挖掘中,大多集中在日军暴行上,因此被学术界批评为“忆苦思甜”型。在整个近代史领域中,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口述资料相对较少。在已经面世的出版物中,有的没有理解口述史料的真正含义,严格区分口述史料与其他史料的界限,所收录的以“口述”冠名的史料中,往往收录有文字资料,比如《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历史口述实录(1921—1949)》(鲁林、陈德金主编,济南出版社2002年版),甚至于收录了部分研究性的文章,且每篇资料均未标明出处。即使在有些质量较好的口述史料中,比如《日军侵华集中营——中国受害者口述》中,也收录了部分文史资料。此外,大多口述资料是一次成型,即仅做了一次访谈,因此难免有史实不清,前后矛盾之处。
口述史料的整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更为突出,除了存在对采访的口述史料任意删改等严重问题外,同时由于采集整理者水平有限,对一些史实不了解,对受访者的口音不熟悉,口述史料存在错讹较多。比如龚育之就指出《文强口述自传》中的一些错误,如“南昌起义的部队不可能到过上海,书中的‘上海’显然有误;‘西晋’公署为‘绥靖’公署之误;‘上海解放以后’为‘上海光复以后’之误;美国珍珠港被日本人偷袭,未被日本‘占领’;三尺土上有神明,应为三尺头上有神明;程贤州、陈仙洲,显系同一人;‘只是’应是‘指示’;孙健应为申健;黔应为‘青(青海)’;京浦应为津浦”,以及送寿礼所写的字应为“花好月圆人寿”,而不应为“花花圆圆寿寿”,毛泽东女儿应为“李讷”而不应为“李娜”等等。[※注] 有些出版物中,对口述资料中存在的错误也没有进行认真的考订。而有些口述史料甚至对采访的时间、地点、采访人都未作著录。
应该承认,通过数十年来口述史研究者深入实地的调查访问,挖掘、整理口述者的口述资料,抢救了一批即将消逝的鲜活的史料,弥补了文献史料中的空白,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可能,推动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展开和深入。近年来,在抗日战争研究中国民党正面战场研究、日军虐待中国劳工问题研究、日军暴行史研究,以及中共党史研究中诸多问题的推进,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时期相关口述史料的整理出版。
(二)口述史料理论的研究与探讨
在进行口述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学术界对口述历史的理论问题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这一时期,除翻译出版[英]保罗·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美]唐纳德·里奇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外,中国学者有关口述史理论方面的专著主要有:杨祥银著的《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周新国主编的论文集《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李向平、魏扬波著的《口述史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发表的相关论文有300多篇。
口述史研究者一般把口述史的研究分成四个相应的阶段,即“口述史研究的准备阶段、口述史访谈阶段、口述资料的整理和保存阶段、口述史的研究阶段”[※注],而前三个阶段,实质上探讨的均为如何搜集整理口述史料的问题,属于史料学研究的内容。更有一些学者认为口述史学就是一种搜集整理史料的方法。而有的学者认为,“口述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史料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注]。杨雁斌在《口述史学百年透视》中将口述史学比之于史料学,因为从表面上看,双方都是以史料研究为基础的,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口述史学的研究工作,说到底,是口述史料的搜集、筛选、整理和利用。史料学也不例外,史料本身的研究工作是该学科关注的重点。由于史料研究的工作流程直接关系到史学成果的质量,因此,每一个环节都显得格外重要,尤其是史料的搜集工作。另外,史料学理论的重要内涵之一,是逐步扩充史学研究的手段和工具,逐步引进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统计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史料学的这些主张和观点显然顺应了当代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口述史学的相关理论不谋而合。”[※注] 虽然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但从这一时期,有关口述历史或口述史学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口述史料理论的探讨上,因此,从史料学上分析口述历史的理论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1.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关系
关于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的概念定义及其二者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而这种分歧源于对口述历史的不同理解。荣维木较早从学科角度对于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的概念定义进行了界定,认为口述历史是“收集和运用口碑史料,再现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从这个意义出发,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从史料学的角度,特指史料留存的一个种类;后者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特指表述历史的一个方式”[※注]。也有学者从研究方法上对二者进行了区别。钟少华认为:“以口述方法为主,广泛收集中国口述史料,进而研究之,这就是中国的口述史学。”[※注] 也就是说,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左玉河在《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一文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口述史料是不需要加工的;但口述历史是必须经过整理者加工的。而这种加工,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与文献史料比较后对受访者的口述进行了筛选”[※注]。梁景和在《关于口述史的思考》一文中认为:口述史的方法应当具备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史学家搜集史料的方法;其二,史学家利用口述史料撰写历史的方法。[※注] 与之相反,杨祥银则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传统的笔录或者录音和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记录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注]。因此,是不需要加工的。但近年来,学术界对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的认识逐渐趋同,一是认为应该把历史学学科中的口述历史研究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口述历史研究加以区别;二是认为,在历史学学科意义上,口述史料不等于口述历史,就如历史文献不能等于历史著作一样。
2.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的关系
传统的史学研究主要以文献史料为主。口述史学在西方兴起的最初动力是旨在弥补现存文献记录不足或档案的缺失,即强调口述历史的史料价值。这与中国口述史学的兴起背景颇为相同。因此,有学者认为,“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让人们尽可能地发现和积累更丰富和更鲜活的史料,为接近更可靠、更可信的历史提供可能。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对现有史料的有益补充,更在于对传统历史观中偏离真相部分的挑战”[※注]。口述历史兴起后,传统文献史料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围绕文献史料与口述史料的价值的优劣,以及二者的关系问题,学术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学者认为,口述历史在复原历史方面,有其他任何档案、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就历史记录的广度而言,口述历史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就形式而言,一个是“死”的材料,一个是“活”的材料。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注] 具体来说,口述史的优势体现在:“其一,口述史往往能够提供非常生动的描述,这是只使用文字史料作为常规历史研究手段无法做到的;其二,口述史能够纠正文字史料中的偏见,这显然比单一的文字史料要全面得多;其三,推进了史料的收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为未来史学的发展做好了铺垫。”[※注] 也有学者从资料的完整性上对文献资料与口述资料进行了比较,认为口述史料具有完整性,而其完整性主要体现在历史资料的搜集方面。口述史学家往往要制定出较为详尽和目的明确的访谈计划,计划越是周密,搜集到的资料也就越全面。同时口述史学家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扩大范围,围绕同一主题进行多次调研,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口述凭证。这样搜集到的口述史料也就显得较为完整和系统。[※注]
口述资料与文献史料具有同样的价值,口述史料的“可信度与文字资料相等,可以归入档案类别”。也就是说,在价值上,它与文献资料中最受重视的档案资料相当。[※注]
但是,也有学者对口述史料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这也正是当前口述史发展的困境之一。回忆作为一种主观性极强的心理活动的反应,其真实性和不稳定性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提供口述史料的人们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无论他的记忆如何鲜明和生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后来经历的影响。比如口述者与访谈者的个人偏见,怀旧的情绪,童年的不幸遭遇,对亲人的感情,健康的妨碍,都使回忆被不同程度地被扭曲。”[※注] 口述史料本身由于口述者对经历的“选择”与“过滤”,已不等于当初的历史真实。此外,作为一种互动活动,其访谈的场所和气氛,访谈者的身份以及他的引导和感染力,也是影响口述史料真实性的因素之一。诸多因素的影响,往往将“过去的声音”变成了“现在的声音”。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文献史料的优越性也就显现出来。“文献记载是稳定的,一旦形成白纸黑字,就能千古不变;口述则是流动的,一次性的,同样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他的口述可以衍化出许多的版本。”因此,承认口述史料的价值,并不意味忽略它的缺陷和不足。[※注]
针对对口述史料真实性的质疑,也有学者认为,可以采取多次访谈的方式,“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注]。美国口述史学家霍夫曼也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口述史料的作者只有一个,而且是明确的,史学家可以对他或她进行重复采访,以确定其所提供的史料的可信程度;而文献史料的作者也许是明确的,也许是不明确的,也许是一个,也许不止一个,而且死无对证,因此不易于考察史料的可靠性。”[※注]
随着对口述史价值的深入讨论,口述史的另一种价值被更多的研究者认同,即可以从这些不真实的回忆中,探寻个体或集体的历史意识的形成因素,也就是说,口述史料也许不是研究历史事实的史料,但却是研究历史意识形成的重要史料。这一观点也直接承继于西方口述史家的思想。唐纳德·里奇在《大家来做口述史》前言中谈道:“口述史家和公共历史学家们的兴趣,正日益逐渐地从主流历史学的学术研究转向对记忆的研究。历史学家围绕这些公共记忆的主题,审视人们是如何从现实的利益出发来构建他们的过去的。”“口述史家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人们为什么和怎样记住和描述他们的过去,记忆中都有些什么内容。”[※注] 约翰·托什进一步作了阐释,认为口述历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注]。受这一观点的启发,有中国学者认为,“口述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社会记忆’或‘活的历史’,它不一定是过去发生的事实,但却反映个人的认同、行为、记忆与社会结构间的关系。研究当代人如何在社会中选择、扭曲或遗忘‘过去’,可能会给历史学者一些启发”[※注]。因此,“口述史学者不应将自己仅限制在一个找寻‘真实的过去’的过程中,而更要去探触一个在更广大范畴中被扭曲、被遗忘的重要的‘过去’”[※注]。
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口述资料与文献资料都有其自身的局限,因此作为史学范畴的口述历史研究,应该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规律及原则,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对口述史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心、医学等学科中的口述历史研究不同的地方。有学者对此作了比较,指出:“在评估口述的功用和价值方面,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存在着一定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个学科的性质和研究特点所决定的。人类学者的工作中心主要在贫困落后的边远地区,研究对象是没有文献或少有文献的少数民族,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下,田野调查、采访口述顺理成章成为重要的工作手段。史学则不然,它的研究范围可能更宽一些,在时间与空间任意穿梭的自由度更大一些,研究对象可以是社会上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也可以是主导社会潮流的精英集团。”因此,立足文献研究,正是史学研究的自身优势,口述方法当然要利用,但优势不能舍弃。“口述与文献互相补充,彼此印证,两者相得益彰,就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注] 更有学者认为,口述史学的发展首先应该从中国史学的理论和传统中汲取养分,如对口述史料收集与使用的技巧,对文献资料的征引与钩沉,都是口述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注]
3.口述资料的类别
作为一种新的资料类型,口述史料包括哪些类别,也就是说哪些资料可以算作口述资料,是口述历史研究中应该界定的首要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口述史料”这一概念。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大的争议。由于中国口述史学直接来源于西方,因此西方口述史学对“口述史料”的定义也相当程度地影响了中国学者。[美]路易斯·斯塔尔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注] 唐纳德·里奇也认为:“口述历史是以访谈录音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注] 强调录音等工具是口述资料的重要媒介。受这一观点影响,钟少华认为,“口述史料是通过口述所搜集的史料,可以是录音形式,也可以是以文字形式,但文字形式要有录音为依据”[※注]。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在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录音工具的使用是不现实的,因此,是否使用录音设备不应成为判定是否是口述史料的依据。[※注]
围绕是否使用录音设备问题,中国口述史学界分为两个鲜明的阵营,一种是不强调录音设备的使用,因此,对口述史料类别作了较为宽泛的划分。如荣维木就认为,口碑史料可分为几种类型:一是口传史料;二是回忆录史料;三是访问记史料;四是录音史料;五是专用口语史料,如帮会切口,用数字概括的专用口语,如“三三制”“二五减租”等。[※注] 也有学者将口述历史定义为“亲历者叙述的历史”,因此,认为目前在中国主要有4种口述史料存在形式:口述史、访谈录、回忆录(其中也包含别人记录整理的),以及写进人物传记和历史著作中的各种口述史料。此外,还有录音、录像的记录和音像形式的传播。[※注]
与之相反,一些学者坚决反对将没有经过录音程序的回忆录、文史资料,以及自述、自传等文字资料划入口述史料类别中。认为虽然不少回忆录也是由采访手记而成的,也是“口述”成果,但由于没有保留录音或根本就没有录音,这就缺失了现代口述史要求的在资料方面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可更改的,可以重复使用的原始声音。[※注]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对回忆录应该区别对待,有些回忆录是通过访谈形式完成的,应给归入口述资料,而有些回忆录是笔撰,不能作为口述史料。
虽然有很多学者反对将回忆录等作为口述史料,但在口述历史的具体实践中,仍然有很多人将回忆录等资料作为口述史料收入,实际上是默认回忆录是作为口述史料的一个类别。
4.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与保存
口述史料作为一种新的资料类别,无论在搜集方式、整理方式,还是保存方式上,都与传统的文献资料迥异,其操作性与技术性极强。为了保证口述史料的真实性,中国口述史工作者一直倡议进行口述史料搜集整理时应该采取规范化操作,并呼吁制定工作守则。但综观数十年来口述史理论问题的探讨中,有关口述史料搜集整理的规范化问题,以及具体的程序、手段、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仍然非常薄弱。目前所见中国学者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杨祥银的《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李向平、魏扬波的《口述史研究方法》。但两书主要是介绍西方的口述史学理论,包括口述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保存等技术性问题,对于西方口述史学与中国口述史学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西方口述史学理论是否均适用于中国口述史学界,其操作手段是否符合中国特色,也未能加以探讨。比如,杨祥银等在其著作中对受访者的取样问题讨论,无论是“随机取样”(根据研究目的,从若干单位组成的事物总体中,抽取部分样本单位来进行调查、观察,用所得到的调查标识的数据,以代表总体,推断总体),还是“分层的有目的取样”(把总体按照某种标准分为几个层次,然后在每个层次中有目的地抽取样本)[※注],实际上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甚至历史学研究领域均不可能做到,因为存活下来的样本——受访者非常有限,难以形成一定数量的受访群体。虽然有学者对此有所质疑,认为口述史研究作为一种以历史学学科为基础的质性研究,其研究对象受访者的取得,并非建立在随机抽样上,因此不论其受访者有多少,对受访者的观察次数如何的多,访谈个案数有多大,仍将永远无法穷尽所有的情景或个案,因而提出了“理论性饱和”的概念(这一理论也来源于西方社会学界,指依据抽样的原则,对于口述资料要一直抽样,直到资料里的每一个范畴都达到理论性饱和为止,即在某一个范畴,再没有新的或有关的资料出现)[※注],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是无法做到“饱和”的。以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幸存者来说,无论是亲历战争的老兵,还是受害的妇女、被虐死的劳工,存世者的数量均非常有限,虽然从事相关问题研究的口述史工作者,竭力搜寻受访对象,也根本无法做到用“随机取样”“分层取样”的方法选择受访者。
由于口述史学的共通性,中国学者对西方口述史学理论的引入和介绍,对规范中国口述史学,促进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还是有所裨益。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