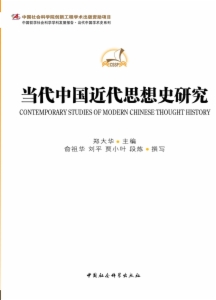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间派别的思想
|
来 源
:
|
当代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8 | ||
|
摘 要
:
|
学者们或从宏阔的视野出发,对思想进程展开新的研究,如对洋务思想,涉及了鸦片战争前后洋务思想的萌芽、甲午战争后洋务思想的发展、反洋务思想等领域。或从新的角度分析、评论近代思想进程,如从近代社会转型、近代思想转型和近代学术转型的角度来讨论经世思潮的发展和影响,重新评价清末的立宪和革命思想。或从史实考订入手,对一些思想史上的文化事件进行考订、厘清,如有的学者对是否真发生过作为戊戌思潮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公车上书”提出了质疑,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或根据从时代发展获得的灵感对近代思想进程做出多元的解读,全新的阐释,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原因、发展进程以及历史意义的多重解读。 | ||||||
|
关键词
:
|
思潮 洋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文化运动 经世 五四新文化运动 维新 立宪 革命 新民主主义社会 革命派 |
||||||
在线阅读
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间派别的思想
字体:大中小
国家主义派。闻黎明指出,20年代中叶,随着工读实验和无政府主义的破产,国家主义一度成为流行于中国知识阶层中的一种社会思潮。这种既不赞成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又对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政策持有异议的思潮,在大革命失败后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他认为,最初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是由于“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激励,方鼓吹国家主义的,并非出自意识形态的分野,如为新民主主义献身的闻一多,就曾与大江会,与“大江的国家主义”,特别是与“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紧密相连。闻一多虽然提倡国家主义,但说到底是反侵略斗争。[※注]孙德高指出,闻一多一生都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只是在对其认识上,前后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期,他主张民族主义主要是出于爱国热情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偏爱;后期,经过对古代文化的长期研究,加上对抗战时期大后方残酷的现实的深刻体会,使他在继续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同时,对民族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注]田嵩燕认为,整个20年代,在曾琦、李璜等国家主义派理论家那里,对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的论述,理论上倾向于以个人为目的,以国家为工具,工具服务于目的。但国家主义对作为手段的国家的意义也视之甚重。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国家危机,国内各政治派别纷纷探索救国之道。国家主义派此时指出,近代的国际斗争是整体国力的斗争,当前的中国只有将国家整合成一个整体,才能动员整个国力,抵御外侮。这种主张反映在国家主义派的国家观上,就是开始放弃“个人为目的,国家为工具”的观点,逐步转向主张“国家与个人合一”。这种转变首先体现在余家菊的思想中,陈启天对它做了极端化的发展,他认为,在国内政治意义上,主权国家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要以国家为中心;在国际政治意义上,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与人类共同体的关系也要以国家为中心。因此,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国家的权威都是毋庸置疑的,它拥有全面的、最高的权力。[※注]敖光旭指出,“醒狮运动”之初,国家主义派致力建构中西杂糅之文化保守主义体系,以为其运动之意识形态。其现代学理是以欧陆玄学为基础的历史文化哲学及实证哲学和实证学科(包括实证主义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玄学与实证本相冲突,且因移植国家主义之中西时空错位,导致醒狮派理论之困境及内在紧张,并驱动其由消极强调国家主义之自在性,走向积极营建“新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并最终促使醒狮派呼唤和回归“五四精神”,走向了文化激进主义。[※注]吴小龙指出,国家主义的理论家们在形成其理论的过程中,考察了国家主义理论在西方历史进程中的演变和发展,分析了它对中国国情的适合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应实行国家主义的论据,并由此进而提出,应当把国家主义确立为中国当时的中心思想,用以凝聚人心,团结国民,鼓舞民心士气。应当说,当他们进行这些理论思考时,确实体现着他们对民族和国家的强烈责任感,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能因为他们对其他党派的政治态度而影响对其探索的真诚做一种历史的客观评价。他们试图用国家主义的口号,用提倡国家意识来唤起民心,整合社会,挽救积弱,渐至复兴;他们既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又反对劳资冲突、贫富悬殊的西方资本制度;既有选择地认同中国传统中有价值的一面而力图保存之,又有保留地赞成社会主义的理想而愿意吸收;大体上,则倾向于以国家社会主义为旗号的、俾斯麦加社会党的社会政策(但这不是希特勒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不妨视之为对“第三条道路”的一种初步探讨,尽管他们并未以“第三条道路”自称。[※注]
“人权派”。鲍和平指出,“人权派”的代表人物是当时在上海任大学教授的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他们大都留学欧美,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民主政治制度较为熟悉,对中国的国情则不甚明了。因而,他们便以其所接触到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为蓝本,以“保障人权”为旗帜,发起了一场较具规模的“人权运动”,“人权派”因此得名。“人权派”针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提出了“保障人权”和“思想言论自由”、施行“法治”和“专家政治”等政治主张,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注]张连国认为人权派的《人权论集》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第一次系统的人权宣言,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其历史局限是‘功能主义人权观’,忽略‘天赋人权’的‘超验之维’,并企图脱离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注]。石毕凡等指出,实行民主宪政一直是近现代中国先进分子梦寐以求的目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新月》月刊为阵地,向国民党一党独裁发起挑战,要求以民治代替党治,实施法治以保障人权,在思想界掀起了一场颇具影响的“人权运动”。[※注]成平认为,人权派认为,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他们要求制定宪法,规定政府的权限,约束政府的行为,矛头所向,直指国民党独裁统治。但是企图叫专制独裁的国民党走上法治的轨道,无异与虎谋皮,是注定行不通的。[※注]赵慧峰指出,反蒋又反共,试图以和平的手段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人权派政治思想的根本特色。[※注]李腊生指出,土地革命时期的人权派是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人权派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其政治主张和言论既有消极乃至反动的一面,又有顺应历史潮流的值得肯定的一面,我们应该进行具体分析,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注]马建红指出,“人权派”揭露和批判在国民党训政之下,人民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现状,主张国家的功用和目的在于保障人权。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用约法或宪法来约束、规范政府行为,最终建立一个个人尊严得到充分尊重、个人价值充分实现的社会。“人权派”以制定约法(或宪法)为起点,以实行法治为手段,以保障人权为鹄的,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严密的思想体系,为我们今天的宪政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注]他又指出,“人权派”从功用的角度出发,揭示了思想言论自由之于个人与社会的价值,指出作为人权的思想言论自由就是批评政府及现政权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的自由,认为这项人权应“绝对不受法律的限制”,“绝对不受何种干涉”。人权派关于思想言论自由的主张有积极意义,但有关二者均属“绝对自由”的结论的局限性、片面性。[※注]张义认为人权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纯正的人权运动。人权派存在的时间虽然非常短暂,其本身的理论也有诸多不足,并且与当时中国现实存在隔膜,但其思想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应占有重要的地位”[※注]。
“战国策派”。20世纪40年代初,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出现过很有特色的文化思想流派——“战国策派”。这是一个在史学革命尝试、文化重建构想中极富理论个性的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他们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并因此而得名。因为战国策派激烈的国家主义主张,一度被视作为国民党统治张目,甚至有“法西斯主义的倾向”。90年代以来,学界对战国策派评价渐趋客观、中性。江沛的《战国策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对战国策派进行了较全面、客观的研究。论著中指出,战国策派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形态史学并非历史循环论,他们在引入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观念,不仅用以观察世界文化,也以之考察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他们运用这种理论准确地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三个大国“称霸世界”的国际政治局势和欧洲国家走向“大一统时代”的前景。这一学派对传统伦理的抨击与五四运动对传统伦理的批判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只是倡导的重点不同而已,前者强调个性解放,后者更多是希望民族在伦理上将家族的孝转为对国家的忠,团结一致打败日本侵略者。该书认为人们指责战国策派“宣扬法西斯主义”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但绝不能论定他们“宣扬法西斯主义”的目的是“为国民党统治提供学理依据”,实际上他们宣扬“尚力”主义,“英雄崇拜”是为了改造中国文化的柔弱气质和国民委顿、颓废的弱点。该书也指出了战国策派思想理论上的负面因素,诸如他们虽不反对民主政治,却认为民主政治必然带来个人主义散漫等问题,不利于抗战,因而主张民主政治缓行等。江沛还以“战国策派”为例,考察了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缠,指出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拯救民族危机与向现代转型是发展的两条主线,由此形成了要反对西方侵略、维护民族尊严,就要倡导中国文化独立性,反对西方文化传入,要开放中国,学习西方以融入世界,就必须反对民族主义思潮,批判传统文化的相互矛盾的双线走向。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战国策派”主要人物与追求自由主义信仰的众多知识界人士一样,在思想理念上发生了迎合民族主义思潮的转变,倡导“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呼吁个人自由暂时让位于民族自由,为时势所迫主张集权政治,并将民主政治与民主主义硬性割裂。救亡与启蒙的两难,观念与现实的冲突,自由主义内核与民族主义外衣的交织,在战国策学人论述中表现十分突出,也是那个动荡时代知识群体中思潮繁杂现象的典型反映。[※注]暨爱民认为“战国策派”是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独特个案”,作为民族拯救历史的一个重要参与,战国策派一反恢复儒家传统主张而要求通过重建战国文化强化民族的文化认同,塑造“列国型”的民族性格,以适应充满竞争的“战国时代”。这种建构性的民族主义,在严肃思考中国民族与文化命脉的过程中体现出了时代关怀。[※注]黄岭峻认为,战国策派是与保守主义相对立的两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派别之一,他们反对传统文化,但反对的目的也是想扫除他们所认为的存在于儒家道德中的假仁假义,提倡尚武风气,从而抗战到底。“战国策派”与保守主义者在对战争与传统的看法上都不相同,如保守主义强调战争应分“义战”与“不义之战”两种;而“战国策派”则认为战争只有“取胜之战”与“歼灭之战”的区别,无所谓正义与否。二者都是非理性的,但这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毕竟缺乏严格的学理基础,尽管它一时也能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却由于其非理性的病疾,这种爱国情怀终难持久。事实上,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战国策派”,都存在难以自愈的“硬伤”,因此不可避免地也影响到其爱国主义功用的正常发挥。[※注]田亮指出,抗战时期兴起的“战国策派”是一个民族主义学术团体。他们用“文化形态学”来解释中国历史文化和世界格局,惊呼“战国时代的重演”,批评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和国民劣根性,大力倡导尚力精神和英雄崇拜,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并重的文化,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并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尽管其历史观有非理性倾向,但其文化重建思想和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具有思想史价值。[※注]尹小玲考察了“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认为“战国策派”极力揭露国民性的劣根性,是为了改造国民性,为了实现中国文化的再造,以争取抗战的胜利,改变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因此林同济、雷海宗运用历史形态学,从历史考察中引发对文化弊端的分析,对民族性格的反省。[※注]宫富就“民族主义”与“战国策派”文艺进行了辨析,他不赞成长期以来学术界所持的那种将“民族主义”文艺和“战国策派”文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相提并论,并被斥为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流派的观点,而是认为它们是两个性质迥异的流派,因为通过对其成员组成、文艺观、时代观以及理论渊源几个方面的辨析表明,“民族主义”文艺派是为国民党政治统制“代言”,“战国策派”文艺则为中国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殿堂中赢得一席之地而“立言”,同时还是实现该派“战时文化反思和重建”主旨的一支重要力量,自觉承担着五四以来改造国民性的重要任务。[※注]王应平从“战国策派”与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建构的视角指出,抗战时期兴起的“战国策派”从应对民族危机和改造积贫积弱的国民性出发,大力提倡“尚力”主义和“英雄崇拜”,提出关于民族国家的建构理想:改造旧有的柔弱衰萎民族而成生命力充沛的进取民族,改造受欺凌的民族国家而成具备强大生存竞争力的民族国家。战国策派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虽有矫枉过正的偏颇性,但其挽救民族危亡的文化重建思想仍有超越时代的历史价值。[※注]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间路线”。陈任远指出,中间路线在中国政治舞台活动的整个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淡入期、整合期、凸显期与淡出期。之所以如此划分,是因为一方面,根据中间路线的观点与组织变化和发展来确认,另一方面,根据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所处的地位与作用来判定。因为不难发现,中间路线的观点与主张,在其整个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分到合,再由合到分的周期;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与影响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由边缘到中心,再由中心到边缘的轮回。[※注]章清指出,战后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确有值得重视的地方:出现了不少明确标榜“自由主义”立场的刊物;也不乏讨论“自由”及“自由主义”的专书出版。尤其重要的是:“自由主义”作为一股政治势力也有所表现,而不只是部分知识分子醉心的理想。可以说,作为一种政治“话语”,“自由主义是什么”“自由主义往何处去”到战后才引起各方热烈讨论。游离于此,要重建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史实,是难以想象的。[※注]左玉河指出,1948年1月,《大公报》发表了社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在中国思想界迅速引起一场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这场讨论,内容涉及广泛,讨论的双方就个人自由与大众民主关系、计划经济与思想自由关系、革命与改良的关系、自由获得方式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国家命运面临抉择之时,《大公报》树起“自由主义”旗帜,显示了难得的道德勇气和批判精神,堪称中国自由主义的“绝唱”。[※注]黄尚力指出,解放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特别是民主党派中一部分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近代中国继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三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呼声。这场争论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产而告结束。[※注]王卫华指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即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革命路线和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斗争。此外,还存在着一条介于两者的中间路线。中间路线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政治路线,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利益。解放战争时期,中间路线虽然对中国革命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对中国革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历史已经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间路线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发展成为国共两党之外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势力集团。在中国的前途及建国构想问题上,奉行一条折中调和、改良的,既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主义的中间路线,认为“只有兼采资本主义制度中之政治自由,与共产主义制度中之经济平等两大原则,调和而为一种新的主义、新的路线,才能够把人类引入真正的和平幸福之境”。然而不幸因其弱小,作为中间路线中流砥柱的民盟于1947年10月被当局强逼解散,这在史学界被称为“中间路线的破产”。多数论者在研究其“破产”的原因时,普遍认为,中间路线那种糅合欧美式的民主自由与苏联的经济平等为一体的政治主张,希望通过不流血的和平道路建立起不纯粹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方案,不符合中国国情,是行不通的,因此难逃“破产”的厄运。但他认为,这条路线具有相当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色彩,与中共的若干政策具有相通之处,从而消除了民主党派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偏见和误解,主动走上与中共长期合作的道路;同时,在中共过渡时期的政策中也能看到中间路线一些政治主张的痕迹,因此中间路线不应当被冠以“破产”之贬词。[※注]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