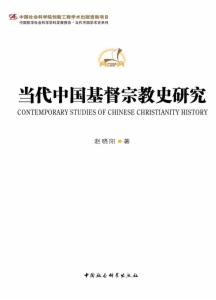第一节 《圣经》翻译
|
来 源
:
|
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1 | ||
|
摘 要
:
|
作为基督宗教最重要的经典, 《圣经》被翻译成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的过程,无论对基督宗教本身,还是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大陆地区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圣经》在中国的翻译过程及其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在1990年之前基本是空白。赵晓阳的《二马圣经译本与白日升圣经译本关系考辨》在吸取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文基督教《圣经》翻译史上几个早期译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她认为,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最早的《圣经》汉语完整译本——马士曼译本和马礼逊译本(统称“二马译本”)于1822年和1823年分别在印度和中国出版,从此开启了基督教新教陆续翻译出版多达三十余种汉语文言、白话和方言版本《圣经》的历史。 | ||||||
|
关键词
:
|
圣经 译本 赞美诗 传教士 方言 翻译过程 东正教 天主教 学者 满文 大陆地区 |
||||||
在线阅读
第一节 《圣经》翻译
字体:大中小
作为基督宗教最重要的经典,《圣经》被翻译成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的过程,无论对基督宗教本身,还是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大陆地区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圣经》在中国的翻译过程及其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在1990年之前基本是空白。1990年以后这一问题逐渐引起历史学者的重视,并逐渐成为基督教历史研究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
一 《圣经》汉语及方言译本
有关《圣经》汉语译本的研究是中国大陆地区所开展《圣经》汉译史最早涉及的领域,出现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研究涉及《圣经》译本的各种版本、翻译的语言特征和翻译过程中所经历的多种争论。
马敏是大陆地区最早开始圣经译本历史研究的学者,他的《马士曼、拉沙与早期的 〈圣经〉 中译》,是大陆地区最早的一篇研究《圣经》翻译历史的文献。早期国内研究圣经学者一般认为,最早来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近代历史上系统地把《圣经》译成中文的第一人。他通过对牛津大学的波德林图书馆所藏马礼逊档案的阅读,敏锐地发现,在马礼逊翻译《圣经》的同时,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马士曼(JoshuaMarshman),在亚美尼亚籍助手拉沙(Joannes Lasser)的帮助下,在印度塞兰坡也开始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在翻译过程中,马士曼与马礼逊互有通信交流,针对这些信息,对马礼逊和马士曼两人谁最早翻译完成并出版《圣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注]
吴义雄在研究近代基督教与中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同时,也注意到《圣经》翻译过程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所产生的影响。他在《译名之争与早期的 〈圣经〉 中译》中认为,在早期中文《圣经》翻译历史上,“译名之争”是一个影响颇为深远的事件,这场争论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清代前期的“礼仪之争”。这场围绕着“God”或“Theos”等基督教核心名词如何中译而产生的争论,在1843—1851年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集体合作修订《圣经》中译本期间达到高潮。这场论争的主角是英国和美国传教士,他们各自坚持己见,展开了长期的论战。“译名之争”的结果,导致了早期新教传教士合作译经事业的结束,从另一方面来看,这项争论也促使其后多种《圣经》中译本相继问世。从中国近代基督教史及世界《圣经》翻译史来看,这次论争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注]
谭树林分析了马礼逊与马士曼(马士曼)两人的“二马译本”之间的关系。由于马礼逊与马士曼两人的《圣经》全译本有许多相合之处,当时在英国国内,马礼逊的名望比马士曼高,因此对两个译本无法做出正确判断的英国人,就相信米怜的说法,认为马士曼的译本是抄袭马礼逊的译本。但是从翻译、出版的时间上看,马士曼译本比马礼逊译本面世要早,尤其是与吉德所举“二马译本”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均是马士曼译本出版在先。谭氏根据大量中外文资料,重新梳理了两人的翻译过程,认为马士曼抄袭了马礼逊译本之说,在逻辑上似难成立,并纠正了这一历史上的成见。[※注]
戚印平的《“Deus”的汉语译词以及相关问题的考察》讨论了《圣经》中译过程中,围绕涉及神学概念的专业术语翻译争论、文化因素的交互影响问题展开。他认为,在研究16世纪之后的天主教东传史时,围绕着“Deus”等神学概念的“译名之争”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然而发生在中国的这一争执并非孤立的偶然事件,由于汉字在东南亚各国被广泛使用,并成为其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亦曾发生在日本和其他国家,这些问题与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尝试与努力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而使这一文化冲突表现得更加复杂而生动。[※注]
赵晓阳的《二马圣经译本与白日升圣经译本关系考辨》在吸取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文基督教《圣经》翻译史上几个早期译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她认为,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最早的《圣经》汉语完整译本——马士曼译本和马礼逊译本(统称“二马译本”)于1822年和1823年分别在印度和中国出版,从此开启了基督教新教陆续翻译出版多达三十余种汉语文言、白话和方言版本《圣经》的历史。在《新约》翻译上,二马译本受到了天主教白日升译本的奠基性影响,其中马士曼译本还参考了马礼逊译本;在《旧约》翻译过程中,因其他事务产生的纠纷,最终导致两人各自独立完成翻译。在参考天主教译本的基础上,两个译本还开始了剥离天主教话语系统、创建基督教汉语圣经话语系统的尝试。[※注]她的另一篇论文《译介再生中的本土文化和异域宗教:以天主、上帝的汉语译名为视角》讨论了《圣经》翻译过程中译名问题。认为《圣经》的中文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文字译介的问题,而且涉及西方宗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适应和转化,以及如何被中国本土社会所认同。在基督宗教唯一尊神的汉语译名问题上,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产生了长达300年的激烈争论。在西方宗教理念的阐释下,中国传统词汇“天主”“上帝”逐渐地被基督教化,失去了其原有本土宗教的内涵,再生演变为象征西方文化的新词语。除被天主教和基督教接受外,“上帝”译名还被更大范围的中国本土世俗社会接受。通过考察译名争议和被接受的过程,可知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外来新思想影响中国的方式和脉络。[※注]
刘念业对1838年出版的圣经“四人小组译本”在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上对《圣经》汉译事业均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深刻影响了后来著名的“委办本”和“和合本”。但因各种历史因素影响,宗教界和学术界对该译本多语焉不详,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作者通过对该译本多方面的探讨,希冀还原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注]
程小娟认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传教士在英文杂志《教务杂志》上几乎讨论了《圣经》汉译过程中涉及的所有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传教问题是其核心议题之一,其中包括翻译原则的确立、是否需要在译本中附加解释性材料及语体的选择等。文章认为,这些讨论为我们认识和反思传教士《圣经》汉译的历史及其遭遇的困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也为我们思考文化交流中的翻译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注]
梁慧、褚良才、黄天海以吴雷川与赵紫宸为个案的研究对象,以他们读《圣经》的原则与方法为例,说明中国文化的古老历史和宗教的多元化决定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多元宗教经典”构成的世界,这些为他们的信仰提出了各种挑战,创造出一种特别的阅读圣经的方法,试图以此为亚洲处境下的圣经诠释学提供研究的一个范本。[※注]
有关东正教《圣经》翻译的研究,与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相比,是比较薄弱的领域。肖玉秋对东正教在中国的官方传教机构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的经书翻译历史进行的大致梳理,指出东正教经书的翻译和刊布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直至1902年俄国在中国设立主教区,传教士团利用庚子赔款,开始了东正教经书的翻译出版工作,并出版了东正教所使用的《圣经》中文译本。[※注]
《圣经》的中文译本包括多种文字形式的汉语方言译本。由于中国方言差异非常大,彼此之间不能互通,于是产生了《圣经》方言译本。在这方面,也有学者开始予以关注。赵晓阳分别对闽方言、粤方言、吴方言、客家方言的《圣经》译本进行了考述,说明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的这些方言有大量的汉字和罗马字《圣经》译本,这里是中国方言种类最多、最复杂的地区,是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最早的地区,也是信徒最多的地区。其中,福州、厦门、汕头、兴化、建阳、海南、上海、宁波、苏州、杭州、台州、温州、金华、客家等众多的方言都有译本。[※注]
大量使用罗马字母翻译《圣经》,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一个独具特色的事件。传教士考虑到信徒中有大量文盲(不识汉字),即考虑采取拼音文字的方法进行翻译,由于拼音文字简单易学,基本上能做到即读即写,大量文盲信徒通过使用这种文字了解其信仰经典的内容,但是由于这种文字仅仅限于宗教用途(只有极少量世俗读物),根本无法与强大的汉字抗衡,目前除个别方言文字外,基本上不再有人使用。传教士进行汉语罗马化拼写尝试的一个积极结果,就是为汉语拼音的创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从历史学角度对汉语教会罗马字拼写系统以及社会、文化影响进行全面研究,不仅有语言学意义,而且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关于汉语罗马字的意义,首先被认为是汉语拼音系统的源头之一,也认为有助于文盲读音断字。但是有关文字拼写系统分化给社会造成的多重影响,尚未见有大陆地区学者讨论。在台湾地区,方言罗马字曾经被特定人群用作与中华文化切割的手段之一。放弃“书同文”的长期结果,必然会带来语言的分化及政治的分离。如果我们考察欧洲语言的文化变迁史,就能充分印证这一点。
赵晓阳是大陆地区针对圣经汉译史展开研究较为深入的学者之一。她的有关圣经译本的系列论文从多种角度对《圣经》的汉译过程和版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解决了之前学术界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圣经中译史研究的学术回顾和展望》一文则对近来大陆地区有关《圣经》翻译史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系统回顾,指出《圣经》是基督教的唯一经典,圣经翻译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重要事件。在中国境内,出现了包括汉语汉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众多圣经译本,这不仅使《圣经》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翻译版本最多的书籍,而且对中国的汉语汉字的近代转型和少数民族文字创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从三个方面对圣经中译的历史、资料、研究及展望进行了叙述。[※注]
二 《圣经》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圣经》也被翻译成中国境内主要的少数民族文字,其最早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朝。据文献记载,《圣经》曾经被翻译成蒙古文。天主教传教士贺清泰曾经将《圣经》翻译成满文,但没有出版。近代以来,《圣经》被翻译成北方几种历史较为悠久的少数民族文字,如蒙古文、满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都有本民族文字的《圣经》译本,其中蒙古文还有几种方言译本。在南方少数民族中,《圣经》被翻译成藏文、傣文等。出于翻译《圣经》需要,传教士创制了景颇文、傈僳文、佤文和几种苗族文字等。这些新创制文字中,有部分文字,如景颇文等,应用功能扩大到宗教范围之外,为整个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近几年来,有学者开始注意到用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圣经的问题,并已经有数篇文章探讨此类问题。薛莲对大连图书馆收藏的满文《新约全书》进行了研究。满文《圣经》是历史上第一部铅印的满文图书,传世稀少。其翻译者是19世纪俄国东正教传教士斯捷潘·利波佐夫。该书翻译工作与初次出版都不在中国本土,但其装帧却是典型的中国古籍形式。作者从语言学角度分析,满文《新约全书》语言平实流畅,语法严谨,不失为满文翻译领域的杰作。[※注]
傈僳族是受基督教影响很大的少数民族,信教人数在民族中占有较高的比例。王再兴指出,基督教传教士创制傈僳族文字并翻译了傈僳文《圣经》,引发了傈僳族大规模皈依浪潮,对傈僳族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结束了傈僳族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结绳记事的文化形态,推动了基督教自身在傈僳族地区的本土化,还导致了傈僳族社会与文化的巨变等。[※注]
王再兴和王贵生对苗语的不同地区的圣经版本进行了考察,讨论了传教士为所在苗族方言区创制文字,并翻译《圣经》后对所在地区信徒造成的直接或潜在的文化影响。[※注]
三 赞美诗研究
赞美诗虽然不属于基督教宗教经典,但它的应用范围却是在各类宗教仪式上,具有强烈的宗教神圣意义。赞美诗是基督教用来赞美上帝的一种诗歌形式,是其宗教仪式中所用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礼拜时信徒咏唱的诗歌和音乐作品。其主要内容都是歌颂上帝、表现教会生活和信徒灵修等。因此,我们把有关赞美诗的研究也列入本节范围。1979年以来,大陆地区学者逐渐开始对中国基督教界赞美诗创作、翻译和使用的历史进行研究,已经有数篇论文发表,包括对个别少数民族语言赞美诗的研究。
基督教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可追溯到唐代景教时期。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手抄本《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和《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即是此音乐现象的文本。
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作为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开启了新教的中文圣诗的历程。1808年,马礼逊出版了《养心神诗》。之后,大量文言文赞美诗或方言赞美诗,或配五线谱,赞美诗不断出版,成为中国基督教会宗教活动的必需品。这些都成为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最大的赞美诗《普天颂赞》的生成背景。1936年,由基督教六公会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普天颂赞》。
目前,对中国赞美诗的研究还很局限,基本只有对《普天颂赞》的某一点做初步研究。林苗、和田飞分别研究了《普天颂赞》产生的历史过程,指出这本赞美诗一经发行,即在基督教信仰范围里广受赞扬,在1947年曾发行了37.8万册。除所用曲调直接引进西方音乐外,还在中国基督教会本土化的号召下,有些曲调借用了中国传统民间音乐,诸如词牌、民歌、古曲、吟诗调等,在马革顺、周淑安、杨荫浏等著名音乐家的努力下,将传统音乐曲调改编而得以保存。歌词除直接翻译外,还有众多信徒的本土化努力和创作。[※注]赵庆文撰写了目前对中文赞美诗的编译过程展开系统梳理分析的少数几篇论文,分析了1936年由基督教在华六公会共同出版的《普天颂赞》圣诗集,认为《普天颂赞》中吸收了大量的中国元素,代表了其时基督教音乐的最高水平,反映了基督教本色化理论在音乐方面的具体体现。《普天颂赞》的出版,是近代赞美诗经由个人编译、团体协作、最终联合编译的结果,其影响巨大,在中国基督教音乐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注]龙伟还研究了1818—1911年基督新教职工的方言赞美诗诗集的出版情况,可知早期的方言赞美诗的比例大于官话赞美诗,并集中在方言最为复杂、基督新教最早传入的东南沿海地区。[※注]
截至目前,有关天主教和东正教赞美诗的研究尚未见到。此外,对于汉语方言赞美诗和少数民族语言赞美诗的研究,也是有待未来学者开展研究的领域之一。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