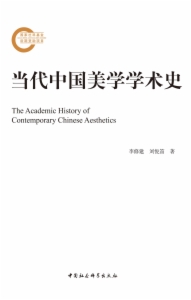第三章 西方美学史研究
|
来 源
:
|
当代中国美学学术史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2 | ||
|
摘 要
:
|
主要包括安海姆(又译阿恩海姆)的“完形心理学美学”、弗洛伊德和融恩(又译荣格)的“心理分析美学”、桑塔耶那的“自然主义美学”、杜威和佩珀的“实用主义美学”、芒罗(又译门罗)的“新自然主义美学”、科林伍德和理德的“表现论美学”、杜夫海纳的“现象学美学”、理查兹的“新实证主义美学”、维特根斯坦和韦兹的“分析美学”、卡西勒与朗格的“符号论美学”。并按照表现主义美学、自然主义美学、形式主义美学、精神分析美学、分析美学、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符号论美学、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社会批判美学、结构主义美学与解释学美学的顺序加以了梳理,从而使其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小通史”。 | ||||||
|
关键词
:
|
美学 西方美学 美学思想 艺术 专著 哲学 美学家 通史 学界 现象学 现象学美学 |
||||||
在线阅读
第三章 西方美学史研究
字体:大中小
第一节 美学通史研究
真正全面论述“西方美学史”的第一篇文章,应该是朱光潜1963年《文汇报》3月23日发表的《美学史的对象、意义和研究方法》,[※注]这篇文章未收曾入朱光潜旧版全集的文章,经过笔者的对照发现,基本上是后来成书的《西方美学史》的“序论”部分的学术缩写版本。更早在1961年8月13日《文汇报》上,朱光潜还曾发表《怎样整理美学遗产》一文,对于美学史的研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到了1978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朱光潜又撰写了《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一文,对于自己的美学史研究方法与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总结,并重在质疑与重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美学的适用性。[※注]
从《美学史的对象、意义和研究方法》这篇文章开始,朱光潜最终确定了西方美学史研究的“对象”:从学科独立来看,美学由文艺批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附庸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从历史发展看,西方美学思想始终侧重在“文艺理论”,也是“根据文艺创作实践作出结论”,又转过来“指导创作实践”。然后,按照朱光潜所接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由于美学也要符合“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回到实践”这条规律,所以,美学就必然要侧重社会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文艺方面的问题,美学必然主要地成为文艺理论或“艺术哲学”。“艺术美”是美的“最高度集中的表现”,所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文艺也应该是美学的“主要对象”。当然,朱光潜所虚心接受并服膺的美学史的研究方法,其指导原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显然,历史唯物主义较之辩证唯物主义更适用于历史的撰写,所以,朱光潜认定研究美学史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南。[※注]
在《西方美学史》成书之前,朱光潜发表了多篇构成了美学史著作主要构成部分的文章,主要包括《克罗齐美学的批判》(《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黑格尔美学的基本原理》和《黑格尔美学体系》(《哲学研究》1959年第8、9期)、《莱辛的〈拉奥孔〉》(《文艺报》1961年第1期)、《狄德罗对艺术与自然的看法》(《光明日报》1961年2月23 日)、《亚里斯多德的美学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2期)、《黑格尔美学的评价》(《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5期)、《法国新古典主义的美学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德国启蒙运动中的美学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维柯的美学思想》(《学术月刊》1962年第11期)、《席勒的美学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除了《关于考德威尔的“论美”》(《译文》1958年第5期)之外,这些文章的主要思想都在《西方美学史》当中得以充分展开。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于1963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版,下册于1964年8月首版,1979年上下两册经过修订后,6月上册出第二版,11月下册出第二版,这也是目前最为通行的版本,此后不断被再版与翻印,其余的出版社也纷纷出版这本经典著作。这本美学史从一开始就满足了高校文科教学与学术启蒙的需要,被誉为“一部具有开创性的教材,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西方美学史》,而且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写成的《西方美学史》”,而且,“善于从全局的观点出发来分析和评价每一个美学家和每一个美学问题”。[※注]该书的成书过程是这样的,供职于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朱光潜1961年应哲学系的需要,为培训讲授美学课的教师而特设美学专业班授课,遂开始编写西方美学史讲义;1962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举行文科教材会议,组织编写美学概论、西方美学史与中国美学史教材,并将西方美学史列入教材编写规划。朱光潜由此根据自己编写的讲义、学习笔记和资料译稿,编写出了两卷本的《西方美学史》。从历史上来看,世界上第一部美学史专著实际上是德国人科莱尔(Koller)1799年出版的《美学史草稿》也是出于教育的目的(贝特尤斯的1747年出版的《艺术美的体系》则尚未形成完整的历史体系),这本叙述到18世纪的美学史的撰写目的,就是为了给德国大学生们指明“美学的产生及其发展的一份明晰的纲要”,朱光潜的美学史也是如此。当然,齐默尔曼(Zimermann)1858年在维也纳出版的三卷本《作为哲学科学的美学史》通常被西方学界当做开创美学史的首部著作,它所强调的哲学视角一直在后来的美学史当中(包括朱光潜的相关著述)所贯穿下来。
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文艺复兴,第二部分是17、18世纪和启蒙运动,第三部分则为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从前苏格拉底时期一直贯穿到克罗齐时代,可谓是贯通古今的简要通史。相比较而言,美国分析美学家门罗·比尔兹利(Monroe Beardsley)1966年首版的《从古希腊到现在的美学史——一段简史》(Aesthetics from Classical Greece to the Present:A Short History),[※注]无论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美学史的价值与影响观之,它在欧美的美学界的地位颇有点类似于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在中国的位置。当然,比尔兹利以分析美学家独特的明晰性言简意赅地梳理了整个西方美学史,这部“简史”在当时也是“全史”,不同于朱光潜写到20世纪初就戛然而止,比尔兹利从美学的起源一直写到出书的20世纪60年代。朱光潜并未写完整恐怕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由于社会原因即所谓“现代资产阶级美学”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因而尼采与叔本华美学就被回避了),二是由于当时学界只向苏联开放从而脱离了国际美学发展的主流,朱光潜更愿意驾轻就熟地写作他留学期间所学到的美学思想。如果进一步比照就会发现:朱光潜的历史写作的确具有中国化的风格与特质,它既不同于苏联的美学史撰写范式,也不同于欧美的美学史书写的基本模式。
实际上,对中国美学界产生了直接影响的翻译过来的西方美学史著作,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产生影响,这些美学史的一部分是来自苏联的美学家,其中有非常出色地梳理了历史材料的奥夫相尼科夫的《美学思想史》(吴安迪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善于采取辩证批判态度的舍斯塔科夫的《美学史纲》(樊莘森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另一部分产生更重要影响的是来自欧美的美学家,其中,最为流行并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是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英国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的《美学史》(张今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初版),由于其黑格尔化的色彩而被中国学者广为接受,他的《美学三讲》(周煦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早就被翻译出版了。尽管鲍桑葵本人在其规划的初衷里面视美学史为深植于各个时代的生活之内的“审美意识”的历史,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当中,他却主要面对的是经过思想家们整理过后的思辨理论,正如他对于希腊美学的“道德主义原则”、“形而上学原则”和“审美(形式)原则”的归纳一样,他的书写方式始终是哲学抽象化的。
在中国美学界,影响最大的还是被当做美学史兼艺术史来读的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sthetik),这本由黑格尔他的学生霍托(Heinrich Gustar Hotho)根据听课笔记并核对于黑格尔本人的授课提纲编纂而成的书,德文版于1835年到1838年分三卷出版,在中国被朱光潜主要借助英文并参照德文翻译出版,这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收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当中,共历时三年才得以全部完成,1979年1月出版了第一卷和第二卷,1979年11月出版社了第三卷的上册,1981年7月才出版了第三卷的下册。以朱光潜的笔调翻译过来的《美学》三卷,在中国美学界的翻译著作当中可能产生了最为巨大的内在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在于对西方美学的基本理解,而且也深入到了对于美学原理的主流建设当中。
相比较之下,由于深受黑格尔主义的影响,较之鲍桑葵更晚近的美学史似乎影响就没有前者那么深远,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1902年出版的《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王天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由于过于关注于语言问题而偏离了大众的期待视野。美国学者吉尔伯特(K.E.Gilbert)和库恩(H.Kuhn)的《美学史》(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由于出版于1939年的纽约,在当时可以说是最新近的美学史,但是这本专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更多在于其史料的价值。实际上,目前为止世界上公认的最有质量的西方美学史,还是来自于波兰著名美学家塔塔科维兹(W.Tatarkiewicz)1962年在波兰首版的三卷本的美学史,具体包括古代美学、中世纪美学和现代美学三个部分,尽管他只写到了17世纪(这是塔塔科维兹用语上的现代时期)没有涉及现当代,但是这套美学史的确是西方美学史撰写史上的历史标杆。[※注]塔塔科维兹的《美学史》的第一卷《古代美学》有两个译本(杨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理然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二卷《中世纪美学》(褚朔维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卷《现代美学》目前正在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寻译者翻译,争取将这三卷本出齐并收入再度启动的“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当中。
通过与这些在欧美俄苏出现的美学史相参照,拥有“中国第一部西方美学史”美誉的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具有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本土化的特色,它可谓是一部“中国的”美学史。这具体体现在材料的选择和史实的安排上面,从而使得朱光潜之后的“在中国”的西方美学史研究由此具有了为自身而设定的格局。按照朱光潜的原本设想与最终实施,对主要美学流派中的主要代表的选择只有符合如下的标准,那就是“代表性较大”,“影响较深远”,“公认为经典性权威”,“可说明历史发展线索”,“有积极意义”,足资借鉴的才能最终“入选”《西方美学史》。从这几条标准来看,朱光潜也就是“以点代面”式地选取了主要流派当中的主要人物,这就非常接近马克思主义“典型说”当中所说的要选择“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只不过朱光潜将这些人物放置到“唯物史观”的历史线索当中,并以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对其进行了评价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如果与苏联美学史比较而言却并不具有更鲜明的特色。
按照共和国建立早期的教材模式,《西方美学史》在撰写模式上采取了“时代背景—人物简介—著述介绍—思想呈现”的结构方式,当时的中外文学史都按照这种模式进行了重新书写。由此形成的所谓的“朱光潜模式”,对于中国化的西方美学史的撰写产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影响。在这种基本格局之下,朱光潜对于美学史人物的选择可谓是千挑万选而最终确定,后来的西方美学史入选的最重要人物也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而且朱光潜的历史叙述始终强调历史的逻辑线索。所以,我们看到了《西方美学史》这样的人物名单与逻辑次序:前苏格拉底时代精选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在苏格拉底之后,是两位无论如何也都占据最重要地位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罗马时期选择的是贺拉斯、朗吉弩斯,普罗丁作为连接罗马与中世纪的重要环节;中世纪选择的当然是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而但丁则成为了连接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重要环节;对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选择,朱光潜显得过于简单并与众不同,所选的是薄迦丘、达·芬奇和卡斯特尔维屈罗等;法国古典主义选择的逻辑起点是笛卡尔,其后就是布瓦罗;英国经验主义的逻辑起点是培根,其后人物丰富,霍布斯、洛克、夏夫兹博里、哈奇生、休谟和伯克都得以充分论述;启蒙主义运动的美学思想,在前苏联美学史当中较之欧美占据更重要的地位,法国启蒙美学被选入的无疑就是伏尔泰、卢骚和狄德罗,其中狄德罗“美在关系说”由于其唯物主义倾向被格外被重视;德国启蒙运动有高特雪莱、鲍姆嘉通、文克尔曼和莱辛,“美学之父”鲍姆嘉通的思想无疑是这段美学的亮点与重点,但是赫尔德这位相当重要的美学家却被忽视了;意大利历史学派选择的是维科,朱光潜对这位关注“诗性的智慧”的思想家情有独钟;德国古典美学当然是朱光潜在叙述古希腊美学之外的第二个高峰时段,他的经典选择就是从康德开始,以歌德与席勒为中介环节,最终终结在“集大成者”黑格尔,但遗憾的是却相对忽视了费希特与谢林,对于德国古典美学(欧美学界称之为所谓“德国唯心论”美学)的特别关注,成为了中国学界的共识与兴趣所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这是中国美学界接近于俄苏的地方,选择的分别是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在中国的许多西方美学简史都愿意结束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理论,并将之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之前最为成熟的唯物主义美学形态;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审美移情派成为了新旧世纪的转折力量之一,遗憾的是朱光潜只关注了其中的费肖尔、立普斯、谷鲁斯、浮龙·李和以巴希(这份名单有所遗漏),并刻意遗漏了唯意志美学的两位大家尼采与叔本华;好在《西方美学史》最终结束在朱光潜颇为心仪的表现主义美学大家克罗齐,以20世纪西方美学的曙光终结了美学的整个的西方历程。
以世界范围内的美学史撰写作为比照,由《西方美学史》这种历史叙述,可以看到,朱光潜的撰写模式既同于又不同于在西方的美学史梳理,因为叙述的线索基本就是按照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德国古典美学的顺序,而且又接上西方审美心理学诸派和克罗齐思想,但是与同时代的欧美的书写不同,朱光潜并没有关注现代美学更新的进展;同时,这种中国化的美学史既同于又不同于前苏联的美学史,相同的就是都将德国古典美学作为叙事的第二个重要的环节,并认定西方美学史的发展过程从古希腊至德国古典美学是自低向高发展的,这种唯物化的进化模式在前苏联美学看来,发展到俄国民主主义才达到了历史的高点,但是朱光潜尽管将俄国民主主义纳入其中,但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将移情派与克罗齐的线索置于最后,但是两者的内心的诉求都是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最终成立才是整个叙事的逻辑终点,“前马克思主义”美学从这种历史发展来看都犹如万江归海一般要在终点得以“辩证整合”。
在后来的西方美学是写作当中,这种“朱光潜模式”最明显地被抛弃的,主要就是那种“逻辑叙事”的部分,其中最明显的就数《西方美学史》结束语当中对于四个关键问题的历史小结,这四个关键词分别是“美的本质”、“形象思维”、“典型人物”、“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注]现在回过头来看,从历史的顺序观之,典型人物由于仅囿于机械反映论而最早被扬弃,[※注]然后是形象思维论被“审美心理学”所替代,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也被更多视为文艺问题,只有通过“美的本质”来通贯美学史的方式至今也没有被彻底去除。事实也证明,用后三个关键词来统西方美学史也是不可能的,那只会得出局限于唯物主义理论的陋论,但是用美的本质来统合从古希腊到20世纪前叶的“西方的”美学史还是基本可行的。然而如果不考虑这种历史的逻辑发展,那么,塔塔科维兹对于西方美学史对象的理解,可能更加接近历史本身,由此美学史的疆界才可以被充分打开:西方美学史理应包括“美学思想史”与“美学名词史”、“外显美学史”与“内隐美学史”、美学“陈述史”与美学“阐释史”、“美学发现的历史”与“美学思想流行的历史”,[※注]理想形态的西方美学史恰恰应该是两方面的统一与整合。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文革”的前夜,从译介的角度来看,大量的国外美学资料继续得以介绍进来,其中,非常重要的丛书和文选有:创始于1959年的《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根据1961年制定的丛书规划,前者计划出版39种(迄今共出版19种),后者计划出版12种(迄今共出版11种);由现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组1957年7月创办的《文艺理论译丛》直到1958年12月为止共出了六期后而停刊,1961年又继续出刊直到1965年止共出11期;由伍蠡甫主编的《西方文论选》上下卷也是1963年至1964年组织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的。
在此,就仅以《文艺理论译丛》的主要内容为例来说明当时的译介情况,第一期主要译介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者的有关言论,第二期主要译介近代德国和法国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第三期主要译介莎士比亚,第四期主要译介东欧国家作家的文章,第五期主要译介18世纪西欧美学思想,第六期主要译介欧洲的悲剧理论,第七期主要译介欧洲的喜剧理论,第八期主要译介19世纪中期以后三位美学家的思想,第九期主要译介莎士比亚评论的文章,第十期主要译介印度古代文艺理论和日本古代文艺理论,第十一期主要为“形象思维”资料专题与戏剧美学研究。通过这份具有选本性质的译丛的介绍,可以看到,在当时占据绝对主流的译介内容,主要就是欧洲古典美学与文艺理论思想,当然东方思想与现代理论也有所涉及。《文艺理论译丛》因不拟刊载当代的文章或资料,从再刊之日起就改名为《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同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苏联文学研究室承办的《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从1963年出版第1期到1964年出版第6期,尽管译丛名表明为“现代”,但是绝大多数的译文都是来自于苏联的研究,或者说是通过“苏联桥”来看待外国美学与文艺思想。
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的历史研究之外,对于西方美学史较早进行个案研究的专著是汝信主笔的1963年4月出版的《西方美学史论丛》,[※注]这本直接以“西方美学史”为题的专著也是共和国建立后第一本西方美学专著,较之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的出版还要早3个月。与朱光潜直接留学海外不同,汝信的西方美学的人物思想研究可以被视为他的导师贺麟先生的西方哲学研究在美学领域的延伸,作者在1961年还与姜丕之合著了《黑格尔范畴论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即普罗丁)、莱辛、康德与18世纪英国美学、黑格尔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西方美学史论丛》以点带面地勾勒出西方美学史的历史大趋势。该书的某些内容都曾以人物研究的方式单篇发表,《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美学的批判——兼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观点的哲学基础》(原载《哲学研究》1958年第1期)作为第一篇论文可以看做汝信进入西方美学史研究的起点,其他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重点文章还有《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兼论亚里士多德对他的批判》(原载《哲学研究》1961年第6期)、《伯克美学思想述评》(原载《新建设》1963年第2期)、《黑格尔的悲剧论》(原载《哲学研究》1962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都抓住了西方美学史上最重要的形象进行了思想描述。
从《西方美学史论丛》到《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汝信对于19世纪启蒙时期“高特谢德—鲍姆加敦—温克尔曼—莱辛—赫尔德—福斯特”发展线索的勾勒,直到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康德—席勒—谢林—黑格尔”的具体深描,还有狄德罗、伯克、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叔本华、尼采与杜威的美学思想,都从不同的切入点进行了深入研究,所以说,这两本西方美学史论丛理应被视为一个整体。在这种研究过程当中,作者不断取得了新的认识: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进行了对照性的研究,对朱光潜的柏拉图灵感说与摹仿说的关系也提出了质疑,认定亚里士多德美感与伦理的目的论不能完全分开,全面解析了普罗提诺这位亚历山大理亚派希腊哲学家的殿军的美学思想,整体描述了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美学的内在逻辑线索,较早深入研究了谢林《艺术哲学》所显现的美学思想,将席勒的美学作为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到黑格尔的《美学》之间的环节,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厘清了其对西方美学的误解。
实际上,汝信最为心仪的还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他从这一美学思想入门,直接导入对黑格尔美学的关注(特别是青年黑格尔的关于人的思想),进而上追到古希腊美学思想,从而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主要思想为基本评判标准,将西方美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思想面貌着重呈现出来。与此同时,更应该看到,汝信的美学史研究当中体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关怀,这是“因为对于美学来说,历史的研究首先不是自然史,而是社会史,也就是人的历史。人始终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注]既然任何一种美学问题都离不开人的存在,那么,研究人与重视人的“人道主义传统”就成为贯穿汝信美学研究的红线。
自从1963年朱光潜开始出版《西方美学史》上卷和汝信、杨宇的《西方美学史论丛》出版之后,更准确地说,在《西方美学史》下卷次年出版之后,在中国的西方美学史研究曾一度衰落。往前看,在《西方美学史》与《西方美学史论丛》之前,中国还没有以“西方美学史”作为标题的专著出版,往后看,直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美学史》再版与《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出版之前,都没有以西方美学史为题的相关著作出现,可见这上下卷与两本论丛本应具有的历史价值。从80年代初期开始,西方美学史研究衰退的局面得到了改观,西方美学研究的专题论文陆续开始出现。随着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被反复重印和再版,其撰写范本也成为了中国式的西方美学史撰写的“基本范式”,其影响的深远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学术影响并不局限在大陆地区,港台地区的美学界也深受这本《西方美学史》的影响,这也就是上文所谈到的“朱光潜模式”,这种模式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东亚学界看待西方美学的独特撰写方式。
目前为止,在中国最大部头的“大通史”就是由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该书为国家社科基金“八五”、“九五”规划重点研究成果,并被当做为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献礼图书。该通史根据西方哲学和美学基本同步发展的实际,将整个西方美学的历史演进划分为“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学”三个阶段,从而力图揭示出西方整体历史的基本发展规律。按照这种区分,本体论阶段从古希腊罗马到16世纪,其中“古希腊美学就是本体论美学,是当时哲学本体论在美学上的展开与体现,也是西方美学史上本体论阶段最典型、最重要的显现”。[※注]认识论阶段从17世纪到19世纪,在哲学和美学的认识论转向过程中,“英国经验主义”与“大陆理性主义”从两条对立的线路上分别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德国古典美学才是西方“认识论美学”的完成阶段。所谓“语言学阶段”则主要就20世纪而言,尽管“语言学转向”在西方哲学语境当中主要是指英美的逻辑实证主义与分析哲学而言,但《西方美学通史》认为,这种转向也体现在大陆人本主义的脉络当中,从现象学、存在主义到解释学的美学都可以纳入到这种转向当中,更具体来说,“实证—分析美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美学”、“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美学”这三个方向、三种思潮、三股力量共同作用而推动了20世纪美学的“语言学转向”的整体发展。
《西方美学通史》不仅从历史的角度将整个西方美学史梳理为“三大阶段”,而且从逻辑的角度将整个西方美学归纳为“两大主线”,也就是被赋予了广义内涵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分别代表了西方美学这两大重要传统的开端,中世纪初期与末期的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也分属于两派,“十七世纪西欧美学分化为旗帜鲜明的两大派,即大陆理想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这正好可以看做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两大传统在新时代的延续和发展”。[※注]18世纪的启蒙主义美学也在延续这两条主线,狄德罗的法国启蒙美学思想总体上更倾向于经验主义,德国启蒙主义美学家则更多保持了理性主义的余韵。德国古典美学则是对17、18世纪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两大主流的“总结和综合”,这是依据中国化的西方哲学史研究直接推论的结果。19世纪原来的经验主义发展为实证主义,进而发展为与科学理性的相互融合,而原本的理性主义则导致了非理性主义的抬头。唯独20世纪的美学难以纳入这种格局,所以《西方美学通史》又继续采取了“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两大主潮来应对20世纪的整个西方美学的历史。
《西方美学通史》第一卷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美学由范明生著,共74万字,该卷更多关注从哲学系统的观照当中来阐释美学思想,并得益于在国内的古希腊罗马的哲学相关研究。[※注]其中的两处亮点,一个就是对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美学的详尽阐释,从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到德谟克利特都多有研究,另一个则是对希腊化和罗马时代的美学的深入研究,主要增加了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怀疑论学派和折中主义的美学思想。第二卷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由陆扬著,共42万字。[※注]该卷在美学史方面有着更多的突破,特别是对于中世纪美学的研究的确扩大了传统的疆域,作者在原来的人物基础上不仅增加了圣经的美学思想和拜占庭圣像之争的论述,对于伪狄奥尼修、波爱修的论述,对于中世纪民间文艺美学的论述,对于国内来说都是崭新的。此外,对于12、13世纪的“神秘主义美学”与“经院美学”的内在谱系都进行了相对完整的阐释。对于文艺复兴时代美学的论述,作者不仅按常规论述了诸多人物思想,进而将美学与音乐美学分而述之,到了16世纪美学则又换取了另一种标准,分头论述了德国、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美学思想。第三卷17、18世纪的美学由范明生著,共72万字。[※注]该卷采取了国别史的方式,分别论述了从培根开始的英国美学(新增了弥尔顿、德莱顿、蒲柏、菲尔丁、约翰逊、雷诺兹的美学思想)、以笛卡尔为起点的法国美学(新增了帕斯卡尔的美学思想)、众星云集的德国美学(新增了赫尔德的美学思想)和以维柯为代表的意大利美学。
《西方美学通史》第四卷德国古典美学由曹俊峰、朱立元、张玉能、蒋孔阳著,近63万字,该卷是整个通史的重点中之重,也可以被看做是以蒋孔阳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研究的延续,[※注]曹俊峰、张玉能和朱立元当初追随蒋孔阳攻读学位的论文所研究的分别就是康德美学、席勒与黑格尔美学。这卷的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康德与黑格尔美学思想的研究,不仅注重整个的逻辑结构的呈现,而且按照他们美学思想形成的历史顺序进行了论述。康德美学思想的进程就被区分为“前批判期”、“过渡期”与“批判时期”,并关注到了康德晚年及其遗著当中的美学思想。黑格尔美学也从前期美学思想谈起,并阐发了《精神现象学》当中的美学思想,也兼及了黑格尔对于康德、费希特、席勒、谢林和浪漫主义思想的批判,同时关注到了“艺术解体”的新阐释与《美学》的内在矛盾所在。第五卷19世纪的美学由张玉能、陆扬、张德兴等著,共62万字,也继续采取了国别史的格局,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俄罗斯民主主义美学思想也被纳入其中。[※注]德法英诸国的美学史的区分都非常宏观,在以黑格尔主义与新康德主义为主导的哲学美学之后,具体区分出形式主义美学、心理学美学、生命哲学的美学、艺术科学与唯意志论美学等五个派系,法国美学区分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实证主义美学、唯美主义与折中主义美学的六个派系,英国美学则区分为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社会学美学、新黑格尔主义美学、心理学美学、进化论美学的六个派系,从而非常精当地论述了近代西方美学主潮。
第六卷和第七卷20世纪的美学由朱立元、张德兴等著,部头最大共125万字,该卷采取了“现代人本主义美学”与“现代科学主义美学”历史性对立的方式加以立论,将现代西方美学区分为“形成、初创时期”(新世纪开始到20年代末),“多元展开时期”(30年代到50年代)、“变动、成熟时期”(60年代以后到80年代之前)和“八九十年代的前沿思潮”四个阶段。[※注]更有特色的是,该卷从研究重点与理论特征方面试图归纳出现代西方美学的基本走向:一方面,两次研究重点的历史性转向分别是从艺术家和创作转移到研究文本方面,从文本研究转向研究读者和接受方面;另一方面,两个根本的转向就在于所谓的从“非理性转向”到“语言学转向”,这两卷的整个论述也贯彻了两大“主潮”、两次“转移”和两个“转向”的基本观点。
进入新的世纪,从2001年开始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汝信主编的《西方美学史》共四卷成为了最新的一部“大通史”,这270万字的四卷本著作共历时近8年方才完成,集中了当代中国美学界老中青三代学者来共同撰写。该美学通史将“美学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发展着的美学思想史,从而将“哲学理念”、“艺术元理论”和“审美风尚”三者结合与互动的逻辑建构的“美学思想”重新置入历史框架内,最终形成了立体型的完整化的历史整体。[※注]这本专著由于对“西方”、“美学”、“历史”三个关键词进行了明确而深入的理解与阐释,从而在总体的研究方法论上获得了新的突破:首先,将“西方”视为以地域概念为基础的文化思想范畴,因而考虑到了以范畴外延来充实这个范畴的合法性问题(比如充实了德意志观念论哲学家的美学在俄国和北欧的影响、法国当代美学的国际影响等方面的内容等等),同时,将美学思想的地域空间的民族文化特点注入到“西方”这个概念的内涵当中;其次,考虑到了西方思想史和学术史对“美学”的三种主要理解的各自的逻辑合理性,从而确定了根据思想的历史实际,将哲学、艺术思想、审美风尚情趣的解释和研究工作结合起来;最后,以学术史为基础,注意梳理和综合学术史、思想史、社会史以及普遍的大历史几个层面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注]
汝信主编的《西方美学》第一卷为“西方古代美学”,分为古希腊罗马美学和中世纪美学两编,分头由凌继尧、徐恒醇撰写。[※注]该卷创新之处在于,首先重新评价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认定柏拉图的理念是以素朴的方式提出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他力图以这种规律来替代古老的神话,柏拉图对万物规律的探索表明了由神话向人的思维的深刻变革;其次,重新评价了柏拉图美学和亚里士多德美学的关系,认定柏拉图哲学和美学的核心范畴“理念”几乎整个地转移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尽管二者都不会舍弃物的理念来思考物,但后者区分于前者就在于认定物的理念存在于物自身,而不存在于物之外的原理;再次,重新评价了普洛丁的美学思想,认定这位作为希腊罗马和中世纪之交的美学家的思想并没有越出希腊罗马美学的界限。古代卷在各种社会思想现象的关联中(如对柏拉图著作中哲学与诗、逻各斯和神话的结合),揭示了古代美学内涵的丰富性、复杂和矛盾性,而且注重揭示历史内涵的当代启示(如对寓意与象征的关系,宗教经典文化意象和审美内涵的关系都进行了新的学术挖掘)。
第二卷为“西方近代美学”的上部,分为文艺复兴时期美学与启蒙运动时期美学两编,由彭立勋、邱紫华、吴予敏著。[※注]该卷从宏观上着重于思潮、流派以及各种问题、理论、学说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突破了罗列和复述的传统研究模式,重在解释思想发展的有机整体性和内在规律性,对休谟的美的本质观、伯克的崇高理论、狄德罗的美在关系论、莱辛的市民戏剧理论、维柯的审美移情论的阐释,不仅遵循这种规律而且皆有新的解读。同时,从微观上在阐释文艺复兴、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时期的美学思想时,既注意这些理论和学说(如内在感官说、审美趣味论、美在和谐论、美即完善论)提出时的原意,又力求从当代的观点和视野进行审视。此外,对薄伽丘悲剧和喜剧观、拉伯雷的怪诞美学观念对文艺复兴美学的研究填补了研究空白,并对蒙田、霍姆的美学思想加以了弥补。
第三卷为“西方近代美学”的下部,分为德国古典美学与19世纪其他诸国(主要指英法两国)美学思潮和流派,由李鹏程、王柯平、周国平等著。[※注]该卷以“德意志观念论哲学家的美学”和“德意志浪漫主义文学的美学”的精确概念,取代了在中国曾占主导的“德意志古典美学”的概念,并关注到美学与哲学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揭示出谢林关于艺术形而上学高于哲学的观点)。创新之处还有,对于康德判断力学说在哲学体系中的意义进行了新颖的阐发,对叔本华和尼采美学的形而上学意蕴的阐释也有开创意义,对英国罗斯金的美学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从历史上看,早在20世纪中期中国就翻译了《罗斯金艺术论》(刘思训译,大光书局1936年版)这样的研究著作。此外,对于19世纪德国美学如何走出哲学而走向心理学和社会学进行了过程性的阐明,从而使得美学史更具有了连贯性。
第四卷为“西方现代美学”,由金惠敏、霍桂寰、赵士林、刘悦笛等著,该卷横亘了整个20世纪,重视对外文原始文献的研读,并力邀许多国外专家参与了撰写(如邀请法国杜夫海纳协会会长Maryvonne Saison撰写杜夫海纳的思想)。[※注]首先,在学说史的系统性和学统源流意义上,对当代西方美学家的个人思想从思想史的总体上进行学术逻辑分类,并进行流派建构的尝试,从而将向美学史的学术系统性建构的方向进行了积极探索。这就突破了中国学界流行的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作为20世纪西方美学史的两大潮流的惯例,认定二者都根植于启蒙理性而属于现代性的范畴。按照这种结构,整个20世纪欧美美学,最初“形式主义美学”与“表现主义美学”为当时美学思想的重要两翼,“无意识美学”的影响也极为深远,还有“生命美学”和“距离美学”也盛极一时。西方美学史逐步进入世纪中叶,“实用主义美学”、“符号论美学”、“现象学美学”和“存在美学”都在百花争艳,从而充分展开了该世纪的美学谱系。在20世纪中期之后,发源于维特根斯坦的“分析美学”占据了欧美美学的主流位置,但是发源于卢卡奇的“社会批判美学”、“格式塔美学”、“解释学美学”和“接受美学”都获得了自身的思想地位。20世纪末期,西方美学步入了后现代的阶段,这也是该世纪美学的终结期。
在这种中国化的“西方美学史”的基本范式的影响与引导之下,西方美学研究进入到突飞猛进的历史时期。在走出闭关锁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全新的历史语境当中,随着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在1979年的修订再版,一批西方美学研究的专著与论文得以出现。这便在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打开了西方美学研究的局面,并确立了通史与断代史研究同时进行的格局,西方美学史也不仅仅局限于对于20世纪之前的西方古典美学的研究,而且将20世纪的美学史直接纳入到研究的视野之内。
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可谓走在前面,而且,这本专著实际上也开启了中国化的西方美学研究的“海派”风格。蒋孔阳的诸多弟子在《西方美学通史》等其他著述当中延续了这种风格,从而区别于以汝信的《西方美学史》以代表的“京派”。如果从1965年《德国古典美学》的初稿完成算,这本在中国关于德国古典美学的第一部研究专著应该属于20世纪60年代的成果。所以,该书仍以对德国美学的“意识形态批判”作为主要基调,但是,它却最终全面地完成了对于这段曾经对中国美学最为重要的西方美学资源的深入研究,从而最终为这段美学史加以宏观的历史定位:“1.总结了以往的美学经验,特别是十八世纪英、法、德三国美学的经验;2.开启了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美学思想;3.把辩证法这一先进的方法全面地引进到了美学研究的领域;4.从十八世纪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美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之间,起了一个中介的作用。”[※注]这种批判当然从康德开始,以黑格尔为终结,在二者的逻辑发展之间,包括两位作为哲学家的美学家费希特与谢林,两位作为文学家的美学家歌德与席勒,这也影响了其后德国古典美学在中国继续研究的基本格局,从而使其成为了一本经典性的美学断代史著作。
1983年是西方美学研究的丰收年。在这一年度,汝信继承了《西方美学史论丛》的美学家个案研究的衣钵,继续出版了《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曾繁仁出版了类似的人物个案专著《西方美学简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同时,西方美学研究的视野,不仅上溯到西方美学两千多年前的源头,以阎国忠的《古希腊罗马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的出版为代表,而且,深入到身处其间的20世纪这个最新的时代,以朱狄的《当代西方美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出版为代表。此外,从门类美学史的角度来看,徐纪敏的《科学美学思想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也非常有特色,还有美学家蔡仪主编的“美学知识丛书”中涂途编著的《西方美学史概观》(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这样的介绍性的小册子,这些都共同推动了第一次西方美学史研究的热潮。
朱狄的《当代西方美学》的出版展现出更为重要的价值,因为,这是汉语学界第一次将整个20世纪的美学史加以整体呈现的第一部专著,至今仍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与研读价值。这本专著首度采取了流派史的手法,将现代西方美学纳入到十个主要流派当中,并将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的美学思想具体呈现了出来,主要包括安海姆(又译阿恩海姆)的“完形心理学美学”、弗洛伊德和融恩(又译荣格)的“心理分析美学”、桑塔耶那的“自然主义美学”、杜威和佩珀的“实用主义美学”、芒罗(又译门罗)的“新自然主义美学”、科林伍德和理德的“表现论美学”、杜夫海纳的“现象学美学”、理查兹的“新实证主义美学”、维特根斯坦和韦兹的“分析美学”、卡西勒与朗格的“符号论美学”。尽管作者将历史截至20世纪60年代左右,尽管许多流派的代表人物还有待商榷,尽管各种流派的历史顺序需要调整,但是,这种以流派区分、“以人带派”的撰写手法,基本上被整个现代美学史的研究承继了下来。与朱光潜一样,朱狄在描述过十个流派的基本思想之后,又从逻辑的高度梳理了几个基本问题: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争论、关于审美经验各种因素的分析、当代西方艺术中的美学问题和各门艺术中的美学问题,其中,对于分析美学家的迪基的艺术“惯例”论的探讨已经将视野拉伸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都证明了《当代西方美学》的前沿性。
如果说,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按照流派划分还是更接近于欧美的撰写方式的话,那么,“现代西方美学”在中国通常主要指20世纪以来的美学史,按照朱狄的《当代西方美学》(其所谓的当代就是通常所指的现代)这种按照西方美学辞典或者百科全书的方式所书写的流派史的做法却始终在欧美学界不占主流。在此,可以将这种在中国的“现代西方美学”的流派史的撰写方式与“在西方”的看待20世纪美学的方式进行比较,一则没有中国学界划分得那么详尽,二则主要是以分析美学传统作为绝对主导。从现任国际美学协会主席、美国学者柯提斯·卡特接续比尔兹利写到60年代的美学史所续写下去的人物为例,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分析美学传统,除了阿恩海姆、苏珊·朗格等少数美学家之外,分析传统的历史核心地位的确是不可动摇的。再以《美学的历史辞典》为例,看看它究竟是如何看待20世纪美学的,按照这种稳妥的观点,20世纪美学主要区分为两大主流,那就是“分析传统”(The Analytic Tradition)与“大陆传统”(The Continental Tradition),此外,“观念论”(国内所论的部分新黑格尔主义与表现主义美学家在其中)与“实用主义”(也涵盖了新自然主义者在内)、批评与阐释、心理学与艺术、艺术运动与艺术史、音乐电影建筑美学都被列在其后;而从90年代以来的新近美学研究,则被区分为分析传统、大陆传统、艺术与艺术史、电影美学与大众艺术、音乐美学这几个主要的学科分支,[※注]这显然与东亚视野当中的恢弘视角与精细划分是有明显距离的。
在20世纪80年代向90年代转型的时期,在中国陆续出现的西方美学史专著主要有彭立勋的《西方美学名著引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杨恩寰的《西方美学思想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张法的《20世纪西方美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曾繁仁主编《现代西方美学思潮》(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丁枫的《西方审美观源流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毛崇杰、张德兴、马驰的《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主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章启群的《哲人与诗:西方当代一些美学问题的哲学根源》(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牛宏宝的《20世纪西方美学主潮》(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周来祥主编的《西方美学主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周宪的《20世纪西方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凌继尧的《西方美学艺术学撷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可以说美学史的研究更加深入与全面了。这个转型时期可以说是西方美学研究的第二次热潮,不仅相关的专著大量出版,而且研究的论文的整体水平也大幅度提高。
其中,最直接接受了“朱光潜模式”并有所拓展的,就是曾作为朱光潜助教的李醒尘的《西方美学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醒尘是国内少数在掌握了德文与俄文的基础上撰写西方美学史的作者,他辩证地定位:“美学史是美学研究或美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专门的和独立的知识领域,实质上是一门学说史或思想史,也就是各种美学思想、美学学说或美学理论,以及美学流派发生发展的历史”,“美学史具有双重性,它既是历史科学,又是理论科学”。[※注]正是因为扎实的德文基础,使得作者对于德国启蒙运动美学与德国古典美学的论述非常得心应手,在前者里面增加了赫尔德与福尔斯特的美学思想,在后者当中对于康德的阐发多有新意,早期浪漫派美学思想的论述也丰富了德国古典美学体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尽管《西方美学史教程》是一部简史,但是它并未像其他著作一样结束在20世纪初期,而是将视角延续到了整个20世纪,并按照表现主义美学、自然主义美学、形式主义美学、精神分析美学、分析美学、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符号论美学、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社会批判美学、结构主义美学与解释学美学的顺序加以了梳理,从而使其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小通史”。
朱立元主编的《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是对于20世纪西方美学进行整体与深入研究的重要著作,较之此前所撰写的简史性的著作如朱立元和张德兴的《现代西方美学流派评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已经大为丰富,该书从世纪初写到80年代的解构主义,共30章总计113三节,但是基本的格局却早已确立了下来,那就是以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矛盾与消长为主要架构。所谓“西方人本主义美学”在该书中主要就是指“表现主义”、“直觉主义”、“精神分析美学”、“心理分析美学”、“新托马斯主义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符号学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美学”、“解释学美学”等,“所有这些流派都或明或暗地贯穿着一种思想:强调审美活动中的主体决定作用,追求审美的绝对自由与超越,用非理性因素来解释艺术创造与鉴赏的本质。这些,恰恰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美学相对立,显示了现代人本主义美学的反传统倾向”。[※注]与之相对的则是“科学哲学美学”,它主要通过“自然主义美学”,“实用主义美学”、“语义学美学”、“分析美学”、“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结构主义美学”等流派得到体现。《现代西方美学史》作为一本标志性的现代西方美学史著作,标志着在中国的现代美学史研究日趋成熟,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现代西方美学史的研究。
进入新的世纪,中国美学界迎来了第三波的西方美学研究热潮,新的世纪第一年,程孟辉主编的《现代西方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上下卷就开始出版,打开了新的局面,此后陆续出版的专著主要有:吴琼的《西方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牛宏宝的《西方现代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张法的《20世纪西方美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章启群的《新编西方美学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张玉能的《西方美学思潮》(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程孟辉的《西方美学撷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章启群的《西方古典诗学与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凌继尧的《西方美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周宪的《20世纪西方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彭锋的《西方的美学和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范畴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朱立元的《现代西方美学二十讲》(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邓晓芒的《西方美学史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程孟辉的《西方美学文艺学论稿》(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张贤根《20世纪西方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最新的多卷本专著则是朱立元任主编,陆扬、张德兴任副主编的三卷本的《西方美学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这一时期的美学研究继续走向深化,一方面可以看到“朱光潜模式”得以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如凌继尧的《西方美学史》资料更为翔实,分析更为深入),另一方面,现代西方美学研究实际上成为了美学界关注的重点,甚至可以说,美学史研究的重心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古典美学为主,转到了新旧世纪交替之后的以现代美学为研究主体,而且,美学史的研究越来越与西方同步了,一个重要的论据就是汝信主编的《西方美学史》第四卷邀请国外著名专家参与了撰写与研究。
在最新的西方美学史研究当中,可以看到,老中青三代学者都投入到这项事业当中。在古典美学研究方面,凌继尧的《西方美学史》与章启群的《新编西方美学史》分别代表两种取向,前者试图将朱光潜模式继续加以推进,后者则通过对人物的更精要的选择而试图突破旧有的格局。在现代西方美学研究方面,张法修订之后的《20世纪西方美学史》还是颇具特色的,比如他提纯出表现主义、精神分析与存在主义美学的关键词分别是“表现”、“隐喻”和“荒诞”,并确定50到60年代为“建造体系的时代”,此后的西方美学便走向了后现代;周宪修订后的《20世纪西方美学》以“批判理论的转向”(其中包括齐美尔、奥尔特加、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利奥塔、波德里亚、杰姆逊的美学)和“语言学转向”(其中包括克罗齐、卡西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巴赫金、巴特、伽达默尔的美学思想)为线索解析了20世纪重要的哲学美学家的相关思想。
在西方美学“范畴史研究”方面,程孟辉的《西方悲剧学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可谓是个案研究的代表作,该书将整个西方美学史当中涉及悲剧的思想都一一详尽进行了理论梳理与客观评价。彭锋的《西方的美学和艺术》也依据西方美学辞书的顺序梳理了重要的范畴,司有仑主编的《当代西方美学新范畴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更是力求将20世纪美学的相关范畴试图一网打尽。朱立元主编的共160万字的三卷本的《西方美学范畴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在逻辑范畴这一更高的理论层面所勾勒的另一部西方美学史,这本集体合作的专著所深描的范畴有“存在”、“自然”、“自由”、“实践”、“感性”、“理性”、“经验”、“语言”、“艺术”、“美”、“形式”、“情感”、“趣味”、“和谐”、“游戏”、“审美教育”、“再现”、“表现和呈现”、“优美”、“崇高”、“喜剧和喜剧性”、“古典与浪漫”、“象征”、“丑”、“荒诞”、“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该书认为美学这座大厦的历史必须落实在美学范畴的历史之上,美学范畴的历史性是美学的历史性的根基,美学的历史性最终要落实在构成美学的基本范畴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含义上。因此,对于美学范畴的历史性把握,就是对美学自身发展史的微观把握和历史还原。
西方美学的研究,在中国之所以得以全方位兴起并成为美学研究的主流,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对于外国美学的翻译和介绍。正如《外国美学》丛刊创刊号上面,朱光潜先生贺信里面的话所言——“放眼世界需外文”,这也是西方美学史研究的最基本的条件。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室编的《西方美学家论美与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马奇主编《西方美学史资料选》上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研究室编的《美学译文》(第1、2、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1982年、1984年版)都曾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到过相关的作用。由汝信主编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美学》系列刊物,采取“以书代刊”的形式,并以专刊的格式出版到了第18期,其中的翻译与介绍文章都达到了国内的前沿水平,在美学界影响深远。这一阶段程孟辉担当了大量的编辑工作,而后在原计划的20本尚未出齐的情况下,江苏教育出版社于2009年终于复刊出版到了第19期。此外,从赵宪章主编的《20世纪外国美学文艺学名著精义》(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阎国忠主编与曲戈任副主编的《西方著名美学家评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上中下三卷,到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许多对于美学家生平与美学专著的介绍性著述也起到了很大的普及作用。
更重要的还是对于外国美学专著的直接翻译出版。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美学译文丛书”,丛书的策源地就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从20世纪80到90年代,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主的出版机构,出版了由李泽厚先生主编的大型丛书“美学译文丛书”。这套被老主编称为“起步最早,但步伐最慢”、“艰难牛步”又“自行停止”的丛书,的确推动了中国的美学、哲学、艺术、文化的巨大发展。[※注]丛书由滕守尧担当实际的操作工作,其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18本,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2本,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11本,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8本。这既是“西学东渐”又一次开拓性的学术工程,也积极推动了当时“美学热”与“文化热”的充分展开,其深远影响恐怕还要待以时日来加以评判。
下面将这丛“美学译文丛书”的书名都列在下面,以证明这套丛书所独具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并向当年这些编者与译者致敬):1.桑特耶纳《美感》(缪灵珠译),2.柯林伍德《艺术原理》(陈华中等译),3.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4.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5.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朱疆源译),6.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7.克罗齐《美学的历史》(王天清译),8.奥尔德里奇《艺术哲学》(程孟辉译),9.斯特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凌继尧译),10.德索《美学与艺术理论》(兰金仁译),11.卢卡奇《审美特性》第一卷(徐恒醇译),12.卢卡奇《审美特性》第二卷(徐恒醇译),13.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查立译,该书还收录了康定斯基的《点·线·面》),14.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杨力等译),15.塔塔科维兹《中世纪美学》(褚朔维等译),16.马尔丹《电影作为语言》(吴岳添等译),17.伊瑟尔《阅读活动》(金元浦、周宁译),18.庞蒂《眼与心》(刘韵涵译),19.加德纳《艺术及人的发展》(兰金仁译),20.杜卡斯《艺术哲学新论》(王柯平译),21.李普曼《当代美学》(邓鹏译),22.阿恩海姆《视觉思维》(滕守尧译),23.加德纳《智能的结构》(兰金仁译),24.萨特《想象心理学》(褚朔维译),25.古德曼《艺术语言》(褚朔维译),26.乌尔海姆《艺术及其对象》(傅志强等译),27.沃尔佩《趣味批判》(王柯平、田时纲译),28.卡里特《走向表现主义的美学》(苏晓离等译),29.加德纳《涂鸦艺术》(兰金仁译),30.阿瑞提《创造的秘密》(钱岗南译),31.巴特《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等译),32.布洛克《美学新解》(滕守尧译),33.沃林格《抽象与移情》(王才勇译),34.沃尔夫林《艺术风格学》(潘耀昌译),35.今道友信《存在主义美学》(崔相录、王生平译),36.里德《艺术的真谛》(王柯平译),37.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王才勇译),38.曼纽什《怀疑论美学》(古城里译),39.霍埃《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40.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41.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傅志强译),42.奥索夫斯基《美学基础》(于传勤译),43.鲍列夫《美学》(乔修业、常谢枫译),44.今道友信《美的相位与艺术》(周浙平、王永丽译),45.贝尔《艺术》(周金环、马钟元译),46.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47.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凌继尧译),48.齐斯《马克思主义美学基础》(彭吉象译),49.门罗《走向科学的美学》(石天曙等译)。其中,第1 到18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19到29本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第30到41本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2到49本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第二节 古典美学研究
西方美学史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期。如果从地缘上看,许多归属于古希腊文化脉络的早期思想家,其实是生活在现在所谓的“小亚细亚”地区,从地理归属上(如孕育出世界上第一个哲学流派“米利都学派”的米利都城邦)应属于东方,但是毫无疑义,他们从“学术传统”来说都被视为西方思想的真正源头。早在1982年,叶秀山的专著《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82年版)可谓是第一本对于哲学起源时代进行研究的中文专著,其中也涉及了南意大利学派的创始人毕达哥拉斯的相关美学思想。古希腊美学一直也是研究的重点所在,这种研究由于古希腊文的准入与美学同哲学混糅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古希腊哲学及诗学研究的相应的成熟与发展。与此同时,古希腊与古罗马美学往往被中国美学界归在一起,它们往往被并称为“古代美学”。
如果说,叶秀山的早期研究倾向于哲学的话,那么,缪朗山的研究则更倾向于文艺思想与诗学。早在1964年至1966年,缪朗山就曾以“古希腊的文艺理论”为专题为指导研究生撰写出讲稿。[※注]二十多年之后,这位被认为是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位开设西方文艺论史的专家,在公开出版的《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当中将古希腊罗马文艺理论思想作为重点推出,尽管这种专著只写到德国启蒙运动美学家莱辛。在这本后来才结集出版的专著里面,具有特色的是,缪朗山将柏拉图的文艺的“认识论”思想归纳为:摹仿说、“参与”与“灵魂回忆”、“美的最高境界”,将亚里士多德的关乎艺术教育功能的“行为学”归纳为:情节与性格的关系、恐惧与怜悯的“净化说”、悲剧的人物“错误说”。进而,在古罗马部分,他对贺拉斯以《诗艺》为主的古典三原则——借鉴原则、合式原则、合理原则——的阐发多有新意,对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崇高的美学原理也分为崇高的思想、感情与想象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述,这在当时的研究当中可谓达到了最高的水准。
阎国忠1983年出版的《古希腊罗马美学》是中国研究西方纯美学源头著作的第一本专著,作者对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美学、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美学、古罗马前期与后期的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比如柏拉图美学思想被区分为四个层面:“理式——美的本质论”、“回忆——审美过程论”、“摹仿——艺术特征论”和“灵感——创作泉源论”。在全书最后,阎国忠还归纳出古希腊罗马美学的六个重要范畴,也就是“和谐”、“善”(有用、有益、恰当)、“理式”、“整一”、“悲剧”和“崇高”,并认定这些范畴是按照历史顺序出版的,从“和谐”到“善”分别展现了美依存于(客体)自然与人(主体),“理式”试图以普遍性来克服主客的局限,“整一”则消解了普遍与特殊性的对象,“悲剧”上升到纯粹精神领域而使得整一得以降低,最终,从悲剧走向“崇高”则高扬了人的个体因素,[※注]从而以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叙述了这段西方美学的断代史。
中国学者陆续出版了古希腊罗马美学的研究专著,其中,断代史性的专著在前期研究阶段占据了主导,主要代表性著作包括:蒋培坤、丁子霖的《古希腊罗马美学与诗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思孝的《西方古典美学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袁鼎生的《西方古代美学主潮》(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方珊的《美学的开端:走进古希腊罗马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古典学”研究模式的引入,对于古希腊罗马美学研究更侧重于个案研究,而且,强调从古希腊语言训练开始进行修辞与思想并重的研究,相关的代表性著作包括:陈中梅的《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陈中梅的《言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柯平的《〈理想国〉的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其中,陈中梅的《神圣的荷马:荷马史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还将美学的视野拉伸到荷马史诗研究,章启群的《新编西方美学史》也赞同将荷马史诗而非前苏格拉底美学作为西方美学的真正源头。陈中梅的《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已成为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相关美学研究著作,关于柏拉图他分别研究了诗与认识论、本体论(诗与摹仿)、神学(诗与形而上学)、心魂学、道德及政治、语言艺术、技巧、哲学的多维关联,并以自然、技艺、诗为关键词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证明了古希腊美学研究已经在中国开花结果。
在中国的古希腊罗马美学研究之所以较早取得了成果,那是因为,对于古希腊罗马美学文献的翻译工作也进行在了前面。由朱光潜执笔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就辑录了柏拉图与美学相关的《伊安篇》、《理想国》、《斐德若篇》、《大希庇阿斯篇》、《会饮篇》、《斐利布斯篇》和《法律篇》的相关选段,为柏拉图美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王晓朝主译的《柏拉图全集》与苗力田主持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中译本出版之后,古希腊美学研究获得了更多的参照。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版本就多达四个,最早且影响最大的通行版本是罗念生翻译的《诗学》(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缪灵珠翻译的《诗学》(收入《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崔延强翻译的《论诗》(收入《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陈中梅翻译的《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译者撰写了附录十四篇加以诠释)。贺拉斯的《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与朗吉努斯的《论崇高》也都很早就有了译本。目前,西方古代美学研究也许正在实现着“古典学转向”,这也恰恰是刘小枫所积极倡导的,他的最新著作《重启古典诗学》(华夏出版社2010 年)正是由此得到的结晶。
中世纪美学由于按照过去的经典观点,中世纪思想被视为“神学的婢女”,所以曾经成为了西方美学研究当中最为薄弱的环节,甚至往往被忽视。这种情况最终得到了改观,不仅九卷本的《西方美学通史》第二卷前半部与四卷本的《西方美学史》第一卷后半部给予中世纪以大量的篇幅,并在入选人物的数量上得以拓展,而且相关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都已经出现。早期的著作主要关注的是基督教与美学的关联,主要代表作是孙津的《基督教与美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该书由作者1988年的博士论文《“黑暗时期”的光环:中世纪美学再认识》修订而成)、阎国忠和章启群的《基督教与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后来的专著主要有陆扬的《欧洲中世纪诗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阎国忠的《美是上帝的名字——中世纪神学美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相关的研究著作相比于西方的神学美学研究还是相当少的。与中世纪美学在中国被“补课”迥异,往往被当做西方美学史发展中介环节的文艺复兴美学的研究成果,较之中世纪的研究成果还少,更多的是在美学“大通史”与“小通史”当中作为历史环节而存在的。
17与18世纪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中国学者的关注焦点,往往忽视了法国新古典主义美学,而是直接关注到了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与大陆理性主义美学身上。缪朗山的《西方文艺理论史纲》的后半部分、《西方美学通史》第三卷“17、18世纪美学”与《西方美学史》第二卷“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美学”部分都对此着墨颇多。彭立勋的《趣味与理性——西方近代两大美学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可谓是这方面的最新代表力作,该书完整地阐述了不同的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经验主义美学以对人的情感和趣味的研究为基点,强调美、美感、艺术的感性基础、经验性质、情感特点以及想象作用等方面;理性主义美学则以对人的认识和理性的研究为基点,强调美、美感、艺术的理性基础、超验性质、认识特点以及理智作用等方面。进而,作者又深入揭示了两大美学思潮的对立与互动,并从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和转型的高度去把握这种矛盾的实质,两种美学的主要哲学基础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随之由审美客体转向审美主体,这恰恰是西方美学由古代和中世纪迈入近代的关键所在。
在大陆理性主义美学方面,“美学之父”鲍姆嘉通的美学思想,尽管没有专门的著作研究,但是李醒尘在《鲍姆加敦的美学思想述评》与蒋一民在《鲍姆嘉通》的论文中都通过拉丁原文与德文(并参照了俄文译文)进行了深入研究。[※注]在英国经验主义方面,章辉的《经验的限度:英国经验主义美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董志刚的《夏夫兹博里美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朝霞的《经验的维度:休谟美学思想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也对经验主义美学进行了思潮与个案的专门研究。在欧美的美学界,休谟美学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当代英美美学最新的研究成果,汤森德(Dabney Townsend)的专著《休谟审美理论:趣味与敏感性》(Hume's Aesthetic Theory:Taste and Sentiment,2001)就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彼得·基维(Peter Kivy)的专著《第七感官:弗朗西斯·哈奇生美学及其在18世纪英国影响研究》(The Seventh Sense:A Study of Francis Hutcheson's Aesthetics And Its Influe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1976)则将视角通过哈奇生的个案扩大到对整个经验主义美学的梳理,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在英语学界始终是古典美学研究的重点所在,因为诸如“无利害性”或者“非功利”(disinterestedness)与“内感官”(internal sense)这样的重要观念都起源于经验主义,国内学界目前对于这一时期美学的关注也逐渐热了起来。与此同时,法国与德国的启蒙主义美学也得到了关注,此外就是意大利维柯的美学在中国也是曾被重点关注的,这与朱光潜的个人兴趣是直接相关的,他晚年翻译出版了维柯的名著《新科学》。
对于欧洲近代美学的研究,从特罗菲莫夫等著的《近代美学思想史论丛》(汲自信、孟式钧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陈燊和郭家申编选的《西欧美学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到李斯托威尔著名的论著《近代美学史评述》(蒋孔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这些历史研究与论集的出版的同时,许多美学家的专著都得以翻译出版。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布瓦罗的《诗的艺术》(任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哈奇生的《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高乐田、黄文红、杨海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荷加斯的《美的分析》(杨成寅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伯克的《崇高与美》(李善庆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鲍姆嘉通的《美学》(简明、王旭晓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卢梭的《论艺术与科学》(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狄德罗美学论文集》(张冠尧、桂裕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温克尔曼的《希腊人的艺术》(邵大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莱辛的《拉奥孔》(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赫尔德的《赫尔德美学文选》(张玉能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维柯的《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等等。
当代中国美学,最为成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德国古典美学”阶段,或者说,对于德国古典美学研究成为了“在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的高潮部分。所谓的“德国古典美学”的称呼,可能是中国的独特转译,“德国唯心论”或者“观念论”美学则是西方学界的通行说法,这种中国化的译名被如此牢固地确立了下来,它其实就是来自于“德国古典哲学”在共和国前期的定译,只是将“哲学”取代为“美学”。
当然,德国古典美学的深入与全面的研究,首先是建立在相应的翻译基础上的。实际上,中国学界对于康德美学的翻译,并不是开始于对“批判系列”的翻译,而是最早翻译自1764年康德早期著作《对美感与崇高感的观察》(Beobachtungen 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nen und Erhabenen,1763)。鲜为人知的是,20世纪30年代就有胡仁源名为《对于美好和崇高的感情的观察》的商务版译本,而1941年改名为《优美感觉与崇高感觉》(关文运译)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则更为人知,近五十年后的1989年改名为《对美感与崇高感的观察》(曹俊峰、韩明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001年又取名为《论优美感和崇高感》由何兆武译再出商务版,从这种历史流变可见康德美学在中国被关注尤甚。
康德最重要的美学专著《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1790)的中译本由德文译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1964年的时候被分为两卷,上卷导言与“审美判断力批判”部分由美学家宗白华译,下卷的“目的判断力批判”与附录部分则是由韦卓民译。这个译本的上卷影响最为深广,所以被广为引用,下卷由于主要是关于有机界合目的性的思想的,所以被美学界所忽视。从“判断力批判”这个中文译名就可以看到,中文翻译起码较之英文译名更贴近德文原题,通常的英译都为Critique of Judgment,可以被直译为“判断的批判”,只有到了“剑桥版康德著作翻译版”(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 in Translation)的时候才定译为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注]也就是将“判断力”中那个“力”的意蕴翻译了出来,这个剑桥版的译者就是著名的康德专家保罗·盖耶(Paul Guyer)。第二个中译本则是由著名新儒家哲学家牟宗三全译的,并在1992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分上下卷出版,但是这位哲学家所采取的“六经注我”的选择译名的方式,的确得到了许多论者的质疑,在大陆学界很少采用这个译本却有人将之作为研究牟宗三“误读”康德的范本。
目前,在中国美学界最被肯定的译本来自邓晓芒的译笔之下,康德研究专家杨祖陶参与校对,由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这第三个中译本的译者所依据的主要是由卡尔·弗兰德尔所编的《哲学丛书》第39a 卷(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汉堡,1924年第6版,1974年重印本),并参照了普鲁士学院版《康德文集》第5卷(柏林,1968年)及其他英译本和中文译本。仅对康德美学的进行集中翻译的还有《康德美学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是以康德美学专门研究方向的曹俊峰,该文集不仅包罗《判断力批判》的新译本,而且还包括了其他的康德美学文本,试图从历史的排列中见出康德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作为康德“第三批判”的《判断力批判》被翻译成中文的最新译本,则是作为整体而被推出的,由李秋零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第五卷《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在2007年得以出版(中国人民大学2007年版)。
黑格尔的《美学》最通行的译本,则是由美学家朱光潜历时三年出版完成的,至今还没有译本超越它,不过这个中译本主要是通过英文翻译的,译者也曾委托到德国进修的学者加以修订,可惜的是并未得以实现。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德国古典美学的著作也大量被翻译了过来。歌德的论文艺的选集在德国本土就被重视,吉尔努斯选编的《歌德论文艺》1953年的德文版影响颇广,由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中文版(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歌德的格言与感想集》(程代熙、张惠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文版都是重要的美学文献。席勒的《美育书简》或译《审美教育书简》,最早的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是冯至主译的,由范大灿补译而成,收入“美学译文丛书”的还有徐恒醇翻译的中国文联出版社版本。席勒的其他美学著述,主要中译本就是《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张玉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与费希特的主要美学资料都嵌入了其哲学本文不同,哲学家谢林的美学专著《艺术哲学》的最早节译出现在《外国美学》第2辑当中(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艺术哲学》上下卷(魏庆征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十年后得以全译出版,但是谢林这本著作的本有价值往往被国内所轻视。此外,非哲学家的美学著作,主要就是德国浪漫派艺术家们的著作与言论,特别是号称“浪漫主义之王”的诺瓦利斯的选集(《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大革命与诗化小说》,林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奥·施莱格尔、弗·施莱格尔兄弟的著作(《雅典娜神殿断片集》,李伯杰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都被译出,还有大量译文收录在《十九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德国卷,李醒尘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当中。
共和国建立之后,对康德美学所进行的全面研究才真正开始。在共和国早期阶段,对康德美学就已经开始进行了整体的把握,宗白华的《康德美学原理述评》(《新建设》1960年5月号)与朱光潜的《康德的美学思想》(《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是20世纪60年代论康德美学的最重要的两篇长篇论文,蒋孔阳的《康德美学思想——简评“判断力批判”》(《文汇报》1961年7月4日)也对于康德美学进行了整体述评。尽管从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学说》和王国维的《汗德像赞》(1903)两篇介绍文字开始算起,中国美学家关注康德已有百年之久,宗白华在1919年也曾撰写《康德唯心哲学大意》一文,但是,真正对于康德美学(而非康德哲学)进行专业研究还得从20世纪60年代初谈起,然而兴起得迅速衰落得也快速,此后的西方美学研究曾一度归于沉寂。但无论怎么说,在中国的康德美学研究总是落后于康德哲学研究的,直到李泽厚70年代的研究成果出版之后,康德美学研究才一度与康德哲学研究并驾齐驱,然后康德哲学研究又超过了康德美学的学术研究水平,至今仍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之后,李泽厚于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不仅成为了康德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经典之作,至今畅销不衰,而且也成为了康德美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在“新时期”的开启之作,该书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和美学界的深远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的。根据李泽厚自己的回忆,康德思想的研究应该开始于1972年,而该书的书稿于1976年就基本得以完成,李泽厚以历史的观念来梳理康德思想体系,所以,康德的“美”作为“真”“善”的统一就会被视为两者的交互作用的“历史成果”。更早发表的《康德的美学思想》则是最重要的一篇康德美学研究论文,该文就是李泽厚同年出版的专著的第十章“美学与目的论”的美学部分。李泽厚对于康德美学首先是按照《判断力批判》的线索加以论述的,分为“美的分析”、“崇高的分析”、“‘美的理性’‘美的理念’与艺术”三个部分陈述,但是,最终在“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形”的部分又回到了他的“主体论实践哲学”的美学观:“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看来,康德提出的‘自然向人生成’和所谓自然界的最终目的是道德文化的人(见《判断力批判》的后半部),实际应是通过人类实践。自然服务于人,即自然规律服务于人的目的,亦即是通过实践掌握自然规律,使之为人的目的服务。这也就是自然对象的主体化(人化),人的目的对象化。主体(人)与客体(自然)、目的与规律这种彼此依存、渗透和转化,完全建筑在人类长期历史实践的基础之上”。[※注]这种新的阐释使得李泽厚的康德研究最终从“我注六经”走向了“六经注我”。李泽厚与其他所有康德美学研究者的重大区别,并不仅仅在于他是以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康德并重铸自身的哲学思想,而且还在于,李泽厚的哲学思想恰恰是从《判断力批判》的后半部生发出来的(而非像美学研究者那样仅仅关注美与崇高的分析),在笔者看来,他的“人类学”的视角更像是将康德晚年的《实用人类学》(1798)的思想通过实践观应用于对于“批判时期”思想的阐发。
如前所述,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则是对于德国古典美学的全面研究的力作,其实,这种研究要来得更早,早在1962年蒋孔阳在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上作过相关报告之后就得到商务印书馆的约稿,但直到1980年才得以出版。然而,在他的指导之下,他的学生辈(特别是他前几届所培养的西方美学史专业研究生)逐渐承担起来了德国古典美学史研究的重任,逐渐形成了一种西方美学研究的整体风格。曹俊峰的《康德美学引论》(天津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尽管出版较晚,但如今再回头来看,仍是康德美学研究当中从德文原文做起的非常重要的研究著作,概念考释准确、历史线索明晰,它梳理出了康德美学发展的整个脉络,对“前批判期”和“过渡期美学”的整体把握更是准确而到位。特别是作者所确定的康德美学发展“过渡期”研究颇具特色,这一时期从“前批判期”一直延续到全部“批判哲学”完成之后。[※注]在这种历史梳理的基础上,作者对于更为细致的文本(康德生前的札记片断、写作与讲授人类学和逻辑学时的思考片断)还进行了深入的挖掘。
康德美学研究著述颇为丰富,主要的专著有:马新国的《康德美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朱志荣的《康德美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徐晓庚的《康德美学研究》(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戴茂堂的《超越自然主义——康德美学的现象学诠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劳承万的《康德美学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政文的《从古典到现代——康德美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杨振的《康德美学思想探绎》(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胡友峰的《康德美学的自然与自由观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和申扶民的《自由的审美之路:康德美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些康德美学研究专著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级推动了康德美学研究的热潮,实际上,在中国黑格尔美学思想更能化入中国人的血脉,但是康德美学研究的数量仍是多于黑格尔美学研究的。从研究生论文选择来看,尽管康德更为艰深但是对他的研究还是德国古典美学当中最多的一位。如果单从哲学阐释的角度来看,戴茂堂的《超越自然主义——康德美学的现象学诠释》非常有特色,他并未如大多数美学研究者那样,强调从作为桥梁的美学来理解康德哲学,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从现象学的角度阐释了康德美学的超越自然主义的方法论,并反过来认定“当代现象学本源于康德先天综合判断”,[※注]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与康德思想一样都超越了传统的“客观主义”与“心理主义”,而将后来成为中国美学界主流的现象学方法与康德美学方法得以相互阐发。
有趣的是,在中国的康德美学研究,从李泽厚的阐释方向逐渐发展到了另一个方向,因为李泽厚从康德那里诠释出来的是“主体性”思想,[※注]并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人性解放契合了起来而具有了更多社会开放性,而发展到90年代之后的中国美学却只能囿于本专业内,继续探索主客合一的现象学化的新的主流之路。然而,通过康德美学来确立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关联与互动,这种思路在现象学介入中国美学界之前就已经成为某种共识了。同样进行康德美学研究的劳承万的另一本具有原论性质的《审美中介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就可以作为明证,作者认定在审美客体到审美主体美感生成、定型之间,存在着一个由审美感觉、审美知觉、审美表象构成的“审美中介系统”,这个具有“审美感知——审美表象”结构的系统一方面联系于审美主体的共通感,另一方面联系于客体的合目的性形式。这种美学视野的根本变化,也同哲学与社会的转换是双重相关的,中国哲学思潮从关注于主体的人走向了主客一体化的过程中,美学也曾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而今美学更多仍是深受哲学本身的影响而难以形成感性化的“反作用力”了。
席勒研究在中国也成为了热点,较之歌德美学研究而言,席勒的研究资料更为规整与集中,而且由于与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和“古希腊情结”都相当接近,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备受关注,然而到了新的世纪,再释席勒的时候“人类学”视角却更为凸显了出来,从中可见历史语境的根本转切。毛崇杰的《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是新时期第一本席勒美学研究专著,尽管作者激进标举出席勒美学的人本主义维度,但是他却采取了有褒有贬的辩证态度来看待这种思想:“席勒第一个在美学中明确提出了人本主义原则,并以此为出发点,为核心,为依归,建立了一套关于人的美感教育的理论”,但“这既是它的贡献,又是它的失误。以人打倒了神,以艺术、以美代替了宗教教义,是他的贡献。然而在这同时,抽象的人又变成了神,美、艺术又成为新的救世主,乃是他的失误。”[※注]张玉能的席勒美学研究,则实现了从“审美人文主义”到“审美人类学”思想的转化。在他的《审美王国探秘——席勒美学思想论稿》(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里面,“人性完整”的人道主义中心议题被认为占据了席勒美学思想的核心,这种思想恰恰是从康德的人道主义转向黑格尔人道主义的中介环节。然而,到了《席勒的审美人类学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的新著当中,尽管“成为完整的、真正的、自由的人”仍作为席勒美学的终极鹄的,但是由《审美教育书简》所解释出的“美处于自然人向自由人发展过程的中间环节”的人类学基础,由《秀美与尊严》所阐释出的“美的各个范畴构成了自然向人类生成”的人类学结构,[※注]都将席勒美学研究推到了新的水平。最新的关于席勒美学研究的专著是卢世林的《美与人性的教育:席勒美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黑格尔美学研究在中国显得更为重要,但是,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却呈现出相对弱化的发展趋势。早在1941年,哲学家贺麟就组织成立并领导了“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有计划地从事西方哲学原著的译介,黑格尔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目前以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的专家为主正在致力于“黑格尔全集”的翻译和整理。贺麟作为中国最早的黑格尔研究专家,早年就有《道德价格与美学价值》一文关注美学问题,在他的学术演讲稿《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当中就以“美是真的”、“美是精神内容与感性形式的完善统一”、“美是客观的”为题对于黑格尔美学思想进行了概述。在朱光潜尚未将黑格尔“美学讲演录”翻译出版之前的那个时期,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的黑格尔美学的大多译名都尚未确定,但是大量的哲学译名都已经确定了下来,诸如“反思”这样翻译成为了中文哲学译名的典范。朱光潜的翻译贡献之一,也在于确定了黑格尔美学的一系列的译名,作为黑格尔美学核心思想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也可以被视为另一个译名的典范之作。
最早的黑格尔美学研究,是由致力于德国哲学研究的学者们作出的,他们都将美学作为黑格尔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给予了美学以非常重要的位置。王树人的《思辨哲学新探——关于黑格尔体系的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全书就分为“逻辑学研究”、“美学研究”和“实践、自由、哲学史等专题研究”三章,其中的美学研究对于《美学》的研究还是相当全面的,具体分为:黑格尔美学思想的发端、关于古希腊艺术的历史分析、关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关于实践与艺术美的创造、关于黑格尔对“一些流行艺术观念”的批判等五个方面。在王树人看来,黑格尔美学思想对中国学界的重要启示就在于“主客观统一论”,这是因为,“事实上,黑格尔关于美的本质的观点,就是在理念基础上的主客观统一……如果承认黑格尔这里在理念这个外壳中所包含的合理内容,确实是人和人类社会及其发展,那么,这种思想对于探讨审美活动中主客观的地位和作用,显然仍有其借鉴的意义。因为,只有人才有区分和联结主客观的能力,也只有人和人所创造的东西才是主客统一体。”[※注]可见,西方哲学界也关注“从现实的实践的人”出发,来弄清审美活动中主客观的地位和作用,并将这种思想启迪归于黑格尔的美学观。
在1985年之后,黑格尔美学成为了“在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最为热闹的地方,特别是1986年成为了黑格尔美学研究的丰收之年,这种兴盛的局面可能不会再度出现了。专著主要有薛华的《黑格尔与艺术难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但此书更多涉及的是对现代西方美学的个案研究)、陈望衡和李丕显的《黑格尔美学论稿》(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朱立元的《黑格尔美学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和《黑格尔戏剧美学思想初探》(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等。其中,朱立元的《黑格尔美学论稿》较之于王树人的专著更为全面地解析了黑格尔美学的思想,但与前者类似的是也发现了黑格尔思想内部包含了把美与艺术看做“实践产物”的合理猜想,从而为实践论美学的发展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朱立元继续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传统,作者将黑格尔美学“作为德国古典美学的顶峰”来加以定位,不仅对于黑格尔美学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前期美学思想与《美学讲演录》核心与构架这样的宏观问题进行了研究,而且,对于美、美的创造和审美思想,自然美与艺术美思想,艺术论的具体论述(包括艺术家和艺术创造、艺术鉴赏标准和作品评论、艺术类型的历史发展、艺术体系的分类、诗论与艺术解体问题)都作出了具体分析,从而成为了一本黑格尔美学研究的相对完备之作。黑格尔美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美学界关注的持续热点,在后来还有一系列的延续性的研究,专著主要是邱紫华的《思辨的美学与自由的艺术——黑格尔美学思想引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朱立元的《宏伟辉煌的美学大厦——黑格尔〈美学〉导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此后再隔十年才有陈鹏的《走出艺术哲学迷宫——黑格尔〈美学〉笔记》(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在一定意义上,黑格尔美学研究的衰落也预示着德国古典美学整体研究的衰落。
19世纪俄罗斯的美学思想研究,从20世纪中叶开始就曾经成为“在中国”的外国美学研究的最重要的领域。尽管依据欧洲人传统的地理划分,这些思想的来源地从地缘上属于“东方”,但是从学术文化的传统来看,这些思想由于深受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影响,所以理应在西方美学的框架与谱系当中加以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西方美学史》研究往往加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独立章节,这里不仅仅有政治意识形态曾经制约美学研究的原因,而且还有“学术传统”本身传承的缘由,但是欧美美学家撰写自身的“美学史”的时候却从未将俄罗斯思想纳入其中。而中国人所简称的“车别杜”,亦即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美学思想确实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局面,但是从80年代开始就逐渐被忽略了,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的第一本美学专著其实是肖三的《高尔基的美学观》(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前苏联美学始终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作为自身思想的基本来源与组成部分,所以经过“苏联桥”这些思想及其相关阐释大量译介过来。特罗菲莫夫等著的《近代美学思想史论丛》在前面论述了伯克、伏尔泰、狄德罗和康德的美学思想,而后又将奥格辽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纳入美学思想史的体系,可见从欧洲美学到近代俄罗斯美学是一脉相承的。再以斯米尔诺娃等所著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观》(曹庸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为例,除了车别杜之外,还包括了赫尔岑、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思想研究。同时代的周来祥、石戈所著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美学的原则》(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当中,除了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文献之外,所引述的主要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别林斯基的美学思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周扬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拥有了最大多数的中国读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论文选》(缪灵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别林斯基选集》第一、二卷(满涛译,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辛末艾译,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末艾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别林斯基论文学》(别列金娜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都拥有大量的读者,这与20世纪80年代西化浪潮之后所形成的历史格局确实迥然相异。
第三节 大陆美学研究
西方美学史从近代转向现代,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进程,这段美学史也为中国美学界所积极关注。在这段转型时期的美学家当中,从共和国建立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影响较大的是法国的丹纳,特别是丹纳原版于1865年的《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 l'art)经过翻译家傅雷的妙笔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在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之后注重社会背景陈述的历史语境下,被推到了极高的位置。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的艺术发展“三要素”论,更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相比较之下,崇尚“实证主义”的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斯宾塞具有进化论意味的美学思想,在中国却没有获得更高的历史地位(在欧美学者看来反倒是斯宾塞在美学史上的地位是高于丹纳的)。倒是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社会学思想,通过他的《艺术论》(鲁迅译,光华书店1930年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和更为著名的《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的翻译出版,较早就广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到了80年代中期,《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Ⅰ、Ⅱ(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继续出版使得人们窥见到了其美学思想的全面,相关的整体研究也出现了,马奇的《艺术的社会学解释——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述评》(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就是代表作,作者从艺术的起源、艺术与社会心理等方面深入探讨了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此外还有王秀芳著的《美学艺术社会——普列汉诺夫美学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而在50年代只有前苏联福明娜的《普列汉诺夫的文学和艺术观》(张祺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这样的译著出版,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国美学界所取得的进步。
关于盛行于19世纪70年代的、起源于德国而流行于英法的“心理学美学”研究,在共和国建立前后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众所周知,恰恰是费希纳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美学研究的新方法论,导致了西方美学从近代转向现代的过程中实现了一次重要的历史转向,亦即“心理学转向”,但是费希纳诉诸科学主义方法的“实验美学”从一开始就难以在中国扎下根来。然而,在20世纪的前半叶,中国学界在接受西方美学而原创出中国美学的时候,以立普斯为代表的“审美移情”说,却由于同中国古典文化的接近也被广为接受。朱光潜这样对于文艺心理学颇为青睐的美学家暂且不论,就以20世纪20年代吕澂、陈望道和范寿康以同名《美学概论》的出版为例,这些美学家在建构本土化美学原论的时候,都援引了立普斯的移情论,而所谓的“移情”被吕澂认为是“纯粹的同情”,被陈望道认为是“投入感情于对象中”,被范寿康认为是“自我生命的投入”,然而,在50年代美学更为注重社会学转型的时代,这些心理学理论却一度被抛弃了,直到80年代心理学美学研究的再度复兴。
从叔本华到尼采的唯意志论美学的研究,在百年中国的西方文化影响史上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80年代可以说都兴起了“尼采热”,尼采思想当中本具有的冲动特质在每个时代都非常契合于青年人的气质。从梁启超的撰文《尼采氏之教育观》开始,王国维深受叔本华人生观影响的《〈红楼梦〉评论》和他的论文《德国文化大改革家尼采传》、《叔本华与尼采》、《德国大哲学者尼采之略传及学说》到蔡元培的论文《尼采的学说》,中国美学家们对于尼采的关注尤甚。然而,50年代之后的尼采研究却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视为“禁区”,在60年代初朱光潜从“尼采式的唯心主义的信徒”转而认定,作为“个人主义思想的极端发展”的尼采思想是“人道主义发展到它自己的对立面:反人道主义”。[※注]这种局面在80年代开始得以改善,延续了冯至的《尼采的悲剧学说》一文的研究理路,汝信的《论尼采悲剧理论的起源——关于〈悲剧的诞生〉一书的研究札记之一》和《论尼采哲学》等文章打开了尼采研究的新的局面,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的翻译出版也在大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在台湾地区,70年代这本尼采早期美学的最重要专著就有了李长俊(三民书局1970年版)和刘崎(志文出版社1972年版)的译本。唯意志论美学的研究在中国的研究,从专著的角度来看,最初的成果都是由汝信的研究生做出来的,主要是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与金惠敏的《意志与超越:叔本华美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此后的专业性的重要研究著作还有杨恒达的《尼采美学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而其他重要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论文的发表上面。
进入到20世纪西方美学史的研究领域,在中国最早被关注就是表现主义美学家克罗齐,克罗齐在中国的命运与朱光潜在学界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对于克罗齐的全面研究,在共和国建立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朱光潜所著《克罗齐哲学述评》(正中书局1948年版)就收入到了当时的“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编辑的丛书当中。当然,对朱光潜纯美学建构产生最重要影响的还是克罗齐的直觉论(在人生观方面朱光潜更多地接受了尼采的日神精神而非酒神精神的影响),在20世纪中叶的美学论争当中,贺麟的《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人民日报》1956年7月9日、10日)和叶秀山的《是批判呢还是宣扬——朱光潜先生的“克罗齐美学的批判”一文剖析》(《新建设》1958年12月号)都从哲学的角度解释了这种内在影响。关于克罗齐美学著作的翻译,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1931年就收录了傅东华译的分两册出版的《美学原论》,1934年又合并出版;1936年正中书局出版由朱光潜译的《美学原理》,共和国成立后的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再版,原来的“克罗斯”与“克洛切”一并改为克罗齐。进入80年代,结合翻译史上的已有成果,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美学纲要》合并出版(由朱光潜、韩邦凯、罗芃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但是这些翻译大都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对于版本也没有更好的选择。这种情况直到田时纲直接从意大利文进行翻译之后才有所改善,《作为表现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理论》(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成为了高质量的译本,克罗齐的文集《自我评论》(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也新录了《作为创造的艺术和作为行动的创造》、《鲍姆加登的〈美学〉》两篇美学论文。最新的出版译著还有《美学或艺术和语言哲学》(黄文捷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这是对克罗齐的论文汇集《哲学、诗歌、历史》的翻译,其中包括《美学的核心》、《艺术表现的全面性》等论文18篇。此外,《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的中译本1984年就被收入到“美学译文丛书”。新近的相关研究专著,如王攸欣的《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9年版)、张敏的《克罗齐美学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基本没有摆脱朱光潜的影响,但也都是从比较美学的角度做出来的研究余绪。
与克罗齐、柯林武德的“表现主义美学”形成双峰对峙局面的,是以贝尔、弗莱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美学”,在欧美学界则称之为“视觉形式主义”。与表现主义美学中克罗齐研究对柯林伍德美学研究形成的压倒之势不同,[※注]贝尔与弗莱的研究最初是齐头并进的,开始时贝尔显得更为重要一些,但随着历史的展开弗莱的研究则更占上风。贝尔1914年出版的最重要的美学文集《艺术》(Art,1914)的中译本1984年就被纳入进“美学译文丛书”,“有意味的形式”的说法从此更广为接受,李泽厚认为这个译法出自他的手笔。弗莱1920年出版的重要文集《视觉与设计》(Vision and Design,1920)由易英翻译出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之后,成为了研读弗莱美学的最基础文献,但对弗莱的深入研究早已得以展开,[※注]最新的翻译著作就是《弗莱艺术批评文选》(沈语冰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该文集可以被看做是《弗莱文选》等多本英文文集的缩略选译版,[※注]国内学者汪正龙的《形式主义美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的深入研究侧重于文学的形式美学,赵宪章、张辉和王雄合著的《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则将整个西方从古至今的形式论美学传统进行了全面的解析。
精神分析美学,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弗洛伊德热”而在中国学界广受关注,但是正如精神分析在西方逐渐扩散和渗透到各个领域的史实一样,在最初的“深度心理学”研究热潮之后,精神分析更是化作一种方法融入到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血脉当中。弗洛伊德的《释梦》、《精神分析引论》、《文明及其不满》(或译《文明及其缺憾》)中译本及其他精神分析学派的介绍性著作奠定了精神分析美学的基石,《图腾与禁忌》与其他各种弗洛伊德美学与艺术文选及二手研究著作的出现,充实了这种研究的相关内容。进入新的世纪,随着“精神分析经典译丛”的出现,对弗洛伊德美学资料的翻译趋于全面,其中的《论文学与艺术》与《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都关系到美学,特别是前一本书所收录的15篇文章,分别论述了舞台上的精神病人格特征、米开朗基罗的摩西、歌德的自传《诗与真》中的儿童回忆、《格拉迪沃》中的幻党与梦、陀恩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形象等,这些也都是精神分析美学的经典之作。[※注]
另一位倡导“集体无意识”理论的精神分析的代表人物荣格,他的思想对李泽厚的“积淀说”影响颇大,他的一系列美学与艺术文选如《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被国人关注,英文版《荣格文集》第15卷《人,艺术和文学中的精神》(The Spirit in Man Art and Literature)在中国就有两个译本(卢晓晨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孔长安、丁刚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此外还有《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从易经到禅》(杨儒宾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更因其对《易经》、《西藏度亡经》的阐发而与中国文化直接相通,但迄今为止仍没有专门研究荣格美学的著作出现。
弗洛伊德的美学选集的中译本,影响较大的除了《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陈伟奇译,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之外,还有翻译自1958年英文选集Freud on Creativity and the Unconcious的《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艺术文学恋爱宗教》(孙恺祥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最新的选集中译本则是《弗洛伊德论美》(邵迎生、张恒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版);被翻译过来的相关二手研究著作主要有:卡尔文· 斯·霍尔等著的《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包华富、陈昭全等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列夫丘克的《精神分析与艺术创作》(泽林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彼得·福勒的《艺术与精神分析》(段炼译,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赖哈·汉吉的《弗洛伊德、萨特与美学》(大连出版社1988年版)、杰克·斯佩克特的《艺术与精神分析——论弗洛伊德的美学》(高建平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再版改名为《弗洛伊德的美学——艺术研究中的精神分析法》),利奥·博萨尼的《弗洛伊德式的身体:精神分析与艺术》(潘源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格里塞尔达·波洛克主编的《精神分析与图像》(赵泉泉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这都说明了中国学界对于精神分析美学研究的持久兴趣。
在20世纪西方美学史当中,“现象学传统”与“分析传统”可谓是最具重量级的两个哲学传统,或者可以这样说,这两股在20世纪产生了最重要和最持久影响的美学流派,各自占据了欧陆与英美学界这“半壁江山”。然而,与欧美学界倾向于只承认“分析美学”与“大陆美学”这两种传统有些差异,在中国本土美学界看来,除了“现象学传统”为代表的大陆美学流派、纯粹“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分析美学”流派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传统,那就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美学流派。更形象地说,欧美学界看待20世纪整个的自身美学史的时候,更倾向于“两元对峙”的格局观,而中国学界看待这百年的西方美学流变的时候,却更倾向于“三足鼎立”的格局观。但还要看到,目前欧洲许多国家的美学沿袭的也有分析的传统,美国亦受到了大陆哲学及美学的横向影响,这两类基于两种哲学基本精神的美学传统仍是各占一半江山的,尽管近些年来呼吁双方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在英语成为主流语言的国际美学界分析传统无疑始终压倒了大陆美学传统。
本书所说的“现象学传统”美学,并不是“现象学美学”传统,前者是广义的,后者是狭义的,前者是指从现象学所形成的历史传统中形成和流变出来的各种美学流派,后者则是指严格按照现象学基本原则形成的一种美学思潮,前者包括后者所意指的“纯现象学美学”,而且还包括从现象学当中孳生出来的“存在主义”美学流派,进而继续包括从前两种思潮当中生长出来的“现代解释学美学”流派(尽管古典解释学也成为了其思想来源),在解释学的影响之下,各种以“接受美学”为代表的接受理论也主要在文学领域萌生了出来,但是诸如“日内瓦学派”这样的受现象学影响的文学批评学派并不在本书的考虑之列。所以说,“现象学传统美学”作为这样的广义概念,它的囊括力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目前,就中国学界而言,“现象学传统美学”无疑是最有影响的现代西方美学流派,无论对于西方美学史的单纯研究,还是对于美学原理的深层建构,甚至对于中国美学史的内在阐释,现象学传统无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都已经成为了“主流中的主流”。
从现象学传统百年来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来看,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全面介绍被上溯到了1929年,然而,大陆学界真正接受现象学传统还得从20世纪80年代算起。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某种哲学思潮舶来中国,一般都要经历“西方思想的引进和传播”、“相关理论的研究和拓展”、“与本土文化结合与整合”这三个阶段。但是,有趣的是,作为哲学分支的现象学美学的最早的引入,却脱离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主流轨迹,是直接从同本土文化结合的最后一个阶段开始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由于,在中国第一本关于现象学美学的著作,应该是1966年出版两次的中国哲学家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注],徐复观1965年8月18日完成的《中国艺术精神·自叙》后的这本专著,被认为是对“中国艺术思想的开创性研究”所取得的划时代的重大成果。然而,这本书并不仅仅是中国艺术和美学思想的典范之作,而且,也是在现象学与中国古典美学之间架设桥梁之作。在该书当中,徐复观从现象学的角度研究了庄子,认定庄子的“心斋之心”类似于胡塞尔所谓现象学还原之后的“纯粹知觉”,这才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由此可见,现象学在中国所即将走的“中西融合”之路,从现象学美学在中国开始的地方就被预示了出来。
然而,到目前为止的整个现象学美学研究,都是要依托于现象学哲学研究的相对成熟。恰恰是由于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伽达默尔等一系列现象学哲学家的著述的翻译逐步完成,与此同时,盖格尔、英伽登、杜夫海纳等纯现象学美学家的著述也得以逐步翻译出来。需要一提的是,盖格尔作为现象学美学史上的早期重要人物,他的思想较之其他成熟的美学家被关注得更晚和更少,盖格尔的《艺术的意味》(艾彦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的翻译出版只能使他在新的世纪之后才产生影响,但主要还是出现在西方美学史或现象学美学研究的角落当中,盖格的美学思想一般被看做处于现象学美学发展尚未成熟的阶段。
在纯现象学美学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一批学者充当了先锋。李幼蒸1980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编的《美学》杂志上的《罗曼·茵格尔顿的现象学美学》(茵格尔顿就是英伽登的旧译),[※注]可以看做是大陆现象学美学研究的开篇之作,这也说明,现象学美学在大陆一落地就具有了相当的高度。
朱狄在1984年专著《当代西方美学》当中设专章对杜夫海纳的“现象学美学”进行了研究,认为杜夫海纳意义上的审美对象,按照现象学的基本哲学原则,就是“联结了呈现出来的对象自身的存在与被意识所意识到的对象自身的存在”,这种研究也成为了当时现象学美学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薛华1986年在他的专著《黑格尔和艺术难题》当中,以胡塞尔的《想象,图像意识和记忆》这篇重要文本作为依据,将审美判断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来尝试回答艺术和审美的起源问题,这是在中国的胡塞尔美学研究的开启之作,但其他胡塞尔的美学文本还需有待时日继续多加挖掘与研读。从时间顺序上,上述的研究就在大陆本土分别开启了英伽登、杜夫海纳和胡塞尔的美学研究的先河。
叶秀山在1988年出版的在西方哲学界具有相当影响的专著《思· 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当中,以反主客两分的、追求主客同一的现象学特征为内在线索,考察了海德格尔与杜夫海纳的美学之思,并赋予了这些西方思想以中国式的独特解读。这都说明,第一代的现象学美学研究者,主要聚集在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为主导的西方哲学研究者那里。此外,在门类美学领域,于润洋的《罗曼·英伽登的现象学音乐哲学述评》(《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和李幼蒸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也都从音乐与电影美学的角度分别探讨了现象学的独特方法。
英伽登是现象学美学家在大陆第一个被研究的,最早译介的相关著述主要是雷纳·威莱克的《西方四大批评家》(林骧华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其中涉及克罗齐、瓦勒里、卢卡契和英格尔登(即英伽登)。英伽登的中译著述很早就有翻译,他于1967年11月6日向英国美学协会宣读的演讲稿《艺术和审美的价值》(朱立元译,《文艺理论研究》1985年第3期)早就被翻译过来,专著《论文学的艺术作品》(张金言译自英文1973年版,译文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也出现了节译本,该书的最新波兰文全译本为《论文学作品——介于本体论、语言理论和文学哲学之间的研究》(张振辉译自波兰文1988年版,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另一本专著《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陈燕谷译自英文1973年版,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版)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中国学界关于英伽登的美学研究,基本形成了艺术作品“本体论”、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论”和艺术的审美“价值论”的模式,这还需要对英伽登加以更全面的认识。张旭曙的《英伽登现象学美学初论》(黄山书社2004年版)是从美学而非文学的角度对于英伽登所进行的最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专著。从总体上,作者将英伽登的哲学美学定位为“属于实在论现象学传统”,它表现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思辨形而上学、波兰分析传统的奇妙结合而又显示出令人惊叹的严谨性和统一性。
杜夫海纳的美学研究,无疑成为了狭义的现象学美学研究的核心方面,他也的确在国际美学界是影响更为深远的具有领导角色的美学家。杜夫海纳最重要专著《审美经验现象学》英译本前言《审美经验和审美对象——〈审美经验现象学〉引言》,早在1985年就被韩树站译出(《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亦收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的《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下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其中梳理了从早期现象学美学家莫里茨·盖格到茵加登(即英伽登)的美学思想,进而分析了三个关键性的范畴:“审美对象”、“知觉主体”和“主体与对象的谐调”。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影响更大的还是杜夫海纳的论文集《美学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这部由孙非从法文翻译的文集让当时的人们直接接触到了现象学美学的精髓。《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自1953年法文版,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两卷出版,使得读者们窥见到了杜夫海纳的思想全貌。此外,杜夫海纳作为国际美学界的引领性的人物,由他主编的《当代艺术科学主潮》(该书是杜夫海纳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的《美学和艺术科学主要趋势》)节译本,刘应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注]、《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朱立元、程未介编,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年版)也纷纷得以出版。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艺理论界取代了哲学界的人士成为了现象学美学研究的主力军。《文艺理论研究》1985年第3期特设了《“现象学美学”简介》专题,转述了韩树占在《光明日报》(1985年3月14 日)上所撰的《杜弗莱纳的现象学美学》(杜弗莱纳即杜夫海纳)的相关内容,其中认定,现象学美学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波兰的英伽登和法国的杜夫海纳。其后,章国锋的《现象学美学和艺术本体论》(《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陈鸣树的《现象学美学研究方法述评》(《学术月刊》1988年第10期)、周文彬的《现象学与美学》(《探索与争鸣》1989年第5期)和英伽登的《现象学美学:其范围的界定》(单正平、刘方炜译,《当代电影》1989年第3期)都对于现象学美学进行了整体的描述,此外,周文彬的《杜夫海纳美论试析》(《探索与争鸣》1987年第3期)诸文从个案研究的角度对于现象学美学进行了解读。
从1986年开始,另一位属于现象学传统的重要人物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研究出现了,刘韵涵的《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美学》(《文艺研究》1986年第5期)从现象学的基本内涵到梅洛-庞蒂的关于画家与可见物存在关系及其与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关联,都进行了一一解析。梅洛-庞蒂的论绘画美学的专文《塞尚的疑惑》(刘韵涵译,《文艺研究》1987年第1期)也被翻译发表。刘韵涵所翻译的梅洛-庞蒂的美学专著《眼与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成为了该书的第一个中译本,中译本的副标题被定为“梅洛-庞蒂现象学美学文集”,而后这本书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地区又被翻译出来(杨大春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龚卓军译,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进入新的世纪,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美学研究在沉寂了一段时期之后,又跃到了美学研究的前台,不仅仅是因为“知觉”研究直接相关于美学,而且其中一个焦点就是通过“身体”的视角所进行的研究,梅洛-庞蒂本人甚至被称为“身体现象学大师”。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相关研究论文的大量出现,现象学美学的整体研究拓展到了各个方向、各个领域并从各种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论文。进入到21世纪,这些成果逐渐开始以专著的形式得以出版,其中主要有:蒋济永的《现象学美学阅读理论》(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苏宏斌的《现象学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王子铭的《现象学与美学反思: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美学向度》(齐鲁书社2005年版)、汤拥华的《西方现象学美学局限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张永清的《现象学审美对象论:审美对象从胡塞尔到当代的发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张云鹏和胡艺珊的《现象学方法与美学:从胡塞尔到杜夫海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这些著作写得都非常有特色,各有侧重,既有全面而深化的研究,也有从独特视角的探索。苏宏斌的专著从方法论变革、意向性理论、审美对象的存在方式、艺术作品的存在、审美经验的要素与动态过程等视角进行了系统梳理;而张永清的《现象学审美对象论》则更为深入地仅以审美对象为研究对象,将现象学悬搁、意向性理论、本质量观、生活世界与审美对象的关系一一进行了阐释,并描述了审美对象的构成要素与深度效应,而这些专著的结束部分又都关注到了现象学的“主体间性”或者“交互主体性”的问题。此外,从门类美学来看,关于视觉现象学研究成为了热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中国现象学会和中国美术学院共同举办的名为“现象学与艺术”的国际会议,后来结集为《视觉的思想——“现象学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孙周兴、高士明主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出版,在其他艺术研究领域还有周月亮、韩俊伟的《电影现象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这样的专著出现。
沿着胡塞尔所创见的现象学道路,海德格尔开启了“存在主义”美学的新途,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德意志现象学而非萨特意义上的法兰西现象学在中国美学界逐渐形成了主流之势。尽管20世纪80年代“萨特热”在中国持续不衰,但是到了90年代之后开始的海德格尔研究的热潮则更为持久,因而现象学传统进而取代了在中国美学界曾占据三十多年主流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有趣的是,“萨特热”更多与80年代启蒙思想运动相关的,特别是同思想解放与青年文化直接相关的,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久编选的《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曾经风靡一时,然而,对于萨特美学的研究后来却往往囿于文学领域,特别是萨特的“介入”思想更多被用以解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与之不同,海德格尔美学的研究取向,从一开始便是哲学化的,海德格尔美学的研究更多关系到学术本身的建设,不仅关系到西方美学史本身的研究,而且更关系到中国美学原理的拓展。
海德格尔美学的作品,从论文上看最重要的莫过于收入德文文集《林中路》(Holzwege,1950)当中的1935年的论文《艺术作品的本源》这篇大作,从专著上看最为流行的是《诗·语言·思》(或译《诗·言·思》)这本英文文集。[※注]在海德格尔的最重要的专著《存在与时间》完整出版之前,海德格尔的美学论文就已经翻译发表了,不仅1963年内部发行的《存在主义文选》当中已经收录熊伟节译的《存在与时间》,而且,1964年由洪谦出版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当中就收录了同为熊伟翻译的、海德格尔1946年的美学论文《诗人何为?》。而《艺术作品的本源》这篇海德格尔最重要的美学论文,较早的规范中译本见于汝信主编的《外国美学》第6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而此前其弟子伽达默尔的《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导言》也由墨哲兰(张志扬)译、刘小枫校而成,载于《外国美学》第3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海德格尔的其他文章如《走向语言的中途》和《诗中的语言》后来也被翻译在《外国美学》第4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里面。
海德格尔的《林中路》是孙周兴从德文直接翻译过来的(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而《诗·言·思》则早在1990年就由彭富春译、戴晖校对而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此外,海德格尔的《尼采》第一卷以《海德格尔论尼采: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秦伟、余虹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也关系到美学问题,1936年到1946年作为授课内容的《尼采》两卷本后来孙周兴翻译出了全译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其他关系到美学的文集,还有海德格尔1936年到1968年所写的《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从1919年到1958年跨度非常大的《路标》(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都由孙周兴翻译成中文,所谓“孙译海德格尔”越来越得到了美学界的接受和青睐。关于海德格尔的二手研究专著,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哲学与政治的,只有两本与诗学相关,一本是更为全面研究的法国马克·费罗芒的《海德格尔诗学》(冯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另一本则为专题研究性质的美国罗森的《诗与哲学之争:从柏拉图、尼采到海德格尔》(张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学者也曾自己编辑过《海德格尔诗学文集》(成穷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这些也都说明,海德格尔的美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一开始就是追随海德格尔的哲学研究的,海德格尔的哲学研究的成熟程度决定了海德格尔的美学研究的成熟程度。
叶秀山在1988出版的《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无论是从哲学上还是美学上说,都可以被视为现象学美学与存在主义美学研究在中国的典范之作,其中所力主的主客融合的思想路数更是浸渍了东方智慧的,而且,作为阐释者的叶秀山本人的基本哲学思想的归宿也是“美学化”的。面对海德格尔的“此在”的意蕴,作者独特的中国式阐释就出场了:“此在”即“指‘人’的一种主客、物我、思维与存在不分的原始状态。”[※注]进而,在叶秀山所撰写的申明自己美学主张的《美的哲学》(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当中,从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出发,对于美进行“哲学化”的阐释就出现了,因为“胡塞尔在超验的精神现象意义上来理解生活世界。虽然胡塞尔没有说他的‘生活的世界’是‘艺术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却是‘直接的’,是将‘本质’和‘意义’直接呈现于‘人’面前,是‘本质的直观’……这已经为他的学生海德格尔将‘诗意’引入这个‘生活的世界’提供了条件。”[※注]
尽管胡塞尔本人虽并未将“本质直观”归于艺术,但具有共同性的是,中国当代学者往往打通了这种关联,这似乎与中国传统的注重现世生活的本有传统不无关系。这些论点先后出现在薛华1986年的《黑格尔与艺术难题》、叶秀山1991年的《美的哲学》与张世英1999年的《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等著作之中。这种共同的本土化的思想取向,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者那里是近似的,黑格尔研究专家张世英,试图将海德格尔“黑格尔化”,并将中国传统艺术当中所蕴涵的“天人合一”思想,与海德格尔的“在世”学说相互得以阐发,这在他的《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得到了最大的显现。张世英认为,中国哲学缺乏主客二分的思想和主体性原则,基本上是以前主体性或前主客二分的“天人合一”为原则的哲学,而胡塞尔所代表的西方现代及其后现代哲学,其特征是主客融合或超越主客关系。
如果说,这些西方哲学研究者的阐释与理论都是渗透着美学智慧,或者说基本上都是“从哲学到美学”的话,那么,后来的海德格尔美学研究则是“从美学到美学”的。在这种纯粹的美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的专著,主要有:刘士林的《澄明美学——非主流之考察》(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贤根的《存在·真理·语言——海德格尔美学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旭光的《海德格尔与美学》(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张弘的《西方存在美学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昌树的《海德格尔生存论美学》(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傅松雪编著的《时间美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这些专著单就海德格尔美学进行深入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相互不可替代的成就,但是阐释的路数仍是遵循前贤的,比如研究最为全面的刘旭光的《海德格尔与美学》就认定,海德格尔“对于形而上学的超越”及对二元对立思维的化解,也成为了该书得以成立的最基本线索。与这些著作比较而言,近20年来在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海德格尔的论文更是蔚为大观,海德格尔在很大意义上已成为了挂在美学学者嘴边的“关键词”之一。
站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之间,既带有美学视角,又具有突破性的海德格尔研究是后来留德的彭富春的德文原著《无之无化:马丁·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1998年该书在法兰克福由佩特·朗欧洲科学出版,这本共165页的专著是中国学者在海外为国际海德格尔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注]该书由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出了中文版,从中可见,彭富春避开了通常阐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套路,而是独辟蹊径地使用了“无”这个本土概念。这意味着,彭富春以“作为无的存在”为枢纽对于海德格尔进行了一番中国化的阐释,从而将海德格尔的思想进程解析为三段经验:以《存在与时间》为标志的“世界性经验”(weltliche Erfahrung);以《论Ereignis》(也就是被编为海氏全集第65卷的《哲学论文集》)为代表的“存在史经验”;以《通向语言之路》为代表的“语言性经验”。所以,彭富春通过“无”的贯通,将“世界”、“历史”与“语言”这存在的“三个维度”整合了起来,也就是始于历史,经过历史,而达于语言。
目前,正如张祥龙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三联书店1996年版)所达到的中西比较哲学的高度一样,从“比较美学”的角度来进行海德格尔研究逐渐成为了某种共识。这些现象学美学的中西比较研究所获得的最初成果是由台湾学者们作出的,主要方向就是海德格尔与道家美学之间的比较,叶维廉对道家美学阐释就浸渍了现象学元素,其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就是认定,山水诗的最高境界是自然的自身显现,这也就是海德格尔的真理自行显现之意。叶维廉出版的《历史、传释与美学》(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8年版)这本具有原创性的著作,采取了原创的“传释学”的名称来取代“诠释学”,这是因为诠释“往往只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去了解一篇作品,而未兼顾到作者通过作者传意、读者通过作品释意(诠释)这两轴之间所存在着的种种微妙的问题,如两轴所引起的活动之间无可避免的差距,如所谓‘作者原意’、‘标准诠释’之难以确立,如读者对象的虚虚实实,如意义由体制化到解体到重组到复音符旨的交错杂合生长等等。我们要探讨的,即是作者传意、读者诠意这既合且分、既分且合的整体活动,可以简称为‘传释学’”。[※注]这就从中国传统美学的角度提出了要对现代解释学作出了本土化的新的诠释和发展,事实证明,这种美学理论的方法是具有适用性的,从而达到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视界融合”。
作为叶维廉弟子的王建元在1988年出版的《现象诠释学与中西雄浑观》(三民书局1988年版)一书也成为了比较美学的重要著作,作为这种比较研究的延续,其中的第四章《中国山水诗的空间经验时间化》认为中国山水诗的特征就在于将空间时间化,这是源于空间知觉的综合就是时间意识的综合的现象学原则。此后,赖贤宗继续追随1988年叶维廉出版的《历史、传释与美学》当中对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方法的援引,在他的《意境美学与诠释学》(台湾历史博物馆2003年版)等著述当中,得出了这样的比较美学的结论:“意与境浑”的“艺术体验论”对应于解释学美学所论的存有意义的开显;“返虚入浑”的“艺术形象论”对应于解释学美学所论的非表象思维与“语言是存有的屋宇”(或译“语言是存在的家”);“浑然天成”的“艺术真理论”对应于解释学美学所论的艺术的真理性。在大陆,比较诗学的论述较之比较美学更占主流,钟华的《从逍遥游到林中路——海德格尔与庄子诗学思想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和那薇的《道家与海德格尔相互诠释》(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都作出了相应的成绩。
解释学美学思想的在中国的兴起,主要以伽达默尔(或译加达默尔)美学作为研究中心。伽达默尔的最重要著作1960年首版的《真理与方法》的最早的节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就是由王才勇翻译并收录到“美学译文丛书”当中的,所翻译的就是《真理与方法》直接涉及美学的第一部分“艺术经验中的真理”。后来直到新的世纪,洪汉鼎翻译出《真理与方法》的全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分两卷出版,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学界的学者还是更喜欢用节译本的优雅译文。伽达默尔的其他美学专著的中译本还有《美的现实性》(张志扬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作为游戏、象征、节日的艺术》,原为1974年在萨尔茨堡大学所作的演讲,但是伽达默尔1964年出版的《美学与解释学》等美学专著尚未翻译过来,而他与杜特的对谈录《解释学美学实践哲学》也已经翻译出来(金惠敏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还有就是文集《伽达默尔论柏拉图》(余纪元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当中还收录了他作于1934年的名文《柏拉图与诗人》。伽达默尔以历史开放性的途径、从历史接受的变动角度,推导出“同时性”的艺术理解活动,倡导审美融入文化的“审美无区别”,从而将真理拓展到艺术领域。进而,又在“游戏本体”、“观者参与”和“存在扩充”的不同维度,对艺术真理观作出了现代解释学的发展,对大陆后来的美学与中国美学的当代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真理与方法》的第一个中译本的前言当中,译者王才勇对伽达默尔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发。从哲学的高度,王才勇准确地抓住了伽达默尔由前人启发而重新提出的艺术真理观当中蕴涵的两个潜在原则——“相对主义的原则”与“主体性的原则”,恰恰是以这两个彼此相关的原则作为出发点,伽达默尔阐释了他的艺术本体论及其关于美学的解释学结论。这是由于,在具体的艺术经验活动中,每次的感知都是特定的,艺术的真理或意义也存在于特定的此时此地的感知活动中,所以,由此而来的相对主义就带来了主体性的原则:“既然艺术真理赖以显现的每一个感知都是相对的,那么,艺术经验中起主导作用的就不会是客体,而是主体,因为艺术感知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主体的不同。”[※注]毛崇杰的《存在主义美学与现代派艺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也是一部对于存在主义的文艺理论思想进行了整体扫描的专著,其另一特点就是结合了中国文学的实情,而且对于新解释学美学、接受美学和现象学美学都进行了研究。然而,其对伽达默尔的阐释却走向了王才勇的反对面,因为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原则来看,伽达默尔只是把“真理与对真理的解释看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认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注]这显然是从不同的哲学观来洞见而出的不同的阐释结论。
对于解释学美学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就是始于《真理与方法》初译的1987年。涂伦在1987年《中国图书评论》的第2期上发表《介绍几部美学方法论名著》可能是最早使用“解释学美学”一语的文章,该文从方法论的角度认为伽达默尔从“现象学本体论”的角度对艺术经验进行了哲学解释学的探讨。此后,张德兴的《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述评》(《学术月刊》1987年第5期)成为了第一篇全面研究伽达默尔的重要论文,特别是在《时间距离与视界融合——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管窥》(《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第2期)这篇文章当中,作者聚焦于伽达默尔不同于布洛的“心理距离说”的“审美时间距离”说,他把时间距离看做是审美理解的前提条件之一,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把审美理解视为并非一次完成的无限过程。王才勇的《略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社会科学家》1991年第6期)、陈传康的《解释学美学与文艺的历史演变》(《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张微的《本文前面展示的可能世界——一种探索解释学美学的新理论》(《法国研究》1992年第2 期)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论文,其中最后一篇还提到了法国的解释学美学的重要哲学家利科尔。
金元浦的《文学解释学——文学的审美阐释与意义生成》(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可谓是中国解释学美学的第一本重要的代表作,该书通过“方法论——对话论”、“过程论——阅读论”、“本体论——意义论”和“范畴论——空白论”的角度展开了多元探索。依据了现代解释学的原则,金元浦提出,文学的意义生成就是“本文与阐释者相互之间的对话。交流、重构,是二者间的相互溶浸、相互包含,是相互从属:你属于我,我也属于你,是一种动力学的交互运作、相互渗透、相互传递的‘共享’过程。”[※注]而且,在一系列的文学解释学问题上,金元浦提出了诸多新的观点,比如阅读的层级性可以划分为“审美感知的理解阅读视野”、“意义反思的阐释阅读视野”与“意义融合的历史重建和集合的阅读视野”的动态三级过程。这本专著在20世纪90年代独树一帜,既对文学解释学的历史进行了历时性的梳理,又共时性地阐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哲学理论,从而将西方解释学与中国诠释学传统结合了起来。
对伽达默尔的个案研究方面,严平的《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述评》(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既是首部对伽达默尔哲学进行全面阐释的专著,也涉及了伽达默尔的美学问题。这是由于伽达默尔本人思想体系内部美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这本以哲学为主的专著当中,作者看定了美学与解释学具有一种“天然的渊源关系”,二者始终是相互联系而非排斥的,既然解释学的任务就是理解,那么,理解必然包含艺术作品。李鲁宁的《伽达默尔美学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则是专门研究伽达默尔美学的专著,在对于现代解释学鼻祖思想深入研究的同时,这本书还对于他的思想进行了客观批判,作者指出,伽达默尔的美学并未超出“唯心史观”的美学视野,其辩证法也由于走向了“恶无限”而走向了反辩证法,而且对形式的贬低也走向了对近代形式主义美学的矫枉过正。王峰的《西方阐释学美学局限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不仅对于西方阐释学的理论进行了全面批判,而且还论及了阐释学美学的“中国学派”的问题。此外,在朱立元主编的集体性著作《现代西方美学史》与牛宏宝独著的《西方现代美学》当中,都对以伽达默尔为主的解释学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霍埃(或译赫什)的《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也被翻译过来,但是他的独特的解释学理论除了程金海等人撰文(关注论伽达默尔与赫什解释角度的差异)之外却少有论述。从门类美学来看,罗艺峰的《从解释学美学角度对音乐存在方式的思考》(《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也都是援引了解释学方法对于门类艺术所进行的研究。
“接受美学”如果从学术影响上来看,由于文学理论界的直接介入,它的影响较之解释学美学在中国更加深远。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接受美学”虽然命名为美学,但是在欧美学界更多被视为文学理论而非作为哲学的美学思想,但是,在中国的学界却毫无疑问地将之归为美学思想。“接受美学”在中国的翻译,曾经形成了一段热闹时期,在1989年集中出版了三本译著就是证明。被翻译过来的第一本专著就是收入“美学译文丛书”的罗伯特·姚斯、R.C.霍拉勃的合集《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刘小枫选编的《接受美学译文集》(三联书店1989年版),直接与文学的接受理论相关的则是汤普金斯的《读者反应批评》(刘峰、袁宪军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张廷琛选编的《接受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姚斯(又译“尧斯”)与伊瑟尔(又译“伊塞尔”)同属于“康士坦茨学派”,他们是接受美学领域最为著名也是最被中国学者所认同的两位美学家。其中,尧斯1967年发表的《文学是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被认为是接受美学的理论宣言,在不同的理论选本当中,这篇文章的中译本都位居前列的重要位置。姚斯其他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还有1977年首版的《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顾建光、顾静宇、张乐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根据迈克尔·肖的英译本译出的。伊瑟尔著作被翻译过来的更多,不仅仅是他的接受美学理论,而且还有他后期的“文学人类学”思想都广受关注。他的代表作1978年版的The act of Reading: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就有中文的不同译本,分别为《阅读行为》(金惠敏、张云鹏、张颖、易晓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阅读活动》(金元浦、周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这本接受了现象学影响的“接受美学”的名著,将“反应”与“接受”作为接受美学的两大核心课题,以本文(如今通译为“文本”)与读者双向互相作用为理论基点,从而全面揭示了产生反应与接受的阅读行为对理解阐释文学本文意义的关系。伊瑟尔其他的译著还包括《虚构与想像: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汪正龙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怎样做理论》(朱刚、谷婷婷、潘玉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这些新著说明了作者走向了对文学的更为本体化的思考。
在大陆学界,较早介绍接受美学的文章是意大利学者弗·梅雷加利的《论文学接收》(冯汉津译,《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3期),而后张黎的《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文学评论》1983年第6期)和张隆溪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阐释学与接受美学》(《读书》1984年第3 期)引发了关注,后来收入张隆溪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当中,该文从解释学的“理解的历史性”出发介绍了接受美学的基本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个时期的接受美学研究出现了几篇重要论文。章国锋的《国外一种新兴的文学理论——接受美学》(《文艺研究》1985年第4期)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接受美学重要学者姚斯、伊瑟尔还有瑙曼的理论。张首映的《姚斯及其〈审美经验与文学阐释学〉》(《文艺研究》1987年第1期)一文,着重于姚斯对审美经验三重意义(亦即“诗的”、“审美的”和“净化的”意义)的思考,创新之处在于从伽达默尔的“问—答”逻辑来阐释姚斯的思想,认为后者既是对前者的继承也是破坏。金元浦、周宁合作的《文学阅读:一个双向交互过程——伊瑟尔审美反应理论述评》(《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则是对伊瑟尔美学研究最早的成熟论文,它以“本文的召唤结构”为主论述了本文研究,以“游移视点”为主论述了阅读现象学、以“文学本文的交流结构”为主分析了“文本——读者的双向交互作用”。朱立元的《文学研究的新思路——简评尧斯的接受美学纲领》(《学术月刊》1986年第5期),对于那篇接受美学的“历史性文献和理论纲领”进行了宏观解析。
在中国学界接受“接受美学”之初,通过这种新的美学视角对中国古典美学进行研究就已经开始,从张隆溪的《诗无达诂》(《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开始,这种比较美学的研究方式一直延续至今。董运庭的《中国古典美学的“玩味”说与西方接受美学》(《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这种早期研究,都是从中国古典美学的接受术语出发的,后来出现的则是中西接受理论的互证阶段,殷杰、樊宝英的《中国诗论的接受意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和龙协涛的《中西读解理论的历史嬗变与特点》(《文学评论》1993年第2 期)都是代表。最终中国古代美学的阐释学思想得到了集中关注,樊宝英、辛刚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与接受》(石油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就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就是一种“泛接受美学”。这体现在后来出版的诸多专著当中,如龙协涛的《文学读解与美的创造》(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版)、张思齐的《中国接受美学导论》(巴蜀出版社1989年版)、邓新华《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李咏吟的《诗学解释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都具有了一种中西美学比较的视野。
在接受美学的原理方面,中国大陆也出现了大量专著,早期的成熟著作就是朱立元的《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这本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专著按照逻辑的线索,从本体论、作品论、认识论、创作论、价值论、效果论、批评观和历史观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其中,从本体论即文学的存在方式角度出发,在整体上阐述——作者、作品、读者——文学“三环节交互作用的活动过程”,这本专著在2004年修订扩充再版改名为《接受美学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它不愧为中国接受美学原理研究方面的奠基之作。此后,接受美学的专著也大量出现,丁宁的《接受之维》(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更是吸收了精神分析学来研究艺术接受的心理过程,胡木贵、郑雪辉的《接受美学导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马以鑫的《接受美学新论》(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林一民的《接受美学》(江西高教出版社1995年版)都是这方面的相关著作。
对于20世纪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在中国美学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独立的领域,它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当中,也被看做是与分析美学、现象学美学两大美学主潮颉颃发展的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美学主潮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顾名思义,从空间上就是与东方相对的马克思主义,从时间上看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之后的新思潮。有论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末,是由哲学家马萨贝克率先提出的,也有人认为,苏联共产主义者在指责西欧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倾向时最早用了这个术语。[※注]从起源来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历史与阶级意识》(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1923)出版之前,匈牙利哲学家和美学家卢卡奇(Gyrgy Lukács)就已经确立了作为美学家的声望,代表作就有《心灵与形式》(The Soul and Forms,1910),还有写于1916年并贯穿着黑格尔主义、1971年英文版才得以问世的《小说理论》(Theory of the Novel,1971)。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国学界,卢卡奇的美学著述《叙述与描写》(上海新新出版社1947年版)早就由美学家吕荧翻译而出,可惜的是,直到80年代卢卡奇的美学思想才重新获得关注的目光。
那么,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译介与研究,应该从哪里开始算起呢?按照通常的观点,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被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开始被广泛探讨。实际上,从50年代开始,中国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翻译与介绍,并不是仅仅囿于“前现代”的视野,还有最新的具有现代性的成果被介绍进来,其中的代表译作就是克林兼德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艺术》(未知译,三联书店1951年版),这本书本就是由F.J.Klingender在1945年出版的Marxism and Modern Art(由纽约的International Publisher出版),当时的发行者还是三联、中华、商务、开明的联营组织。还有那位在法国被称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的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文化研究形成热潮的今天,这位思想家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空间生产理论都广为瞩目,然而早在50年代,列斐伏尔的《美学概论》(杨成寅、姚岳山译,朝花美术出版社1957年版)就从俄文被翻译出版了。列斐伏尔在这本美学专著当中,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思想,认为其所提出的“社会生产”的观点第一次使得人们有可能来阐明“审美需要”和“艺术活动”的产生,正是人类本身的改造和改变的结构,才在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出了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的动力,从中可见晚期列斐伏尔思想的影子。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的、由陆梅林直接选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在中国曾是最为全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编选的第一部分“《历史和阶级意识》发表之后”,主要聚焦于卢卡契(或译卢卡奇)的美学思想,“德国和奥地利部分”的美学家包括布洛赫、本杰明(或译本雅明)、马尔库塞、费歇尔和阿多尔诺(或译阿多诺),“法国部分”的美学家包括勒斐伏尔(或译列斐伏尔)、萨特、阿尔都塞、戈德曼和马歇雷,“英美部分”的美学家包罗威廉斯、伊格尔顿等等。董学文、荣伟编辑的《现代美学新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也是非常全面的文选,主要分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主要包括卢卡奇、布莱希特、本雅明的论文)、“本体论美学研究”(主要包括阿多尔诺、布洛赫、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的论文)、“艺术形式与文本结构”(包括戈德尔曼、杰姆逊、马舍雷、沃尔芙的论文)等部分,而早在1980年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就被翻译过来,其后,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专著和选集被纷纷翻译成中文。
从历史角度看,整个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法兰克福学派阶段,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的分期,也相应地可以大致分为“早期形态”、“中期形态”和“晚期形态”三个时期,但是,这种区分并不严格,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思想就已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所有这些成为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中国学界都进行了或深入或综合的研究。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是较早的全面研究专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被作者归纳为:“美学观与文艺观混为一体”、“反对决定论、机械论和宿命论”、“方法论上提出总体性的思想”。[※注]赵宪章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基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孙盛涛的《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傅其林的《审美意识形态的人类学阐释——二十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文艺理论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黄应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也是相关研究的重要专著。
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则是更为全面、更具系统性的专著,该书赋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最广泛的理解,其中主要思潮包括以卢卡奇、费歇尔、加洛蒂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美学”,以布洛赫、勒斐伏尔、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美学”,以布莱希特、阿多尔诺、本雅明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美学”,以阿尔都塞、马歇雷、戈德曼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美学”,以萨特、前南斯拉夫实践派为代表的“艺术政治学的美学”,以葛兰西、威廉斯、伊格尔顿、杰姆逊为表达的“走向文化学的美学”,它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当中都得到整体性的研究和阐释,从1998年开始,刘纲纪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杂志陆续出版,后来改由王杰主编,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至今,在这本杂志里面集中了大量从经典到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论文:最初经典研究占据了主导,进而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成为焦点,新近的几期则更为关注当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最新动向,这也充分说明,在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正在追赶上全球化的脚步。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以卢卡奇为代表,主要被翻译的相关美学著作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的《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一、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张伯霖等编译的《关于卢卡契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卢卡契的《审美特性》第一、二卷(徐恒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卢卡契的《托尔斯泰论》(黄大峰等译,台北南方丛书出版社1987年版);卢卡奇的《现实主义论》(台北雅典1988年版);艾尔希编辑的《卢卡契谈话录》(郑积耀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卢卡契、贝托特·布莱希特等著的《表现主义论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作为译者的徐恒醇发表了大量如《卢卡契美学的开拓性及其当代意义》(《哲学研究》2006年第8期)这样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张西平的《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三联书店1997年版)侧重于哲学思想,而刘昌元的《卢卡奇及其文哲思想》(台北联经1991年版)和黄力之的《信仰与超越:卢卡契文艺美学思想论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则是对于卢卡契美学的专论。
第二个历史阶段,也就是“法兰克福学派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更是中国美学界关注的焦点。王才勇的《现代审美哲学新探索——法兰克福学派美学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杨小滨的《否定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批评》(台北麦田1995年版)、朱立元主编的《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都是这方面的精品力作。王才勇的专著作为第一本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研究的成果,从德国切入文本将这一学派的美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提升到较高的水准上面,他认为:“本雅明基本活跃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早期阶段……他的审美哲学思考,密切关注当时的艺术实际,他的美学思想主要由对当时艺术实践的分析和研究所组成;阿多尔诺活跃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中期……他的审美哲学思考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至于马尔库塞,同样也由于活跃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哲学时期,因为,他的美学思考也具有强烈的审美哲学色彩。”[※注]朱立元主编的专著则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思想特征归纳为“鲜明的批判性”、“现代的人道主义”、“深受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反对科学理性的浪漫倾向”、“参与了审美乌托邦的营建”与“标举马克思主义旗号”等若干种,并将该派美学区分为奠基时期(20世纪20到40年代)、发展成熟期(50、60年代)和后现代主义时期(60、70年代以后)这样三个历史时段。
在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的诸多代表当中,马尔库塞和阿多诺的美学得到了非常特别的关注。这两位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领衔者都将美学作为其思想归宿。马尔库塞也以论文集《审美之维》(The Aesthetic Dimension,1978)来终其一生,这本文集被李小兵译出更名为《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三联书店1989年版),此前翻译出版的《现代美学析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由绿原翻译而出,其中收录的三篇文章都被归入《审美之维》。阿多诺生前留下最后一本专著是《美学理论》(sthetische Theorie,1970),这本书由王柯平从英文版译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但是阿多诺大量关于音乐美学的论文却没有整体翻译过来。马尔库塞和阿多诺都认定艺术是对现实生活产生“异在的效应”的“疏隔的世界”。按照这种基本观点,艺术的基本功能,一方面对客体而言在于使艺术自身与现实他者相互“疏离”,从而艺术成为与现实截然不同的“异在”;另一方面就主体来说,是使人通过审美与艺术的“幻象”彻底地超越和颠覆现实,从而为人们提供一条虚幻的超越之途。
正是这种思想的独特影响力,使得学者们对于他们关注尤甚,包晓光1990年在北京大学的硕士论文《马尔库塞“美学形式”理论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本质》是较早的研究成果,马尔库塞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影响绝对超过任何一位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陈伟和马良的《批判理论的批判——评马尔库塞的哲学与美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特别关注到了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但是,进入到新的世纪,阿多诺的研究逐渐增多了起来,主要出版专著有:孙斌的《守护夜空的星座:美学问题史中的T.W.阿多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孙利军的《作为真理性内容的艺术作品:阿多诺审美及其文化理论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弢的《非总体的星丛:对阿多诺〈美学理论〉的一种文本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凌海衡的《交往自由与现代艺术——重读阿多诺的审美批判理论及其政治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和张静静的《艺术真理审美乌托邦——阿多诺〈美学理论〉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三个历史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也就是对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阶段”的研究,哈贝马斯、伊格尔顿和杰姆逊到中国讲座都成为了研究的关注点。这是由于,哈贝马斯以其“沟通行动理论”和“现代性”思想赢得了世界的瞩目,他认为审美在文化现代性内所起到的“中介论”,都颇有启发意义,从而凸显了审美和艺术所本应发挥的“沟通理性”的作用。当然,更多的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视野转向文化问题,从威廉斯以“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为枢纽建构了一套“文化唯物主义”的美学原则开始,伊格尔顿也在一般意识形态中区分出“审美意识形态”(Aesthetics Ideology),强调了文化生产与审美意识形态之间的有机关联。杰姆逊以“政治无意识”(political unconscious)为纽带综合各派的批评方法,其所谓“辩证批评”的文化解释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杰姆逊来华的演讲结集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使得中国学界从新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于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接触。曹卫东的《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论哈贝马斯的文学概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孟登迎的《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段吉方的《伊格尔顿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都是深入研究之作。
第四节 英美美学研究
与大陆美学传统颉颃发展的,当然就是英美的美学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说是继承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优良品质,并在20世纪得以发扬光大。在20世纪整个一百年的西方美学史当中,如今反观之,横亘的历史时间最长的美学流派、占据主流的时间也最长的美学流派、在欧美学界所产生的影响范围也最广的美学流派,就是“分析美学”(Analytic Aesthetics)传统,它几乎占据了20世纪后半叶这整整半个世纪的主宰并将其主导地位延续至今。然而,由于分析美学最初是追随着分析哲学而发展的,分析哲学在20世纪前期就已在英美占据主流,所以,分析美学在英美占据主流的时代应该是在20世纪中期。遗憾的是,在中国分析美学始终不被关注,直到新世纪充分展开之后,分析美学传统才得到了真正的研究。而在分析美学的绝对主流之外,还有其他各种美学流派,它们更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已经被中国学界广为接受,这些流派有的“历久不衰”(如完形心理学美学),有的“风靡一时”(如结构主义美学),还有的至今“余波未逝”(如符号论美学),[※注]在中国美学界构成了一道道的风景线。
在20世纪60年代,对于英美美学的研究还是相对开放的。按照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哲学译丛》编辑部所编的《现代美学问题译丛(1960—1962)》的选辑,可以看到共和国前期对于西方美学的翻译是在稳步进行的。在这个选本当中,既有前苏联、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文章,其主要聚焦点就在于探讨“审美本性”、“美学与生活的联系”、“艺术的客体与主体”的问题,[※注]也有英、美、法、比利时、西德与日本学者的研究论文,美国的实用主义美学得到了关注(如美国G.E.高斯的《关于约翰·杜威美学的一些意见》),但更多的还是分析传统的美学研究(如英国R.索的《什么是“艺术作品”?》、英国H.哈卡图良的《艺术名称与审美判断》、日本川野洋的《分析美学的结构主义》)。在附录当中,还选译了分析传统统治地位的《哲学》、《大不列颠美学杂志》、《哲学杂志》、《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的相关论文目录近80篇。这充分说明,在20世纪中期,中国美学界对于分析美学传统还是关注的,尽管德国古典美学后来形成了一枝独秀的局面,遗憾的是,随着闭关锁国而与国际美学主流疏离,使得分析传统在21世纪才得以继续发展壮大起来。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如果说,还有对于英美的美学进行研究的话,那么,最早进行研究的就是李泽厚,代表性的著述就应该是李泽厚的单篇论文《帕克美学思想批判》(《学术研究》1965年第3期),这位美国美学家帕克(Dewitt H.Parker,1885—1949)的美学被作者认为属于“经验唯心主义”体系,他的关于艺术本质的美学原理“把艺术看做是个人欲望的想象满足,以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社会需要和个人欲求”[※注]。但是,由于大陆美学传统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传统在中国几乎占据了全部江山,所以英美美学研究始终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帕克的《美学原理》(张今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也是当时最接近国际美学前言的著作,帕克其实是早期分析语言论美学的研究者,他认为,主导美学史的普遍性概念的“摹仿”、“想象”、“表现”和“语言”都与日常语言不同,并进而归纳出“审美语言”(aesthetic language)具有悖论性质和意义的多样性,[※注]这明显属于早期的分析美学研究传统。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篇研究英美美学的论文还是李泽厚写出的,那就是1979年11月出版的《美学》杂志第一卷上的那篇《美英现代美学述评》,作者署名是“晓艾”,由于李泽厚在同一期上还撰写了《康德的美学思想》的文章,所以用了这个笔名,据作者自己说这个笔名取自他儿子的名字“李艾”。
李泽厚的长文《美英现代美学述评》,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可谓是对英美美学进行初步研究的第一篇重要文本。李泽厚从19世纪末以来的英美美学开始谈起,对于斯宾塞、鲍桑葵、科林伍德、贝尔、布洛、芮恰兹、杜威、韦茨的美学进行了匆匆素描,然后,重点分析了“分析哲学的‘美学观’”、“苏珊·朗格的符号论”、“托马士·门罗的新自然主义”和“心理学的美学”(涉及从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学到理德、帕克的美学思想)。在全文的结语部分,李泽厚概括出来现代英美美学的三个基本特点:其一,这种美学“避开对美学中的哲学根本问题,美学的哲学基础或美的本质等问题作理论探讨论证加以排斥,这些问题被一概斥之为所谓的‘形而上学’”,这与现代哲学特别是流行在英美的逻辑实证论和分析哲学的潮流是相一致的;其二,这种美学“常常从经验主义走向神秘主义”,但“由于反对与逃避探究美的本质问题,大肆提倡和风行对艺术和审美经验作现象上各种实证的细致论证和经验描述”,取得了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成果;其三,“现代英美大美学理论与其文艺创作实践与流派、思潮是互相呼应、彼此配合的”。[※注]显然,这已经勾勒出英美美学的基本特点,第一点就是转向以艺术为研究中心,第二点就是以经验主义为基本取向,第三点就是与艺术实践相匹配,这些确实都是现代英美美学的最具概括性的特征。
实际上,更早对英美的美学作出充分研究的,主要是来自港台地区的学者。刘文潭的《现代美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基本上是从英美美学家那里获取资源的,该书分为三部,第一部“艺术的创造过程”具体分析了艺术与游戏、美感、情感、直觉和欲望的关系,第二部“艺术品”分为了艺术与媒材、形式和表现的关系,第三部“艺术的欣赏与批评”对于审美态度的解析包括“感情的移入与抽离”、“美的孤立”和“心理的距离”。刘昌元的《西方美学导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则是介绍和借鉴英美美学更为成熟的专著,该书在“论美”的部分,重点观照了桑他雅纳(桑塔耶纳)的“美感论”;在“审美态度、审美经验与审美价值”部分,重点关注了杜威的“审美经验论”;在“艺术论”部分,重点阐发了柯林悟(科林伍德)的“表现论”、贝尔的“形式主义”、兰格(苏珊·朗格)的“符号论”,进而,试图来解答“美是什么”、“审美是什么”和“艺术的本质”及“艺术的解释、评价和功能”的问题,可谓是全面地归纳了现代英语学界美学的四个主要问题。
“实用主义美学”作为美国“新大陆”的最新产生出来的哲学传统,相应地滋生出实用主义的整个美学思想谱系。正如托马斯·门罗在《走向科学的美学》当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欧洲旧大陆的传统美学总是聚焦于有关“美的纯粹的抽象论证”的话,那么,从爱默生到杜威的新大陆的传统则是强调哲学、艺术应该与日常生活保持紧密的关联,这就是为何分析美学在美国于20世纪50年代压倒实用主义主流传统之后,在当前时代“新实用主义”得以反弹性地复苏并倡导一套“生活美学”的真正原因与历史源头。
实用主义美学的最大代表,到目前为止非约翰·杜威莫属。对杜威进行深入研究的第一篇力作,就是汝信收入《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的《杜威美学思想简论》,从深入程度与哲学反思角度看,这篇文章至今还难以超越。汝信从作为杜威艺术观基石的“经验”这个概念出发,探讨了“一个经验”(an experience)、“情绪”(而今emotion更多地被翻译为“感情”)与“审美情绪”、“表现”及其时间建构、“艺术产品”与“艺术作品”、“经验与自然”的关系、“文明”与“交往”等关键语汇,既深描了《艺术即经验》这本美学专著的方方面面,又对杜威美学进行了深入批判。“杜威的艺术观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把艺术和人的其他活动相混淆,抹杀了审美经验与一般生活经验之间的原则区分;一是把人的艺术活动和动物活动中的活动相混淆,取消了人与一般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注]作者从艺术与生活的关联谈起,将重点置于杜威的恢复艺术与生活经验的“连续性”上面,又从社会生活与生产活动的角度,反过来批驳了杜威以“生物的人”为核心的进化论美学思想,的确批判得有理、有力、有节。
直到新的世纪,随着新实用主义美学的复兴,在大陆对于杜威的政治化批判早已尘埃落定,杜威哲学与美学思想才再度得到关注。张宝贵所编的《杜威与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与《实用主义之我见——杜威在中国》(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版),是研究杜威思想与中国关联的重要著作,从中可以看到杜威与本土之间的思想互动。张宝贵坚持从原典阅读出发,以一本《世俗与尊严:杜威的艺术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开启了大陆的杜威美学思想研究,并将这种研究从开始阶段就提升到了较高的高度。王晓华的《西方生命美学局限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的第五章将过程美学与实用主义美学都归属于生命美学的边缘流派;赵秀福的《杜威实用主义美学思想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从作为经验的艺术观念出发,论述了艺术与科学、宗教、教育和健康的多种关联;李媛媛的《杜威美学思想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具体论述了杜威美学的几对范畴:情感与表现、实质与形式、节奏与对称、知觉与想象,并关注到了艺术与文明之间的关联。2010年第5期的《文艺争鸣》杂志,在“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的生活论转向”的西方美学专辑当中,实际上就是关注到了从杜威到当代的新旧实用主义美学传统,主要的文章是高建平的《艺术:从文明的美容院到文明本身——杜威美学述评》、刘悦笛的《杜威的“哥白尼革命”与中国美学鼎新》、阿诺德·伯林特的《介入杜威——杜威美学的遗产》和李媛媛的《杜威与中国思想的双向互动》,可见,杜威美学思想研究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不大不小的高潮。但遗憾的是,其他早期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无论是更倾向于文学创作的爱默生,更倾向于科学家角色的逻辑学家C.S.皮尔士和C.I.刘易斯,更倾向于彻底经验主义的詹姆士,还是与杜威同时代的具有符号论色彩的C.W.莫里斯,都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历久不衰”的“格式塔美学”(Gestalt Aesthetics),全称为“格式塔心理学美学”或者“完形心理学美学”,是20世纪中叶在欧美影响很大的心理学美学流派,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风靡一时,直到现在还在为中国学人所津津乐道。所以,阿恩海姆也是其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大陆最多的美学家,自从1980年《色彩论》(常又明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翻译以来,他的著作就纷纷被译介过来,这本名为《色彩论》的小册子只是《艺术与视知觉》单章的节译。德裔的阿恩海姆的主要学术成就都是在美国取得的,其中包括1954年使其名声大噪的《艺术与视知觉:创造之眼的心理学》,1974年又进行了全面修订,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出现了14种以上的译本。该书的中译本去掉副标题就叫做《艺术与视知觉》,它被滕守尧、朱疆源两位著名译者集中三个月时间翻译成中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在台湾地区和大陆后来都重译),在大陆成为了影响至今的经典译著,文笔流畅而达到得意忘言的译境。其他阿恩海姆的重要著作主要有:《视觉思维》(滕守尧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被列到“美学译文丛书”里面,《对美术教学的意见》(郭小平等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中心的力量:视觉艺术构图研究》(张维波、周彦译,四川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书名译为《中心力》似乎更好),《艺术心理学新论》(郭小平、翟灿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等,这种翻译热一直延续到新世纪,最新的译著是《建筑形式的视觉动力》(宁海林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收入到了“国外建筑理论译丛”。
收入“美学丛书”当中的滕守尧的专著《审美心理描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不仅是一部倾向于科学话语的审美心理学专著,而且也是第一部对于“格式塔心理学美学”进行研究的专著。在该书中,作者将格式塔学派作为与心理分析派、行为主义心理美学、信息论心理美学和人本心理学美学并列的“现代审美心理学”的重要流派,无论是审美心理要素描述还是审美经验的过程描述,无论是对再现、表现还是符号与审美经验关联的考察,这本专著都浸渍了格式塔心理学的深刻影响。其中,第四章《纯粹形式及其意味——格式塔的启示》专论阿恩海姆的美学思想,滕守尧结合了中国古典的“形神”论来阐释这一心理学美学流派的特质:“格式塔艺术心理学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艺术的‘形’,如形的本质,形的各种形态,形的效果和作用等等……艺术之形主要不是指头脑中或画面中出现的再现意象,而是绘画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各种‘质’之间构成的复杂关系;神不是再现内容,而是形本身的紧张力所暗示出的一种活力——或者就是这种复杂的紧张力的活动。这是与生命相同形成或同构的力,代表着生命本身。”[※注]这显然已经赋予了这种西方心理学美学以一种生命化的本土理解。在滕守尧的翻译与专著之后,格式塔心理学美学成为了中国学界接触西方最新“科学化”美学思潮的主要通道之一,《艺术与视知觉》在中国成为了造型领域领域的必读书目,至今还在为莘莘学子与学者们所研读,各种研究论文层出不穷,最新的专著是史风华的《阿恩海姆美学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宁海林的《阿恩海姆视知觉形式动力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它们都对阿恩海姆的视觉美学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风靡一时”的结构主义美学,在中国可谓是曾经为美学界和文学界所广泛认同。结构主义大师级的人物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译本,J.M.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也梳理了结构主义的“莫斯科—布拉格—巴黎”的历史线索,法国学者吉莱莫·梅吉奥著的《斯特劳斯的美学观》(怀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也聚焦于结构主义的原创性的美学思想,但是,结构主义的影响在大陆却更多是从90年代开始的。其实,早在1976年台湾地区就出现了埃德蒙·李区的《结构主义之父——李维史陀》(黄道琳译,台北桂冠出版社1976年版)的译著,1983年高宣扬的《结构主义概论》(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版)也得以出版,但第一本关于结构主义美学的本土化专著应该是周英雄、郑树森合编的《结构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1980年版)。从1996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就开始出版“斯特劳斯文集”13卷,两卷的《结构人类学》与四卷的《神话学》,还有与美学直接相关的《看·听·说》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大陆学界结构主义结出了许多果实,俞建章、叶舒宪的《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接受了结构主义基本方法、结合了本土思想撰写而成。王一川在不仅撰写出了《语言乌托邦——2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探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且还独辟蹊径撰写出了《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在对于西方语言论美学研究方面,王一川大致区分出两个历史阶段,一个就是“语言乌托邦建构”时期,主要包括心理分析美学、象征形式美学、存在主义美学、分析美学、视觉意象美学和符号学美学等形态;另一个则是“语言乌托邦的解构”时期,主要包括阐释学美学、后结构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美学等形态。在这种历史考察基础上,作者继续关注语言论美学与中国文化的交集,进而提出了一种“文化修辞学美学”的新主张,这种美学“将是认识论美学的理性精神的历史感、本体论美学的个体存在体验与语言论美学的话语探究的融合。在这种融合中,艺术作品被认为是文化本文,它以话语结构显示特定的文化语境及其历史意义。……艺术,总是特定文化的修辞形式。它的产生、存在和接受都取决于它与这种文化的修辞关系”,[※注]随着作者本人将修辞论美学从理论继续向批评靠拢,这种美学也最终落归为一种修辞批评实践。
至今“余波未逝”的还有“符号论美学”(Symbolist Aesthetics),它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便在欧洲获得了主流地位的美学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50年代又开始风靡美国,后来逐渐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是“符号论哲学”的奠基者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和美国女性哲学家苏珊·朗格(Susanne K.Langer)。卡西尔1944年的英文版专著《人论》(An Essay on Man),实际上是他1923年、1925年和1929年出版三卷本德文巨著《符号形式哲学》(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的简写本,它由甘阳翻译成中文之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在80年代的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当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朗格最重要的美学专著是《情感与形式》(Feeling and Form,1953),然而,美学研究者忽视了这本书本是《哲学新解》的续篇,而《心灵》又是《情感与形式》的续篇,从而构成了朗格符号哲学的环环相扣的“三部曲”。《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中国社会科学院1986年版)和《艺术问题》(滕守尧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都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正如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未被翻译一样,朗格的《哲学新解:关于理性、仪式和艺术的符号论研究》(Philosophy in a New Key:A Study in the Symbolism of Reason,Rite,and Art,1942),晚年巨制还有三卷本《心灵:论人类情感》(Mind:An Essay on Human Feeling,1967-1982)都没有被翻译过来。刘大基的《人类文化及生命形式:恩·卡西勒、苏珊·朗格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从哲学的角度对于两位符号论美学大家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最新的专著还有谢冬冰的《表现性的符号形式——“卡西尔-朗格美学”的一种解读》(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
“分析美学”作为20世纪后半叶唯一占据国际美学主流的美学流派,至今已经得到了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发展,它已经成为了从20世纪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广的国际美学主潮,它并不仅囿于英美学界,而今早已在欧陆的美学界攻城略地。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分析美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目前仍是99%的研究者都倒向了大陆传统,而只有1%关注分析传统,而欧美主流美学已经走向了反思分析美学本身的“后分析美学”阶段,但是无论如何,分析美学都应该在中国得到更为全面与深入的研究,掌握分析美学也是当代中国美学直接与国际美学界“接轨”的最重要通道。
中国美学界之所以不能接受“分析美学传统”,原因恐怕就在于:其一,本土美学界难以接受舶来自欧美的科学传统意义上的美学传统,因为这同“自本生根”的古典传统和历史形成的现代传统都是绝缘的;其二,当代中国美学的传统更注重“得意忘言”,往往对于美学研究当中的语言要素关注得不够,当代中国美学基本上是“非语言分析”的人文美学;其三,分析美学的研究还要等到分析哲学的研究相对成熟以后方能进行,而且,这种美学研究对于研究者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那就是要接受相当程度的分析哲学的基本训练。
当代中国对于西方美学的整体研究的现有问题在于,从20世纪中叶开始就偏重于康德、黑格尔以来的大陆哲学传统,20世纪80年代之后现象学、存在主义传统的美学又得到了普遍关注,即使关注英语美学也更多是对于“格式塔美学”和“符号论美学”颇有热情,而真正对于在英美世界占据绝对主导的“分析美学”传统却鲜有研究。这是当代中国美学界对于西方美学研究的现状,亦即更加注重去借鉴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美学,而对于具有科学精神的西方美学传统却采取了拒斥的态度。其中,语言问题是最为关键的,如果说当代的盎格鲁—撒克逊美学传统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走出语言”的话,那么,当代中国美学恰恰没有经历这种“语言学转向”的洗礼,如何“走进语言”,并且在语言哲学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美学,势必在将来成为新的美学生长点。
在中国大陆最早论述分析美学的,还是李泽厚的《美英现代美学述评》那篇长文,该文介绍到西方学界所认定的“当代对美学的最重要的贡献”,也就是“为语言分析所激动和指导”的美学思潮,其共同点就在于“各人从不同角度对美学中的各种基本概念、理论作了语言上的琐细分析,以证明这些概念和理论的毫无意义或含混笼统”,并以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批判”、“家族相似”和“游戏理论”作为基本原则。[※注]这种作为正宗学派的思潮被李泽厚称为“美学取消主义”,它们对“实体论”和“概括倾向”的攻击,被认为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美学理论存在的可能。由此可见,李泽厚主要论述的仍是早期分析美学学派,所以他论述的人物只涉及爱尔顿所主编的分析美学的奠基之作《美学与语言》当中的某些作者,[※注]还有就是艾耶尔和韦茨。叶秀山也在他的《书法美学引论》设置了“分析哲学对艺术和美学的挑战”单节,认为分析美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就在于探究艺术语言的“意义”的特殊性,由此“艺术语言的合法性已经确立了,它是人类语言价值成员之一,同样应该研究这种语言的结构,研究它们之间的思想性、逻辑性的关系”,[※注]而且作者关注到了后期维特根斯坦以“游戏性”对早期“逻辑性”的取代。
薛华在他的《黑格尔与艺术难题》当中,特别关注晚期维特根斯坦的审美理论,并对维特根斯坦的美学较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维特根斯坦致力于描述人们在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审美表达和审美经验。在他看来,审美是一种复杂而多样的现象,审美可以从惊赞、表情、姿态,从言语、理解、行动等等方面和形式中表达出来。这些形式一方面是表现审美进程的可能的形式,另一方面在人们运用它们时又可能带有误解、混乱和模糊。所以对这类审美形式的描述也意味着对它们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明确它们的内容,明确是否表达了内容,以及是否适当地表达了应当表达的东西。”[※注]由此出发,薛华一方面注意到,凡是审美活动进行的地方就有规则存在,凡是作审美判断的场合便是在运用规则,而这种规则被维特根斯坦认为是带有非私人的性质;另一方面,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试图将审美的基础从“正确性”转到“生活和文化”,把审美看做一种生活和文化的游戏,这恰恰是其后期美学思想的枢纽和精神所在。
曹俊峰的《元美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尽管倾向于原理的解析,但是他所谓的“元美学”(metaaesthetics)其实就是语言分析美学,它以一般的美学陈述为对象,以更高层次的语言对美学陈述作语义和逻辑分析,这显然是借鉴早期分析美学的方法论。根据作者所提出的总体诊治方案,首先要从审美和美的分析转变为美学用语的分析,从而把美学陈述或语句作为解析对象加以研究,进而还要考虑到美学陈述的内在逻辑问题。显然,这一方法论来自于从弗雷格、罗素到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特别是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对其影响尤甚。但是,同样在此影响下而产生的“后分析美学”却只关注艺术陈述和概念的语义分析问题。与这种美学流派转向艺术哲学领域而发展分析美学不同,《元美学导论》径直地聚焦在美学理论陈述的逻辑问题上,这倒更为接近于英美分析哲学的传统形态。同时,这种取向使作者的研究更加迫近了美学理论的“元哲学”层面,从而体现出将分析哲学的思维范式落实到美学并对之加以本土化设计的努力。进而,作者看到了美学中各个层次的陈述是不可相互推导的,美学理论体系也不能由初始概念借助于公理、规则经演绎和归纳而建立起来。虽然一般逻辑原则在美学中是失效的,但依据现代逻辑的诸多原则,作者又通过对否定、析取、蕴含、等值等符号的某些真值函项的考察,论证了逻辑运用于美学时的有效性,并从中得出美学概念具有模糊性、判断的个体情感性、逻辑值非标准性等特征的结论。
在中国大陆早期的分析美学研究者张德兴认为,“分析美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所谓的情感主义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语境论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多元化阶段。”[※注]情感主义阶段的基本特点是强调美学中的各种重要概念只是起到了表达某种主观情感的作用,它们并没有指称客观事物的功能,因而无法对它们严格定义。语境论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注重从日常语言运用方面研究美学和艺术问题,否定对美学概念下定义的可能性,并最终走向彻底的美学取消主义。多元化阶段分析美学呈现出与其他美学流派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趋势,在对美学基本概念的看法上也由以前彻底否定下定义的可能性的立场回到肯定这些概念的可定义性的折中主义立场上来。[※注]
刘悦笛则更为全面地认为,分析美学的整体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50年代),这是利用语言分析来解析和厘清美学概念阶段,主要属于“解构的分析美学”时段,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分析为此奠定了基石,而此后的三个阶段均属于“建构的分析美学”时段。第二阶段(20世纪50、60年代),是分析关于艺术作品的语言阶段,形成了“艺术批评”(art criticism)的“元理论”,门罗·比尔兹利可以被视为此间的重要代表人物。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是利用分析语言的方式直接分析“艺术作品”(artwork)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取得成就最高的非古德曼和沃尔海姆莫属,特别是通过分析方法直接建构起了一整套的“艺术符号”的理论,为分析美学树立起一座高峰。第四阶段(20世纪70、80年代),则直面“艺术概念”(the concept of art),试图给艺术以一个相对周延的“界定”,这也成为了分析美学的焦点问题,从丹托的“艺术界”理论到乔治·迪基的“艺术惯例论”都被得到了广泛关注。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是分析美学的反思期。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分析美学内部就开始了对自身的反思和解构,各种“走出分析美学”的思路被提了出来,在美国就形成了分析美学与“新实用主义”合流的新趋势。[※注]
刘悦笛著的《分析美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不仅是中文学界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分析美学的专著,而且也是较早的分析美学史的专著,与西方学界纷纷撰写分析哲学史不同,分析美学史的著作在欧美学界迄今也尚未出现。该书收入作者主编的“北京大学美学与艺术丛书”当中,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分析美学在中国的研究。这本近40万字的专著,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文献基础上写成。全书共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分析美学“思想史”,对(1)维特根斯坦(作为“语言分析”的美学)、(2)比尔兹利(作为“元批评”的美学)、(3)沃尔海姆(作为“视觉再现”的美学)、(4)古德曼(作为“艺术语言”的美学)、(5)丹托(作为“艺术叙事”的美学)和(6)迪基(作为“艺术惯例”的美学)的美学思想进行了详尽的述评,每章之后“述评”一节重在对于该美学家思想的评判和批驳。下编为分析美学“问题史”,主要聚焦于“艺术定义”、“审美经验”、“美学概念”与“文化解释”的问题,涉及从维茨到列文森、从迪弗到卡罗尔、从西伯利到马戈利斯等几个序列美学家们的思想,每个问题之后都试图超越分析美学而提出作者的观点,其所关注的是“分析美学之后”这些问题该如何被重思的问题,并由此寻求新的美学生长点,从而试图(1)在“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来解答艺术的定义、(2)复归到“整一的经验”来解答审美经验、(3)以“共识观””与“解释学”的统一来回答解释的难题。此外,该书附录收录了与丹托、马戈利斯等哲学家们的对话录多篇,生动地呈现了分析美学家们的思想境界。正如国际美学学会(IAA)现任主席柯提斯·卡特在序言当中所说:“刘悦笛的《分析美学史》这部及时性的著作,是对于分析哲学的令人欣喜的贡献。这本书出现在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哲学界的学者对于哲学美学的兴趣逐渐增长的年代,这有助于形成对20世纪西方社会中的哲学美学的整体进程的基本理解”,“刘悦笛所选择的美学家们对于这部分析美学简史而言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们形成了在这场运动当中的最重要的形象。这种选择代表了一种系统的结构,这对于非西方读者们更深入地理解分析美学具有特别的重要价值。”[※注]
目前,在中国国内对于“分析美学”这一20世纪后半叶唯一占据国际美学主流的美学流派研究才刚刚兴起,说这一美学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是最合适不过了。由于从20世纪中叶始,中国美学界与国际美学前沿脱轨,本土的审美思维方式好感悟而轻分析,使得分析传统从来没有在本土美学这片土地扎下根来。日本美学也与中国美学一样,单方面深受欧陆相关思想的影响,而韩国美学由于直接受美国影响亦开始注重分析美学。所以说,只有对发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又得以全球化的这一美学思潮进行深入的研究与阐发,才使得分析美学传统与大陆美学传统的研究在中国获得动态的平衡。
中国美学界对于分析美学的研究,首先是建基在本土的“分析哲学”研究相对成熟的基础上的,国内学界的确开始出现了对于分析美学研究的热潮。以《哲学动态》2010年度连续集中发表的关于分析美学的6篇论文为例,主要包括:姬志闯的《美学的“认识论转向”:纳尔逊·古德曼的美学思想及其当代意蕴》(第3期),邓文华的《比厄斯利分析美学思想初探》(第5期),余开亮的《当代分析美学艺术定义方式的转向》(第8期)、殷曼楟的《从迪基艺术体制论的转变看后分析美学当代转型中的尴尬》(第8期),刘笑非、闫天洁的《分析美学视野下的艺术和道德关系研究》(第5期),史红的《“美”的范畴语义模糊性及量化方法研究探析》(第12期),研究对象包括了从早期到晚期分析美学的重要人物,使用了从量化方法到语言分析的各种方法,它们与关注早晚期维特根斯坦美学思想的刘程的《语言批判——维特根斯坦美学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道,推动了分析美学研究在中国的全面起步工作,分析美学研究在中国已经得以兴起。
第五节 比较美学研究
在中国的比较美学研究,具有优良的历史传统,从20世纪初叶开始,从王国维开始的第一代美学家,在《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当中就自觉地运用了比较的方法。直到40年代,第二代美学家朱光潜的《诗论》可谓是代表了当时在诗歌比较美学方面的最高成就,宗白华的一系列的名文《论中西画法的渊源和基础》则代表了在视觉比较美学领域的至高境界。还有,邓以蛰的《画理探微》也是比较美学在绘画研究中的重要范例,通过比较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西画绘也,绘以颜色为主;国画画也,画以‘笔画’为主。笔画之于画犹言词声之于诗,故画家用笔,亦如诗人用字。”[※注]然而,这种优良传统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却一度被阻断了,既是由于同西方世界整体脱离,也是由于以中西分殊为主的比较美学已不能成为当时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了,这恰恰折射出学术语境的根本转换。
“文化大革命”之后,比较美学研究才被有识之士重新提出,胡经之1981年发表的《比较文艺学漫说》(《光明日报》1981年2月25日)从比较文学推导出了“美学的比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84年中华全国美学会与湖北省美学学会联合在武汉举行了“中西美学艺术比较研讨会”并结集出版《中西美学艺术比较》(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其中蒋孔阳提交的大会论文《对中西美学比较研究的一些想法》首度将“比较美学”作为一个独立门类的问题提了出来并做了理论的充分论证。饶凡子主编的《比较文学与比较美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则是更晚近推定相关发展的文集,王生平的《“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中西美学的宏观比较》(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则是20世纪80年代从宏观角度研究的较早专著。总之,学术的出版与学科的设立,使得比较美学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独立研究方向。尽管佟旭、崔海峰、孙宝印、李欧和樊波曾经为“中国文化书院”编写过《比较美学》的内部资料,但是比较美学的真正繁荣,还要等到20世纪90年代。
如果应用比较文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的术语,从“平行研究”来看,周来祥、陈炎的《中西比较美学大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张法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马奇主编的《中西美学思想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牛国玲主编的《中外戏剧美学比较简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版)、朱希祥的《中西美学比较》(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邓晓芒和易中天的《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潘知常的《中西比较美学论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李吟咏的《走向比较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赵连元的《比较美学研究》(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季水河的《阅读与阐释——中国美学与文艺批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袁鼎生的《比较美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阎国忠和杨道圣的《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美学:中西马克思主义美学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张法的《20世纪中西美学原理体系比较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薛永武和王敏的《先秦两汉儒家美学与古希腊罗马美学比较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舒也的《中西文化与审美价值诠释》(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高建平的《全球与地方:比较视野下的美学与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阳黔花的《中美大学美学课程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支宇的《术语解码:比较美学与艺术批评》(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这些著作都从不同的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影响研究”来看,目前出版的专著显然没有“平行研究”那么丰富,主要的专著有:卢善庆的《近代中西美学比较》(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陈伟和王捷的《东方美学对西方的影响》(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宛小平的《边缘整合——朱光潜和中西美学家的思想关系》(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陈伟和杉木主编的“东方美学对西方的影响丛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后者主要包括四本专著:《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绘画艺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陶瓷艺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文学艺术》和《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丝绸艺术》,这方面的研究的确需要加强。
周来祥、陈炎的《中西比较美学大纲》是最早的“宏观比较美学”研究的成功之作。周来祥始终认为,作为世界美学思想史上的两大美学体系,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古典美学主要特色可以概括为“体系的不同”与“理论形态的差异”,西方偏重于“再现”,而东方则偏重于“表现”,进而可以看到,尽管东西方都强调再现与表现的结合,但是西方仍更偏重再现、摹仿和写实,而东方更侧重在表现、抒情和言志,西方更注重美与真的统一,而东方更侧重美与善的结合。[※注]这种“二元对立”的整体化的比较结论,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被广为接受,比如蒋孔阳就异曲同工地认为西方艺术重摹仿,摹仿说一直是西方美学思想的中心,而中国艺术重抒情和“感物吟志”,其美学思想偏重于“表现说”。[※注]在《中西比较美学大纲》里面,作者采取了黑格尔式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得出了诸多比较美学的结论:从形态论上说,中国古代是“经验美学”而西方古代是“理论美学”;从本质论上看,中国古代是“伦理美学”而西方古代是“宗教美学”;从审美理想论上说,中西方都经历了从追求和谐的古代美、追求对立的近代美到既对立又和谐的现代美的历程;从艺术特征论上看,中西方都经历了从古代的一元艺术、近代的二元艺术到现代的多元艺术的进程。
张法1994年出版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提出了许多崭新的比较美学的论点。该书认为,中西文化精神的差异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西方是实体世界而中国是虚实相生的世界,西方重实体的形式,中国重形式后面的虚体,西方因形式而讲明晰,中国因重虚体而讲象外之象的境界。这三个方面的差异,具体体现为中西美学两个体系的差异,一是围绕着美学类型体系而出现的审美范畴上的差异,该书以“和谐”、“悲剧”、“崇高”、“荒诞与逍遥”为基点论述了这四大范畴在中西美学上的差异。二是围绕着以艺术作品为核心的审美对象的理论体系,从审美对象,审美创造、审美欣赏三个方面进行展开,审美对象中包括审美对象的结构和审美对象的境界,前者体现为文与形式的深入,后者体现为典型与意境的不同。在审美创造上分为一般创作理论和灵感理论,在审美欣赏上突出了中国观、品、悟和西方的认识与定型等一系列的不同理路。[※注]该书的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的附录里面,作者对西方的逻各斯、中国的道和印度的梵为基础而产生出来的文化差异进行了比较,指出西方是由实体哲学而来的实体与虚空的对立,印度是由宇宙本空而来的空幻结构,中国是由气的宇宙而来的虚实相生。
“外来视界”内的中国美学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外学者们的贡献往往被忽略了,其实他们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法兰西科学院院士雷奈·格鲁塞出版于1929年到1930年的《东方的文明》当中,就对于“中国艺术法则的确定”进行了美学解析。当代新托马斯主义主要代表人物雅克·马利坦1953年的《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当中也有关于中国美学的探讨。中国美学更多还是作为“东方美学”的最重要构成部分而得以研究的,美国新自然主义美学家托马斯·门罗1965年所撰的英文专著《东方美学》当中,还对中日美学与印度美学继续进行了东方文化内部的比较研究,难怪他的儿子孟旦成为了一位不折不扣地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汉学家;受到门罗东方美学研究的直接刺激,时任国际美学协会副主席的日本美学家今道有信,在中国学者的协助下于1980年出版了《东方的美学》,其中“孔子的艺术哲学”研究对于中国学者也颇有启示,其实不为中国学者所知的是,今道有信更痴迷于古希腊思想的研究,还曾独著过研究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专著。
在更为微观的研究方面,日本学者笠原仲二1979年出版的《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从辞源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人原初的美意识,俄国学者克里瓦卓夫在1982年的《中国古代美的概念》当中对此也深有探讨,曾受业于宗白华的俄罗斯学者叶·查瓦茨卡娅1987年的《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则对于中国绘画美学有着更为全面的把握。俄罗斯许多东方美学家都曾编写过多卷本的《世界美学思想史资料选》,当然奥斯瓦尔德·西伦选编的《中国人论绘画艺术》(1936)和苏珊·布什选编的《中国文人论绘画》(1971)更侧重于绘画艺术基础文献的翻译,而最新的研究成果,就是曾撰写过多卷本东西美学史的俄罗斯著名美学家康士坦丁·多果夫在2010年国际美学大会上所发送的《中国美学》的小册子,对于儒家、道家和佛教的美学都进行了系统观照。
在欧洲大陆,被称有“求异”倾向的德国波恩汉学学派,不同于传统的德国汉学研究,中国美学研究恰恰成为了其内在组成部分。特劳策特尔(Rolf Trauzettel)与顾彬(Wolfgang Kubin)构成了这个学派的核心性的角色。顾彬1985年出版了《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Der durchsichtige Berg:Die Entwicklung der Naturanschauung in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1985)对中国的自然美学进行了深入探讨。表面上看,作者是从《诗经》、《楚辞》到唐代诗歌中出现的自然描写来进行美学升华的,实际上他真正关注的重点是汉魏至南朝这一段中国文人之“自我意识”的勃兴时期,对于“作为象征”、“作为危险”、“作为历史进程”和“作为心灵的宁静”的中国文人镜像中的自然观进行了深入解析。此外,顾彬的中国古典戏剧研究也颇有特色。顾彬还把特劳策特尔学和法国汉学家于连(Franois Jullien)的汉学研究看做是同一类型,于连1992年的《势:中国功效的历史》及其《不可能的裸体》等著作当中,都关注到了中国美学思想。这些学者的共同特点,就是以一种更新的西方视角来反观中国美学,就连阿恩海姆也曾在1997年《英国美学杂志》的春季号上写过《中国古代美学与它的现代性》这样的论文。
另一位重要的德国汉学家卜松山于1982年以研究郑板桥的诗、书、画的美学在多伦多大学获得东亚研究博士学位,他不仅在1990年撰写了《象外之象——中国美学史概况》(Bilder jenseits der Bilder–ein Streifzug durch die chinesischesthetik),而且他的更为全面深入的专著《中国美学与文学理论》(sthetik und Literaturtheorie in China,2006)在2006年也得以出版,该书属于德文版《中国文学史》的第五卷。该书从“语言与思维”的中国美学的基本元素和观点谈起,从《诗经》一直写到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两千年间的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史,重点论述了“情景交融”、“意在言外”、“无法之法”、“自然创造”和“天人合一”等重要美学命题,勾勒出了中国古典美学由儒、道、佛三家思想合流而产生出的独特格局,除了以文学为主的叙述之外,作为中国画的美学基础的“气韵”、苏轼与“胸有成竹”竹画美学、清代的“无法之法”绘画美学则是作为插述而存在的。[※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苏源熙(Haun Saussy)的《中国美学问题》(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1993)则采用解构主义的修辞阅读法重构了儒家对于《诗经》的注释史,并视其为一种“讽寓性”的古典美学模式。与这部专著类似,许多直接命名为《中国美学》(Chinese Aesthetics :The ordering of Literature,the Arts,and the Universe in the Six Dynasties,2004)的专著,或者倾向于对文学的研究,或者只是断代史的陈述。
真正将原汁原味的中国美学史呈现给海外的,还是通过中国哲学家和美学家李泽厚一系列著作的翻译出版来完成的。李泽厚的1981年文物出版社首版的《美的历程》,在1988年就被北京对外的朝华出版社(Morning Glory Publishers)依据1983年中文版翻译出版,当然对世界影响更大的还是1988年的牛津大学出版社版本,副标题被补充上了《中国美学研究》(Path of Beauty:A Study of Chinese Aesthetics)。李泽厚的关于美学原理的专著《美学四讲》1989年由三联书店首版,被翻译成英文后由李泽厚与译者联合署名,副标题被补充上了《通向全球视角》(Four Essays on Aesthetics:Toward a Global Perspective)于2006年出版。2009年,李泽厚1989年首版于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的《华夏美学》被翻译出版,这个版本的译文是非常精致的,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直译为《中国美学传统》(The Chinese Aesthetic Tradition)。
其他中国美学研究者的外国专著,主要有朱立元和美国学者布洛克(Gene Blocker)所共同编辑的《当代中国美学》(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被归于《亚洲思想与文化》的第17卷在1995年得以发表,针对海外介绍了当时国内的美学研究状况。高建平的博士论文《中国艺术的表现性动作:从书法到绘画》1996年出版于乌普萨拉,该书论述了中国艺术理论中的表现性与动作性、情感与艺术形式的关系,具体探讨了中国绘画中的线的性质,线条美的标准和线与线之间的关系,中国艺术的特征与人的动作的关系,表现性的动作怎样挑战再现性的形象等问题。最终,全书对中国与西方的艺术思想进行了比较性的总结,区分了“形式性的美”和“表现性的美”、区分了以“别异”与以“表现性”为目的的符号的两种的书写性意象,最终归结到两种整体观——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有机整体”思想和建立在主客一体基础上的表现性动作整体——的差异上,落归于从“意”到“气”到“势”再到“笔”的由创作主体的活动所决定的艺术整体思想。[※注]
最新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专著,就是由国际美学协会美国执委玛丽·魏斯曼与总执委刘悦笛所共同主编的英文版新著《当代中国艺术策略》(Strategies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这本书由世界著名的布里尔学术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通过中西美学家和艺术批评家之间的积极对话,将当代中国艺术的理论与实践所展现出来的当代性与丰富性展现给了世界,包括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在内的中西学者都积极参与其中。整个文集以魏斯曼的《当代中国艺术的策略》为开篇,终结于刘悦笛的《观念、身体与自然:艺术终结之后与中国美学新生》,预见了艺术与生活的关联将愈来愈紧密。正如玛丽·魏斯曼所言,这部新的文集力求显现出中国艺术及其理论的再生,刘悦笛从2009年度的《国际美学年刊》开始到本书都积极倡导一种中国美学与艺术的“新的中国性”(Neo-Chineseness)。[※注]美国布林茅尔学院迈克尔·克劳兹将该书评价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跨文化影响的重要贡献,对于中国文化意义的哲学理解的重要贡献。作者既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的哲学家与艺术史家们,这是他们关于当代中国前卫艺术研究的第一次合作”,这的确是一项“显著的成就”。[※注]
进入全球化的时代,当代中国美学研究逐步追赶上全球化的脚步,这可以以2010年在中国举办的“第18届国际美学大会”(18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Aesthetics)作为标志。实际上,在这种高度的中西美学频繁交流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美学比照的研究范式也开始得到了转换。正如笔者在第2009年举办的“第八届文化间哲学国际大会”(8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Intercultural Philosophy)上发言所见,当代全球哲学当中的“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被凸显了出来:如果说,“比较哲学”还只是犹如在两条“平行线”之间在做比照、“跨文化哲学”更像是从一座“桥”的两端出发来彼此交通的话,那么,“文化间哲学”则更为关注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融会和交融。
同理可证,从“比较美学”、“跨文化美学”到“文化间美学”的转换,也将是未来的基本走势,而分殊(diversity)、互动(interaction)与整合(integration)将成为这三种美学思路的不同层级的任务。正如国际美学协会所积极倡导的国际美学领域的新运动所坚定宣称的那样:今日的全球美学面临着“文化间性转向”的问题,这种转向所赞同的是一种文化间的“杂语”而非仅仅“对话”,这是因为,过去的理论家们是从东往西看、从南往北看,而今则要改变观念:在世界舞台上去展现东方和南方过去和现在是怎样看西方的。这意味着,国际美学界不仅要推动美学上的文化转向,同时也对更广泛领域的“文化间性转向”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