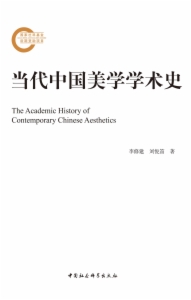四 魏晋南北朝美学研究
|
来 源
:
|
当代中国美学学术史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 | ||
|
摘 要
:
|
断代美学史研究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是美学思想的研究,如施昌东的研究,以“美”为核心,梳理相关文献中的论美资料并加以分析。王明居的《唐代美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郑苏淮的《宋代美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皆属对美学思想的研究。第一编论隋代美学,第八编讲五代美学,主体部分共六编研究唐代美学,第七编探讨了传奇小说美学、园林美学、书法美学、乐舞美学、美术美学和服饰美学等门类美学。在研究方法上,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多依据唯物主义反映论或实践美学的思路, 90年代以后,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有所拓展与深化,如文化史的视角、阐释学的视角、身体美学的视角等。 | ||||||
|
关键词
:
|
美学 美学思想 思潮 文化 美学思潮 文艺理论 研究方法 美学范畴 审美观 观念 文学 |
||||||
在线阅读
四 魏晋南北朝美学研究
字体:大中小
魏晋南北朝,又称六朝。六朝时期常被视为文学艺术的自觉时期,在这一时期,不唯士人审美大受重视,文学艺术繁荣异常,理论著作亦竞相迭出。因此之故,六朝美学尤其是魏晋美学是最受中国美学界关注的一个研究对象,理论成果非常之多。此处对两本六朝美学史进行分析。
六朝美学史,以袁济喜的《六朝美学》和吴功正的《六朝美学史》为代表。
袁济喜的《六朝美学》(1989)是较早出版的六朝美学史专著,1999年进行了修订。该书以审美范畴及命题为研究中心,探讨了人物品藻、玄学思潮和佛教哲学影响下的六朝美学,分析了六朝文艺理论中有关审美创作、审美鉴赏、审美风格、形式美的理论。第一章“人物品评与审美”是六朝美学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梳理了从汉末到六朝的人物品鉴及相关的人格美、文艺美等审美观念的变迁,重点探讨了曹丕的“文气说”及顾恺之的“传神写照”等文艺理论;第二章“‘有无之辨’与审美”分析了魏晋玄学对美学思潮演变的作用,及其影响下的自然山水赏会和艺术理论中的本体论审美观,玄学领域的“言意之辨”对审美理论的影响(如隐秀、意象等理论);第三章“自然之道与审美”,分析了与有无本末密切相关的自然范畴在六朝的新发展,分别从人格美、艺术美和创作构思理论方面进行了探讨;第四章“佛教与审美”论述了佛学对六朝美学范畴“形神论”、“造像论”的阐释和发挥,及佛学影响下的审美境界论与修养论;第五章“情感与审美”分析了六朝美学审美主体论的情感论,重点探讨了文学情感的个体性与表现性;第六至八章“审美创作与审美鉴赏”、“个性风采与审美风格”、“形式美理论”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为重点文本,阐发了六朝美学中艺术创作理论和鉴赏理论中的重要范畴,如审美创作的“虚静说”、“神思说”、“感兴说”,“披文以入情”所体现出的审美鉴赏论,“风清骨峻,篇体光华”中的风骨说,以及“文笔之辩”、齐梁声律论等形式美理论。可以说,该书抓住了六朝美学的理论关键(人物品藻、玄学、佛学),对六朝时期的主要审美范畴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梳理。
如果说袁济喜的《六朝美学》探讨的是审美思想,那么吴功正的《六朝美学史》(1994)则是审美思想与文艺理论并重。吴功正指出:“我所理解的中国美学史(当然包括断代美学史)是由两大板块所构成的,即元美学和美学学双峰并峙却同归一脉,二水分流却共出一源。美学学属于理论形态,有较强的可认知性,就六朝而言,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萧统的《文选序》、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等,而文学实践性创作现象却是感性的、灵动活跃的、变动不居的、其审美活力是旺盛的。”也就是说,他的美学史写作是元理论与文艺理论并重。他的几部断代美学史都贯彻了这种研究思路。全书共七章,第一章从学术思想(经学到玄学)、审美观念、美学风格等方面,介绍了汉代美学到六朝美学的过渡。第二章探讨了六朝美学的时代背景,如庄园经济、玄学思潮、士人风气、隐逸情调、佛学思潮和社会风习等。第三章简单分析了六朝时人对人的自我的发现以及对自然的发现,亦即宗白华所说的“魏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第四、五两章为全书重点,篇幅占全书的近三分之二。第四章探讨的是审美范畴,包括妙、言意、丽、气韵。第五章为门类美学,包括了绘画美学、书法美学、乐舞美学、雕塑美学、园林美学和文学美学,文学美学又分为诗歌部门(郭璞、陶渊明、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谢眺、沈约、萧氏父子等人)、骈赋散文部门(分东晋、刘宋、刘梁陈三个时期)、小说部门(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和理论部门(《文心雕龙》、《诗品》、萧氏父子的文学理论)等。第六、七两章对六朝美学进行了总结。作者认为:“六朝是中国美学走向自觉、基本定型的时期。六朝是中国美学在各个门类领域全面发育的时期。六朝是审美主体的人的审美器官基本成熟的时期,发现和感受到人的情绪结构的多面性。”[※注]这种观念基本代表了学界对六朝美学的定位。总起来看,全书篇幅巨大,对六朝美学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以文学为主的门类美学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当然,其中亦有值得探讨之处,如文学美学部分,对曹魏及西晋时期的文学似乎重视不够。
李戎的《始于玄冥反于大通——玄学与中国美学》一书,前五章对魏晋玄学史进行了梳理,从正始时期玄学的倡导者何晏与王弼、竹林时期的嵇康与阮籍、东晋时期的佛玄合流到化玄理为情思的陶渊明,后六章主要对玄学论美学的审美范畴以及受到玄学影响的人物进行了分析。宗白华先生提出魏晋是中国美学转变的一个关键,中国人的审美趣味由“错采缕金”转向了“芙蓉出水”,追求一种自然的表达与个体人格的显露,作者认为魏晋玄学是中国美学大转折的契机,它转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从“立象以尽意”到“得意而忘言”,导致了主体意识的复归和悲剧情怀的兴起;玄学使人们的审美理想从质实转向了空灵;这些观点无疑都深受宗白华的影响。作者以三章的篇幅讨论了玄学论美学的若干审美范畴进行了梳理,包括无与空、玄与妙、自然、得意忘象与得意忘言、传神与神韵、气韵、风骨、滋味、意境等。在具体写作中,作者以魏晋玄学及文艺理论中的相关材料加以解析。作者还对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以及苏轼的人生观和文艺理论进行了探讨。作者将司空图界定为“玄学论诗学理论家”,通过对《二十四诗品》与《老子》、《庄子》中相关文字的对比,作者指出《诗品》中的一系列重要概念都来自老庄著作,“司空图的不朽之功,正是在于他把道家哲学艺术化了”[※注]。作者将苏轼认定为“追慕陶潜、归诚佛玄”,透过其人生历程及文艺主张,分析了其中的玄学倾向。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