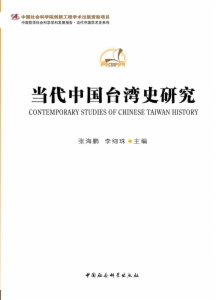二 历史观与方法论问题
|
来 源
:
|
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3 | ||
|
摘 要
:
|
讨论台湾史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研究台湾史的基本立场问题,其次是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如果用这样的后殖民史观解释台湾历史,实现“台湾独立”,就应该把所有的汉人(包括坚持“台独”立场的所有汉人)都撤出台湾, 2000—2008年的民进党政权也是殖民地政权,全部应该撤出去,还政于原住民。“台独”人士的目的是要使台湾脱离中国,由“台独”人士在那里“独立建国”,他们不想与国民党分享政权,不想与共产党分享政权,当然也不想与台湾原住民分享政权。当然,如果从现代中划出一个当代,也许隐含的社会形态分期更清楚一些,这个意见以后修订时可以采纳。 | ||||||
|
关键词
:
|
殖民地 台湾 台独 政治立场 中华民国 历史事实 社会形态 台湾人 立场问题 政权 台湾史 |
||||||
在线阅读
二 历史观与方法论问题
字体:大中小
(一)指导思想问题
研究台湾史,与研究中国史、世界史一样,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可以有各自的指导思想。但是,从思想体系来说,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物主义历史观最核心的是尊重历史事实,在历史研究中尽可能收集有关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全部史料,进行考证、辨识、逻辑梳理,弄清楚历史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追求历史的发展规律。
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历史著作的要求,其实并不那么复杂高深,无非是处理历史问题,一切按时间地点为转移,也即历史的方法,因为离开了时间和地点,历史事件将无法获得正确的说明和解释;对历史发展的重要情节,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因为人类历史的关键环节,往往受经济利益的支配,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离开了受经济利益支配的阶级博弈,很难说明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动向;对历史发展的大势,不能忽略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注意历史发展中的规律性,只关注历史进程中的某些细枝末节,难以说明和解释历史发展的方向。
在台湾史研究中,指导思想上的分歧,史观上的分歧很明显。海峡两岸的台湾史研究者之间,由于政治立场的差异,历史观差异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台湾史研究的宏观认识上,在台湾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上,差异几乎难以抹平。在具体历史问题研究上,差异可能不那么显著。
(二)史观问题
史观,即历史观,表示用什么观点看待历史问题,或者如何看待历史问题。随着台湾问题的突出,随着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显学,有关台湾历史的史观问题,引起学者的重视和讨论。
1996年台北出版的《历史月刊》第105期推出一个专辑,以“两岸对峙下的台湾史观”为题,发表了王明珂、陈芳明、陈映真、陈其南、陈孔立五位学者的意见,这五篇文章,无论是其政治立场的明确性或者隐含性,基本上代表了台湾史观认识上的几种不同的或者说对立的观点。
中研院史语所副研究员王明珂指出:“数千年来,历史记忆与失忆使得许多人群成为中国人;也赖历史记忆与失忆使得许多人群成为非中国人。在现实的两岸关系中,历史失忆与重建历史记忆,成为台湾人试图脱离中国、建立本土认同的工具。”他还说:“台湾在历史记忆的本土化方面,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便是如何建立一个岛内各族群皆能接受的本土历史记忆以凝聚台湾人认同”,“近年来在台湾进行的重建历史记忆与失忆风潮,其主要倾向便是以‘日据时代的经验’与‘南岛民族的本质’,来诠释台湾人与台湾文化的特质,并借此脱离中国联系”。[※注]这篇文章隐约指出了台湾史观正处在演变过程中,似乎表明了作者的关注与忧虑。
如前所述,静宜大学副教授陈芳明以明确的政治立场主张台湾史研究中的后殖民史观。他指出:“所谓后殖民史学,系指殖民地社会在殖民体制终结后对其历史经验进行的反省与检讨。……对于殖民经验的全面检讨,从而理清何者属于外来者的观点,何者属于本土的观点,正是后殖民史学的重要课题之一。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台湾历史的发展,后殖民史观的建立是值得追求的。”所谓后殖民史学,是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家脱离殖民地独立的历史反思,这是有它的合理性的。问题是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不存在民族独立问题。在这样的前提下,从后殖民史学去追求台湾历史的真相,无疑缘木求鱼,基本立场站错了,所以他对台湾历史的解释也是错的。怎么可以把这样的史观当作研究台湾历史应当追求的史观呢?其实,陈芳明的后殖民史学并不新鲜,基本观点都是从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中抄过来的。
应当指出,台湾作家陈映真有关台湾史观的见解是值得称赞的。陈映真从唯物史观(他在文章中称作社会经济史论或者社会史论)对台湾的历史做了历史的、阶级的分析,认为台湾历史上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指出:“台湾的殖民地化……并不是一个原本独立的社会、民族或国家的殖民地化,而是从中国被分断窃占出去的领土之殖民地化。因此殖民地化期间台湾的反殖民地压迫的斗争,就历来不是反帝→独立的斗争,而是反帝→复归祖国的斗争。而当支配的殖民者败亡时,台湾的斗争也历来不是‘恢复独立’的斗争,而是复归祖国的斗争,这是理所当然的。”[※注]这是一个中国史观,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陈其南认为,台湾历史研究所遇到的问题,是在于无法摆脱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立场之纠葛。他指出:“有些论著更是清楚地在为台湾的政治独立寻求历史研究和学术理论的根据。如果将之视为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或区域研究样本,当然也不能说有何不妥。”他自己的看法是:“在不同的中国人社会中,不论他们是属于一个或多个国家,均应体现出理性的政治生活之本质;及国家的性质和国籍的归属应以人民的意愿和福祉为前提,而不能单由历史传统或既存政体的主体势力来规定;政治问题的解决应着眼于民主政治的建立,而不是一味地以民族感情和文化主义来强求。”[※注]作者当时为“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虽然用政治语言讲台湾史,立场貌似公正,其实他的“台独”史观在这里也是很清楚的。
厦门大学陈孔立教授认为:“台湾历史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全国的历史有着共同性:但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它的历史也必然有其特殊性。如果只强调共同性,而忽略其特殊性,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台湾的历史,也不能正确地认识台湾的现实;如果只强调特殊性,而忽略了共同性,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上的两岸关系和当前的两岸关系,也无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台湾的前途问题。”[※注]陈教授的台湾史观大体上代表了大陆学者的台湾史观,即从一个中国的历史观来观察台湾的历史。
此外,还有一种所谓“兼顾史观”。所谓“兼顾史观”,即既要照顾到台湾人的观点,也要照顾到(台湾的)大陆人的观点。据陈孔立文章,这是美籍华人教授许倬云的看法。陈孔立把它概括为台湾史中的“兼顾史观”,对它作了分析,指出“兼顾史观”难以兼顾的“难题”:“有史观就有认同,有认同,就有‘我者’与‘他者’的区别,就很难做到‘兼顾’,兼顾史观无法避免‘认同不能兼顾’的难题。”[※注]
宋光宇在《台湾史》中设专章讨论台湾史观,列举了台湾地区台湾史研究中的11种史观。他评论说:“这些理论也都不是全面的、完整的。有如瞎子摸象,看谁摸到什么部位,就说象长得像那个样子……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些史观非常狭隘,如日本强权论、新台湾人论、同心圆论等。也有的史观是从全世界来看,如依赖理论。理论的涵盖面越大,内容就越容易粗疏,涵盖面小,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要想找到一个切中时弊,又可以用来解释同一时候,东亚、已开发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理论,似乎相当不容易。”[※注]
毋庸置疑,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地区,研究台湾史的学者之间,在处理史观方面都会有差异,会有不同的定义与解说。可以说,上面引证的五种意见,大体上代表了两岸学者间台湾史观方面的不同见解。
陈孔立最近指出:“总之,两岸存在不同的史观,这就影响到对具体历史的不同看法。”[※注]我同意这个判断。可以举出大量例证来证明这个判断。
上举陈芳明的文章,足可以明了这种分歧。陈芳明假设台湾自古就是一个国家,那里的住民就是今天所谓的原住民。早期汉人来台湾开发就是殖民,以后在台湾建立的所有政权都是殖民地政权,包括明郑、荷西、清朝、日本以及1949年后的国民党政权。所有在台湾建立过政权的政治力量,都一贯在压迫原住民。如果用这样的后殖民史观解释台湾历史,实现“台湾独立”,就应该把所有的汉人(包括坚持“台独”立场的所有汉人)都撤出台湾,2000—2008年的民进党政权也是殖民地政权,全部应该撤出去,还政于原住民。如果实现这个局面,提倡“台独”的人士还能落得什么呢?今天台湾的争论还有意义吗?这当然不是“台独”人士的目的。“台独”人士的目的是要使台湾脱离中国,由“台独”人士在那里“独立建国”,他们不想与国民党分享政权,不想与共产党分享政权,当然也不想与台湾原住民分享政权。认识台湾历史问题的最重要关键是台湾历史上是否存在过一个国家这样的历史事实。正如陈映真文章所指出的,台湾史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或“民族”,也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这才是台湾史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让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回归台湾史,那么,一切所谓“台独”史观,包括所谓后殖民史观,都只是子虚乌有,好似建筑在沙滩上的高楼大厦,沙滩一旦松动,大厦立即垮塌。因此,“台独”史观既没有确凿的历史事实做支撑,也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做支撑。
不同的史观对台湾历史总体发展的认识差异也极大。如有关台湾四百年史,一些书的书名就如此标出。[※注]著名“台独”理论家史明最早推出《台湾人四百年史》,明确把台湾历史与祖国大陆相切割。此后,台湾一些政客开口闭口“台湾四百年”。事实上,公元230年(三国吴黄龙二年)卫温等率甲士到夷洲以及随后沈莹作《临海水土志》,是汉文典籍最早记录台湾的历史,也是台湾最早进入人类史册。元朝在澎湖建立巡检司,要比荷兰侵入台湾早得多,也要比葡萄牙人命名“福尔摩萨”早得多,为什么不用这些历史记录呢?2003年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杜正胜组织的“福尔摩萨”展,就是要把台湾与祖国区隔开来,就是“去中国化”的表示。究竟是400年还是1700年,不同的台湾史观在这里区别得再清楚不过了。
“台独”史观者极力表彰“日据时期的经验”,大谈日本对台湾的开发,却对清朝对台湾的开发视而不见;大谈“南岛民族的本质”,却对自宋以来汉族人对台湾的辟荆拓莽视而不见。台湾的少数民族固然值得认真研究,早期汉族人对台湾的开发就不值得认真研究吗?只强调汉族人对原住民的掠夺,不研究汉族人与原住民的合作,这样公平吗?陈芳明的文章判定:“综观整个满清历史时期,统治者并未负起开发台湾的责任。”[※注]这句话太不公平了!清朝的统治固然是封建统治,但是清朝统治者对台湾的建设与开发的史迹也不能抹杀。这就是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康熙以后,台湾的政权建设日臻完善,文化教育建设也在逐渐开展,难道不是事实吗?1885年建省,是一个重大举措。那时候祖国大陆拟议中的建省也还没有实现。台湾建省前后沈葆桢、刘铭传等在台湾开展的开山抚番以及早期现代化事业,不仅载诸史籍,而且有口皆碑。台湾的洋务事业的开展不落后于大陆各省,甚至还走在前列。怎么能说没有负起开发台湾的责任呢。可见台湾史观的不同,对具体历史事实的解释相差甚远。
日据、日治之争,是近几年台湾政界与学术界有关中学历史教科书编纂中的一大争议。这恰好反映了两种对立的台湾史观在处理日本统治时期评价时的差异。我在前些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在台湾出版的台湾史著作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主体性倾向。比如一些著作,把清朝时期的台湾称作清领时期,又把日据时期的台湾称作日治时期,贬此扬彼,泾渭分明。所谓‘清领’,是指台湾曾经为清朝占领或领有的意思。台湾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历史上曾经有短暂的时期为荷兰、日本占据,不久便为中国收回。所谓‘荷领’‘清领’‘日治’,分明是把台湾的主体性无限扩大为‘台湾国’,是为‘台独’制造历史根据的用语,虽然一字之差,却体现了一种春秋笔法。”[※注]
更有甚者,把“台湾史”与“中国史”对立起来,“台湾史”是本国史,“中国史”是外国史,以致出现所谓中国是“外国”,是“敌国”,“中华民国史是外国史”,“孙中山是外国人”,等等,这样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苦涩笑话。这是前些年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湾教育部门的认识,这怎么可以说是正确的台湾史观呢?
(三)历史分期问题
台湾史的分期问题也是在处理台湾通史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一定会要加以处理的问题。
《台湾史稿》出版后,有学者对该书的分期提出了质疑。该书分成上卷、下卷,上卷是台湾的古代与近代,下卷是台湾的现代。书中找不到古代、近代、现代的起讫点;因为该书下限截止于2010年,似乎应该从现代中划出一个当代。[※注]台湾历史分期,是一个可以商榷、讨论的问题。
刘大年等著《台湾历史概述》将台湾历史分期为封建制以前的时期(1661年以前),封建制度时期(1661—1840年),半殖民地半封建和殖民地时期(1840—1945年)。这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形态学说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做的分期,大体上与整个中国史的历史分期方法相同。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台湾历史做这样的分期,这是第一次。我认为这是一种科学的分期。
陈碧笙著《台湾地方史》没有做明确的分期。全书21章,每章大体上是按时间顺序安排的。从章节安排看,台湾历史可以分为原始社会时期、封建社会时期和半殖民地时期。
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按照早期台湾、荷兰入侵的38年、明郑时期、清代前期、清代后期、日本统治的50年、当代台湾来分章,这也是一种分期方法。这种分期方法大体上类似于中国通史按照朝代分期的方法。宋光宇和戚嘉林的《台湾史》,分章很多,大体上类似《台湾历史纲要》的分期法。
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对台湾历史进行分期,台湾也有学者做这种主张。陈映真是一个典型代表。陈映真认为,从社会史的角度看台湾历史的各阶段,最概括地说:荷据时期的台湾,是一个殖民地的、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支配下的欧式封建社会;明郑时期,台湾的殖民地性格消失,明郑在台湾实行豪族部曲的封建制;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期间,台湾社会进一步成为较为发达的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1840年)到马关割台(1895年)期间,台湾和大陆一道遭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使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95年马关割台,台湾进一步沦为日帝总督府直接统治下的殖民地。[※注]这样的认识,大体上与《台湾历史概述》相同。
我作为《台湾史稿》的主持者是认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台湾史稿》本来可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来给台湾历史分期,考虑到台湾一般读者的接受程度,没有在分期问题上突出社会形态的区分。但是,该书把台湾历史分作古代、近代和现代,是与我们对中国历史的总体认识相一致的,其中也隐含了社会形态的分期用意,即古代是封建社会,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和殖民地社会。台湾的现代比较复杂,与大陆的发展走着不同的道路,这是台湾历史的特殊点。中国大陆在1949年后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台湾作为尚未完成统一的一个省,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下成为一个政治实体,沿用了“中华民国”的称号。从社会形态的角度说,这个政治实体在1949年后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为台湾处在美国控制下,接受美国经济援助,政治上、军事上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美国的安排。1979年后,中美建交,美国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从国际法上放弃了对台湾的政治保护。此前,台湾也放弃了美援。此后,台湾社会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无论是在政治形态上,还是在经济体制上,都在沿着美式资本主义道路发展。
《台湾史稿》没有标明台湾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时限,似是一个缺点。编写者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鸦片战争前是古代,鸦片战争后进入近代,该书第四章“中国边疆危机与台湾建省”,就是从鸦片战争讲起的,这里就包含了时限概念。下卷从1949年开始叙述,也是一个时限的标志。当然,如果从现代中划出一个当代,也许隐含的社会形态分期更清楚一些,这个意见以后修订时可以采纳。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