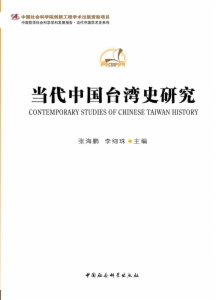三 明以前台湾经济贸易史
|
来 源
:
|
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5 | ||
|
摘 要
:
|
针对众多台湾通史性著作忽视台湾史前历史,以及“台独”论者所谓“台湾岛为西洋人最先发现”“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只有四百年历史”的谬论,张崇根详细叙述了上自3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长滨文化,下迄明朝天启四年。黄俊凌编著《史前时期的台湾》[※注]是一本学术性通俗读物,简要介绍了台湾史前时期的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铁器文化,以及从三国至宋元时期台湾与大陆关系的基本状况。尽可能地创造条件亲自赴台调查研究,进一步利用台湾学者发掘的丰富资料,加强两岸台湾史学界的交流与协作,是大陆学界推进早期台湾史研究的必由之路。 | ||||||
|
关键词
:
|
文化 大陆 台湾 原住民 台湾少数民族 新石器时代 岛夷 流求 民族 起源 东番记 |
||||||
在线阅读
三 明以前台湾经济贸易史
字体:大中小
明代以前,台湾岛上的少数民族土著居民仍然处于原始经济形态,过着原始的狩猎、渔耕生活。陈国强具体探讨了台湾少数民族原始农业的起源和发展,认为在台湾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左镇人”和长滨文化的主人,还过着渔猎和采集的生活,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坌坑文化时期便有了原始农业的发明。在圆山文化与凤鼻头文化时期,农耕已经成为当时台湾少数民族先民的主要生产方式,这既可以从考古发现来证明,也可以从历史文献记载获得佐证。但是,直到明末清初,台湾少数民族农业仍然处于原始状态,他们大部分还使用简单石器农具,集体劳动,过着平均分配、共同消费的生活。随着郑成功收复台湾与大量汉族移民迁入台湾,带入铁器农具、耕牛和汉族先进农耕技术,才使一部分少数民族逐渐学会使用铁农具、牛耕等先进技术,推动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以至整个台湾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陈国强还专门研究三国时吴国沈莹的《临海水土志》和《隋书·流求传》两篇史料,认为三国时期台湾“山夷”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还处于新石器时代,尚未进入金属时代。从社会组织看,他们还没有等级的差别,还没有政权和国家组织,过着氏族部落的生活。按恩格斯和摩尔根关于原始社会史的分期法,“山夷”的社会经济应还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还没有产生私有制和“零星现象的奴隶制”,是母系氏族社会繁荣的时代。隋唐时期台湾“流求”人的社会经济情况和生活文化特点等,已较“山夷”进步。从生产工具看,“流求”人主要使用石器骨角器,虽也使用铁器,但还不是自己采矿冶炼,尚未进入铁器时代,只处于金石并用时代。从社会组织看,当时还没有阶级社会的等级制度和观念。“流求”人已经有了私有制,离开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母系氏族,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父系氏族社会。[※注]
向安强根据现有的台湾史前农业考古资料,结合华南乃至整个东南亚和太平洋区域的同类遗存,吸收古地质学、人类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对台湾史前农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他指出,虽然台湾的原始经济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但其史前农业的发展并未落伍,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初期曾先后经历了“刀耕火种”期、锄耕农业前期、锄耕农业后期和发达锄耕农业期四个发展阶段,表明台湾是农业起源与发展研究所不可忽略的区域,这一研究也有助于全面认识华南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农业起源问题。向安强还专门对远古至清初的台湾原始稻作农业形态进行探讨,认为台湾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直至明末清初,台湾土著仍然生活在一种独具特色的原始社会之中。台湾稻作农业至迟始于新石器时代中期;17世纪初叶,荷人侵台,既奖励大陆汉人移民开垦土地,又教化蒙昧土著,使其从事定居农耕,是为台湾稻作的发展时期;继之,郑成功入台,采取“寓兵于农”政策,积极开垦荒地,始奠定台湾稻作农业发展的根基;清朝前期,台湾稻作进一步发展,但台湾“番”族的稻作形态仍较原始,耕作技术比较落后,特别是其中的“野番”和“生番”,稻作农业或无或处于相当原始的阶段。[※注]
朴寅吉研究17世纪前后台湾平埔人的社会经济形态,认为在17世纪前后平埔人的狩猎经济与农业经济两大部门之间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由于打鹿业的衰落和汉族移民的影响,平埔人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很快,并逐步取代打鹿业成为整个社会经济中最主要的经济生产部门。在17世纪中叶,平埔人在两大主要经济部门中已基本上放弃石器和骨角器而普遍使用铁制工具,并已有五分之一平埔人进入牛耕铁犁阶段,标志着平埔人已跨入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注]
早期台湾商业史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黄福才做了开拓性研究。他认为,台湾商业是伴随着大陆汉族人民在台的开发活动而产生的,其萌芽、产生过程有其特殊之处。台湾土著居民长期过着原始的狩猎、渔耕生活,在这种经济形态中,不可能产生原始商业。宋元时期,大概在南宋中后期,随着对澎湖经营与开发的加强,福建沿海渔民已可通过澎湖到达台湾西南海岸,在台湾岛的南部、北部栖息,并逐渐与岛上土著居民接触、交往,以自己有余的米、盐、杂货等与土著民交换狩猎物,从而兼事所谓“汉番贸易”。台湾商业由此得以萌芽,并在元明时期进一步发展。其时台湾商业显著的特点是,其产生并不是台湾岛内社会分工的结果,而是大陆汉族人民活动的产物,在萌芽、初兴阶段,规模小,交易量小,交换方式为原始的物物交换,台湾岛上没有出现固定集中的商品交易市场,台湾早期商业与大陆经济、政治状况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注]
关于早期台湾对外贸易,主要是闽台经贸交流,廖大珂认为福建与台湾两地早在汉代就开始了交往,东汉时期已开辟了从福建经由澎湖抵达台湾以至菲律宾的海上交通航线,闽台之间有了最初的贸易往来,当时东冶(福州)已有人因贸易关系通过台湾而移居菲律宾,不过这只是偶然性移民,且此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唐中叶以后,随着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台湾的交流逐渐密切起来。到了宋元时期,澎湖正式被划入福建的海防和行政司法管辖范围,福建人民移居澎湖及台湾地区,从事开发和经贸活动,闽台经贸摆脱了就船贸易和“鬼市”的原始形式,过渡到稳定的组织形式,由此以澎湖为桥梁,闽台两地各种形式的交流也日益频繁,从而揭开了闽台关系史上新的一页。[※注]傅宗文认为,宋元时期开发澎湖群岛,促进闽台交往,以及因此而发现和开辟东洋航线,使闽台海上贸易终于以更加清晰的轮廓出现在太平洋盆地西缘的海岸线上。[※注]林仁川认为,宋代与台湾贸易关系还没有非常明确的文献记载,但从考古发掘可以看到台湾,特别是澎湖出土了许多宋代瓷器,这可能是福建商人路过台澎地区时卖给当地居民的。元朝汪大渊《岛夷志略》已经明确记载了福建与澎湖及台湾岛的贸易情况。另外,从捕鱼业的发展也可看出大陆渔民与台湾土著居民的交易关系,随着新渔区的开拓,从福建沿海经澎湖绕过台湾南端到菲律宾的所谓“东洋针路”(即东洋航线)得以开辟。明代福建与台湾的贸易关系比元代又发展一步,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福建移民的增多,台湾经济的发展,海峡两岸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经济联系非常密切,这对台湾地区的开发和福建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注]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