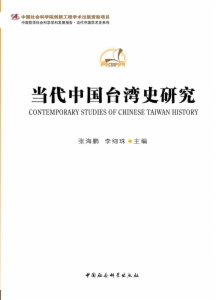第二节 荷兰、西班牙殖民时期台湾史研究
|
来 源
:
|
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2 | ||
|
摘 要
:
|
明清易代之际,台湾遭受荷兰、西班牙等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略,荷兰占据台湾38年(1624—。比如,关于荷据时期的历史分期,台湾被荷兰人侵占的原因,荷兰人对日本人、西班牙人、明清当局及郑芝龙势力的不同策略,荷兰人对“原住民”与汉人的统治政策,荷兰人由从事转口贸易为主到以经营本岛为主的转变,台湾转口贸易从兴盛到衰落的演变。针对荷兰学者包乐史(Leonard Blusse)所谓荷兰人最先在台湾设立行政机构,并对台湾的开发有过重大贡献的观点,黄志中撰文批驳,认为台湾和中国大陆有长达几千年的经济、文化联系, 1624年荷兰人进入台湾时,当地并非如包乐史所说只有寥寥几个汉族商人。 | ||||||
|
关键词
:
|
荷兰人 原住民 贸易 汉人 台湾 殖民势力 荷兰 转口贸易 商人 学界 大陆 |
||||||
在线阅读
第二节 荷兰、西班牙殖民时期台湾史研究
字体:大中小
明清易代之际,台湾遭受荷兰、西班牙等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略,荷兰占据台湾38年(1624—1662),西班牙侵占北部台湾16年(1626—1642)。荷兰、西班牙殖民势力与明清政府、郑氏集团及日本势力之间的纠葛,使台湾早期历史呈现错综复杂面相。荷据时期台湾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杨彦杰的《荷据时代台湾史》。[※注]该书系统论述了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湾及其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并走向败亡的全过程,对荷据时期许多重要的历史问题都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比如,关于荷据时期的历史分期,台湾被荷兰人侵占的原因,荷兰人对日本人、西班牙人、明清当局及郑芝龙势力的不同策略,荷兰人对“原住民”与汉人的统治政策,荷兰人由从事转口贸易为主到以经营本岛为主的转变,台湾转口贸易从兴盛到衰落的演变,荷据时期对台湾的经济掠夺与开发及其对台湾发展的影响,等等。这是第一部全面研究荷据时期台湾历史的学术著作,具有开拓与奠基之功。中国学者研究荷兰、西班牙殖民台湾历史的最大困难,就是不能充分利用当年殖民者留下的荷兰文、西班牙文原始档案,杨彦杰的《荷据时代台湾史》,最大的遗憾正是未能充分利用荷兰海牙国立综合档案馆中当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留下的档案资料[※注],而西班牙殖民侵略台湾的历史之所以少有问津,难以利用西班牙文原始档案资料的限制大概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 荷兰、西班牙对台湾殖民统治
荷兰入侵台湾本岛之前,曾短暂侵占澎湖,并与明朝福建地方政府进行过断断续续的战争和交涉,此即所谓澎湖危机。陈小冲具体考察了1622—1624年澎湖危机的背景、进程与影响,认为澎湖危机是荷兰殖民者在远东的贸易扩张及其与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竞争的必然产物。荷兰殖民者侵占澎湖,主要是为了打开对华贸易,因当时澎湖早已被纳入中国东南沿海军事与海防辖区,明朝福建地方官员与前线将领坚决要求荷兰人退出澎湖,但并不反对荷兰人退处“大员”(台南安平地区)。对于荷兰殖民者退据台湾,有些国外著作竟然称之为“割让”,甚至有个别学者声称台湾最早是荷兰的领土。陈小冲认为,澎湖危机中福建地方当局和明军前线将领充其量不过是口头上暂时允许荷兰人在“大员”滞留,以“大员”作为中荷通商贸易的口岸。双方既没有通过谈判签订正式的书面和约,也没有通过战争强迫某一方接受既成的领有事实,因此根本无从谈起任何形式的“割让”。但不可否认的是,澎湖危机的结局,客观上直接导致了荷兰殖民者对台湾的占领,之后殖民台湾达38年之久。[※注]在荷据台湾时期,澎湖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以及其在后来的荷、郑对抗中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杨彦杰撰专文探讨,认为荷兰人占据台湾后,明朝政府对于收复的澎湖相当漠视,使荷兰人有机会就近窃占利用,以之为船舶停靠、货物装卸与贸易的中转站和据点,并利用这个据点,大量收购和转运中国商品,从而取得台湾转口贸易的繁荣。与此同时,郑成功势力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以往台澎地区的军事、政治格局,特别是1650年以后,为对抗荷兰殖民势力,郑成功更加重视澎湖的战略地位,不仅重新恢复澎湖游击,而且经常派遣官员、军队到澎湖地区巡察设防,甚至把政令直接送入台湾岛内,加强对澎湖地区的管理和控制,有效地遏制了荷兰殖民势力的扩张,为郑成功最终收复台湾奠定了重要的战略基础。[※注]
针对荷兰学者包乐史(Leonard Blusse)所谓荷兰人最先在台湾设立行政机构,并对台湾的开发有过重大贡献的观点,黄志中撰文批驳,认为台湾和中国大陆有长达几千年的经济、文化联系,1624年荷兰人进入台湾时,当地并非如包乐史所说只有寥寥几个汉族商人,而是已有成千上万的汉人在此定居,最先在台湾建立政权的并不是荷兰殖民者,而是当时在台湾活动的中国海商,如林道乾、林凤、颜思齐、郑芝龙等人的武装力量。郑芝龙招募大批汉人入台,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台湾的统治,绝不是以“荷兰东印度公司雇员”的身份为荷兰侵略者效劳,更不是包乐史所说的“执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政策”。在荷兰统治38年间,台湾经济是有发展的,但并不能归功于荷兰殖民者的“开明政策”,相反,荷兰殖民者的残暴统治与掠夺则阻碍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徐晓望进而认为,在颜思齐、郑芝龙之前,袁进、李忠等海盗已在台湾的北港盘踞12年,他们实际上掌控着台湾,是台湾最早的开拓者。郑芝龙作为后起的海盗头目,是袁进事业的当然继承者。郑芝龙参与了为解决澎湖危机与荷兰人的谈判,知道北港是为了促使荷兰退出澎湖而作为交换条件暂时让给荷兰人的,所以他非常清楚荷兰人在台湾的地位。从这一背景看,1662年郑成功向荷兰人讨回台湾有其合法性的根据,只是荷兰人无视这一点而已。[※注]
台澎地区自宋元以来就成为中国开拓海洋世界的前出要区。晚明以来,日本、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班牙殖民势力都对台湾有所觊觎和行动,最后荷兰殖民势力控制了台湾,但其侵占既没有法理基础,又缺乏长期占台的实力,终于难逃被中国郑氏海上力量驱逐的命运。[※注]汪曙申撰文认为,17世纪荷兰海权崛起,凭借强大的海上实力向东方拓展贸易,并趁明朝陷入内忧外患、陆权衰弱之际侵占台湾,将之纳入其构筑的远东殖民贸易体系,使台湾成为荷兰海外贸易的中转站、出口商品生产地和税收来源地,以及打击西班牙和葡萄牙海上对手的重要据点。台湾沦为荷兰殖民地在某种意义上是东西方传统陆权与新兴海权势力消长的结果,也反映了中国封建王朝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台湾地缘政治价值的不同认知。[※注]宋洁利用《热兰遮城日志》中译本等珍贵资料,系统地考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台湾“原住民”殖民统治建立的历史过程。他认为,17世纪上半期,为了追求贸易利益,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到台湾,并在“大员”建立贸易转口站。为了巩固公司在“大员”的贸易阵地,荷兰人开始与岛上“原住民”发生接触。从1640年开始,东印度公司在“大员”的转口贸易稳定下来,并将目光转向台湾本岛的物产资源鹿皮、黄金、硫黄等,为了攫取这些资源,公司与岛上“原住民”矛盾激化,并展开对“原住民”的大规模武力征伐。经过近十年的武力征伐,公司最终建立起对台湾“原住民”的殖民统治。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原住民”的统治方式,主要包括政治上的地方会议制度和村社长老制度,经济上的贌社制度和年贡制度,文化上的传播基督教。[※注]张曙光则对“荷兰统治台湾三十八年”说提出质疑,认为在1624—1662年,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盘踞时间的确长达38年,但在这38年间台湾本岛内部形势错综复杂,多种势力互相牵制,并非如论者所谓“荷兰统治台湾三十八年”。这期间,中国势力郑芝龙集团及其子郑成功对台湾的建设、开发和守卫,有效地阻击了荷兰殖民者独霸台湾的阴谋。外国势力日本、西班牙与荷兰互相争夺,在此争斗过程中荷兰殖民者并未占据上风。实际上,荷兰殖民者统辖人口、地域并未广及全岛,即使在其盘踞的鼎盛时期,亦未真正统治台湾全岛。[※注]
荷兰殖民者对台湾的侵略与统治遭到中国人民的激烈抵抗。17世纪初,荷兰通过东印度公司在东方扩张殖民势力,起先侵占澎湖,随后在明朝政府的压力下退出澎湖而占据台湾南部,又通过清除日本、西班牙殖民势力,一度成为独占台湾的殖民者。荷兰殖民者残暴的压迫和掠夺,一开始就激起台湾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的不断反抗。目加溜湾、新港、麻豆、萧垅各社族人不堪忍受东印度公司的欺压和盘剥,经常起来反抗。汉人郭怀一起义是最大一次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郑芝龙势力也曾给荷兰殖民者以沉重打击。最后,郑成功率军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注]李祖基根据荷兰人的《东印度航海记》等资料,论述了荷兰殖民者在闽南沿海进行武装骚扰并侵占澎湖的活动,以及中国军民的抗荷斗争并把荷兰殖民者赶出澎湖的历史事实。[※注]
荷据时期,台湾处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荷兰殖民者与各方面势力的关系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荷据台湾早期荷兰与日本的冲突,学界一般认为是商业冲突。陈小冲撰文认为,其实在所谓商业冲突表象的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可以说是由初始单纯的商业冲突,逐渐演变为由长崎代官末次平藏精心策划实施的夺取台湾统治权的政治阴谋,其实质是日本与荷兰争夺台湾统治地位的政治冲突,最后被日本锁国政策所终结。[※注]徐晓望利用新翻译的荷兰档案《热兰遮城日志》等,研究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湾的战略意图及其与福建商人争夺台湾海峡控制权的斗争,认为荷兰殖民者侵略澎湖与台湾,其主要目的是垄断中国的商品出口,切断福建与马尼拉、澳门及东南亚之间的直接贸易,并取而代之。他们的侵略行动受到福建商人的抵制,以郑芝龙为首的福建商人利用包买制度反而控制荷兰人。但在荷兰人的军事压力下,郑芝龙被迫同意开放对台湾的贸易,并运去大量商品。这标志着荷兰从福建商人手中瓜分了相当一部分的商业利益。荷兰殖民者最终被郑成功驱逐,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妨碍了东亚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注]郑氏海商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是17世纪中叶台湾海峡最为强大的两股军事力量。陈思通过对当时荷郑双方在台海军事力量的比较分析,认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强大的海、陆军,其武器装备代表着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而郑成功领导下的郑氏海商集团,虽然军队武器装备不如荷军,但在人员数量、训练水平、作战经验、战略战术指挥等各方面都要比荷军更具优势。郑氏海商集团正是充分发挥了这些军事上的优势,才能在17世纪中叶的台海霸权争夺中屡次挫败荷兰东印度公司,并最终从其手中收复中国神圣领土——台湾。[※注]
西班牙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一直较少被学界论及,其中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博士研究生台湾人刘彼德的相关研究成果值得关注。西班牙人于1626年进占台湾鸡笼建立基地,接着扩张统治到淡水。不及十年,遭到淡水“原住民”强力反抗,淡水城堡在1636年一次夜袭中被毁,西班牙人被迫撤离,退守鸡笼。1636年,淡水“原住民”大败西班牙人可能是17世纪台湾“原住民”反抗外国殖民势力最大的一次胜利,是台湾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据统计估算,西班牙驻台湾总人口数历年之变化,1626年驻台人数为最高峰,超过1000人,其后持续减少,到1635年降至1000人以下,1639年总人数降至最低点为240人,后稍有增加,1642年西班牙投降荷兰时有446人。在西班牙人控制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只有鸡笼附近和淡水河流域的一些聚落,估计总人口数不到3000人,他们被迫为新迁入的数百上千的西班牙人供应粮食,无疑是极为沉重的负担。淡水“原住民”以原始武器激烈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原因是,西班牙人收到的大米补给远低于需求量,而且现金不足,粮食来源不继,唯有不断地向“原住民”需索存量不多的粮食,导致“原住民”不满。加以两个族群间的文化差异太大,淡水居民没有如西班牙人期望的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即使神父慈爱和关怀也没有能够化解淡水“原住民”长期累积的怨怒。最后“原住民”联合起来反抗殖民统治,赢得胜利。由于“原住民”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可以参考,只能从以西班牙文件为主的历史数据中,从殖民者的眼光揣测“原住民”的立场和想法,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注]
二 荷据时期台湾经济贸易史
关于荷据时期台湾经济的性质,大陆学界普遍强调荷兰统治者的殖民侵略性,因而认为台湾经济是荷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殖民地经济,台湾成为荷兰殖民者在亚洲地区侵略扩张、奴役掠夺的一个基地,台湾经济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经济附庸和原始资本积累的工具。[※注]针对既往学界沿用荷兰对台湾殖民统治施行“结首制”的观点,陈国强提出商榷意见,认为“结首制”实际上是台湾噶玛兰汉族人民的垦地组织(后来也是政治制度),并不是荷兰殖民者奴役台湾人民的殖民统治制度,荷兰殖民者奴役统治台湾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是通过“长老”制度来进行的。[※注]
关于荷据时期台湾经济生产与商业贸易的基本情况,黄福才著《台湾商业史》和林仁川、黄福才合著《台湾社会经济史研究》有比较系统的论述。[※注]林仁川研究荷据时期台湾的社会构成和社会经济,认为荷据时期荷兰人霸占台湾的土地、猎场、渔场等所有生产资料,不仅向台湾人民征收稻作税、狩猎税、渔业税,而且还征收人头税。当时台湾人民的职业构成有从事渔业为主的渔夫、从事贸易的商人、从事狩猎的猎人、从事农耕的农民和从事手工业的工匠等。荷据时期的台湾处于开发的起步阶段,人口比较稀少,农民种植的农作物主要以甘蔗和水稻为主,物产也比较缺乏,岛内的市场不大,能够输出的产品,只有鹿皮、硫黄以及后期的部分砂糖,其转口贸易主要从中国大陆运输丝、糖、瓷器三大商品,其时台湾的出口贸易是大陆海上贸易的组成部分,“大员”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转运中心。[※注]厉益、吴玮着重探讨荷据时期台湾蔗糖产量增长的原因,认为荷据台湾期间,随着蔗糖贸易利润的增加及市场的扩大,对蔗糖的需求益增,荷兰采取众多的奖励和扶植政策以推动制糖业的发展,加之来自大陆的移民解决了甘蔗种植和蔗糖生产的劳动力问题,使台湾的蔗糖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并一跃而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蔗糖贸易的供糖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荷兰人采取的这些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利于台湾农业的发展,但是本质意义上荷兰人是以台湾的蔗糖为其取得贸易利润的工具。台湾对于荷兰的意义首先是殖民地,其次是贸易中转站,最后是商品供应基地。[※注]
荷据时期,闽台经济交往频繁,台湾海峡商业贸易发达。17世纪上半叶,漳州港区与台湾荷兰人贸易是东西洋贸易网络的重要一环。荷兰档案文献记载Hambuan是30年代海峡两岸贸易中最重要的中国商人之一。杨国桢撰文指出了台湾学者把Hambuan比定为同安士绅林亨万的错误,并利用荷兰资料和Hambuan致荷兰台湾长官的十封信函,重建了一位通晓荷兰语、具有经商技巧和公关能力的明末自由商人的典型个案,分析Hambuan在海峡两岸贸易及中荷交涉中的作用,认为把海寇商人、豪绅商人视为明末海商的普通模式,抹杀了自由商人存在的事实,歪曲了中国海洋发展的历史。[※注]以往学界关于17世纪东亚海上贸易史研究,特别强调欧洲的经济、军事、外交等得以在亚洲扩张的力量,并形成自从欧洲人来到亚洲后,就支配了亚洲贸易的观点。张彩霞、林仁川在解读新近出版翻译的荷兰档案史料后,认为17世纪的中国海商实际上仍是台湾海峡两岸贸易的主导者。17世纪初期,荷兰人到达台湾海峡,以“大员”为据点,采用招诱与拦劫等策略,意图在中国海外贸易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却遭到郑芝龙海商集团和明政府的抗争。荷兰人为了顺利得到中国的货物,不得不融入华商经贸网络,接受中国海商的经贸惯习。由此,台湾海峡贸易市场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郑芝龙等中国海商手中,表现在中国海商掌控着贸易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主导贸易商品定价、制定台海贸易市场规则三个方面。[※注]
关于荷兰在台湾贸易的研究,是学界关注较多的课题。陈小冲把17世纪上半叶荷兰殖民者的对华贸易扩张过程以1624年为界标分为两个时期,认为前期处于试探机会、寻找突破口的阶段,其时对华贸易的主要方式是走私或转贩等间接贸易,商品来源不稳定,数量也不太大;到了后期,由于通过澎湖事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漳泉地区的近旁——台湾建立了商业据点,从而步入对华直接贸易阶段,台湾成了远东贸易的一个重要中继站。通观整个17世纪上半叶,与对手的竞争又是荷兰对华贸易扩张的重要特色,前期有葡萄牙、西班牙,后期为郑氏海商集团,荷兰殖民者的对华贸易扩张过程也就是排斥、打击对手,以图建立自己的商业优势的过程。[※注]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迫切想打开对华贸易的大门,达不到目的后,即在福建沿海一带实行海盗式的掠夺,并先后占据澎湖和台湾南部,在那里设立贸易据点,把中国丝织品、瓷器等货物转贩到日本、欧洲等地以攫取巨利。然而,荷兰殖民者采取的是极其野蛮的强盗行径,因此屡遭明朝军队的无情打击,被驱逐出澎湖岛。终明之世,荷兰从未取得直接对华贸易的权利。[※注]杨彦杰、李少雄专论荷兰人在台湾的转口贸易,认为荷兰人占据台湾后,虽然没有获得直接与明朝贸易的机会,但却获得在台湾转口贸易的实惠,他们以“大员”湾为据点建立台湾商馆,收购大陆的生丝、瓷器、砂糖、丝织品及台湾的鹿皮等商品,销往日本、巴达维亚,甚至转销欧洲,再把东南亚的香料及日本、欧洲的货物返销中国大陆或其他地方,从中获取商业利润。荷兰人在台湾的转口贸易,并不是建立在台湾本岛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主要是依靠大陆商品供给,并通过郑芝龙等中国商人进行,因而难以持久而必然走向衰亡。[※注]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热兰遮城日志》《东印度事务报告》有关台湾资料被整理和翻译成中文,为研究荷据时期台湾对外贸易史提供了珍贵史料。李蕾利用荷兰文献,论述17世纪台湾地区对外贸易网络的形态及建构过程,并分析台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商业网络以及亚洲海域贸易关系中的地位及扮演的角色,认为在17世纪20年代荷兰人占据台湾后,即积极介入以往由华商和日商建构的贸易线路,并将之与东南亚、南亚的贸易航路相联系,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商业网络。台湾的“大员”商馆因其地理位置和当时特殊的贸易条件而在这一网络中扮演着极其关键的中转站角色,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不可或缺的贸易基地。[※注]林仁川利用荷兰的档案材料对17世纪台湾海峡贸易形势、荷兰人在台湾海峡的商战策略及其效果进行评述,认为荷兰人到达台湾海峡时,各国海商集团已经群雄鼎立,各自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荷兰人为了打破已有贸易格局,在东亚贸易网络上占有一席之地,采取和战结合、各个击破、海上拦阻等一系列的商战策略,但是无法实现称雄的愿望,最后在郑成功部队围攻的炮声中,结束了其东亚海上商业霸主的美梦。[※注]李德霞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活动为中心,阐述大陆—台湾—日本的三角贸易,认为17世纪上半叶,随着东亚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台湾地区成为中日贸易的一个理想中转站。中国人、日本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都不失时机地在此展开贸易竞争,最具竞争实力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终于排除了各国对手,独占台湾,经营着大规模的中日贸易,并赚取了高额利润,台湾因此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远东贸易网上的一个重要商站。[※注]
西班牙占据北部台湾时期的贸易活动同样被学界忽视。徐晓望的研究论文值得关注。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继荷兰人之后,侵占中国台湾北部的鸡笼和淡水作为殖民地。让西班牙人感到困惑的是,虽然这两个港口离福建主要贸易港口很近,但福建商人到本港贸易的数量极少,让西班牙人无法维持港口的经营。徐晓望根据何乔远《镜山全集》所载相关史料,分析明末福建商人不去鸡笼、淡水贸易的原因在于:台湾海峡的海盗活动、荷兰殖民者的干扰、福建官府对贸易的限制、闽南商人经商意愿在于台湾南部,以及日本锁国政策对西班牙商人的拒绝导致淡水中转港地位的下降等。[※注]
三 移民、族群与社会文化
荷兰占据台湾后,为了发展殖民地经济,以便掠夺更多的财富,实行鼓励大陆汉族人移民台湾的政策。林国平、邱季端主编《福建移民史》对于荷据时期福建人移居台湾的基本情况有比较简要的介绍。[※注]杨彦杰则撰专文,论述了荷据时期中国大陆向台湾的移民情况,认为其时移民主要来自闽南一带,尤以厦门、安海两地附近的农村和市镇为主,主要是农民和商人,人数逐年增加,1640年约5000人,到1661年达到3.5万人。汉族移民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中华文化,加强了两岸联系,同时严重威胁了荷兰人的殖民统治。[※注]
汉族移民改变了台湾的人口状况与社会结构。钟挥锷认为,大陆人口大规模移居台湾肇始于荷据时期。荷据以前,已有大陆移民到台湾,但较少长期定居者。荷据时期,大陆赴台者既有季节性流动的农民和渔民,也有不少人开始在台湾定居。1650年,台湾岛内中国人有10万人,其中少数民族8万多人,汉族移民约为1.5万人,到1661年,大陆移民总数当在3.4万左右。大规模的大陆移民赴台,改变了台湾的人口构成,引起了台湾人口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台湾人民生存方式和生计模式的改变。[※注]荷据时期台湾究竟有多少汉人,以往学界有3.4万、5万、10万等多种看法。陈孔立通过先由耕地面积估算谷物产量,再估算人口的办法,认为荷据时期台湾赤崁附近有汉人3.4万—4.4万人,全岛汉人达4.5万—5.7万人。[※注]当时台湾“原住民”人口究竟有多少?郝时远撰文,认为历史文献中对台湾“原住民”人口比较系统的记录始于荷兰殖民统治时期。但是,学界对这一时期“原住民”人口的规模及其消长却缺乏研究,以致某些人为制造“台湾民族”而肆意夸大“原住民”人口的历史基数。根据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的相关文献和“番社”户口调查资料,台湾“原住民”纳入统计的人口为5万—7万人。荷兰退出台湾时,全岛“原住民”人口为11.83万—15.8万人。由于疾疫的流行、荷兰殖民者的屠杀、部族之间的争斗及自然灾害等原因,“原住民”人口锐减。那种认为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原住民”人口基数为50万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注]
荷据时期,由于汉族移民的涌进,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员工和眷属等来自欧洲、印度及东南亚的外国人的加入,在台湾构成一个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的殖民地社会。刘彼德撰文,讨论荷据台湾殖民地社会的结构及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和特性,认为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首先,它是一个阶级不平等的社会。统治阶层包括荷兰东印度公司员工、“自由市民”和眷属,以荷兰人为主,欧洲人占绝大多数。被统治阶层有汉人、“原住民”和荷兰人的奴隶。其次,它是一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女性不能出外工作,没有谋生能力,一辈子只能做男性的家属。再次,它是一个宗教不平等的社会。独尊基督教,唯有基督徒才能进入荷兰人社会。基督徒享有政治和生活上的特权,汉族没有人接受基督信仰,不能得到等同荷兰人的地位,只能处于被压榨和被统治的阶层。最后,它是一个种族不平等的社会。台湾“原住民”即使成为基督徒,还是不能得到等同基督徒的地位,大多数“原住民”仍然属于被统治阶级,受到荷兰人的重重限制,只有极少数跟荷兰人通婚,或者在荷兰家庭中成长的“原住民”才被接受成为“自由市民”,进入荷兰人社会。[※注]
关于汉族移民与荷兰殖民者的关系,一般认为荷兰人鼓励汉族移民迁台是为了掠夺更多的殖民利益。但近年,有美国学者提出荷兰人与汉族移民在台湾共同构建殖民地(所谓“共构殖民”,co-colonization)的观点。[※注]王玉国撰文全面梳理荷据时期荷兰人与汉族移民的关系,认为荷兰人既吸引和鼓励汉族移民,甚至拉拢和利用汉族移民,但也防范和限制汉族移民,尤其是压迫和掠夺汉族移民。无论如何,其根本目的都是维护其殖民统治,以保证实现殖民利益的最大化。汉族移民与“原住民”一样,都是荷兰人殖民的对象,都是荷兰人压迫和掠夺的对象。所谓荷兰人与汉族移民“共构殖民”是根本不存在的。[※注]
荷据时期的汉人何斌是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功臣,但事迹不彰。陈碧笙撰文做了开拓性的研究,详细考证了何斌的生平事迹,以及何斌利用其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通事与“华人长老”的身份,三次到厦门接触郑成功,并劝说郑成功占取台湾,还向郑成功进献台湾地图,引导郑氏军队入台,最后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充分肯定何斌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中的积极作用。[※注]王昌、刘彼德利用《热兰遮城日志》等汉译荷文新资料,进一步探讨了何斌的家世及其在台湾的基本活动。王昌认为,在何斌向郑成功进献台湾地图的背后,是他在“大员”近30年的复杂活动。自17世纪30年代到达“大员”以后,何斌跟随父亲经营商船贸易,担任荷兰人通事,并承包荷兰人的贌税。何斌的商贸活动,是华人贸易网络的一个缩影。以何斌为代表的华人在“大员”的土地垦殖促进了“大员”地区的开发,并且带有经营性农业的性质。由此形成的华人社会运作模式,体现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的特征。何斌在荷兰统治台湾的政权中扮演的角色,是中国民间海洋社会群体与外来海洋强权接触、周旋、共存的重要环节。[※注]刘彼德认为,何斌的事业和在荷据台湾社会中的地位是继承自他的父亲何金定。何金定在17世纪40年代移居台湾时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为何斌在台湾的事业和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何斌的家世背景、事业及其与郑成功的关系推测,何金定与郑芝龙早年认识,甚至是贸易伙伴;何氏父子之所以受到荷兰人器重,主要原因之一是荷兰人知道何、郑两家关系密切,希望利用何氏父子作为中间人与郑氏父子打交道。由于何斌从台湾叛逃,投奔郑成功,并协助郑氏收复台湾,改变了台湾的历史,可以说何斌是荷据后期台湾最重要的一个汉人长老。[※注]
关于汉族移民与台湾“原住民”的关系,其实既有交流融合,也有矛盾冲突。针对有人所谓台湾“原住民”被汉族移民“赶上山去”或“被消灭掉”的偏见,陈碧笙具体考察了17世纪中叶台湾平埔族社会经济及其与汉族的关系,认为平埔族各部落居民与来自大陆的汉族移民,在相当长时间里交换、杂居、通婚、互相学习交流以及联合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过程中逐渐融合,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根本不存在所谓被汉人“赶上山去”或“被消灭掉”的事实。[※注]林仁川进一步考察大陆汉族移民向台湾的移动、分布及其与“原住民”的关系,认为荷据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绝大部分是漳泉的闽南人,移出地集中在厦门、金门、烈屿、海澄、安海等地,同时还有福州和广东沿海,甚至还有从马尼拉、巴达维亚移居台湾的汉族移民。这些移民流动性大,在台湾定居的比例并不高,但也有相当多的移民长期在台湾居住。移居台湾的汉族移民除一部分居住在热兰遮城附近以外,大部分散居在岛内各“原住民”生活区内,与当地居民朝夕相处,共同开发台湾,反对荷兰殖民统治。大部分汉族移民能与“原住民”和睦相处,但毋庸讳言,在争夺生产和生活资源时,他们之间也难免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荷兰殖民者甚至有意挑拨离间,但并不能阻止汉族移民与“原住民”共同携手开发台湾。[※注]
关于荷兰殖民者与台湾“原住民”的关系,主要是荷兰人以武力征服与安抚相结合的方式对“原住民”实行殖民统治。一般的论述可参阅郝时远、陈建樾主编《台湾民族问题:从“番”到“原住民”》和罗春寒著《台湾平埔族群文化变迁之研究》的相关部分。[※注]刘彼德具体考察了小琉球岛“原住民”被荷兰殖民者灭族事件的前因后果,认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进驻“大员”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以台湾为转口基地,拓展海外贸易获利;其次是利用台湾出产的农渔产品和鹿皮、鹿肉外销赚钱。由于小琉球居民对东印度公司而言不具经济和军事价值,又和台湾隔绝,容易围剿清除,因此荷兰人选择放过麻豆人,而将小琉球岛民全数铲除,以警告台湾其他“原住民”不得反抗荷兰殖民统治。17世纪的荷兰人是有名的经济动物,东印度公司一切决策都是以公司的利益为考虑,即使牧师提出的基督徒人道观点也不能跟公司利益抗衡。台湾“原住民”的福利因此被剥夺,生命遭到蹂躏,小琉球人的悲剧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注]
荷据时期荷兰人在台湾传播的主要是基督教文化,至于中华文化向岛内传播的情况,以往学界较少关注。杨彦杰撰文进行了专题研究,认为荷据时期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是伴随着汉族移民进行的,其时汉族移民主要来自闽南一带,传播的主要是闽南文化,移民以农民和商人为主,使“俗文化”传播占重要地位,诸如闽南话和闽南人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在台湾岛内非常流行。尽管荷兰殖民者对汉族移民采取既鼓励又限制的政策,但并不能阻止中华文化在台湾岛内传播,因为当时两岸人口流动性大,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力量有限,中华民族具有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和英勇顽强的民族性格,是任何外来殖民势力都难以摧毁和征服的。中华文化在台湾传播,加强了岛内民众的凝聚力,极大地威胁着荷兰人的统治,同时也加强了两岸人民的血肉联系,为郑成功收复台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注]吴慧颖则探讨了大陆戏剧文化在台湾的传播,认为台湾早期的民间戏曲是由大陆,主要是从福建和广东的潮、梅地区传入。就目前掌握的资料,台湾最早的戏曲活动应该出现于荷据时期。当时台湾的戏曲演出活动,与闽南原乡类似,也是在节庆神诞时表演,观音、妈祖的诞辰都是重要的演出时间,同样崇奉戏神田都元帅。荷据时期戏曲从大陆传播到台湾,与台湾汉人聚落的形成,以及移民的信仰习俗和民俗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荷据时期是台湾戏剧历史的开端。历经明清,闽南戏曲文化全面移植台湾,并且促进了汉人与当地“原住民”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戏曲文化也由此获得了发展与创新。另外,17世纪闽南地方戏曲在台湾的传播,也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展示了大航海时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注]
关于荷据时期基督教文化在台湾传播的一般情况,可参阅宇晓的论文《十七世纪荷兰、西班牙传教士在台湾高山族地区的活动及其影响》、林仁川的论文《十七世纪初基督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和林金水主编的著作《台湾基督教史》。宇晓与林仁川的论文概述了荷兰与西班牙传教士在台湾传播基督教的基本史实,注意到西班牙传播天主教、荷兰传播新教以及其分别在北部、中南部不同区域传教的情况,并对其为殖民侵略服务的性质及其最终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比较分析。林金水主编的著作则主要论述了荷兰殖民者传播新教的基本事实,具体论述了荷据时期新教在台湾从开创、发展到衰败的过程,教会学校的教化事业,新教传播失败的原因及其社会影响。[※注]
与荷据时期其他领域的研究情况相似,学界较多关注荷兰人的传教活动,而对西班牙有所忽视。关于荷兰传教士在台湾创办教会学校、教学与教化的基本情况,学界多有论及。一般既强调其本质上是殖民地奴化教育,但也不否认其在客观上开创了台湾学校教育的先河,对台湾社会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注]熊南京等人探讨了荷兰殖民者在台湾推行的语言政策及其影响,认为出于殖民利益和同化教育的需要,荷兰传教士积极传教并开创了台湾的学校教育,为台湾“原住民”的多种民族语言创制了拉丁文,并且教给“原住民”用文字来记录自己语言以及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存民族文化及开启民智的作用。但是,荷兰殖民者推行语言政策的结果非常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语言生态:他们为了复仇,血腥屠杀小琉球的“原住民”,使这种方言彻底消失;他们不考虑实际语言的差异,用新港语对凤山八社的马卡道人进行教学,导致该语言的异化;另外,他们在“原住民”中推广荷兰语以达到同化的目的,也对“原住民”的语言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注]
综上所述,关于荷据时期台湾史研究,总体上较为薄弱。相对而言,大陆学界对荷兰殖民者侵略与中国人反侵略的历史论述较多,而荷据台湾殖民地本身研究较少,尤其是有关此时期内西班牙侵占台湾北部的历史明显关注不够。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荷兰、西班牙殖民台湾时期的荷兰文、西班牙文原始档案没有充分挖掘和利用。这方面,台湾学者与日本、荷兰、比利时等海外学者走在前面,岩生成一、中村孝志、曹永和、江树生、包乐史(Leonard Blusse)、胡月涵(Huber Johnnes)、鲍晓鸥(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韩家宝(Pol Heyns)、程绍刚、林伟盛、郑维中等学者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整理翻译了《巴达维亚城日记》《热兰遮城日志》《荷兰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荷兰人在福尔摩沙》《邂逅福尔摩沙——台湾原住民社会纪实:荷兰档案摘要》《荷兰时代台湾告令集:婚姻与洗礼登录簿》和《西班牙人在台湾史料汇编》(Spaniards in Taiwan)等与台湾相关的重要档案资料。近年来,大陆学者也在尽可能地利用这些珍贵资料进行相关研究。可以预见,充分挖掘和利用荷兰东印度公司留下的档案资料,将大大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荷据时代台湾史。西班牙侵台时期原始档案的保存、整理和利用远不如荷兰方面,因而西班牙侵略台湾史研究非常薄弱不足为怪。这方面的任何进展都值得学界殷切期待。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