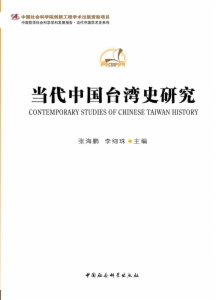一 郑芝龙与郑氏家族
|
来 源
:
|
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7 | ||
|
摘 要
:
|
该书以郑芝龙、郑成功、郑经、郑克塽四世的史迹为基本线索,系统叙述了明郑政权的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过程,认为明郑政权名义上是南明政权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一个以海商为主体并与部分汉族地主共同组合的反清地方割据势力。清朝入关之初,是落后文化对先进文化的武力征服,郑成功抗清对历史发展有积极作用,不妨碍其作为民族英雄。而郑经、郑克塽时代,清朝统治者已逐渐被先进的汉文化所同化,统治已相对稳固,生产也逐渐恢复和发展,郑经、郑克塽抗清,只能阻碍统一的进程,没有积极意义可言。至于郑芝龙抗荷、郑成功驱荷复台、郑经开发台湾与郑克塽归清,均应予以充分肯定。 | ||||||
|
关键词
:
|
郑成功 郑克塽 政权 贸易 荷兰人 天地会 集团 学界 华侨 家族 崁 |
||||||
在线阅读
一 郑芝龙与郑氏家族
字体:大中小

郑芝龙早年到澳门投靠母舅黄程,在澳门学会葡语,从事“通事”职业,替葡萄牙人做“掮客”,并皈依天主教。后来,郑芝龙有一个女儿在“日本教难”时逃到澳门。郑芝龙为从澳门接回女儿,甚至扬言要武力攻打澳门,因此与澳门结怨。郑芝龙的女婿从澳门到安海时,带来大量的黑人充军,这些职业铳手为郑氏海商集团的兴盛助益良多。金国平、吴志良撰文对此做了详细考证。[※注]吴凤斌则考证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侨居日本的史实,认为郑芝龙是因有了一段侨居日本的经历,并依靠日本华侨的力量,才得以起家的。[※注]
关于颜思齐、郑芝龙入台的时间,清代史籍记载不一,近人著述也经常互异,主要有明朝天启四年(1624)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之前入台、天启四年与荷兰人同时入台、天启五年在荷兰人侵占台湾之后入台三种说法。有荷兰学者取颜郑于1624年与荷兰人同时入台之说,从而把开发台湾的功劳算在荷兰殖民者身上。黄志中考证认为,颜思齐、郑芝龙率众入台各有先后,颜思齐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已入台,郑芝龙则是在天启元年(1621)才入台,时间虽有先后,但都分别比荷兰人先到三年至六年。这就是郑成功要求荷兰人还“我先人故物”的根据,也是施琅对康熙皇帝说“六十余年间,无时不仰廑宸衷”的内涵。[※注]中国学界对于郑芝龙开发台湾的贡献,都给予肯定评价,但有些外国学者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台湾是荷兰人首先开发的。关于郑芝龙与颜思齐、李旦的关系,以及有没有颜思齐其人,颜思齐与李旦是否一个人等问题,也长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徐健竹考证认为,颜思齐、李旦各有其人,李旦是在台湾海面最大的海商集团的首领,同时也是在日本平户的华侨首领,郑芝龙是依靠李旦这位同乡富商发达起来的,而不是颜思齐。正是以李旦、郑芝龙为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在荷兰人尚未进入台湾本岛以前,就有组织地招来大陆汉族人民到台湾从事开荒活动,所以说荷兰人是最早开发台湾者的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注]
郑芝龙是明末中国东南沿海著名的海商集团首领。方裕谨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代兵部档案内,编选有关郑芝龙海上活动的文件公布,这对于研究明末东南沿海情势、郑成功家世及郑氏海商集团等课题,有重要参考价值。[※注]郑以灵具体探讨了郑芝龙海上商业集团兴起与发展的原因及其对历史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认为郑芝龙海上武装集团,也和其他“海寇”一样,骚扰沿海,与官军对抗,但郑芝龙的目的不仅仅是劫掠和走私,他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即用武力胁迫官府招抚,进而以合法地位控制海疆,冲破海禁的羁绊,开放自由贸易。为此,郑芝龙还同进犯沿海的荷兰殖民者进行坚决斗争。郑芝龙在海上经营20年,为郑成功留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郑芝龙武装集团代表了海上贸易商阶层,这点为郑成功所继承。为保护海商利益,排除荷兰殖民者对海外贸易的阻碍,是郑成功最终决策进取台湾的一个重要因素。[※注]夏蓓蓓论述了作为17世纪“闽海巨商”的郑芝龙的生平事迹。[※注]徐翠红研究郑芝龙与荷兰人的三次贸易协定,认为以郑芝龙为首、以郑氏家族为核心的海商集团,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强大贸易集团,掌握了中国东南海岸的制海权,使荷兰人占领台湾之后向中国东南沿海扩张的势头受到了遏制。郑芝龙集团的存在也影响了欧洲列强之间的互动和消长,荷兰人利用其抵制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和澳门的葡萄牙人,但郑芝龙最后也控制了荷兰人的对华和对日贸易。郑芝龙投降清朝后,郑氏集团虽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实力仍旧保存下来,为郑成功后来继续以商养战留下了较好的根基。[※注]王恩重则考察了郑氏海商集团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地位,17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率先展开了由传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向以海洋经济为导向的商品经济过渡的结构性转型。郑氏海商集团依傍这一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得以发展为私人海上贸易的龙头。其发展虽与西方新兴资本主义海上贸易势力的发展特点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从其发展轨迹来看,走的是一条完全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由于历史条件和机遇等原因,郑氏海商集团无力改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走向,但为台湾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及抵御外敌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注]
郑芝龙生逢明清易代之际的乱世,先以海盗而投明,又以明之国公而降清,因此为后世所诟病。孙福喜、丁海燕探讨其原因,认为郑芝龙之所以要投明降清,既是他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大潮冲击的结果,更是他曾先为商、后为盗、再为官的个人经历,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既无封建正统忠君思想、又无因清朝统治而产生的民族压迫感,只有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利益高于一切的人生价值观的必然产物。[※注]郑芝龙受抚于明后,担任福建总兵之职,并借助明廷的名号和力量,垄断了东南沿海的贸易。明亡后,明的残余势力先后在南京和福州建立福王、唐王政权。郑芝龙遂翊赞唐王(隆武帝),统管当时全闽兵马,以至权倾朝野。但他拥立唐王的目的并非抗清复明,而是保住自己海上贸易的特权,故当清军大兵压境时,他不作任何抵抗就投降清廷。杨友庭撰文认为,历来史家都把唐王政权的灭亡归咎于郑芝龙,其实不够客观。他具体分析了唐王政权灭亡的内在原因,认为郑芝龙确实气节有亏,但若把唐王政权的灭亡完全归咎于郑芝龙,也并不公平。[※注]徐晓望详细研究了隆武帝与郑芝龙关系的变化,认为隆武帝政权内部海商与士大夫阶层的冲突相当激烈,隆武帝一开始倚重于郑芝龙,而后逐渐向士大夫倾斜,最后与郑芝龙决裂,表明士大夫难以接受海商与其分享政权的事实,双方的破裂最终无法避免。传统的史书多将隆武帝当作郑芝龙的傀儡,实际上,隆武帝是一个颇有谋略的帝王。隆武帝登基后,来自各省的财源与政治支持使他的地位日益巩固。于是他便利用文臣与郑芝龙的矛盾,展开了与郑氏家族的权力斗争。隆武帝北征闽北之后,郑芝龙留在福州,而其他郑氏将领被派到前线作战,借此机会,隆武帝逐渐压倒郑芝龙成为隆武朝真正的掌权者。隆武政权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内部的权力之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注]隆武二年(1646),博洛率清军势如破竹地进入福建,擒杀隆武帝等人,隆武政权就此灭亡。清军入闽如此顺利,民间文献认为是郑芝龙降清使清军入闽几乎不战而胜,但《清史稿》等书则认为博洛等清军将领苦战而得闽中。徐晓望考证了清军入闽之后的仙霞岭之战、分水关之战及清军攻克建宁府、延平府、汀州府、福州府的过程,证明《清史稿》等书所载博洛等人苦战而得闽中的记载为谎言。对郑芝龙降清一事,作者也根据新史料对其动机与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订,认为明末清初的中国海洋势力有拥清派与拥明派两大派系,郑芝龙降清,其实是想与没有海上利益的清朝协调,力争得其支持,从而可以全力对抗荷兰人,在东亚海上争霸,确保海商的长远利益,但郑芝龙降清失利,表明获得统治权的清廷尚不理解东南的海洋势力,这一问题最终在康熙朝获得解决。[※注]
郑氏家族史一直是中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有关郑氏家族的中文资料已得到比较系统的整理与研究。相比之下,除了部分荷兰文档案外,数量庞大的相关西文资料却一直未获有效开发与利用。张先清研究17世纪三位天主教传教士利胜、闵明我与帕拉福克斯所撰写的西班牙文书稿,挖掘出丰富的郑成功家族史料。这些传教士基本上是同时代郑氏家族兴衰的见证人,利胜甚至还与郑成功及其家族重要成员有过直接的接触,对郑氏家族的内外活动有着细致的观察与描绘。解读这些欧洲天主教文献的相关记载,并将其与现存中文文献相互贯通,有助于深化郑氏家族史研究。[※注]林梅村考证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雪尔登中国地图》入藏始末、年代,论证了《雪尔登中国地图》实乃《郑芝龙航海图》,以及《郑芝龙航海图》的西方图源与图名。据初步调查,这幅明代航海图绘制于崇祯六年(1633)至崇祯十七年(1644)。图中东西洋航线以泉州为始发港,绝大部分航线在郑芝龙海上帝国控制范围之内。同时发现,郑芝龙旧部施琅之子施世骠所绘《东洋南洋海道图》与此图一脉相承,皆源于西方投影地图,《郑芝龙航海图》借鉴了料罗湾大捷缴获的西方海图。明万历以后所谓“西洋”指东南亚海域,清初更名“南洋”,《雪尔登中国地图》的原名或为《大明东洋西洋海道图》,康熙六十年(1721)由施世骠献给了康熙皇帝。[※注]
关于对郑芝龙的评价,学界颇有争议。有人认为他“喜为两端”。陈碧笙纵论郑芝龙一生事迹,认为他是海商资本的代表,不论是对明清王朝,还是对荷兰殖民者,都尽可能加以利用和控制,为海商资本的利益服务。通过与郑成功比较,他认为郑芝龙是海商资本初起阶段的代表人物,船众有限,力量薄弱,或则同时依靠明王朝和荷兰殖民者两方面共同的支持,或则单独投靠一方以抵抗另一方,其对外斗争是有节制而不彻底的。郑成功则是海商资本成熟阶段的代表性人物,拥众数十万,有船数千号,雄视海上,纵横莫敌,无论是对清王朝,还是对荷兰殖民者,态度都要强硬得多。同样从海商资本的利益出发,一则以妥协为主,一则以斗争为主。归根结底,这是由自身所拥有的力量来决定,不存在什么“两端”的问题。[※注]邓孔昭则认为,郑芝龙因投明又降清,在政治上反复无常,而为人所不齿,但他对开发台湾和抗击荷兰殖民者在福建沿海的骚扰做出过贡献,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注]邓孔昭还探讨了郑成功对郑芝龙的批判与继承问题,认为批判主要表现在对待隆武和降清的问题上,这是由于他接受的教育和信仰与郑芝龙不同;继承则表现在海上商业活动和“牌饷”的征收,以及与荷兰殖民者的斗争和对台湾的经营方面,这是由于维护家族的利益和抗清的需要所决定的。郑芝龙降清,并没有能够维护郑氏家族已经取得的利益,反而断送了自己的海上事业;郑成功在政治上同父亲决裂,并不能说他脱离了自己的家庭,不顾自家的利益,相反,郑成功没有随同父亲降清,才使他有可能继承和发展父亲的海上事业,从而更加有效地维护郑氏家族的利益。[※注]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