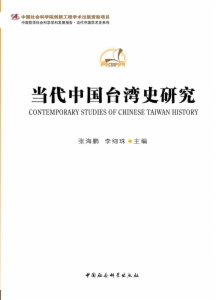二 经济开发
|
来 源
:
|
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9 | ||
|
摘 要
:
|
康熙统一台湾后,把台湾纳入清朝版图,便开始治理与开发台湾。本节论述学界有关清前期治台政策与制度建设、台湾的经济开发、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等问题的研究成果。针对台湾学者林文龙所谓“清代台湾巡道‘兼督船政’一事,前所未闻,似为‘兼督学政’之误”的说法,李祖基撰文考证认为,清代分巡台湾道“兼督船政”一事最早由尹士俍的《台湾志略》所记载,所谓“船政”,主要是指台澎水师战船的修造。刘正刚、刘文霞注意到移民开发台湾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大陆各省文武官员,利用清代台湾方志记载,具体考察河南籍官员在台活动,认为他们贯彻清朝中央政府的政策,对台湾实行有效管理,对。 | ||||||
|
关键词
:
|
政策 台湾 大陆 移民社会 清廷 学界 台湾少数民族 制度 贸易 台湾人口 天地会 |
||||||
在线阅读
二 经济开发
字体:大中小
清代是台湾历史上重要的经济发展与开发时期,大陆学界对此多有关注,但迄今没有专著对清代台湾经济史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黄福才著《台湾商业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林仁川与黄福才合著《台湾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陈支平著《民间文书与台湾社会经济史》(岳麓书社2004年版),只涉及清代台湾商业贸易、农业经济及闽台经贸关系等经济史研究的不同侧面。
关于清代台湾经济开发的宏观研究,一般被纳入清政府治台政策框架之内考察。郑泽清探讨清代治台方略对台湾经济开发的影响,认为清前期采取“为防台而治台”的消极方略,影响了台湾经济的开发;清后期“防外患而治台”之方略,促进了台湾经济全面开发并向近代化起步。[※注]邓孔昭论述清代前期政府官员关于台湾开发的一些不同主张,认为尽管有姚启圣、蓝鼎元等一些有远见的官员主张积极治理台湾,但清政府中“为防台而治台”的思想总是占了上风。清朝统治者企图通过限制台湾人口的增长与土地的开发来到达消除“乱萌”的目的,但“民变”并未见少,致使台湾的开发受到一定影响,直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后,出于抵御外侮的需要,才对台湾开发采取积极的态度。[※注]
关于清前期台湾经济的性质,一般认为主要是封建经济,但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如黄福才、吴锦生认为,清代初年的台湾虽然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至康熙末年特别是雍正年间,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已逐渐萌现。[※注]黄福才还专门论述了清初台湾封建经济的特征和清代台湾商品市场的演变,认为清初台湾的社会经济结构,主要是地主所有制与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的结合。当时地主阶级在台湾仍是一种新兴的阶级势力,大规模的开发均由他们组织,其土地的激增并非通过兼并,其势力主要伴随着土地的开发而发展,他们不同于大陆上已经腐朽没落的地主贵族,对台湾的开发和封建经济的发展主要起到促进作用。台湾并没形成一种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典型的自给自足经济,而是一种以粮、糖生产为主,手工业等日常用品依赖大陆的半开放型的经济。对比大陆封建社会初期及当时某些地区那种完全自给自足、闭塞排外的经济,清初台湾的经济形式是较为进步的。它加强了台湾与大陆的交往和联系,繁荣了海峡两岸的经济,同时促进了台湾农作物商品生产的发展。这些正是台湾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发展较快,以至近代经济也较迅速发展的历史原因。清代是台湾商品市场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台湾的开发垦殖程度、人口数量、市场结构、商品经营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台湾商品市场逐渐发展,并完成了向近代意义的市场体系演变的进程。[※注]
中国以农立国,农业是基础,清代台湾也不例外。颜章炮考察康熙朝对台湾的农业政策和措施,认为这些政策和措施有利有弊,对农业经济的作用有促进,亦有阻碍。一方面鼓励垦荒,大力兴修水利;另一方面却封禁山区,禁垦“番地”,限制农业劳动力入台,甚至重科田赋。各项政策措施之间,存在着矛盾、脱节的现象,导致积极的政策措施的作用受限制,甚至被抵销,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注]杨国桢通过考察台湾在明末清初的农业开垦史,认为雍正年间,台湾耕地面积成倍地增加,粮食自给而有余,这就标志着台湾作为一个新兴的农业区域已经基本形成。乾隆以后,台湾取得东南“粮仓”和“糖库”的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中血肉相连、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土地垦殖的历史来看,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三角洲等从开发到形成农业区域,都经历数百年的经营。台湾在归清之后短短数十年间就基本形成农业区域,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个局部地区出现的飞跃现象。[※注]水稻、甘蔗是台湾的主要农作物。马波、林仁川分别撰文论述了台湾明清时期稻米产区的分布与稻米生产[※注]。陈学文则考察了明清台湾蔗糖业的发展。[※注]阮思华从“大农业”的角度,从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人口状况、土地的开发与利用、水利事业的发展、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生产与分布、渔牧副业的发展等方面入手,对清代台湾农业经济进行了系统论述。[※注]
清代台湾是通过大规模垦荒而崛起的新兴农业区域,又是明清时期地权分化最为普及、最为典型的地区。康熙、雍正时期,在垦荒中移植大陆永佃关系的结果,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量荒埔被辟为良田,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一部分佃户“私相授受”转佃土地,实际上占有了田面权(俗称“田底”),使垦户土地所有制向“一田两主”转化。乾隆时期,不仅垦熟地上的“一田两主”关系确立,而且在新垦地上,垦户一开始便以收取“垦底银”等方式,给予佃户田面权。同时,随着垦拓向土牛线外的内山推进,垦户“向番买垦”,导致田主层分化的“一田两主”关系也发展起来。这就引起地租的再分配,业主租(大租)和佃主租(小租)并存,开始成为台湾地租分配的基本形式。杨国桢撰文具体考察了清代台湾的“汉大租”“番大租”和“官大租”等不同类型的基本状况,认为清代台湾大租的千姿百态,反映了台湾地权分化普遍逆转为一田两租,体现了封建经济结构抵制地权分化的坚韧性。在农业生产中上升为实际业主地位的那部分“佃户”,以转租形式成为地主阶级中的小租户层,而原业主大多因脱离生产而腐化为寄生的大租户层。这种逆转,从一个侧面说明台湾的地主经济从乾隆以后迅速走向腐朽,台湾农业经济从此转入迟缓发展的状态。[※注]邓孔昭论述了大小租在台湾出现的时间和社会条件,认为在清初大规模的移民垦荒过程中,以一种较低的租率并给“佃者”以某种物权,是当时新形成的租佃关系的需要;台湾“一田二主”的现象最初是在垦荒过程中形成的,但它又是大陆某种经济关系的移植,大陆移民,尤其是漳州府籍的移民,为“一田二主”的租佃关系提供了“大租”的形式;雍正七年(1729)以后,清政府调整了台湾新垦土地的赋率,为大租的普遍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乾嘉以后,台湾人口日益增多,土地供求关系有了新的变化,一部分新来的移民已逐渐感到无适宜的荒地可垦,他们只好以较高租率从别人手中租种已经垦熟的土地,加上原佃户中一部分人实力增长,除自耕外,已有剩余“田面”可以出租,于是“小租”随之出现。[※注]陈碧笙认为清代台湾的大小租制度起源于大陆,在形成过程上,台湾大租或由垦户出钱出力经营,或领有官府发给垦照,或两者兼而有之,比大陆通行者更为完备而集中,在业权分割上,两者的精神实质完全一致,而台湾学界所谓“庄园论”者强调的中世纪农奴制从来没有存在过。[※注]
有关清代台湾开发与农村经济史的研究,周翔鹤对清代台湾土地契约文书的系列研究值得注意。关于清代台湾开发过程中的佃户与业户的经济状况及其作用与地位,周翔鹤认为,佃户进入生产时都具有一定经济能力,为了租垦业主的荒地,须付出犁分银(或称埔银等)、水利设施投资,以及牛、犁等工本。清代台湾的佃户人身是自由的,他们和业主在身份上平等,但受到以业主为代表的乡族势力一定程度的控制。佃户初期是小农,而小农的地位可以上升,可以改变,但并非所有小农都有相同的发展道路。在佃户上升为小租主后,向小租主租种土地的小农发展的可能性就大不相同了。在开发过程中,土地开垦工作由佃户单独进行,业户的工作是获取、出租土地和开凿陂圳。垦首制向来被认为是清代早期台湾(特别是中、北部平原和盆地)开垦的主要形式,周翔鹤提出商榷,认为不能简单地将业户(或垦户、大租户)等同于垦首。所谓垦首制,存在于清代后期,主要是埔里社盆地和“开山抚番”的山地开垦形式,而非早期台中盆地、台北盆地及最南部的开发形式,早期中、北部平地开发高潮中的拓垦形态,大部分表现为业户出资兴修水利(尤其是大型水利)、佃户出资开垦荒地的业佃合作形态。清代早期台湾乡村社会往往被重建成以“垦首制”开发模式为中心的移垦社会,周翔鹤认为这是错误的。早期业户经济存在于其兴修的水利之中,水利成功,其投资方能收回以积累发展,业户的投资以佃户租谷形式收回,水利的兴修使得佃户的土地开垦有了成功的保证,同时也保证了向业户交纳佃租。因此,早期的业户和佃户是互相依赖的,他们分工兴修水利和开垦土地,使得大片荒地得到开垦,乡村经济也繁荣起来。周翔鹤还认为,清代台湾各种拓垦形态中的称呼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垦户、业户、业主这几个称呼是适用于全台湾各个地区的,佃首、佃户首适合于屯地,而垦户首、垦首则适合于山地。在台湾土地开垦中,由于地理、人文等条件的差异,也必然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模式,以往被学界忽视的个体开垦,实际上也是台湾开发史上的一种模式。周翔鹤还用产权经济学理论解释清代台湾一田二主制模式,并利用典契分析清代台湾的地权交易,得出新的认识。[※注]
田赋是清代台湾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清政府统一台湾后,议定了台湾地方的田园赋则,将其作为征粮纳赋的标准。然而,由于历史与地理因素的影响,这一赋则与大陆有许多不同之处。至雍正九年(1731),清廷又允准台属自雍正七年(1729)起的新垦田园改照同安则例征赋,但有关论著对这次赋则调整的记载却颇多歧异。李祖基撰文对清代前期(乾隆以前)台湾田园赋则的若干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并对清廷在田赋问题上所显示出的治台政策进行探讨。[※注]陈支平认为,清代前期,台湾各地特别是台北淡水河流域的土地赋税关系大多处于无政府状态,民间土地开垦与政府赋税征收的相互脱节现象相当普遍。清代中期以来,政府虽然采取许多措施,试图加强对于民间土地开发与赋税征收的控制,但是始终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注]李祖基还专文探讨清代台湾的官庄,特别指出台湾学者认为官庄是以农奴生产为基础,并把官庄视同中世纪欧洲庄园的观点缺乏根据,官庄佃户既要交租又需纳赋的“双重负担”并不存在。[※注]
合股经营是清代台湾一种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郑振满考察了清代台湾合股经营的行业与地区分布、合股资本的经营管理与权益分配,认为清代台湾的合股经营形式多样、规模不一,遍及各种经济领域和各个社会阶层,深刻地影响着清代台湾的社会经济结构。清代台湾草莽初辟,必须有效地组织各方面的人力和财力,才能顺利地进行规模空前而又富有冒险性的开发事业。这是清代台湾盛行合股经营的内在原因,也是合股经营在台湾历史上的主要作用。[※注]曹树基把清代台湾拓垦过程中的股份制经营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结合起来考察,认为由于台湾特殊的生态环境,清代台湾大多数垦号一开始便实行了股份制经营方式,具备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些基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台湾垦号确实已具有了资本主义性质。然而,闽粤移民固有的合约制宗族在本土环境中并不能演变出这种具有现代资本意义上的土地垦殖方式,在台湾地区的拓垦期结束以后,资本主义性质的垦号也向封建租佃制转化。据此可以认为,在中国特定的人口增长背景和中国产权继承制度下,学者们定义的“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完全没有发展的前景。因此,“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这个命题本身也不能成立。[※注]周翔鹤撰文对曹树基提出的清代台湾土地拓垦中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拓垦中的股份制经营是资本主义性质企业的结论提出商榷,认为从实证角度来说,清代台湾土地拓垦中存在的还是封建的土地租佃关系;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只有在严格界定的概念创新或缜密的理论综合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新的理论命题,而曹文没有做到这一点。[※注]曹树基撰文反驳,并进一步归纳自己的观点:清代中前期的台湾拓垦过程中出现的以股份制经营为特征的垦号组织,是具有现代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特征的“类资本主义”的农垦企业,这一形式的企业是台湾拓垦时期特定的生态背景的产物。同一时期的大陆因缺乏这一背景,发展不出这种经营形式。当台湾的生态条件发生变化时,这种“类资本主义”的农垦企业转变成为封建的租佃经营,所以台湾此种“类资本主义”的农垦企业并不是对封建生产方式的替代或发展,“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完全没有发展的前景,其命题本身也不能成立。[※注]
两岸经贸关系是清代台湾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林仁川、陈杰中把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咸丰十年(1860)间台湾与大陆的通商贸易分为三个阶段: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至雍正三年(1725)台南三郊的成立,是台湾同大陆贸易逐步发展的阶段;从雍正三年(1725)至嘉庆初年“蔡牵事件”以前是台湾同大陆通商贸易的繁荣鼎盛时期;从嘉庆初年至咸丰年间台湾与大陆的通商贸易处于衰疲之中。台湾与大陆的通商贸易,有两种经营形式,一种是官府监督控制的“合法贸易”,另一种是违禁的走私贸易。合法贸易的经营,是在“郊行”的主持之下进行的。走私贸易有三种类型:行商、商船贿买官吏,规避“台运”类;渔民、私商的走私贸易类;清军官弁“夹带贩私”类。清代台湾与大陆的通商贸易物资,可分两大部类:台湾对大陆输出的大宗商品物资是粮食与蔗糖,另外就是“内山番地”出产的皮革、骨角、羽毛和鹿茸、麋茸、鹿角胶、鹿肚草等贵重山货药材;由大陆输入台湾的商品物资,从布帛百货、果品药材至砖瓦木石,无所不有,包罗万象。清代台湾与大陆的通商贸易,是在清政府的监督控制下,由台湾和大陆的民间海商组织和经营的,大陆福建的漳泉地区海上贸易商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贸易商人所拥有的商船中,已开始出现了近代航运企业的雇佣劳动关系,只要随着贸易的正常发展,不需要任何外部力量的干预,就有可能产生出一部分近代的航运企业主和商业资本家。[※注]黄福才认为清代(1644—1912)是两岸贸易史上最重要的时期,陆台贸易经历了不稳定发展—持续发展—兴盛—衰落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具有闽南地方特征的商业贸易习俗,其间尽管各阶段所处的历史条件、发展情况不同,但相互间还是有联系并具有共同点。从贸易对象和地区而言,大陆始终是台湾最主要的贸易地区;从贸易商品结构看,尽管各个阶段洋货不同程度地进入两岸的贸易领域,但华货始终是其最主要的货物;从贸易的组织形式看,在较长时期内,两岸贸易处于自发状态,而日据初期殖民当局的介入,严重地破坏了两岸传统的贸易关系;从贸易活动形式来看,两岸贸易受政治等因素的制约,先后出现走私、半公开贸易、公开贸易等形式,说明两岸贸易关系的坚韧性,以及两岸经贸联系和发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活动规律。[※注]黄国盛论述了清代前期闽台对渡贸易政策的形成,闽台对渡贸易的发展状况,认为清朝统一台湾后即开始弛海禁,允许福建厦门与台湾鹿耳门进行单口对渡贸易,后在闽台人民私航活动的推动下,逐步改为指定多口对渡贸易。清代闽台对渡贸易政策的实施和不断调整,有力地将海峡两岸社会经济推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而闽台通航贸易,亦是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注]
清代台湾作为新形成的农业区域,对大陆沿海特别是福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台湾输出的大宗农产物是砂糖和米谷,砂糖远销大陆北方及欧美、日本等地市场,而米谷则主要在国内埠际间进行贩运,其最主要的输出地是福建。台湾大米对福建的输入,大致可分为“官运”和“民运”两大系统:就官运言,又可分为兵眷米谷的调运与平粜米谷的买运;就民运论,又有商船贩运、租谷内运以及非法走私等。杨彦杰对台运兵眷米谷的起源、基本情况、发展变化及其衰败原因进行了系统考察。[※注]清代福建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粮荒”问题,在其前期粮食市场不甚发达的情况下,主要依赖江浙漕粮及所属台湾府米谷的调拨协济而得以解决。孙清玲专论清朝前期台米协济漳泉地区的特殊政策,认为漳泉地区因与台湾在地缘、族缘等方面的关系,在台米进口上享有特殊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专拨”“专买”制度上,清政府要求台湾官员突破地方主义,以全省大局为重,为台米协济漳泉地区提供方便。[※注]刘正刚专论清代移民与台湾食盐贸易制度化,认为台湾市场的发育与成长,与大陆闽粤汉人移民在台湾的社会经济活动分不开。清廷统一台湾后,随着移民的涌入,政府的控制不断加强,并以政权的力量在台湾制造食盐商品的特定市场,使食盐贸易由原先的物物交换转化为专卖形式。政府力图通过食盐专卖收取饷银,解决军饷及财政支出。台湾食盐贸易的制度化,其实是台湾内地化进程的重要表现。政府通过这一过程将台湾纳入有效的管理体系中。[※注]
关于清代台湾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研究,也是学界关注的重要内容。郭志超考察清代汉族大规模移垦影响台湾少数民族农业技术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与途径,认为汉族先进的农耕文化流向台湾少数民族原始耕猎文化的途径是多方面的:生产技术的学习和引进;以通婚为渠道接纳汉族劳动力;台湾少数民族内部人口流动促进生产技术的扩散;生态环境的变迁促进生产系统的变化。随着汉族移民农业区域的拓展,台湾地区原来适应于原始农业,特别是狩猎业的原始生态环境也在迅速改观。这导致传统的原始农耕与狩猎在生产部门中的比重发生重大调整,对生产技术的提高乃至原始农业的变革起着明显的催化作用。[※注]刘如仲、苗学孟认为狩猎和捕鱼仍是清代台湾少数民族的重要生产活动:“生番”多以狩猎和捕鱼为主,兼之粗放农耕;“熟番”主要从事农耕,辅之以渔猎。狩猎和捕鱼丰富了台湾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并促使其社会向前发展。[※注]
台湾少数民族平埔人土地私有制代替公有制,虽然在清初已经发生,但其发展过程十分缓慢。随着台湾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大约经过一个多世纪,私有制最后代替公有制而成为主导的土地所有形式。林庆元把这个过程大体分为三个时期:(1)从1683年到1750年,是私有土地发生时期;(2)从1751年到1850年,是土地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的重要时期;(3)从1851年到1900年前后,是平埔人私有制确立的时期。[※注]清代台湾平埔族在和汉人移民的接触中,引进了汉人移民的地权观念、租佃习俗和农耕模式,使平埔族群内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既往研究多认为,土著部落接受汉人移民的私有地权规范,并被卷入商品货币经济和土地市场后,因地权的疏离而导致普遍的贫穷化。周翔鹤以竹堑社为例,利用土地文书,研究这一变化的进程和由此产生的平埔族社群内部的贫富分化现象,发现大部分“社番”都因“番产外流”而贫困,但平埔族内部也存在差别,许多人尤其是通事、土目,通过引入汉人移民的开垦模式当垦户而成为强者,只是后来他们汉化太深,在历史上失去了踪影。[※注]关于清代台湾“番”地开发,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完全是依靠民间的力量,政府和官员的态度是消极的,不仅未给予支持协助,反而多方留难限制。李祖基认为这种情形并非一成不变,从分巡台湾道张嗣昌所撰《巡台录》对大甲西社“番”变事件善后的处理和官方劝垦“番”地的记载,以及减轻台湾田园赋税和开放移民搬眷入台的种种措施,可以看出雍正年间政府对台湾的土地开垦政策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与雍正皇帝重视农本,奖励垦荒政策有很大关系。[※注]李凌霞考察清代台湾“原住民”不同社群的地权争夺,认为清代台湾在汉人移垦的推动下,汉“番”土地矛盾日渐突出,清政府基于治安考虑,划界隔离汉“番”,并于乾隆年间派“熟番”于“番”界险要处设隘把守。随着土地资源竞争日趋白热化,“熟番”不同社群以守界名义争夺界外荒埔的地权,这个过程推动了清政府汉“番”隔离政策的变化,促进了国家行政力量在“原住民”社会的深化,体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台湾实现的由经济而政治的历史逻辑。[※注]
在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汉族人民大量移居台湾等因素的促动下,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贸易活动也兴盛起来。这种贸易活动的进行,对台湾少数民族自身经济文化的进步及与移居岛内的汉族关系的发展,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谢冰认为,清代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族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关系,其贸易活动普遍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台湾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程度,在尚未达到其社会内部分化出商业及商人,也没有形成本民族商品交易市场的情况下,贸易能够发展到一定规模与水平,与这一时期大陆汉民的大批迁台有直接的关系。[※注]郭志超认为,他们分为“熟番”“归化生番”“化外生番”,清代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贸易也就形成各种相应的类型。这些不同形式的汉“番”贸易,共同揭示了台湾少数民族由商缘而法缘的国家认同过程。清代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贸易发展,加强了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成为共存于同一个政治体制的坚实基础,以及参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经济奠基。[※注]
关于清代台湾区域开发研究,宜兰(噶玛兰)颇受学界重视。张文绮注意到开发宜兰的主要是漳州移民,因而在宜兰地区崇祀开漳圣王的民间信仰非常盛行。[※注]周翔鹤利用清代台湾宜兰地区水利古文书资料,探讨垦拓初期宜兰社会状况,指出宜兰在嘉庆、道光年间得到开发,是台湾开发较迟的地区。关于宜兰开发及早期社会变迁状况,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开发初期移民采取结首制的模式;二是在租佃关系方面没有像台湾其他地方普遍形成大小租制那样,而是形成一田一主制;三是水利事业都是移民私人投资开发的。水利事业对宜兰开发至关重要,周翔鹤从水利事业考察清代宜兰的社会领导阶层与家族兴起,认为由于宜兰自然条件相对良好、水利开发较为容易等原因,在宜兰的开发和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中,个体小农的力量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相应地,社会领导阶层发挥作用的空间就受到限制,他们的豪强色彩比不上西部地区,其家族的形成与发展也就受到限制。这是宜兰较少大族豪户的一个原因。周翔鹤还以清嘉庆、道光年间台湾宜兰水利合股经营为个案,研究传统中国农村合股经营企业的状况。通过对300多份水利合股契约的分析与归纳,认为在资本、劳动、土地、技术诸要素中,资本在农村企业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围绕着资本,农村企业建立起明晰的产权关系。在农村企业的组成和运营上,等量资本占有等量利润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大股套小股等方式,形成了少数人合伙或一定范围内多数人以小额资金入伙等不同合股经营模式,这有利于企业的形成、发展。但由于缺乏近现代信用制度,农村企业在吸资范围和融资渠道上均受到限制,不利于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注]另外,姚莹、杨廷理对噶玛兰开发的贡献,也有学者撰文论及。[※注]李若文考察了清代台湾嘉义地区汉人的拓垦活动与环境变迁。[※注]其他地区开发史研究,学界较少涉及。对台湾开发史进行区域研究,是清代台湾史研究亟待进一步加强拓展与深化的领域。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