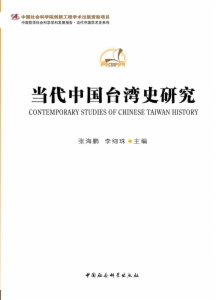四 社会变迁
|
来 源
:
|
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9 | ||
|
摘 要
:
|
康熙统一台湾后,把台湾纳入清朝版图,便开始治理与开发台湾。本节论述学界有关清前期治台政策与制度建设、台湾的经济开发、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等问题的研究成果。针对台湾学者林文龙所谓“清代台湾巡道‘兼督船政’一事,前所未闻,似为‘兼督学政’之误”的说法,李祖基撰文考证认为,清代分巡台湾道“兼督船政”一事最早由尹士俍的《台湾志略》所记载,所谓“船政”,主要是指台澎水师战船的修造。刘正刚、刘文霞注意到移民开发台湾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大陆各省文武官员,利用清代台湾方志记载,具体考察河南籍官员在台活动,认为他们贯彻清朝中央政府的政策,对台湾实行有效管理,对。 | ||||||
|
关键词
:
|
政策 台湾 大陆 移民社会 清廷 学界 台湾少数民族 制度 贸易 台湾人口 天地会 |
||||||
在线阅读
四 社会变迁
字体:大中小
关于清代台湾社会发展变迁的总体研究,即社会转型模式的研究,台湾学者曾提出不同看法,引发所谓“内地化”与“土著化”争论。“内地化”观点由历史学家李国祁首先提出,认为清代台湾移垦社会的转型,主要是一种“内地化”运动,即台湾社会变迁在取向上以中国本部各省社会形态为目标,转变成为与中国本部各省完全相同的社会,其结果是台湾成为中华文化的文治社会。[※注]“土著化”观点以人类学家陈其南为代表,认为整个清代是来台汉人由移民社会走向“土著化”变为土著社会的过程,土著社会以建立在本土地缘和血缘关系上的新宗教和宗教团体取代了移民社会的祖籍地缘和血缘团体,其结果是台湾社会与中国本土社会逐渐疏离。[※注]大陆学者陈孔立认为,尽管“内地化”与“土著化”理论研究方法不同,立场不同,但其对清代台湾历史发展模式的探索值得称赞。这两种看法都认为台湾经历了从移民社会(或移垦社会)到土著社会(或文治社会)的转型,都考察了宗族制度、民间信仰等对社会转型的影响。“内地化”论者还总结了移民社会的若干特征,考察了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文教事业和士绅阶层的发展对社会转型的影响。“土著化”论者则对祭祀圈、宗族组织、械斗以及社会结构等问题做了比较细致的探讨。两者都对台湾历史研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但用“内地化”或“土著化”来概括台湾社会的发展模式都不够确切,不够全面。清代台湾社会发展的结果,有许多方面和大陆社会更加接近了,也有一些方面更加体现出台湾本地的特点。大体上说,在社会结构以及政治、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更加接近闽粤社会,而在经济方面和大陆的关系则有所削弱,台湾居民日益扎根在台湾当地。陈孔立对清代台湾社会发展模式提出新的设想,认为它是双向型的,而不是单向型的,即一方面日益接近大陆社会,一方面日益扎根于台湾当地,但也不是“内地化”加“土著化”,因为直到被日本割占之前,既没有“化”成与大陆完全相同的社会,也没有“化”成从大陆疏离出来的土著社会,而是处于双向发展的过程之中。“双向型”发展模式比“内地化”和“土著化”模式更加符合清代台湾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是故把移民社会转型后的台湾社会称为“定居社会”,似乎比“文治社会”或“土著社会”更加符合当时的历史特点。[※注]李祖基进一步论证清代台湾从移民社会转型为定居社会,认为清代前期的台湾属典型的移民社会。到了晚清,在台湾移民的后裔逐渐取代新移民成为居民中的大多数;居民中祖籍分类意识趋于淡薄,超祖籍的祭祀圈和血缘宗族普遍出现,居民对现居地认同感增强;地方文教的普及和科举的兴盛造就了一个士绅阶层;中华文化及传统道德观念已在台湾扎根。台湾由移民社会转变为定居社会。[※注]林仁川对于海峡两岸学界关于清代台湾社会发展变迁讨论的主要观点“内地化”“土著化”和“双向型”进行分析,指出其分歧的焦点主要在两个方面,即对台湾社会转型的前提和标志有不同的看法,并认为这些观点主要是从历史学或人类学的角度提出社会转型的标志,虽都有一定道理,但均不够全面。林仁川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考察清代台湾社会的转型,提出新的观点,认为清代台湾转型前的社会与大陆闽粤社会没有质的区别,都属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到19世纪80年代,在国际现代化潮流的影响下,台湾社会既不是向“内地化”,也不是向“土著化”或“双向型”转型,而是逐步转向现代社会,其主要标志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经济发展工业化,社会生活空间城市化,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现代化,清代台湾社会已逐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注]史坤杰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待台湾社会的转型,认为“内地化”和“土著化”这两种观点都有谈到移民的认同感,其实南北是有很大差异的。所谓清代台湾社会的转型,是从整体上而言的,实际上南部是最先进入定居社会的。汉人移民台湾,最先垦拓的就是台湾南部地区,而后循着由南向北、由西向东、由沿海向内陆的途径,逐渐开发台湾全岛。台湾南部民众移居台湾的年代相对久远,随着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化,祭祀先人也从大陆祖先向开台始祖转变,与大陆的联系日益疏远,南部民众的认同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不能因此就否认中华文化在南部的存在,台湾南部社会结构仍保留了传统的中华文化的特点。清代台湾社会转型,实际上是汉文化的逐步移植,所谓“内地化”和“土著化”只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本质上都是认同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台湾文化,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注]
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这个移民社会在清前中期形成,并在清末向定居社会转型。关于清代台湾移民史的研究,首先值得关注的是陈孔立著《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初版,九州出版社2003年增订本第1版、2006年第2次印刷)。该书从移民与移民社会理论问题入手,系统分析了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发展进程与特点,进而讨论移民与人口及社会结构变迁,最后考察社会矛盾与动乱问题,涉及清代台湾社会变迁诸多复杂面相,是一部全面深入研究清代台湾社会史的奠基之作。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专辟一章(第八章“台湾的移民垦殖”)论述明郑以来尤其是清代闽粤移民渡海迁台的历程与台湾移民社会的形成,以及移民开发台湾并推动台湾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史实。林国平、邱季端主编《福建移民史》(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上编第五章第四节“清统一台湾后闽人移居台湾”,也简要叙述了清代福建移民迁台的基本情况。邓孔昭主编《闽粤移民与台湾社会历史发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和陈小冲主编《台湾历史上的移民与社会研究》(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则是有关台湾移民问题研究的专题论集,对于清代台湾移民政策、移民与社会经济、移民与文化等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曾少聪著《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1版、2007年第2版)是一项跨国比较研究,刘正刚著《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第1版、2007年第2版)则是一项国内区域研究,两书从不同角度深化了清代台湾移民史研究。另外,庄为玑、王连茂编《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提供了福建移民渡台重要的基础性资料。
移民史的研究在台湾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以往清代台湾移民史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错误说法,例如,清政府禁止大陆沿海人民“偷渡”台湾、禁止赴台者携眷的政策的实行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和二十三年(1684),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政府取消了不许赴台者携眷的禁令等。邓孔昭通过史料的比对,逐一予以澄清,认为中国学者所谓清政府治理台湾之初即奉行禁止大陆人民“偷渡”台湾、禁止赴台者携眷政策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些错误说法主要来自错误引述日本学者伊能嘉矩的《台湾文化志》,伊能嘉矩把《大清会典事例》变成“六部处分则例”,而中国学者却又从他那里“引进”,并进一步变成“台湾编查流寓六部处分则例”,而且还将清政府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雍正八年(1730)、乾隆十六年(1751)、嘉庆五年(1800)四个不同时期里所作的规定当作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规定。至于清政府废除禁止赴台者携眷政策的时间,所谓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二十九年(1764)、光绪元年(1875)诸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实际上应该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注]
关于清代移民渡台的原因与类型,李祖基撰文做了深入探讨,他按照移民的性质,把移民分为生存型和发展型两种,认为其中因大陆地区发生自然灾害、瘟疫、战乱等原因渡海来台的生存型移民占了相当大的部分。郑氏时期的军事移民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移民,但就其性质而言,仍可归入生存型移民之列。同时在此期间也有不少以开垦、经商以及冒籍考取功名为目的而渡台的发展型移民。尽管发展型移民与生存型移民在迁移目的上有所不同,但由于个人的能力、机遇等主客观条件的差异,两者的目的与结果并不一定统一。在长达三四百年的先民渡台的历史长河中,虽然不乏成功的个案,但对更多的人来说,留下的可能是辛酸与不幸。[※注]周典恩进一步考察明清时期大陆移民渡台的原因与类型,认为明清时期闽粤沿海地区的民众之所以源源不断地渡海入台,除了受自然灾害、战乱频繁、人稠地狭、欺骗性谣言、垦户招佃等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外,移民勇于冒险打拼的人文性格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生存型移民”和“发展型移民”的分类并没有明确的界线,本质上无法区别。按照渡台的最初动机,大陆移民主要有两种类型,一为追求生存型移民,二为投资营利型移民。[※注]
在清代移民渡台过程中,由于清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行种种限制,故很多民众是以“偷渡”的方式移居到台湾的。“偷渡”是清代移民渡台过程中一个严重的问题。清代前期福建有许多平民偷渡台湾,陈孔立主要根据档案史料,比较具体地描述当年的偷渡情况、运载船只、上船与下船的地点、偷渡的组织、船资以及偷渡客的命运,认为从康熙至乾隆年间,形成了偷渡的高潮,台湾人口也从十几万增加到100多万。偷渡所使用的船只,主要是商船、小船,也有清军的哨船参与偷渡。从大陆向台湾偷渡的主要口岸是厦门、铜山(东山)、蚶江,台湾没有主要的登陆地点,几乎所有的小港都是偷渡者上岸的地方。清代前期向台湾的偷渡已经形成一种行业,有组织,有分工,如客头、窝家、船户、舵水、招引之人以及在台湾的接应,此外,还与来往港口的员弁、兵丁、差役以及当地的地保澳甲等互相勾结,形成关系网,为偷渡大开方便之门。偷渡的费用,即船资,当时称为“舡钱”,又称“水脚银”,不同时期价格略有不同,一般是2—4两,或3—4元为多,以乾隆年间米价作为对比,当时台湾米价大约每石2两,船资相当于一二石米的价钱。当年福建平民是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偷渡台湾的,在顺风的情况下,可能两三天可以到达,有的人经历千辛万苦到达台湾,已是不幸中的大幸,更多的偷渡者死在渡台途中。众多的偷渡者成为台湾的开发者,为台湾的开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注]为什么当时“偷渡”入台会如此盛行?邓孔昭、陈后生利用恩格斯的合力理论,从闽粤人民移居台湾的推力、台湾对闽粤移民的拉力、清政府对移民台湾设置阻力所形成的反作用力、“偷渡”的助力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大陆移民“偷渡”入台盛行的现象。[※注]
女性移民研究在清代台湾移民史研究中一直是一个薄弱的环节。相关研究中只是提到清政府曾经奉行禁止赴台者携眷的政策、清代台湾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区出现妇女稀少的状况,但很少深入论述。近年来,台湾岛内更流行着一种极端的说法,即所谓台湾“有唐山公,无唐山妈”,表示台湾历史上只有大陆男性的移民,而没有女性的移民。这种说法的流行,固然是特定政治生态的产物。邓孔昭从清代实行禁止赴台者携眷政策的概况、官方查获“偷渡”案中的女性移民、族谱资料中的女性移民、女性移民与清代台湾人口性比例的分析等几个方面入手,指出由于清政府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了禁止赴台者携眷的政策,也由于女性移民要进行“偷渡”会比男性移民更加困难,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台湾社会的人口性比例并不平衡。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雍正末年、乾隆初年两次开禁,很多女性移民得以“合法”请照渡台,以及更多的女性想方设法渡台与家人团聚,都有助于缓和台湾社会中人口性比例失调的状况,清代向台湾的大陆移民中,人口性比例的失调实际上是很有限的,而且在乾隆末年取消禁止携眷赴台政策后,台湾人口只在20年间就几乎翻了一番,这种社会人口的高速增长,除了移民增长之外,人口自然增长也应达到一个较高水平,表明成年男女的婚配率比较高,人口中的性比例已经比较平衡。[※注]
闽粤移民是台湾汉族移民的主体,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闽台汉族与河南固始却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翻阅福建、台湾籍汉族人的族谱,可以发现大多自谓其祖先来自河南固始县。闽台汉族籍贯固始问题,是一个饶有趣味而严肃的学术问题。徐晓望通过考证相关史志与族谱,认为固始人大批入闽,于史可征的仅唐末一次,其他不甚可靠;而闽人多称祖籍固始,除了唐末五代的一批之外,凡在其他时期入闽的家族,若说自己的祖先是固始人,则多有疑问。闽台人中有20%以上的固始血统,是由于千百年来北方汉人大迁徙及通婚导致的混血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固始确为闽人的“根”。闽台人籍贯固始是具有特别文化意蕴的社会现象,固始说正反映他们对自己“根”的追寻,亦即对中原文化的记忆。[※注]刘正刚、刘文霞注意到移民开发台湾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大陆各省文武官员,利用清代台湾方志记载,具体考察河南籍官员在台活动,认为他们贯彻清朝中央政府的政策,对台湾实行有效管理,对推动台湾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史实证明台湾的开发与大陆各地人民密切相关,从而证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注]
移民改变了台湾人口状况。林仁川、王蒲华认为,福建人口流入台湾在清代达到高潮,嘉庆十六年(1811)在台汉民已逾200万,其中以漳泉二府人为最多。清代福建人口流入台湾可分四个阶段:(1)顺治末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以军队移民为主体;(2)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雍正十年(1732),从候鸟式的往来到单身入台定居;(3)雍正十年(1732)至光绪元年(1875),准带家眷大规模迁移;(4)光绪元年(1875)以后,清政府彻底开禁并主持移民。清代福建人口流入台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禁民入台到入台者不准携眷,从多次开禁准台民携眷到设立官渡,直至最后解除一切禁令,不仅允许自由入台,而且鼓励入台。由于清政府对台湾实行半封锁政策,福建移民进入台湾,大多是偷渡的,偷渡入台的方式多种多样,从而使台湾人口不断增加。清代福建移民进入台湾之后,以台南地区为中心,分别向北、向南流动,主要分布于台湾西海岸的平原地带及东部宜兰平原等地。福建人口大规模流入台湾,或开垦荒地,或承佃土地,或从事贸易,或经营手工业,对开发台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注]研究清代台湾人口历史的论著,一般只列举三个关键数字:清朝取得台湾时12万人,嘉庆十六年(1811)194万多人,光绪十九年(1893)254万多人。陈孔立撰文进行修正和补充,对清代人口增长情况做出新的估算:1683年12万人,1762年73万人,1782年100万人,1811年194万人,1840年250万人,1893年300万人。同时指出,乾嘉年间台湾的人口增长有两个特点:第一,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的增长率高于乾隆前期和中期;第二,当时台湾人口的增长率高于全国,而增长最快的年份则比全国稍晚。影响台湾人口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是清朝严禁或弛禁的政策,而不是“动乱”,因为乾嘉年间台湾的人口增长主要不是依靠自然增长,而是依靠移入增长。[※注]关于清代台湾人口的性比例问题,台湾有所谓“有唐山公,无唐山妈”的谚语,陈孔立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早期台湾妇女人数确实较少,但早期移民中的无妻者并不占多数,因为许多移民在原乡已经娶妻,然后才到台湾来。从族谱资料看,早期娶台湾女子者为数不多,且主要是娶汉人移民的后代,“娶番女”的情况虽然存在,但实际上只是少数,且受到明令禁止。至于说会导致“在血缘上唐山人只不过占一半”,则无法找到根据,“有唐山公,无唐山妈”这句所谓谚语值得怀疑,笼统地说“无唐山妈”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注]段佩君研究清代台湾人口地理,把台湾分为南部、北部、中部、东部和澎湖五个人口地理分区。清代台湾的人口数量增长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台湾人口达90余万,增长率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绝大部分属于迁移增长;第二阶段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到嘉庆十六年(1811),台湾人口总数超过190万,增长速度超过前一阶段;第三阶段从嘉庆十六年(1811)到光绪十九年(1893),台湾人口总数达250余万,但增长率降低,人口增长方式以自然增长为主。清代台湾人口分布变迁,清初几乎全部集中在南部,清中期向中北部发展,清末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重心北移,人口分布也随着开发的进程走向均衡。清代台湾人口内部迁移分为农垦性迁移、商业性迁移、械斗民变性迁移和灾荒性迁移四种。清代台湾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移民社会和新开发地区,其人口的空间变化具有自己独有的区域性特点,这些特点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台湾人口的增加与迁移同样对于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台湾的开发,正是由大陆移民开始并最终完成的。[※注]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大家庭、小家庭及不完整家庭。所谓大家庭,是指包含两对及两对以上配偶的家庭;所谓小家庭,是指只有一对配偶的家庭;所谓不完整家庭,是指完全没有配偶关系的家庭。在代代分家析产的条件下,家庭结构的基本格局及其长期演变趋势,一般表现为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动态平衡,或者说是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周期性变化。然而,在清代台湾,不完整家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大家庭的发展也不稳定,从而在总体上呈现出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注]
清代台湾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生活及其与汉族的关系,也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施联朱、许良国主编《台湾民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和陈国强著《台湾高山族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有多篇论文涉及,刘如仲、苗学孟著《清代台湾高山族社会生活》(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则系统论述了清代台湾少数民族的族源和分支、家庭和社会关系、社会经济、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娱乐等方面。
族群关系是研究清代台湾少数民族的重点问题。陈国强考察康熙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就是从其与汉族关系的角度考虑的。认为在政治上,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广泛接触,进一步共同开发台湾;在经济上,传播汉族先进生产技术,促进生产,改善生活;在文化教育和民族关系上,创办社学,传播文化,与汉族通婚,虽有局部、短暂的矛盾与斗争,但友好相处是民族关系的主流。[※注]陈碧笙探讨清代汉族与平埔族之间的矛盾和融合,认为矛盾大半发生于前期,只带有暂时的局部的性质,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缓和,在民族关系中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民族融合方面,交换日益扩大,杂居日渐增加,通婚愈来愈经常,教化也日见其效力,这是经常的普遍的而且大量存在的因素,也是民族关系中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台湾平埔族与汉族之间有矛盾,有融合,矛盾中有融合,融合中有矛盾,最后就是在矛盾中融合在一起的。[※注]潘云东认为清代台湾平埔族汉化原因是:汉族移民拥有比平埔族高得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而且人口也占绝对优势,是平埔族同化于汉族的首要原因;在汉化前平埔族零散分布的小型非固定性集村的聚落形态有利于汉族移民介入,从而为民族同化发生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汉族移民的素质及其构成,也是平埔族汉化过程迅速完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汉族移民小传统文化影响下,平埔族移风易俗,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平埔族汉化过程。[※注]陈在正认为,在大陆移民入垦台湾中部的过程中,平埔族不断汉化,其宗教信仰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接受妈祖信仰就是其内容之一。[※注]刘正刚、刘文霞认为,清代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族联姻,既与早期移民性别比失衡有关,又与少数民族婚俗及汉化程度有关。少数民族与汉人联姻不仅扩大了移民生存空间,也加快了少数民族融合汉化的步伐,最终促进台湾社会经济发展。[※注]刘正刚进而认为,清代大陆移民在台湾的开拓,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接触、冲突、融合的过程。由于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族接触的历史较短,双方的矛盾比较尖锐,但移民经过相当长时间与少数民族的接触交往,彼此间逐渐认同乃至融合,在此过程中,官方的政策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注]
清代台湾的宗教与民间信仰颇为复杂。福建漳州籍移民是开发台湾的主力军,他们在清代移民台湾时带来了开漳圣王崇拜。邓孔昭认为,台湾的开漳圣王庙,最早建立于清朝乾隆年间。早期修建的开漳圣王庙主要有台北市的惠济宫、碧山庙,台北县的广济宫、太平宫,宜兰县的永镇庙、威惠庙、灵惠庙,桃园县的景福宫、仁和宫、建安宫,南投县的开漳圣王庙等。随着漳州移民的日趋增加,开发日渐,开漳圣王庙在台湾不断呈增长之势,开漳圣王崇拜也成为台湾一种重要的民间信仰。[※注]黄新宪论述了清代台湾城隍信仰中的功利主义色彩。[※注]颜章炮考察了清代台湾民间的守护神信仰和分类械斗的关系。[※注]妈祖信仰是清代台湾最重要的民间信仰。朱天顺认为,清代台湾妈祖信仰的发展,其最大的特点是清廷统一台湾、维持台湾的统治以及闽粤两省人民移居开拓台湾成为其传播的主要历史条件,因此使闽南、粤东等台湾垦民的故乡和台湾的妈祖信仰,无论就广度和深度来说,都有很大的发展。康熙统一台湾以前,台湾仅有妈祖庙10座,平均2万人有一座妈祖庙;清廷统治台湾以后,妈祖庙大量增加,新建者达222座之多。到清末,全台湾除花莲县因未有大批汉人进入垦殖而没有妈祖庙之外,其他每个县市都有妈祖庙,连开发很迟、汉族人口很少的台东县也有两座妈祖庙,多者如台南县和台南市有42座,从密度来看,平均约1.2万人就有一座妈祖庙。清代台湾妈祖信仰之迅速发展,与清廷采取鼓励传播的政策不无关系。[※注]李祖基从清代台湾移垦社会的特点分析了妈祖信仰发展的多重因素,认为清政府的渡台禁令与移民“偷渡”的风险,移居地环境的恶劣,社会动乱,地方官员的推动,以及台海间商业贸易的繁盛与郊商的兴起,均对妈祖信仰在台湾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湄洲妈祖庙董事会、湄洲妈祖文化研究中心、莆田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编《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为妈祖信仰研究提供了基础性资料。王荣国、汪文娟以清代台南大天后宫为例,考察台湾妈祖信仰“佛教化”问题,认为妈祖信仰普遍存在于清代台湾社会,其庙宇不乏与佛教关联者。台南大天后宫自竣工时至日据时代皆有僧住持。其宫内存碑、牌记二件:乾隆重修“碑记”保存妈祖宗教归属二说:其一,视其行迹近“仙道”,实则杂糅佛道而以佛为多;其二,将其视为佛、菩萨“化身”。咸丰铸钟“牌记”,从佛教角度解释宫内“佛像”(含“妈祖像”),尤其是“大钟”的佛教功用,赋予更多佛教内涵。因僧住持庙宇使民间神的妈祖信仰被赋予佛教内涵与色彩,谓之“佛教化”。此类现象在台湾鹿耳门妈祖庙、北港朝天宫、鹿港天后宫等皆有。台湾妈祖信仰“佛教化”源于福建莆田湄洲,可远溯至宋代南方。[※注]连念通过对清代编修的六部《台湾府志》和连横著《台湾通史》中寺庙的分布、数量、规模和主祀神等方面记载的分析,认为清代台湾的宗教信仰特点有四:第一,神明种类与信仰复杂多样;第二,佛教发展迅速,成为台湾主要的宗教信仰;第三,道教中的上帝、保生大帝、关帝信仰和民间信仰中的妈祖信仰发展尤为迅猛;第四,清代台湾宗教信仰不仅种类多,而且各种信仰还相互渗透、融合,体现出台湾多神信仰的特征。明清时期,台湾的宗教信仰状况由其移民社会的形态所决定,台湾的宗教信仰根源于祖国大陆,与闽粤民间社会的宗教信仰更是几乎一致。[※注]
关于清代台湾佛教研究,颜章炮利用台湾学者汇编的《台湾南部碑文集成》《台湾中部碑文集成》和《台湾北部碑文集成》中的寺庙碑文的系列研究论文值得注意。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寺庙主要是作为祀神和供信徒瞻拜的场所,但清代台湾的寺庙却成为民间社会的权力中心,并在民众当中表现出更强的文化凝聚力。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台湾特殊的社会构成——移民社会,以及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清代台湾寺庙具有不同于大陆的特殊的社会功用,即移民的自治中心、官府发布示谕的场所、戍台士兵的公馆。随着台湾社会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变,寺庙功用的特殊性也逐渐消失。清代台湾官民双方建庙祀神的动机截然不同,官方是从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这一中心出发,是想叫神癨为王朝政权服务,而民间祀神则是从一村一社或个人的利益出发,是希望神灵降福植祥。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差别,是由二者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决定。清代台湾民间对寺庙有一套完备的管理系统,主要由总理、董事和炉主构成,他们之间在管理方面有所分工。总理、董事属寺庙管理的决策层,决定和负责寺庙的修建,制定寺庙的管理原则,并参与寺庙的具体管理工作。炉主属寺庙管理的具体执行人,负责寺庙的房产、田产和秩序环境的管理,负责祭祀神明的具体事务。清代台湾商人、商行与当地寺庙修建和管理的关系非常密切。商人是寺庙的重要捐资者,从商户对寺庙的捐助可见台湾商业的兴衰。商人在寺庙管理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那些财力雄厚、社会影响大、对寺庙捐资多的商户,其作用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豪商巨贾直接担任修建寺庙的总理或总董事。寺庙的管理模式和祭祀活动还直接影响郊行的管理,有些商行甚至还以寺庙为议事公所。可见,清代台湾的商人、商行与寺庙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注]
清代台湾的灾变与社会慈善事业,学界也有所论及。马波考察了清代闽台地区主要灾种——寒害、水灾、风灾、旱灾、雹灾的时空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他认为灾害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是自然现象变化失调的结果,但又与人类有密切的关系,受生产技术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清代闽台地区人民的一些不合理活动,导致了农业灾害的发生和加重。[※注]除了自然灾害之外,随着大量东南沿海居民移往台湾,无业游民、流亡乞丐人数不断增加,贫困无助、老幼无依等社会现象也开始出现。为解决诸如此类的社会问题,台湾设立了许多慈善机构,进行社会救济活动。王尊旺对清代台湾的慈善事业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认为清代台湾在官民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形成了以养济院为中心的贫困救济机构,以育婴堂为中心的幼儿慈善事业,以义渡为中心的行旅帮扶机构,以医院为中心的医疗保健事业,以义冢为中心的丧葬救助体系,从而在台湾形成一整套多方位、多层次的社会慈善机构。在经费的来源上,许多捐款人以财产出租生息的方式保证了经费的正常收入;在管理上,无论是官办还是民办,都在不同程度上纳入了官方管理的范畴。这些慈善事业对于台湾的社会发展起了相当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的稳定。[※注]孙杰专论清代台湾义冢的救济对象与捐助者,认为就义冢的救济对象而言,大陆移民、戍台官兵等占较大比重。至于义冢的捐助者,除绅士阶层外,像开垦组织、郊商等社会群体,更值得关注。通过义冢的救济对象以及捐助者,可以透析清代台湾特殊的社会阶层,从而更好地了解清代台湾作为移民社会、海疆社会的特质。清代台湾地区开发环境的恶劣、特殊的人口结构以及与大陆原乡隔海相望的地理形势,都增加了社会对于义冢的需求度。而清代台湾的边疆社会特性,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性,又塑造了戍守官兵与义民存在的社会环境。为戍台官兵及义民专门设置的义冢,固然体现官方对其教化意义的重视,实则更反映出清代台湾作为边疆社会的动荡特性。[※注]尹全海等整理出版《中央政府赈济台湾文献·清代卷》(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选编了清代起居注、兵部与户部档案等原始文献,为研究清政府赈济台湾提供了重要资料。
清代台湾有所谓“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说法,表明其时社会动荡不安,“民变”事件迭起,主要有农民起义、游民骚乱与分类械斗等类型。关于清代台湾农民起义的研究,重点在朱一贵起义、林爽文起义、蔡牵起义等几次影响较大的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资料。
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起义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陈孔立把朱一贵起义参加者47人和家属23人的供词,与雍正十年(1732)吴福生起义参加者26人的供词进行比较研究,比较分析了两次起义者的籍贯、年龄、家属、财产、职业,以及起义的原因与目的、起义队伍的组织、起义者的所作所为。他提出两点看法:一是两次起义的性质不同。朱一贵起义是在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条件下,由农民阶级组织领导的、体现广大农民愿望的农民起义;吴福生起义还不能称为农民起义,尽管也是在封建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爆发的,但没有提出任何符合农民愿望的要求,也不能吸引广大农民参加斗争,所以把这个事件称为游民暴动可能更确切些。二是两次起义对清代台湾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民间械斗有着深刻的影响。朱一贵起义时有福建、广东两省籍民参加,后来闽粤籍民发生分裂与冲突,造成闽粤移民之间深刻的矛盾,而粤籍客家人不但没有参加起义,甚至还组织“义民”对抗起义;吴福生起义是由福建籍人发起,也受到客籍“义民”攻击。在这两次起义中形成的闽粤籍民之间的矛盾,为民间械斗种下了恶根。[※注]关于朱一贵起义与天地会的关系,长期以来,由于对天地会起源时间的说法不一,因此对发生在康熙六十年(1721)的朱一贵起义是否系天地会的起义,学界有不同看法。主张天地会起源于乾隆年间者,认为朱一贵起义只是清代早期的农民抗清起义;主张天地会起源于康熙十三年(1674)者,虽然肯定朱一贵起义是天地会的起义,但都未作具体说明。何正清认为,天地会起源最迟不晚于清代顺康年间,朱一贵起义是天地会创立以后,对清政府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促进了天地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反清活动范围日益广泛,组织日趋完善,逐渐形成一套反清复明理论,成为尔后天地会传说的根据。[※注]张莉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兵、刑两科档案及满文朱批奏折中选编《台湾朱一贵抗清史料》(上、中、下,《历史档案》1988年第2、3、4期)和《朱一贵余部抗清斗争史料》(《历史档案》1989年第4期),为研究朱一贵起义提供了重要的原始档案资料。张莉在整理清宫档案的基础上,还探讨朱一贵抗清起义的历史原因,认为朱一贵起义是在阶级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并在局部地区不断激化的历史条件下,爆发的一次农民的阶级反抗斗争,但不能简单地把朱一贵起义说成是郑成功抗清斗争的延续。朱一贵起义之所以发生,与台湾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密切相关,其斗争的开始是清政府驻台官吏加紧盘剥、任意骚扰而导致的一场民情激变。由于缺乏较完备的组织准备,未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起义很快失败。这场人民群众的武装反抗斗争,揭示出盛世中的腐败,对雍正帝的整治与新政策的推行,起到了客观推动作用。[※注]谢重光考察朱一贵事件与闽客关系问题,认为在朱一贵事件中,同为潮籍移民的杜君英集团参加造反,而李直三、侯观德等一万二千余人则拥戴官府与乱民相抗,实与他们不同的族群属性密切相关。杜君英一伙是福佬族群,所以与朱一贵为代表的闽籍福佬人结盟造反,李直三、侯观德等是客家人,所以联合了同为客家人的永定、武平、上杭等汀州属县的客家人,一起抵御福佬人的侵扰,并联合官府与朱一贵、杜君英之党作战。这对后来台湾的闽客关系总体上趋于恶化有很大影响。[※注]
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起义是清代台湾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刘如仲考察林爽文顺天政权的性质,认为林爽文起义所建立的顺天政权,是反对地主阶级及其封建统治的政权,不是封建性政权,而是一个产生于农民起义过程中的农民革命政权。由于这次起义是借助天地会的宗教外衣组织发动起来的,所以军事、政权和宗教的合一,又成了这一政权的特点。当然,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顺天政权也受到封建制度的许多影响,不但借用封建政权的组织形式和名称,如唐代的节度使、明代的左右都督、清代的提督等,而且档案资料中曾说到顺天政权还设有管理皇族事务的“宗人府”,这说明在那样动荡草创的状态下,皇权思想和宗法思想的影响,在顺天政权的组织中也已经反映出来。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顺天政权的性质。[※注]刘如仲还与苗学孟合编《台湾林爽文起义资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为研究林爽文起义提供重要的基础性资料。陈孔立进一步通过对林爽文起义若干关键问题的考察,认为这次起义的性质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虽然这次起义有少数地主参加,但起义是农民阶级领导和发动的;虽然斗争的矛头没有直接对准当地的地主,但起义是在阶级矛盾的基础上发生的,斗争双方的阶级阵线相当分明;虽然起义者没有提出土地要求,但这只能说明起义的水平问题。可以说,林爽文起义是在封建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爆发的、由农民阶级领导的、受到地主阶级镇压的起义事件,是一次比较典型的农民起义。同时他明确指出,以林爽文起义为例说明清代台湾人民起义不是反对地主阶级的农民起义,是讲不通的。[※注]关于台湾番族与林爽文起义的关系,针对有些论者充分肯定番族参加起义并起到了不小作用,而很少提及清政府利用番族镇压起义的现象,陈孔立撰文辨正,认为番族参加起义之事尚待考证,而有一部分番族确实被清政府利用参加了镇压起义的活动,因此论述林爽文起义时,如果只讲番族参加起义而不讲番族参加镇压起义,那显然是十分片面、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过去有些论著所谓“高山族人民纷纷参加起义”等说法,应予澄清。清政府一方面利用番族镇压起义,一方面要使熟番绥戢,生番化熟,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恩威并用、剿抚兼施是清政府始终坚持的政策原则。所以,在评论清政府对番族的政策时,不能强调友好合作,封建统治阶级不可能采取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实事求是地揭示其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利用番族镇压汉族人民起义以及恩威并用、剿抚兼施的政策,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注]刘平检讨以往研究者针对林爽文起义爆发的原因,都是从阶级斗争、阶级矛盾的角度展开论证的,但是从具体史料分析来看,土地矛盾、阶级矛盾在嘉庆以前的台湾社会并非主要矛盾,以往论者所采用的论据,多为嘉庆朝以后的史料,因此有必要重新考察林爽文起义爆发的社会背景和动因。他认为,林爽文起义不是天地会有意识、有目的发动的一次起义,而是东南沿海,尤其是台湾地区拜把结会传统在特定条件下发生的一次裂变;分类械斗不仅是林爽文起义的主要诱因之一,也是起义发展、败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林爽文起义是台湾移民社会诸种矛盾综合运动的产物。他还特别撰文辨正天地会与林爽文起义的关系,指出过去往往把林爽文起义称为“林爽文天地会起义”或“天地会领导的林爽文起义”的说法不确切。清前期的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游民众多,社会矛盾尖锐,这是会党与暴力产生的温床。天地会与林爽文起义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只是在其中充当了一个不自觉的主要角色。林爽文起义是天地会蔓延、演变的契机。[※注]林爽文起义爆发后,清廷从内地调拨军队赴台平乱。刘正刚、魏珂考察了藏兵赴台湾参与平叛的经过,四川藏族屯练降番二千多人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八月从四川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跋山涉水进入台湾。藏兵在台英勇作战,屡立战功,受到朝廷丰厚奖赏。战后,清廷还将四川屯练模式在台湾熟番中推广,取得较好的实效。[※注]刘新慧系统探讨清政府在平定林爽文起义后的善后措施,如放宽渡台,加强吏治,强化官吏督责权,添兵、增汛、建城,以资守御,整饬驻台班兵与营伍,镇抚番民,强化治安,认为清廷初期的治台政策带有明显的防范色彩,而在乾隆年间,随着台湾地区开发的深入,社会矛盾的加剧,清廷逐渐意识到了治乱和稳定海疆同样重要,开始实行新的治台政策,加强对台地的管理。[※注]针对学界普遍认为乾隆年间台湾林爽文起义是一场“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或所谓“恢复明室”的“革命”,季云飞撰文从林爽文起义爆发的原因、初期起义参与者的诉求、起事后林爽文竖旗建号许封文武官员、乾隆帝平定起义的根本出发点四个方面考察,认为林爽文起义的性质是:由危害台湾地方治安转化为危害台湾的“动乱”,实质上是一宗企图分裂国家的事件。[※注]
清朝乾隆中叶以后,在东南沿海的“海盗”活动中,蔡牵势力最大。蔡牵集团曾经在台湾竖旗起事,自称镇海王,占凤山,攻府城,戕官杀弁,在闽、浙、粤三省海面,坚持抗清十几年之久。关于蔡牵集团及其活动的性质,有的认为他们是武装走私的大商队,是市民阶级的代表;有的认为他们是海商集团或海盗,他们与清政府的矛盾是统治阶级内部两种政治势力的斗争;有的直接把它称为农民起义。陈孔立撰文认为前两种观点是误解,并对第三种观点做出修正:蔡牵集团是沿海人民的抗清力量,他们的活动是沿海人民的反清起义,是当时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一种反映。但是,他们又不同于一般的农民起义,因为他们打击的主要对象不是农村的地主阶级,他们的活动并没有触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因而对广大农民没有什么好处。蔡牵集团长期抢劫商船,对于发展生产和海外贸易产生了破坏作用。蔡牵起义比起一般农民起义来说,消极作用更为明显,这是与其流民阶级特性分不开的。[※注]叶志如利用清代档案文件,进一步分析蔡牵集团成员的成分,认为嘉庆前期活跃在东南沿海的蔡牵武装集团,是由一批无生活出路的贫困破产渔民、盐户、樵夫、水手、船工、疍户、农民和无正当职业的流民阶层等社会最底层人民所组成的反抗封建腐朽统治的人民起义队伍。[※注]叶志如还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中选编《蔡牵攻打大小担清军炮台史料》(《历史档案》1986年第4期),为研究蔡牵反清斗争提供原始档案资料。季士家撰文介绍清朝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蔡牵反清斗争项》档案,并利用档案考证蔡牵研究的九个方面的问题:(1)蔡牵的生年卒月:生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卒于嘉庆十四年(1809)八月十八日。(2)蔡牵下海的起始时间:乾隆五十九年(1794)。(3)蔡牵队伍基本成员的成分:以闽、粤青壮年人为主,自愿入伙与被迫人伙者几乎各占一半,成员以渔民居多。(4)蔡牵集团的领导核心:以蔡牵为首,有其侄子蔡添来和帮内唯一的知识分子“管账洪先生”组成的三人领导核心。(5)蔡牵集团与天地会的关系:有天地会员加入,蔡牵可能是天地会小头目。(6)蔡牵称王与建元问题:道光年间《福建通志》和《厦门志》都说蔡牵“自称镇海威武王”,并且建元“光明”年号,其说有误;清宫档案证明蔡牵在台湾“自称镇海王”,并无建元年号。(7)封建社会盗匪成因的基本认识:民生多艰,被迫为盗。(8)蔡牵海疆斗争的性质:初期斗争,自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七年(1794—1802),属传统的海盗行径;后期斗争,自嘉庆七年五月至嘉庆十五年(1802—1810),为反清起义。(9)蔡牵帮与同时存在于海上各帮的性质区分:其他各帮始终停留在传统的海盗行为,蔡牵帮从海盗行径发展为反清起义。[※注]关于蔡牵集团的性质,关文发对所谓“官逼民反”起义说提出质疑,认为以蔡牵为代表的海上武装集团,虽曾进袭台湾,其活动又几乎与川楚白莲教起义、湘黔苗民起义同时进行,从而分散了清廷镇压上述起义的力量,在客观上对清朝统治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如果把握住蔡牵集团的主轴,从其成因、队伍之构成,与安南夷艇之关系,及其一贯之剽劫活动作总体考察,其海盗性质是十分明显的。[※注]陈在正认为,谢金銮代撰的《祭天后宫文》实质上是一篇对蔡牵海上武装集团的讨伐令,从中可见镇压蔡牵集团的清水师官兵与反清的蔡牵集团都虔信妈祖。[※注]蔡牵事变爆发,官军屡战屡败,东南海疆危急。嘉庆帝不得不从内陆各地调兵遣将赴台平乱。藏兵因有赴台参与平定林爽文事变之先例,再次被调遣赴台。刘正刚考察藏兵赴台湾经过,认为藏兵在陆续开赴台湾过程中,因台湾战事形势逆转,行动终止,但这一行动再次验证了藏兵在清朝军事行动中的重要地位。[※注]杨国桢、张雅娟从海洋人文社会类型的视角,分析海盗这一特殊海上族群与清代海洋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蔡牵崛起所代表的民间海洋社会权力及其控制海域的作为,是清中叶民间海上力量的一次展示。这是王朝政治“盗匪”观念极力掩盖的事实和意义。但这一时期的民间海洋社会权力又是一把“双刃剑”:冒险、进取,同时又带来破坏性、掠夺性;不守成规,处于无政府状态,加剧了海洋社会的内耗,消解了向海洋发展的能力。他们以法外暴力的形式争取权力,是以海洋社会分裂为代价的,不利于海洋渔业、航海贸易经济的正常发展,也就不能使他们争取海洋权力的合理性变为海洋社会的合法性,得到大陆民众的同情和理解,发展出重视海洋、支持海洋发展的社会氛围。清王朝更没有从丧失制海权中得到教训,认识海洋的重要,提升水师的外洋作战能力,反而更加内敛,强化隔绝海洋、“严防其出”的措施,和世界强国发展海洋权力的差距越来越大,陷入有海无防的困局。[※注]
其他农民起义。道光十二年(1832)台湾嘉义张丙起义是清代前期台湾历史上一次比较大的起义事件。这个事件与闽粤械斗交错在一起,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例如,起义者多是漳州府属的移民,而粤籍移民则基本上站在对立的一方;起义者把斗争矛头主要指向清朝官员,打出“开国”“兴汉”的旗号,而凤山县的起义者则提出“灭粤”的口号。因此,在评论这个历史事件时,有人认为它是一次大规模的闽粤械斗,或是由官方介入闽粤械斗而扩大成的民变,有人则认为它是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起义,而不是反对地主阶级的农民起义。陈孔立撰文认为,从张丙起义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它是在社会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的基础上爆发起来的;从起义过程的斗争情况,可以看出两个阶级的对立。尽管这次起义中夹杂着闽粤械斗的因素,但它并不起主导作用,不能改变其农民起义的性质。[※注]同治元年(1862)三月,戴潮春领导的台湾八卦会起义在彰化县爆发。戴潮春起义,在台湾历史上规模仅次于清康熙年间的朱一贵起义和乾隆年间的林爽文起义,而整整坚持三年,持续时间则最长。邓孔昭撰文论述台湾八卦会与戴潮春起义,认为虽然戴潮春领导的会党组织使用的是八卦会的名称,实际上它就是天地会系统的一个支派组织。这次起义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是起义初期,戴潮春提出了“连和二属(漳、泉)”“协衷共济”的主张,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执行;二是起义中妇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三是起义在某些方面完全仿效太平天国,但其实质和太平天国仍有很大的区别。造成起义失败的每一重大因素都与八卦会的弱点和局限性有关,如政治觉悟低,组织分散,纪律松弛,没有建立集中统一的领导,都是台湾八卦会显著的弱点。尽管戴潮春领导的台湾八卦会起义最后失败了,但它仍然是中国近代史上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主体的第一次农民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注]
关于清代台湾游民骚乱与分类械斗的研究,也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陈孔立系统考察清代台湾游民阶层,从游民的概念、来源、活动状况、与各阶层的关系等方面,联系台湾社会的特点及其变化,观察游民阶层的社会地位,及其对台湾的开发和社会的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游民又称罗汉脚,是无业或无固定职业的单身汉;台湾游民由闽粤两省的游手无赖和逃犯、闽粤移民到台湾后的失业者和半失业者、台湾本地滋生的失业者三个部分组成,其人数占台湾人口总数的10%—30%,不同时期所占比重有所不同;游民对台湾社会影响最大的是他们参与各种社会动乱,几乎每一次起义、暴动、分类械斗都有游民参加,由此对社会产生副作用,成为台湾社会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尽管游民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都有互相结合和互相对立的两面,但对立关系占主导地位,不仅对官府、地主、富户,还是对农民及一般平民来说,游民阶层都是社会上的一大祸害;游民通常处于寄生状态,好逸恶劳,不事生产,对台湾开发的副作用十分突出;游民参与各种社会动乱,虽然不起主导作用,但由于其破坏性而往往产生负面影响;台湾游民问题主要是移民社会的产物,随着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变,游民问题也成为一般的社会问题了。[※注]陈小冲认为,罗汉脚是清代台湾游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基本特征有六:单身,穷人,无业,边缘人,拉帮结派,违法犯罪。罗汉脚的存在,既是清代台湾移民社会发展进程中固有矛盾发展的产物,又在某种意义上与清廷对台政策有着较大的关联。罗汉脚的历史定位可以流氓无产者视之,其中虽有相当多的流氓、游棍成分,在社会动乱中有时起着危害社会的作用,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是台湾开发的力量,也曾参与反抗封建王朝的斗争,一概将之视为社会负面因素,似乎是不公平的。[※注]乾隆三十三年(1768),台湾以黄教为首的武装暴动,规模较小,影响不大,但情况却比较特殊。一些论著或称之为反清运动,或称人民起义,还有的说是民变、匪乱或作扰。陈孔立通过具体研究,认为这次暴动的参加者主要是游民,不论从暴动的动机和目的、暴动者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同各阶层人民的关系来看,都和一般农民起义有明显的差别。这次暴动既提不出经济要求,也提不出政治要求,连反对贪官污吏也没有涉及,所以不能称为起义。暴动者没有反映农民的任何要求,只是单纯进行焚杀抢劫,得不到广大农民的同情和支持,因而也不能称为农民起义。把以黄教为首的暴动事件,称为游民暴动是比较合适的,这样可以更明确地体现这个事件的特点和性质。[※注]在雍正年间及乾隆初年,台湾竖旗事件不时出现。竖旗是指有人在旗上写一些口号之类,将旗插于某个地方,以此向清政府示威、反抗;竖旗者还在旗上随便写上一些与己无关的人的姓名,借以掩护自己,或者写上一些与己有怨仇的人的姓名,加以陷害。当地政府官员往往把竖旗事件说成纯粹是竖旗者为报私仇而“挟仇陷害”。谢峰达通过具体考察竖旗案的内容,认为多数竖旗案与当时的天地会活动有关。清朝台湾竖旗事件屡见不鲜,可能是由于天地会的力量还不足以发动起义,或慑于清政府的淫威而不敢贸然起义,因此以竖旗这种方式向清政府示威;而当力量壮大,或因台湾官吏腐败等社会原因引起社会矛盾激化时,就演变成大规模的天地会反清起义。[※注]
在清代台湾移民社会中,每当发生农民起义或游民暴动,民间就会出现一种协助官府与“乱民”相对抗的社会力量——“义民”。如何评价义民,学界颇有分歧。当人们肯定那些反抗官府的“民变”时,对于“依附官府镇压起义”的义民就会持否定的态度,所谓义民“不义”,是封建官府的帮凶。反之,则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义民是针对游民(罗汉脚)对社会的破坏而产生的民间自卫组织;义民反对“乱民”的焚掠行为,协助官府恢复社会秩序,“含有相当社会正义行为的成分”;义民是“社会团结的力量”;义民与乱民之间并不是既得利益阶级与非既得利益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陈孔立撰文认为,要把义民问题放在清代台湾移民社会整个社会结构中进行考察,通过具体分析义民及义民首领的构成成分,以及义民与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义民的性质问题得出四点结论:(1)义民由官府或士绅阶层组织领导,帮助官府镇压起义,保护官府和士绅阶层的利益,这就决定了义民在台湾移民社会中所处的社会地位——统治阶级的附庸和工具。(2)义民既有保卫乡里、避免受到起义者侵害的一面,又有乘机焚抢、侵害一般平民的一面,把他们看成是保护社会安定的力量不符合历史真实。(3)义民与游民并不是一对矛盾,游民可以是“乱民”,也可以是义民,不能简单地把义民说成是游民(“社会破坏力量”)的对立物。(4)义民与“乱民”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转化,说明义民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对于所谓“义民不义”、义民与“乱民”的阶级界限、义民与祖籍的关系问题,陈孔立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所谓义民是清朝当局眼中的义民,“义”与“不义”,是从清朝统治者的立场来判断的;义民与“乱民”既对立,又可互相转化,如果一旦成为义民,便站在统治阶级一方,成为维护既得利益阶级的一种社会力量;义民和“乱民”的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祖籍矛盾。[※注]谢重光在准确界定清代台湾客家义民身份的前提下,探讨了清代台湾客家义民的历史评价问题,批驳了近年来台湾某些学者提出的客家义民“依附官府镇压起义”,“义民不义”之类错误观点,阐明清代台湾客家义民是乡村团结自保的民间武装,其首要的第一位的任务是保卫家园,在历史上起到稳定地方秩序的作用,是保护社会安定的力量。[※注]
“分类械斗”是清代台湾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从乾隆中叶开始逐渐发展,到嘉庆、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高峰,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也是台湾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陈孔立撰文论述分类械斗的名称与含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具体原因与历史过程等问题,得出如下结论:(1)分类械斗是不同祖籍居民之间的械斗,是在台湾移民社会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台湾移民社会中存在着以地缘关系组合的社会群体,它们之间在开发过程中产生了矛盾和冲突,清政府统治的薄弱和游民的大量存在等因素,促进了上述矛盾的发展,为分类械斗的产生提供了条件。(2)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逐渐发生变化——从以地缘关系组合的社会群体为基础,转变为以宗族组织为基础,即从移民社会转变为定居社会,产生分类械斗的社会条件发生变化,分类械斗也就逐渐消失,并逐渐为大陆上常见的一般械斗所取代。(3)分类械斗是台湾社会中的一个消极因素,它破坏各籍居民的团结,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阻碍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分类械斗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它终于走向了反面——为自身的消失提供了条件。陈孔立还对台湾学者关于分类械斗研究的史实进行辨误,指出“康熙六十一年凤山下淡水溪一带闽粤械斗”“乾隆五十一年彰化闽粤械斗”并非械斗事件,“雍正元年南路闽粤械斗”“乾隆十六年台湾县李光显械斗”“乾隆五十一年诸罗同姓械斗”“咸丰三年北部四县漳泉械斗”提法均有误,“乾隆四十年彰化漳泉械斗”“乾隆四十八年彰化等地漳泉械斗”均应是四十七年事,“乾隆三十四年闽粤械斗”应是三十三年事,“乾隆四十八年淡水械斗”不是漳泉械斗而是闽粤械斗,“乾隆五十六年徐祥伯械斗”与“乾隆五十六年嘉义沈川械斗”是同一件事,“嘉庆十四年彰化漳泉械斗”与“淡水漳泉械斗”也是同一件事,当年另有淡水闽粤械斗事件,“道光六年彰化闽粤械斗”与“淡水闽粤械斗”是同一事件,“咸丰三年淡水闽粤械斗”并不存在,只有咸丰四年(1854)淡水闽粤械斗,“咸丰九年淡水漳同械斗”实际上主要是漳泉械斗。清代台湾发生过许多次“分类械斗”事件,其中主要是闽粤械斗和漳泉械斗。唯独咸丰三年(1853)发生了一次“顶下郊拼”。它是居住在台湾北部艋舺附近的泉州府籍移民内部发生的械斗事件。所谓“顶郊”,指的是晋江、南安、惠安三县的移民,又称“三邑人”;所谓“下郊”,指的是同安县的移民。这次事件以及咸丰九、十年(1859、1860)间发生的漳泉械斗,形成了清代台湾分类械斗的高峰,时间很长,损失很大。陈孔立撰文专论咸丰三年(1853)台湾北部“顶下郊拼”的前因后果,进而深入剖析清代台湾社会结构的状况以及福建对台湾的影响。[※注]吕小鲜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录副奏折和上谕档,选编《乾隆四十七年台湾漳泉民人械斗史料》(《历史档案》1996年第1期),为研究该次械斗提供了重要的原始档案资料。季云飞研究清代台湾民间械斗与清政府的对策,认为清代移居台湾的漳泉、闽粤民人间发生的“分类械斗”不同于台湾人民反清起义,它有害于海疆稳定、社会安宁和经济发展,无任何积极、进步可言。发生“分类械斗”的原因在于:闽粤及漳泉民人移居台湾时间的先后而造成在台居住地区的不同;开发、经营台湾过程中,经济利益的冲突;移民在原籍“械斗”恶习的沿袭;游民恶棍从中挑拨煽惑;在台官员查处不力,甚至放肆贪虐。清代历朝统治者采取劝谕、镇压、制定防范章程和整顿吏治等措施加以制止和防范,但由于清政府政治及吏治的日趋腐败,以及台湾地方官员“积习疲玩”积重难返,“械斗”愈演愈烈。只有到了近代,闽粤移民停止“械斗”,和台湾少数民族人民一起抗击外国侵略者,显示了中华民族所固有的民族凝聚力。[※注]汤韵旋分析了清代移垦时期台湾“闽客械斗”的复杂原因及其“惨烈”结果,并进一步分析了“闽客械斗”对于台湾客家族群心理、性格方面的影响,认为了解清代台湾移垦时期的“闽客械斗”,不仅是了解清代台湾历史的重要环节,而且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当今台湾族群分布、族群意识及其族群心理。[※注]
有关清代台湾“民变”的总体分析及清政府的应对方略与社会控制研究。陈孔立用社会动乱指称“民变”,根据事件的性质把清代台湾的社会动乱分为起义、游民骚乱(包括暴动、骚乱、竖旗、结会)、地方豪强的骚乱、其他抗官事件、民间械斗、土汉冲突六类,通过全面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从总数来看,动乱次数达到365次。其中土汉冲突多达206次,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是土著居民和汉人移民之间的纠纷和冲突,不与官府为敌,不具政治性。民间械斗有73次,占总数的20%。这是民间的私斗,不与官府为敌,也不具政治性。这两项实际上都是民间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清政府也没有视之为“叛逆”。此外,游民骚动占动乱总数的18.08%,其中有的只是单纯的竖旗和结会,而没有实际的行动,一般骚乱和暴动主要是为了抢掠财物,不具政治性,也没有形成较大的规模。只有其中几次规模较大影响较大的事件,清政府才把它们列入“乱”的范围。至于地方豪强的骚乱,主要是土匪性质的,属于社会治安问题,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在其他抗官事件中,主要是属于地主抗粮性质的事件,这在大陆各地也是常见的。所以,从统计数字来看,绝大部分属于民间内部的冲突,而不是政治性的反清事件。第二,大量动乱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的移民社会中,到了19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逐渐转化为定居社会,动乱次数有了明显的减少。可见台湾社会动乱次数较多,主要应当从移民社会的角度加以探讨,才能看出问题的实质。第三,从严格意义上说,真正可以算是“反”的事件,主要是起义事件。台湾的起义事件共7起,占动乱总数的1.9%,为数不算多。它们是在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发生的,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起义者往往提出反对官府的口号,把贪官污吏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这与大陆各地的许多农民起义也是相同的。第四,所谓“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只是一种民谣,它把所有的社会动乱都包括在“反”的范围内,实际上如果对这些事件做出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其中有不同的原因和性质,不能一概而论。有些不了解台湾历史真实的人,把所有的社会动乱都说成是反清事件,进而把它说成是台湾人“反唐山”的斗争,甚至认为这些事件表明台湾人为了要摆脱中国的影响而不断地进行抗争。这种说法完全脱离了台湾历史的实际。实际上找不到任何一个事件是“反唐山”的,当时的台湾人并没有任何要脱离中国的意愿。相反地,许多起义与大陆有密切关系:朱一贵起义提出“大明重兴”;林爽文起义是在福建传入的天地会组织下发生的;陈周全起义是由从同安来的天地会员发起的;蔡牵起义是从福建开始,然后与台湾本地力量结合发动的;林恭、戴潮春起义都是在太平天国起义影响下发动的。[※注]褚静涛论述清朝台湾开发过程中的族群冲突,包括闽粤移民与原住民族的冲突,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之间的分类械斗,以及游民暴乱等,认为这些族群冲突与移垦社会的结构密切相关,在以地缘关系组合的社会群体中,移民间因经济利益、文化信仰等问题难免产生冲突,而清政府的管治力量十分薄弱,未能加以有效疏导,游民大量存在,无事生非,一哄而起,成为动乱之源。[※注]林仁川、朱建新从清代台湾社会的乱象探索社会自我控制机制的效能,认为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失调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反”与“乱”,赌博成风,以及吸食鸦片的盛行等。但是,台湾移民社会同时又产生极强的自制力,这种自制力主要表现在祭祀圈的形成,建立社区的自治中心——庙宇,防御圈的建立。通过以上的社会控制,保障了台湾移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注]关于台湾移民社会自制力,也即民间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而清政府对台湾社会的政策与制度性调控,更是值得深入探讨。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