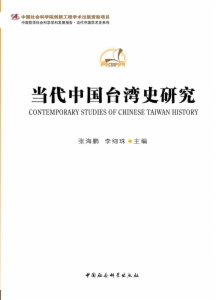二 晚清治台政策与洋务事业
|
来 源
:
|
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7 | ||
|
摘 要
:
|
作为清朝版图的一部分,台湾与大陆命运相连,既不免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同时也开始步入近代化的历程,最终却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被迫割让给日本。台湾近代史是中国近代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关于台湾近代史的研究,杜继东曾撰文进行较系统的考察[※注],本书拟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全面论述。陈旭麓认为,台湾建省是清季认识台湾的战略地位及其危机所采取的重要步骤,历史的责任由洋务派承担,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洋务派为加强海防和建设台湾,推动台湾建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湾的近代化。随着台湾近代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闽台教育交流逐渐实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新的闽台教育关系。 | ||||||
|
关键词
:
|
防务 台湾 海防 中法战争 抗法 教案 大陆 军民 政策 刘铭传 传教士 |
||||||
在线阅读
二 晚清治台政策与洋务事业
字体:大中小
为应对列强侵略台湾,清政府在加强台湾海防的同时,其治台政策也有适当调整。李祖基以大陆移民渡台及理“番”政策为例,考察清政府治台政策的转变,认为清前期对台湾之开发持消极态度,如对大陆移民渡台实行限制,并禁止汉人进入“番”地,实行汉“番”隔离政策,渐为后人所诟病。如果说领照渡台规定之本意是要将大陆移民渡台纳入政府的有效管理,但在实行中兵弁的刁难、需索,反而造成偷渡的盛行;而对内山“番地”的封禁,实行汉“番”隔离则造成界内“番”民的自生自灭和政府行政管辖的不力乃至完全缺失,渐使台湾地方官员形成视番界为“化外”“瓯脱”之地的错误观念。晚清时期,随着台湾口岸开放,外国势力入侵,清廷消极治台政策的弊端日渐凸显,乃至为列强窥伺觊觎提供种种借口和可乘之机。“牡丹社事件”之后,沈葆桢奏请开放大陆移民渡台和“开山抚番”,表明清政府治台政策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由原来的消极转向积极,不仅废除了限制大陆人民渡台及不准台民进入“番地”的种种禁令,后来还在厦门、汕头及香港等地设立招垦局,由官方提供船票、种子、农具、耕牛及一年半的生活费用,招徕大陆移民前往台湾东部内山从事开垦。其后,经过丁日昌、刘铭传等历任官员的努力,不仅内山的开发和“番”地的教化管理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而且近代化的建设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在短短的近二十年时间内,台湾由原来的边陲海岛一跃成为全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注]
沈葆桢、丁日昌、刘璈等人的治台政绩及其对清政府治台政策的影响,学界有所论及。季云飞论述了沈葆桢治台政策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以“开山抚番”为主要内容的对台湾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政策;第二,以“整顿防务”为主要内容的海防建设政策;第三,以“教化番民”为重点的文化政策;第四,以“开禁”、“招垦”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政策;第五,以“筑城设官、析疆增吏”为核心内容的“外防内治”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加强清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治理,对于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对于中国海防的巩固、台湾社会的稳定以及海峡两岸的交流,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注]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规定福建巡抚“冬春驻台,秋夏驻省,两地兼顾”。李祖基认为,丁日昌是实行此一规定之后的首任福建巡抚,在其两年多的闽抚任上,对台湾的海防建设和经济开发做出全面的规划,提出兴办铁路、矿务,设立电报线等主张;继续开山抚“番”,移民实边,开垦台湾后山;大力整顿吏治营务,裁革陋规,豁除杂饷,纾解民困,取得令人瞩目的政绩。闽抚“冬春驻台”的目的是要加强海防建设,但由于此一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清廷未能在经费上给予必要的支持,故闽抚驻台未能发挥出预期的作用,这一规定也于光绪四年(1878)六月取消,恢复了由督、抚隔年轮赴台湾巡查的旧制。[※注]林其泉认为,刘璈任台湾兵备道期间(1881—1885),不但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而且领导台湾军民大力开展建设工作,加强海防力量,在中法战争的台湾保卫战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为台湾建省做了准备。[※注]
“开山抚番”是晚清治台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清前期在台湾推行汉“番”民族隔离政策,沿山设立“番界”,禁止汉“番”人民互相往来。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武装侵台,清政府遂一反常规,实行“开山抚番”政策。林冈全面评价“开山抚番”政策,认为实行“开山抚番”政策,不但防止了“番地”陷入外国侵略者的魔掌,加强了台湾以及南北洋的海防力量,而且还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与民族间的团结,对于这一政策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理应给予充分的估价。在这个过程中,“生番”的反抗有的属于正义性质,有的属于非正义性质,那种全面否定“开山抚番”政策的进步性,对“生番”的反抗一概加以赞美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个政策的实施,还受到清朝统治阶级本身主观条件的限制,如将吏不能称职,财政开支困难,清政府态度不一,因而有其历史局限性,只能取得局部成功。[※注]周翔鹤认为,清代前中期的台湾,清政府(中央与地方政府)无法解决“番害”问题,以“隔绝番汉”的策略把它掩盖起来,实际上问题还是存在的。晚清,在“开山抚番”与樟脑生产中,这个问题重新又爆发出来。因汉人深入山地,不断侵占山地土著生存、活动空间,并与山地土著直接交易,产生军火走私等问题,汉“番”冲突比清初激烈许多。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虽采取“开山抚番”政策,但长期的“隔绝番汉”政策所形成的后果,并无法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得到解决。实际上,“开山抚番”难以取得成功。[※注]吕宁、白纯认为,“开山抚番”是沈葆桢、刘铭传办理台湾防务建设中的重大举措。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沈葆桢临危受命,赴台筹办台防。鉴于台湾“生番”地区的重要性,沈葆桢审时度势,着眼于台湾防务建设,施行了以“外防内治”为目的的“开山抚番”政策:开山修路、开禁招垦、增府置县、设立“番”学等,为促进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巩固台湾防务,发挥了积极作用。刘铭传出任台湾首任巡抚以后,进一步实施“开山抚番”政策,强化了清政府在“番”地的治权,有利于巩固台湾防务;促进了汉“番”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加强了民族团结,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利于台湾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维护祖国统一;加速了“番”地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台湾近代化的进程。[※注]

台湾洋务运动是中国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孙文举把台湾与大陆的洋务运动相比较,指出其共同点和不同点,表现有四:(1)台湾与大陆的洋务运动都是在列强入侵的背景下由洋务派主持和推动下开展起来的,其动机、目的、内容、方式、结果,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是一脉相承的关系。(2)洋务运动在“自强”的口号下开始,以增强防务为中心。大陆的“防务”有一个由对内转向对外的过程,其结果是增强了对农民起义镇压的能力,而在对外上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台湾的“防务”从一开始就完全放在对外上,结果是显著地增强了台湾防务的实力,提高了台湾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士气。(3)大陆洋务运动所需要的经费,特别是举办一些较大的项目,主要靠中央政府调拨,包括以海关收入留成做保证。台湾基本上靠本省的财力来解决。(4)台湾的洋务运动虽然比大陆开始晚而结束早,但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成果也显而易见,是大陆任何一个省份和地区所不能比拟的。[※注]詹学德认为,由于台湾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氛围,其洋务运动与大陆既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有着巨大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走向。台湾洋务运动为台湾的贸易发展带来了机遇,台湾在洋务运动期间贸易一直呈顺差状态,并且这种状态呈上升趋势,而同时期的整个中国的对外贸易却呈逆差状态,并且这种状态的趋势不断加强。两个地区的对外贸易状况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表明了在洋务运动期间,这个运动给两地社会带来的作用正好是一种反差。[※注]陈延杰则把闽台地区洋务新政联系起来考察,认为晚清闽台洋务新政开始的标志是福建船政局的创办,是变法自强的产物;新政的主体内容包括编练新式军队,建设闽台海防,发展新式工业,创办新式教育;资金不足是导致新政失败的重要原因。闽台洋务新政是该区域的第一次近代化,对闽台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制约,决定了新政最终不能走向成功。[※注]
以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为代表的洋务派人物是台湾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台湾洋务运动是在清王朝陷入严重的海疆危机,被迫转变治理台湾政策的特殊背景下发生的,主要经历了发生、发展、高潮三个阶段。方亮认为,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分别是三个阶段里洋务派经营台湾的代表人物。台湾洋务运动成效突出,与日、法两次武装入侵的强烈刺激下清政府重视台湾防务有关。清末台湾在洋务派近二十年的经营下,使边疆海岛新建的行省,成为全国洋务运动中的先进省份,为此后台湾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方英关注淮系人物与台湾近代化的关系,认为台湾的近代化运动起步稍晚于大陆,但其成效却超过了内地。在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中,除了起关键作用的首任巡抚刘铭传外,淮系人物中还有丁日昌、吴赞诚等,包括淮系首领李鸿章本人,都起到过不同程度的作用。[※注]刘根勤从捐款防务、赈灾、创办团练、垦荒、抚番、清赋、修造铁路、兴办洋务、保卫台湾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林维源的生平事迹,认为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著名绅士林维源居功至伟。[※注]台湾士绅对台湾近代化建设的贡献值得深入研究。
与开发进程相适应,台湾曾发生过经济重心北移的现象。台湾的经济重心何时从南部向北部转移,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台湾学者周宪文认为,台湾的经济开发,到嘉庆年间业已渐渐北移;林满红则明确提出,直到台湾通商口岸开放以前(即1860年以前),台湾的经济重心仍在南部。王长云提出商榷意见,认为米谷的生产及贩销在清代台湾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产稻中心与台米贩销中心的北移,便在很大程度上喻示着台湾经济重心的北移。通过对台米产销的考察,确定台湾经济重心之北移当始于乾隆时期,中经嘉庆时期,到道光年间便已基本完成。[※注]李祖基又对王长云的论文提出商榷,认为王文在论述经济重心北移时片面地强调了米谷产销的作用,完全忽略了蔗糖生产在台湾经济中的地位。由于台糖生产主要集中于台湾南部,所以讨论经济重心北移时非将其考虑进去不可,否则,单凭所谓米谷贩销中心的北移(即使实际上已经北移)就得出全岛的经济重心也已经北移的结论,很难令人信服。王文所述的乾隆年间,台湾中、北部已成为本岛主要产粮区,乾、道年间台米贩销中心已北移,以及道光年间北部地区在生产、交换消费方面已超过南部等论点缺乏事实根据,因而其提出的台湾经济重心之北移到道光年间便已基本完成的观点也不能成立。台湾经济重心开始向北移动和北移的完成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量变”虽然比较早就开始了,但直至同治年间台湾通商口岸开放时,台岛的经济重心仍停留在南部地区,“质变”并没有发生。岛上的经济重心开始移到北部地区,应在同治以后光绪初期的10年之间。通过南、北两口岸进出口贸易额的比较,可见从19世纪70年代中开始北部口岸的贸易额已渐渐接近于南部,表明北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已接近于南部,到1881年以后就超过了南部。这是台湾历史上南北两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注]另外,周翔鹤关于清代后期台北、基隆地区的山区和平原经济定量比较研究和杨彦杰关于清末同光之际台湾东部山地开发研究的论文,也值得关注。[※注]
关于晚清闽台经济贸易关系研究。黄福才认为,1840—1895年,经营闽台贸易的商人组织有外国洋行、台湾的郊行和福建沿海市镇的商行。闽台贸易范围,在福建以闽南特别是厦门为中心,在台湾则以基隆、鹿港、高雄为中心,外国洋行的介入逐渐控制了闽台对外贸易,对传统的闽台贸易关系产生了诸多影响。近代闽台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中,由于洋货的倾销破坏了闽台间原有的土货贸易。外国洋行、商人在闽台两省倾销洋货,竭力拓展市场,掠夺两省的物产、资源,根据国际市场之需要发展茶、糖、樟脑等物产的对外贸易。在此过程中,闽台市场与国际市场发生了更密切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闽台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闽台贸易关系的发展,加强了两省间的经济联系。[※注]丁振强考察了大陆农业科技,包括农业工具、农田水利、种植制度和农作物引种几方面,通过移民向台湾地区进行地域传播和社会传播的历史过程,并揭示其对台湾近代的农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贡献。[※注]徐心希撰文剖析了福建船政对于提升台湾经济地位,加强两岸经贸关系,以及推动台湾经济近代化的积极作用。[※注]
台湾自开港以后,海关税收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汤象龙编制台湾海关税收和税收分配(1862—1894)的两个统计表,为研究福建和台湾两省近代财政经济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注]邓利娟具体分析了19世纪下半期台湾海关税收的基本情形,认为总体上台湾海关税收增长很快,但各项税收增加的快慢极不平衡。(1)出口正税是台湾海关税收的最大项目;(2)鸦片税厘引人注目,进口正税为数甚微;(3)子口税收入为数最小,并且时有时无;(4)复进口半税及船钞为数皆小。台湾海关税收的第一个特点是南北海关税收增长速度不平衡,北快南慢是台湾贸易中心北移的结果;第二个特点是绝大部分税款征自洋船,华船所纳税款为数甚微,直到开港后期,才略有起色。但是,如汤象龙所谓没有华商纳税说明大陆与海岛之间贸易不很发达的观点值得商榷。[※注]
关于近代台湾对外贸易的研究,李祖基的相关论著值得关注。在系统探讨台湾开港前后贸易状况及近代台湾对外贸易基本结构的基础上,李祖基从五个方面探讨了近代贸易(1858—1895)对台湾社会经济的影响:(1)台湾成为列强倾销洋货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市场,使台湾的地方进出口市场由开港前的完全依赖大陆转变为基本上依赖国外;(2)鸦片贸易的掠夺和商业高利贷的盘剥,使广大下层劳动者身受西方商业资本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剥削,整个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更加严重;(3)外商的挤压使台湾本地的“郊商”生意受到很大损失,地位日趋降低;(4)出现了买办、民族商业资本家、工人等新兴阶级,给台湾社会的阶级结构注入了新的血液;(5)由于经济的发展、市镇结构的变化和人口的流动,台湾的地方经济重心逐渐由南向北移动,并趋于都市化。[※注]
清末台湾洋务运动与近代化的一些具体研究。晚清台湾军事变革与大陆军事变革息息相关。韩文琦认为,“御外侮”的台湾防务观是晚清台湾军事变革的动因;“师夷技求自强”是晚清台湾军事变革的主线;台湾社会的综合开发是晚清台湾军事变革的基础。晚清台湾军事变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并在日后的抗日保台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注]开矿山是重要的洋务事业。郑泽清考察沈葆桢与台湾基隆煤矿的开发,认为沈葆桢为了开发台湾基隆煤矿,力奏台煤出口减税,并奏准聘请外国矿师和采煤技术人员,引进西洋先进的机器采煤技术,使台湾基隆煤矿的开发进入施工、生产阶段,为开发台湾做出了贡献。[※注]潘君祥进一步论述基隆煤矿的经营及其出现弊端的原因,以及虽经刘璈、刘铭传大力整顿而终归失败的结果,认为即使是崭新的机器和技术,在落后的管理体制下,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在清季,腐朽的生产关系已根本不能容纳较为先进的生产力,这是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深刻的内在原因,基隆煤矿引进先进生产技术的失败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注]孙海泉在描述台湾煤矿的近代化历程之后,指出其近代化的标志是,技术设备的更新和经营方式的改变,以及企业经营性质从官办到官商合办的转变。官商合办的出现是中国近代民用企业从官办到商办过渡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脚印。[※注]修铁路也是重要的洋务事业。谢小华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中选辑《光绪年间台湾修建铁路史料》(《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为研究清末台湾铁路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台湾铁路的修筑是清末洋务派在台湾开展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清朝政府内外交困、积贫积弱的情况下,筹建这样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如何解决资金问题一直是困扰着主办官员的中心问题。蒋宗伟考察了清末台湾铁路修建过程中的经费筹措问题,认为丁日昌因无经费可用而未及铁路修筑就憾然离去;刘铭传为筹集筑路资金四处奔走,但最终还是因经费不足而不得不改变原先的工程计划;到邵友濂时,更是面临经费紧张的局面,虽然最后千方百计完成了剩余段的铁路修建,但这与最初的筑路计划相差甚远。为修建台湾铁路而进行的筹集资金活动反映了当时在台湾进行洋务运动的艰辛。[※注]
近代文教事业往往与西方宗教传播关系密切,台湾也不例外。林金水主编《台湾基督教史》(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在详细描述英国和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在台湾传播的过程中,不少内容涉及台湾近代文教及医疗事业的发展。刘凌斌专论基督教会与晚清台湾教育事业的关系,认为晚清30多年间(1860—1895),尽管教案频发,但英国和加拿大基督教会在台湾进行的传教事业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与此同时,基督教会在台湾创办了近代教育,设立各类学校,推广白话字、创办报纸等。教会教育引进西方先进教育观念和方式,客观上对晚清台湾教育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注]创办中外文报刊,是19世纪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的重要宣教事工和传教手段。陈才俊考察了台湾最早的报刊——《台湾府城教会报》在清末创办的基本史实及其发展历程,认为《台湾府城教会报》虽是以传播教会信息、沟通信徒灵修、开阔教友视野为主旨而创办的,但其所刊载的内容却异常丰富,所反映的文化也相当多元,而且充分显现出现代报刊的特征。它是研究台湾教会史、社会史、交通史、语言史、文字史、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的活档案。[※注]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