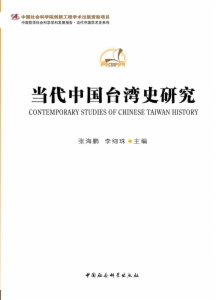三 台湾建省与刘铭传研究
|
来 源
:
|
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6 | ||
|
摘 要
:
|
作为清朝版图的一部分,台湾与大陆命运相连,既不免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同时也开始步入近代化的历程,最终却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被迫割让给日本。台湾近代史是中国近代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关于台湾近代史的研究,杜继东曾撰文进行较系统的考察[※注],本书拟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全面论述。陈旭麓认为,台湾建省是清季认识台湾的战略地位及其危机所采取的重要步骤,历史的责任由洋务派承担,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洋务派为加强海防和建设台湾,推动台湾建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湾的近代化。随着台湾近代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闽台教育交流逐渐实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新的闽台教育关系。 | ||||||
|
关键词
:
|
防务 台湾 海防 中法战争 抗法 教案 大陆 军民 政策 刘铭传 传教士 |
||||||
在线阅读
三 台湾建省与刘铭传研究
字体:大中小
台湾建省是在西方列强武力侵逼之下清政府加强控制台湾的需要,也是台湾近代化发展的需要。这是清朝治台史和台湾历史上的大事,对于清朝政府加强治理和开发台湾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政府于光绪十一年(1885)决定建台湾为行省,但台湾建省之议最早始于何时尚存疑点。一般认为是先由沈葆桢建议,后由左宗棠奏请,时间在清末同光时期。台湾学者盛清沂从《明清史料》发现清朝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吴金奏折,认为台湾建省之议最早始于乾隆二年(1737),比清末说早一个半世纪。许良国进一步申论,指出吴金奏折之所以未被清廷采纳,与清初朝廷在治理台湾问题上所持的消极政策有关,但确是开台湾建省奏议之嚆矢。[※注]
清末台湾建省从动议到决策有一个过程。同治十三年(1874),因日军侵犯台湾,东南海疆出现危机,清政府内部展开了一次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使清政府开始重视台湾在东南海防上的重要地位,台湾的防务政策也从过去的防内为主转变为御外为主。为了加强对台湾的行政管理,沈葆桢首先提出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的新方案,此后福建巡抚及其他廷臣又先后提出巡抚分驻、总督移驻、简派重臣督办、改设台湾巡抚等不同方案,而清廷则实行闽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的方案。三年后,又恢复旧章,仍实行督抚轮赴台湾巡查的方案。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在清政府内部又一次展开关于加强海防问题的讨论,进一步肯定了台湾在东南海防中的重要地位。在此新形势下,左宗棠重议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旋奉旨允准,翌年改为福建台湾巡抚。光绪十三年(1887),添设府县,建省规模粗具。陈在正系统地考察了各种治理台湾政治体制形式提出的背景及其演变过程,并充分肯定台湾建省具有加强台湾及东南沿海的海防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积极作用。[※注]陈旭麓认为,台湾建省是清季认识台湾的战略地位及其危机所采取的重要步骤,历史的责任由洋务派承担,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洋务派为加强海防和建设台湾,推动台湾建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湾的近代化。[※注]白纯、季云飞分别撰文缕述台湾建省的历程,从乾隆时期吴金动议到光绪时期正式建省的决策,表明清政府对台湾在中国海防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及其加强海防建设的重要意义。[※注]
台湾建省涉及方方面面,尤其与日本侵台及中法战争直接相关。杨彦杰着重论述了中法战争对台湾建省的影响,认为台湾建省是在中法战争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从建省的提出,到建省的过程,直至最后的结果,无不展现这场战争带来的深刻影响,而这些影响又使台湾建省具有明显的融筹防、建设于一体并不同于一般省份的特殊制度的特征。就清政府对于台湾建省的态度而言,也有一个从积极到消极的转变过程。建省初期的积极态度表明其对台湾在海防上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建省后期的消极态度则给台湾建设大局带来了不良影响。[※注]白纯则具体论述了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至中法战争时期,清政府官员袁保恒、沈葆桢、丁日昌、左宗棠、刘铭传等人有关台湾建省的主张,认为台湾建省是在当时国家面临严重外侮内患的背景下,尤其是在日本侵台事件和中法战争的直接冲击之下完成的,也是众多晚清爱国志士在强烈的忧患意识驱使下努力奋斗的结果。将台湾建成行省,对于加强中国东南海防,加速台湾的近代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注]
台湾建省由闽台分治而成,建省进一步加强了闽台关系。吴玫考察了闽浙总督杨昌浚与台湾建省的关系,认为通过杨昌浚与刘铭传的协商,台湾辖地的划分、省会的确定、人员的安排、职权范围的划分、经费的分配、澎湖等地的海防建设都已基本完成,事实上完成了闽台分治,台湾建省的各项工作稳步走上正轨。[※注]汪毅夫探析了清代台湾建省以“‘甘肃新疆’之制”为模式,在建省后称“福建台湾省”,仍然在教育行政、财政、幕府制度等方面同福建保留了若干行政上的关系,认为官方的行政区划和行政设置加深和加重了台湾建省初期闽台之间的关系。[※注]
台湾建省是清政府在列强的环环紧逼下所做出的战略决策。清政府在推行这一决策的过程中得到了广大社会力量尤其是台湾地方精英的强力支持。郑榕撰文以台北板桥林维源家族为例,考察地方精英在台湾建省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正是由于国家与社会双方的良性互动才使得台湾建省得以顺利实施。[※注]郑镛撰文认为台湾建省前后的19世纪70—90年代,台湾巨族板桥林家、雾峰林家等相当活跃,成为国家与大陆移民、原住民对话与沟通的中介。围绕财政、兵源、水利诸问题,巨族士绅或输财物,或组土兵,或修水圳,为台湾建立行省,抗御外敌,开发建设出力尤巨。晚清的台湾地区正是通过国家与士绅阶层的互动来实现社会网络的通畅,并逐步走上近代化道路。[※注]
台湾建省以后情况如何,也是学界关注的问题。闽台分省之初,经闽浙总督杨昌浚与台湾巡抚刘铭传反复协商,决定由福建每年协济台湾饷银44万两,以5年为期。邓孔昭具体考察了福建协饷对台湾海防与新政建设的作用,认为福建协饷在建省初期的台湾财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保证建省初期台湾财政的正常运转、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关于台湾建省以后每年的财政收入,以往学界采用的数据,主要是根据刘铭传的传记材料,或连横《台湾通史》度支志中“建省以后岁入总表”,而得出300万两或440万两的数字。邓孔昭考证认为,不论是300万两或440万两都是错误的。实际上,当时台湾的财政收入,每年只在200万两上下。对于第二任台湾巡抚邵友濂,以往学界多有批评指责,认为他尽废刘铭传创办的新政。邓孔昭撰文认为,对邵友濂的评价,实际上关系到对刘铭传的评价及那个时期台湾历史的评价。如果说邵友濂尽废了刘铭传的新政,使其成果荡然无存,那么刘铭传的新政对台湾历史的实际影响就必须重新估量。事实上,正是邵友濂基本上维护了刘铭传新政的成果,使台湾这样一个新建的行省,在短暂的十年中,不但各项事业粗具规模,而且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还走在大陆一些省份的前面。因此,在研究台湾建省以后的这段历史时,随意贬低邵友濂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注]
刘铭传是台湾建省的关键人物,又是首任台湾巡抚,一生事业主要在台湾,故学界相关研究论著最多。关于刘铭传的生平事迹,可参阅姚永森著《刘铭传传——首任台湾巡抚》(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徐万民、周兆利著《刘铭传与台湾建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则主要以台湾建省为中心,论述刘铭传开发与治理台湾的贡献。1985年、1995年、2005年,安徽学界相继举办“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逝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先后出版会议论文集《刘铭传在台湾》(萧克非、仲冲、徐则浩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集》(本书研讨会组委会、学术委员会编,黄山书社1998年版)、《刘铭传与台湾建省》(程必定主编,黄山书社2007年版),集中展示了有关刘铭传研究的最新成果。马昌华、翁飞点校《刘铭传文集》(黄山书社1997年版),则为刘铭传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资料。
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事业的总体评价。姚永森详细论述了刘铭传抚台期间的所作所为,认为刘铭传是一个积极抵抗外国侵略势力的爱国疆吏,一个巩固祖国统一事业的促进派,一个台湾近代资本主义开发的先驱者。[※注]戴逸提出从大清史角度看待刘铭传保台建台的意义,认为刘铭传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将领,有远见的政治家,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奠基人。他为维护祖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为保卫台湾和建设台湾,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他身上,爱祖国和爱台湾得到了高度统一。[※注]来新夏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必一分为二,而应择其一生中的重要阶段作评论。刘铭传一生三件大事:镇压农民起义,抗法保台,开发台湾。其中,开发台湾不仅是刘铭传事业的最亮点,也是晚清时期最值得纪念的历史光彩,更是台湾史上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对历史人物虽然要作全面的历史的评价,但应从大节着眼以论功过。刘铭传曾有镇压太平军、捻军的罪过,但他也有抗法保台、开发台湾的重大民族功绩,足以成为在中国近代史册上熠熠发光的历史人物。[※注]
刘铭传对台湾建省持谨慎的态度,并为建设台湾采取了积极的举措。光绪十一年(1885),清政府下令台湾建省。可是,被清政府任命为台湾第一任巡抚的刘铭传却认为“台湾暂难改省”,提出了趋缓的台湾建省主张。邓孔昭认为,刘铭传的意见被清廷驳回之后,其所提出的台湾建省方案,仍然秉持了一贯的务实思想,强调抚“番”、清赋、设防这些基础性的建设必须优先,而城垣、衙署的建设可以稍缓。在此方案的主导下,台湾建省工作稳步进行,使一个新建的省份在不长的时间里成为全国比较先进的省。[※注]陈碧笙认为,台湾建省,标志了清政府对台湾的认识已从“患自内生”转变而为“患从外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台湾既然是为了适应国防的需要而建省,则建省以后的一切兴革必然要以国防的整顿和建设为中心。刘铭传初期提出了“设防”“练兵”“抚番”“清赋”等四项措施。前三项属于国防方面,都符合当时形势的要求,所以能够顺利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后一项为财政,尽管清赋触犯到地主豪绅的利益,任用人员又有勒索害民、激起民变之事,但所增加的收入高达四五十万两,比过去多了好几倍,应该承认这些改革还是成功的。可是,在此以外所实行的改革,除了铺设海底电线、创办邮政和建设台北略有成效之外,大部分都含有资本主义因素与封建主义因素斗争的性质,牵涉到社会制度问题,就不是刘铭传所能为力的了。这些有关实业、交通方面的兴革,牵涉到究竟是商办还是官办,牵涉到外商的利益,与其他官僚集团的关系,能否摆脱封建官僚作风、习惯的束缚,等等,问题就远为艰巨而复杂。刘氏思想上虽然具有资本主义倾向,但不可能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在屡次遭受申斥之后,只好称病求去了。[※注]吴玫考察刘铭传在台湾建省后的财政措施,认为其为了台湾的建设而采取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举措,如整理旧财政,举办公营事业,申请援款、借款,发动台湾富绅捐款,节省军费开支等,增加了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注]黄天祝专论刘铭传在台湾实行的丈田清赋,认为使台地之财以供台地之用,是刘铭传丈田清赋的指导思想,其丈田清赋,是为了抵御外侮,以裕饷需,保卫海疆,建设台湾。刘铭传的丈田清赋,大致可以分为设立机构、编查保甲、清丈土地、改定赋税和发给丈单五个阶段。通过丈田清赋,清丈的民田达400余万亩,比原来田额增出四倍,田赋实征额由原来每年的183366两增至674468两,净增近50万两。刘铭传对田赋的整顿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注]陈国强专论刘铭传的台湾少数民族政策,认为刘铭传为了促进台湾及台湾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在经济上,继续“开山抚番”,扩建抚垦局,任在籍绅士林维源为总办,并创设经营脑务局,课征茶厘金等以充“抚番”经费;在政治上,恩威并施,广泛招抚“土番”归顺,对不愿服从的反抗者,给予坚决镇压;在文化教育上,颁发条教,设番学堂,培养青少年,提高族人的文化教育水平,也加强了民族团结,对于民族地区的开发做出了贡献。[※注]
台湾建省具有加强台湾海防与促进台湾近代化的双重功效,其间刘铭传的贡献最大。李友林考察刘铭传与台湾防务,认为刘铭传的台防思想以留台、保台为前提,其核心内容是以大陆为后盾的台闽联防思想,在台防务又以陆守为主而重点设防。据此台防思想,刘铭传在台期间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台湾防务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有练兵整军、划分防区、兴办军事工业、添修军事设施四项,为巩固台防、重建台湾防务体系做出了积极贡献。[※注]陈婷、杨春雨指出,刘铭传依靠大陆人民的支持,以维护国家统一为建设台湾防务的根本目标,积极发展台湾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铁路、通信建设和矿产资源开发,培养人才,执行以抚为主的民族政策,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将台湾的防务置于一个比较稳固的基础上。在军队建设方面,裁汰冗员,大力购置西方军械,按照西洋的样式编练军队,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还根据台湾的具体地理状况和假想敌人进行军队布防和修建军事设施,在台湾防务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有效地防御了侵略,巩固了祖国的统一。[※注]张燕清认为,刘铭传基于“宁以外备为重”的治台思想,采取整训防军、添设军事设施,筹建电讯、邮政事业,创办台岛铁路,购置轮船、器械等措施,加强了台湾的海防建设,促进了台湾人民凝聚力的形成,密切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并由此揭开了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序幕。[※注]王生怀认为,刘铭传继承了沈葆桢筹划台湾海防的思想:讲求武备,力主保台;善后筹划,防患于未然;依托大陆,台闽联防;派大员常驻。由于时代、形势的变化,刘铭传的海防思想又有所发展:一是入手点不同。沈葆桢的思路是开发台湾、建设台湾,然后以台湾的经济发展来加强台防力量的长线筹防方案;刘铭传则直接突出防务的重要性,把台湾的开发与建设都立足于防务。二是布防的重点不同。沈葆桢在台布防时把侧重点放在台南;刘铭传进行调整,确定把战略重点放在台北,认为保住了台北府,就是保住了台湾。[※注]苏小东探讨刘铭传的海防思想与实践,认为刘铭传虽然也曾就海防及其相关问题有过全面系统的论说,但其认识水平显然不及同时代之佼佼者。关于台湾在中国海防中的战略地位,他是在领导抗法保台、建台的过程中逐步加深认识的,并以首任台湾巡抚之地位不遗余力地将其思想主张付诸实践,开创了包括海防在内的台湾近代化新局面。[※注]
关于刘铭传与台湾洋务事业及近代化的关系,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李莉通论刘铭传与台湾近代化的关系,认为身为洋务派的刘铭传在抚台的七年时间里,不仅加强了台湾防务,而且开始了台湾近代化进程。政治上,刘铭传通过清赋、抚番、分治添官使台湾成功地完成由一府向一省的转变,并营造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经济上,刘铭传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机器,兴建一批近代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新式邮电通讯业,同时对外贸易得到蓬勃发展,改变了台湾整体经济面貌,使台湾民众的生活开始具备近代性质和意义;文化教育上,刘铭传兴办西学堂、电报学堂等新式学堂,使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得到传播,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有效推动台湾近代化的发展。[※注]近代化建设具体落实到邮政、煤矿、铁路与新式教育等方面。中国近代自主的新式邮政起于何时,一般邮政史论著均认定其始于邮政官局正式在西方列强把持的海关中成立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潘君祥通过对刘铭传在台湾的邮政改革进行详细考察,认为早在邮政官局成立前八年,即1888年,刘铭传就在台湾创建了独立于当时殖民海关邮政部门的邮政局。[※注]关于刘铭传在台湾巡抚任期内拟将基隆煤矿交外商承办一事,学界看法颇有分歧,或曰出卖祖国矿权、民族利权,或曰敢于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或曰最早提出关于经济特区的设想。何平立、戴鞍钢认为,无论从促使刘铭传做出将基隆煤矿交于外商承办的主观动机与方案本身,还是从其一贯思想与活动,都不能得出刘铭传此举是出卖民族利权的结论,但必须注意刘铭传这个设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与社会背景下并不可行,而且对中国矿权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是由于刘铭传囿于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同时,也不能用现代的眼光拔高刘铭传,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屡遭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与掠夺的历史条件下,根本就不存在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更不会有创设经济特区的设想。[※注]陈九如认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注]沈和江认为,刘铭传抚台期间,以其对铁路之于台湾海防和经济建设作用的深刻认识为思想基础,把兴办铁路作为治台要务之一。在台湾铁路建设的筹备、施工和铁路竣工后的运营等各个环节上都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台湾铁路的修建,成为台湾近代化进程的重大标志,开启了中国自行筹集资金兴办铁路的先河。[※注]郭剑波简要考察了刘铭传在台湾进行教育实践的大气候和小环境,并把他在台湾的教育实践归纳为继续维护科举取士制度、创办西学堂以培养新式人才和对少数民族推行“汉化教育”三个方面,认为刘铭传的教育实践活动对台湾近代化和少数民族人民的抗日斗争有积极意义。[※注]陈晓君探讨了刘铭传担任台湾巡抚期间,福建与台湾的教育交流情况及其历史影响。重点研究当时台湾在中国大陆特别是福建的影响下,进行的延续传统教育、创设新式教育、发展番社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改革及其取得的成就,深入探讨闽台教育的深厚历史渊源,认为刘铭传抚台期间所取得的一系列教育改革的成效,是基于积极开展闽台教育交流、借鉴福建的实施经验而取得的。随着台湾近代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闽台教育交流逐渐实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新的闽台教育关系。[※注]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