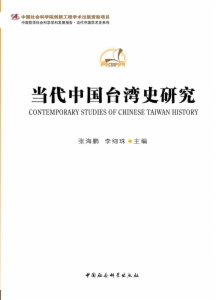第三节 社会文化变迁与“殖民地现代性”
|
来 源
:
|
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 | ||
|
摘 要
:
|
大陆学者对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开始时间也较晚,但研究成果较之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要多,研究对象也涵盖了社会、教育、宗教、思想文化等多项专题。其他学科的介入,使社会文化史领域有些议题得到更深入的讨论,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文学史界对“殖民地现代性”的深度辨析,触摸到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殖民性”与“现代性”相互并存、相互纠葛的一面,对把握该时期台湾社会文化的内涵有积极意义。对大陆台湾史学科来说,还需要从扎实的史料工作入手,辩证地分析延续与断裂、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等多重命题相互纠葛的局面,如此才能真正把握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中的“殖民地现代性”特质。 | ||||||
|
关键词
:
|
新文学 殖民当局 台湾人民 台湾 殖民地 佛教 殖民政府 台湾社会 宗教 民族主义 中华文化 |
||||||
在线阅读
第三节 社会文化变迁与“殖民地现代性”
字体:大中小
大陆学者对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开始时间也较晚,但研究成果较之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要多,研究对象也涵盖了社会、教育、宗教、思想文化等多项专题。从研究群体来说,“跨界”的情形比政治史和经济史领域更为突出。不少研究者来自教育学、文学等非台湾史学科,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史研究因此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其他学科的介入,使社会文化史领域有些议题得到更深入的讨论,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文学史界对“殖民地现代性”的深度辨析,触摸到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殖民性”与“现代性”相互并存、相互纠葛的一面,对把握该时期台湾社会文化的内涵有积极意义。不过,研究群体的跨学科特点,也使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史研究整体上呈现出基于一手资料的实证研究相对不足的局面,对有些问题的讨论也因此还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现有研究中,长时段、大视野的考察也较为欠缺,因而鲜少能同时把握该时期社会文化“变”与“不变”的双重特性。还有些研究仅关注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被“殖民”的一面,对交织在其中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关注不够。对大陆台湾史学科来说,还需要从扎实的史料工作入手,辩证地分析延续与断裂、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等多重命题相互纠葛的局面,如此才能真正把握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中的“殖民地现代性”特质。
一 社会变迁与移民问题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社会发生了种种变化,并在经历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征。对于日据时期台湾社会变迁,汪思涵借助“殖民地现代性”这一概念,从文化转变、教育政策、原住民生活、殖民地建设等方面,观察现代性的力量如何渗透进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而揭示日据时期台湾民间社会不仅充斥着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纠葛,同时还存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这一复杂情形对光复后的台湾社会依然有深远影响。[※注]
社会转型在社会习俗层面会有所体现,尤其是殖民当局曾有意识推动社会习俗的变革。李跃乾围绕殖民当局的断发放足政策,阐述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风俗如何发生改变。[※注]王莹则从衣着服饰、食物消费、住宅起居、行旅交通、新年习俗等角度,介绍了日据时期台湾社会习俗的变化。[※注]
社会转型也深刻影响到社会精英阶层。陈韵根据其不同的活动情况,将战时台湾知识分子划分为皇民派、抗争派、中间派三大类型,并总结他们不同的社会角色及其对台湾社会意识的影响。[※注]
唐次妹注意到日据时期台湾城镇的变迁,指出殖民当局为了满足殖民统治与资源掠夺的需要,先是在台湾城镇大力推行基础建设,继而通过实施“市区改正”计划,对台湾城镇进行改造,使台湾城镇的内部结构及其形态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中国式的台湾城镇的发展模式因此中断,城市发展走向日本及欧美近代化城市模式。在迈向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同时,台湾城镇也被改造成为适应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需要的大小中心据点。[※注]
在关注社会转型的同时,也有学者注意到传统社会结构延续性的一面。陈小冲通过对宜兰地方社会经济与教育文化状况的分析,指出在社会经济领域,宜兰地方社会殖民地化的进程相对缓慢,殖民政府对地方经济的改造,尚未触动宜兰地方社会的底层结构,传统经济模式依然是当地社会的主流。在教育文化领域,无论是教育体系,还是当地社会权力结构,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整体来说,宜兰地方社会的变化较小,传统社会底层结构依然延续,殖民地化对宜兰地方社会的影响还相对有限。[※注]
台湾是个移民社会。在日本占领台湾之前,来自闽粤等地的大量大陆移民是台湾开发的重要力量。到了日据时期,大陆人民移入台湾受到总督府的政策限制,闽粤民众移民台湾被迫中断,台湾的移民问题因此呈现出新的特征。陈小冲研究了《清国人入境台湾条例》出台的背景和执行等情况,指出日本占领台湾后,总督府刻意限制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闽粤人口迁移台湾的潮流因而中断。该条例出台后,大陆对台湾的影响力逐渐下降,来自日本的影响力则逐渐加强,台湾与大陆被强制分离,对台湾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陈小冲总结了日据时期台湾移民问题的新特征,指出由于殖民政府实施两岸隔离政策,台湾的移民问题表现为由日本占领之前的自西向东的单向度移民,转向多维方向移民态势发展,这些移民方向包括从北向南的日本对台移民、自西向东的大陆对台移民,以及自东向西的台湾对大陆和南洋移民。[※注]
在限制大陆民众赴台的同时,日本殖民政府鼓励本国人口移入台湾。吴本荣撰文指出,日据时期殖民政府为了掠夺台湾资源、转移国内过剩人口、同化台湾人民,实现长期占领台湾的目的,鼓励本国人口移民台湾于是成为对台殖民统治的重要一环,其中,农业移民又是移民的重心。鼓励本国农业人口移民台湾除了前述因素外,还有移植本国农业技术,并以台湾为跳板继续“南进”,实现向南洋扩张的目的。日据时期日本对台农业移民分官营和私营两种,即分别由总督府和糖业公司出面招徕。由于种种原因,日据时期日本对台农业移民计划并不成功,在台日本人中,以公务员、自由职业者及工商业者为主,农民数量极少。[※注]
尽管殖民政府有意隔断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联系,但两岸之间依然有人员往来。陈小冲对日据时期大陆劳工赴台即有专门探讨,指出赴台大陆劳工大多来自闽粤浙等省份,赴台后主要从事底层劳役,并受到日本殖民当局和资本家的压榨。为维护自身权益,赴台大陆劳工也曾组织劳工团体,如中华会馆及其下属各分馆、大陆劳工工会组织等,进行互助自救,为台湾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注]黄俊凌根据福建省所藏档案资料,对日据时期福建在台“华侨”,也就是赴台闽籍移民进行了研究,指出在福建赴台民众中,除少数人加入日本籍,成为“日籍台湾人”外,多数人仍保留中国籍,成为所谓在台“华侨”。和日据之前的大陆移民一样,该时期福建赴台民众,多数也是出于谋生需要前往台湾,还有一小部分是赴台求学,或为了继承在台祖辈或亲属的产业。闽籍在台“华侨”的身份大多是劳工,在台湾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均不高,生活状况也普遍艰苦。[※注]
另外,胡澎以台湾“爱国妇人会”在战时的活动为线索,考察日本殖民者如何对台湾妇女进行“皇民化”改造,进而思考性别、殖民主义与民族认同等问题。[※注]朱云霞同样关注日据时期的妇女问题,认为日据时期台湾妇女解放运动的精神动力来自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而其实践动力则来自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运动。同时,日据时期台湾妇女解放运动,在精神层面是被启蒙、被引导,在实践中则属于被推动,女性领导者很少,性别平等的议题也未得到关注。日据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被纳入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运动之中,未发展成独立的社会运动。[※注]汪毅夫则就台南石姓某甲的户籍誊本记载的收养婢女、婚嫁与子女情况、女子缠足情况等信息,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社会存在的一些情形。[※注]
二 教育
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在台湾建立起新的教育体系,并大力推行日文教育,以同化台湾人民。关于日据时期的教育,大陆台湾史学界与教育学界均有关注,并有较多成果面世。
钟安西将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划分为四个时期:1895—1898年为草创期、1898—1919年为成型期、1919—1937年为扩展期、1937—1945年为蜕变期。他又将教育体系划分为初等普通教育(小学教育)、高等普通教育(中学、大学先修教育)、实业教育(初等、中等教育)、专门教育(大专教育)、师范教育及大学教育六大类。在分析各时期及各类别教育体系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将殖民教育体系的特点归纳为:始终为殖民政策服务,带有强烈的“同化主义”色彩;明显的愚民政策痕迹;日台人双轨差别教育等。对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可取的一面,如在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上均有若干建树,也予以肯定,并指出日据时期的大专教育乏善可陈。[※注]
对于日据时期台湾教育的分类与分期,陈小冲有不同认识。他将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四大类。在时段上,则划分为三个阶段:1895—1921年为创始期,教育机构逐步完备,实施日台人教育分而治之的双轨制;1922—1941年为发展期,完整的教育体系基本建立,中等以上学校实行日台人共学制;1941—1945年为成熟期,取消公学校与小学校的区别,实施义务教育制度,近代化教育体制形成。陈小冲还对殖民教育体制下台湾人的反应进行了分析,认为殖民教育体系的建立,主观上是为了同化台湾人民且培养中下级技术人才,客观上引进了新的教育观念和科技文化知识,对台湾人有有利的一面,台湾人民对殖民教育体系因此既有抵触也有接纳。[※注]
龚放将日据时期的教育政策演变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同化教育”和“差别教育”为特征的“渐进主义”时期(1895—1918年);二是名实难副的“日台共学”和“内地延长主义”时期(1919—1936年);三是“战时教育”与“皇民化”时期(1937—1945年),并对各阶段的教育政策进行了分析。[※注]龚放的分期法与前述钟安西的分期法较为接近。
陈荟、段晓明对日据时期学校教育体系的分类则与陈小冲的前述分类法比较相似,他们将日据时期学校教育体系分为学前教育(幼儿园)、初等教育(小学校、公学校、山地教育所)、中等教育(高等普通学校、实业学校、大学先修科或大学预科学校)、师范教育(小学师范部、公学师范部)、高等教育(专门学校、综合性大学)五大类,不同之处仅在将幼儿园阶段也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内。他们还将日据时期学校教育体系的实质归纳为奴化教育、“差别化”教育、教师结构日籍化、把持师范教育等几个方面。[※注]
薛菁认为日据时期的台湾教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具有殖民特性,以教育为手段,达到同化台湾人民、方便殖民统治的目的;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引进了近代西方教育体制,促进了台湾教育体系的近代化。[※注]杨晓对矢内原忠雄的殖民地教育理论进行了辨析,指出矢内原忠雄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不够彻底。在杨晓对矢内原忠雄教育理论的辨析背后,同样是对殖民地教育具有双重性的理解。[※注]
杨晓对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确立殖民教育方针的过程进行了梳理,从初期的“以无方针为方针”到同化方针,再到日据后期的皇民化方针,认为不同时期殖民教育方针的变化反映了殖民政策的变化,并形成殖民教育语境,对台湾人民造成精神奴役与现实伤害。[※注]汪婉从分析首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殖民地教育观入手,指出由于受到日本近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影响,日据初期总督府并未实施彻底的同化政策,而是采取日本人、台湾人和原住民三个系统的“差别教育”和“隔离教育”政策。不过受伊泽修二的同化教育主张的影响,总督府在一开始就明确以初等教育为重点、以日语教育为中心的教育政策,奠定了后来同化教育、“皇民化”教育的基础。[※注]都斌探讨了日据时期台湾语言教育,也就是“国语”(日语)教育政策的产生、发展及影响,指出“国语同化”是日据时期殖民当局同化教育政策的重要内容。[※注]周翔鹤根据20世纪30年代编撰的街庄志,观察位于台北市周边、属于乡镇农村地区的板桥街、中和庄、三峡庄以及莺歌庄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状况,从而从地方社会层面观察日据时期台湾的教育及其与殖民当局同化政策的关系,指出殖民当局通过早期的公学校教育以及后来的中等教育、专科教育等,培养了大批社会精英和中坚分子,之后又通过这些社会精英和中坚分子展开了更广泛的社会教育,从而实现利用教育手段对台湾人民的同化。[※注]
殖民教育政策影响台湾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传统书房(私塾)的没落。黄新宪认为,台湾的书房对于保存中华文化、维护汉民族特性、培养造就爱国知识分子,有重要意义。[※注]刘丽霞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私塾教育的发展阶段、特点及其历史文化意义,指出由于受到殖民政府的不断打压、限制和取缔,日据时期私塾生存极为艰难。[※注]陈小冲分析了殖民当局如何通过书房调查及一系列收编措施,对传统书房教育进行改造、打压,指出由于日据初期殖民地教育面临传统书房的激烈竞争,“国语”推广计划也受到传统汉学教育的挑战,台湾总督府于是在全岛开展书房调查和整顿工作,对书房进行所谓改良,在书房增设日语课程,并对书房教师进行包括日语、算术、礼节三科在内的“职业培训”,使书房经营方向向公学校靠拢。殖民政府对书房教师也进行收编,通过延聘有名望的书房教师到公学校教授汉文的方式,进一步削弱书房的竞争力。在殖民当局的政策打压下,台湾传统的书房教育在1922年后日渐走向衰落。[※注]
对于日据时期各级学校教育,龚放撰文探讨了日据时期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及其殖民地性质,并重点介绍了台北帝国大学的设立情况。[※注]黄新宪从教育学角度就日据时期台湾各级教育发表了多篇论文,《日据时期台湾小学校初探》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小学校的发展源流及其主要特征,《日据时期台湾公学校论》考察了公学校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其主要特点,《日据时期台湾女子初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探讨》《日据时期台湾女子中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探讨》《日据时期台湾女子留学日本考》则考察了各级女子教育的情况及台湾女性留学日本的情况,《日据时期台湾籍民教育探微——以福州和厦门为中心》对福建的台湾籍民教育进行了研究,《日据时期台湾职业教育探讨》则对日据时期的职业教育,也就是实业教育,从政策与体制角度均有论及。[※注]在其专著《台湾教育:从日据到光复》中,黄新宪对日据时期台湾教育更有全面论述,其内容涉及伊泽修二对日据时期台湾教育的影响,“皇民化”教育、书房教育、公学校、小学校、女子教育、以“台北帝国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少数民族教育、台湾籍民教育、留学教育以及音乐教育、体育教育等。[※注]
另外,吴丽仙对由雾峰林家创办的民间区域性启蒙团体雾峰一新会的教育活动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在重视妇女教育、提倡体育与艺术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等方面的贡献值得肯定。[※注]蒋宗伟讨论日据时期台湾青年赴大陆求学的情况,并对他们在大陆参与抗日与收复台湾工作的经历尤为关注,指出他们中大部分人通过在大陆的学习和实践,认识到台湾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注]
三 宗教
对日据时期台湾各种宗教的研究,也是该时期社会文化史领域较为集中的议题。
翁伟志以长老会为中心,按台湾人民抗日斗争活动的阶段进行分期,分别考察基督教会的政治态度与政治立场,指出基督教会自日据初期就置身于中国人的抗日运动之外,并逐渐认同日本人的统治,乃至甘愿为日本人所用。日据时期以长老会为中心的基督教会无法融入台湾主流社会,与台湾教会的“本土化”水平不高有很大关联。[※注]林立强将日据时期基督教发展史划分为两个时期:从1895年到1930年,是信仰自由时期;从1931年到1945年,是宗教压制时期。日据时期基督教发展呈现出下述特点:一是以长老会的发展为代表;二是地域发展不平衡,南部逐渐超越北部;三是发展阶段不平衡,1930年以前是良性发展时期,1930年以后是停滞时期;四是教会逐渐组织化;五是建立了完整的教会人才培养体系。日据时期,台湾基督教由于丧失了清代不平等条约保护下的传教特权,并受到是否参拜日本神社等问题的困扰以及殖民当局的严密控制和监视,其传教吸引力逐渐弱化。到日据后期,基督教逐渐被殖民政府控制,成为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组织。[※注]
天主教也是由西方传入台湾的宗教,并与基督教一直存在竞争关系。王晓云、雷阿勇对比了日据时期天主教(主要是多明我会)和基督教长老会在台湾信徒数量与传教区域的增长情况,对日据时期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台湾传教过程中相互竞争并发生摩擦的原因做了分析,认为既有教义与门派分歧,也有现实利益冲突,还有对传教空间的争夺等。他们还将日据时期天主教会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1895—1913年为过渡时期、1913—1937年为发展时期、1937—1945年为阻滞时期,并分期考察了天主教会吸收本土信徒的情况,指出本土信徒的增加,促进了天主教会的发展,也对台湾社会产生很大影响。[※注]
和天主教、基督教等来自西方的宗教不同,佛教在台湾民间社会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并成为两岸文化一脉相连的纽带之一。为了割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同化台湾人民,佛教因此和教育体系一样,成为殖民当局改造的对象,力图使其日本化。陈进国指出,日本在占领台湾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宗教政策,试图从意识形态上控制与同化台湾。这些政策措施包括数次的宗教和旧惯调查,在斋教徒发动的“西来庵事件”后,又通过日本佛教各宗派与台湾本土佛教各派的联合,成立一些佛教教育机构和全岛性佛教组织。殖民统治后期,殖民当局更是推行“信仰皇民化运动”,强化日本化的宗教礼拜仪式和国家神道地位。日据时期日本佛教入台和殖民当局的一系列举措,使包括斋教和缁衣佛教在内的台湾佛教逐渐日本化,并对战后台湾佛教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殖民当局之所以竭力推动台湾佛教日本化,目的是通过铲除台湾固有的宗教习惯和信仰,确立对日本的国家和文化认同,从而解决其在台的“统治合法性危机”。[※注]王志平、吴敏霞考察了日据初期日本官方和非官方组织在台湾进行的一系列以佛教为中心的宗教调查,这些调查涉及日本佛教在台的布教、台湾寺庙僧侣、台湾原有习俗信仰、台湾佛教历史发展等。在宗教调查的基础上,殖民当局形成了其初期的宗教政策,对来台的日本佛教加以有限的控制和限制,对台湾旧有宗教实行有限的“放任主义”,这一宗教政策体现了其“旧惯温存”的殖民统治策略。日据初期的宗教政策确立了殖民当局对台湾宗教发展的统辖地位,对台湾传统佛教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影响,并为以后日本佛教在台湾的发展开拓了空间。[※注]吴敏霞还对日据时期台湾佛教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将日据时期台湾佛教区分为三大类,包括台湾固有的中国传统佛教、在家佛教(即斋教),以及由日本殖民者输入台湾的日本佛教。日据初期和中期,日本佛教努力进入台湾,并试图控制台湾人民的佛教信仰,但台湾传统佛教仍然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在台湾佛教中具有主体地位。斋教到日据中期则因受到殖民政府的严厉打击而有所削弱。日本殖民统治末期,由于殖民当局推行“皇民化运动”,包括传统佛教、斋教和日本佛教在内的三大佛教均遭到毁灭性打击。[※注]
尽管殖民当局试图通过宗教殖民割断台湾与大陆佛教界的联系,但两岸佛教往来并未就此中断。何绵山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僧人不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即使在1917年台湾开始独自传戒后,仍然有增无减地前往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戒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出两岸佛教界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有无法割断的联系。[※注]陈小冲考察了日本殖民当局以台湾为跳板,对福建进行宗教扩张的情况。他以外务部档案中有关日僧在闽布教的六则史料为基础,指出甲午战后来闽布教的日僧均来自台湾,台湾成为日本对闽实行宗教扩张的基地。日僧在闽的布教活动,得到台湾总督府在人力、财力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成为台湾总督府对岸扩张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些政策的目标既为了对外扩张势力,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台湾本身的统治。[※注]
范景鹏、马世英对1945年以前台湾的回教进行了回顾,其中提到日据时期,台湾回教受到殖民当局的压制,在“皇民化运动”中更受到严重打击,以致几乎断绝。[※注]
四 思想文化
在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最多,其涉及的内容又可以细分为若干个小的专题。
(一)关于文化抗争与民族认同
日据时期,殖民政府一直试图通过种种手段,割断台湾人民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其中就包括文化的手段。同时,台湾知识分子在文化战线展开了对抗日本殖民统治、保护传统中华文化的斗争。
林其泉较早撰文指出,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通过历史著作撰写、文学创作,以及运用戏剧和电影等方式,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注]通过创作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这在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中有突出表现。汪毅夫通过研究日据前期台湾文人王友竹、洪弃生、林痴仙、连雅堂等人的诗文,指出日据前期的台湾旧文学充分表现出抗日爱国的民族精神。[※注]黎湘萍将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置于民族抗争的大背景下,指出面对日本殖民政府通过长期推行文化统合措施、旨在彻底割断台湾与“原乡”(大陆)种种血脉联系的企图,台湾文学界沿着赖和、杨守愚等人于20年代开创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道路,以笔代剑,积极抵制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的“愚化、奴化和同化政策”,即使用日语写作,也依然完整保留了鲜明的本民族文化传统和强烈的“中国意识”及“台湾属性”。[※注]肖成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展现出的对妇女问题、农民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国民性问题、殖民体制问题等的批判,指出日据时期台湾作家创作的大量带有现实批判色彩的小说,是台湾人民反抗殖民暴政、追求祖国统一的文学见证。[※注]
除通过文学创作与殖民当局的同化政策相抗争,日据时期的民俗与歌仔戏等也蕴含了反殖民的精神特性。韩春萌通过考察台湾新文学中有关民俗的描写,揭示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对殖民当局扼杀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抵制。[※注]李立平探讨了日据时期台湾歌仔戏的民族性与“现代性”,指出歌仔戏的发展史,既是台湾人民的日常生活史,也是台湾人民反抗殖民的历史。[※注]
陈小冲对20世纪20年代以文化协会为中心进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进行了个案研究,指出台湾人民通过传播与保护中华文化,对抗日本殖民当局的文化同化政策,坚持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注]才家瑞按照历史脉络,对日据50年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进行了梳理,指出日据时期台湾人民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祖国的认同与忠诚。[※注]在《日据时期台湾人民保存汉文化运动》一文中,宋淑玉则通过对日据时期台湾汉学运动的研究,来看在殖民者的文化同化政策下,内心深处始终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的台湾社会各阶层,对汉民族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注]
蒋渭水是日据时期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杰出知识分子代表。陈小冲对蒋渭水的反殖民斗争思想进行了研究,以蒋渭水在总督府医学校、文化协会、民众党三个不同人生阶段为脉络,探讨其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思想与实践,指出在蒋渭水身上,凸显出对中华文化的强烈眷恋和身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自豪感。这一方面说明殖民当局试图将台湾人日本化的同化政策是失败的,另一方面也可证明所谓日据时期台湾走向“脱中国化”的“台独”史观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注]汪小平对20世纪20年代台湾文化协会启蒙运动中新知识阶层的民族论述进行了辨析,尤以蒋渭水的民族论述为考察中心,探讨了蒋渭水及其同时代知识分子对“民族”这一概念的思考及其对民族论述的建构。[※注]
朱双一对连雅堂、洪弃生、丘逢甲等台湾文人的文化民族主义论说进行了分析研究,包括其自强保种思想、地理环境和语言文字问题上的民族主义、植根于历史的民族主义以及有关中国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的论说等,指出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环,并且和祖国大陆的文化民族主义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主题、表现形态和话语形式。[※注]在《从旅行文学看日据时期台湾文人的民族认同——以彰化文人的日本和中国大陆经验为中心》一文中,朱双一又分析了包括叶荣钟、虚谷、洪弃生、施梅樵、庄太岳、赖绍尧、杨树德等在内的彰化作家群体有关祖国的旅行文学描写,发现彰化作家群体通过自己或亲友的大陆旅行经历,加强和深化了其民族意识与认同。[※注]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殖民统治的强化,台湾人民的种种抗争被殖民政府无情打压,在台湾文化人中间不可避免出现了分化,有些人逐渐从抗争走向消隐,乃至妥协与顺从。计璧瑞对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进行了全面研究,重点探讨殖民地处境与台湾新文学的关系,透过台湾新文学作家的书写,分析殖民社会政治、文化对被殖民者精神的压抑和渗透,以及对写作者身份认同和心理的影响。她对中文写作和日文写作的作家群体的文学想象和身份认同进行了辨析,指出殖民时期台湾作家因各自所处时期和经历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身份和类型。中文作家一般民族意识强烈,且写作有着深刻的反殖民、反封建色彩。而在日文作家中,其社会观念和文学观念则出现一定的分化,即使如吕赫若等早期小说中充满左翼色彩的作家,后期的写作中其民族意识也变得曲折隐晦。部分作家面对殖民者带来的“资本主义”,面对殖民者的“现代性”言说,对自身和相对的日本的文学想象,其立足点由昭示鲜明的民族立场转向考察复杂的传统与现代关系。至于日据后期对殖民统治完全表现出顺从乃至膜拜的“皇民文学”,则是殖民意识形态对被殖民者长期侵蚀的结果,呈现出被殖民者扭曲的心态。[※注]
(二)台湾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
受大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台湾也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和倡导白话文写作、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学运动。台湾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及其主张都与祖国大陆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卢善庆分析了台湾新文学运动崛起的过程以及包括黄朝琴、张我军等新文学运动主将们的主要主张、新文学运动创作等,指出无论从台湾新文学运动及对五四新文学的理论、作品的传播和推崇,还是从台湾新文学的语言形式、内容、主题等方面来分析,都很清楚地表明台湾新文学运动和中国大陆的文学革命极为相似。[※注]张光正从追溯白话新诗的缘起入手,回顾并探讨台湾新文学运动,指出台湾新文学运动是岛外社会文化新思潮本土化的产物,其实质是民族文化与殖民文化的一场搏斗,而台湾新文学在扬弃旧文学糟粕的同时,继承并发展了台湾文学的民族主义传统,反帝、反殖民的民族性既是台湾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特点,也是贯穿台湾新旧文学的一条主线。[※注]庄明萱也认为台湾新文学运动和祖国新文学运动同步,采取的模式和发展轨迹也大致相同,台湾新文学创作表现出的反殖民、反封建的精神和祖国新文学也一脉相通,并认为台湾新文学运动和台湾的社会运动、文化运动一样,是民族精神的产物。[※注]武柏索也提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反殖、反帝、反封建,希望推翻日本殖民统治,使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并对本土社会文化结构进行革新。[※注]朱双一研究了1941年前后台湾《风月报》上爆发的“台湾诗人七大毛病”的论争,鉴于论争中鲁迅、胡适等的一再被提起,以及注重时代性、社会性等文学理念与五四新文学理念相契合,认为台湾新文学与祖国五四新文学确实有密切渊源。[※注]白润生、胡静波与武柏索分别撰文,探讨台湾知识分子创办的《台湾民报》在台湾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注]
何标对新文学运动内部的白话文和台湾话文之争、乡土文学之争进行了辨析,认为这些争论属于“大同”中的“小异”,不宜人为“拔高”其中的部分主张,进而提出所谓的“台湾文学主体论”和“台湾民族文学论”。[※注]陈小冲对新文化运动中的台湾话文运动进行了专门研究,对部分“台独”意识深厚的学者提出的台湾话文运动的目标是图谋建设独立的台湾民族文学,其精神是既反对日本文化也反对中国文化的论调进行了批驳,认为台湾话文运动事实上是“一场由台湾本地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为抵制日本殖民者的日语普及运动、拯救台湾地区中华文化及闽南语这一中国地方语言文化而进行的民族文化自救运动,是对日本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直接反抗”。[※注]
(三)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化往来
日本殖民当局利用同化政策等各种手段,企图将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但日据时期台湾与祖国大陆仍保持着直接的文化往来,两岸之间在文化上的血脉相连并不会因外力而完全被割断。前述台湾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发生,并与其相似度极高,其实就反映了两岸之间深层次的文化联系。陈小冲指出,随着近代民族运动的兴起和台湾人民民族意识的高涨,一批富有爱国心的台湾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传播中华文化、恢复和发展同祖国大陆的文化联系的重要性,以庄遂性、蒋渭水为代表的台湾民族运动领导者,在台湾开办书局,大力引进祖国大陆出版的书籍,进行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弘扬工作。为了维护中华文化传统,文化协会还以成立读报社和汉文学习班的方式,将人民组织起来,传播祖国消息,学习中华文化。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坚持中华文化传统、努力维护两岸文化联系的种种活动,充分显示了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台湾人民不可征服的特性。[※注]吕若淮对《台湾文艺丛志》的研究也显示,日据时期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学交流并未间断,台湾文社发行的文学期刊《台湾文艺丛志》就转载和引进了大量京沪等地文艺刊物发表的文章,台湾的传统文人和大陆文人也保持了相当密切的联系。[※注]
日据时期,文化名人梁启超、章太炎曾前往台湾,对于两岸文化交往也有重要影响。张寄谦指出,梁启超1911年访台,是希望了解台湾的情况,进而为大陆发展提供借鉴,但结果却大失所望。[※注]汤志钧从梁启超的著作《说常识》及筹组国民常识学会谈起,认为梁启超1911年台湾之行的缘起是因为筹组常识学会工作进展不顺,在日本筹款无果后,想乘访问台湾的机会,和“旅台遗老”林献堂等再作磋商,以期获得林献堂和台胞相助。而台湾之行中对日本殖民统治者歪曲“常识”、美化殖民统治的做法,梁启超极为愤懑,进而促使其更致力于常识学会的创立工作,但因辛亥革命爆发,形势变化,最终作罢。[※注]杨齐福指出,虽然梁启超在台湾时间不长,但他在台期间和台湾同胞的直接接触、发表的诗文等,对台湾的政治、思想、文化等均有深远影响。杨齐福还对梁启超在台期间发表的一些美化殖民统治的言论进行了辨析,认为这并非是梁启超的真情流露,而是权宜之计,并且和其内心的“日本情结”和“亚洲主义”思想有一定联系。梁启超离台后依然和台湾知识界保持密切联系,使其对台湾社会一直保持着深远的影响力。[※注]罗福惠、袁咏红依据译读未刊日文档案,对孙中山、梁启超旅台的背景和经过进行了补充说明,指出孙、梁二人在台期间的言行,和其赴台背景及二人的对日态度有关。[※注]许俊雅根据一批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中所发现的相关新材料,对梁启超台湾之行对台湾知识界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注]朱双一考察了梁启超1911年台湾之行中对日本殖民地所谓“现代化”真相的洞悉,并指出梁启超提出的“刘铭传”诗题,寄托了民族情感和反殖民的现代化追求,对此后台湾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注]
章太炎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底避居台湾,在台停留时间约半年,期间任职于《台湾日日新报》,其在台期间的诗文也多发表于该报。汤志钧对章太炎在台湾的活动及其间发表的诗文进行了研究,指出章太炎在台期间发表的诗文主要针砭对象是清政府,其后来之所以不容于《台湾日日新报》,不得不离开台湾,也是因为章太炎的文章中表现出同情康、梁,同情变法,对清政府则多有不满的情绪。[※注]李德霞从新闻角度对章太炎的在台活动进行了研究,指出章太炎曾在《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了一些抨击总督府政策以及希望利用报刊对当局进行必要的监督的言论。[※注]
(四)辨析“殖民现代性”
所谓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带来现代化的“台独”言论,不仅影响到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的研究,文化史研究中同样受到这样的言论干扰。朱双一对这种“台独”言论进行了驳斥,他将日据时期分成三个阶段,透过各阶段台湾文学中的相关描述,展示台湾人民在殖民统治者所谓的现代化政策下并未得到幸福,反而经历重重困难的历史事实,认为1937年以来殖民者推动的“皇民化运动”对台湾造成“殖民遗毒”,是战后台湾“台独”理论的重要成因。[※注]黎湘萍通过对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梳理,也对类似言论进行了批驳,认为日据时期所谓的“台湾意识”,并非附庸于日本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反而是对这种外来“现代性”的消解和抵抗。[※注]
计璧瑞将殖民现代性区分为两层含义:一是殖民者自己认为的现代性;二是被殖民者眼中的现代性。日据时期台湾作家既是殖民现代性的接受者,也是拒斥者和批判者,他们在写作中体现出对殖民现代性的接受、反思与批判,其认知中展现了传统性与民族性、殖民性与现代性等多重关系的纠葛。[※注]
大陆文学史界对日据时期台湾作家有关现代性的理解与反思进行了相对深入的研究。朱双一研究了台湾作家赖和、赖贤颖、谢春木等人的祖国之行及其对殖民现代性的反思,指出这种经历不仅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而且具有扩大视野、从祖国接受现代文明的意义。通过在祖国之行中的所见所闻,他们对殖民现代性有了更深的反思,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输入所谓“现代”“文明”,其实包含着掠夺的目的,不仅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反而带来痛苦和危害。[※注]李立平对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的反现代化叙事进行了研究,指出台湾作家通过这种叙事模式,希望以“防卫的现代化”对抗日本的“殖民现代化”,而这使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呈现出“现代性”“民族性”和“殖民性”纠葛在一起的特殊景象。[※注]
张羽围绕1935年的台湾博览会,分析了总督府“殖民统治有功论”的官方表达,以及台湾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小叙述”对策展者“大叙述”的纠正或对抗。[※注]张羽还透过受到西方医学熏陶的赖和、蒋渭水、吴新荣、周金波四位台湾医师的涉医书写,观察在殖民现代化过程中,台湾医师对疾病医疗的态度,对医疗现代化、传统中医乃至公共卫生等问题的看法,进而探讨殖民性、现代性和本土性在台湾医师精神世界里的“厮杀与角力”,并认为从台湾医师的医疗书写中可以看出:“他们希望台湾现代化,但批判殖民化,希望保留本土化,但批判封建化,这四个维度的切割,显然是殖民地台湾的难题。”[※注]在《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糖业文化书写研究》中,张羽按照历史脉络对日据时期糖业文化书写进行了梳理,并透过其中反映出的蔗农在殖民糖业现代化过程中的艰难处境,探讨当时蔗农、知识分子对糖业现代化的认知,进而揭示糖业现代化复杂的面相,并为学界讨论“殖民现代性”提供新的视角。[※注]
(五)学术研究及其他
关于日据时期台湾的学术研究,邓孔昭分析了连横所著《台湾通史》和其他著作中有关郑成功的内容,指出连横对郑成功的研究和对民族精神的宣扬,使原本对郑成功就有深厚情感的台湾民众对郑成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这对当时台湾社会的民族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些民族运动的社会团体及其领导人,如蒋渭水、林献堂和李友邦及其领导的台湾义勇队等,从郑成功身上受到了精神鼓舞。[※注]哈正利、马威介绍了日据时期台湾官方和民间人类学研究机构的设立情况,重点论及一批日本学者及其田野工作和学术论著,分析了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特点,指出人类学进入台湾,是作为殖民知识的一部分,日本学者在台湾生产的人类学知识在形态上是殖民主义的。[※注]张崇根对日据时期的民族学调查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包括日本民族学会派出的鸟居龙藏等学者、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东台湾研究会等地方团体以及学校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等进行的调查工作,指出日据时期民族学调查的根本目的,是为殖民统治服务。[※注]左玉河围绕1930年儒墨学论战中以黄纯青、连雅堂为代表的“儒墨并尊”派和以颜笏山、张纯甫为代表的“非墨”派的相关言论,对日据时期台湾的墨学研究进行了考察,指出在这场儒墨学论战背后,反映了台湾思想界的分化与困惑,因求新、崇墨势必会对台湾学者安身立命的儒学思想造成冲击,而台湾学者则更多希望在不触动儒学地位的情况下引入新思想新文化。[※注]
除以上小的专题外,还有一些研究涉及其他方面,如吕若淮根据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中的记载,考察日据时期的台湾文社。李诠林考察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民间方言歌谣。许彬彬、李无未从语言学角度对日据时期台湾闽南语会话课本的编写与教学进行研究,并强调闽南语方言史的研究价值。何元春、陈媛媛研究了日据时期登山活动的发展脉络,并对殖民主义文化在登山活动中的渗透进行了探讨。另外,李倩对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和大连的电影业进行了比较研究,张羽则对比研究了台湾和东北沦陷区的殖民文化政策等。[※注]
总之,相对于明清时期台湾史而言,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有其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关于殖民地与现代化关系问题。这便涉及从宏观上把握日据时期台湾史的评价问题,也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史的基础。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具有掠夺性与先进性的双重性质,控制与掠夺是其战略目标,先进性的赋予只是附带效果。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也不例外。应该说,日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台湾带来了某些现代性,但无可否认,这是建立在日本对台湾全面掠夺的基础上,而且是从属于其殖民侵略战略目标的附带效果。那种无视日本殖民侵略的掠夺性,而一味片面美化所谓“殖民现代性”效用的观点,完全是非历史主义的无稽之谈。二是资料问题。大陆地区虽有《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300册影印档案史料的出版,但该汇编收入史料主要为台湾与大陆往来资料,大量日本治台或台湾地方史料仍有待于挖掘。台湾地区“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原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等处对大批日据时期资料进行了整理出版或数字化,但由于两岸交流尚有一定限制,这些资料大陆学界还不易获得。因该时期的历史特殊性,日本亦藏有不少重要史料,这方面的发掘和利用也很不够。日据台湾史研究尚有较大推进与提升的空间,这种推进与提升应是基于新史料的学术创新。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