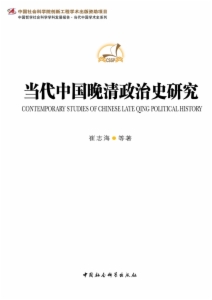第三节 1963—1976年的太平天囯史研究
|
来 源
:
|
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2 | ||
|
摘 要
:
|
而在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太平天囯领导人洪秀全,更被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洪划线成了评判太平天囯其他人物的唯一标准。究其原因,是他在1864年天京城破突围被俘后,应太平天囯的老对手、湘军领袖曾国藩的要求,在囚笼中写下了数万字的供述(即《李秀成自述》),又被曾国藩在删改后刊刻了出来。[※注]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太平天囯虽然还被正面肯定,但其领袖人物中,却仅剩下洪秀全一人处于至高无上、全盘肯定的地位,而同为太平天囯主要领导人的杨秀清、石达开等,都程度不等地受到批判,或被指为篡夺最高权力的阴谋家,或被斥为自取灭亡的分裂主义者,等等。 | ||||||
|
关键词
:
|
囯 洪仁玕 洪秀全 太平天国历史 领导人 人道主义 话语体系 叛徒哲学 人格尊严 人生价值 太平天国 |
||||||
在线阅读
第三节 1963—1976年的太平天囯史研究
字体:大中小
1962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左”的专制思想越演越烈。太平天囯史领域是受害的重灾区,其代表性的标志是戚本禹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发表而由《人民日报》1964年7月24日摘要刊登的《评李秀成自述》,此文就所谓“忠王不忠”的问题向罗尔纲等人发难。其结果,不仅李秀成被打成“叛徒”,凡不赞成戚文意见者,都受到了批判,并在随后而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程度不等的冲击。而在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太平天囯领导人洪秀全,更被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洪划线成了评判太平天囯其他人物的唯一标准。
在太平天囯人物中,争议最大的焦点人物是忠王李秀成。究其原因,是他在1864年天京城破突围被俘后,应太平天囯的老对手、湘军领袖曾国藩的要求,在囚笼中写下了数万字的供述(即《李秀成自述》),又被曾国藩在删改后刊刻了出来;而其供述原稿,后来又由曾氏后人于1962年在台北全文影印发表。李秀成的这篇供述,使得他在身后遭致了种种非议,而在死后一百年竟成了公开声讨和批判的对象。
戚本禹于1963年第4期《历史研究》上发表了题为《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的文章,一年后,《人民日报》于1964年7月24日将其摘要发表(原文为1.6 万余字,摘要为1万字),文章的矛头指向《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的作者罗尔纲以及整理出版了自述部分真迹的梁岵庐和校补自述刻本的吕集义。原因是这三人都认为李秀成是“伪降”。
196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戚本禹的题为《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一文,言辞更为激烈,不仅对罗尔纲等史学家大张挞伐,还连带批判了歌颂李秀成的戏剧。戚本禹的文章说:经常有一些人对《李秀成自述》抱有怀疑态度,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大英雄’的‘自传’竟然会充满背叛革命的语言?更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充满背叛革命语言的文件,竟然会受到人们这般的尊崇?”戚文指责罗尔纲是“主观唯心主义”,“自立例,自破例”,只依据对自己观点是否有利而判别材料的真假。戚文慷慨激昂地指斥:
一个变节分子的“自白书”,被一些专门研究它的专家捧到了九天之上,他们不仅自己对它视之若香花,敬之若神明,而且还要号召我们的青年一代,一起来认真阅读“这部革命英雄的自传”,一起来“表彰”和“热爱”这位革命的先烈。……我们的大、中、小学,我们神圣的无产阶级教育的讲坛,也在向学生们进行着李秀成“崇高伟大”的教育,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可以不知道农民革命元勋洪秀全、杨秀清,却必须知道“农民领袖”李秀成。我们的革命舞台,也在向观众推荐着关于李秀成“慷慨就义”的戏剧。一个人变节了,却仍然可以得到人们这般的歌颂,难道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合理的吗?
据说他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后,毛泽东曾在一张刊有此文的报纸空白处批了“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等16个字。应该承认,戚本禹的几篇文章气势磅礴,逻辑谨严,言语锋利,相当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按照革命的话语体系,他不仅政治正确,而且在理论上无懈可击。可是有一条:这种套用阶级斗争公式的话语体系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因而史学界的多数研究者并不买他的账。1964年春天,著名史学家陈恭禄教授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史教研室组织的一次李秀成评价讨论会上,十分尖锐地指出:戚本禹的文章“没有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还说,“如果这篇文章是我的学生写的,评分就不得及格”。但他和其他务真求实的史学家们因此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并在其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恭禄被公开点名批判。南京大学的茅家琦和扬州师范学院的祁龙威因在《文汇报》发表了基本肯定李秀成的文章,成为批判“叛徒哲学”的靶子。茅家琦由于是中共党员,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全省党员大会上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批判。《新华日报》两次用整版的篇幅点名批判他在李秀成评价问题上的所谓“叛徒哲学”。[※注]。
多年以后,已年届桑榆的茅家琦对所谓“忠王不忠”的问题作了重新辨析。他认为:一部农民战争史充分说明农民战争与人道主义、皇权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农民战争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中,皇权主义思想显得特别浓厚;而参加起义的广大农民群众则主要是为了“活命”,自己和家庭成员能够活下去——也就是“人道”方面的要求。人道精神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尊重自己的人生价值与人格尊严;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与人格尊严。孟子对“忠”的解释最为明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人道主义的立场看,忠于人民忠于社稷是绝对的,忠君应是相对的。李秀成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提出的收齐太平军余部的十条“收齐章程”,是当年“忠王不忠”论的主要依据,但实际上完全体现了一种人道关怀,是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茅家琦指出:“忠王不忠”论在理论上和思辨方法上都是肤浅的。20世纪60年代宣扬这种观点,从认识水平来看,是倒退到了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水平。[※注]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太平天囯虽然还被正面肯定,但其领袖人物中,却仅剩下洪秀全一人处于至高无上、全盘肯定的地位,而同为太平天囯主要领导人的杨秀清、石达开等,都程度不等地受到批判,或被指为篡夺最高权力的阴谋家,或被斥为自取灭亡的分裂主义者,等等。太平天囯史的正常研究被迫中断。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太平天国历史陈列》也不再对外开放。
1974年全国掀起“批林批孔”的热潮,《红旗》杂志第1 期刊登署名文章《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称:
十九世纪中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也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声势浩大的讨孔运动。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一开始就明确地把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同摧毁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学结合起来,对孔子及其反动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太平天囯因而再次引起了世人的注目。但相关的评论或批判文章已不再属于严肃的历史研究的范畴了。
同年10月,太平天囯历史博物馆的《太平天国历史陈列》重新开放。当时有观众受“左”的思想影响,说洪仁玕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建议把他写的《资政新篇》撤下来。太博的同志就此向方之光咨询。方说: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的天敌,当时走资本主义道路与走封建主义道路相比,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资政新篇》的内容得以保留。[※注]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后,9月中旬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第9期(总第37 期),发表了《地转实为新地兆——读洪秀全的〈地震诏〉》一文。1853年太平天囯攻占南京并建都后不久发生过一次地震。洪秀全为此发布《地转天旋好诛妖诏》。在这篇以七言诗写就的诏书中,有“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以及“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按即宽心)任逍遥”等句。《学习与批判》读洪秀全《地震诏》的文章,声称当年洪秀全在天京地震后所作的《地震诏》是旧世界的“声讨书”、新世界的“宣言书”,居然借洪秀全的《地震诏》中所谓“山崩地裂若等闲”的“伟大气魄”来鼓舞人心,其风格之低下已到了可笑的地步。[※注]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