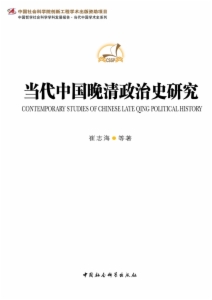第四节 1977—1989年的太平天囯史研究
|
来 源
:
|
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3 | ||
|
摘 要
:
|
也鉴于太平天囯史研究在史学领域一枝独秀,有类于《红楼梦》研究在文学史领域的处境,曾任北京太平天囯史学会会长的戴逸教授即建议:仿照《红楼梦》研究之称作“红学”,太平天囯史的研究也可称作“太学”。在太平天囯史的研究中,人们囿于“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习惯思维,往往过分看重洪秀全的天王身份和地位,从而贬低杨秀清在太平天囯革命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但太平天囯之向封建政权转化又有其历史的必然:首先,太平天囯起义并没有自觉地反对封建地主阶级。[※注]罗尔纲在太平天囯政体问题上,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解,即太平天囯是一个虚君制政权。 | ||||||
|
关键词
:
|
囯 洪秀全 太平天国 洪仁玕 政权 上帝 政体 农民 良言 人物 译文 |
||||||
在线阅读
第四节 1977—1989年的太平天囯史研究
字体:大中小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且“拨乱反正”之后,“左”的路线及其思潮得到初步清算。太平天囯史成了史学界最先复苏的研究领域。
1977年,王庆成发表题为《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性质不容否定——驳梁效、罗思鼎对太平天国历史的歪曲》一文,批判了梁效等的“反动历史观和方法”。该文指出:梁效们对于太平天囯如何的伟大斗争并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所谓天国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利用历史反党,为其篡党夺权政治需要服务。[※注]
1979年5月下旬,由北京太平天囯历史研究会和南京史学会联合举办的太平天囯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界首次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也是新中国成立30年来史学界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讨论会。参加这次讨论会的不仅有来自全国各高校院所、文博和出版机构的专业人员,还有太平天囯史研究的业余爱好者,加上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西德、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的外国学者,以及在南京就读的外国留学生,260多人济济一堂。会议收到各种专题论文200余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史学界的初步繁荣。
此后直到1989年的十余年间,可以说是太平天囯史研究空前繁盛、最为活跃的时期。各地的太平天囯史学会纷纷成立,各种大中小型的学术讨论会相继召开,学术论著、研究资料的出版、发表数量更是空前。南京大学等高校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还招收了太平天囯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一时间太平天囯史研究领域聚集起众多的研究力量,有人为此戏称:研究太平天囯的简直比太平军还要多。也鉴于太平天囯史研究在史学领域一枝独秀,有类于《红楼梦》研究在文学史领域的处境,曾任北京太平天囯史学会会长的戴逸教授即建议:仿照《红楼梦》研究之称作“红学”,太平天囯史的研究也可称作“太学”。
“太学”领域的拨乱反正,首先是人物评价问题。
1980年在苏州召开的太平天囯史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一致赞成为李秀成“恢复名誉”,在苏州的忠王府也报请国务院批准,重新恢复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他人物也相继得到了重新评价。
洪秀全与杨秀清是太平天囯最主要的两位领导人。固然,没有洪秀全就没有太平天囯;但若没有杨秀清,洪秀全作为一个失意书生,充其量也就是个基督教的传道牧师,而不可能成为太平天囯的天王。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人们多将洪杨并列。张德坚的《贼情汇纂》将洪秀全与杨秀清并称“首逆”。谭嗣同称太平天囯为“洪杨之徒”。到了20世纪30年代,邓之诚在其整理的《汪晦翁乙丙日记》的序言中也依然说“晚近治洪杨史事者日多,诚以洪杨创业垂统历十有五年”云云。洪杨并列,也有附会的成分在内。古人本即有所谓“红羊劫”之说,以天干“丙” “丁”和地支“午”在阴阳五行里都属火,为红色,而地支“未”在生肖上是羊,因而每六十年即可出现一次“丙午丁未之厄”。太平天囯起义,虽然并未发生在这两个年份,但因为洪秀全和杨秀清姓氏的关系,亦被附会为“红羊劫”或“洪杨劫”。
在太平天囯史的研究中,人们囿于“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习惯思维,往往过分看重洪秀全的天王身份和地位,从而贬低杨秀清在太平天囯革命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罗尔纲所撰纪传体的《太平天国史稿》,将天王洪秀全和幼天王洪天贵福入本纪,而将杨秀清和其他人入列传。几经反复后,在其最终定稿的《太平天国史》中,终于将本纪改为纪年,而将洪秀全等也列入传记之中。他也正是考虑到洪杨两人的特殊关系,而提出了太平天囯为“虚君制”政体之说。
随着《天父天兄圣旨》于1983年被发现,杨秀清在太平天囯开国史中的作用有了更多的显露,但迄今对他的研究,尤其是他在太平天囯开国史中的作用,研究得还很不够。
韦正即韦昌辉,在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囯前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的民族成分究竟是汉族还是壮族?1954年广西太平天囯文史调查团在调查中曾因多种证据而得出他的民族成分“无可置疑”是壮族的结论。[※注] 但罗尔纲通过其族谱乃至对韦志俊后人的调查,认为韦家是来人客籍,也即客家人。钟文典的《太平天国人物》一书中,以确凿的事实支持了罗尔纲的结论。[※注]
冯云山与福汉会的关系同样引人注目。1973年,澳大利亚学者克拉克在其著作《上帝来到广西》(The Coming of God to Kwangsi)一书中称:冯云山曾经参加过郭士立所组织的福汉会。他将这一研究成果带到1979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引起人们的兴趣。茅家琦经过认真的考察辨析,并援引简又文、施其乐等人的研究成果,得出的结论是:冯云山从未参加过郭士立的福汉会。[※注]
钟文典对太平天囯人物的研究极为深入。他的《太平天国人物》一书中,共收入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等14 个重要人物,且于每人都有翔实的考辨。这些人物中,客家人占了大多数。但也有本地土著,如萧朝贵即系壮族。
太平天囯人物中,最富传奇和神秘色彩的要数萧朝贵的妻子杨宣娇。杨宣娇,在《太平天国起义记》中作杨云娇,是拜上帝会最早的成员,在其敬拜上帝之初,甚至比萧朝贵更有名,有“男学冯云山,女学杨云娇”的口号。但在太平天囯文献,如《天兄圣旨》中,杨云娇均作杨宣娇。太平天囯凡年岁较幼或身份地位较低者,如与尊长者名字有相重,必须改名以避讳。“宣娇”之名很有可能是后来避冯云山名讳而改。杨宣娇(云娇)与洪秀全等人为高天结义的兄妹,李秀成在其自述中误以为她是洪秀全的亲妹,所以太平天囯野史和一些研究著作中,曾将杨宣娇误作洪宣娇。王庆成、钟文典乃至罗尔纲本人,对杨宣娇事迹都有所考订。
研究太平天囯人物最多且最有成就的仍数罗尔纲。成稿于20 世纪80年代而于1991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是其集大成,仅其“传一辑”中即收有洪秀全等84位主要人物的传记。但其“传二辑”的《妇女传》中既不收杨宣娇,亦不收东王府中那位很有名的女簿书傅善祥,殊可奇怪。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天囯的对立面,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研究,也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其中较为突出的有龙盛运对湘军的研究,樊百川对淮军的研究,朱东安对曾国藩的研究,苑书义对李鸿章的研究,董蔡时对左宗棠的研究(以及在他的指导下,研究生王国平对胡林翼的研究),贾熟村对太平天囯时期地主阶级的研究等。
太平天囯史研究中曾经提出过的若干问题,如政治制度、宗教性质、军事组织、战争状况、各地政权建设、土地制度与社会经济政策,乃至妇女解放等,都有了新的进展。其中太平天囯政权性质的问题,依然是争论的热点。
太平天囯政权究竟是什么性质?农民革命能否建立农民政权?这一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有人提出,并引起争论。1961年史学家翦伯赞就此发表自己的见解:
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
他的结论是:
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注]
翦伯赞的相关论点,于1965年受到戚本禹的不点名批判。[※注]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有人重翻旧案,并引发了新的热烈讨论。孙祚民在《试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注] 一文中,从三个方面对太平天囯政权作了剖析:
关于政权构成的形式,从职官制度、等级制度和礼仪制度来看,基本上是沿袭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关于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不论是从中央政权到地方政权来看,还是从洪秀全、杨秀清等最高掌权者的转化来看,都是封建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占着统治地位的;关于土地制度,大量史料说明,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以后,始终是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支持地主收租的,根本没有实行过什么“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更谈不到实行平均分配土地。
他的结论是:
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北伐进军的同时,沿着历史规律所规定的方向,走完了向封建转化的道路,农民英雄们在南京建立的天国,已经是新的封建王朝了。
沈嘉荣的《论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也认为:太平天囯定都天京之后,建立的就是一个封建政权。[※注] 而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之所以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因为:第一,在新的生产力没有出现之前,不可能实现旧的生产关系的改变;第二,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上,不可能建立非封建的或超封建的上层建筑。但他又指出:
我们否定农民政权,但决不是贬低或否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其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都超过了前代;这场规模壮阔的农民起义,确实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统治,从而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推动历史的前进;太平天国政权尽管是个封建性的政权,但其内外政策同已经腐朽了的封建的清王朝还有着一定的区别。
吴雁南在《太平天国前期的等级制度——兼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与政体》[※注] 一文中,坚持了自己于1978年提出的太平天囯政权具有“两重性”的见解。他认为:太平天囯政权带有一定的封建性,但在当时仍是农民革命政权。政体具有一定的民主性,选贤与能,集体议事,赏罚比较严明,除诸王外,物质生活不太悬殊。
苏双碧的见解又有所不同。他提出:初期太平天囯政权主要是农民政权,平等和平均思想表达了千百万苦难农民的愿望;太平天囯政权在建都南京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政权的革命性是非常明显的;前期“照旧交粮纳税”是有利于农民的政策。但太平天囯之向封建政权转化又有其历史的必然:首先,太平天囯起义并没有自觉地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其次,农民本身就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贪官,但拥护“好皇帝”;第三,洪秀全本身就有强烈的取而代之的思想,即想推翻了清朝皇帝后,自己便可以充任“太平天王”;最后,太平天囯政权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注]
这场讨论,并没有形成尖锐的对立,最后似乎不了了之。
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离不开对国体和政体的辨析。在这一问题上所遵循的理论前提是毛泽东于《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的论断:所谓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而所谓政体,则是指国家政权构成的形式。[※注]
罗尔纲在太平天囯政体问题上,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解,即太平天囯是一个虚君制政权。[※注] 他说:
太平天国以“主”(天王)为国家元首,以“军师”为政府首脑,采取“虚君制”,天王“临朝而不理政”,实际权力在于军师。这是一种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制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的政体。太平天国前期行虚君制,经过天京事变后,遭到破坏了。于是太平天国从具有农民民主性质的虚君制,走上了君主专制的道路。
他认为:作为国家元首的天王,确是沿袭封建制度的;但掌握实权的军师(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影响,亦受天地会影响),则是农民民主思想的产物。这种虚君制,是和太平天囯的国体,即政权的阶级性质相适应的。他的结论是:
太平天国虚君制,杨秀清迫称万岁,觊觎君位,破坏于前;洪秀全剥夺军师权力,厉行君主专制,彻底破坏于后。洪、杨对太平天囯的败亡,都要承担重大责任。但是,我们不应该专责个人,而必须追溯到阶级根源上去。农民不可能摆脱封建生产方式带给他们的深刻影响。洪、杨事件,正说明了农民革命的本质的规律性。
罗尔纲的“虚君制”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论,但并不等于人们都同意了他的见解。体现在洪秀全和杨秀清身上的这种因人设事的极不稳定的二元结构,能否称为“虚君制”,很值得进一步探究。
郦纯研究太平天囯制度多年,其所著《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一书初版及增订本先后于1956年和1962年出版。1970年,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将此书再作修改,于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第二次修订本,字数也增为50 余万字。他的另一巨著《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上、下编全5 册,约109 万字,也由中华书局于1982年出版。该书根据可信资料,对太平天囯军事史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记事也多较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为详。
太平天囯的宗教问题,在80年代成为新的热点。
太平天囯宗教,源于洪秀全、冯云山的敬拜上帝。韩山文据洪仁玕口述而编著的《太平天国起义记》[※注] 一书中论之甚详。该书曾提及:洪秀全在第二次赴广州应考时,在贡院前正好得到基督教华人牧师梁发所派发的宣扬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并从此走上了敬拜上帝的道路。有人认为:洪秀全吸取了西方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并把它和中国古代儒家的大同思想揉合起来,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三篇理论文章。
茅家琦对此提出质疑。他指出:洪秀全是在1843年阅读《劝世良言》的,1847年3月以后才读到《圣经》。而《劝世良言》中并没有任何宣扬原始基督教平等思想的地方。大约在1845、1846年,洪秀全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阐述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思想,这些思想和《劝世良言》风马牛不相及,和《圣经》更无关系。他所描绘的“天下为公”的美好蓝图,甚至连语言都是直接来自《礼记·礼运篇》。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所吸取的,只不过是“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就是敬拜上帝本身,洪秀全也是引用儒家经典予以证明的。我们今天说洪秀全向西方找到了上帝,但洪秀全自己却认为是“尽返真醇”,也就是“复古”,而不是向西方学习。[※注]
不过1847年以后,洪秀全开始有了与外国传教士的直接接触。王庆成通过在美国查阅罗孝全的档案,对太平天囯与罗孝全的关系已有较为清楚的勾勒:
1847年春,洪秀全曾到罗孝全在广州的教堂学道。这段时间,并不是人们所通常认为的两个多月。因为从他3月23或24日(二月初七或初八)来到教堂,到7月21日(六月初十日)离开广州,洪秀全在罗孝全教堂的时间当在三个半月以上,并得到了《圣经》的某种中译本。1848年冯云山羁于桂平县狱时,洪秀全曾再次返回广州。此次他是否与罗孝全见面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他肯定与罗的中国助手周道行有过接触。1849年2月萧朝贵假借天兄下凡时曾承认番人罗孝全“是真心,有牵连”。说明罗孝全确曾对洪秀全表示过某种同情和支持。而罗孝全的神学观念,即视其他一切宗教为异教和邪教,全力抨击本地人的偶像崇拜,可能对洪秀全也有很大的影响。洪秀全信仰上帝之初,虽排斥佛、道,但未有大肆捣毁偶像之事。1847年离广州去广西后,则打庙毁偶像、斥邪神之事屡有发生。[※注]
引起人们较多兴趣的是太平天囯起义之初敬拜上帝的组织问题。通行的说法是:1843年洪秀全读过《劝世良言》后,建立了“拜上帝会”。“拜上帝会”四字,本系《太平天囯起义记》英文1854年版中所附的中文原文。说明确实是有这么个称呼。那么,洪秀全究竟有没有创立一个名叫“拜上帝会”的组织?
茅家琦最先对此提出质疑。他指出:就我们翻阅过的太平天囯官书和参加太平天囯革命的人所写的材料,从没有发现“拜上帝会”的记载。再查《太平天囯起义记》,据简又文的译文,作:“此等新教徒即自立会结集礼拜,未几,远近驰名,而成为‘拜上帝会’。”而依据英文的原文,准确的译文应该是:“他们自己成群地汇合起来,在一起举行宗教礼拜,很快,他们以‘拜上帝会’而远近驰名。”
茅家琦的结论是:“可见,根据韩山文的记载,并不是洪秀全建立了‘拜上帝会’,而是别人用‘拜上帝会’这个名字,称呼经常在一起举行宗教仪式的拜上帝的人。”[※注]
停滞多年的外文史料的翻译工作也得以重新起步。20 世纪80年代中,北京太平天囯史研究会先后编辑了三辑《太平天国史译丛》,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不仅选译了若干重要史料,也介绍了国外学者太平天囯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如1981年出版的《译丛》第一辑,就收纳了参加1979年南京太平天囯史学术讨论会的外国学者所提供的论文、资料或所作的学术报告。1983年出版的《译丛》第二辑,登载了英国学者柯文南和南京大学蔡少卿共同翻译的《镇江与南京——原始的叙述》(原文于1857年1月在香港出版的《中国之友》报15、21、30日副刊连载)。该文的叙事者,也即裨治文、麦高文等人于上海《北华捷报》发表的有关天京事变两篇报道中的叙事者。但该文叙事较后两者更为翔实,保存了较多的原始性。裨治文和麦高文的两篇报道,原已有简又文的译文,但不甚完整,也有不准确的地方,该辑也特地登载了新的更为准确的译文。这几篇译文的发表,对当时业已展开的天京事变的学术争论,尤其是否存在天府广场大屠杀、所谓第八位者究竟是谁的争论,提供了史料佐证。
形形色色的太平天囯资料,有些早于五六十年代即已编就,此时也相继出版。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注]、《吴煦档案选编》[※注] 等。罗尔纲所主持的《太平天国资料汇编》此时也交由中华书局出版,可惜在出版了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第一册)和李滨《中兴别记》(第二册)两种之后即戛然而止。
太平天囯自身的史料,于此期间有了最为重要的发现。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庆成研究员于访英期间,在英国图书馆得见太平天囯官方印书《天兄圣旨》卷一、卷二和《天父圣旨》卷三。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萧朝贵假借天兄下凡,都是太平天囯史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正如王庆成所指出的,“我们不充分了解各次天父天兄下凡,也就差不多等于不充分了解太平天国”,所以当他在英国图书馆找到这两种书打开封面见到第一页时,“不禁激动得双手剧烈震颤,翻不开第二页……”[※注] 这两种太平天囯官方印书包含了太平天囯开国直至天京事变之前许多事件的重要信息。太平天囯前期的历史,尤其是开国的历史,多要为之重写。但这一发现的深刻影响,一直到20 世纪90年代才得以渐次展现。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