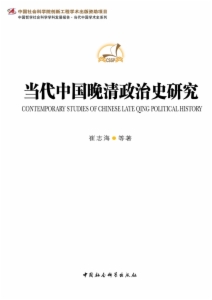第二节 1949—1978年的洋务运动史研究
|
来 源
:
|
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2 | ||
|
摘 要
:
|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30年间的洋务运动研究史上,有两件事情值得重点提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资料汇编共分12编,包括综合编、育才编、海防海军编、练兵编、制械编、马尾船政局、轮船招商局、铁路编、电报编、矿务编、纺织制造编以及传记编,涵盖了洋务运动的大部分主题,书末附录的“洋务运动书目解题”篇。总之,新中国成立后,系统的洋务运动史研究有所起步,虽然没有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专题领域中的“热点”,但学者们在史料整理、理论论辩以及史实考证方面,仍然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可贵的探索,其学术价值不可忽视,成为以后开展深入研究的基点。 | ||||||
|
关键词
:
|
近代史资料 洋务派 洋务运动 近代史 资本主义 学界 史料 军事工业 近代史学界 丛刊 高潮 |
||||||
在线阅读
第二节 1949—1978年的洋务运动史研究
字体:大中小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30年间的洋务运动研究史上,有两件事情值得重点提出。一是在5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以“洋务运动”命名的第一本研究专著和第一部研究资料集;二是在此基础上60年代初出现了第一个洋务运动研究小高潮。
前述范著和胡著对洋务运动的描述与评判,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学者们进一步展开研究工作具有指导性、经典性、权威性意见的理论基础和依据。尤其是1954年胡绳以阶级斗争为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论[※注]被提出后,旋即引起近代史学界广泛的赞誉与认同,随之而来的便是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以及辛亥革命这“三次革命高潮”事件成为学者们蜂拥而上的研究热点,作为人民革命斗争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洋务运动,自然被打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冷宫”[※注],处于边缘位置,乏人问津。笔者根据《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所列各研究专题论文进行统计后得出的数据(见下表),似乎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近代史研究领域“旱涝不均”的状况。姜涛先生根据历年《历史研究》刊载论文的情况,也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晚清政治史各研究专题中,洋务运动是位居最末位的。[※注]
如果再仔细检视一下新中国成立后前10年间发表的这20 篇讨论洋务运动的文章,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论文其实并不多见,大多是应近代史教学需要而作兼及特定政治宣传之类性质的短文,如《清末的洋务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什么作用与意义?》《说满清同光时代的“洋务运动”——讲堂讲授内容纪要》《洋务运动(历史教学小词典)》等[※注],对洋务运动评价也是基本沿袭范、胡的立场与标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56年牟安世的《洋务运动》出版,虽然作者自称是本“小册子”,仍不失为系统研究洋务运动史的拓荒之作。必须承认,牟著将“洋务运动”置于毛泽东从政治角度提出的近代史发展规律权威论断框架内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无疑仍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产物,具有典型的时代特色。[※注] 这一点,牟安世在书末做了明确表述:
我们从洋务运动的历史中,既然认识到中国的工业化乃是中国人民近百年的理想,并一直为它奋斗而没有成功,只有今天才有实现的可能,那么,我们就应当虚心学习,客服困难,加倍努力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注]
在对洋务运动的整体评价上,牟著继承并进一步阐释了胡绳“洋务运动为外国侵略者开辟道路”的观点,强调它是以军事为中心的反动卖国运动,是封建官僚在向西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外交政策的产物,其实质是助长了他们对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多重侵略。[※注]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牟著引用大量的原始史料特别是外文资料以及统计数字作为分析研究的基础,相较于之前或同时期有关洋务运动的泛泛之论,无疑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显示了作为第一本洋务运动史著作应有的学术生命力。牟著中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断,值得重视。如牟著强调以军事建设为中心,将1860—1894年的洋务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860—1872年的建立军事工业阶段,1872—1885年的围绕军事工业建立其他企业阶段,以及1885—1894年的北洋海军成军和建立炼铁厂阶段,从而突破了以往笼统以“自强”“求富”为划分洋务运动阶段标准的研究框架,代表了一家之言。牟著虽然批判洋务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作用,但也承认初期的官营军事工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注] 这些见解在其对洋务运动强大的政治定性的批判下反而被后世学者给忽视了。
值得注意的是,牟著中引用的统计数据已经包括最新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的资料。该书初版于牟著问世的前一年,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体编纂的第一部专业工具资料书。[※注] 随后,到60年代,经济史领域整理汇编了十几种资料集,相继以“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系列的形式出版,其中很多都涉及洋务运动时期的工业、企业等内容,从而大大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史料匮乏的缺陷。
然而这一时期真正推动洋务运动研究史料建设工作的还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的编纂与出版。它是在中国史学会的提倡与主持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洋务运动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的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大规模、系统的科学整理的成果。承担编纂任务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和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相关研究人员,历时数年之功,最终在1959年编纂完成8册共计320余万字的资料集,两年后出版。毛泽东“两个过程”论中述及的“八大事件”,本是不包括洋务运动的。50年代先后编成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系列包括《义和团》《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捻军》《戊戌变法》《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辛亥革命》以及《洋务运动》10种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志着洋务运动正式跻身中国近代史学科“八大事件”序列。洋务运动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愈来愈成为学者关注的议题。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开篇的“序例”,集中反映了资料汇编的选编者——其本身首先也是研究者——对待洋务运动的基本看法与认识。他们承认洋务运动的封建性、买办性和政治上的反动性,认为洋务运动是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勾结的自救运动,为的是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妥协。但同时他们也注意到洋务运动某些积极的方面,比如“它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造成了某些有利条件。并且,使中国的无产阶级获得了一些发展。同时,清政府既办理洋务……栽植了一些通达外情、理解科学的技术人员。这些人中,一部分在洋务派官僚集团中做了走卒,但也有些人因接触西洋事物而接触了新的思想,对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桥梁作用”[※注]。姜涛认为这种看法与认识代表了50年代近代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一种“经典性表述”[※注],笔者深以为然。这种对洋务运动相对来说较为全面的定位,可能更为同期研究者所乐于遵循,姜铎、黄逸峰在60年代提出的观点就是在此基础上形式上走向极端的阐发。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资料汇编共分12编,包括综合编、育才编、海防海军编、练兵编、制械编、马尾船政局、轮船招商局、铁路编、电报编、矿务编、纺织制造编以及传记编,涵盖了洋务运动的大部分主题,书末附录的“洋务运动书目解题”篇,详细提供了研究洋务运动可资利用的基本史籍线索。这套大型资料汇编为洋务运动史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60年代初学界围绕洋务运动性质和作用问题展开的第一次较为活跃的学术争鸣,便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这次争鸣的核心人物,研究经济史的姜铎后来回忆说:
我在1957年才从机关调到上海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当时正在主持编写《江南造船厂厂史》,并负责执笔撰写江南制造局的一章,由此我开始接触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问题。由于对洋务运动素无谓研究,所以我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初期只能依据范文澜、牟安世等人的全面否定观点,竭力贬低江南制造局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后来,我认真翻阅了1959年由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 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在史实面前,我开始对全面否定论有所怀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注]
姜铎的看法也就是他后来一直坚持的所谓基本否定基础上的“两点论”,即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洋务运动同时存在着反动与进步、消极与积极的双重作用,不应偏废或忽视任一方面,当然前提是反动和消极作用是主要方面。应该说,姜铎的“两点论”并不是什么石破天惊之语,在前述著作如吕振羽《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的“序例”中,都可找到相似的思想因子,只是他将研究重心放在了前人或当时学界没有充分展开的进步与积极方面,并作了集中讨论。他从分析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入手,提醒学界要“全面地对待历史事实”,“全面地”研究与认识洋务运动的性质与作用。他特别强调洋务运动对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同时存在着“刺激和促进”作用,洋务企业的经济活动“和外国资本还存在着显著的矛盾,对外国资本的侵略,还起着一定的抵制作用”,“洋务派所进行的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尽管它的政治动机和目的是反动的,力量是微弱的,效果也是不大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反映和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因而在改变古老落后的封建经济,促进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方面,不能不在客观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注]
姜铎毫不讳言洋务运动的进步因素,为了论证自身的观点,甚至不惜过分强调、突出乃至放大洋务运动在经济活动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重视政治层面判断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近代史研究框架中就显得是异军突起,一时间成为近代史学界“商榷”话题最多的活跃人物,批评他孤立地、片面地放大洋务运动的经济效果,没有“从当时阶级斗争的全局出发”,没有“放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总体中”加以考察的意见纷至沓来。[※注] 在此基础上,洋务运动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如洋务运动的目的、分期、失败的原因,洋务企业的性质、与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关系、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等,也进一步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与兴趣。上述1949—1978年发表的94篇有关洋务运动主题的论文中,仅1961—1964年就有57 篇,其中姜铎发表的文章有6篇[※注],与姜铎商榷的文章多达10 余篇。长期饱受冷遇的洋务运动史研究领域终于迎来了一次难得的小高潮。
除了对洋务运动宏观意义上的性质讨论之外,具体史实和相关洋务人物的研究在这次小高潮中也取得一定进展,邵循正和汪敬虞二人在不同观点的交锋中对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办、改组、人事更动等关键性史实的考订与阐发[※注];邵循正通过主持《盛宣怀未刊信稿》对盛宣怀作为淮系洋务派人物代表的评价与分析,对郑观应与洋务派特别是与盛宣怀的关系及分歧的梳理与探究[※注];戴逸对慈禧、奕集团、顽固派等晚清统治阶级集团内部派系纷争和同光之际政治格局的考察与解析[※注]等,均是之前学界没有重视或研究不够充分的内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对洋务运动史事的了解与认识。另外,戴逸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洋务派及其活动的两面性、动机和效果辩证关系的探讨,对洋务运动三阶段分期的论断[※注],也对重新认识洋务运动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然而,学界对洋务运动研究的小高潮仅是昙花一现,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恶化,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洋务运动研究又陷入了冰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几乎付诸阙如。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系统的洋务运动史研究有所起步,虽然没有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专题领域中的“热点”,但学者们在史料整理、理论论辩以及史实考证方面,仍然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可贵的探索,其学术价值不可忽视,成为以后开展深入研究的基点。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