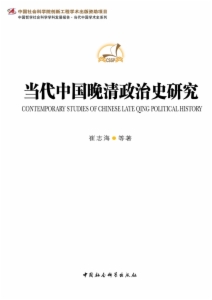第五节 关于戊戌变法的性质和历史评价问题
|
来 源
:
|
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 | ||
|
摘 要
:
|
一早期关于戊戌变法评价与性质的争论新中国成立初对戊戌研究的主要目标都集中在对戊戌的整体评价上,即对戊戌变法性质、历史作用等理论问题的具体评价。首先,学者们纷纷撰文,反对强加给戊戌维新以“改良主义”的恶谥,力主肯定戊戌变法的积极作用,充分肯定戊戌变法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猛烈的冲击,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救亡爱国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如何将康、梁的变法思想及活动与清政府的改革进程协调起来,找到其中的契合点和区别,反映一个改革时代真实全面的历史场景,应是今后戊戌变法史研究的努力方向之一。 | ||||||
|
关键词
:
|
改良主义 资产阶级 学界 资本主义 戊戌维新 政治 纲领 封建主义 激进主义 顽固派 政治纲领 |
||||||
在线阅读
第五节 关于戊戌变法的性质和历史评价问题
字体:大中小
一 早期关于戊戌变法评价与性质的争论
新中国成立初对戊戌研究的主要目标都集中在对戊戌的整体评价上,即对戊戌变法性质、历史作用等理论问题的具体评价。戊戌变法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是进步和爱国的,在这一点上,学界并无分歧。但是在具体表述方面,学界也有细微差别,并产生了相应的学术争鸣。
对于戊戌变法的性质,邵循正认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因为维新派虽然主张在政治上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一些改革,却不触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基础,形式上基本采取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逐渐变革。因此,“它是地主阶级中有一部分人企图使自己转化为资产阶级这一事实而发生的政治运动。他们企图在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利用原有的政权力量来发展资本主义。因此,就其本质上看,它只能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注] 黎澍则强调,“当时中国农村中已有许多征象足以表明农民革命运动可以再起,但维新派是站在反对农民革命立场上的,他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皇帝一人身上,这正是改良主义思想的必然表现。”[※注] 汤志钧在分析了戊戌变法时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的主张和动态后,也认为甲午战后统治阶级出现分化,由顽固派和洋务派形成的后党把持着政权,而光绪帝身边则聚集了一些没有实权的官僚形成帝党。维新派要求进行从上而下的改革,遂与帝党结合,主张在皇帝的独断下改革某些弊政,基本上还是拥护封建制度的。但是,“从本质上看,这是改良主义运动,他是向封建专制要民主,他的目的是要达到君主立宪”[※注]。
刘大年从维新派的阶级基础和政治构成,论证了戊戌维新是改良主义运动的根源。在他看来,维新派的成员是从地主官员转化而来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者,他们“主要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国内新式企业的创办者,不满现状的中小官吏和地方绅士”。他们不是当权派,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革命的要求,因此,只能选择“在他们看来是最可行的改良主义道路”[※注]。尽管表述各有侧重,但改良主义的定性是一致的。
另一个讨论较为激烈的问题是康有为《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及其评价问题。李泽厚认为,《大同书》是“通过乌托邦的方式比较集中和没有掩盖地表达了康有为前期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注]。汤志钧则认为评价过高,指出该书成书年代较晚,大约在1901—1902年,反映的是康氏晚年“反对民族民主革命”,“主张保皇复辟的理论基础”。[※注]为此,李泽厚写了反驳文章,继续申述自己的见解。[※注]
二 80年代之后关于戊戌变法的性质和历史评价问题的探讨
80年代初期学者们回到唯物史观的立场,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揭露“文化大革命”中颠倒是非的错误做法,倡导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同时,对于“文化大革命”前研究中所存在的忽略中国历史自身的特殊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化、公式化,过于强调阶级斗争的分析方式,动辄给历史人物“贴标签”的非历史主义倾向,以及庸俗化地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夸大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农民起义和战争的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反思和总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80年代对戊戌变法的性质、历史作用这些老问题的讨论和争鸣又有了新的高度。
首先,学者们纷纷撰文,反对强加给戊戌维新以“改良主义”的恶谥,力主肯定戊戌变法的积极作用,充分肯定戊戌变法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猛烈的冲击,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救亡爱国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林增平认为,把戊戌变法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很不妥当,导致人们对其评价偏低。其实,称戊戌变法为改革、改良均可,称作改良主义则是错误的。[※注] 陈旭麓也认为,改良主义是19世纪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种很不光彩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流派”,维新派实行的改革,虽然没有发动群众,也没有触动旧的社会基础,却要求做较大的社会革新,与改良主义迥然不同,他们遭到封建顽固派的镇压也可说明这一点。[※注]
叶林生也认为,改良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一种“恶谥”,用这个概念硬套戊戌变法和维新派,同样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何况,维新派策划杀荣禄、围颐和园等行动多少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注] 另外,汤志钧、苑书义等学者,坚持认为将戊戌变法确定为改良主义是适宜的,称其为改良主义,也不意味着会贬低其进步作用;况且,改良主义也非专指工人运动中以不触犯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少许改良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潮流,列宁对改良主义特征的论述对研究中国的戊戌变法也有指导意义。[※注]
李时岳的评价更鲜明一些。他认为百日维新“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维新派和守旧派的斗争,实质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顽固势力之间的阶级斗争”。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国,具有明显的反封建主义性质,绝非改良主义。[※注] 杨立强也提出戊戌变法要求君主立宪,已经是资本主义的政权形式了,将其说成仅仅要求改变旧事物的某些枝节方面,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尽管维新人士有过无意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的言论,但事实上变法过程中激烈的斗争已经昭示出它是“一场真真实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变革运动”[※注]。更有论者认为“戊戌维新的中心内容是要向封建顽固派夺权,实质是资产阶级向地主阶级夺权,是辛亥革命的一次预演”[※注]。对此,陈锡祺表示异议,认为可以给予戊戌维新以较高的评价,但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还不能令人信服。从理论准备和当时的国情分析,都不具备通常我们所理解的“革命”的意义。[※注] 上述讨论在当时颇为热烈。
对于戊戌维新的历史作用及其评价问题,50年代学界普遍认为,维新派指望光绪皇帝自上而下进行变法来摆脱封建主义束缚,实在近乎幻想,而百日维新自身的彻底失败更加证明“改良主义的破产”不可避免。[※注] 到了80年代,仍有类似的评价,而且表述更为严谨全面。胡绳指出,维新派要求变法,要求上层建筑发生某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变革,但对于封建制度的批判是肤浅的,也不是站在封建制度的对立面进行批判,恰恰相反,维新派面对封建制度的灭亡,抱着一种“无限悼惜的心情”,唱着“绝望的挽歌”。可见,戊戌维新运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但主观上不过是想为旧制度注入新的“生机”而已。[※注] 与此相比,李时岳的观点有所不同,他将戊戌维新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相并列,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四个阶梯,认为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客观作用’,更不在于它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而在于它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召唤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注]。相比而言,对戊戌变法的评价似乎更高一些。
关于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关系,20 世纪50年代的基本看法是二者不存在承继关系,因为,洋务运动是“反动的”,推行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化路线,与具有进步意义的戊戌变法不可同日而语。[※注] 到了80年代,随着对二者的重新评价,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得到提升,学界开始认为,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存在着既否定又肯定的继承关系;二者是前后交错、互相联系的两个阶段,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阶段的代表。李时岳、陈旭麓、徐泰来等先后撰文对此进行了新的阐释。[※注] 同样,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以前过于强调彼此对立的一面,而其相通之处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运动的性质来看,二者有鲜明的继承关系,同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注]
有关戊戌维新与帝国主义的关系,50年代普遍一边倒地认为维新派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对如何摆脱帝国主义侵略无计可施,没有把帝国主义视为造成中国贫困的最大根源,相反却把这种侵略活动看作可以刺激中国“奋发图强的一副良药”,最终导致变法的失败。[※注] 这些结论与抗美援朝前后高涨的反帝斗争气氛是有直接关系的。当然,这样的分析不免片面之处。80年代后,学界主张具体分析问题,在一些学者看来,帝国主义当时并未公开反对变法,有些言论还是有利于维新派的;无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也还有利于维新运动。即使外国人中也有外交官、传教士的区别,所以,评价也要具体研究,不宜泛泛而论。[※注]至于戊戌时期传教士在西学宣传和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积极作用,也不可一概抹杀。[※注]
关于维新派的政治纲领问题,80年代学界也曾有过讨论。刘大年认为,“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是戊戌年四月以前维新派的政治纲领,实际上百日维新中康、梁等改良派争取到接近光绪帝的机会后,就抛弃了建立“立宪政体”的政治理想,背弃了自己的政治纲领。[※注] 宋德华则认为“背弃”说有失公允,维新派其实一直坚持“革弊政、变成法、去尊隔、通下情、改官制”的政治纲领,其核心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试图依靠君权来推行变法,而非“尊君权。”[※注] 房德邻重申“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作为维新派的政治纲领不容置疑,康有为提出的“设议郎”可视为近代议院的初阶;维新派不提开议院而提出设制度局是因为受到阶级力量薄弱条件的限制,与“开国会、定宪法”的目标相比,只是在实行立宪步骤的迟速上不同而已,不可说维新派“背弃”了自己的政治纲领。[※注] 虽然,上述讨论立论各异,却明确了康、梁曾调整政治纲领和目标的实际情况。
另一方面,自80年代末,起源于文化评价中的“保守主义”思潮,逐渐渗透到史学研究领域。有学者一反学界对戊戌的积极评价,认为戊戌时期乃至整个近代中国,“救亡压倒了启蒙”,因而延误了本来可以正常发展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对戊戌变法的激进主义倾向提出了批评。到底是救亡唤起启蒙,还是救亡压倒启蒙,金冲及以为,恰恰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这是近代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他认为,“救亡不是启蒙的对立物。如果没有救亡这种燃眉之急的强烈推动,中国的民主启蒙运动要在全国范围内达到如此广泛的程度,可能还要经过漫长得多的路程。”[※注]本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已认识到“革命”与“改良”二者既能互相兼容,又可彼此牵动,基本上已经抛弃了关于戊戌变法是保守主义与改良主义的评判,予以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不料,又出现了视其为“激进主义”的观点。马洪林认为,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前有“保守反动”的恶溢,后有“激进主义”的鞭挞,这种反差现象说明,仅仅用现代观念去解释戊戌变法,很容易偏离历史真实、历史文献和学术规则,这种研究方法是不可取的。不可用简单化、绝对化的“保守”与“激进”来概括戊戌变法。[※注]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迄今为止的60多年,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迅速发展的时期。以1979年为界,又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历史时期。史学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了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就戊戌变法研究而言,80年代及80年代以前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戊戌变法的性质、历史作用、历史地位,以及主要历史人物的评价等问题上,理论色彩强,问题讨论集中,形成了热烈的学术争鸣;90年代后,这种活跃的氛围已经很少,研究热点比较分散,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往往很具体细微,缺乏理论关怀,考据与实证研究更加受到推崇。这种现象已到了值得反思的时候。尽管我们对历史细节的了解增多了,并且纠正了不少既往的谬误,但对整体戊戌变法史的宏观思考可能削弱了,对于目前戊戌变法叙述体系存在的偏颇缺乏整体反思。究其原因,或在于既有研究对康、梁在戊戌变法中的实际影响有夸大的嫌疑;相反,对于清政府在甲午后的整体改革评价过低。如何将康、梁的变法思想及活动与清政府的改革进程协调起来,找到其中的契合点和区别,反映一个改革时代真实全面的历史场景,应是今后戊戌变法史研究的努力方向之一。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