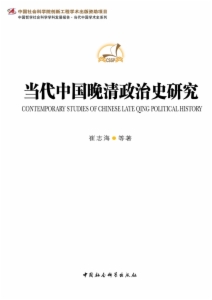第三节 义和团运动与国内政局关系研究
|
来 源
:
|
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 | ||
|
摘 要
:
|
就清朝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来说,大致说来,在1950—1966年义和团研究起步阶段,国内学者从义和团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出发,强调清政府与义和团之间的对立关系,比较倾向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一开始就采取镇压政策,只是在义和团力量愈来愈大、剿不胜剿的情况下。而在80年代之后,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趋于客观和全面,有的学者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对义和团的态度和评价其实并不一致,既有持肯定或同情态度的,也有持否定态度的, “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对义和团一概持否定态度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注]。该著代表了国内庚子勤王运动研究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 | ||||||
|
关键词
:
|
义和团 东南互保 态度 学界 民族资产阶级 勤王 学者 政策 帝国主义 保皇 湖广总督 |
||||||
在线阅读
第三节 义和团运动与国内政局关系研究
字体:大中小
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和发展除了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地域文化及国际背景之外,它与中国国内政局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中,又与清朝政府的关系最为密切,这是国内史学界比较一致的共识。
就清朝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来说,大致说来,在1950—1966年义和团研究起步阶段,国内学者从义和团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出发,强调清政府与义和团之间的对立关系,比较倾向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一开始就采取镇压政策,只是在义和团力量愈来愈大、剿不胜剿的情况下,清政府才改剿为抚,不赞同清政府在反对西方列强中与义和团存在同盟或合作关系。[※注]
与此相一致,国内学者对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也极力作正面诠释,认为这个口号具有策略意义,“是农民善于用计策的高度表现”,利用清朝政府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吸引反教群众加入,便于进行斗争,“是革命人民解决当时最主要的民族矛盾在斗争策略上的大胆创举,它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使人民反帝斗争运动踏上了一个新的阶段”[※注]。
在这个问题上具有指导意义的是,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颇有见地地将清朝统治者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具体细分为以下几派:1.以袁昶、许景澄等为代表的反对派;2.以载漪、刚毅、徐桐等为代表的赞成派;3.以荣禄和奕劻等为代表的反复派;4.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动摇派;5.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代表买办地主阶级的实力派疆吏。但站在义和团农民阶级立场上,范著与这一时期国内学者一样,对各派清朝统治者都持否定态度。[※注]
进入8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的观点发生明显转变,趋于客观,比较一致倾向于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开始时采取了“以抚为主”的政策,或认为清政府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或谓实行“一种有限度的镇压”政策,或曰摇摆在“武力镇压”和“以民制夷”之间,或曰奉行“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的政策。并且,国内学界在讨论中还比较一致地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前后有所变化,经历了由剿抚兼施发展到招抚,最后又转向坚决剿办的演化过程。[※注] 围绕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国内学界还就慈禧太后,山东巡抚毓贤、袁世凯、荣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清朝官员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进行了广泛持续的讨论。因限篇幅,兹不做具体介绍。
而在如何看待清政府剿抚政策及清朝官员对义和团态度的问题上,国内学界也趋于理性和客观,不是站在义和团的立场上进行简单的肯定和否定,而是从统治阶级政策的动机和后果进行判断,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进行具体分析。如林敦奎和李文海在1981年发表的《封建统治阶级与义和团运动》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不能简单地以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作为判断当时某个政治派别和政治人物是非好恶的唯一标准。不能认为,凡是支持义和团的,都是爱国的、进步的;凡是反对并主张镇压义和团的,都是卖国、发动的。当然也不能反过来,如解放前大多数论述和研究义和团运动的著作那样,认为支持义和团的一律都是昏昧顽固之徒,而反对义和团的则统统都是明达有识之士。历史的真实要比这个远远复杂得多。”[※注]
具体说来,国内学界对载漪、刚毅、徐桐等顽固派支持义和团运动基本都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鼓动义和团排外,完全出于私利,达到拥立载漪之子大阿哥继承皇位目的,不但不是爱国者,反而是中国历史的罪人[※注];或认为他们鼓吹和崇尚迷信,与中国近代进步潮流背道而驰。[※注]对于袁昶、许景澄等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反对派,不但不再简单斥为帝国主义的“奴才”或“卖国贼”,并且认为是出于理性,“应属于近代爱国主义的范畴”,“应归于爱国者行列”,体现了传统士大夫的理性与激情。[※注] 对于如何看待清政府政策和慈禧太后态度的反复与变化,虽然存在一些分歧,但基本都认同系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1.受义和团运动发展状况及清政府和西太后对义和团认识的影响;2.受西太后在训政和废帝立储等问题上与列强矛盾的影响;3.受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影响,承认清政府和慈禧太后支持义和团一定程度上也有抵御外侮的动机。[※注] 这较诸80年代之前一味强调义和团与清政府之间的阶级对立,是一个重大进步。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义和团运动的关系,国内学者在前期的研究中多站在义和团的革命立场上,比较笼统地批评民族资产阶级对义和团运动持轻蔑和敌视态度。[※注] 而在80年代之后,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趋于客观和全面,有的学者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对义和团的态度和评价其实并不一致,既有持肯定或同情态度的,也有持否定态度的,“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对义和团一概持否定态度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注];有的学者则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对义和团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前后有所变化的,他们在义和团运动初期和高潮时采取了敌视和批判态度,但在义和团遭列强和清政府残酷镇压之后,他们又较多地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义和团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和肯定,并指出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和批评义和团的反洋教,并非他们对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和危害缺乏认识或不思抵制,也不存在所谓对帝国主义软弱或仇视人民群众的问题,而是由于义和团本身浓厚的反维新色彩及其宗旨的盲目性和落后性,由于维新派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已基本摆脱了中国传统封建主义和落后意识的束缚及影响,由自发的因应抗拒转变到了较自觉的调适和斗争,因此,维新派批判和否定义和团反洋教,不但不具有反动性,而且恰恰相反,表现了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的维新派在思想意识和政治行动上的进步性。[※注]
此外,学界对义和团运动时期南方发生的“东南互保”和“勤王运动”(又称自立军起义)也分别作了较为深入和持久的研究。
对于在清政府对外“宣战”之后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和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等策划的“东南互保”,国内学界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评价。
一派完全持否定态度,认为刘、张等人策划“东南互保”,投靠侵略者,目的在于维持和发展个人及小集团权势,是十分卑鄙无耻的行为,是刘、张等人推行对内镇压、对外投降路线的一个必然结果,不但严重阻碍了东南地区各地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而且为列强集中兵力入侵华北、镇压义和团,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给华北地区义和团斗争带来严重困难。[※注]
另一派则持肯定态度,认为刘、张策划的“东南互保”,不但没有丧失新的国家主权,而且以地方外交形式阻止了列强对东南和长江流域的武装入侵,这在一定程度上既维护了中国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也在客观上对稳定东南社会秩序、维护东南和沿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表示对“东南互保”“应该予以正确的正面评价,赋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注] 有的虽然承认“东南互保”对列强集中兵力镇压华北义和团运动有负面影响,但同时不赞成将“东南互保”完全看作卖国和分裂中国之举,指出刘、张等策划“东南互保”的目的主要为维护东南地区免受战乱之苦和力保国土再遭列强践踏,不能一概以对外“主战”和“主和”作为区分爱国和卖国的标准。[※注] 有的则对“东南互保”进行中性分析,认为刘、张等策划“东南互保”,源于对清廷“招抚”政策的彻底失望、外国的军事压力和政治诱惑及来自东南社会精英阶层的强烈要求;指出“东南互保”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是晚清东南社会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场域在受到外部挑战过程中萌发的一种自觉的集体政治行为。[※注]
大致说来,前一派的观点代表了90年代之前国内学者对“东南互保”的认识水平;后一派观点代表了90年代之后国内学者的最新认识,折射了不同时期学界两种不同史观。
关于义和团运动时期南方发生的“勤王运动”或“自立军起义”事件,国内学界主要对这一事件的性质存在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自立军起义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或序幕。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自立军起义的主要领导者都是从维新派中分化出来的革命分子和兴中会会员,它的基本队伍是具有反清传统的哥老会,它的政治纲领为爱国救亡和反清革命,起义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已经超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范围。[※注]
另一种观点认为,自立军起义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是戊戌变法的继续或尾声,他们的理由是自立军起义受康梁保皇派领导,它的直接目的是“勤王”,迎光绪复位,抵制当时势如燎原的义和团运动和方兴未艾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注]
第三种观点认为,自立军起义是当时政治局势、阶级力量、社会意识的综合产物,既有保皇勤王色彩,也有反清革命的基本特征,是一个由保皇走向革命的过渡性事件,革命或保皇都不足以准确概括其性质,它具有复杂的两重性。[※注]
鉴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国内的许多先进分子的思想正处在改良和革命的抉择之中,革命和改良的分野尚不像稍后那样泾渭分明,同时也鉴于革命和改良两派的政治势力都参与了对自立军起义的领导,以及自立军起义表现出来的矛盾纲领和主张,上述第三种观点应该说更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情况。
而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自立军起义研究中,桑兵教授的《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以详尽的史实,揭示了这场运动远较我们认识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以及对这个复杂历史事件进行简单定性所遭遇的尴尬和窘境,并从庚子前后中国政局的演变对这一事件做了重新定位,认为勤王事件是庚子年中国趋新各派(包括海外华侨)在南方发动的一次变政救亡努力,它与北方义和团的本能反抗斗争不但相辅相成,而且更代表了中国救亡的方向,其意义远在义和团之上。该著代表了国内庚子勤王运动研究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