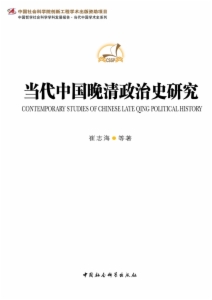第四节 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外关系问题研究
|
来 源
:
|
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 | ||
|
摘 要
:
|
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德国对华政策,国内学者既指出19世纪末德国在山东的殖民侵略和传教活动对义和团兴起的影响,以及德国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认为德国是八国联军的“积极参与者之一”,其陆军元帅瓦德西担任联军总司令,无数爱国同胞死于侵略军的屠刀之下。对于日本,国内学者揭露其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是通过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取得充当欧美列强承认的“远东宪兵”的资格,进而确立其在东亚的霸权,指出日本侵略军在大沽,特别是在天津、北京的战役中,成了八国联军的主力,从而取得了列强公认的“远东宪兵”的资格。鉴于义和团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中外战争,加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努力方向。 | ||||||
|
关键词
:
|
八国联军 学者 对华政策 列强 侵华 门户开放 联军 政策 元凶 帝国主义 拳民 |
||||||
在线阅读
第四节 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外关系问题研究
字体:大中小
义和团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中外战争。因此,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中外关系一直以来是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主要涉及八国联军侵华和各国对华政策两个方面。
关于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在这一研究领域,由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三位同志编撰的《八国联军侵华史》一书代表了目前国内学者所达到的最高水准。该书根据各国扮演的角色,将八国联军从酝酿组建到最后撤军过程分为以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0年1月至5月底,即从列强向清政府提出第一次严重照会到决定联合出兵,这是八国联军的酝酿组建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法国是倡议列强进行武装干涉的带头者,英、美、德、意是附和者,俄国和日本则未参加列强对清政府的抗议行列。第二阶段从1900年5月底至6月中旬,即从列强“使馆卫队”进京到西摩联军北犯,为八国联军侵华的初期。在这一阶段里,英国在进京的“使馆卫队”和西摩联军中均起了主要作用与领导作用。第三阶段从1900年6月中旬至7月中旬,即从联军大规模驶抵大沽至攻克天津,这是八国联军武装侵华的第一高潮。在这一阶段里,俄国不仅出兵最多,而且是炮轰大沽炮台的主谋者、镇压天津外围义和团的主力军、攻陷天津城的急先峰和统治天津的决策人,其作恶之甚和影响之坏,超过了联军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第四阶段从1900年7月中旬至8月14日,即从联军计划进军北京到攻克北京,这是八国联军武装侵华的第二高潮。在这一阶段里,俄国退居次位,起先锋和主力作用的是代之而起的日本。第五阶段从1900年8月15日至1901年9月,即从北京沦陷到联军最后撤兵,这是八国联军侵华的尾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德国是扩大武力侵略的主谋和元凶。
在论述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过程中,国内学者还对列强特别是英俄之间的关系和矛盾进行了探讨,其看法出现一些分歧。李德征认为列强在侵华过程中虽然形成了以英、美、日为一方和以俄、法为另一方的两大侵华集团,但勾结仍是其主流,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并一直服从于它们镇压中国军民的反抗和讹诈中国的需要。[※注]胡滨则更加强调列强之间的矛盾,认为义和团运动时期列强在华的矛盾和斗争是十分尖锐和复杂的,以致后来爆发日俄战争,重新划分它们在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当时并不存在以英、美、日为一方和以俄、法为另一方的两大对立集团的情况,事实是俄法结成一伙和英日结成一伙的倾向比较明显,而德、美两国则不然,态度并不固定,各列强之间始终是既有勾结,又有矛盾,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
在关于谁是组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元凶和组织者这一问题上,国内学者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说俄国起了主导作用,认为俄国在八国联军中充当了“主角”“元凶”或“祸首”的角色。[※注] 但另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八国联军是一个松散的军事联合体,内部矛盾重重,各国实力的消长不断变化,谁也无力总执牛耳,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始终如一的主谋和元凶,事实是法、英、俄、日、德分别在不同阶段扮演主要角色。[※注] 也有学者指出,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过程中俄国完全可以成为联军的主角,充当元凶,然而俄国政府却自动采取有限干涉政策以保持“行动自由”,这里主要是出于与英国争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战略考虑。[※注]
关于义和团运动时期各国对华政策,国内学者的研究受现实国际政治的影响,同时也受语言和资料条件的限制,很不平衡,对义和团运动时期美、俄两个大国的对华政策作了较多探讨。
就义和团运动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来说,50—60年代国内学者多站在反对美帝的立场,一定程度上将美国看作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最凶恶敌人,称“美帝国主义是参加这次武装镇压的主要刽子手之一”,“滔天的罪行证明美帝国主义一贯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注]。同时,对这一时期美国推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完全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凶狠毒辣的政策”[※注],“是美帝国主义为最后独占中国开辟道路的政策”[※注]。七八十年代,随着中美建交、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国内学者就如何重新评价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展开热烈讨论。一些学者指出“门户开放”政策虽然是根据美国需要提出来的,但它在客观上对抑制或延缓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不宜完全否定其历史意义。[※注] 进入90年代,一些学者又对“门户开放”政策进行新的诠释,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个不同于19世纪欧洲旧殖民主义的新的扩张方式,目的在于谋求美国的大国地位。[※注] 也有学者对义和团时期美国与其他列强之间的分歧和不同进行具体考察,指出义和团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对列强来说,它采取独立的、不合作的立场;对中国来说,避免她被进一步瓜分成势力范围;对美国自身来说,它追求更多的商业利益,并认为这是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一个具体体现。[※注] 有的学者认为在1898—1901年义和团运动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是美国对华政策承上启下的转变时期。[※注] 另有学者从跨文化学角度,对不同时期和不同群体美国人心中的拳民形象及拳民形象对美国人中国观的影响进行了长时段的考察和分析,指出尽管拳民形象在美国延续与演变的过程中大众想象与学术研究之间有着不断对话的关系,美国的中国学专家为澄清大众有关拳民形象的误解作了不懈努力,也为美国政府的决策提供了较为全面、客观的历史,但植根在美国大众中的模式化和妖魔化的拳民形象迄今仍然深刻影响着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仍然有待中美两国共同努力化解这一负面形象,以增进两国的相互理解。[※注]
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俄国的对华政策,既往研究除对俄国与英国的矛盾做了较多分析外,着重对沙俄侵占中国东北和东北军民的反抗斗争作了充分的论述,内容涉及沙俄出兵东北,制造海兰泡事件,血洗江东64屯,先后占领齐齐哈尔、吉林和奉天,揭露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在东北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及侵略野心,指出沙俄武装占领东北,只是为把中国东北变为其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步骤,不但激化了俄国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同时也激化了俄国同英、日、美等帝国主义的矛盾。[※注] 另一方面,国内学者还就中俄围绕交收东三省所进行的艰难和错综复杂的交涉过程及英、德、法、日、美等国的态度等作了深入的探讨,既肯定1902年4月8日签订的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挫败了沙俄吞并东北的图谋,俄国终于同意从东三省撤军,同时也指出该条约的某些条款为俄国后来拒绝撤兵,引发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注]
关于义和团运动时期英国的对华政策,国内学者认为英国作为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它在策动对华侵略和镇压义和团运动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注] 有的则对义和团运动时期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动向,特别是英国在策划“东南互保”中的角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指出英国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充分体现了英国一贯以来对在长江流域特殊利益的关心及将长江流域看作英国势力范围的意图。[※注] 另有学者还对英国与“门户开放”政策的关系作了深入的考察,指出该政策实由英国最先于19世纪末向列强提出,但由于英国倡导“门户开放”政策和参与瓜分活动的双重身份,导致英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面临破产,于是它转而向美国施加影响,促使出面争取各主要侵华国家承认“门户开放”政策,著名的海约翰照会便由此而来。[※注]
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德国对华政策,国内学者既指出19 世纪末德国在山东的殖民侵略和传教活动对义和团兴起的影响,以及德国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认为德国是八国联军的“积极参与者之一”,其陆军元帅瓦德西担任联军总司令,无数爱国同胞死于侵略军的屠刀之下,德国还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留下极不光彩的记录;同时也对德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友谊加以肯定。[※注]
对于法国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对华政策,国内学者一是对天主教会特别是北京主教樊国梁的侵略活动作了揭露和批判[※注];二是对法国政府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了探讨。有的学者指出法国作为在中国传教势力最大的国家,它在最初促成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过程中,曾扮演了元凶的角色,在义和团运动初起时法国驻华公使毕盛率先作出反应,联络各国公使向清政府递交照会,催促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镇压义和团,同时法国政府也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竭力促成列强联合出兵侵华,并最先建议列强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以便从根本上削弱清政府的抵抗力量。在谈判签订《辛丑条约》的过程中,法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与他国不同的主张,并始终把维护列强的联合置于对华外交的最优先地位。[※注]
对于日本,国内学者揭露其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是通过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取得充当欧美列强承认的“远东宪兵”的资格,进而确立其在东亚的霸权,指出日本侵略军在大沽,特别是在天津、北京的战役中,成了八国联军的主力,从而取得了列强公认的“远东宪兵”的资格,第一次加入帝国主义侵华的国际“俱乐部”。[※注] 有的学者进一步揭露日本在义和团运动中不但将入盟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看作日本“脱亚”进而“入欧”的跳板,而且试图利用义和团运动之机单独出兵占领福建厦门,作为其推行“大陆政策”的新起点,并通过放弃占领厦门,赢得英美的支持,由此进一步奠定日本在列强中的地位,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之一。[※注]
关于中外议和谈判和《辛丑条约》的签订。国内学者对议和谈判的出台及列强围绕议和条件的矛盾和争吵作了具体考察和探讨,并且一般多认为所谓议和谈判只是列强之间的分赃会议,议和谈判并不是在列强与中国之间进行的,而是由列强自行商定,无所谓中外互议,《辛丑条约》是中华民族一个空前的大屈辱。但个别学者对此虽然也完全认同,而为说明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却将议和谈判看作“瓜分危机已经缓解”的一个标志,指出“帝国主义列强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五六年间瓜分中国的野心和实践已经被义和团运动所阻止。否则,他们在京、津沦陷以后完全可以由他们自己来开一个会,讨论一下那一块土地属于那个强国的势力范围,由那个强国来统治,成为那个强国的殖民地也就够了,这样的分赃会议根本用不着重开中外议和谈判”,这说明“他们毕竟不得不承认中国为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作为谈判的一方对待”。[※注]。该观点的失误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外议和只是列强将通过战争所攫取的各种侵略要求合法化的一种方式,并不意味着瓜分危机的缓解或对中国主权国家的尊重。
对于辛丑议和,有的学者还从国际法角度指出其非正义性,批评列强发动大规模的持久的对华战争,却不承认战争状态的存在,又要按战争法迫使中国议和,攫取大量政治、经济权益,这些都是违犯国际法规定的,充分表现了它们凭恃强权、蔑视公理的可耻面目;批评列强提出的赔款和“惩凶”等要求,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注]
在过去的60年里,国内学者对义和团时期的中外关系虽然做了一定的研究,有些不乏新见,但由于受资料和语言条件的限制,比较而言,还是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领域,高质量、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鉴于义和团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中外战争,加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努力方向。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