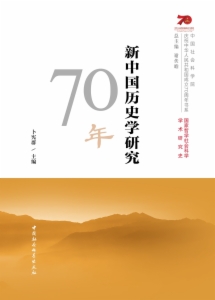第二节 帝陵和墓葬考古的全面化
|
来 源
:
|
新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3 | ||
|
摘 要
:
|
都城、城市和村镇是不同等级的人所聚居之地,是不同层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活动的差异化空间,是秦汉至明清时期考古发掘和研究最为主要的内容。2010年以后,为配合丝绸之路申遗工作,考古工作者对未央宫遗址进行全面考古勘探和重点发掘,取得一些重要的新进展。内蒙古文物工作队于1959 — 1960年对辽中京遗址进行过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 ※注] , 1962年对辽上京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和试掘,绘制了实测示意图[ ※注] 。二秦汉至明清地方性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秦汉至明清时期都城之外的城址发现很多,有州郡县城、村镇、军镇和军事要塞等,但大多都是考古调查资料,经过考古发掘的城址和村镇遗址很少。 | ||||||
|
关键词
:
|
考古 城址 都城 遗址 发掘 墓葬 考古工作 调查 考古发掘 窑址 勘探 |
||||||
在线阅读
第二节 帝陵和墓葬考古的全面化
字体:大中小
陵墓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历史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不同的社会阶层所形成的陵墓,体现出非常鲜明的等级差异。宋代以后,墓葬形制规模、墓葬壁饰和陪葬品等的差异,从贵贱之分越来越多地被贫富差异所取代。70年来的陵墓考古发掘资料,是最为丰富的领域,成为研究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问题的最主要资料。
一 秦汉至明清帝陵考古研究
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的陵寝。其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1974年以后,对陵区进行复查,并发掘了陵园旁的1—3号兵马俑坑[※注]、铜车马坑,陵园和陵区内的陪葬坑、陪葬墓和刑徒墓,陵园内的陵寝建筑等,取得了震惊世界的重要发现。20世纪末开始的秦始皇陵考古工作,推进了对陵园布局的整体研究[※注]。
西汉帝陵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2000年以前,主要是对西汉帝陵地面的考古调查,其中汉宣帝杜陵[※注]和汉景帝阳陵[※注]陵园进行过考古发掘。21世纪以来,国家文物局实施大遗址考古战略,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用新技术,开始对西汉帝陵进行全面的测绘和勘探,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推进[※注]。东汉帝陵在20世纪考古工作较薄弱。2003—2007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第二文物工作队启动“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开始对东汉帝陵分布和地望进行调查和勘测,并陆续发掘了一些陵园建筑基址和重要墓葬,极大地推进了东汉帝陵的研究[※注]。此外,河南省的所谓曹魏“高陵”[※注]的考古发现曾轰动一时。
北魏永固陵[※注]是北魏文成帝拓跋濬之妻、文明皇后冯氏的永固陵和孝文帝拓跋宏的寿宫万年堂。北魏迁洛后的邙山陵区共有孝文帝长陵[※注]、宣武帝景陵[※注]、孝明帝定陵、孝庄帝静陵[※注]和节闵帝[※注]5陵。21世纪的“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对北魏帝陵也进行了重新调查和测绘。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对东魏北齐帝陵区进行调查,发掘河北磁县湾漳壁画墓,推定其为北齐文宣帝高洋的武宁陵[※注]。
隋唐帝陵考古工作始于1953年。21世纪之初,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6—2012年开启“陕西唐陵大遗址保护项目”[※注],对关中十八陵中的10座唐代帝陵进行了重点考古调查、勘探和测绘工作,并对部分陵寝建筑进行了发掘[※注],初步了解唐代陵园形制发展演变及其陵园设计理念,取得重要的新突破[※注]。
北宋帝陵的调查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1992—199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北宋皇陵陵园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并发掘宋真宗永定陵上宫的建筑基址和永定禅院等,初步搞清了各陵的位置分布,陵区的构成和陵园的基本布局[※注]。南宋六陵在20世纪鲜有考古工作。2012年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南宋六陵的分布和陵园布局开始进行考古调查和测绘和试掘工作[※注],2018年对“宋高宗”一号陵园进行了考古发掘,开启南宋六陵考古的新阶段。
辽帝国有五处帝陵,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于2007—2010年率先对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进行全面调查、测绘和考古发掘。发掘了陵园内一号陪葬墓[※注]、四号建筑基址、甲组建筑基址和黑龙门遗址[※注],以及陵园外的龟趺山建筑基址[※注]。2012—2018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辽宁北镇医巫闾山辽代帝陵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新发现偏坡寺、骆驼峰、新立一号大墓和二号大墓等,发掘了新立建筑基址、琉璃寺遗址和琉璃寺西山遗址等,以及洪家街陪葬墓地、小河北陪葬墓地等,确认了辽显陵和乾陵的茔域,以及乾陵祭殿和玄宫等,取得十分重要的考古新成果[※注]。
西夏陵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始于1972年。考古学者重点发掘6号陵,以及一些陪葬墓和碑亭。1986—1991年,绘制西夏陵区总平面图,调查确认9座帝陵和200多座陪葬墓[※注]。2000—2001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3号陵陵园进行了发掘[※注],推进了对西夏王陵的研究。
金陵考古工作始于1986年。2001—2002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金陵进行了全面调查和钻探,在北京房山周口店龙门口村的主陵区,发掘了金太祖睿陵和世宗兴陵,以及神道及周边遗迹等[※注],但陵园内的布局尚未清楚。
明朝有5处帝陵。1956—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发掘明定陵,取得了重要的学术资料[※注]。朱元璋夫妇的明孝陵在下马坊区域进行过考古勘探[※注]。清代帝陵考古工作还是空白。
20世纪50年间,中国古代帝陵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还处于资料积累阶段[※注]。21世纪以后,国家文物局加强大遗址保护的政策,促进了汉代、唐代、辽代帝陵等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大突破和大发展。而且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注]。
二 秦汉至明清墓葬考古研究
秦汉至明清时期的墓葬发现数量巨大,研究成果也很丰富。但是墓葬发现数量存在明显的朝代和区域的不平衡性。汉代和唐代墓葬发现多,研究也较为丰富;辽代、宋代和明代次之。帝陵之外的墓葬,墓主人主要是贵族和平民。但在西汉和明朝还有一类墓葬介于帝陵和一般墓葬之间,即诸侯王墓。故这里分诸侯王墓和一般墓葬两类分述。
第一类:诸侯王墓
汉代和明代都有诸侯王墓,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存在。其他朝代的王墓不在此列。
70年来,西汉发现数十座类型丰富的诸侯王墓[※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是凿山为藏崖洞墓的代表[※注];北京大葆台广阳顷王刘建夫妇墓是“黄肠题凑”葬制的典型墓例[※注];河南永城西汉梁孝王墓及其寝园遗存[※注],是陵寝建筑的重要资料;广州象岗南越文王“赵昧”墓[※注]反映了附属国王陵的特点。21世纪以来,山东菏泽定陶发掘了哀帝之母定陶共王刘康之姬丁后墓[※注]。湖南马王堆軑侯家族墓[※注]、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注]等是汉代列侯墓的典型代表。东汉诸侯王墓发现的数量有限,研究较弱。
明代皇族诸王陵墓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重要的发现有山东邹县鲁荒王朱檀墓[※注]、成都凤凰山蜀王世子朱悦燫墓[※注]、湖北钟祥梁庄王朱瞻垍墓[※注]、山东长清德庄王朱见潾墓(M4)[※注]和江西南城益端王朱祐槟墓。明朝亲王墓基本都是仿皇陵,其建筑平面布局应该也是仿照当时的王府宫殿建筑。
第二类:一般墓葬
秦墓发现比较少,汉墓发现的数量在历史时期各王朝中最多,研究不断走向深入。20世纪的50年间,考古学者基本构建了汉墓的时空框架,并开始对汉墓进行综合研究[※注]。21世纪以来,学者对不同地区各时期不同类型墓葬的发展与演变、时代特征、地域特点和墓葬制度、埋葬习俗等研究均取得很大的成果[※注]。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揭示出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文化差异和融合情况,探讨秦汉统一帝国内各地发展的差异性和文化发展的趋同性[※注]。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墓葬发现多,集中于关中、华北和东北地区,在河西、新疆等地区也有发现。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注]、西安安伽墓[※注]、太原娄睿墓和徐显秀墓[※注]等都是重要发现。南方地区发现的江宁上坊孙吴墓[※注]、马鞍山朱然墓[※注]和当涂“天子坟”[※注] 等都是重要的高等级墓葬。一些学者根据新发现和新成果进行了综合研究[※注]。
唐代墓葬讲究厚葬,随葬品丰富,墓葬壁画精美,重要发现很多。以淮河为界,唐墓分为南北两大区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是唐代墓葬的大发现和基本框架构建的时期[※注]。随后的20年间,根据隋唐墓葬新的重要发现,学者逐步搭建起隋唐墓葬的时空框架,并对隋唐墓的形制类型、壁画题材、典型随葬品等,及其墓葬所反映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注]。21世纪以来,关于隋唐墓重要的新成果不是很多[※注]。
辽宋金元明清时期墓葬在20世纪,主要都是在基建中发现清理,研究水平较弱,处于时空框架的构建阶段[※注]。河南禹县北宋末赵大翁墓[※注],是北方地区墓葬形制的范例。《白沙宋墓》考古报告成为历史时期的学术经典。未被盗掘的内蒙古奈曼陈国公主与驸马墓[※注]和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注]、宝山壁画墓[※注]等都是辽代考古的重要成果。黑龙江阿城齐国王墓[※注]、山西稷山马村墓地[※注]、大同冯道真墓[※注]是金代考古的重要发现。陕西蒲城洞耳村壁画墓[※注]和安徽安庆范文虎墓[※注]分别是北方和南方地区的典型元墓。江苏苏州吴王张士诚父母墓[※注]是依照南宋帝陵攒宫制度建造成石藏子的结构,形制特殊。
历史时期陵墓考古的重要发现,从一开始就被史学工作者作为证经补史的手段,长期缺乏考古学本身的研究。进入21世纪,各个朝代墓葬的分期和分区、墓葬形制结构、随葬品及其组合特征和墓葬礼俗等研究有了很大的推进[※注]。历史时期墓葬考古研究有着美好的前景,必将为中国古代史的深入研究做出较大的贡献。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