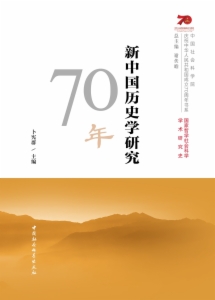第一节 隋唐五代史研究
|
来 源
:
|
新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4 | ||
|
摘 要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隋唐史研究是在辉煌与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的,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及改革开放以来两个阶段。一方面,得益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刊布,唐代政治史与制度史研究涌现了大量优秀成果,始终占据着隋唐史研究的核心地位,而近年随着“活的制度史”取径的流行,公文运转、信息渠道等话题使制度史研究呈现出新的样貌。可以说,他的研究在思考方式、研究角度上都与此前静态的职官研究有了很大不同,展示了邓小南提出的以“过程”与“关系”为中心的制度史研究取向的广阔前景。 | ||||||
|
关键词
:
|
文书 制度 敦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版 整理 吐鲁番 墓志 研究成果 社会经济 史学 |
||||||
在线阅读
第一节 隋唐五代史研究
字体:大中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隋唐史研究是在辉煌与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的,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及改革开放以来两个阶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与“以论代史”等影射史学的肆虐,隋唐史学界基本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成果。因此,第一阶段的隋唐史研究成果,大多完成于“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些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得以正式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隋唐史研究,一方面延续了民国时期的学术传统,如陈寅恪在抗战期间出版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基础上,继续撰写了《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等大批隋唐史论文,这些文章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结集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元白诗笺证稿》等,对“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隋唐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位延续民国传统的唐史学者是著作等身的岑仲勉,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发表的《登科记考订补》《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元和姓纂四校记》等之外,其《隋唐史》《府兵制度研究》等诸多论著都出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注]。如果说陈氏的隋唐史研究体现了中西汇通的“文化史观”,那么岑氏的研究更像是在以考据为核心的乾嘉学派基础上的更上一层楼。
另一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史学界影响的不断深入,这一时期隋唐史学界也出现了阶级分析等新的研究范式,涌现了一批以均田制、租庸调制为核心的经济史研究成果,也出现了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1979)这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关系、地租形态和地主经济等核心问题的理论著作。由于农民战争史成为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黄巢起义甚至规模不大的陈硕真起义等,都得到了细致研究。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除了胡如雷之外,还有唐长孺、汪篯、王仲荦、韩国磐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多种断代史著作,它们对隋唐史学科体系的建设颇具意义。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学术研究回归正常秩序,隋唐史研究也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首先是全国性专业学会的成立与各高校及科研机构隋唐史研究梯队的形成。1980年唐史研究会(1984年更名为中国唐史学会)和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相继成立,对隋唐史与敦煌学研究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复旦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隋唐史学科,都各自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梯队,成为隋唐史研究的重镇。
其次,专业学术集刊的创办,为隋唐史研究成果的刊布搭建了平台。唐长孺创办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史念海创办的《唐史论丛》、荣新江创办的《唐研究》无疑是隋唐史研究的三大核心集刊,其中《唐研究》在多学科交流、严格的学术规范及学术书评的写作等方面,颇有引领潮流之功。最近十年来,又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唐宋史评论》、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主办的《中国中古史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中古中国研究》等新刊问世,显示了隋唐史研究的繁荣。
再次,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刊布取得巨大成就。隋唐史的基本典籍如《隋书》、两《唐书》与新旧《五代史》等正史,《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唐会要》等法典与政书,以及大多数现存的唐人文集都得到了现代整理。[※注]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以墓志为核心的石刻史料先后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隋唐史研究的增长点。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古籍数字化的浪潮,“四库全书”“中华基本古籍库”“中华经典古籍库”等大型数据库相继建立,虽然也带来某些消极影响,但对古籍的普及和利用、对于材料的收集,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最后,在选题与研究路径上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一方面,得益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刊布,唐代政治史与制度史研究涌现了大量优秀成果,始终占据着隋唐史研究的核心地位,而近年随着“活的制度史”取径的流行,公文运转、信息渠道等话题使制度史研究呈现出新的样貌。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拓展与欧美、日本研究成果的引进,礼制史、宗教史、社会史等新领域呈现出活跃态势,这使隋唐史研究走出思路单一、选题陈旧的困境,呈现出多元化的繁荣景象。可以说,隋唐史研究中的宏大叙事(如所谓的“唐宋变革”“城市革命”等)与细节深描并存,共同为理解这一时代做出贡献。
一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石刻史料的整理与刊布
(一)敦煌吐鲁番文书
70年来的中国敦煌学研究也可大致分为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如1961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一辑出版,收录170 余种社会经济文书的录文,虽然在定名和录文方面还有一些缺憾,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文献整理工作。其他重要的文献整理研究成果还有《敦煌变文集》《敦煌古籍叙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等[※注]。
改革开放以来,敦煌学迎来了大发展和大繁荣。英藏、法藏、北图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在70年代末都已公开发行,1981年起黄永武《敦煌宝藏》又将缩微胶卷影印成册,为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提供了契机,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便是影响颇大的一种录文集[※注]。由唐长孺主持的新中国出土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顺利进行[※注],吐鲁番文书研究从此成为新的热点。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文集,如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1—5 辑[※注]、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及《二编》等[※注]。
20世纪90年代以后,敦煌文献的整理出版进入新的阶段。1990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编的《英藏敦煌文献》陆续出版[※注],该书收录文书齐全、图片清晰、定名准确,开创了整理出版大型敦煌图录的新模式。此后,《俄藏敦煌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大型图录相继出版,基本涵盖了敦煌文书的大宗收藏机构,敦煌文书的刊布接近完成。这一时期,王永兴、姜伯勤、宋家钰、陈国灿、杨际平、荣新江、郝春文等重要学者的敦煌学研究著作都结集出版,内容涵盖了丝绸之路、均田制、勾检制度、归义军、寺院经济等多个领域,展示了敦煌学的全面进步。《敦煌学大辞典》的编纂出版也是这一时期敦煌学进行总结的标志性成果[※注]。
进入21世纪,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出现了新的方向,吐鲁番、西域新出土文书及世界各地散藏文书的刊布成为新的趋势。例如,荣新江等主编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全用彩版并附有精确录文,成为新时代文书整理的典范[※注]。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数字化也逐步推进,由中、英、俄、日、德、法等国参与的“国际敦煌项目”(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简称IDP)陆续将各大机构收藏的文书高清照片上传网站,实现了敦煌资料的网络共享。随着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进步,一些新的视角也开始出现,如黄正建等先生提出的“古文书学”研究等。
(二)石刻史料
石刻史料的种类很多,如碑、墓志、摩崖、造像等,对隋唐史研究而言,墓志资料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张钫千唐志斋的贡献毋庸置疑。虽然一些重要学术机构都收藏有整套原拓,但迟至改革开放之后其拓本才得以全部刊布[※注]。
对于传统金石学的继承,是新研究的起点。从1977年到2006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陆续印行了《石刻史料新编》1—4辑,共计100册,收录金石学著作千余部,成为利用传统金石学成果的重要途径。1989—199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全100 册,使国图善本部收藏的大量珍贵拓片为普通研究者所知晓。几乎同时,《隋唐五代墓志汇编》30 册也陆续出版[※注],收录拓本5000 余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两套大型唐代墓志录文总集即《唐代墓志汇编》及其《续集》与《全唐文补遗》系列相继出版[※注],极大便利了学者对墓志的使用。
进入21世纪,一些公立博物馆如故宫、国博、陕博等相继把馆藏墓志整理出版,但更多的则是一些私人收藏家将其收藏的大量拓片印行出版,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洛阳的赵君平与齐运通,他们编著的诸多图录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唐代墓志[※注],可惜没有录文,整理工作不够彻底。从研究者使用的角度来看,录文与图版对照本无疑是最佳整理形式,胡戟、荣新江主编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2012)图版清晰,录文精审,堪称典范。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2007)及其《续编》(2014)、毛阳光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2013)及其《续集》(2018)等也都是成功之作。
总体而言,新发现的唐代墓志数量之巨令人震惊,仅气贺泽保规《新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和目录》收录的唐代墓志就已达12523件,远远超出两《唐书》人物传记的数量。这些墓志的志主既有大量中下层官员与处士,更有为传统史书忽略的女性与佛、道等宗教人士,不仅为隋唐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也生发出一些具有挑战性的新课题。
当然,对于石刻史料的利用也有需要反思之处:首先,要处理好“新”“旧”关系。学者追踪新材料是天性,但许多新材料尚未得到真正深入的研究,就已经变成旧史料了。其实,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旧材料就是新史料,甚至金石学著作中还有大量隋唐石刻未得到重视。其次,新出墓志固然重要,但那些体量巨大的碑刻可能更富研究旨趣,如颜真卿、柳公权等书写的那些书法名碑,其中蕴含的史学价值并未得到充分发掘。最后,此前学者大多关注碑志文本性层面,而甚少关注其物质性层面。最近,这个问题已开始被学者认识,《唐研究》第23卷被确定为“文本性与物质性交错的中古中国”专号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为今后的碑志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 从三省制到中书门下体制
政治史与制度史历来是中国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而现代意义的隋唐史研究,某种程度上是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出版之后才真正开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虽然整体理解隋唐时代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全超越陈氏两稿,但在许多领域依然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政治史方面,唐长孺提出的唐朝“南朝化”理论[※注],可能是最有启发性的宏观理论,他认为唐代在很多方面都接续了南朝传统,魏晋南北朝的出口在南不在北,这与田余庆的看法迥异,而适可互补。对于士族问题、牛李党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等传统题目,学界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之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视角。以藩镇为例,张国刚早年对中晚唐的藩镇问题进行了多方面考察[※注],其对藩镇类型的划分在学界颇具影响。近年来,年轻学者如李碧妍更强调从藩镇内部的组织形式与形成过程来思考藩镇问题[※注]。
至于五代十国史的研究,向来比较薄弱,早期的陶懋炳《五代史略》(1985)、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1991)有筚路蓝缕之功。进入21世纪,成果渐丰,任爽与杜文玉在这一领域用力颇深,如任爽先后主编了《十国典制考》(2004)、《五代典制考》(2007),杜文玉也出版了《五代十国制度研究》(2006),制度史的研究渐次深入。与此同时,对于十国中的个别政权如南唐与吴越国等,也出现了一些综合性的研究[※注]。此外,王赓武早年的英文著作《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近年有了中译本[※注],值得重视。
在隋唐制度史方面,宰相制度、三省六部制、使职差遣制、勾检制度、幕府制度、科举制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70年来的唐代政治制度史,一个明显的脉络,是从传统的静态的职官研究走向动态的政治体制运行研究[※注],而“中书门下体制”的提出,正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对三省制的形成与演变的考察,一度是隋唐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核心工作,吴宗国指出,隋朝将门下省、中书省从地处禁中的侍从顾问转变为在外廷独立处理政务的纯粹国家机关,三省最终成为一个按政务处理流程分工的有机整体,它们各有分工而又互相依存,共同组成了最高政权机关。至此,三省制才基本确立[※注]。
由此出发,刘后滨力图以政治体制的演进、官僚系统的运作、国家政务的运行三个层面来考察唐代前后期中枢体制的变迁,而其切入点正是奏抄、敕牒、商量状、起请等官文书的运行[※注]。刘氏勾勒的,是中晚唐独立的宰相机构“中书门下”从三省制内部出现并凌驾于三省之上的过程。可以说,他的研究在思考方式、研究角度上都与此前静态的职官研究有了很大不同,展示了邓小南提出的以“过程”与“关系”为中心的制度史研究取向的广阔前景。
三 均田制与唐代经济史研究的兴衰
民国时期,隋唐经济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如陶希圣、鞠清远、全汉昇等人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史长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自然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密不可分。在财政、土地、赋税、人口、货币、工商业等诸多方面,隋唐经济史研究都取得了重要进步。例如,在财政史方面,有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1991)和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1995、2001);在人口史方面,有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1993);在工商业方面,有张泽咸《唐代工商业》(1995)。不过总体而言,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曾长期占据着隋唐经济史研究的中心舞台。
从北朝到隋唐,均田制在具体规定上有了不少变化,但其国有土地所有制的基本性质并无二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关于唐代均田制是否实施的问题成为热点。1954年邓广铭根据敦煌户籍文书指出唐代并未真正实施均田制[※注],引发了大讨论。岑仲勉、韩国磐、胡如雷等学者先后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基本确认唐代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均田制。
改革开放之初,随着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的深入,关于均田制的讨论重新成为学界热点,对于应授田、实授田、常田、部田、自田等概念,乃至与田制密切相关的手实、户籍、计帐等文书,都有了大量成果。而日本学者相关成果的出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均田制研究走向深入[※注]。除去数量庞大的论文,相关专著就有近十部[※注]。随着戴建国利用天一阁所藏明钞本宋《天圣令·田令》对唐田令的复原[※注],均田制研究中长期争议的一些问题也有了解决的可能,杨际平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注]。耿元骊依据复原的完整《田令》,对均田制性质也提出了新的看法:“‘均田制’不是唐代存在的一种制度,只是后人的一种解释方法,是一种学术观点而非唐人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实践。”[※注]
进入21世纪之后,隋唐经济史的研究热潮逐渐退去,曾经汗牛充栋的关于均田制与赋役史研究更变得门可罗雀,这既有时代变迁的因素,当然也有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因素。值得关注的是,在经济史内部也出现了新的趋势如区域经济社会史研究,而江南成为主要的关注点。
四《天圣令》与唐代法制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隋唐法制史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这首先得益于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法制文书,如著名的《永徽律疏》《神龙散颁刑部格》《开元水部式》等,刘俊文对此有系统整理[※注],极便学界使用。刘氏《唐律疏议笺解》(1996)更是唐律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至于唐式,目前已有霍存福《唐式辑佚》[※注]。在唐令研究方面,从仁井田陞的《唐令拾遗》到池田温主持编集的《唐令拾遗补》,几代日本学者为唐令的复原做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发展迅猛,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宁波天一阁所藏《天圣令》的整理与后续研究。
1999年,戴建国首次公开了宁波天一阁所藏北宋《天圣令》钞本的存在[※注],唐宋史学界为之震动。《天圣令》于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修订完成,天圣十年(1032)颁行,其编修原则是在唐令的框架内修改、编订适于当时制度的条文,而将废弃不行的唐令内容附录于后。天一阁藏《天圣令》残存十卷,包括田令、赋役令等12篇。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达成合作协议,经过一年的整理复原工作,于次年正式出版《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以下简称《天圣令校证》),开辟了唐宋史研究及唐、日古代法制的比较研究的新领域。
《天圣令校证》的出版标志着以此文本为契机的唐宋令研究的全面展开。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中国学者已经发表相关研究论著500篇(部)。从总体来看,《天圣令》诸卷研究各有热点,如《田令》研究集中在土地制度与管理的讨论,《赋役令》较为关注的是工匠的问题、食封制度,《狱官令》研究聚焦流刑与流移人。《天圣令》中出现的一些语词,有的是出现在以往史籍中但语焉不详,有的则是首次出现,如“诸色人”的传统史料非常零散,《天圣令》则集中了一批各色人等的令文,引发了诸多对各类身份人释义与法典用词的探讨。《营缮令》的出现,使得国家公共工程的制度性研究首次有了切实的材料支持。这些新研究取向的获得,均有赖于《天圣令》新内容的支持。
《天圣令》最有价值的还是在法制史研究方面:第一,唐宋令关系。从法典编纂整体结构、条目顺序、文字继承关系等方面的讨论中,深入思考唐宋令文“移植与嫁接”的关系。第二,体例与令文复原。对《天圣令》整体研究还有较大空间,包括法典体例、编纂特色、与其他法律形式的联系与区分等。第三,唐日令比较。《天圣令》与日本《养老令》的高度契合,而缘此进行的中日比较研究还比较薄弱,这主要是对日本古代官制及相关政治、经济制度的研究欠缺所致。随着研究的深入,唐令复原工作将会更上层楼,而《天圣令》必将在传世文献与敦煌吐鲁番文书之间建立有效联系中发挥更为重要的桥梁作用。
五 粟特人入华与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
作为一个世界帝国,唐代沿着丝绸之路的中外文化交流始终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研究领域,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而向达早年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57)无疑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深入及北朝隋唐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对唐代丝路贸易的主要承担者粟特人的研究,一时蔚为热潮。粟特是属于伊朗人种的中亚古族,原本生活在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索格底亚那地区,主要范围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在中国古籍中,他们被称为“昭武九姓”或“九姓胡”“杂种胡”等。粟特人是天生的商人,也是勇敢的战士,他们不仅是丝路贸易的主要承担者,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粟特人的迁徙路线与聚落、粟特人的汉化、商业活动以及粟特地区与唐朝的文化、宗教关系等方面。荣新江等主编的《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2005)将28篇论文归入“粟特萨宝与商队贸易”“粟特聚落与地方社会”“入华粟特人的宗教与艺术”三部分,恰好归纳了粟特人入华问题上的主要研究方向。
早在1994年,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就有专章讨论粟特人的商业与宗教文化。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1998)展示了作者数十年粟特研究的心得。在世纪之交,北周安伽墓、康业墓、史君墓以及隋代虞弘墓相继在西安和太原发掘,其中刻有精美浮雕的围屏石榻或石椁内容极为丰富,立即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粟特祆教考古、美术的研究热潮,许多学者都积极参加其中,后来姜伯勤将其系列论文结集为《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2004)一书。必须提到的是,林悟殊对唐代“三夷教”有深入研究,其中也包括了粟特人信仰的祆教。
当然,中国粟特研究的领军人物无疑是荣新江,其代表作《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001)及其姊妹篇《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2014)收录了他关于粟特研究的诸多重要论文和书评。首先,荣氏用一系列论文勾勒了北朝隋唐粟特人从西域、河西走廊、两京、营州乃至江南的迁徙路线与沿途聚落,分析这些聚落的组织形式与内部形态。其次,粟特人的汉化及其与隋唐政权的关系,是荣氏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他讨论了粟特胡人对武周政权的态度,分析了作为粟特杂胡的安禄山家传的祆教信仰在其起兵叛乱过程中的动员作用,还认为敦煌归义军曹氏政权也是粟特人后裔,这些都令人耳目一新。最后,荣氏也从艺术史的角度对中古来华粟特人的多元文化有深入探讨,特别是对粟特祆教美术东传过程中的转化有极具说服力的解说。可以说,这两本书代表了自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以来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巨大进步。
六 礼制史与宗教史的崛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隋唐史研究在传统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社会史、日常生活史、数术史等异军突起,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礼制史与宗教史研究的崛起。
中国唐史学界关于礼制的研究,或可追溯到陈寅恪早年的经典《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该书第一章“礼制”甚至是全书的核心部分。不过,陈氏的研究并未被后来的唐史学者所继承,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唐礼研究是在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相关成果的刺激之下,由姜伯勤、胡戟等先生倡导起来的[※注]。20世纪末,有几部通论性著作相继出版,如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1998)、任爽《唐代礼制研究》(1999)等。
进入21世纪,中国内地的唐礼研究取得了真正令人瞩目的进步,其中代表性学者是吴丽娱。2002年,她出版了《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2002),此书通过对书仪“礼书”性质的把握,探讨一般民众如何了解和使用礼仪规范的问题,十分精彩。丧服礼制向称艰深,而吴氏《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2012)考察了唐代丧礼的诸多方面,大大提升了这一领域的学术水准。此外,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2009)跳出郊祀与宗庙,以更广阔的视野考察了国家祭祀的宗教性内涵、国家祭祀与佛道教及地方祠祀的关系等问题,对后来的唐礼研究有一定的引领之功。吴羽《唐宋道教与世俗礼仪互动研究》(2013)也有着类似的切入角度。朱溢对郊祀、宗庙与释奠礼仪等作了跨越唐宋的长时段考察[※注],王贞平则从东亚史的角度考察了唐代的宾礼[※注]。
随着石刻史料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深入利用,隋唐宗教史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荣新江主编的《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2003)涉及道教、佛教、三夷教及民间信仰,预示着宗教史研究即将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道教方面,葛兆光揭示了道教对国家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某种“屈服”[※注]。白照杰、李平分别对唐代前、后期道教形态的变化做出新的归纳,前者关注魏晋南北朝的宗派道教如何在隋与唐初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后者则关注了晚唐五代道教在修道方式上发生的变化[※注]。吴真采取一个类似于“层累造成”的史学分析方法,细致梳理了盛唐高道叶法善信仰在唐宋时期的演变[※注]。程乐松通过对《三洞珠囊》《道教义枢》等道教类书的分析,讨论了唐代道教知识与思想体系的构成[※注]。雷闻以石刻史料为中心,对王远知、邓紫阳、刘从政等高道的生平与传法谱系,以及两京重要宫观如龙兴观、大弘道观等都有细致考察。
佛教方面,范文澜《唐代佛教》(1979)虽然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但其对唐代佛教各宗派的分析相当犀利,至今仍有其独特价值。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1982)则更显平和,对唐代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佛经传译与著述、宗派研究等更加深入。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1997)对汉传佛教寺院的布局、管理、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讨论。敦煌文书对唐代佛教史研究有着重大意义,这在早年胡适的禅宗史研究中就表露无遗。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1998)、陈大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研究》(2014)都是利用文书研究唐宋敦煌佛教社会史的重要论著。另有两本书值得一提,余欣利用敦煌文书中丰富的宗教社会史材料,对敦煌的神灵谱系、墓葬神煞等都作了深入探讨,并提出“民生宗教”的概念,显示了超越文献考证、建立新解释框架的努力[※注]。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2014)探讨了隋唐时期的政治神秘性与合法性建构的关系。这些著作与以往以教义、哲学思想等为中心的宗教学研究已有了很大不同,而成为隋唐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