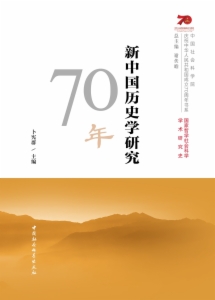第三节 明清史研究
|
来 源
:
|
新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22 | ||
|
摘 要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隋唐史研究是在辉煌与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的,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及改革开放以来两个阶段。一方面,得益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刊布,唐代政治史与制度史研究涌现了大量优秀成果,始终占据着隋唐史研究的核心地位,而近年随着“活的制度史”取径的流行,公文运转、信息渠道等话题使制度史研究呈现出新的样貌。可以说,他的研究在思考方式、研究角度上都与此前静态的职官研究有了很大不同,展示了邓小南提出的以“过程”与“关系”为中心的制度史研究取向的广阔前景。 | ||||||
|
关键词
:
|
文书 制度 敦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版 整理 吐鲁番 墓志 研究成果 社会经济 史学 |
||||||
在线阅读
第三节 明清史研究
字体:大中小
20世纪30年代,孟森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明史、清史,开创了明、清断代史研究之先河。孟森除关注一般的制度史外,亦重视明代女真史(满洲开国史)、康雍乾三朝边疆经营史[※注]。其关于明清时代划分及重要人物、事件的评价,受到后世研究者的广泛重视,影响持续于今。此外,梁启超有关清代学术史研究、郑天挺有关满族史及清初制度史研究、梁方仲关于明代黄册的研究、吴晗有关朱元璋及明初人物的研究、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研究、傅衣凌的明清佃农研究、李洵的晚明民变研究,也是当时明清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明清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逐步确立,明清史研究开始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一方面,制度史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如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1961)结合文书与文献,将制度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全面地阐述了明代黄册制度的始终。王毓铨《明代的军屯》(1965)全面地探讨了军屯的历史渊源与制度结构,阐述了军屯的生产关系与军屯的破坏过程,说明了军屯最终以民田化而终结。另一方面,有关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明末农民战争、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清初社会主要矛盾、明末清初启蒙思想等研究备受关注,相关专题性成果不断涌现,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珍稀古籍不断影印出版,中央与地方档案不断公布,民间文书大量发现,明清史研究进入全面繁荣时期。一方面,断代史著作不断,如戴逸主编《简明清史》(1980、1984),汤纲、南炳文著《明史》(1985、1991),中国史稿编写组的《中国史稿》第六册(明代卷,1987)、第七册(清代卷,1995),李洵、王戎笙等主编的十卷本《清代全史》(1991、1993),等等。这些断代史成果总结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既有所创新,亦有所突破,为全面地把握明清两代的治乱盛衰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经济史、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与中外关系史等不断向广度、深度拓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1989年8月,中国明史学会正式成立,成为团结国内外明史学人的重要组织。中国明史学会编辑出版《明史研究》和《中国明史学会通讯》,并与各方合作,举办各种类型学术研讨会,扩大了学术交流,推进了研究的深入。2002年10月,国家成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启动清史纂修工程。从那时到现在,该工程动员了全国清史相关专业人员近1500 人,历时12年完成初稿,总字数达3500万。[※注] 通过清史工程项目,大量珍稀资料得以刊布,许多重要的海外研究成果翻译出版,对于清史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有很多学者对于明清史研究的各个领域进行全面的总结,包括高翔《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注],南炳文《辉煌、曲折与启示: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注],钞晓鸿、郑振满《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注]、李治亭《改革开放中的清史研究40年》、赵世瑜《改革开放40年来的明清史研究》[※注],等等。本书将参照以往的研究成果,概要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明清史的伟大成就。本书只是对明清史研究中一些重要成果的评述,故不可能面面俱到。如果想了解更详细研究情况,可以参照相关的专题研究。
一 官府档案、民间文书的整理与研究
在明清史研究中,官府档案与民间文书数量庞大,史料价值尤为重要。官府档案包括中央政府档案与地方政府档案,以清代为主。中央档案主要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共推出档案出版物187种2986册,其中满文档案史料39种898册,《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清宫颐和园档案》《满文老档》等出版物荣获国家级出版奖项”,同时“馆内档案信息化平台开放数字化档案达386万余件,一史馆官方网站公布数字化档案目录达150余万条”[※注]。2001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辽宁省档案馆共同出版了《中国明朝档案总汇》100 册,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明朝档案影印出版,这对于档案相对缺乏的明史研究的意义尤为重要。其中“武职选簿”等档案已经受到明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取得了一大批新成果。
地方档案包括孔府档案以及清代淡新档案、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等等。早在1962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就开始与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合作,选录了大批明清孔府档案。并初步完成了分类、拟题等工作。到了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曲阜师范学院等机构组成了曲阜档案史料编辑委员会,对于选抄的档案资料进行了统一校点、断句,进一步加工整理,完成了《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1980)。这套选编的出版,推动了地方官府档案整理与研究的深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等清代地方官府档案公布,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极大地推动了明清政治史、法制史、社会史研究的深入。
除了官方档案以外,以徽州文书为代表的明清民间文书的大量发现,也成为推动明清史,特别是明清社会经济史取得飞跃发展的重要原因。1957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徽州发现宋元时代的契约》,提到了安徽省新华书店屯溪支店在抢救古书文物中,“陆续在农村里发现了大批的远至宋元以来的田地山林买卖契约”,昭告了徽州文书的发现。正是这一时期,通过屯溪古籍书店等,徽州文书开始流传到全国的许多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大学与科研机构,成为这些机构的重要收藏,为日后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的兴盛创造了条件[※注]。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作为徽州文书的主要收藏机构,开始推动徽州文书的整理工作。1985年,“徽州文书的整理”课题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七五”重点项目。1989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等领导的重视下,由周绍泉、王钰欣等人组成了“《徽州千年契约文书》编写组”,他们从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南宋到民国七百多年的徽州文书中精选了散件文书2820件,簿册90部,分成《宋元明编》《清民国编》两编,共40册,于1991年影印出版。《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认为“可以与中国古代史带来飞速发展的殷墟出土文物与敦煌文书新资料相媲美”[※注]。
随着徽州文书的整理与出版,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1987年,周绍泉《田宅交易中的契尾试探》[※注] 一文以徽州文书为中心,分析了始于元、终于清末行用达六百多年的土地税契凭证——契尾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展示出徽州文书对于制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1988年,栾成显《龙凤时期朱元璋经理鱼鳞册考析》[※注] 细致地考析了徽州文书中一部甲辰年间的鱼鳞册当为宋(元末农民起义军建立的国号)龙凤十年(1364年,即元至正二十四年)攒造,从而为明代鱼鳞册的始造时间提出了新的论断。1998年,栾成显的《明代黄册研究》出版,该书以徽州文书中现存的黄册文书为中心,通过个案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对黄册制度本身及明清社会经济史中某些问题做了深入的探索。该书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比如作者纠正了四十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明代“黄册原本”照片的错误认识,并对《明史》中关于明代甲首户的记载提出质疑,认为甲首乃为一种职役,不应当作一甲之首来理解。对于黄册人口登载事项,特别是妇女的登载情况,作者认为不同时期有不同变化,明代中叶以后,黄册所载女口一般不包括妇女小口在内。该书还通过对黄册资料的统计分析,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各阶层土地占有、田土占有分布形态、土地买卖、农村经济结构、大户地主经济形态,以及国家、地主、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展示出徽州文书对于明清史研究的重大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古代民间契约研究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除了安徽、江西、福建、台湾等传统的契约大省外,贵州因为清水江文书、浙江因为石仓契约的发现而成为契约遗存大省。北京、甘肃、内蒙古、云南、湖北、四川、河北等地也发现了大量的契约文书,改变以往契约研究只能局限于某些区域的弊端,为全面研究明清社会史提供了方便。[※注]
二 内阁、军机处与明清政治制度史研究
明清两朝是帝制中国最后的两个王朝,其政治制度对于今天的中国也有深远的影响。明代首废宰相而设内阁,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重大变局。清代又在内阁基础之上设立军机处,成为皇帝集权制度的政务中枢。不过,有关明代的内阁与清代军机处在当时中央权力结构中的位置,特别是内阁大学士与军机大臣是否具有前朝宰相的地位,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议。
近代以来有关明代内阁的研究,一般都遵循清修《明史》的说法,认为明嘉靖时,“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明史·宰辅年表》)。不过,关于阁权与相权究竟有何区别,一直缺乏系统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整个制度史的角度深入探讨内阁制度的成果不断涌现。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一书通过明代的中央权力结构的全面考察,认为内阁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禁直机构,“无论从立法角度上看,还是从实际权力的运作看,内阁大学士都不是前朝的宰相”[※注]。谭天星《明代的内阁政治》系统地分析了内阁制度的演变过程,也认为对于明代内阁只是皇帝的辅佐机构,无法对政治产生宰相般的影响[※注]。
有关明代内阁研究的深入也推动了清代军机处的研究。高翔将内阁、军机处与奏折制结合起来,探讨清代军机处的地位。他认为,清代军机处在清代政治中出现有较大的偶然性,它不是雍正皇帝为强化皇权而采取的一项精心的政治举措,而是纯粹为了处理西北军务。他同时分析清代内阁与军机处的关系,认为两者并不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权力系统,而是在维护皇帝独裁权威、完善独体制原则指导下进行的政务分工。实际上,并不是军机处,而是奏折制在清朝皇权强化过程起着特殊的作用[※注]。
明代的宦官制度与清代的八旗制度是明清两代各自极具特色的政治制度。了解明清两代的政治制度的特色,必须了解宦官制度与八旗制度。
明代政治存在着“三元二轨”的基本结构。所谓“三元”就是包括内官、文官和武官三种权力体系,“二轨”则分指内府与外廷。[※注] 在明代,“宦官”是与内阁分庭抗礼的政治力量。《明史·职官志》亦有“相权转归寺人”的说法。因此,了解明代中央的权力机构,不能忽视宦官的影响。胡丹的《明代宦官制度研究》从明代国家制度构造的背景以及明代的文书行移程序,全面地分析明代宦官制度与“宦权”的兴衰演变过程。指出明代宦官对于政治有很大影响,“但宦官并没有形成一个拥有自身核心利益的政治性集团,也缺乏这样的基础”。所以,“明代宦官的影响,是不足以动摇国脉的根基的”。“宦官亡国论”是缺乏说服力的。[※注]
八旗制度清代从努尔哈赤初创,一直持续民国初年,是清代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被视为“国家根本所系”。姚念慈《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1996)全面地分析八旗制的形成过程,提出满洲八旗制国家的理论。定宜庄认为,满洲统治者竭力维持的“根本”,亦即八旗制度“是建立在一个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都与关内迥异的背景之下的,它对汉族农耕社会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种种制度从根本上的格格不入,使它不可能超载汉族中央集权制度的种种弊病,而且在入关初短时期发挥效用之后即陷入种种难以自拔的危机”[※注]。
三 资本主义萌芽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从基础到上层建筑,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则,从各方面提出能具有一定说服力的体系及规律性的阐明,就成了史学责无旁贷的事”[※注]。1955年1月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提出了18世纪上半期是“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围绕《红楼梦》时代背景的讨论,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空前发展的重要契机。此后,各个领域的史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明清时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成果卓著。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收集了王仲犖、傅衣凌、侯外庐、吴晗、尚钺、翦伯赞、彭泽益、李文治、黎澍、韩大成、白寿彝等学者有关明清农业、手工业、商业资本主义萌芽的相关论文33篇,约80万字,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一次重要总结。这一系列研究,提出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始于明代中叶,到了清代乾隆、嘉庆时期(18世纪)有所发展的基本论点。
不过,这一时期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还缺乏理论指导,对于史料还存在着过度解读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承明等经济史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些缺陷,他们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细致的史料考察与定量分析,指出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不但较西欧出现得晚,同时发展也非常缓慢。在农业领域可以说微不足道,在手工业领域也只占极小比重。因此经过300 多年的萌芽,直到鸦片战争前,手工业也未能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而这大半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基本原因,是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源之一。[※注]
“资本主义萌芽”对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打破自黑格尔以来盛行于西方“中国停滞”论以及20世纪中期西方兴起的“冲击—回应”模式的束缚,使得我们能够从发展的眼光,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过去的历史。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学者们对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等问题进行了充分和透彻的探讨,可以说基本上弄清了事实的真相。[※注] 包括后来江南市镇研究、商人与商帮研究,以及海外贸易研究,大都受到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则是“早期工业化”研究。所谓“早期工业化”,是指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近代工业化之前的一个历史阶段。尽管早期工业化并不能必然导致近代工业化,但是前者仍然可以视为后者的一个先行阶段[※注]。早期工业化研究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李伯重,他以明清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为中心,通过对于轻工业、重工业以及能源、材料及人力资源等问题的分析,指出“明清江南轻工业规模扩大的程度,远远超过重工业规模扩大的程度”,这种为了节省能源与材料而形成了“超轻结构”。结果就是,虽然江南在早期工业化方面曾有出色的表现,从而江南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地区之一。不过,这个早期工业化,如果没有外力的话,很难发展成为近代工业化[※注]。
早期工业化理论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区别就在于摆脱“西方中心论”,从工业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明清时代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情况。这两种理论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最后的结论还是有一定的相似性。它们都认为中国的传统工业虽然有所发展,但极其缓慢。也就是说,无论是资本主义萌芽,还是早期工业化,其与近代工业化之间并不一定出现必然的因果关系。
有关资本主萌芽的研究也推动了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走向深入。早在1934年,梁方仲与吴晗等人成立“史学研究会”,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研究集刊》,倡导社会经济史研究。1936年,梁方仲发表了《一条鞭法》,利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以田赋制度为切入点,研究中国的农村社会经济问题。他指出:“明代自十六世纪初年正德以后,国内的农工业生产方法及生产关系,虽然没有重大的变化。但因历史上的机缘,如西洋航海术的进步等,使中国与外国的贸易却逐渐兴盛起来,国内的社会经济情形亦逐渐从自然经济时代发展到货币经济阶段上去。”1952年,他又发表了《明代一条鞭法年表(后记)》,指出:“商业资本的发展,只是增加了封建社会的内在矛盾。它只标志着封建主义底解体过程,它本身并不可能就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条鞭法就是为了适应这个变动环境而设的赋役制度。”梁方仲从田赋制度这个侧面入手,指出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内部很难自动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将契约等民间文献引入社会经济史研究,则是社会经济史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早在1939年,傅衣凌在福建永安县发现了数百件民间契约文书,他后来利用这批契约撰写了《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1944)。傅衣凌以福建文书为突破口,开创的利用契约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方法,影响了此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衣凌倾心于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注重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在明清契约文书的研究上,在明清商人和商业集团史的研究上,在山区经济的研究上,他都做出极大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后,梁方仲、傅衣凌等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逐渐成为显学,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其中,杨国桢对于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的研究,刘志伟对于明清广东赋役里甲制度的研究,郑振满对于福建家族组织的研究,陈支平对于民间文书与赋役制度的研究,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成果。他们倡导从民间文献与田野调查出发,强调“自下而上”的制度史研究,主导了明清史研究的方向。
四 农民战争与社会反抗行为研究
元末明初及明末清初均发生了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农民战争。有明一朝,因农民战争而兴,又因农民战争而亡,农战史研究是理解明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环节。早在1944年,郭沫若就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注],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总结了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1952年,郑天挺编辑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从清代档案中辑录出200余件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史料。此后,学界对明代农民战争的研究热情持续不断,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顾诚先后完成《明末农民战争史》(1984)与《南明史》(1997)两部专著而达到高峰。有关清代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则主要关注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天理教起义。
整体而言,明清两代农战史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体现在两点:其一是辨析、还原出大量被明清两朝统治者故意篡改、遮蔽或长时期为学界错认的史实。特别是顾诚的《明末农民战争史》基于对史料涸泽而渔式的爬梳,并加以辨析,成为农战史研究的一个经典。第二,全面实践阶级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对明清时代农民起义的原因、农民政权建立过程、政权性质作了论证,从新的角度认识农民战争的性质。
20世纪90年代,有关明清农民战争史研究趋于沉寂。但与此同时,学者开始更加注重区分明清时代各类社会集体反抗行为,引入农民抗租、市民暴动、宗教暴乱、盗乱贼寇等新的研究视角,并与社会史相结合,探讨了社会反抗行为对于国家及区域社会的影响。例如,刘志伟《明代广东地区的“盗乱”与里甲制》[※注] 等论文探讨了黄萧养起义对于珠江三角洲社会重组的分期意义。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注] 认为“盗寇”这种国家话语背后实际上是对人口流动和区域开发的控制过程。[※注]
五 启蒙思想与乾嘉学术研究
1949年以后,随着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思想史研究逐渐开始摆脱传统学术史的束缚,注重与社会史相结合,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探讨明清思想史的变化。侯外庐的《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想的特点》一文,在系统分析17世纪资本主义萌芽、阶级关系出现新变化的基础上,研究了明末清初启蒙思潮的特征。他指出,“启蒙时代思想的轴线也是资本主义萌芽状况的发展的轴线相平行着的”,因此,如何心隐、李贽、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启蒙思想家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中国社会条件的反映”。侯外庐对于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尤为推崇,认为其《明夷待访录》类似《人权宣言》,具有明显的民主主义思想[※注]。
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明清思想史变迁,特别是从启蒙思想到乾隆考据学(汉学)这一转换过程的背景开始受到广泛重视。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册全面地总结宋明思想史中各种学派的观点,以明代王学的变迁为中心,分析了宋明以来理学的发展脉络,认为“处于明清之际的人们既要总结明朝的教训,又想了解动荡变化的现实生活。客观实际迫使一些具有探求真理精神的知识分子从哲学、经学、史学、政治、经济诸方面去进行认真的研究,由此产生了理学的重新认识”[※注]。这种重新认识,也就成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以及清代乾嘉考据学的渊源。陈祖武也认为,清初的思想与学术,“从对明亡的沉痛教训入手,在广阔的学术领域去虚就实,尔后又逐渐向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方向过渡,最终走向经学的复兴和对传统学术的全面总结和整理”[※注]。此外,高翔也指出,“清初无论是激进思想家还是正统的理学家,其思想学说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学术研究始终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其出发点,即所谓经世致用”,“清初的经世思想,深刻影响了18世纪的中国思想的发展方向”[※注]。这些观点的提出,有助于从思想史的脉络去发现明清思想与学术转换的原因,而不是单纯将考据学的兴起归结于清朝的严格的文化政策,特别是文字狱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开始,杨向奎主持撰写的《清儒学案新编》[※注],近400万字,资料翔实,极大地推进了清代学案研究。漆永祥的《乾嘉考据学研究》(1998)将学术史与古典文献学研究相结合,对乾嘉考据学的名称、派别、代表人物、学术思想、成就得失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郭康松《清代考据学研究》则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入地分析了清代考据学的源流,探讨了考据学兴起的社会历史原因,并分析了乾嘉考据学的学术宗旨、治学精神、研究方法、学术特点等。作者指出:“在分析考据学的缺陷时,应将其放入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从历史事实入手,客观地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以考据学派的末流来否定整个考据学派,不能以考据学派中的某一流派代替整个考据学派,应对考据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流派作具体分析。”[※注]
六 内陆边疆与海洋中国研究
明清时代,内地与中亚、蒙古高原、东北、西南地区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对于这一地区的统治方式,明清两朝具有不同的特色。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成果非常多,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出版的《中国史稿》第六册(明代卷)、第七册(清代卷)所确立的研究范式与思路,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中国史稿》第六册指出,明朝对于边疆民族地区更多地实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和随时羁縻的政策。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随着“互市”的展开,明朝与蒙古各部基本上保持着相对和平的状态。同时通过茶马贸易,加强与西藏的联系。对于西南夷,则主要采取“羁縻”政策,西南少数民族“虽受天朝爵号,实自王其地”,这种土司制度与卫所制度、屯田制度相配合,确保了明朝政府对于西南地区的有效控制[※注]。《中国史稿》第七册认为,清朝建立后,鉴于俄国势力对于西北、东北的介入,设立了将军、驻藏大臣,通过军事、宗教等手段加强对于蒙古高原、中亚地区的直接控制。对于西南地区,则通过改土归流,消除了地区间隔阂状态,扩大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往来,使清朝的统治深入到边远偏僻地区[※注]。近年来,虽然对于清代的内陆亚洲的统治方式有不同理解,认为这种方式更具有满洲特色,或者内亚特色。但从总的来看,当时民族融合的趋势才是主流,多元文化的交融才构成了清朝的特色[※注]。这种融合,事实上是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明清时代,中国人进出东亚内海,进出西洋,主导了当时东亚、东南亚的国际关系与国际贸易。特别是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成为当时世界外交、航运史的壮举,很早就受到研究者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后,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1985),刘重日、周绍泉《郑和家世资料》(1985)等,系统地讨论郑和的家世以及郑和下西洋的全过程。此外,还《新编郑和航海图集》(1988)等,结合科技史,采用古今对照的方式,介绍郑和的航行路线。近年来,郑和研究又与“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史等新观念相结合,被赋予更深刻的意义。
有关明清时代东亚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的研究,一直是围绕着“朝贡体系”展开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朝贡”制度是分析东亚国际秩序和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基本模式[※注],受到广泛关注[※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岩井茂树又提出“互市”理论,认为从16世纪开始,从内陆到海上,以礼制为基础的朝贡贸易逐渐让位于以经济相互依存为基础的“互市体系”[※注]。对于这些理论,中国学者也有自己的解释,有的学者称之为“华夏秩序”[※注],有的学者称之为“华夷秩序”[※注],还有学者提出了“藩属体系”[※注]。陈尚胜对于这些观点进行总结后认为,“朝贡体系”论中的“朝贡”,只是点明了周邻国家对中国封建王朝的单向性活动,未能表达出中国与周邻国家之间的主要政治关系。而“朝贡体系”“藩属体系”只是点明了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周边秩序状态的追求,却未能表达出东亚地区传统秩序的关系结构。“互市体系”则忽略甚至回避了这种经济关系制度安排的政治性前提。所以,他认为,中国封建王朝在追求周邻国家来中国“朝贡”时,往往采取“册封”和“回赐”的方式予以回应。其中,“册封”是奠定双方关系的上下尊卑名分,而“回赐”则是上国对藩属国家王朝的经济奖赏。正是通过这种“册封”和“朝贡”双向活动的关联,中国封建王朝与周邻国家才结成了相互之间政治关系,从而达到他们所期待的周边地区国际关系秩序。因此,东亚地区传统的国际秩序应该是“册封—朝贡关系”体系,简称为“封贡体系”。当然,“封贡体系”相对“朝贡体系”,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当时双向的国际关系。[※注] 不过,两者的实质还是相同的,就是册封与朝贡构成东亚国际关系秩序的基础。但两种说法还是忽视了从16世纪到18世纪东亚国际关系发生的变化,特别是清朝与日本贸易关系的改变,而这正是岩井茂树“互市体系”理论的基础。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