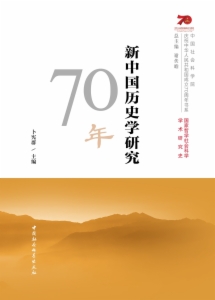第三节 史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深入
|
来 源
:
|
新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2 | ||
|
摘 要
:
|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征程,而且开启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篇章。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下,史学界返本清源,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思与重建,有关古史分期、社会形态、研究范式等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不断走向深入。第一节新中国史学理论问题探讨( 1949 —。针对以上质疑,不少学者加以反驳,例如汪敬虞认为, “半殖民地”与“半封建”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 ※注] 。近年来学界对于秦汉以后为“封建社会”的质疑使“两半论”中的“半封建社会”受到冲击,为“两半论”的理论探讨增添了新的关注点。 | ||||||
|
关键词
:
|
史学 范式 社会形态 史学理论 学者 马克思主义史学 马克思主义 近代史 中国历史 历史研究 争论 |
||||||
在线阅读
第三节 史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深入
字体:大中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伴随着学术界思想解放潮流的涌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焕发出勃勃生机,古史分期这朵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王冠旧识新说,百家争鸣,成为新时期史学的一道亮丽风景。而关于近代史研究范式的讨论则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一 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新进展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纪之交前后,几乎每隔十年就会出现一次古史分期的讨论热潮。
1978年10月,中国古代史分期学术讨论会在长春召开,吸引了全国51个单位的80 余名学者参加,与会学者讨论热烈,勇于突破古代史分期的“禁区”。嗣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后期,全国各地又陆续举办了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奴隶制问题和史学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有关论著和论文也纷纷出现。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一时热潮涌动,相关研究、讨论虽然是在传统的古史分期思路和框架下进行的,但仍然收获不菲。
关于西周封建说的研究颇丰[※注],在相关代表性著作中,赵光贤的《周代社会辨析》(1980年),马曜、缪鸾和的《西双版纳傣族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1989年),王德培的《西周封建制考实》(1998年)贡献颇多。相关研究指出,井田制是封建领主的等级所有制,剥削形式以劳动地租为主,“民”“众”等农业主要生产者的个体经济和隶属关系更多地类似于农奴而非奴隶的境况。这些论说颇能根据当时社会的具体实况立论,但不足之处则是在处理殷周之际社会形态转换时难以提出有力的证据,以证明生产力、生产关系所发生的急剧转换。
战国封建说此前在学界一直居于主流地位,新时期以后虽面临各方压力,但仍有斯维至、王明阁、侯绍庄、杨宽、田昌五、林甘泉等诸多倡导者[※注]。战国封建论者以春秋战国这个公认的历史转折时代的一系列变革为依据,从生产力进步、礼崩乐坏、陪臣执国命、诸国变法、土地私有制确立、租佃制产生与发展等角度进行论证,论据丰富,但对于上述现象为何就一定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的解释,以及对于战国秦汉时期为何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走向强化的解释等,仍然难以令人满意。
关于魏晋封建说,新时期的主张者有何兹全、尚钺、陈连庆、唐长孺、范传贤等人。何兹全在《中国古代社会》[※注] 中全面申论自己的主张,但却表现出对“奴隶社会”叫法的迟疑态度。尚钺作为魏晋封建说的主要代表,在1979年也撰文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注] 素有魏晋封建说“盟主”之称的陈连庆在新时期也积极撰文,认为商鞅变法大大发展了奴隶制,而奴隶制在汉代则处于高级阶段,到东汉才走向崩溃。[※注] 此外,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注]和范传贤等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卷》[※注] 也都是魏晋封建论的代表作。魏晋封建论者紧紧抓住两汉时期奴隶数量众多,比之此前更盛这点立说,从奴隶的数量及其生产地位、人身依附关系的演变,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入手,论证魏晋封建说,富有特色,但在回应奴隶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是否为社会主要生产者的问题上,则显得较为无力。
除了以上“三论”外,还有“五说”也值得注意。其中,祝瑞开、吴慧、侯志义等的春秋封建说[※注],白寿彝、金景芳、陈振中等的秦统一封建说[※注],赵锡元、马植杰等的西汉封建说[※注],周谷城、郑昌淦等的东汉封建说[※注],梁作干的东晋封建说[※注]等,与“三论”一样,都在新时期得到了申述、补充和发展。21世纪以后,古史分期讨论已无法形成讨论热潮,但仍有三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偶尔也会出现以社会形态论分析古史或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注],但已与传统的古史分期讨论大相径庭。二是学者们越来越多地专注于具体问题的研究,相关专题研究也是硕果累累,成为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某种延续。其中,土地制度、阶级问题、传统经济结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尤为值得关注。三是围绕封建制问题的探讨吸引了多方兴趣。以下重点谈谈有关封建问题的争论。
针对封建社会问题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来自何新、冯天瑜等人的质疑之声[※注],但真正形成讨论热潮则是在21世纪以后。其间,日知、马克垚、李根蟠、侯建新、冯天瑜等学者在“封建”概念考辨中的工作引人注目。[※注] 而在“封建”“封建主义”概念是否适合中国的争论中,何新、冯天瑜、周东启[※注]、叶文宪[※注]、黄敏兰[※注]等学者基本持否定态度,冯天瑜的“泛化封建论”是相关主张的集中体现。而在另一方面,马克垚[※注]、林甘泉[※注]、李根蟠等学者则作积极回应,不但肯定马克思的封建生产方式学说具有普遍意义,认为秦以后封建社会论对封建社会的理解并未背离马克思的原意,而且是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成果;他们从大土地所有制、自然经济、小农生产和君主专制等角度去论证秦以后是封建社会。总之,争论双方虽在商周时代存在“封建”的问题上有共识,但对秦以后的封建社会性质说则各执一词,这涉及对“封建”“封建社会”的概念、内涵的不同认识。
由上可见,新时期以后传统的古史分期观似乎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由于分歧无法完全消弭,争论仍将持续下去,但人们对世界和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有了更清晰的把握。争论一方面能够促进我们对于古史分期说的认识,推动分期理论走向完善,同时,也有助于构建新的中国历史学的解释体系。新时期以来,诸如白寿彝等提出的远古时代、上古时代、中古时代、近代的分期,田昌五提出的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的分期,晁福林提出的氏族封建、宗法封建、地主封建的分期,叶文宪提出的酋邦时代、封建王国时代、王国与帝国转型时期、专制帝制时代的分期,等等,都是在历史研究的新基础上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体系的努力,既反映了中国历史的自有特色,也是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结出的硕果。
二 社会形态理论认识的多元化
以往的史学界,是否赞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界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标准。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学者的认识推动了社会形态理论认识的多元化。相关争论涉及社会形态的概念、内涵、类型、起源与演进等问题,其中尤为史学界所关注的是社会形态演进规律与五形态论的起源问题。
关于社会形态的演进规律,一些学者在否定“五形态说”的同时,先后提出了“六形态说”[※注]“四形态说”[※注]“三形态说”[※注] 等主张。随着1979年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国内翻译出版,书稿中所提出的以“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自由个性”为基础的三大社会形态说也逐渐为一些学者所重视[※注],成为“三形态说”的又一内涵。此后,“三形态说”倡者日多,渐有与“五形态说”争锋之势。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围绕五种生产方式的争论再次形成高潮,尤以1988年在烟台举行的全国史学理论会议为典型。会上围绕五种生产方式说是否为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展开了激烈论争。[※注] 而三形态说也引发了更多学者的兴趣[※注]。与此同时,五种社会形态说虽然承受了来自各方的批评,但同样也有着不少拥护者[※注]。争论主要是围绕五种社会形态的提出和适用范围展开的。批评者或认为五种社会形态不是马克思本人,而是后人提出的(胡钟达、刘佑成、杜文君、赵轶峰、段忠桥、罗荣渠),或者认为它只是马克思基于欧洲历史经验提出的,不适用于世界上其他地区(陈剩勇、何兆武、田昌五)[※注],或者认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是历史发展的单线论,而马克思实际是主张多线的(吴大琨、陈剩勇、罗荣渠、李杰)。支持者则肯定五种生产方式说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反映了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周自强、谢本书、伍新福、吴泽、赵家祥、刘忠世)。从论争双方所提供的论据和思路看,分歧主要出现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解读和理解上。双方在争论中所共同意识到的则是,马克思的历史分期主张是多样的,不同民族所经历的历史发展过程存在较大差异性,不能教条化地理解和套用社会形态理论。
三 近代史研究范式与核心概念的讨论
对近代史领域的“范式”问题和有关近代史性质核心概念的讨论在近代史研究中影响广泛。
(一)研究范式之争
近代史领域的“范式”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始于美国学者德里克(Arif Dirlik)1995年发表的《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一文。他运用库恩的概念,表述美国中国学研究中曾经主导中国近代史解释的“革命范式”,受到晚近崛起的“现代化范式”的剧烈冲击。德里克将之命名为后革命时代的“范式危机”(crisis of paradigm)。[※注] 范式概念的引入,为近代史诠释体系的巨大变革提供了颇富解释力的理论工具,因而很快在中国大陆学者中激起热烈的反响,并引发了近代史学界有关“范式”问题的论辩。
争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第一,中国近代史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在“现代化范式”论者看来,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无疑应是“现代化”。“革命史范式”论者,则坚持中国近代史以“革命”为主题。第二,“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究竟孰主孰从。“现代化范式”论者,其主流意见并不否定“革命”以求得民族独立的价值,并不希图完全替代“革命史范式”,但认为“现代化范式”能包容“革命”,比“革命史范式”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对此,《近代史研究》杂志主编徐秀丽评判说,“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均试图以己为主体而包纳对方。这种争论持续有年,“事实上不大可能说服对方,达成共识。而且,任何解释系统都应该有自身的界定,‘无所不包’常常导致自身意义的稀释”[※注]。
对于“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在近代史研究中的实际地位,不同的学者观点颇有出入。不过大体可以确定的是,“现代化范式”虽然打破了原来“革命史范式”一统天下的格局,但总体说来,“范式转换”的局面很难说已在近代史学界完成。
事实上,“范式”之争的始作俑者德里克就曾表示:“在史学领域,出现一种支配性范式是既无可能又不可欲的。”[※注] 在中国史学界,不少学者强调“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并非对立,而可以“兼容并蓄、相互借鉴与共同繁荣”,即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注]学者力图超越研究范式的争议,认为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争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之争,此两种范式的合理性限度固然都应该继承和发扬,学科体系的有效进展又要求对之皆予超越。[※注] 更有学者力图以唯物史观对“范式”之争加以整合[※注]。实际上,近代史研究领域颇具影响的两位学者——胡绳与刘大年——对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早有所论述。胡绳在1990年提出:“在近代中国前面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注]刘大年则提出:近代化与民族独立“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不能互相代替,但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注]。论者指出,在胡、刘二人的言说中,“对于近代史两大任务(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完成,虽分了时间上的先后,却全然未作主次的分野”[※注]。
“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的争论主要是学理之争,在此过程中为中国学界逐渐接受和运用的现代化理论,作为历史认识的工具,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二)核心理论概念的新探讨
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论战,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简称“两半论”)获得相当程度的认同。其后经毛泽东在其著作中进一步阐发,[※注]“两半论”成为唯物史观派中国近代史诠释体系的理论基石与核心命题,也是中共民主革命理论的基本出发点。长期以来在学界被视为定论,无人提出异议。但这种一致其基础并不牢固,对此概念也并无深入探讨。有学者指出,很多带指导性的理论概念,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虽为大多数研究者接受,但因“缺乏严格的、科学的、建立在大量事实基础上的论证,因此难以经受住来自反面的挑战”[※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和挑战。李泽厚在1986年率先对“两半论”提出质疑[※注],同年,刘耀撰文提出半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变化,“决不能把它们等同或混淆起来”[※注]。1988年,李时岳明确提出二者分属不同范畴,并无必然联系[※注];并表示“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提法,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注],向“两半论”发出了尖锐挑战。
针对以上质疑,不少学者加以反驳,例如汪敬虞认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两半论”的讨论渐趋平息,但仍然不乏涟漪。由于挑战“两半论”者虽不无学理根据,却并不能提出取而代之的概念。强调“两半”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并维护“两半论”的声音似重新居于主流。张海鹏认为,如果因过去的研究存在缺陷,就对“两半论”提出否定意见是不妥的。实际上提出异议者也没有拿出新的观点,也没能找到更好的概念来对近代社会性质作出说明。[※注]
有关“两半论”的争论众说纷纭,并无定论。近年来学界对于秦汉以后为“封建社会”的质疑使“两半论”中的“半封建社会”受到冲击,为“两半论”的理论探讨增添了新的关注点。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