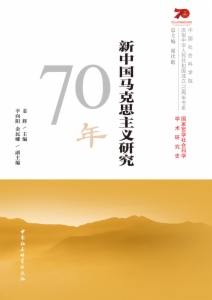第三节 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流派研究
|
来 源
:
|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70年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28 | ||
|
摘 要
:
|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涉及不少流派,因此,要介绍和分析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70年的情况,实有必要给予具体论述。就研究的问题而言,这一时期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后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界定、基本内容的划定(定义域、问题域) 、理论特征、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的内在逻辑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等上,专题式的深入研究尚未充分展开。作为国内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集中成果体现在周凡的《后马克思主义导论》一书中。 | ||||||
|
关键词
:
|
马克思主义 女权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社会主义 生态学 流派 学者 学派 女性主义 西方 |
||||||
在线阅读
第三节 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流派研究
字体:大中小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涉及不少流派,因此,要介绍和分析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70年的情况,实有必要给予具体论述。
一 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呈现为这样一种格局:随着萨特等人的逝世,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衰落了;继之而起的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可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兴起,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又成了明日黄花;法兰克福学派在六七十年代曾一领风骚,成为西方学生和左派造反的指导思想,与该派有渊源关系的思想家中,如今能独树一帜的,也唯有哈贝马斯。正是在这样一种“不景气”的思想背景之下,“分析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它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是很自然的。[※注]分析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兴起的一种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为主的新思潮,是西方传统分析哲学、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产物。鉴于分析哲学对这种新的社会思潮的重要影响,以“分析马克思主义”来冠名确能代表这一理论的发展方向和基本特征。
20世纪90年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转向政治哲学研究。1995年柯亨发表了《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这标志着柯亨的学术观点与研究重点发生转变,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走向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学术重心也开始从马克思主义转向规范的政治哲学”[※注]。罗默在1988年出版了第一部有关政治哲学的著作《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以及后来的《分配正义理论》等著作,还有其他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都出版了关于政治哲学的著作,埃尔斯特的《局部正义:社会机构如何分配稀缺物品和必要负担》、赖特的《审问不平等》、斯坦纳的《关于权利的一篇论文》、乔舒亚·科亨的《新的不平等》等。这些著作的问世说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向转向了规范性的政治哲学。
我国学术界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始自80年代末。1988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罗默、埃尔斯特等人来我国讲学。1989年2月,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在我国翻译出版。此后,一些报纸杂志还刊登过少量国内外学者介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直到余文烈的《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出版以前,我国学术界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总的来说缺乏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因此可以说,余文烈的这本书填补了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是一部评介性的专著。全书共有八章,除第一章是从总体上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特征做一般性的介绍以外,其余各章是围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七个主要问题对其有代表性的观点做逐一的评介。《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一书的最大成就就在于它第一次勾画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并对其主要成员的基本观点和所运用的方法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评介。
在之后的1995年9月,柯亨应邀来中国人民大学讲学,并做了专题报告,在国内引起较大的反响。其后,余文烈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段忠桥还曾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上,就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不是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结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等问题进行了引人注目的争论。这一阶段,国内学术界对分析学派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翻译出版该学派学者的个人专著和多位学者的合著专集,由徐崇温主编的译丛和由段忠桥主编的译丛就是典型的代表作品;二是对国外学者对该学派的相关文章的译介,对该学派代表人物专访,如郑一明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评介》、文成的《英国学者埃·赖特评约翰·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模式》、魏小萍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怎样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访G·A.柯亨教授》;三是对该学派几位主要代表人物各自专题观点的评析,这主要体现在国内各种刊物和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论文。如孟鑫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新论证——罗默的〈社会主义的未来〉述评》认为,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时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和对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值得称道的探索[※注]。他的有关实施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的建议,对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有借鉴意义。不过,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他的论证存在不少理论上的失误,尤其体现在他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平等主义,并进而认为公有制对社会主义是可有可无的。此外,他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分配决定论和平均主义为依据的。由于在这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失误,罗默提出的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综上所述,这一阶段国内进行研究的现状是:第一,对分析学派的研究论文大都是从个别层面作出的探讨性分析,深度有待加强。还缺少系统、深入的专著。对他们著作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需要进行深入论证和提炼。第二,学者们探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相关问题时大都仅停留在评析其思想内容上,还很少有对其理论基础进行深入挖掘、追本溯源的。第三,分析学派一些重要著作尚未翻译成中文。
二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研究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或模式的理论,它试图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主义。它是西方一个多世纪以来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思想理论,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由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首次系统阐述,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在西方左翼学者提出的种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影响较大的是英国学者戴维·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美国学者约翰·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美国学者戴维·施威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
现在人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究竟产生于何时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则是肯定无疑:这一派别真正产生重大影响,其理论真正得以深化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张宇等人全面阐述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分析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大大向前推进的原因,以及其最新形态的将征和当今的形形色色的分支。
对“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的理论讨论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在西方展开。到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新自由主义危机等原因,欧美再次掀起建立“社会主义新模式”热潮,其中主要模式之一就是“市场社会主义”。同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党的十四大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开始把“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介绍进国内,并做了一些积极的探讨。这一阶段有关“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理论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阶段,分五阶段、四阶段或者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说。但不管阶段如何划分,都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发展过程,围绕着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主要有这样几个依次深入的重大理论突破。一是“兰格模式”,虽然它只是一个“模拟市场社会主义”,还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架,但其重要理论意义在于它已内在地蕴含着市场机制是一种可以与所有制相分离,从而有一定相对独立性的资源配置形式。二是“中性机制论”和“联姻论”。“中性机制论”是“兰格模式”发展的必然结论,它明确提出了“兰格模式”中蕴含着市场和计划仅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和工具的思想。“中性机制论”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大发展提供了理论前提。“联姻论”则是“中性机制论”的明确化,实现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三是“市场主导机制论”,它是“联姻论”的进一步发展和逻辑结果,是对市场和计划关系的新认识,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的重大突破。
第二,对“市场社会主义”概念的界定。国内一些学者认为,虽然不同理论家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界定各有不同,在这些定义中所关注的要素及其侧重点也不同,但都离不开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利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既具有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这一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又利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注]在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主张用最概括的语言来表述就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目的。“市场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目的状态的理论,将市场则视为程序性制度。既然市场只是一种程序性制度而与任何实质性的目的状态无必然联系,它就可以被作为一种手段来运用于任何目的,它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目的服务。因此,市场与社会主义是可以兼容的,“‘市场社会主义’正是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注]。
第三,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性质及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在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性质问题上,国内外学者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有的认为它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有的认为在现阶段只有市场社会主义才是真正可行的社会主义等。究其分歧的实质是对于市场、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关系的不同理解。[※注]认为市场社会主义者根本看不到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趋势,而只是把社会主义肤浅地等同于资产阶级政府的一种经济政策,其目的是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二者在它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方面,都存在根本的不同。同时,在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也包含着一些具有科学价值的思想材料。比如“联姻论”“中性机制论”“市场主导机制论”及一些具体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等。这些具有科学价值的思想材料,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完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由北美形成后影响迅速扩大,在西方世界原先的各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中,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当属“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并没有给“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带来多少负面影响,相反,自20世纪的90年代以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无论是在理论建树方面,还是在实际作用方面,其发展势头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阶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飞速发展,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为扫除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的各种疑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人甚至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飞速发展视为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生的主要标志,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非但没有走下坡路相反还大步前进,这与它所探讨的主题密切相关。最近几十年,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地出现在人类面前,解决生态危机已成了人类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生态问题作为研究主题,而且由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作为出发点,从而比其他任何生态主义派别都要具有吸引力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获得了飞速发展的有利条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建树一方面在于,它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系统批判,特别是“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的提出,使这种批判与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表现在它全面推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这一构想比起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的要求,更为完整、成熟,完全改变了以前还或多或少接受生态运动的政治纲领和社会理想的局面。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学术界,我国学者自此开始了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支学术研究的群体,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归结起来体现在下面两个层面上:一是总体层面上如何理解和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研究;二是具体层面上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人物思想的研究,在这个层面上还可做一个地域的划分,即分为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欧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四 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在西方世界另一个发展比较迅速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它的飞速发展同样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方“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明显受到文化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形成了具有明显后现代特征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它成了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于西方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复活”,正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强劲发展的背景下实现的,因此这种“复活”不能不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不能不带有后现代主义的印记。“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
“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女权主义”的一个分支,又常常被称作“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当代的“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侧重于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态度和历史方法的同时,结合自己的经验,努力冲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束缚,确立自己的理论框架。郤继红等将“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女权主义”的一些其他派别,如“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特别是作为当代“女权主义”主流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做了详细比较,并指出,它与其他“女权主义”派别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强调消除妇女压迫必须以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以一种新的视角把女权主义的关怀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结合起来。
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20世纪末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这一阶段国内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划分和界定问题。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是否是一个流派?如果是两个流派,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如何划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关系如何?我们可以从国内有关西方女权主义流派的介绍和评价中看出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1)流派介绍中对二者界定不清晰。例如在李银河主编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中介绍了艾丽森·扎嘎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流派;在王维和庞君景著的《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同样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作为两个不同的流派加以介绍;在肖巍的《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中亦是如此。但是在俞可平的《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并没有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而是将其中的一些观点融合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观点中介绍。王跃华、张国盛的《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中所阐述的一些内容与李银河、肖巍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内容的介绍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对生产、再生产、性和儿童社会化的介绍。(2)代表人物的身份重叠。例如,海迪·哈特曼是哪一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在王谨的《新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中海迪·哈特曼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俞可平的著作中她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朱丽叶·切尔身上,在王跃华、张国盛的《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中,她是重要观点阐述者;在肖巍的《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中她是主要代表人物。(3)在目前介绍到国内的观点中,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主要观点重复较多。例如,对私有制的批判,对父权制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等等。这些现象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界定和划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困惑。
关于女权运动的分期问题。关于女权主义运动的分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郤继红将其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而张晓玲则认为女权主义的探索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根据郤继红的观点,可将其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18世纪—20世纪初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玛丽·玛穆勒、美国的伊丽莎白·凯·斯坦顿。第二阶段,20世纪初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激进女权主义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凯特·米丽特、西蒙娜·波伏娃。第三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权主义多元化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戈尔·卢宾、凯瑟琳·麦金侬、朱迪斯·巴特勒。而张晓玲在《妇女与人权》中认为,当代女权主义的探索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妇女研究理论,以西蒙娜·波伏娃的名著《第二性》和贝帝·弗里丹的名著《女性的奥秘》为代表;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理论。[※注]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内研究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和学者将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流派介绍到中国,传播女权主义思想,介绍西方妇女解放理论,借鉴西方妇女学的研究经验,在拓宽国内对西方思想的研究领域方面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同时,他们给人们带来了西方有关妇女解放的较完整的、较系统的思想,为国内妇女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丰富当代中国妇女发展理论方面同样作出了贡献。但是,仔细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国内对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对流派和观点的介绍阶段,缺乏深入的分析和评论。虽然有的专家和学者对一些流派进行了简单地评价,但是,大多数研究者没有从妇女解放运动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流派的产生、发展、未来走向进行客观的论证和探讨,并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对其哲学基础、理论主张、实践效果进行全面的分析。同时与中国妇女运动实践相结合的研究也十分匮乏。总之,相对于国内对西方其他思想流派的研究来说,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较少,研究者之间的争论和商榷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五 后马克思主义研究
探讨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能不涉及“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形成与广为流传,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世界获得了更进一步的认同和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遭到了空前的扭曲与损害。“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经过十余年的孕育,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以来,“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终于形成理论思潮。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立场试图在作为政治与文化力量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祛魅中拯救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仍有价值的一些方面。它的理论先驱一开始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随着1968年“五月风暴”的结束和西方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出现,部分新左派理论家开始以多种方式解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并对意识形态的自主性进行立论和论证,这一趋向和后现代思想的一些成果的嫁接使后马克思主义以积极的理论建构姿态呈现。
20世纪80年代初,“后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我国学者的理论视野。围绕“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理论性质、现实意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争论,在我国当代学术论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在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出现是一个重大事件。大体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该时期基本上是无意识地翻译了一些与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一些论著。国内早期涉及后马克思主义内容的主要文献有南斯拉夫学者S.朱罗维奇的《评〈人类的发展和社会〉》[※注],日本学者山琦熏的《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注]和詹宇国的《后马克思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访莱文教授》[※注]等。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贝斯特与凯尔纳的《后现代理论》(1991)以及詹姆逊、德里达等人的系列著作的翻译出版直接酝酿了我国后来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奠定了最基本的文献基础。之后是有意识的文本传入、系统介绍与初步研究并存时期,这大体上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90年代初已有少数学者开始初步研究后马克思主义了,如童世骏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第5期发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市民社会》一文。1997年6月20日至7月9日,美国著名学者、马克思批评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来华参加学术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和湖南师范大学在长沙联合举办的“批评理论:中国和西方”国际研讨会)并进行学术交流,先后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和哲学所、湖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
1999年8月17日至22日在云南召开的“世纪之交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议,首次将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提到议事日程,成为我国学术界开始自觉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促使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密切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的事件是2002年12月13日由江苏省哲学学会和南京大学联合召开的“后马克思思潮与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着重就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欧、美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划界标准问题,以及“后马克思思潮”和“后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新范畴的合理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003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在南京大学召开的第三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单独设立有关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分论坛。上述各类会议的召开,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起。
就研究的问题而言,这一时期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后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界定、基本内容的划定(定义域、问题域)、理论特征、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的内在逻辑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等上,专题式的深入研究尚未充分展开。由于国内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几乎是与其代表性著作的翻译出版同步进行的,部分研究者本身就是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文版的翻译者,所以,虽然国内自觉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时间不长,但整体研究起点较高。不过,毕竟囿于时间、文本等方面的原因,总体上来说,这一阶段我国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尚不深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足够的重视,应该说该方面的研究依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作为国内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集中成果体现在周凡的《后马克思主义导论》一书中。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