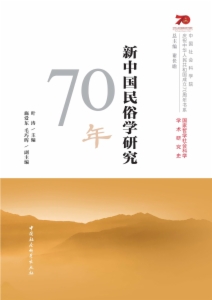第二章 神话研究
|
来 源
:
|
新中国民俗学研究70年0 \ 上编 民间文学 |
作 者
:
|
张多 |
浏览次数
:
|
5 | ||
|
摘 要
:
|
神话研究是中国民俗学深具传统的重要学术领域。三是神话研究紧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产出了一大批重要成果,比如对中华文明溯源的神话学方案、中国神话谱系的梳理、少数民族活态神话的调查、当代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等研究课题,都十分有助于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建设与发展。面向未来,中国神话学当积极拓展智能化社会中神话传承与流变的探索,积极推进古典神话精神资源助力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积极总结前人学术遗产并锐意创新,使神话学成为新时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高地。 | ||||||
|
关键词
:
|
神话 母题 山海经 神话研究 民族志 民俗学 中国学者 学者 学术 神话母题 调查 |
||||||
在线阅读
张多 第二章 神话研究
字体:大中小
神话研究是中国民俗学深具传统的重要学术领域。神话研究不仅对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的建立有启蒙之功,更在百年民俗学发展过程中始终焕发光彩。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神话研究业已呈现出流派纷呈、新论频出、采撷西学、阐发本土的良好局面。一大批前贤如章太炎、梁启超、蒋观云、鲁迅、周作人、顾颉刚、茅盾、闻一多、徐旭生、钟敬文、杨宽等,为中国神话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其中,基于文学文本的文艺学范式、基于文献文物的历时考据范式、基于田野调查的民俗学人类学范式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神话研究的主要学术范式。
1949年之后,中国神话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不仅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神话研究得到全面发展,而且在1980—2000年期间出现了一股知识界的“神话研究热”。从1949年至今的70年间,中国神话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逐步摆脱了以西学理论为中心的旧有格局,基本确立了中国神话研究的本土问题意识和理论方法。诸如钟敬文、丁山、孙作云、杨宽、袁珂等老一辈学者继续发表新见,并且还涌现出张振犁、乌丙安、萧兵、马昌仪、李子贤、王孝廉、吕微、叶舒宪等一大批神话研究者,他们中相当一部分都具备民俗学的专业训练。这些学者所培养的学生,也形成了中国神话研究稳定的、传承有序的学术梯队。
总览70年来的中国神话研究,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本土问题意识逐渐增强,学者们从中国的考古、文献、田野材料出发,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看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创建。二是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学者在与国际学术界的交往过程中,有的系统译介国外神话学著述,有的直接用外语做中国神话研究著述,有的致力于中外神话的比较研究,还有的在国际学术场合积极发出中国神话学的声音。三是神话研究紧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产出了一大批重要成果,比如对中华文明溯源的神话学方案、中国神话谱系的梳理、少数民族活态神话的调查、当代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等研究课题,都十分有助于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建设与发展。以下将就70年来中国神话研究取得的成就做一撮要性论述。
第一节 神话的界定:多元化视角
“神话”这一学术概念,自19世纪末经由孙福宝、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假道日语从西学中引进中国以来,对其概念界定问题的讨论从未间断。尤其是1949年之后,中国学者对汉语意义上“神话”概念的界定,出现了许多新的见解。
1949年以来中国学者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之下的“神话”概念界定,这种概念的表述以《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神话”词条为代表。第一版该词条的执笔者是张紫晨,认为神话是:“远古人民表现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它是人类早期的不自觉的艺术创作。神话并非现实生活的科学反映,而是由于远古时代生产力的水平很低,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自然现象和原始社会文化生活的起源和变化,以他们贫乏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和客观世界拟人化的结果。”[※注]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外国文学卷,由刘魁立执笔的“神话及神话学”词条,也采取了相似的界定。武世珍1987年首刊的《神话思维辨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神话观有较为深入的讨论。[※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神话”界定表述方式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依旧是学界普遍采纳的主要神话界定方式。
基于对以往狭义神话界定的反思,袁珂于1982年提出了“广义神话论”。[※注]袁珂基于对中国古代典籍和文学文类的深入研究、考释,他认为中国神话的概念界定不能照搬西学。在中国古代,仙话、话本、传说等文类与后世所谓神话者难以分割,中国的神话体系也并不仅仅局限于“远古”时代,数千年来,神话叙事一直在发展。他认为:“广义神话,其实就是神话,它不过是扩大了神话的范围,延长了神话的时间;它只是包括了狭义神话,却并没有否定狭义神话。”[※注]袁珂的广义神话论是中国学者基于中国实际的理论创建,在海内外神话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如果说袁珂的“广义神话论”拓宽了神话的外延,那么吕微对神话的哲学界定则深化了神话的内涵。吕微认为:“神话的信仰—叙事(或叙事—信仰)原本就是人的本原性存在的实践行为,而在人的本原性存在的实践行为——这里指的就是神话的信仰——叙事行为中,神话信仰—叙事的内容和形式是无以(也无须)区分的:神话叙事的内容就是其信仰的形式,而其信仰的形式也就是其叙事的内容。”[※注]吕微站在先验论的立场上,批评经验论的神话定义容易陷入自我矛盾。他后来进一步解释,“所谓‘神话’,讲述的就是人对人自身最本原、最本真的道德性、超越性、神圣性存在的信仰形式和信仰对象的信仰故事(形式优先的‘神话’形式—内容双重定义)”。[※注]吕微的观点对中国神话学来说尤为可贵,其哲学思辨对反思“神话”概念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运用有重要价值。
对于“神话”在中国语境中的意涵,陈连山的观点指出了其中的要害。陈连山认为西方式的神话定义对中国神话的实际情形来说并不完全适用,在中国文化中,类似于“神话”这样的神圣叙事往往与“历史”概念有联系。陈连山明确指出西方“神话”概念在中国的运用存在局限,很大程度上,中国古代用“历史”概念包括了“神话”概念。[※注]他在《论神圣叙事的概念》一文中说:“西方社会选择了神的故事作为其主要神圣叙事形式,而中国古代选择了古史作为自己的主要神圣叙事形式。神话与古史尽管在叙事内容上存在差异,但是其社会功能是一致的,且都被信为‘远古时代的事实’。”[※注]陈连山的见解揭示了中国神话传统有别于古希腊古罗马传统的特点,也即“古史”观念是比神话观念更为宏观的神圣叙事系统。这一点,在谭佳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神话学研究“神话—古史”范式的研究中也得到了更为细致的勾勒。[※注]
针对西方神话定义的局限性,杨利慧也曾提出质疑,她认为“神圣性”作为神话定义的必要条件,并不能准确客观反映神话存续的社会事实。[※注]“神圣性”的规定与中国古典神话的实际地位并不相符,并且当代社会中也存在大量非神圣性的神话创编、流布现象。基于这种考虑,杨利慧在探究中国现代口承神话时,倾向于借鉴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的“最低限度的定义”,也即以内容为主的定义。她认为:“神话是人类表达文化(expressive culture)的诸文类之一。它通常具有这样一些特点:是有关神祇、始祖、文化英雄或神圣动物及其活动的叙事(narrative),通过叙述一个或一系列有关创造时刻(the moment of creation)以及这一时刻之前的故事,解释神祇、宇宙、人类(包括特定族群)、文化和动植物的最初起源,以及现时世间秩序的最初奠定。”[※注]这一界定站在神话本体的立场上,较为恰当地提供了一个可供操作的神话定义。
除此之外,中国学者在神话思维问题上也有出色的研究成果。傅光宇的《三元——中国神话结构》[※注]受到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三功能论的启发,建构了中国神话的“三元结构说”。邓启耀在赵仲牧的指导下撰写了《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注]一书,该书基于中国哲学和中国多民族神话实例,较好地阐释了中国神话的内在思维结构,具有原创价值。
台湾学者对神话的界定也有许多新见。张光直在研究殷商历史时曾专门论及“神话”的界定。他认为神话定义的核心要素,一是神话最起码是一个“故事”,于中国古代文献而言一个神话至少包含一个句子;二是神话材料必包含“非常”之人物、事件或世界;三是神话持有者信以为真,且作为社会行为的基础。[※注]凡符合这三条标准的殷商材料,都被张光直视为神话材料。钟宗宪在其著作《中国神话的基础研究》中也意识到西方神话概念与中国事实的差异。他主张界定神话时从三个范畴即神话的起源、神话的意义、神话的表现形式来考虑。[※注]钟宗宪特别强调中西神话思维的差异,主张在中国神话材料的立场上界定神话。同时,也有学者从宏观的哲学层面界定神话,比如关永中认为,神话蕴意着“超越界的临现”,是一种“超越的统觉”。[※注]
总的来看,有关“神话”的界定问题呈现出多元视角的特征,但学者们共同强调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重新审视西方神话定义。70年来,这种本土问题意识以及本土的概念界定实践,超越了前贤成就,也逐步树立了中国神话研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多元化的视角,为深入认识中国神话提供了全方位的观照,中国神话的厚重积淀、广博涵括、复杂多元和重大意义都在对神话的界定中逐步显现,为进一步深掘中国神话学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节 神话谱系建构和溯源研究
现代中国神话研究自19世纪末滥觞以来,基于古典文献和考古材料的溯源研究一直是主流的学术范式。这种回溯历史、爬梳古典的溯源研究成为主流,一方面有中国具备海量古典材料的现实原因,另一方面也有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意图借助神话研究重建文化认同的原因。
这种学术传统集中体现在对“古史”中神话的考据、整理和体系化实践中。众所周知,汉文古籍中有关神话的记载是碎片化的,与此同时则有较为系统的上古帝系建构实践。这种情形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文化界曾引起普遍的思考,知识分子们大多将中国缺乏像古希腊那样的神话谱系认为是一种“文化缺憾”。西方学界长期以来也普遍认为中国缺乏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系统的神话。
早在20世纪20年代,茅盾就致力于建构中国神话的谱系,他的著作《中国神话研究》(1925)和《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等,在重构上古神话的工作中走出了重要一步。茅盾之后,也有许多学者试图构建中国神话的体系,比如徐旭生对疑古思潮的质疑和古史研究[※注]、程憬的古代神话体系研究、[※注]丁山的神话与宗教研究[※注]、孙作云对古代神话的综合研究、[※注]田兆元的古代社会与神话研究[※注]等。
但就神话谱系的建构而言,袁珂的成就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大量著述,尤为引人注目。袁珂终其一生都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他的《古神话选释》(1979)、《山海经校注》(1980)等著作在神话学领域堪称经典,在广大读者中拥有极高的声誉。袁珂尤其善于运用流畅的现代汉语注解、翻译古奥的古代汉文典籍。他构建中国古代神话谱系的实践始于195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神话》[※注],该著出版后广受欢迎。1984年他的《中国神话传说》[※注]出版,在前书基础上进一步搭建上古神话谱系的框架。该书于1998年更名为《中国神话传说:从盘古到秦始皇》再版。[※注]袁珂的上古神话谱系,从历代学人错综复杂的论辩中选取恰当的材料和观点,将不同的古代典籍神话置于合理位置,构建了完整的基于汉文典籍的中国古代神话系统。
在古代典籍神话的研究中,《山海经》研究最具代表性。袁珂的《山海经校注》[※注]是学界公认的最佳《山海经》校注本之一,代表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学者《山海经》研究的水准。自1949年以来,《山海经》研究始终是学术热点。
1951年吕子芳写作了10万字的长文《读〈山海经〉杂记》[※注],从科技史的角度阐释了《山海经》在地理、天文、矿产、医药、神话等方面的价值。1962年蒙文通发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注],对当时《山海经》研究基本问题的诸多观点作了梳理和辨析。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山海经》研究涌现出一批佳作[※注],代表了当时《山海经》研究的新成就。80年代,袁珂发表了一系列《山海经》研究的论文,奠定了他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1999年,叶舒宪的《〈山海经〉神话政治地理观》[※注]一文从文学人类学的新视角重新解析《山海经》的神话意涵。这些代表性成果反映了《山海经》研究步步深入、视角多元的特征。
及至21世纪,《山海经》研究开始走向深入,许多大部头的专著相继问世。2001年马昌仪出版《古本山海经图说》,全面汇集《山海经》各种版本的图像部分,后来又出版了增订本。[※注]这部集古图之大成的著作,堪称《山海经》研究史上专攻古图的标志性著作。此外,鹿忆鹿对《山海经》图像的细分个案研究、版本比较研究也颇有声势。[※注]2006年,刘宗迪的著作《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注]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这部《山海经》研究专著对前人诸多观点进行了修正和反驳,吸纳古典文献、神话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学术精华,构建了民俗学视角下的《山海经》研究范式。2012年陈连山的著作《〈山海经〉学术史考论》[※注]对《山海经》研究的漫长学术史尤其是20世纪的研究走向进行了整体梳理与评骘,显示出该领域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2013年,吴晓东出版专著《〈山海经〉语境重建与神话解读》[※注],以《山海经》文本中隐含的四面环海景象分别与二十八座定位山和二十八宿的对应两大规律,重建了《山经》和《海经》的叙事语境。该著对比较语言学、口头传统等理论方法的借鉴,拓展了《山海经》研究的视野。此外,中外学者合作研究的成果也引人注目,叶舒宪、萧兵与韩国神话学家郑在书合著的《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触》[※注]运用文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方法,深化了《山海经》的文化研究,也鲜明地呈现了神话学方法对《山海经》阐释的有效性。
总的来看,尽管《山海经》研究有多元化的学术范式,但是具备民俗学背景尤其是神话研究训练的学者的成果占有重要位置,甚至可以说极大推进了《山海经》的研究。这体现了1949年以来中国民俗学者的古代神话研究,已经逐步建立了自身的学术范式和话语,其学术旨趣大异于文献考据的研究范式,更多体现活态民俗文化的视角和整体文化观。这种研究范式还体现在其他古代神话典籍、文献、文物中,比如《楚辞》《淮南子》《竹书纪年》《路史》,以及新出土的神话文物比如子弹库楚帛画、马王堆汉墓帛画、汉画像等。
1949年以来以古典文献和文物为核心的神话溯源研究,成果极为丰富,难以一一述及,权以《山海经》为例管中窥豹。中国的古典材料是一个神话研究的宝库,可以生发出无穷无尽的研究论域,这也是中国神话学独树一帜的学术资源。
值得一书的是,叶舒宪提出的“四重证据法”和“N级编码理论”是具有中国本土原创意义的方法论,并且该方法论的探索和完善主要是在神话研究领域完成的。四重证据法系由前人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发展而来。叶舒宪所谓的“四重证据”主要指:传世文献;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现已拓展为包括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石刻、碑文、简帛、玉书、玉版书、玺印、封泥等的庞大新资料群;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所提供的相关参照资料,包括口传材料、活态的民俗礼仪、祭祀象征等,现亦包括跨文化比较的材料;物证,如考古出土或传世的文物和图像。[※注]
在“四重证据法”基础上,叶舒宪进一步提出“神话历史”“大小传统”“神话编码”等理论模型,并将其运用到中华文明溯源的神话学研究中。[※注]在《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一书中,叶舒宪等人详细论述了文学人类学的“大小传统”理论体系。[※注]这里的“小传统”是指文字发明之后的文明,比如甲骨文、金文出现以后的汉字文明和文字叙事。“大传统”是指文字出现之前的文明传统。
为了适应对“文化大传统”的研究需要,叶舒宪提出了“N级编码”的方法论,“大传统”对应一级编码(物与图像),“小传统”对应二级编码(文字)→三级编码(古代经典)→N级编码(后代创作)。N级编码理论是一套历时时序的分析模型,弥补了“四重证据法”蕴含“多重证据”无限多可能性的缺点,补充了“四重证据法”缺乏对材料逻辑阐释的缺憾。[※注]
总的来说,1949年至2019年间,中国神话学者在古代文明研究中展现出强劲的学术创造力,逐步从向西方学习转变为自主创新,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本土学术创见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的话语权,这也是神话学者对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一大贡献。
第三节 神话母题研究与母题索引的编纂
在以民俗学为背景的神话研究中,母题、类型是国际通行的经典研究方法。安蒂·阿尔奈(Antti Aarne,1876—1925)1910年编纂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经过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1885—1976)修订增补后,形成了“阿尔奈—汤普森分类体系”(简称AT分类法)。汤普森不满足于类型划分的粗疏程度,因此他编纂了六卷本的巨著《民间文学母题索引》(1932—1937)。[※注]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学者主要是翻译借鉴西方母题、类型的理论和方法,并且类型研究多见于民间故事研究中。[※注]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对神话母题的研究,显示出超越西方话语、反思西学不足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其中陈建宪较早地运用母题方法系统研究中国神话(尤其是洪水神话),其专著《神祇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注]《神话解读:母题分析方法探索》[※注]是神话母题方法运用于中国神话研究的范例。陈建宪的母题研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能够适应各民族神话的研究,因而其母题分析方法具有广泛影响。
吕微结合汤普森的“母题”和普罗普(Vladimir Propp)的“功能”,提出了“功能性母题”[※注]的概念,力图将母题和功能视为叙事本质而非直接的内容。户晓辉认为母题和功能是未完成和未封闭的存在现象,是民间叙事的整体存在方式。他认为母题是自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存在是自由的。[※注]王宪昭认为“母题”可以作为一个特定单位或标准对神话叙事进行分析。他强调母题的“最自然”和“基本元素”特性,而反对“最小单位”的规定,认为母题辨识不应是机械的。[※注]
相对于国际上神话母题索引、类型索引的编纂,中国神话母题索引的编制较晚。1971年,何廷瑞在《台湾原住民的神话传说比较研究》一书后面附了神话母题索引。[※注]这是较早的由中国学者编制的中国神话母题索引。2007年,金荣华根据AT分类法编制了《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注]2008年,胡万川编制了《台湾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含母题索引)》。[※注]2013年,杨利慧、张成福合编的《中国神话母题索引》[※注]出版,这是首部中国神话母题索引的专门著作。同年,王宪昭的《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出版,[※注]这部编目虽然没有检索母题来源的功能,但是其对母题的编排独出机杼,有重要价值。王宪昭的W编目在2015年进行了数字化数据库建设。[※注]
中国神话母题索引的编纂,得益于杨利慧、王宪昭等学者的贡献。杨利慧通过对中原地区女娲伏羲兄妹婚神话的田野研究,发现语境固然对神话的传播、变异有极大影响,但是往往神话的核心性母题及其组合却相对稳定。神话母题研究依然能有效说明神话本体的特征。[※注]为此她从1997就开始着手系统编制中国神话母题索引。这部“索引”与王宪昭的《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同时出版,成为引领中国神话母题研究的两部“大部头”著作。后来王宪昭在编目基础上,又编纂了《中国人类起源神话母题实例与索引》[※注],创造了一种为母题举证叙事实例、关联书刊的工具书。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神话母题研究、神话母题索引编纂方面的研究成绩,充分显示出中国神话研究的本土问题意识。西方的母题、类型研究方法在解决中国本土学术问题时产生了“水土不服”的问题,而通过中国神话学者的修正、检验,母题、类型方法得到了发展。可以说,对神话母题的研究和神话母题索引的编纂是中国神话学对国际学术的一大贡献。
第四节 活态神话与民族志研究
中国学者用民族志方法进行神话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就初现端倪。芮逸夫、凌纯声、杨成志、陶云逵、庞新民、姜哲夫、李霖灿等学者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调查,确立了中国神话田野研究的范式。这一批学者的田野调查非常扎实,所运用的摄影、速写、语音、地图方法都能与民族志有机融合。他们用西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揭示了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的仪式、宇宙观和口头传统。
1949年之后,基于对中国神话存续现状考察的民族志研究,逐渐成为声势浩大的学术流派,民俗学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诸如张振犁[※注]、乌丙安[※注]、管东贵、李子贤、王孝廉、[※注]富育光[※注]等学者都运用田野方法,较好地阐释了中国神话多元的特征。这些基于田野调查的神话研究,都有很强的本土问题意识,对西学的借鉴比较恰当。其中,管东贵对川南苗族神话的研究,是在继承其老师芮逸夫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注]该研究说明整理田野材料的眼光与长时段跟踪研究至关重要。张振犁及其学生对中原神话的搜集整理则尤为注重第一手口承神话的记录,出版了四卷本《中原神话通鉴》。[※注]该著作兼顾方志、语境信息、专业评点和图片,堪称口承神话调查与搜集整理的范本。
在少数民族活态神话研究方面,李子贤和孟慧英的成就最具代表性。李子贤基于对云南“神话王国”的研究提出“活形态神话”理论,呈现出具有本土特征的神话学田野研究论述。[※注]李子贤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坚持在云南各少数民族社区中开展田野调查,经历了民族地区社会剧变的整个过程,其活形态神话研究贯通文本、口承与仪式的神话载体,且具有宏阔的文化比较视野。孟慧英的活态神话研究从神话本体的特征入手,分析了活态神话在少数民族生活文化中的不同表现形式。[※注]
杨利慧从20世纪90年代跟随张振犁“中原神话调查组”在华北进行田野调查开始,就意识到运用民族志方法阐释鲜活的本土神话的重要性。她从河南淮阳太昊陵人祖庙会的空间和事件入手,探讨女娲、伏羲神话的表演与变迁。[※注]《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注]鲜明地倡导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口承神话。“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立足于民俗学的学术立场,扣住了神话学本身的问题。她的理论方法有别于在民族志中涉及神话的研究,并且积极吸收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的理论优势,有效地阐释了当代中国人的神话世界。
还有一些神话研究虽然没有书写成体系的民族志,但是使用了田野调查的方法,体现了民族志资料对阐释神话的有效性。诸如王小盾[※注]、刘惠萍[※注]、高莉芬[※注]、陈器文[※注]等学者将田野调查与古典文献、出土文物相结合,较好地展现了古典神话在当代社会流变的过程。诸如过伟[※注]、白庚胜[※注]、那木吉拉[※注]、汪立珍[※注]等学者对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充分运用田野民族志资料,擘画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神话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以来许多青年学者在对中国神话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研究方面,做出了相较前人更为深入、前沿的研究。比如吴乔对云南花腰傣族宇宙观、神话观的民族志《宇宙观与生活世界——花腰傣的亲属制度、信仰体系和口头传承》[※注],不仅克服了语言障碍,而且在民族志深描方面具有相当的水准。高海珑、高健、雷伟平、张多等学者的神话学民族志,都积极推进了对当代中国神话现状的深描与阐释。[※注]
中国学者在20世纪国际神话学民族志研究的序列中起步较晚,但是成绩可观。以李子贤领衔的西南少数民族神话调查和张振犁领衔的中原神话调查,不仅体现了中国神话资源的多元与富集,更体现了中国学者立足本土的学术研究精神。总的来说,1949年以来的中国神话研究,越来越注重“朝向当下”的民族志调查。民族志方法的推进,不仅呈现了人类当代社会的文化多样性,也大大拓展了中国神话研究的视野。神话学逐渐从诗学、哲学,从历史比较之学,从文学符号之学,走进了当代人的生活世界,为以往主要依赖古典文本的神话学开辟了新途径。
第五节 从新神话主义到神话主义
1949年以来,中国神话研究虽然越来越重视对当代社会中神话的调查,但是依赖古文献记录或者结合考古学资料来进行研究依旧是主导的范式。即便是民族志研究,也大多关注的是前工业社会生活中的神话表现形式,极少有专注于当代工商业社会中神话表达的研究。因此,“向后看”的主导性研究视角极大地限制了学者对古老神话如何与现代社会“接轨”、如何激活其在当下的生命力的探讨热情,阻碍了神话学对当代大众文化以及文化产业中神话存续的深掘。
自2005年以后,叶舒宪着力关注20世纪末西方兴起的“新神话主义”思潮,接连撰写了系列文章阐发“新神话主义”对中国的意义。[※注]在叶文的介绍中,“新神话主义”是指20世纪末以来,借助于电子技术和虚拟现实的推波助澜作用,而在世界文坛和艺坛出现的、大规模的神话—魔幻复兴潮流,其标志性作品包括《魔戒》《指环王》《哈利·波特》等一系列文艺、影视产品。这一概念主要强调作品中体现出当代消费者对前现代社会神话想象和民间信仰传统的极大兴趣。
21世纪以来,中国的旅游业、现代传媒、互联网等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在这些新的文化情境中,古典神话显示出强大的文化吸引力和生命力。针对这种“新神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叶舒宪撰写了《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注]《文化与符号经济》[※注]两部专著,深入阐释了这些新的现象。在这种研究思路的启发下,许多学者都开始关注神话在当代工商业社会、互联网社会中的变迁与创造性转化。比如陈建宪从文化产业角度观察神话的当代转化。[※注]孙正国从“神话资源”的角度阐述了这种资源的特征以及转化过程。[※注]在这些探究神话当代转化的学者中,杨利慧所倡导的神话主义研究,最集中地代表了国内神话学对于当代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的前沿探索成果。
杨利慧在前人基础上,重新界定了“神话主义”(mythologism),它是指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现代文化产业和电子媒介技术的广泛影响而产生的对神话的转化、挪用和重新建构,神话被从其原本生存的社区日常生活的语境移入新的语境中,为不同的观众而展现,并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意义。[※注]杨利慧把在遗产旅游以及电子传媒(包括互联网、电影电视以及电子游戏)等新语境中对神话的转化、挪用和重建,都纳入“神话主义”的范畴。[※注]她更多地参考了民俗学者有关“民俗主义”及“民俗化”等概念的定义和讨论,强调的是神话被从其原本生存的语境中抽取出来,在新的语境中为不同的观众而展现,并被赋予新的功能和意义。
神话主义的关注点,聚焦于现当代社会中对于神话的转化和重述。而将神话作为地区、族群或者国家的文化象征来进行商业性、政治性或文化性的整合运用,则是神话主义的常见形态,并且这种运用是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注]吴新锋、祝鹏程、高健、包媛媛、张多等学者从更为具体的案例中阐发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现象,充分显示出神话主义研究的阐释力。[※注]
从新神话主义到神话主义,不仅能够反映70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与嬗变的历史进程,更能够凸显中国神话在不同时代焕发出的生命力。持续开展对中国神话古今对话、创造性转化的研究,必将能够为当代中华文化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第六节 面向未来的中国神话学
综观70年来中国神话学的成就,既有“百年神话学”框架下对20世纪上半叶学术遗产的继承,又有21世纪中华文化复兴与“东学西渐”潮流中的神话学贡献。[※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神话研究进入“再度辉煌”的新时代,其成就在多方面超越前人。[※注]这些成就集中体现在对古代神话典籍和文物深入、系统、创新的研究,对中国多民族神话的调查与阐释,对神话学理论方法的拓展和建构,对当代社会神话生命力与创造性转化的探究与前瞻等。
当然,中国神话学经过70年的发展,也留下许多亟待深拓的课题,比如有学者指出的:古代神话对民族精神的表现和价值,以及这种神话精神对当代乃至未来的影响是什么,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仍然阙如。[※注]再如学科建设不尽如人意,尤其是神话研究最为倚重的民间文学,在当代学科建设中几经波折,仍面临诸多困境。[※注]又如对神话存续现状的调查研究远远不够、对新出土文物的解读工作任重道远、同国际神话学同行的对话亟待加强等。这些问题也将是下一阶段中国神话学努力的方向。
但总的来说,中国神话研究在1949—2019年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神话学在多学科交叉、中西理论方法融汇、文明互鉴与比较、构建中华民族认同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展示了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骄人成绩。面向未来,中国神话学当积极拓展智能化社会中神话传承与流变的探索,积极推进古典神话精神资源助力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积极总结前人学术遗产并锐意创新,使神话学成为新时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高地。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