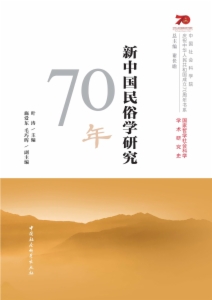第六章 歌谣研究
|
来 源
:
|
新中国民俗学研究70年0 \ 上编 民间文学 |
作 者
:
|
王娟 |
浏览次数
:
|
5 | ||
|
摘 要
:
|
作为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源于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史上最可纪念的事件之一” 。1949年之前的歌谣运动和歌谣研究最大的功绩在于唤起了知识界对歌谣的空前关注,此外,歌谣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之后的歌谣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之后的70年里,歌谣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取得了空前的成果,歌谣学、歌谣史、少数民族歌谣、歌谣理论研究方面尽管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整体看来,歌谣研究还没有形成规模,歌谣研究仍缺乏新的理论导向和新的研究方法的支持。 | ||||||
|
关键词
:
|
歌谣 歌谣研究 研究方法 民俗学 民歌 儿歌 民间文学 出版 征集 整理 吴歌 |
||||||
在线阅读
王娟 第六章 歌谣研究
字体:大中小
作为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源于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史上最可纪念的事件之一”。[※注]它不仅标志着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诞生,更重要的是它转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对社会、对民众,乃至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态度和认识。以《歌谣》周刊为阵地、以北京大学为依托、以新知识群体为主力的全国近世歌谣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活动,是中国学术界对歌谣和民间文学材料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挖掘和研究,对中国歌谣,乃至民间文学的学术范式产生了奠基性的影响。“运动”式的歌谣搜集方法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是民间文学搜集的主要途径,其关于搜集的“周遍性”、真实性等要求也成为后世学术规范的范本。
1949年之前的歌谣运动和歌谣研究最大的功绩在于唤起了知识界对歌谣的空前关注,此外,歌谣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之后的歌谣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之后的70年里,歌谣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取得了空前的成果,歌谣学、歌谣史、少数民族歌谣、歌谣理论研究方面尽管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整体看来,歌谣研究还没有形成规模,歌谣研究仍缺乏新的理论导向和新的研究方法的支持。
第一节 歌谣文本的搜集、整理与出版
歌谣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从1918年就开始了,1949年之前,已经出版的歌谣集有近300种,而1949年之后出版的各种歌谣集更是达到了近千种之多。[※注]1949年之后歌谣的搜集活动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成立有着密切的关系。1950年3月29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周扬致开幕词,他说道:
大会通过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和《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民间文艺集刊》第1集刊登了《本会征集民间文艺资料的办法》,对征集内容、征集要求进行了详细介绍,如“切勿删改,要保持原样”“资料中的方言土语及地方性的风俗习惯等须加以注释”[※注]等。实际上,歌谣征集的办法和理念早在歌谣征集活动之初学者们就曾经展开过广泛的讨论,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歌谣征集在理念和方法上延续了1949年前歌谣征集的基本方法和原则。这些原则包括:
第一,忠实地记录,不作任何甄别与删改。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常惠就提到,“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他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要自己先加甄别,尽量地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微或粗鄙的”。[※注]
第二,走入田野,亲自调查。因为“书本上的,一点也靠不住,又是在民俗学中最忌讳的。每逢写在纸上,或著成书的……多少总有一点润色的地方,那便失了本来面目。而且无论怎样,文字绝不能达到声调和情趣。一经写在纸上,就不是他了”。[※注]
第三,收集歌谣的同时,注意收集与歌谣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歌谣的出处”“歌谣的起源”“歌谣的流传范围”“歌谣的讲唱环境”等。[※注]
第四,记录歌谣应尽量保持其方言方音,或者干脆发明一些语音符号,以保留歌谣音调的本真。因为我们现有的语言不足以记录复杂多变的方言和方音。而如果不用方言和方音记录歌谣的话,那么歌谣也就失去了生命,失去了价值。[※注]
关于歌谣的搜集,刘兆吉在《西南采风录》中强调,田畔、牧场、茶馆、街头访问等,随处都可以搜集到歌谣。同时还应注意街头墙垣、庙壁上的涂写,以及当地印行的歌谣及抄本等。[※注]现在看来,刘兆吉的这些经验依然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作者提到了街头墙垣和庙壁上的涂写,即使是在当下,很多学者依然都没有意识到这些材料的重要性。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之后,民间文艺,包括歌谣的征集和采集活动广泛展开。从1950年到1958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征集到了大量的歌谣,并通过整理和筛选,出版了《陕北民歌选》[※注]《信天游选》[※注]《东蒙民歌选》[※注]《爬山歌选》[※注]《青海民歌选》[※注]等。1958年,民间歌谣的征集活动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新民歌”运动的一个重要推动作用是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谈话:
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社论说:
社论还提到了当时已经整理出版的各种长诗短歌,如蒙古族的《嘎达梅林》、彝族的《阿诗玛》、苗族的《古歌》、傣族的《召树屯》、蒙古族的《爬山歌》、回族的《花儿》、壮族的《欢》等,指出要同时“发掘尚有踪迹可寻的历代口传至今的歌谣宝藏,使它们不致再消失”。[※注]
此后,郭沫若、周扬编辑的《红旗歌谣》[※注]以及大量的红色歌谣集出版,如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编《红色歌谣》[※注]、河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河南红色歌谣》[※注]等。这些歌谣集中收录了大量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及各根据地流传的革命歌谣。一些歌谣资料集也陆续出版,如《中国歌谣资料》[※注]《中国古代民间歌谣选》。[※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歌谣选集也陆续出版,如《中国歌谣选》[※注]等。此外,还有一些儿歌集,如赵景深、车锡伦《中国古代儿歌资料》[※注]、谭达先、徐佩筠《广东传统儿歌选》[※注]等。长篇叙事歌有《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注]等。少数民族的歌谣,如《傣族古歌谣》[※注]《藏族民歌选》[※注]《瑶族民歌选》[※注]等,每一个少数民族,如侗族、哈萨克族、布依族、白族、纳西族、苗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等都出版了自己民族的歌谣集。
值得一提的是几种大型歌谣丛书的出版发行,包括舒兰《中国地方歌谣集成》[※注]、娄子匡的三套民俗学丛书和《中国歌谣集成》。舒兰《中国地方歌谣集成》总共为65卷,其中前十卷为歌谣理论研究。收入了许多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和有一定影响力的歌谣研究论文。后45卷为各省的歌谣集,分为儿歌、情歌和民歌三类。娄子匡自1970年起在台湾编辑出版的三套民俗学大型丛书,包括《中山大学民俗丛书》《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和《影印期刊五十种》,收录了大量的歌谣集、歌谣研究论文和研究专著。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歌谣提供了系统的、丰富的材料。
《中国歌谣集成》是一套由文化部和中国音协主持编辑的包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民间歌谣集,共30大卷,为1949年之后全国歌谣搜集的集大成者。《中国歌谣集成》是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贾芝等学者最早发起。在《我与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中,贾芝谈到:
在贾芝的建议下,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中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发文,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力量编辑和出版《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周扬任总主编,下设《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三部分,分别由钟敬文、贾芝和马学良任主编。贾芝是《中国歌谣集成》的主编。历经30年,《中国歌谣集成》省卷本终于出齐。《中国歌谣集成》是中国歌谣研究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歌谣研究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此外,一些歌谣研究机构如“歌谣研究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歌谣学会”等也对歌谣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例如,歌谣研究会的建立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它揭开了现代新诗改革运动的帷幕,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对歌谣反映的大量社会问题的注意,同时促进了文人学者接近普通民众,而后一点是更重要的。1984年,“中国歌谣学会”的成立在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收集和研究歌谣等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节 歌谣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张紫晨《歌谣小史》[※注]、祁连休、程蔷主编《中华民间文学史》[※注]等都对中国歌谣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论述。
张紫晨《歌谣小史》详细而全面地论述了中国歌谣发展的历史,全书分为十五章,包括歌谣的原始、夏商歌谣、周代民歌、春秋战国时期歌谣、楚国民歌、秦汉歌谣、汉乐府民歌、南北朝民歌、隋唐五代歌谣、宋元歌谣、明代歌谣、清代民歌、近代歌谣、现代歌谣和新中国歌谣。《歌谣小史》堪称歌谣史的拓荒之作。此后的歌谣史研究一直停滞不前,没有出现过有代表性的整体的歌谣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王娟《中国古代歌谣:整理与研究》[※注]对中国历代歌谣进行了梳理,按照现存的古代歌谣资料,该书将历代歌谣分为九类,包括神话传说歌谣、故事歌谣、时政歌谣、谶言歌谣、仪式歌谣、游仙歌谣、抒情歌谣、风俗歌谣和儿童歌谣。由于民间歌谣的口传性特点,历代歌谣中的许多歌谣文本存在大量异文,该书在编纂过程中,不仅将歌谣的异文一并收入,而且将歌谣出现的文本语境也一并进行了收录,便于读者进行研究。段宝林认为:
该书没有按照年代的顺序编排歌谣资料,主要是因为许多歌谣的存在是跨朝代的,如果按照朝代编排,势必会有很多重复,而且除了部分歌谣如时政歌谣外,许多歌谣的时代性非常弱。《中国古代歌谣整理与研究》是在现代民俗学学术理念下对古代歌谣的一次新的整理与研究。
歌谣运动之后,顾颉刚的《吴歌小史》发表,其堪称歌谣史研究的奠基之作。顾颉刚认为:
该文将吴歌的起源上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吟”,并清晰地梳理出了吴歌的发展和传承脉络,即从《战国策》中的“吴吟”,到《楚辞》中的“吴歈”,再到《汉书·艺文志》中的“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以及《隋书·经籍志》中的“吴声歌辞曲”,《晋书·乐志》中的“吴声杂曲”等。此外,该文对吴歌的谐音特点以及句式格律也有分析。顾颉刚还将刚发现不久的冯梦龙的《山歌》纳入吴歌的传承体系中,认为“自从发现了这样丰富的材料,吴歌始有研究的工作可做”。[※注]《吴歌小史》在发表后不久,陆侃如评价说其“源源本本,实为治文学史者所必读”。[※注]
也正是在顾颉刚《吴歌小史》的启发下,很多学者开始继续吴歌的研究,1949年之后,歌谣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吴歌领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出版)的第十章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明代民歌,尤其是高度肯定了冯梦龙的《挂枝儿》和《山歌》,说《山歌》十卷以吴地方言写儿女私情,其成就极为伟大,是吴语文学中最大的发现,也是文学史里难得的好文章。[※注]周玉波《明代民歌研究》[※注]对明代民歌,包括明代民歌的历史文化语境、地域特征、演进轨迹、主要内容、艺术特色,以及李开先、冯梦龙等人在民歌传播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尽管其研究方法和理念还带有文学式的歌谣研究范式,但是,该书无疑将明代歌谣研究带入了一个高峰。此外,刘旭青《吴越歌谣研究》、[※注]吕肖奂《中国古代民谣研究》[※注]、朱秋枫《浙江歌谣源流史》[※注]也是歌谣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值得关注。
第三节 歌谣学基础理论的探讨
歌谣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歌谣的一些基础性研究,如歌谣的定义、歌谣的特点、歌谣的分类、歌谣的价值和功能等方面。
朱自清的《中国歌谣》是中国歌谣学的代表著作。此书是根据他1929年在清华大学讲授“歌谣”课的油印本讲义整理出版的,其中包括歌谣的释名、歌谣的起源与发展、歌谣的历史、歌谣的分类、歌谣的结构和歌谣的修辞等篇章。另外,还有四章只粗具纲目,为“歌谣的评价”“歌谣研究的面面”“歌谣搜集的历史”“歌谣叙录”。这四章只收罗了材料,可惜没有完成。“这是部有系统的著作,材料通乎古今,也吸取外国学者的理论,别人没有这样做过。可惜没有写成。单就这六章,已足见他知识的广博,用心的细密了。”[※注]《中国歌谣》对歌谣的起源、定义、歌谣发展史、歌谣的分类、结构和语言文字技巧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述,初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歌谣理论体系。该书材料丰富,高度概括了“五四”以来国内外歌谣研究的状况和成果,对建立中国现代歌谣学具有开创意义。
除了朱自清《中国歌谣》,朱介凡《中国歌谣论》[※注]也是一部全景式的关于中国歌谣的理论著作。其内容涉及很多歌谣类型,如花儿、儿歌、情歌、仪式歌、工作歌、生活与叙事歌、谣等。另外,江明惇《汉族民歌概论》[※注]、赵晓兰《歌谣学概要》[※注]等也都是较有影响的歌谣综合研究专著。此外,台湾和少数民族歌谣研究成果突出,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歌谣综合研究成果,如黄勇刹《壮族歌谣概论》[※注]、简上仁《台湾民谣》、[※注]祜巴勐《论傣族诗歌》[※注]、王松《傣族诗歌发展初探》[※注]等。这些著作对台湾和少数民族诗歌的起源、艺术特色、分类、搜集、翻译,以及歌谣与文学、宗教的关系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
姜彬,笔名天鹰,对中国歌谣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出版了一系列歌谣研究的著作,包括《论歌谣的手法及其体例》[※注]《中国古代歌谣散论》[※注]《杨风集》[※注]《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注]《论吴歌及其他》[※注]等。在《论歌谣的手法及其体例》中,天鹰集中论述了歌谣的几种表现手法,如夸张、比兴、排比、对比、反比、反复、重叠、拟人化等。对于歌谣的艺术性、体例、思想性、表现手法、研究方法和歌谣发展史方面,天鹰都有所贡献。
在歌谣格律研究方面,段宝林、过伟主编《古今民间诗律》[※注]《民间诗律》[※注]和《中外民间诗律》[※注]的出版是歌谣格律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式的成果。这三册民间诗律的编纂过程耗时17年,“涵盖了古今中外最主要的民间诗歌体式和各种格律形式,包括中国汉民族各大方言区和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以及二十多个国家与语言的民间诗律研究成果。其中介绍的民歌体式不下数百种,格律形式不下数千种,为诗歌研究和新诗的创作提供了许多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和研究成果”。[※注]
在歌谣的功能方面,学者们重点关注的是歌谣的教育功能。顾颉刚说过,“既然民歌,尤其是情歌,最能表达民众的真实情感,那么它就可以用来当作拯救国家命运的武器”。[※注]谈到教育,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儿童。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将童话和儿歌的内容纳入教科书来改善儿童的教育状况。褚东郊认为,儿童教育的重要教材是儿歌,儿童几乎天天与儿歌打交道,他们自然受儿歌的影响最深。因此,儿歌对于儿童思想性格的形成有深刻的意义。如果“一社会中流行的儿歌富于冒险性质的,其国民亦多冒险精神。偏于利己主义的,国民亦多利己思想”。[※注]虽然儿童在后来的成长中也要受到大量通俗读物和其他文学作品的影响,但他们的思想基础的奠定,主要依赖儿歌。
一般来说,儿歌和童谣具有如下功能:(1)作为儿童获取知识的途径,如从儿歌中获得关于色彩、季节、植物、动物方面的常识。(2)激发儿童的想象力,促进儿童智力的发展。(3)培养儿童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道德品行。(4)培养儿童的集体主义观念,为进入社会做好准备。在学者们看来,儿歌既能帮助儿童走进自己的世界,也能让他们凭直觉初识人类社会的一般状况。儿歌的教育绝不亚于学校的课本。因此,很多学者包括周作人、钟敬文、郑振铎、叶绍钧等都认为应该把儿歌作为儿童早期教育的重要手段。遗憾的是一直到现在,儿童和童谣的这种功能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
第四节 歌谣研究的方法论
关于歌谣的研究方法,学者们讨论和运用较多的是比较研究法、文学研究法、人种学研究法和社会人类学研究法。早期的学者们借鉴的是西方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法,如比较研究法、历史演进法和母题研究法等。其后,学者们尝试将西方的比较研究法与中国传统的国学研究法,如训诂、考订等结合起来,创造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歌谣研究方法。近十几年来,随着民俗学学科的成熟,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多元化,歌谣理论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比较研究法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创始人是芬兰民俗学家科隆父子,所以比较研究法又被称为“芬兰学派”。该理论主要是通过搜集同一故事类型(或者歌谣,或者其他民俗事象)的所有异文(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然后对所有异文进行细节方面的梳理和比较,最终确定故事(或歌谣)的起源地、原始形态和传播途径。这种理论又因此被称为历史—地理学派。比较研究法是由胡适首先提出来的,在《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中,胡适写道:
董作宾是中国学者中第一位用比较研究法研究歌谣的学者,也是最为成功的一位。但是,由于材料的限制和比较研究法本身的缺陷,董作宾的《看见她》无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材料的使用、类比和结论,但这并不影响《看见她》在中国歌谣研究史上的地位。实际上,1949年之后,歌谣的理论研究,始终无法摆脱比较研究法的窠臼,用天鹰的话说:
刘魁立也认为,比较研究法“作为一种手段以及作为方法论系统中的一种方法”[※注],几乎被所有涉及民俗和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学派或多或少地加以利用。比较研究法因为更偏重于文本,因此与中国传统的文学式的研究方法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因此更容易被学者们所掌握和接受。
歌谣研究中的另一种方法是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的基本观点是从民间歌谣材料中发现民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人种学的研究方法强调研究者应尽量避免对各种民俗现象做出自己的理解、推断和臆测,而是根据民众的表述作出客观的描述和归纳。运用人种学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前的歌谣研究领域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因为这种研究方法是20世纪中期才逐渐得以完善的。但“五四”时期的学者们在不自觉中运用了这一理论。
刘经庵《歌谣与妇女》便是此种研究方法的有代表性的专著。此书共收录了386首歌谣,分别从“妇女与她的父母”“与媒妁”“与公婆”“与小姑”“与兄嫂”“与丈夫”“与儿子”“与舅母与继母”“与情人”和“与其他人”十个方面真实地再现了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和遭遇。这十个方面的确非常具有代表性。它们几乎涵盖了妇女生活的全部。在作者看来,妇女无论是做女儿、做媳妇、做嫂子、做母亲,还是做妻子,都毫无自主和自由。她们永远都是附庸和奴隶,生活在一个备受歧视的黑暗世界里。《歌谣与妇女》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歌谣完全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材料。其价值等同于任何其他书面资料。这说明当时学者对歌谣的认识是非常准确和深刻的。其次,歌谣对妇女的关注,对妇女悲惨遭遇的揭示,引发了全社会对妇女的同情和对妇女问题的思考和重视,吹响了妇女解放的号角。另外,歌谣在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生活上,相对于书面资料更具有普遍意义和典型意义。这种研究方法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的歌谣研究领域,实际上,一直到今天,还有许多学者依然沿用了这种研究方法,即通过歌谣文本,进行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考察研究。
当代民俗学意义上的歌谣研究,不能忽视的是歌谣的活态性和歌谣的唱诵传统。无论是比较研究,还是文学式的研究,因为过于重视歌谣的文本,因此,不可避免地就会忽视歌谣原本是用来交流和沟通的。歌谣是观念的载体,歌谣是文化传承的有效工具和手段,因此,歌谣的研究不能忽视其演唱环境和演唱过程。20世纪中期,台静农《从〈杵歌〉说到歌谣的起源》[※注]便是一篇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歌谣的非常有代表性的论文。论文探讨了歌谣的起源问题,但不是从典籍中进行考证,也不是依据书面材料进行推断和臆测。文章是从人类的“实生活”探讨歌谣的起源。作者依据自己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始终还“活”在民间的材料认为,歌谣产生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如从舂米的杵声,进而演变成乐歌。作者认为,“研究歌谣,应该从题材里看出它的生活背景,从形式上发现它的技巧演变。题材所包含的是人类学同社会学的价值,由某种题材发现某一社会阶段,及其生活姿态,这也就是朱光潜先生所‘想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注]
郑土有《吴语叙事山歌演唱传统研究》便是一部成功的尝试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根据自己大量的田野调查,尝试通过对吴语叙事山歌的文本、演唱语境、演唱歌手的综合分析,对吴语叙事山歌的演唱“传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试图发现吴语叙事山歌的口头即兴创作过程、创作规律和模式、传承的内在机制等。作者认为:
当代一些学者如段宝林一直强调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立体性”,经过三十多年的摸索,“立体性”研究也已经从概念和观点发展成为可以具体操作的实践活动。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成果涌现。
第五节 歌谣研究中的问题与展望
70年歌谣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歌谣研究缺乏科学、系统的基础理论建设。从学理上讲,我们对歌谣的一些基本概念,包括歌谣的定义、分类、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以及歌谣的价值、功能等问题还缺乏理论总结和梳理。以什么是歌谣为例,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学者们就对歌谣的定义和源流展开过争论,包括什么是“歌”“谣”“诗”“徒歌”“合乐”等,当下也有一些论文涉及歌谣的定义,如《“歌”、“谣”、“诵”小考》[※注],但是歌谣的基础研究还需加强。
其次,歌谣研究指导思想的滞后不利于歌谣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如何对待歌谣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问题上,早在20世纪歌谣运动的初期,常惠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中就曾经指出,“文化愈进步,歌谣愈退化……如果现在不赶快的去搜寻,再等些年以后,恐怕一首两首都是很难的了”。[※注]这种保存“残余物”的“焦虑”显然是受到了西方进化论思潮的影响,人们担心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会导致民间传统文化的消亡。基于这种紧迫性,常惠甚至提出当时可以“尽先收集,不忙研究”。[※注]在民俗学和歌谣研究产生的初期,这种观点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当代,随着民俗学学科的成熟,如果还是一味地强调搜集和整理,则不利于歌谣的深入研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歌谣是“活态”的,而非“死”的材料。我们研究的歌谣是保存在民众口头唱诵行为中的歌谣,每一首歌谣都有其特定的唱诵“语境”,因而也就不同于作家书面创作的文本。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抢救”歌谣,实际上就等于是把口传歌谣的“活”的文本记录下来,把歌谣文本从其生存语境中“剥离”出来,其结果就是把“活”歌谣变成“死”歌谣。
最后,曲调和旋律是歌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老舍就强调:
但是实际上,即使是在当下,歌谣的音乐、仪式、语境等部分仍然没有引起我们充分的关注。将歌谣的演唱者、歌谣文本、歌谣的曲调和旋律、歌谣的唱诵语境、唱诵过程等一起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成果仍然不多见。希望在21世纪里,随着各种民俗理论,如“立体性”“表演理论”“过程研究”“现象研究”的提出,能有更多的民俗学者积极关注歌谣,使歌谣研究取得更多的突破性的发展。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