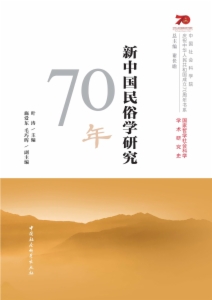第十五章 民间信仰研究
|
来 源
:
|
新中国民俗学研究70年0 \ 下编 民俗学 |
作 者
:
|
王霄冰 林海聪 王玉冰 |
浏览次数
:
|
10 | ||
|
摘 要
:
|
“民间信仰”是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人文社会学科普遍关注的议题。在中文语境,学者们在不同的语境中也用俗信(包括“民间俗信” “民间信俗” “民俗信仰” ) 、民间宗教(包括“民众宗教” “大众宗教” ) 、民俗宗教、民生宗教、通俗信仰、普化宗教(包括“扩散性宗教”。针对民俗的实践主体,他提出一个“民俗精英”的概念,并将“民俗精英”分为七个层级:普通村民、秀异村民、巫性村民、会社执事、民间知识分子、政府官员、文化他者[ ※注] ,并指出“民俗精英”之间“既互相联合,又充满纷争,总是维持一种动态平衡” 。 | ||||||
|
关键词
:
|
信仰 民间 民俗学 民俗 宗教 非物质文化遗产 互动 人类学 礼俗 调查 仪式 |
||||||
在线阅读
王霄冰 林海聪 王玉冰 第十五章 民间信仰研究
字体:大中小
“民间信仰”是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人文社会学科普遍关注的议题。在中文语境,学者们在不同的语境中也用俗信(包括“民间俗信”“民间信俗”“民俗信仰”)、民间宗教(包括“民众宗教”“大众宗教”)、民俗宗教、民生宗教、通俗信仰、普化宗教(包括“扩散性宗教”“弥漫性宗教”“混合宗教”)、宗法性传统宗教、民众祠神信仰等词语来指代民间信仰。[※注]从概念用语的繁杂中不难看出,学界对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与实践活动存在着不同的定位标准和分类观念。同时,不同语境下不同的词汇选择也会造成概念在内涵上各有侧重,表现出使用者对这一研究对象所持的不同学术立场。然而无论概念有多繁杂,他们讨论的具体范畴大致包括民众的宗教思想、信仰和仪式实践活动。因此,本章仍然选择“民间信仰”这一受到广泛采纳的概念来指称民众的信仰与仪式行为。根据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民间信仰(民俗信仰)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灵魂、自然神、图腾、生育神、祖先神、行业神等”。[※注]
当然,在梳理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时,我们不仅仅局限于民间信仰这个关键词。正如高丙中所言:“关于民间信仰的学术成果,我们不能仅从一个单纯的范畴进入,而要从一个知识谱系的宽度来把握。围绕‘民间信仰’,从制度发展水平来看,相关研究的范围包括系统化、组织化的‘民间宗教’,也包括弥散性的民俗活动;从学者立场来看,相关研究的对象包括偏向贬损的‘迷信’,也包括偏向正面对待的‘民间文化’,后者现在又转化出价值肯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注]
第一节 民间信仰研究的发展脉络
对于中国民众宗教信仰活动的学术关注,始自明末清初的中西方礼仪之争,及至晚清的定孔教为国教,将中国宗教问题的争议推到了顶峰。从“清末新政”的“废庙兴学”、民国“风俗改革运动”与“反封建、反迷信”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破四旧”到当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民间信仰不断地被重新解读和阐释。1949年以来,政府和学术界对于民间信仰的态度与研究,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 1949年至1978年对于民间信仰的定位与研究
民间信仰的学术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低潮期,但并不意味着民间信仰的研究全面停止。一方面,仍有一部分历史学者针对以会道门为代表的民间信仰活动进行了一些学术研究。这些历史学者们“比较普遍地使用过‘农民宗教’或‘起义者的宗教’等概念来表述民间教门”[※注],且多使用历史文献研究法展开。例如曾在民国时期对中国秘密宗教展开研究的李世瑜,就利用过去积累的学术人脉,开始搜集与整理民间宝卷这种特殊的民俗文献,在1961年出版了《宝卷综录》。[※注]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也搜集整理了大量会道门的组织情况,一部分发表在诸如《人民日报》《公安通讯》《人民司法》和《人民警察》等报刊上,更多的则以内部资料的形式,流通和保存在政府部门或高校的研究机构资料室里。[※注]
此外,全国在1956年至1964年间开展了大规模、有组织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其中也涉及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习俗的内容。这些资料最初多数以内部资料的形式保存,1979年之后,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持下,学者们才陆续将之重新编辑整理,出版成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注]
二 1978年至2000年民间信仰学术价值的重新发现
1982年3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文件(简称“19号文件”),这既是党的宗教问题基本观点的一个修订版,也是新时期宗教政策和法规的一个大纲。文件提到,在社会主义中国,虽然“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失”,但是由于人们意识的发展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旧的思维方式会继续存在,因此宗教仍然会继续存在并且发挥它的功能。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重新展开民间信仰的调查与研究。首先是对民间信仰的文化价值重新定位,弱化概念所引起的政治敏感。吴真曾指出,“1979年顾颉刚、钟敬文诸先生发起《建立民俗学及有关机构的倡议》之后,全国民间文学研究者们开始广泛讨论如何重建民俗学,其中一项便是恢复对信仰风俗的研究调查。由于长期以来整个文化界惯用的‘迷信’一词容易引起意识形态的政治敏感,1980年以后,民俗学者们非常默契地共同使用了‘民间信仰’一词,借以取代‘迷信’一词”。[※注]例如乌丙安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民俗学》便辨析了民间信仰与宗教的十大区别,以凸显民间信仰的民俗性。[※注]其次,宗教学、历史学的学者们以“眼光向下”的姿态开始对民间信仰进行研究,但是一般使用“民间宗教”这一概念,来替代传统的“秘密宗教”“秘密结社”以及“会道门”研究。[※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民俗学者们全方位展开了有关中国境内民间信仰的调查研究,出版了一批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研究丛书。如上海三联书店的《中华本土文化丛书》,收录了十多本民间信仰研究著作。[※注]这些民间信仰著作或以“萨满”“中国巫术”“神判”等特定的民间信仰表现形式为研究对象,或以特定的神祇崇拜类型如关公、财神信仰等为研究主题。刘锡诚、宋兆麟与马昌仪等主编了《中华民俗文丛》(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和《中国民间信仰传说丛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前者按神灵崇拜对象进行分类,涵盖了20个民间信仰主题,单独成册,后者则主要是针对传说这一民间文学文类,分为12个民间信仰主题进行整理。
这一时期民间信仰研究的特点还表现为区域民间信仰研究成为一种趋势,正如吴真所总结的,这些区域民间信仰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江南地区(以稻作文化与蚕神崇拜为主)、东南沿海地区(以妈祖研究为核心)以及华北地区(主要围绕碧霞元君、女娲、关公等神祇展开)。这些研究成果汇集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民间信仰志”体系,它们“大多遵循一定的写作模式:追溯本地信仰源流与历史,分析巫鬼、祖灵、地方俗神等信仰形态,介绍岁时节日风俗与庙会盛况,铺陈禁忌习俗,最后总结本地区民间信仰的若干特性”。[※注]
此外,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信仰情况也受到了民俗学者的关注,研究的方式既有跨学科的团队合作,也有学者个人的深入调查与研究。其中吕大吉主编的《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凝聚了包括民俗学者在内的五十多位学者的成果。学者个人的研究也涵盖了全国不同地区少数民族独特的信仰传统,如北方少数民族满族、蒙古族等的萨满信仰[※注],彝族的毕摩信仰[※注]、西藏高原的各种民间信仰[※注]、土族的民间信仰源流[※注],广西壮族的师公信仰与仪式等。[※注]
三 21世纪以来民间信仰活动的合法化及相关研究
经过多年来的政策实践和学术讨论,21世纪以来的民间信仰活动得到了更为充分和迅速的发展。首先是国家宗教管理方面,政策制定进入了成熟阶段。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民间信仰发展现状,逐步形成了湖南模式、福建模式、浙江模式。[※注]民间信仰一定程度上被视为特定的宗教文化现象,将其重新纳入政府部门的管理之下,赋予其信仰场所的合法性。2005年,国家宗教事务局设立业务四司,负责民间信仰(此外还负责政策研究和新兴宗教)的管理工作。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语境下,民间信仰还获得了另一种寻求制度合法化的路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家政府部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倾向于将民间信仰纳入民俗文化体系进行管理,以充分肯定民间信仰的传统性与民俗性,重塑地方社会的活态文化,增进民众的文化自觉。文化部于2006年在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纳入了“祭典”这一“非遗”项目类别。2009年,文化部公布的新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增加了“庙会”与“民间信俗”项目。民间信仰的表述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妈祖信俗的合法化与申遗过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注]
21世纪以来的民间信仰研究可谓成果丰硕、枝繁叶茂。以《民俗研究》为例,2004—2018年发表的民间信仰类论文共有337篇,而且2008—2018年的民间信仰类论文与杂志每年发文总篇数的比率都超过了20%,2005年和2010年两年甚至高达30%和34%。从主题来看,大部分论文都可以归至高丙中总结的民间信仰研究四大系列,即“神灵系列”“庙会系列”“灵媒系列”“仪式系列”。[※注]此外,“综合性研究”“概念和学术史”“礼俗互动系列”“民间信仰与制度性宗教的互动研究”这些研究主题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中有超过一半的论文是围绕“仪式”和“神灵”展开的,可以说“仪式”和“神灵”是民间信仰研究的重点。“神灵系列”涉及的神祇有碧霞元君、女娲、关公、妈祖、四大门等30多个信仰类型。“仪式系列”包括进香仪式、民间祭典、冥婚、祖先祭祀以及其他地方仪式活动。
综上所述,国家对民间信仰的态度与定位不仅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民间信仰的生存状况,也影响到民间信仰的学术研究的走向与进展。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国家将民间信仰定性为“封建迷信”,学术研究多数围绕“反动会道门”的历史发展与文化属性展开,仅有少量历史学者对民间信仰的民俗文献进行搜集和整理。改革开放后的40年,民间信仰得以重新恢复,其文化价值与社会功能再度得到学术界的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增长。民间信仰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第二节 新时期以来民俗学在民间信仰研究中的理论贡献
纵观新时期以来国内的民间信仰研究历史,民俗学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
一 民间信仰的概念与本质属性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民间信仰概念的探讨,始终贯穿着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并大多围绕民间信仰的宗教性和民俗性两重属性展开。主张使用“民间宗教”“大众宗教”或“民众宗教”概念的学者,多来自人类学或宗教学。他们对于民间信仰宗教性的强调往往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受到国外人类学理论的影响,参照英语中popular religion、folk religion、diffused religion等表述方式,为求与国际学界保持一致而将民间信仰视为一种特殊的宗教形式。例如王铭铭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介绍海外人类学研究的论文中就使用了“中国民间宗教”的概念,并在开篇指出:“中国民间的宗教文化包括信仰(神、祖先和鬼)、仪式(家祭、庙祭、墓祭、公共节庆、人生礼仪、占验术)和象征(神系的象征、地理情景的象征、文字象征、自然物象征)三大体系。”[※注]
第二种原因是从借鉴国外经验、完善我国宗教政策的角度出发,主张将民间信仰上升到与五大宗教平等的地位加以讨论和对待。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周星认为,可以“把包括祖先祭祀、表现为各种庙会形态的民间杂神崇拜(如关帝、妈祖、龙王、娘娘、老母、王爷、刘猛将、家宅六神等)、各种形态的民间道教、民间佛教以及基于泛灵论的自然精灵崇拜和鬼魂崇拜等在内的民间信仰,概括地定义为‘民俗宗教’,进而对相当于‘民俗宗教’的上述少数民族社会中各种不能为官方宗教分类所包罗或容纳的信仰和崇拜现象,则可对应地称之为‘民族宗教’。然后,再进一步修订官方现行的宗教分类体系,把此类‘民俗宗教’和‘民族宗教’均纳入到国家宗教政策和法规的切实保护之下”。[※注]与王铭铭有所不同的是,周星的立场似乎更加坚定。虽然他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中也使用了“民间信仰”,但特意在脚注中重申他在民间信仰概念选择上的学术取向:“笔者倾向于用‘民俗宗教’一词取代‘民间信仰’,但为尊重本课题负责人的立场,本章仍使用‘民间信仰’这一用语。”[※注]
金泽在概念使用上一直对“宗教”和“民间信仰”进行区分。虽然他最早将宗教人类学的理论应用到对于民间信仰现象的观察和分析中,并和陈进国一起创办了《宗教人类学》杂志,但他始终强调民间信仰的特殊性,认为“民间信仰属于原生性宗教,而不属于创生性宗教”。[※注]从1989年出版的专著《中国民间信仰》,到2018年的论文《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形态建构》,金泽更多地把民间信仰看成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并指出“民间信仰与其他的宗教形态,与民俗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传承或再生产,有着复杂的互动关联”。[※注]
与上述人类学者和宗教学者有所不同的是,一些民俗学者另辟蹊径,选择了一条“去宗教化”的定义路线。为替代被污名化了的“迷信”和“民间信仰”,他们创造出了“俗信”“信俗”“信仰民俗”等一系列概念。早在1984年,乌丙安从日本访问回来不久,在接受《民俗研究》采访时就提出了“俗信”概念,用以指代那些并非“迷信”,而“是要长期存在的,也是可以存在和允许存在的”民众信仰现象,并强调“这就是民俗学的观点”。[※注]很多年后,他自己又回忆道:“有关‘俗信’的概念,我最早是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民俗学》一书中,论述‘信仰的民俗及其特征’时提出,后来又在《中国民族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加以阐释。”[※注]但在乌丙安的民间信仰理论体系中,“俗信”与“民间信仰”一直都是并存的。他本人在为10年后出版的概论性著作命名时,也没有使用“俗信”,而是采用了与金泽此前出版的著作一样的名称——《中国民间信仰》。[※注]事实上正是这两部同名的著作,奠定了新时期民间信仰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时也确立了“民间信仰”作为一个通用名称的学术地位。
在民俗学研究中,“信俗”虽然并未能取代“民间信仰”,但在21世纪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这一概念却为许多民间信仰事象进入“非遗”名录提供了文化价值当代转换的学术依据。用当事人乌丙安的话说,“信俗”就是民俗学研究中的“民间信仰习俗”的简称,这是“一个中立的、在学术上能成立而官方话语也能接受,国际组织评审也认同的词语”。[※注]在“申遗”的过程中,把“妈祖信仰”改称为“妈祖信俗”,实质上就为其进入国家“非遗”名录并申报UNESCO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开辟了道路。而促成这件事的,恰恰就是像刘魁立、乌丙安这样一批热爱中国民间文化并能从国家立场出发考虑问题的民俗学家们。
除去表面上的这种实用功能,“非遗”保护语境下“信俗”概念的确立对于民俗学来说还带有另外一层特殊的意义,即它“更多地把人们的关注目标引向了民间信仰的主体”,强调“把民众的信仰形式重新还原为活生生的生活”。而且正因为民间信仰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民俗活动,在家庭/家族、社区和自发性民间群体当中完成其信仰实践”,所以,“注重亲自到场、身体感受和个体叙事的民俗学方法”才更显优越。[※注]
当然,“信俗”概念本身的理论建构尚未完成,仍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在概念上,信俗与信仰文化有何区别?在方法上,信俗研究与宗教研究又有何区别?民俗学能否通过树立信俗的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方法,找到本学科独具特色的宗教信仰研究路径?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民俗学者去继续探索和解决。
二 礼俗互动——民间信仰的核心要义与运作机制
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指出了“礼俗互动”视角之于中国社会研究的重要性:“在传统中国的复杂社会系统中,‘礼俗互动’奠定了国家政治设计与整体社会运行的基础,并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有所延续。礼俗互动的核心要义,是借助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将国家政治与民间‘微政治’贯通起来,保障社会机制内部的脉络畅通,以文化认同的方式消除显在与潜在的社会危机。”[※注]
在彭牧看来,中国的礼起源于人情,是为了教化、节制和规范人情而设置的。因此人情既是礼产生的基础,又是礼所节制、规范的对象。礼既包括国家层面上的正统礼仪,也包括民间层面上的礼,即“人们交往互动和日常行为中视为理所当然而共同遵循的规范与准则”。她通过对湖南茶陵民间礼仪的考察,发现“在很多场合中,礼和俗两个概念大致同义而可以替换使用”。[※注]民间礼仪的性质,就是“地方风俗传统和精英礼仪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为了生存而彼此斗争、互动融合的产物,而儒家的礼亦源于俗,所以俗与礼实际上是一对共生的二元”。[※注]
基于礼俗共生的认识,并将礼俗互动的视角带入到民间信仰的历史研究和田野调查中,民俗学界近年来产生了一批富有新意的学术成果。张士闪《民间武术的“礼治”传统及神圣运作——冀南广宗乡村地区梅花拳文场考察》通过深描当地梅花拳传统的文化形态及其运作机制,探讨了民俗文化作为“在野之礼”的功能特征。作者认为,“这种在民间自发生成的规范力量,与国家政治的规范意志之间有分立也有合作,有异议也有对话,可在对话与合作中从地方生活规范上升为当代公共价值,从而为中国社会礼治传统的当代重构提供难得契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深厚基础”。[※注]
“礼俗互动”作为历史学、民俗学和人类学共同关心的话题,今后也将是民间信仰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民俗学对于“民间礼仪”及其文化功能的发现,是礼俗关系研究中的一大突破。如何将此视角应用到相关研究中,在分析具体案例的基础上形成可为其他学科所借鉴的理论,是目前应着重考虑的问题。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多从历史角度切入,也有学者倾向于使用文献研究结合田野考察的方法。[※注]在今后的研究中,民俗学应更多地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探索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下和现实的信仰实践中礼俗互动的形态与机制。
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信仰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民间信仰提供了新的生存契机,使得很多信仰形式从历时性的存在又转变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申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为本身又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化事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与传统之间的关系都在这些事件之中得以确认或重组。
在研究理念上,高丙中提出“以广义的社会理论为依据梳理中国民间信仰的历史演变,调查民间信仰的当前状态,反思关于‘民间信仰’的表述与现代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探讨把它转变为建构民族国家内部正面的社会关系的文化资源的可能性和方式”。[※注]这意味着首先要在经验的层次,“调查、描述、理解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仪式活动及其相关的组织和观念”,其次要在理论的层次,“换一个角度认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史、思想史、政治史和学术史”,进而要在实践的层次,“厘清民间信仰与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公民社会建设之间的密切关系”。[※注]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确已有大量经验、理论和实践层次的研究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些文章都带有反思性质,且都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给民间信仰实践带来的影响这一中心话题。例如日本学者佐藤仁史《“迷信”与非遗之间:关于江南的民间信仰与农村妇女的一些思考》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展开,只使得部分曾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民俗活动获得了合法的地位,而让剩下的不适合成为“非遗”的民俗,仍作为“封建迷信”存在,这只不过是“‘封建迷信’主流叙事的新面貌而已”。即便不再冠之以“封建迷信”的帽子,但将民俗文化视为“迷信”或“邪”的表象认知方式仍然根深蒂固。[※注]
叶涛《关于泰山石敢当研究的几个问题》回溯了“石敢当”成为“泰山石敢当”,进而在海内外得以广泛传播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当地政府提出了具体的保护建议,即“政府恰恰要做到有所不为——绝不为石敢当的产品开发、市场运作去买单,把精力用到前面所说的文化宣传、政策把关等方面上,把商业性的开发、创意产品的设计、市场的培育等交给企业去做、交给市场去检验”。[※注]
王霄冰有关祭孔礼仪的系列研究,一方面对其在当代社会的传承模式进行了总结,[※注]另一方面则探讨了这一祭典作为“非遗”项目应如何得到“本真”传承的问题。由于“祭孔大典”特别是其中的“祭孔乐舞”本身就带有表演性质,所以仪式展演的正当性不存在争议,但为了达成一种“表演的本真性”,她认为首先应制定一套相对标准的表演程式,[※注]其次,表演者和参与者都须怀有一颗“真诚之心”,不求“形似”,但求“情真”,以建构“非遗”表演的“灵韵”。[※注]
总之,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新鲜事物,民俗学者并非持观望或批评态度,而是积极投入到了研究和保护的实践当中。这也说明了民俗学是一门很“接地气”的学科。这里的所谓“接地气”,指的不仅仅是人类学家一贯强调的田野调查,[※注]而是包含了能够直面当下、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意思。不过,目前的研究多数还存在视角单一、田野调查不够深入的缺点,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拓展和加强。
第三节 从事象研究到事件研究
——以民俗关系为方法
陈进国曾指出,民俗学的民间信仰研究大多限于以下三种研究或写作范式:一是“通论性研究”的范式。即以概论或通论的手法描述民间信仰或其中的某一门类。二是“民俗事象研究”的范式。主要“吸纳了史学之重视考辨和文化重建的传统”,加之以搜集史料的田野功夫。事象研究的主题则大多集中在“神灵崇拜类型”和“特定信仰习俗”两大块。三是“民俗整体研究”的范式。即“从活态的信仰民俗事象入手,参与观察在特定语境下的信仰主体的存在方式和生活状态、历史心性和文化表情”。其“特点是重视当下的、日常的信仰生活,透过语境(context)看信仰民俗变迁,既审视信仰民俗事象活态的生成机制,也关照信仰生活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在突出民间信仰的‘民俗性’、‘民间性’、‘生活性’之余,该研究取向也关注‘宗教性’要素,诸如仪式过程、象征体系、主体灵验经验或体验、社区性的祭祀组织等等”。[※注]
上述的第三种研究范式的局限性,恰如陈进国所批评的那样,就在于往往把关注点放在“构成信仰底色的‘语境’、‘生活’、‘整体’等等之上,难免忽略了民间信仰作为信仰要素——宗教性本身的整体性思考,如宇宙观、崇拜体系、仪式与象征体系、信仰体验等”;同时,在使用以社区等“微世界”为中心的田野调查方法时,又不如人类学者娴熟,故而未能“将民间信仰放在社区的宗教生态处境中考察”,以至于一些民俗志的“立体深度”还赶不上传统的民俗事象研究本身。[※注]
陈进国在反思现状之后曾提出如下疑问:“在‘地方’的民间信仰研究当中,关注语境的民俗学家止于何处,非‘民俗学的叛徒’止于何处?”[※注]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得在民俗学自身的学术史中去寻找。民俗学的研究取向实际上并不完全局限于静态的事象或“事象+语境”。在许多研究案例中,学者们都采取了在动态的事件中研究事象的考察方法。其特点是以民俗事件为中心,通过研究者的现场跟踪与亲身感受,发掘、记录事件过程中呈现出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王霄冰把这种关系统称为“民俗关系”,并将此定义为“民(民众群体)与俗(知识体系)的关系”,在类型上有传承型、革命型与认同型等。[※注]考虑到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民”的民俗主体经常都不是一个均质化的存在,而是由多元主体以各种方式组合而成的社会/文化共同体,所以民俗关系也应是反映在民俗行为与民俗过程中的各种社会—文化关系的总和。它包括以下三种主要关系:(1)民俗主体(整体、部分或个人)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2)民俗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3)民俗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民俗学的研究目的,就在于揭示一种生活文化实践背后的各种民俗关系,进而挖掘其中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和精神信仰因素,即该项文化实践的民俗意义。
以第一种民俗关系为例,张士闪《灵的皈依与身的证验——河北永年县故城村梅花拳调查》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现代社会难得一见的案例。由于该村落相对比较封闭,历史系统保留比较完整,所以尽管村中人际关系复杂,但在民间信仰方面却体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村民普遍信仰梅花拳,尽管经历过岁月的洗礼,但直到现在,村中仍存在“泛梅花拳信仰”。[※注]
如果说上述案例反映出的民俗关系相对还比较单纯,民俗主体建构文化的过程脉络也较为清晰的话,那么,在刘晓春《“约纵连衡”与“庆叙亲谊”——明清以来番禺地区迎神赛会的结构与功能》[※注]、徐天基《地方神祇的发明:药王邳彤与安国药市》[※注]等论文中,民间信仰的仪式展演和神灵符号的建构过程都呈现出了地方社会结构与民俗功能的复杂性。民俗学家们在研究这类事件时,不仅着重于揭示不同人群与信仰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勾勒出了多元民俗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美国民俗学家诺伊斯(Dorothy Noyes)所说的“分裂的本土”。[※注]乡土社会的这种裂变在陈泳超所关注的山西洪洞一带“接姑姑迎娘娘”信仰活动中表现尤为明显。针对民俗的实践主体,他提出一个“民俗精英”的概念,并将“民俗精英”分为七个层级:普通村民、秀异村民、巫性村民、会社执事、民间知识分子、政府官员、文化他者[※注],并指出“民俗精英”之间“既互相联合,又充满纷争,总是维持一种动态平衡”。[※注]
应当指出的是,以事件为中心、通过跟踪事件过程来研究反映其中的各种民俗关系的调查方法,实际上并不是当代民俗学者的发明。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俗学的创始人顾颉刚在妙峰山香会调查中就使用了这种方法。妙峰山香会,从历史研究和民俗志书写的角度来看,可算是一种民俗事象。然而出身史学的顾颉刚却没有采取史学研究的方法,而是抓住了每年四月香客们“朝山进香”这一民俗事件,通过与香客们一道步行登顶,考察其中由实实在在的人所组成的香会组织,他们在进香中的活动,以及在活动中呈现出来的个体的信仰实践。[※注]
1996年,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30多名中外学者和研究生考察了河北省赵县范庄村的“龙牌会”,开启了当代民俗学范庄研究的先河。部分调查结果当年以专题形式在《民俗研究》发表。[※注]调查围绕“龙牌会”活动,从起会、准备供品、吊棚、迎龙牌,到正会、进香、送龙牌的整个过程。“龙牌会”的19位会头,参与活动的范庄人、外村花会,以及上述人员在活动中担任的不同角色,成为调查关注的重点。
此后,在叶涛《泰山香社研究》[※注]、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注]等研究中,事象与事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更为娴熟的应用。王晓葵、周星等在对为灾难死难者举行的祭祀活动进行研究时,则完全采取了以事件为中心的考察方法。[※注]这种调查方式,与人类学的长时期蹲点式调查有所不同。它强调的是在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流动的事件过程中,民俗学者把自己的身体变为工具,通过亲身参与以及与当事人的互动,感受和体会其中的民俗模式、民俗关系与民俗意义。这种身体感受型的事件调查法,是必须基于同族人或者同乡人的亲近感才有可能付诸实现的。
刘铁梁曾把民俗学定义为“感受生活”的学问。他指出,民俗学的独特性,应该表现在它直接面对生活本身时,会具有怎样的学术眼光和运用怎样的研究方法。民俗学者“感受生活的深刻程度决定着他研究的深度。劳里·航柯主张从‘民俗过程’的整体着手来发展搜集民俗的手段,争取获得‘深度资料’,这也说明了后来民俗学者对于感受生活中各种人的经验是越来越重视的”。[※注]显然,这里的感受所指的并不只是民俗学者个人的感受,而是包括了参与活动的所有人的感受。搜集他们的感受经验,即“个人生活史”,也就成了民俗学者调查的主要内容之一。例如叶涛《泰山香社研究》记录了邹城泰山香社香头刘绪奎如何成为民间信仰组织头领的个人生命史。[※注]徐霄鹰《歌唱与敬神——村镇视野中的客家妇女生活》聚焦于具有灵媒身份的“童身”秋分姑的得神经历,及其得神后家人的态度,和她本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及自我评价。[※注]
对于田野调查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尤其是在身体感受方面,彭牧在研究中践行着自己提出的“从信仰到信”的观察视角转换。[※注]在湖南茶陵农村调查纸扎技艺的过程中,她不仅从旁观察,而且亲自动手、跟随纸扎师傅学习纸扎,并对自我与当事人的身体感受加以细致描述。作者指出,作为传统学徒制核心的模仿和实践,“其本质上旨在通过长期的身体训练来特化和锤炼特别的感觉方式。因此仪式专家不仅凭借背诵秘传的文本,更通过学徒生活培养的训练有素的身体和敏锐的感觉而成为乡村社会中特别的一群”。[※注]
民俗学在民间信仰研究中可谓独树一帜,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上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探索将有助于宗教学的理论建构以及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面对目前民间信仰研究中的多学科参与现状,民俗学者更应该坚持事象研究与事件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提高观察、解读田野中的民俗关系的能力。研究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对其进行学理化的抽象,理应成为民俗学学科的追求方向与立足点。民俗学者应通过踏实、细致的田野调查,做出高质量的个案研究,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式,以与兄弟学科展开对话。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