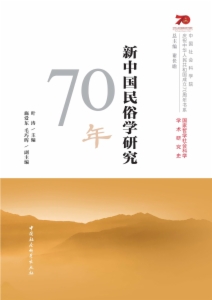第三节 新时期:民间文艺学的恢复及其文化学走向
|
来 源
:
|
新中国民俗学研究70年0 \ 上编 民间文学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8 | ||
|
摘 要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间文艺学得到迅速发展,但是1958年至1976年,作为学术研究的民间文艺学陷于停滞, 1978年开始恢复,新时期民间文学进入了另一个发展期。在钟敬文的论述中,集体性与口头性成为民间文学的主导特征,其他两个特征是在它们基础上的派生,而且它们成为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分水岭,因此民间文学的理论建构集中关注它的创作者与创作形式。从大文学理论到整体文学观,与韦勒克总体文学理念相吻合,可见中国民间文艺学自身的发展与西方也有可对接之处,只是后来的研究者在引进西方理论中一味强调西学,忽略了中国民间文艺学自身的发展,这就使得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中的自主性因素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深化。 | ||||||
|
关键词
:
|
民间文学 文艺学 民间 文学 民间文艺学 新时期 民间文学研究 集体性 文学艺术 民间文艺 民间文学范围 |
||||||
在线阅读
第三节 新时期:民间文艺学的恢复及其文化学走向
字体:大中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间文艺学得到迅速发展,但是1958年至1976年,作为学术研究的民间文艺学陷于停滞,1978年开始恢复,新时期民间文学进入了另一个发展期。
一 民间文学研究的恢复
20世纪70年代末,民间文艺学开启恢复重建旅程,首先就围绕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重新展开探讨。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中论述了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与变异性,这四种特征从8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处于高校民间文学教育的基础位置。其他还有姜彬、陈子艾等提到了民间文学的匿名性、“文学与非文学的双重组合性质”等。[※注]但他们的研究指向没将其置于民间文学的文学特性,而是逐步滑向民俗学,注重对民间文学的文化学意义的探讨。此外,段宝林强调民间文学的“立体性”[※注],刘锡诚则提出“整体研究论”[※注],他们关注到了民间文学的存在场域和生活特性。朱宜初、李子贤、陶立璠等则提到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人民性和民族性的特性[※注],但其讨论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
新时期有关民间文学研究中民间文学范围的讨论成为热点。对于民间文学范围的讨论是为了厘清它的边界,这一时期关于民间文学范围的讨论主要聚焦于:(1)民间文学与文学领域其他文学的区别。如魏同贤认为,“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群众创作、通俗文学、流行创作、民间语言、民间文艺、原始素材不同”。[※注](2)民间文学不能完全排斥书写。对民间文学口头性的狭隘理解,有将其简单化的趋向,特别是将它与书面完全对立。[※注](3)集体性与口头性是民间文学范围厘定的基本。“与专业作家文学和通俗文学相比,民间口头文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它是一种世代相传集体性的创作……口头方式是民间文学创作与传播的基本方式。”[※注]
“民间文学的分类理论是民间文艺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学作品品种多样,在形态上既相近似,又有不同,既有整体特征,又有个体表现。民间文学的分类学正是在这同和异中间求出规律。因此,分类的建立有赖于结构学与形态学的发展。”[※注]对于民间文学的分类,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一直伴随着民间文学范围的讨论,但并未出现专门的体裁学讨论。1949年以后,民间文学的分类基本参照作家文学体裁,但当时对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等并未专门进行讨论,比如当时对于“神话故事”“传说故事”等的并用,当下民间文学领域普识性的“四大传说”,在当时则为“四大传统故事”[※注]。新时期,随着民间文学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国家开启对于民间文学全面搜集整理工作后,民间文学保存就直接与分类相关。在1986年4月4—16日,中芬两国学者在广西南宁和三江侗族地区进行了联合考察和学术交流。研讨会论文共计30篇,其中专门讨论民间文学分类的有7篇,话题如此集中,可见分类对于中芬民间文学研究领域都是重要的问题,尤其与民间文学资料的保管、搜集直接相关。乌丙安《分类系统》以赫哲族《满斗莫日根》(Manduomelgen)和达斡尔族《阿波卡提莫尔根》(Apekati Melgen)、彝族阿细人《阿细卜》为例,指出在传统的分类体系中,这三者被归入英雄叙事诗、英雄故事和英雄祖先传说不同的类别,这一分类在当下须再讨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各民族、各地区体裁的特殊性已引起调查者的思考。尤其对于少数民族中某些特殊体裁如史诗,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注]《民族民间文学理论基础》[※注]中都单章论述,而非如其他概论性著作的体裁分类,将其与民间叙事诗归入一部分[※注];并且两部著作在具体的讨论中还对史诗的概念有所推进,过去史诗的研究,主要就是英雄史诗,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只有《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三大史诗,而否认或忽视南方少数民族苗族的《苗族古歌》、纳西族的《创世纪》《黑白战争》、彝族的《梅葛》《勒俄特衣》《阿细的先基》以及前文所提及的赫哲族、达斡尔族等东北少数民族的史诗。民间文学研究中对于分类的重视,既可推动民间文学理论的发展,如“以口头作品的题材、体裁和表现方法三结合的标准作为分类的出发点,在实践中可以比较准确地分辨作品的异同,也便于集中归纳资料形成的类别”。[※注]当然,那一时期对于民间文学分类的探讨出现了很多“削足适履”的现象,尤其是文类名称不结合“地方性知识”,以及劳里·航柯(Lauri OlaviHonko)所批评的“孜孜于孤立文化现象的研究……从书面上研究而脱离了其社会环境……不依照其在文化中的功用和结构而依其内容和形式予以分类整理”。[※注]但总体而言,民间文学分类的讨论推动了分类学以及民间文学基本理论的发展。
二 学人的思想应对
1978年4月,钟敬文、贾芝、毛星、马学良、吉星、杨亮才组成筹备组,筹备恢复民研会的工作,民间文学中断近十年后开始了新的历程。新时期民间文艺学的发展紧随当时的政治与学术形势,处于恢复与转折时期。从钟敬文、贾芝、毛星等学人的民间文学研究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二。
民间文艺学开始恢复之后,钟敬文在多次讲话与著述中均提到民间文学的特殊性[※注],这沿承了他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开始提倡的特殊文艺学之思想。在民间文艺学开始恢复并发生转折的新时期,他开始逐步构建这一特殊文艺学。他在《谈框子》中提出要突破狭隘化了的古为今用和一般文艺学的框架,这两点实际上是他的系统民间文艺学之通俗化表述。前者主要针对忽视民间文学与特定社会环境的关系[※注],后者主要针对民间文艺学中的作家文艺学模式。[※注]从陈述中可以看到他构建中国特色民间文艺学的框架,那就是民间文艺学一般理论、民间文艺学史和多视角的交叉研究。新时期钟敬文民间文艺学基本理论的构建主要体现于《民间文学概论》一书的编写。他在“前言”中陈述了自己的思想,即:民间文学跟它周围文化现象密切相关,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它在内容与形式上具有自己的特性。民间文学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变异性四种特征及其关系是多年来民间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在钟敬文的论述中,集体性与口头性成为民间文学的主导特征,其他两个特征是在它们基础上的派生,而且它们成为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分水岭,因此民间文学的理论建构集中关注它的创作者与创作形式。传承性与变异性,本来属于民间文学的内在研究部分,但由于其在四种特征中的派生性,它们一直没有成为钟敬文民间文艺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对它们的研究可以推演出民间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特殊性,从而丰富和扩充一般文艺学理论。[※注]对于它们的忽视,使得钟敬文特殊文艺学的解读外在性更为明显。钟敬文自己也提到,“我过去(1935年)虽然创用了‘民间文艺学’这个学科术语,并对它的对象、特点和研究方法作了简要论述,但是对它与作家书面文学的疆界,概念始终比较模糊,这种概念比较明确的出现,是近年来学界解放思想大浪潮影响的结果”[※注]。可见他自己也认可关于民间文学基本特征并没有实现自己特殊文学的界定目标。引文中的“大浪潮”从该文的写作年代,可知是指20世纪80年代中叶西方学术思想大规模引进,特别是文化学的引入。1986年开始,他的研究中出现文化学的转向,他著文《谈谈民族的下层文化》,这可以说是他民间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之思想的扩展与顺延。关于民间文学与社会生活、下层文化的关系没有指向民间文艺学的文学“特殊性”。
1976年以后,中断了近十年的民间文学研究开始了新的历程,在这一发展阶段,贾芝是该研究领域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从新时期开始至20世纪末学术主导思想变动不大,为了更清晰地展现他的思想脉络,此处将其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学术进行集中论述。他的著述以及活动,可以分成民间文学、民族文学研究与探索;为新的论著所撰写的序文;国际交往三部分。1976年以后,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讲话》精神,重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事业发展源头的寻索”[※注],这句话道出了他学术研究的原点与终极追求。他积极整理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民间文学资料,编辑出版了《延安文艺丛书·民间文艺卷》[※注]《中国解放区书系·民间文学编》[※注]《中国解放区书系·说唱文学编》[※注],希望作为一个亲历者为后人的研究提供资料基础,从他的序言以及内容编排、体例等方面可以看到他从文艺视野对民间文学的定位。在他的思想中,民间文学作为艺术具有强大魅力,它属于文学殿堂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具有文学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功能。他重视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新时期他积极推进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主编《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成为他事业的核心。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他将民间文学当作人民的诗学,与作家文学并存于文学领域,同时又将民间文学视为文学之源。[※注]他希望民间文学最后能为国家政治思想与民众生活服务,而不是单纯追求学术研究,这与他的经历以及身份是相符的。他遵循《讲话》精神,围绕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开展自己的学术与活动,具体表现在人民的诗学与根植民间两个方面。他对于民间文学更注重的是它与作家文学之文学的共通性,在他的研究中,重点不是析分这两种文学,更注重的是为民间文学在文学领域争得一席之地,让民众的文学为民众服务,因此他的研究更多呈现出的是一种活动,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学者与民众的对接、书斋与田野的对接、民族与世界的对接”。[※注]不可否认,这种理念同时也给他的研究造成了一定局限性。在20世纪80年代学界出现文化热潮时,他关注过,对民间文学的多视角研究也持肯定态度,但是他的核心思想则没有动摇过。
毛星的民间文学研究,学人提及较少,如果从知识积累的学术史而言,他在民间文学领域的成果不算很多,但从思想史来说,他对民间文艺学则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民间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调查研究和文学艺术特性两方面。前者主要是20世纪50—60年代,他带领中国科学院与民研会的成员到云南对少数民族进行调查,他提出自己关于实地调查的见解,当时在民间文艺学界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极大影响了民间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关于文学艺术的特性,他强调文学艺术的现实性与阶级性,认可形象是文艺的基本特性。他认可民间文学可以成为多学科研究对象,也可以从多角度探析,但是民间文学范围的界定必不可少。他提到,为了减少误解,可以重新运用新的词语指称自己的研究,这一点是可取的,同时也能减少民间文学不必要的学科纠纷与危机。他明确自己对民间文学的观点,其归属于文学艺术,同时它自身又具有独特的艺术特性,虽然他没有进一步阐述,但他的这一研究指向则非常明确,只是后来的学人并没有沿承他的思考路径。[※注]调查研究和文学艺术特性两部分研究贯穿了他的整体文学观之基本思想。毛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间文学调查,就一直努力实践自己的整体文学观思想,后来则与贾芝、钟敬文、马学良等一起推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他主持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空白,对于中华完整文学史的建构更是意义重大。[※注]1979年钟敬文提出民间文学是总的文学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它与作家文学、通俗文学共同构成文学。[※注]毛星的整体文学思想则是对钟敬文大文学理论的一个推进,这一思想影响着民间文艺学领域,最显著的就是《中华民间文学史》的编纂,该著从体例到布局都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承继与发展。[※注]从大文学理论到整体文学观,与韦勒克总体文学理念相吻合,可见中国民间文艺学自身的发展与西方也有可对接之处,只是后来的研究者在引进西方理论中一味强调西学,忽略了中国民间文艺学自身的发展,这就使得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中的自主性因素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深化。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