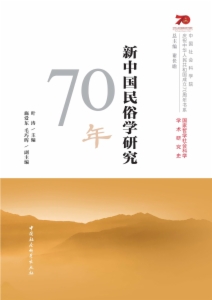第一节 神话的界定:多元化视角
|
来 源
:
|
新中国民俗学研究70年0 \ 上编 民间文学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31 | ||
|
摘 要
:
|
“神话”这一学术概念,自19世纪末经由孙福宝、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假道日语从西学中引进中国以来,对其概念界定问题的讨论从未间断。针对西方神话定义的局限性,杨利慧也曾提出质疑,她认为“神圣性”作为神话定义的必要条件,并不能准确客观反映神话存续的社会事实。多元化的视角,为深入认识中国神话提供了全方位的观照,中国神话的厚重积淀、广博涵括、复杂多元和重大意义都在对神话的界定中逐步显现,为进一步深掘中国神话学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 ||||||
|
关键词
:
|
神话 神圣 信仰 中国学者 广义 神话定义 中国文化 本原 词条 古史 西方 |
||||||
在线阅读
第一节 神话的界定:多元化视角
字体:大中小
“神话”这一学术概念,自19世纪末经由孙福宝、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假道日语从西学中引进中国以来,对其概念界定问题的讨论从未间断。尤其是1949年之后,中国学者对汉语意义上“神话”概念的界定,出现了许多新的见解。
1949年以来中国学者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之下的“神话”概念界定,这种概念的表述以《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神话”词条为代表。第一版该词条的执笔者是张紫晨,认为神话是:“远古人民表现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它是人类早期的不自觉的艺术创作。神话并非现实生活的科学反映,而是由于远古时代生产力的水平很低,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自然现象和原始社会文化生活的起源和变化,以他们贫乏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和客观世界拟人化的结果。”[※注]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外国文学卷,由刘魁立执笔的“神话及神话学”词条,也采取了相似的界定。武世珍1987年首刊的《神话思维辨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神话观有较为深入的讨论。[※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神话”界定表述方式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依旧是学界普遍采纳的主要神话界定方式。
基于对以往狭义神话界定的反思,袁珂于1982年提出了“广义神话论”。[※注]袁珂基于对中国古代典籍和文学文类的深入研究、考释,他认为中国神话的概念界定不能照搬西学。在中国古代,仙话、话本、传说等文类与后世所谓神话者难以分割,中国的神话体系也并不仅仅局限于“远古”时代,数千年来,神话叙事一直在发展。他认为:“广义神话,其实就是神话,它不过是扩大了神话的范围,延长了神话的时间;它只是包括了狭义神话,却并没有否定狭义神话。”[※注]袁珂的广义神话论是中国学者基于中国实际的理论创建,在海内外神话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如果说袁珂的“广义神话论”拓宽了神话的外延,那么吕微对神话的哲学界定则深化了神话的内涵。吕微认为:“神话的信仰—叙事(或叙事—信仰)原本就是人的本原性存在的实践行为,而在人的本原性存在的实践行为——这里指的就是神话的信仰——叙事行为中,神话信仰—叙事的内容和形式是无以(也无须)区分的:神话叙事的内容就是其信仰的形式,而其信仰的形式也就是其叙事的内容。”[※注]吕微站在先验论的立场上,批评经验论的神话定义容易陷入自我矛盾。他后来进一步解释,“所谓‘神话’,讲述的就是人对人自身最本原、最本真的道德性、超越性、神圣性存在的信仰形式和信仰对象的信仰故事(形式优先的‘神话’形式—内容双重定义)”。[※注]吕微的观点对中国神话学来说尤为可贵,其哲学思辨对反思“神话”概念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运用有重要价值。
对于“神话”在中国语境中的意涵,陈连山的观点指出了其中的要害。陈连山认为西方式的神话定义对中国神话的实际情形来说并不完全适用,在中国文化中,类似于“神话”这样的神圣叙事往往与“历史”概念有联系。陈连山明确指出西方“神话”概念在中国的运用存在局限,很大程度上,中国古代用“历史”概念包括了“神话”概念。[※注]他在《论神圣叙事的概念》一文中说:“西方社会选择了神的故事作为其主要神圣叙事形式,而中国古代选择了古史作为自己的主要神圣叙事形式。神话与古史尽管在叙事内容上存在差异,但是其社会功能是一致的,且都被信为‘远古时代的事实’。”[※注]陈连山的见解揭示了中国神话传统有别于古希腊古罗马传统的特点,也即“古史”观念是比神话观念更为宏观的神圣叙事系统。这一点,在谭佳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神话学研究“神话—古史”范式的研究中也得到了更为细致的勾勒。[※注]
针对西方神话定义的局限性,杨利慧也曾提出质疑,她认为“神圣性”作为神话定义的必要条件,并不能准确客观反映神话存续的社会事实。[※注]“神圣性”的规定与中国古典神话的实际地位并不相符,并且当代社会中也存在大量非神圣性的神话创编、流布现象。基于这种考虑,杨利慧在探究中国现代口承神话时,倾向于借鉴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的“最低限度的定义”,也即以内容为主的定义。她认为:“神话是人类表达文化(expressive culture)的诸文类之一。它通常具有这样一些特点:是有关神祇、始祖、文化英雄或神圣动物及其活动的叙事(narrative),通过叙述一个或一系列有关创造时刻(the moment of creation)以及这一时刻之前的故事,解释神祇、宇宙、人类(包括特定族群)、文化和动植物的最初起源,以及现时世间秩序的最初奠定。”[※注]这一界定站在神话本体的立场上,较为恰当地提供了一个可供操作的神话定义。
除此之外,中国学者在神话思维问题上也有出色的研究成果。傅光宇的《三元——中国神话结构》[※注]受到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三功能论的启发,建构了中国神话的“三元结构说”。邓启耀在赵仲牧的指导下撰写了《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注]一书,该书基于中国哲学和中国多民族神话实例,较好地阐释了中国神话的内在思维结构,具有原创价值。
台湾学者对神话的界定也有许多新见。张光直在研究殷商历史时曾专门论及“神话”的界定。他认为神话定义的核心要素,一是神话最起码是一个“故事”,于中国古代文献而言一个神话至少包含一个句子;二是神话材料必包含“非常”之人物、事件或世界;三是神话持有者信以为真,且作为社会行为的基础。[※注]凡符合这三条标准的殷商材料,都被张光直视为神话材料。钟宗宪在其著作《中国神话的基础研究》中也意识到西方神话概念与中国事实的差异。他主张界定神话时从三个范畴即神话的起源、神话的意义、神话的表现形式来考虑。[※注]钟宗宪特别强调中西神话思维的差异,主张在中国神话材料的立场上界定神话。同时,也有学者从宏观的哲学层面界定神话,比如关永中认为,神话蕴意着“超越界的临现”,是一种“超越的统觉”。[※注]
总的来看,有关“神话”的界定问题呈现出多元视角的特征,但学者们共同强调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重新审视西方神话定义。70年来,这种本土问题意识以及本土的概念界定实践,超越了前贤成就,也逐步树立了中国神话研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多元化的视角,为深入认识中国神话提供了全方位的观照,中国神话的厚重积淀、广博涵括、复杂多元和重大意义都在对神话的界定中逐步显现,为进一步深掘中国神话学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