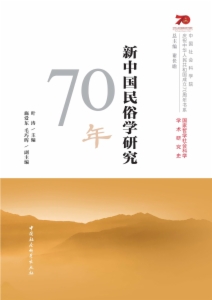第一节 以民歌搜集为主的采风运动
|
来 源
:
|
新中国民俗学研究70年0 \ 上编 民间文学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6 | ||
|
摘 要
:
|
集体性是民间文学的主要特征,而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往往也是集体性的活动,甚至会形成全国上下总动员、历时数年的大规模运动。” [ ※注]这次提出的全面搜集与忠实记录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原则被一直延续至今,而适当加工后来在某种程度上被表述为慎重整理,从1979年张紫晨编写《民间文学基本知识》 、 1980年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开始,各种民间文学概论层出不穷。几乎每种概论都会专辟章节来介绍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原则,但大多是全面搜集、忠实记录与慎重整理三点的复述。 | ||||||
|
关键词
:
|
民间文学 民歌 整理 采风 采风运动 歌谣 大跃进 调查 记录 少数民族 毛泽东 |
||||||
在线阅读
第一节 以民歌搜集为主的采风运动
字体:大中小
集体性是民间文学的主要特征,而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往往也是集体性的活动,甚至会形成全国上下总动员、历时数年的大规模运动。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活动即为采风运动。
1958年,“大跃进”开始,从国家领导人到知识分子,再到普通民众逐渐开始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抱有极大的自信与乐观情绪,这其中也包括民间文学,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大量涌现出来的新民歌。作为一种新的歌谣形式,新民歌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崭新的文学形式”,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歌,它受到当时“大跃进”思潮的影响,内容浮夸,主要以歌颂为主,往往表现出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幻想,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全民创作新民歌,对新民歌进行大规模搜集整理以及印刷出版被称为新民歌运动、1958年新民歌运动或采风运动。
采风运动缘起于毛泽东1958年3月、4月在成都和汉口的两次会议讲话。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举足轻重的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的采风运动全面开展。
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出现了创作、搜集、整理、出版新民歌的高潮,1958年《边疆文艺》中的一篇文章,描绘了当时采风运动的场景:
采风运动中,各省主要依靠汇总各县、区、乡搜集到的新民歌,自人民公社到县,再到州、市,层层编选,最后汇总到省“民歌编选委员会”“民歌搜集整理小组”等。在这期间,出版了大量的新民歌选集,从《红旗歌谣》《大跃进歌谣选》等全国范围的歌谣选,到各省的歌谣卷,再到《工人歌谣》《部队跃进歌谣选》《哲学民歌选》等各行各业的歌谣选,天鹰(姜彬)曾说道:“如果有人要问一九五八年在中国整理出版了多少民歌集子,就是最有本事的统计家,在短时间内,也是无法正确计算出来的。”[※注]
采风运动的过程虽然轰轰烈烈,但是并没有持续过长的时间,一般认为其结束的标志性事件还是毛泽东的一次会议讲话,1959年3月在郑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
至此,只能说采风运动开始落下帷幕,但是在民间还陆续有新民歌出现,之前采风运动期间搜集到的大量作品也过了若干年才出版“消化”完。
“大跃进”时期的采风运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究其原因,首先是毛泽东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的号召;其次在当时“大跃进”的乐观主义氛围下,群众运动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采风运动就成为全民参与的一项狂欢活动;最后,采风运动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前夕,所以这些能够体现各族人民社会主义意识以及农业、工业和文化“大跃进”丰硕果实的新民歌必然成为国庆献礼。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这场轰轰烈烈的采风运动的评价都偏向负面,认为这个时期所搜集整理的作品大多内容空洞、浮夸等,但是,当我们将视域扩展开来,并把聚焦点从新民歌上挪开,就会发现采风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我国民间文学的基础。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1949年至1958年采风运动之前全国各地就已展开了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活动,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对内蒙古、云南等地的民间文学调查,云南省人民文艺工作团对《阿诗玛》的搜集整理。而采风运动之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新民歌的创作热潮虽然逐渐消退,出版发表的新民歌也越来越少,但是各机构组织的民间文学调查活动依然延续,尤其是1962年《文艺八条》的制定,中国民间文学的调查活动再次掀起一个小高潮。
其次,正如刘锡诚所说:“对这次搜集民歌运动,应该一分为二,既不能像过去一些民间文学工作者们那样全盘肯定,也不应像有些文艺研究家们那样全盘否定。在全党动手搜集民歌运动中,各地编辑出版的民歌集,既搜集了大量的所谓新民歌(有些是‘浮夸风’的产物),也搜集了大量的旧民歌。”[※注]在“党委挂帅,人人动手”的采风运动中,全民都在创作新民歌、搜集新民歌、阅读新民歌,但是“旧民歌”依然存在,周扬1958年初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这是采风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文中说:“中国不但是一个具有丰富革命传统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具有长期灿烂文化传统的国家,这种文化传统的精华有许多还保留在人民中间。因此,除了大力搜集革命民歌外,还必须有计划地继续搜集和整理旧时代传下的民歌及一切民间文学艺术和民间戏曲。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的宝藏是特别丰富的,应当积极地加以挖掘和整理。”[※注]贾芝1958年7月9日在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上作了题为《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的报告,在批判厚古薄今倾向的同时也强调:“但是,这不等于说可以容许轻视至今仍然活在群众口头上的传统作品……传统作品,特别是各地方、各民族的著名史诗、传说,可以是长期研究的对象,但必须尽快地记录下来。因为这些作品多半保留在老年人的记忆里,若不赶快搜集,就会有失传的危险。”[※注]
随着这次运动的消退,被尘封在图书馆角落里的一册册新民歌集也逐渐发黄。但是,这个时期搜集整理的英雄史诗、民间故事、长诗[※注]却不断再版。仅1958年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搜集整理出版的长诗就有:彝族的《梅葛》《阿细的先基》、纳西族的《创世纪》《相会调》、傣族的《娥并与桑洛》《线秀》《葫芦信》《松帕敏和嘎西娜》《苏文纳和她的儿子》等。这并非“无心插柳”的结果,事实上,我们在回溯采风运动的同时,还应注意以下事件也在同时发生:1955年4月《民间文学》创刊,1958年7月9日至17日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三选一史”[※注]的实施、《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下发、“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十六字方针的确立等。
20世纪50年代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中央政府对中国有多少个民族以及各民族的具体情况都不是很了解,所以依照当时苏联民族学理论确定了当时民族学的四项任务:“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的研究以及关于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研究。”[※注]50年代分别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其中就包括了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尤其是传统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这些事件都促进了对传统民间文学的重视以及相对科学的搜集整理。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采风运动时期前后可以说是我国民间文学搜集的黄金时期,相较于之前,此时统一多民族国家已经建立,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开始增强,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进一步关联起来,这无疑使得民间文学的搜集,尤其是带有政治任务的普查性质调查工作能够更加顺利,“全面搜集”“大力推广”等原则得到更好的贯彻实施;而相较于之后,此时民间社会依然存在大量杰出的民间文学演述人,民间文学赖以生存的演述场域并没有完全消失。
采风运动除了为中国民间文学储备了大量的书面文本,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张紫晨、刘锡诚、仁钦道尔吉、李子贤、杨知勇等学界前辈都参加过这期间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活动,许多学者都将这时期的调查经历作为其学术生涯的标志性事件。数月的田野调查以及整理工作使他们受到了相对专业的学术训练,大量的活形态民间文学也对这些调查者尤其是在校大学生或多或少产生了文化震撼,而这种亲身体悟对于其之后研究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人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者转为民间文学研究者也都以此次调查为基础。
前文提出采风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我国民间文学的基础,除文本与人才的基础外,采风运动还奠定了中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范式基础,即确立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十六字方针”。
1958年7月北京召开了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贾芝在题为《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的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一全面搜集,重点整理……二大力推广,加强研究。”[※注]其中,全面搜集与重点整理为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原则,大力推广与加强研究是民间文学的应用与研究原则。全面搜集中的全面指的是全国各地方、各民族新时代和旧时代的各种各样的民间文学,周扬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也强调全面搜集的方针:“凡是今天在活人中流传的民间文艺,包括各种形式,全部把它搜集起来,不要把它看成封建的东西,好像‘古’呀、‘落后’呀,就歧视它。”[※注]总之,全面包括民间文学的时代、地域、民族、文类、载体、异文以及“优劣”等都要兼收并蓄。重点整理则是在全面搜集后所积累的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有选择的整理。在这份报告中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了“忠实记录、适当加工”的原则。忠实记录被认为是一切工作的基础,“作为科学研究资料,如果真伪莫辨,是无法判断问题的;作为文学作品,群众也喜欢看到真正的民间创作,而不要看涂抹得似是而非的东西;整理加工也首先需要有忠实的记录作底本”。[※注]而适当加工则是意在纠正当时民间文学界的“国粹主义”“烦琐主义”“一字不动论”。并且报告还提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即整理出两种版本,一个是用作科学研究资料,一个是用作文学读物。
当然,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十六字方针”很难切实得到贯彻。对于全面搜集的实践算是比较好的,但是一些文类如神话,以及与民间文学相关的一些民俗事象、宗教仪式等的搜集则相对薄弱;对重点整理中的重点把握也是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出发,像《嘎达梅林》《阿诗玛》这样符合当时价值观的代表性作品被一再整理,而一些民族真正重要的文本没有被发掘整理出来;关于忠实记录更难把握,尤其是搜集设备、翻译等因素限制,想要达到完全的忠实记录是不可能的;适当加工也会因不同的整理者有所偏差,有的可能只是在语言上进行润色,在文本整理阶段,当时流行一种做法是请来一些作家对文本进行文学润色,当然,有的整理者也会对情节进行一定的修改,如《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中就举例:“有人为了‘提高’思想性,将佤族故事的人与兽斗争的情节,改为农民与地主斗争的情节。”[※注]
这次提出的全面搜集与忠实记录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原则被一直延续至今,而适当加工后来在某种程度上被表述为慎重整理,从1979年张紫晨编写《民间文学基本知识》、1980年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开始,各种民间文学概论层出不穷,几乎每种概论都会专辟章节来介绍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原则,但大多是全面搜集、忠实记录与慎重整理三点的复述。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