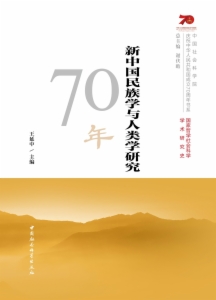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藏学研究领域的纵深发展
|
来 源
:
|
新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70年0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 | ||
|
摘 要
:
|
《通鉴吐蕃史料》《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藏族编年史料集》《清代藏事辑要》《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清代藏事奏牍》《唐宋元明清藏事史料汇编》(690余种)、《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200余种)、《元代至民国治藏政策法规汇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西藏历史档案丛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民国边政史料汇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续编》《民国时期藏事问题英文档案选编》《近代传媒与中国西藏的社会变迁》《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刘赞廷康区36部图志点校》《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等汉文史料的整理出版。 | ||||||
|
关键词
:
|
藏文古籍 藏传佛教 史料 档案 学界 民族 藏族社会 研究成果 学者 工具书 藏文文献 |
||||||
在线阅读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藏学研究领域的纵深发展
字体:大中小
一 藏学研究的全面发展
1966年至1976年,中国藏学研究进入了十年的沉寂时期。学科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时期发表的与藏学相关的文章仅325篇。1976年10月,五省区首次藏文协作会议在拉萨召开,中国藏学的研究局面一度出现好转。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全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1980年3月,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目标。在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理论战线、文化工作方面,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为藏学研究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进一步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尊重和继承西藏文化固有的优良传统,发展藏族的语言、文学、史学、艺术、医学等,建设具有西藏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藏学研究确立了主要研究对象和发展方向。
藏学研究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己任,服务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藏学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一些重大课题和项目由国家财政作为强大的后盾和支持。中央、省市区、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设立了各层次、各类基金资助藏学研究。代表性的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出版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各类项目基金,等等。仅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而言,目前设立有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后期资助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艺术学项目、学术期刊资助项目、特别委托项目、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据库的统计,与藏学相关的项目,1994年8项,占411项的1.95%;至2018年已达231 项,占6653 项的3.47%。25年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总数增长16 倍多,涉藏项目增长了近29倍。据不完全统计,1992—2018年,西藏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达404项。[※注]
改革开放和民族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全面推进了藏学研究走向繁荣发展。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等一些原有的基础性学科的研究继续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加强。一些应用性的新兴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等与藏学的交叉学科应运而生,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藏学学科从民族学学科中脱离出来。有关藏学学术论文比例增加,政策性新闻性报道时的文章比例日趋减少。从1977年开始。见于报刊的藏学文章逐年上升。学科类别达到了18个大类,43个子类,学术性文章比例大幅度提高。从 1980年开始,文章数量几乎每年以 10%的速度递增。1980—2018年,用汉文在全国各类报刊上发表的藏学研究论文或文章56700篇,其中1980—1990年的11年间为10300余篇,每年平均940余篇。从 1985年开始每年发表的文章数量突破了 1000 篇。1991—1995年发表的文章为8200 篇,每年平均1640 篇;1996—2004年13000篇,平均1440 余篇。2015年文章数量接近2000 篇。1979—2018年用藏文发表的学术论文近2万篇,其中1979—2014年间的论文有近17000篇,2015—2018年为2800余篇。[※注]政治研究仍是中国藏学研究的重点,政治通论和宗教事务工作方面的文章增长较多。经济研究迅速升温。有关西藏与祖国关系史、民族与民族史的内容成为研究重点。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类的研究得到加强。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著述和论文,东嘎·洛桑赤列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黄奋生编著、吴均校订的《藏族史略》、王尧、陈践的《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王尧的《吐蕃金石录》、王辅仁、索文清编著的《藏族史要》、才旦夏茸的《藏族历史年鉴》、毛尔盖·桑木旦的《藏文文法概论》、格桑居冕的《藏文文法教程》,等等,对中国藏学的飞跃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藏学界十分重视国外藏学的发展动态。改革开放以后,各地民族研究机构创办了多种主要用于介绍国外藏学研究的文集和刊物。如《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国外藏学研究选译》《国外藏学动态》《民族译丛》《民族史译文集》《民族文学译丛》《民族研究情报资料摘编》《民族研究动态》《世界宗教资料》等。《国外西藏研究概况》是一部单行著作,专门介绍了1949—1978年间的国际藏学研究。这些公开或内部出版的著作和刊物,以翻译国外藏学研究论文、介绍国外藏学研究状况、国外学者与中国的交流动态等内容为主,在改革开放初期开阔了国内学者的视野。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外学术交流活动更趋深入,但以翻译国外学者论文为主的刊物数量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萎缩,这种现象与中国学者外语能力的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有关。
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藏学界的许多重要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这其中包括几种类型:一是国外藏学研究的经典作品;二是外文档案;三是西方探险家的笔记;四是工具书;五是海外藏人学者的著述。另外有一些不适于公开出版的译著,作为内部资料供国内学者参考。
二 以藏汉文古籍整理和工具书为代表的基础性工作
藏文古籍整理和汉译工作是藏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藏族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不仅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而且用文字书写刊印了大量藏文文献,是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为藏学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了宝贵的资源。藏文古籍就数量而言,仅国内藏文典籍就有60万函。中共中央文件中曾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1995年底共出版藏文图书(包括重版藏文古籍)4513种。这些图书的出版一方面为广大藏族学者提供了重要文献线索。1950—1959年间重版的藏文古籍只有 10 种。1960—1979年间,藏文古籍的重版处于停滞状态。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稳定,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教育事业受到重视,藏文古籍的重版数量逐年增加。1980—1989年共重版藏文古籍123种,1990—1995年重版藏文古籍135 种,出版的藏文原著1411种。[※注]据不完全统计,藏文古籍已经整理出版4200本(辑)。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按照从远少到近多的顺序,已经完成普查登记的有那曲、阿里、林芝地区;正在推进的有拉萨、山南等地区。截至目前,西藏古籍普查已经完成1.37余万条、制作版本书影6.9万多幅,约1160家(其中102个私人)古籍收藏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注]以藏文古籍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为代表的出版机构,为藏文文献的出版发行搭建了传播平台。藏文古籍出版社自1986年成立至2013年,出版的“雪域文库”典籍有40 余种,约40万册。中国藏学出版社的《先哲遗书》“五明精选丛书”等产生了良好社会反响。1953年成立的民族出版社设有藏文编辑室,专门从事藏文古籍和出版物的编辑工作。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手段的巨大进步,藏文古籍文献在保护与抢救、开发与利用、古籍收藏与古籍研究、目录学、数字化信息服务、文献馆藏建设及与藏文古籍文献相关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
藏文《大藏经》内容广博,既是佛经,也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领域的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藏文古籍。历史上较为完善的写本藏文《大藏经》大约形成于公元14世纪初叶,主要有“那塘”“卓尼”“德格”和“库伦”等十多种版本。1987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四川成都设立了《大藏经》对勘局。对勘工作历时近25年,先后有200余位藏学专家和高僧受聘参与对勘工作,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藏文《中华大藏经甘珠尔》(对勘本108卷)、《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124卷),对保护和传承藏族传统文化、提高藏学研究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方便藏学研究工作者和普通读者的阅读使用,国家和各出版机构组织了许多精通藏汉双语的专家从事藏文古籍的汉译工作。大量重要的藏文典籍被翻译成汉语,例如《西藏王统纪》《西藏王臣记》《拔协》《青史》《红史》《新红史》《汉藏史籍》《安多政教史》《布顿佛教史》《贤者喜宴》《朗氏家族史》《萨迦世系史》《萨迦世系史续编》《娘氏宗教源流》《卫藏道场胜迹志》《历辈达赖喇嘛传》等。郭和卿、刘立千、王沂暖等诸多专家学者为藏文史籍的汉译工作和藏汉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涉藏汉文文献整理工作同样成就显著。汉文古籍从内容而言有官方文书档案、方志、私人笔记等不同的类型之分。代表性著作是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整理的“中国民族史地资料丛刊”和西藏社会科学院整理的“西藏学文献丛书”。前者主要是由吴丰培先生主持校订、整理,包括了清人关于边疆的史料30 余种,涉及藏区的有10余种;后者包括“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西藏学汉文文献别辑》及《西藏学参考书》4类,共200多种500余册。另外,《通鉴吐蕃史料》《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藏族编年史料集》《清代藏事辑要》《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清代藏事奏牍》《唐宋元明清藏事史料汇编》(690余种)、《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200余种)、《元代至民国治藏政策法规汇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西藏历史档案丛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民国边政史料汇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续编》《民国时期藏事问题英文档案选编》《近代传媒与中国西藏的社会变迁》《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刘赞廷康区36部图志点校》《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等汉文史料的整理出版,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的使用。
文献目录和工具书是研究的基础。随着藏学研究的发展,书目、文献研究方面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极大的进步,文献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成果丰硕,书评目录、索引资料和专著等相继问世,文献目录的整理研究更趋专业化、系统化、理论化。藏文文献的分类编目有传统的大小五明分类方法、喜饶嘉措提出的藏文古籍21种分类方法、拉卜楞寺图书总目17 种分类法、黄明信4 种分类法等。东嘎·洛桑赤列的《目录学》被认为是当今藏文文献目录的权威著作。[※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是清代西藏和藏族专题满藏文档案的检索工具书。该书共辑录条目13334 条,其中满文档案条目13040 条、藏文档案条目294 条,是研究清代藏族史的重要大型工具书。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各省档案馆也编辑了各自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在资料索引方面,刘洪记、孙雨志合编的《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收集了1996—2004年国内报纸杂志上刊载的藏学研究论文和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14000 余条,涉及报刊900多种2万余册,反映了中国藏学研究的成果和历史全貌。在工具书方面,由张怡荪主编的《藏汉大辞典》于1985年问世。2002年,《东嘎藏学大辞典》出版。由土登尼玛活佛主持编写的《藏汉大辞典》已经在国外出版了英文版。
三 藏族史学研究的继续深入
史学研究是藏学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研究成果集中的几个主要方向是:
第一,藏族通史、断代史和区域史方面。
通史方面有两部巨著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一是由包括台湾学者在内的全国近30 家科研机构、94 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历时14年完成的《西藏通史》。该通史共8 卷13 册850 余万字,是国内首部完整、全面、系统介绍西藏地方历史的通史著作,全面记述阐释了西藏地方从新石器时代起直至当代的地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宗教、军事、科技、交通、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研究重点侧重“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藏族与内地民族交往”“西藏地方历史自身发展特点”三方面。在编写通史的过程中,专家学者还整理出版了42册2000 余万字的《西藏通史·资料丛书》和10余册600 余万字的《西藏通史·专题研究丛刊》。二是藏文版《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该书是对传统藏族治史方法的扬弃,引用了100多部古代藏文史籍,时间跨度从藏族的起源直到1951年,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医学、天文历算、科技等各方面。
吐蕃史是断代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吐蕃时期的历史文献主要有金石、简牍和古藏文写本手卷等,还包括具有藏族特色的伏藏文献。这些文献以不同的载体形式记录了藏族社会在不同时期的各类重要事务和重大事件。学者对吐蕃史相关问题的探讨,不局限于吐蕃王朝的历史,在时间象限贯穿了从公元7世纪甚至更早期直到近代。相关研究大概可以归纳为几个主要类别和方向:一是有关吐蕃特定的制度、事件、人物等历史问题的研究,二是吐蕃与周边各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对古藏文文献和其他文献的研究解读,四是对吐蕃时期各种文化现象的描述和解析。
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藏文化内部可以划分为许多不同的亚文化类型。以语言和历史地理为依据区分的卫藏、安多和康区,在历史上有各自的发展历程。学者以不同的亚文化区域为研究对象,出现了很多区域史方面的佳作。更有学者提出了“安多学”“康巴学”等区域史概念。
第二,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藏族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研究方面。
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施政和管理一直是藏族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特别是到近现代,由于西方列强的干涉和藏族内部分裂势力的活动,在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何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对藏区实施更为有效的管理,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和研究。藏族与其他各民族关系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入拓展的议题,既包括政治关系,例如汉藏、蒙藏、满藏之间重要的政治互动关系,也包括大量的经济、文化、人员的相互往来。后者更是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鲜活例证。
第三,经济史、文化发展史、社会生活史方面。
藏区特有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学者在畜牧业、手工业、商业贸易、金融财政等方面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农牧业发展、茶马互市、边境贸易等都是经济史研究的经典话题。文化史研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对物质文化、观念文化、社会关系乃至深层心理的研究。藏文明在历史上有其自身发展的特点,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要影响。学界对藏文明的研究也有分析、评价和再认识的过程。社会生活史是近年来学界比较关注的话题,在方法论上受到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影响,突破了历史研究中政治、经济、文化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通过具象研究丰富和拓展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式,促进了交叉研究的发展。
第四,外国涉藏史方面。
外国涉藏史的研究涵盖了许多方面,比如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外国人在藏区的考察游历、基督教传播、藏区与周边接壤国家的关系等内容。帝国主义的涉藏活动和侵略、藏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反抗侵略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议题重点是通过档案和史料文献分析批判英、俄、美、日等国家及其代理人在各藏区的分裂活动,阐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青藏高原作为特殊的地理和文化单元,也吸引了不少科学家和怀有不同目的的旅行家和官员前来考察。他们的记录对了解青藏高原自然环境和藏族社会也具有研究价值。西藏与南亚次大陆的国家地区之间有源远流长的关系,既有文化传播、人员往来,也有各种纷争。随着中国学者对外交流的增加,一批利用国外档案和多种文献资料撰写的论文,推进了西藏地方涉外关系史的研究。《英国外交部涉藏档案选译》《民国时期藏事问题英文档案选编》《俄国与西藏:俄国档案文件汇编(1893—1914)》等英、俄文涉藏原始档案文献,被翻译成中文,更加便于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利用。
四 宗教学和宗教艺术研究向多元化发展
藏传佛教对于整个藏区的影响极为巨大,是藏学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从研究内容上划分,主要包括:宗教哲学、僧伽制度、教法史、宗教的社会功能等若干方面。与其他内容的研究成果相比,藏传佛教研究以藏文发表的成果比较多。
藏传佛教哲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印度、汉地佛教哲学和藏族本土文化结合而形成的产物,其理论系统博大精深。从宗教哲学的角度而言,学术界不仅继承了宗教教法义理等研究方面的传统优势,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等角度展开的宗教哲学研究正在拓展,视野不断开阔。在教法史方面,对藏传佛教各派教义思想展开研究的著作不断涌现。藏传佛教寺院是藏传佛教信仰的一种载体,其对于藏文化的保存与弘扬有重大意义。对寺庙经济制度、管理制度和文化教育的研究,是藏传佛教研究在内容上的深入和拓展。寺庙经济活动的内容、形式、发展方向,对宗教职业者和信教群众的经济生活,对藏传佛教自身的兴衰,以至对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从宗教的社会功能角度而言,学界还从更多的学科角度研究佛教对藏族社会的影响,反映出国内学界对于藏传佛教的研究已经从单一的研究方法向多学科、多视角的转变。
除了广受关注的藏传佛教研究以外,苯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藏区的传播,也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苯教是藏族的原始宗教,至今仍对藏族民众的宗教信仰和民俗生活具有广泛影响。藏族先民创造出以冈底斯山周边地区为地理中心、以苯教文化为信仰基础的古代象雄文化,既是青藏高原古代文明的源头之一,又是中华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远古起源之一,近年来逐渐受到学界和公众的关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由于受到藏传佛教的强势影响,在藏区的宗教文化中处于边缘地带但是研究成果却比较深入细致。比如学者对西方传教士的研究、对卡力岗人的研究,表明藏族公众的宗教信仰在佛教的强势地位下仍具有的多元化的存在。
从宗教信仰衍生而来的宗教艺术,是近年来最为活跃研究领域之一。藏传佛教艺术包括建筑、绘画、雕塑等形式,其中尤以绘画、雕塑两大类型占了较大比例,并受到考古工作者、文物工作者和艺术史家的高度关注。20世纪上半叶,西方艺术史研究中出现了图像学的研究方法。近年来,藏传佛教艺术研究中涌现了一大批活跃的专家学者,成果丰硕。他们从构图、造型、工艺等入手,不仅研究艺术元素和符号,而且研究宗教艺术的社会功能和观念表达,推动了艺术人类学等交叉学科的快速发展。
五 考古和非遗保护方面成绩斐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家有关部门的部署下,西藏文管会与相关省份考古工作者合作,先后于1984—1986年、1990—1992年分两次在西藏全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工作,不仅较为全面地掌握了西藏境内各类文物古迹及重要考古遗址的分布状况,而且调查发现和发掘了一批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考古资料。为研究西藏古代史提供了新的更为丰富的资料。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承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活性载体,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不仅代表着人类文化遗产的精神高度,更是国家、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近年来,对“非遗”的挖掘、保护、研究和利用的探讨与实践成为一种潮流。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