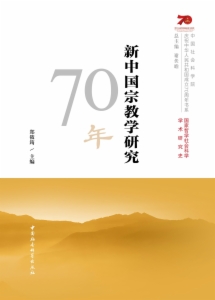第六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道教研究(1949—2019)
|
来 源
:
|
新中国宗教学研究70年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7 | ||
|
摘 要
:
|
道教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传统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将道教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方式,得到普遍认同,出现了几部具有开拓意义的道教史著作,如许地山的《道教史》 (上编) ,傅勤家的《道教史概论》 《中国道教史》 ,刘鉴泉的《道教征略》等。虽然此时研究道教的学者大都不是以道教作为其主要研究领域,属于附带性地研究道教文化,但这些学者又都是文史哲领域的学术大家,如刘师培、胡适、汤用彤、陈寅恪、许地山、陈垣、王明、陈国符等,故他们的研究成果,眼界高远,考证扎实,很多都是道教研究的名作,影响深远。 | ||||||
|
关键词
:
|
道教 出版 道教研究 道藏 中国道教 道教文化 道家 成果 整理 研究成果 碑刻 |
||||||
在线阅读
第六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道教研究(1949—2019)
字体:大中小
引言
道教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传统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道教形成实体,大约始于东汉后期,是在汉代黄老道家理论基础上,吸收古代神仙家的方术和民间巫术、鬼神信仰而形成的一种宗教实体。道教信奉“道”,主张通过精神形体的修炼而成仙得道。道教有其独特的教理教义、经典科书、神仙信仰和仪式活动,还有其独特的道派传承、教团组织、活动场所、教戒制度等,具有中国本土宗教的典型特征。道教实体形成后,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变更和文化潮流的演进而不断发展,至今绵绵不绝,已有约两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之一,曾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民族关系等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人格理想、审美情趣以及风俗民情等,无不烙印着道教文化的痕迹。因此,要想全面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就不能不深入研究和了解道教。
近现代学术界对道教的研究,大约起始于20世纪初,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早在1911年,刘师培先生发表《读道藏记》;1914年,黄季刚先生发表《仙道平话》;1921—1922年,陈教友先生发表《长春道教源流考》等,这些可以说是近现代道教学术研究最早的成果。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和文化人士对道教的起源和文化地位进行了思考,如鲁迅于1918年提出“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的断语,尽管没有详细论证,但这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对道教在中国文化中地位思考的开始。
1923—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其图书室“涵芬楼”的名义,借用北京白云观藏明代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进行影印出版,缩为六开石印线装本,装订为1120册,共印350部。这一整理道教典籍的举措,改变了长期以来《道藏》深藏宫观、鲜为人知的状况,使一般学人能够利用与研究,从而吸引了学术界的注意和兴趣,此后道教研究成果逐渐丰富起来。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道教研究呈现上升趋势,出现了不少学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将道教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方式,得到普遍认同,出现了几部具有开拓意义的道教史著作,如许地山的《道教史》(上编),傅勤家的《道教史概论》《中国道教史》,刘鉴泉的《道教征略》等。上述几部有关“道教史”的著作,具有填补空白和开创性意义。同时,道教的专题研究也出现了一些重要成果,如陈寅恪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胡适的《陶弘景的〈真诰〉考》,汤用彤的《读太平经书所见》,翁独健的《道藏子目引得》,吕思勉的《道教起源杂考》,陈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王明的《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周易参同契考证》《黄庭经考》《论老子与道教》,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等等。总之,这些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是道教研究的名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代道教界还有一位著名学者陈撄宁先生(1880—1969),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建中华仙学院,撰写了不少关于道教仙学的文章。他还主编了《扬善半月刊》和《仙道月报》,这是两份关于道教研究的早期刊物。
从20世纪初到1949年之前,属于道教研究的奠基阶段,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道教研究开始纳入现代学术的视野,并形成了一些开创性成果,奠定了后世研究道教的学术基础。这个阶段的道教研究,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一是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据初步统计,在这段时间发表的论文大概有200篇,专著十余部。无论是从研究力度,还是从成果数量来看,都比较薄弱。
二是研究成果多为名作。虽然此时研究道教的学者大都不是以道教作为其主要研究领域,属于附带性地研究道教文化,但这些学者又都是文史哲领域的学术大家,如刘师培、胡适、汤用彤、陈寅恪、许地山、陈垣、王明、陈国符等,故他们的研究成果,眼界高远,考证扎实,很多都是道教研究的名作,影响深远。
三是研究人员多为自发。据初步统计,这段时间涉足道教研究的人员大约有160人,他们的研究全都是自发的、分散的,并非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研究。[※注]
四是奠定了后来的研究范式。后世中国学者研究道教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大体于此时奠定。主要就是重视历史学和文献学的方法,善于发现新资料,能够广泛搜集、运用《道藏》和碑刻、方志等教外文献,进行道教历史的分析和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19年,正好70 周年。在这70年间,道教学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道教研究也出现了颇多新局面新气象,成就斐然。以下将对70年来道教研究的发展历程和重要成果进行简要总结,以此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第一节 中国道教研究70年的基本历程与主要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道教研究大致可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即前 30年(1949—1978)为第一阶段,后四十年(1979—2019)为第二阶段。在前30年中,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和“左”的思潮影响,道教学术研究受到一定的冲击,发展缓慢,但还是有一些学者继续从事道教研究,取得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成果;在后40年中,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带来学术研究的繁荣,道教研究也进入全新的时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40年来,道教研究大致经历了复兴、发展和繁荣的过程,成果大量涌现。为方便叙述这40年的研究状况,将以10年为一个小阶段进行总结,即分为恢复发展期(1979—1989)、繁荣兴盛期(1990—1999)、深入拓展期(2000—2009)、创新转型期(2010—2019)。
一 道教研究的缓慢开展(1949—1978)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政策,保障公民个人宗教信仰自由。1957年,中国道教协会(以下简称“中国道协”)成立。1961年,在中国道协成立了道教研究室,这是国内最早成立的道教研究机构。著名的道教学者、第二届中国道协会长陈撄宁先生亲自主持制订了研究计划,指导研究人员搜集整理文献资料,创办了当时宗教界唯一的内部刊物《道协会刊》,一些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和资料,发表在此刊物上,推动了道教研究的进展。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道教协会停止活动,道协研究室和《道协会刊》均停止工作。
在学术界,1949年以后,一些前辈学者如王明、汤用彤、陈国符等先生,继续从事道教研究,取得了非常有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的成果。但由于此时期政治运动不断,后来又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由此影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的开展,所以道教研究进展缓慢。这种缓慢不仅表现在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难以发表,而且也几乎没有新生力量投入到道教研究中来。特别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老学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其他学者也不敢从事学术研究,大陆的道教研究一度处于全面停顿状态。
尽管如此,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前,一些从事道教研究的老学者还是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在这期间,发表的论文有50篇左右,专著只有王明《太平经合校》等极少几部。研究路向还是延续之前的传统,以历史和文献研究为主,但研究方法和讨论问题都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如普遍关注农民战争、唯物唯心等主题。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方面的研究成果。
(一)道教历史研究
关于道教历史的研究,仍然是此阶段研究的重点。如1950年,陈寅恪发表《崔浩与寇谦之》;1963年,喻青松发表《道教的起源与形成》;1964年,喻青松发表《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同道教的关系》;而蒙文通的《道教史琐谈》,脱稿于1958年,发表于1980年《中国哲学》第四辑,也应属于这个时期的作品。
(二)道教文献整理与研究
在道教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成果较多。如1960年,王明所著的《太平经合校》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是系统整理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的力作。1963年,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由中华书局出版增订本,对1949年版进行了少量修订,并新增了《道乐考略稿》《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等附录。另外,还有一些学术论文也探讨了道教经典问题,如王明的《敦煌古写本〈太平经〉文字残页》《太平经目录考》,汤用彤的《读〈道藏〉札记》,陈撄宁的《〈老子〉第五十章研究》《〈南华内外篇〉分章标旨》《论〈四库全书提要〉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等。这些学者的文献研究,均延续了先前的学术传统,考证扎实,至今仍被视为名家之作。
(三)道教思想与哲学研究
在道教思想的研究方面,也有一些成果,如王明的《试论〈阴符经〉及其唯物主义思想》,汤一介的《寇谦之的著作与思想》《康复札记四则》。这时期在道教思想的研究进路上,大家普遍关注的是唯物和唯心的问题。
(四)道教外丹与医药养生研究
此阶段有几位化学史研究者关注道教,研究外丹,发表了比较重要的成果。如袁翰青写有《推进了炼丹术的葛洪和他底著作》《从道藏里的几种书看我国的炼丹术》等论文。同时,还有几篇介绍葛洪及其炼丹术的文章,如徐克明的《研究化学的先驱者——记我国古代的炼丹家葛洪》,陈曼炎的《我国古代化学家葛洪》。而化学家出身的陈国符先生发现,不搞清楚道教,就说不清楚中国化学史,于是他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花费巨大精力研读《道藏》,撰有《道藏源流考》一书,于1949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国符先生继续研究外丹,撰有《中国外丹黄白术史略》。1963年,《道藏源流考》出版增订本,其中就新增了《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说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外丹》等外丹研究的新成果。
关于道教与医药养生的关系,也在本阶段有所关注,主要集中于介绍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道士医家的医学成就,如邝贺龄的《晋代医家葛洪对祖国医学的贡献》,王明的《陶弘景在古代科学上的贡献》,方昭的《孙思邈——唐代伟大的医学家》等论文。
(五)道教音乐艺术研究
此时期对于道教音乐艺术,也有一些调查和介绍。如1957年,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油印的《苏州道教艺术集》,对于苏州道教音乐和舞蹈艺术等进行了整理;1958年,扬州市文联油印的《扬州道教音乐介绍》,对扬州地区的道教音乐进行了整理介绍;1958年,民族音乐研究所油印的《湖南音乐普查报告》,对湖南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进行了记谱整理和文字分析,该书于1960年由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另外,1963年,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增订本出版,其中新增了《道乐考略稿》一文,这是对道教音乐的历史文献学研究。
以上是 1966年之前,中国大陆地区道教研究的大致状况。1966—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泛滥,中国大陆地区的道教研究几乎完全停止,也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发表。
二 道教研究的恢复与发展(1979—1989)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克服多年来“左”的指导思想,按正确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进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五大传统宗教的组织教务活动得到恢复,各地寺庙宫观陆续修复开放。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带来了学术研究的繁荣,道教研究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专门的道教研究机构得以成立,专业的道教研究人才也不断培养出来,从此,道教研究步入崭新的历史时期,获得了蓬勃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在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间,道教研究获得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无论从研究的领域、研究的深度,还是成果的数量来说,都实现了快速超越。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1989年,共出版各种研究道教的著作26部,论文300多篇,超过之前30年的6倍以上。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以出版著作为例,不包括单篇论文)。
(一)道教历史与文化研究
20世纪80年代,道教研究恢复之后,研究的重点首先集中在研究道教历史,尤其是道教通史上。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研究室在20世纪80年代组织集体的力量,编写了国内第一部比较完整的道教通史《中国道教史》;[※注] 1987年,萧坤华翻译日本窪德忠的《道教史》出版;1988年,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第一卷)出版。这几部道教通史类著作的出版,标志着道教历史研究的新进路。
同时,道教断代史、教派史、区域史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如1985年,李远国的《四川道教史话》出版;1987年,王家祐的《道教论稿》出版;1988年,汤一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出版;1989年,詹石窗的《南宋金元的道教》出版;1989年,胡孚琛的《魏晋神仙道教》出版。这些断代或专题的论著,也反映了道教历史研究的深化。
(二)道教文献整理与研究
对道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也是本阶段研究的重心。首先是老专家的著作得以重印,如王明的《太平经合校》在1979年重印;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初版于1949年,修订重版于1963年,又于1985年重印。其次,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如1980年,王明的《抱朴子内篇校释》由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周士一、潘启明的《周易参同契新探》出版;1983年,王卡点校的《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出版;1983年,陈国符的《道藏源流续考》出版;1988年,陈垣等的《道家金石略》出版。另外,1988年,由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和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出版了大型道教典籍丛书《道藏》,该系列丛书是以中华民国涵芬楼影印本为底本缩印而成,共36册,该版《道藏》的影印出版,为道教学术研究的广泛开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总之,上述成果既有对《道藏》和专门经典的整理研究,也有对碑刻资料的搜集整理,反映了道教文献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三)道教思想与哲学研究
在道教思想与哲学研究方面,也出现新气象和新成果。1980年,卿希泰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第一部系统阐发道教思想的著作,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有关道教的学术新著。1985年,该书第二卷出版。1984年,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出版,里面的论文多是研究道家、道教思想方面的精品力作。
(四)道教文化与基础知识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出现文化热,主要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文化学成为道教研究的重要视角,出现不少关于道教与传统文化的著作。如葛兆光的《道教与中国文化》,卿希泰的《道教文化新探》,马西沙、王卡等的《道教文化面面观》,刘仲宇的《中国道教文化透视》等。上述著作从文化学的视角,将道教与其他宗教当成人类的文化现象,有利于解放思想,客观公平地进行评价和分析。
另外,还有一些介绍道教基础知识的读物,以及道教辞典等工具书的编纂。如曾召南、石衍丰的《道教基础知识》,李养正的《道教概说》,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辞典》,均有道教分支学科部分的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也对此部分进行了详细探讨。
(五)道教内外丹与医学养生研究
关于道教的外丹与科技、内丹气功、医药养生等方面,也是本阶段研究的热点,出版了不少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如何丙郁的《道藏·丹方鉴源》,张觉人的《中国炼丹术与丹药》,赵匡华的《中国炼丹术》等。另外,学者们还做了外丹黄白术模拟实验,公开发表的成果有孟乃昌的《汉唐硝石名实考辨》,郑同等的《单质砷炼制史的实验研究》等,都对道教炼丹术的研究有重要推进。
在内丹方面,李远国的《道教气功养生学》,王沐选编《道教五派丹法精选》,陈兵的《道教气功百问》等,主要从气功的角度研究道教内丹;在医学养生方面,有边治中的《中国道教秘传养生长寿术》,陈撄宁的《道教与养生》等。
总之,改革开放之后的10年间,道教研究获得快速恢复和发展,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出版著作近30部,论文300余篇,平均每年大概新增2部著作、30多篇论文。这样的数量和速度,不仅超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也超越了1900—1949年的近50年,可以说,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飞跃。那么,道教研究在此10年间能取得如此成就,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这主要表现在国家级研究机构的设立和专业型研究人才的培养,以及学术刊物的创办等。
首先是国家级研究机构的设立。1978年之前的道教研究,只是在少数学者当中分散地进行,很少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改革开放后,道教研究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了道教研究室;1980年,四川大学成立了以道教研究为主的宗教学研究所;198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宗教研究所。此后,其他一些科研院校也陆续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成立了道教文化研究室;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有专门从事道教研究的研究员,并有道教方向的硕士点;北京大学于1982年创办了中国大学的第一个宗教学本科专业,于1989年成立了北大宗教研究所;1984年,云南省社科院成立宗教研究所,主要开展云南道教的研究。这些国家级研究机构的建立,使得道教研究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能够形成一股集体攻关的力量,能够开展一些集体项目。事实上,当时的一些重点课题就是这样完成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研究室成立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集中力量研读《道藏》,花费几年的时间,集体编撰了《道藏提要》一书。同时,道教室还集中力量花费3年时间编写了《中国道教史》,该书是国内第一部比较完整的道教通史,在国内外影响深远。同时,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也在集体编写一部《中国道教史》,该课题列入国家“六五”规划。
其次是专门人才的培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都先后招收了道教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王明先生,自1978年开始招收道家哲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84年开始招收道教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也招收了攻读宗教专业的本科生,从而培养了一批专门从事道教研究的专业人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招收道教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同时,上海、四川、陕西等省市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通过公开招聘,从社会上吸收了一些中青年研究人员。另外,在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部门,还涌现了一批积极从事道教研究的学者。
最后就是学术刊物的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创办的《世界宗教研究》杂志,每期都刊载有道教研究的论文。1982年,四川大学宗教所也创办了以刊登道教研究内容为主的刊物《宗教学研究》,先在内部交流,出了六期;从1985年起,改为公开发行。另外,中国道教协会主办的《道协会刊》,也改为《中国道教》,公开发行。而陕西、上海道协还创办了《三秦道教》《上海道教》等刊物,进行内部交流。这些学术刊物的创办,为道教研究提供了发表和交流的平台,促进了道教研究的发展。
三 道教研究的繁荣与兴盛(1990—1999)
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10年,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道教研究开始走向繁荣。这种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学术研讨会的增多。在20世纪80年代,也召开过几次小型的学术研讨会。而到20世纪90年代,道教学术研讨会明显增多,规模也明显增大,研讨的内容更加广泛而深入。这些研讨会的举办单位,不限于内地科研院校等学术机构,更多的是学术界与道教界联合举办,有的是海峡两岸共同举办;有地方性的,有全国性的,也有国际性的,非常活跃。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大大推进了道教研究的繁荣。
第二,学术机构和学术刊物的增多。20世纪90年代,又有一些科研院校成立了道教研究机构或研究中心,如1999年厦门大学成立了宗教学研究所;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道家与道教文化中心;1999年,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成立武当研究院;1999年,山东师范大学成立齐鲁文化研究中心;1992年,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成立宗教研究室,1994年撤历史所改为历史宗教研究所,1999年正式更名宗教研究所。一些地方还成立了群众性的道教文化研究会,如泉州市道教文化研究会、湖北省道教学术研究会、天台山道教文化研究会、福州市道教文化研究会等成立并开展活动。除此之外,道教界自身也重视学术研究,中国道教协会于1989年成立了道教文化研究所,地方道协也相继成立了道教文化研究机构。同时,道教学术刊物也在增多,如陈鼓应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自1992年创办,到1999年已经出版了17 辑,每辑均刊登有道家道教研究方面的文章20余篇,有力地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厦门大学创办了《道韵》,每年出版1—2 期。在道教界,更多的地方道协也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如福建省道协的《福建道教》、河北省道协的《河北道教》等。这些学术机构和刊物的创办,反映了道教研究的繁荣发展。
第三,学术新人和学术成果的大量涌现。改革开放伊始,从事道教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不多,只有王明、汤一介、卿希泰等少数几位。他们培养的学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长,进入90年代,这批学者已经成为主力,并且已经成为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开始培养第三代人才。这样,随着学术新人的不断出现,道教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更是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这10年期间出版的各种专著、工具书、论文集、通俗读物等著作,有200 余部,平均每年新增20余部;发表的学术论文达数百篇,平均每年在50 篇以上。
20世纪90年代道教学术的繁荣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表现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也具有很高的水平,很多成果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以下就这期间出版的成果进行择要介绍。
(一)道教历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道教历史研究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研究室集体编写的《中国道教史》,于1990年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比较完整的道教通史。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四卷本《中国道教史》,于1988年出版了第一卷,1992—1995年又陆续出版了第二卷至第四卷。两部通史均是当时学术界中坚学者的集体著作,代表了当时道教研究的辉煌成就和最高学术水平,推动了海内外道教学的发展。
通史之外,在道教断代史、区域史、道派史等方面,也出版了非常丰富的成果,如李养正的《当代中国道教》,汤其领的《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史研究》,韩小忙的《西夏道教初探》,萧登福的《周秦两汉早期道教》等;在区域道教史方面,有杨立志等的《武当道教史略》,黄兆汉的《香港与澳门之道教》,赵亮等的《苏州道教史略》,樊光春的《长安·终南山道教史略》,赖宗贤《台湾道教源流》等成果;在道教宗派史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如郭树森等的《天师道》,张继禹的《天师道史略》,王士伟的《楼观道源流考》,黄小石的《净明道研究》等专题研究。
(二)道教文献整理与研究
对道教文献的整理仍然是此阶段研究的重点之一,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首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集体编写的《道藏提要》一书,于1991年出版,该书对《道藏》中的1400多种经书撰写了提要;其次是胡道静、陈耀庭等主编的《藏外道书》丛书,于1992—1994年由巴蜀书社出版,该丛书搜集整理影印了1000余种明《道藏》之外的道教典籍;再次,是汤一介主编的大型丛书《道书集成》,共60册,影印出版了明《道藏》及其未收或新出的道经两千余种,这些都是从提供资料的角度,对道教文献进行的影印整理。最后,尚有不少研究道教文献的著作出版,如朱越利的《道经总论》,卿希泰、郭武的《道教三字经注释》,饶宗颐的《老子想尔注校证》,杨明照的《抱朴子外篇校笺》等。
对于道教文献中碑刻资料的搜集整理,本阶段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有张华鹏等编的《武当山金石录》,王忠信编的《楼观台道教碑石》,陕西省耀县药王山博物馆等编的《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龙显昭、黄海德的《巴蜀道教碑文集成》,刘兆鹤等的《重阳宫道教碑石》等。
(三)道教思想与哲学研究
在道教思想与哲学研究方面,此阶段出版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如卢国龙的《中国重玄学》《道教哲学》,李刚的《汉代道教哲学》,陈鼓应的《易传与道家思想》等专著,对于道家道教思想和哲学都有突破性研究。此外,牟钟鉴、胡孚琛等主编的《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李刚的《劝善成仙——道教生命伦理》,姜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伦理论稿》,李大华的《道教思想》,吕锡琛的《道家与民族性格》,何建明的《道家思想的历史转折》,陈德安等的《道家道教教育研究》,王利器的《葛洪论》,张广保的《超越心性——20世纪中国道教文化学术论集》,姜生等的《明清道教伦理及其历史流变》,陈霞的《道教劝善书研究》等著作,亦对道教的伦理思想、心性思想、教育思想、劝善思想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
(四)道教文化研究与工具书编纂
对于道教基础知识的介绍,以及道教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仍是此阶段探讨和研究的重要路向,出版了不少相关成果。首先是朱越利等译、日本福井康顺等监修的三卷本《道教》,于1990年、1992年陆续出版,对于道教历史及其文化诸方面有比较全面的介绍。此后,陆续出版的著作有:卢国龙的《道教知识百问》,李养正的《道教与诸子百家》,刘国梁的《道教与周易》,张志哲主编的《道教文化辞典》,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1—4卷),郭武的《道教历史百问》,等等。
同时,此阶段还编辑出版了多部道教辞典,如1994年,闵智亭、李养正主编的《道教大辞典》出版;1995年,胡孚琛主编的《中华道教大辞典》出版;1997年,李叔还编的《道教大辞典》出版。这些道教辞典类工具书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道教学术研究的进展。
(五)道教内外丹与医学养生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道教内丹与气功的研究,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热点,在90年代初期,涌现出众多道家气功与养生类著作。如王庆余的《秘传道家筋经内丹功》,周晓云等编的《道家气功宝典》,胡孚琛的《道教与仙学》,郝勤的《龙虎丹道——道教内丹术》,等等。
在外丹方面,有金正耀的《道教与科学》,孟乃昌的《道教与中国炼丹术史》,陈国符的《中国外丹黄白法考》,容志毅的《中国炼丹术考略》等著作出版。
道教与医学养生的关系,更有不少学者关注,出版的成果有:洪建林编的《道家养生秘库》,洪丕谟的《佛道修性养生法》,陈耀庭、李子微、刘仲宇等编的《道家养生术》,孟乃昌的《道教与中国医药学》,张钦的《道教炼养心理学引论》等。
(六)道教与文学艺术研究
关于道教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是本阶段道教研究的热点之一,出版了相当多的成果。主要著作有:葛兆光的《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詹石窗的《道教文学史》《道教与戏剧》,伍伟民、蒋见元的《道教文学三十谈》,刘守华的《道教与民俗文学》,杨光文、甘绍成的《青词碧箫——道教文学艺术》,钟来因选编的《中国仙道诗精华》,黄世中的《唐诗与道教》,张松辉的《汉魏六朝道教与文学》《唐宋道家道教与文学》,潘显一的《大美不言——道教美学思想范畴论》,苟波的《道教与神魔小说》等。
道教与音乐艺术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此阶段也相继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如1993年,由王忠人、向思义、刘红、史新民、周振锡采录、记谱、编辑而成的《中国龙虎山天师道音乐》出版;王纯武、甘绍成的《中国道教音乐》出版;蒲亨强的《道教与中国传统音乐》出版。1994年,周振锡、史新民、王忠人、向思义、刘红合著的《道教音乐》出版。
四 道教研究的深入与拓展(2000—2009)
历史进入21世纪,道教研究承前启后,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的道教研究,继承传统,开拓创新,不仅在研究领域上不断拓展,而且在研究范式上有一些新的转变。此前的道教研究,侧重于对道教历史文化的解读以及对道教文献的整理诠释。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继承研究道教历史和文献的传统,研究不断深入;另一方面,人们开始较多地关注现实道教,并挖掘道教内部所具有的文化资源,以运用于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从而更多地关注和肯定道教文化的当代价值,这不仅体现了道教研究领域的拓展,更体现了道教研究视角和范式的新趋向。
21世纪的最初10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三个10年,经过前20年的积累,道教研究更是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范式有所转换。据初步不完全统计,2000—2009年的10年间,共发表道教相关学术论文上千篇,平均每年100 篇左右;出版道教相关学术论著约300 部,平均每年30部左右。
道教研究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与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的国内环境有关,道教学术研究也因此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这种机遇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学术研究机构的继续成立和学术刊物的创办;学术人才的培养和研究队伍的壮大;各种课题资助的数量和力度加大。
在此期间,一些大学的宗教所和研究中心成为重点学科或重点研究基地,出版多种著作和刊物,培养研究人才,有力地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如1999年,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并更名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以道教史研究、道教思想史研究为主要特色,承担了大量各级科研项目,培养了众多道教方向的研究生。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被正式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以研究所为主要依托的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学科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2001年,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成立道学研究中心;2006年,山东师范大学正式成立了全真道研究所;2002年,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成立,下设老庄学研究室、全真道研究室、地方道教研究室等专门研究机构,该中心于2009年获批为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3年,厦门大学成立厦门大学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创办学术刊物《道学研究》;2003年,西南大学成立宗教研究所,2004年开始招收宗教学硕士研究生;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华东师范大学明道道教研究所,开展正一道教史、上海道教史等课题研究。
与此同时,在道教学科人才的培养上,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成立较早的宗教(哲学)所系继续培养人才之外,其他院校随着研究机构的成立和科研骨干的引进,也成为新的学位授权点,培养了一批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学术新人不断涌现。如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挂靠历史文化学院,依托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在专门史学科点招收道家道教文化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培养了不少专门型人才。此外,如西南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兰州大学等,均可以培养道教方向的硕士生。
除此之外,在各级各类课题的申报上,道教学科也得到了较好的机遇。据统计,1991—1999年,道教学科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项目有24项,平均每年不足3 项。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2004年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国家项目数量大幅增加,道教学科也获得较多的资助。据统计,2000—2009年,道教研究项目共获得52项国家社科资金资助,平均每年有5项多。[※注] 在国家政策扶持和项目资助的良好环境下,我国的道教研究在21世纪初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道教历史研究
21世纪初,道教历史研究继续深化和拓展。20世纪已经完成出版了两部奠基式的《中国道教史》,此后这两部道教通史不断进行修订和重印。如2001年,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经过修订,分为上下册再版重印。在此期间,虽然有一些通史类新著出版,但都比较简略,而道教历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转向断代史、区域史、教派史等方面,出版了众多著作。
断代道教史方面,有张广保的《唐宋内丹道教》,李大华等的《隋唐道家与道教》,汤一介的《早期道教史》等;区域道教史方面更是成果突出,有郭武的《道教与云南文化》,樊光春的《陕西道教两千年》,福建省道教协会编的《福建道教史》,张宗奇的《宁夏道教史》,萧霁虹等的《云南道教史》,杨世华等的《茅山道教志》,任颖卮的《崂山道教史》等。
教派史方面,有王志忠的《明清全真道论稿》,张金涛的《中国龙虎山天师道》,赵卫东的《丘处机与全真道》,吴亚魁的《江南全真道教》,刘固盛的《道教老学史》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大大地丰富和深化了道教历史的研究,拓展了研究领域。
(二)道教文献整理与研究
关于道教文献的整理,在新时代也进一步深化,呈现出新的气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大型道教文献整理项目的完成和出版;二是宫观山志、道教碑刻、出土文献、敦煌文献等新材料的进一步搜集整理和出版;三是道教经典的专题研究。
自1996年至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文化中心与中国道教协会、华夏出版社等单位联合发起《中华道藏》的编修工程,这是明代以后中国首次全面整理编修《道藏》的大工程,全国各地科研院校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编纂和点校工作。2004年,张继禹主编的《中华道藏》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全书在《明道藏》的基础上,增补了部分黄老简帛书、敦煌道经写本、金元藏经刻本等,计1526种,分为49册,约6000万字。
除了《中华道藏》,还有一些大型文献整理项目也完成出版。如2005年,王卡、汪桂平主编《三洞拾遗》(全20册)由黄山出版社出版,共收录明道藏之外的道经200 余种。此外,陆续出版的《中国道观志丛刊》(全36册)、《中国道观志丛刊正续编》(全28册),也是大型道教文献整理项目,收录了近百部道教名山宫观的方志资料。
在新材料的发掘和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成果。如2004年,王卡的《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出版,著录敦煌道教文献800多件,含早期道教文献170 余种,其中有80多种是明《道藏》未收的道书。新材料的发掘,还表现在道教碑刻的搜集与整理,此阶段出版的成果有:杨世华主编的《茅山道院历代碑铭录》,赵世瑜的《北京东岳庙与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辑录》,张华鹏的《武当山金石录》,王宗昱的《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吴亚魁的《江南道教碑记资料集》,张泽珣的《北魏关中道教造像记研究——附造像碑文录》等。
除了各类文献的搜集整理,对于道教经典的专题研究也是本阶段的热点,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如王宗昱的《〈道教义枢〉研究》,俞理明的《〈太平经〉正读》,王承文的《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潘雨廷的《道藏书目提要》,陈国符的《陈国符道藏研究论文集》,任继愈主编的《道藏提要》(2005年第三次修订再版),郭武的《〈净明忠孝全书〉研究》,姜守诚的《〈太平经〉研究》,叶贵良的《敦煌道经写本与词汇研究》,丁培仁的《增注新修道藏目录》,朱越利主编的《道藏说略》(上、下册),郑开主编的《水穷云起集——道教文献研究的旧学新知》等。这些著作既有对道藏目录和经典的专题研究,也有对敦煌文献、田野文献的考察研究,反映了新时代道教文献研究的新进展。
(三)道教思想与哲学研究
在道家与道教思想方面,此阶段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出版了一些相当有分量的成果。如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思想史》(全四卷)于2009年出版,填补了道教思想通史研究的学术空白。此外,李大华的《生命存在与境界超越》,李申的《道教本论:黄、老道家即道教论》,詹石窗的《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刘宁的《刘一明修道思想研究》,吕锡琛的《道家道教与中国古代政治:道家道教政治伦理阐幽》,郑开的《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孙以楷主编的《道家与中国哲学》(全6卷),孙亦平的《杜光庭思想与唐宋道教的转型》,李霞的《生死智慧:道家生命观研究》,孔令宏的《从道家到道教》,章伟文的《宋元道教易学初探》,李刚等的《道治与自由》,金兑勇的《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的道教哲学研究》,刘笑敢的《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唐明邦的《论道崇真集》,丁常春的《伍守阳内丹思想研究》,吕锡琛的《道家健心智慧:道学与西方心理治疗学的互动研究》,李养正的《道教义理综论》(上、下编),朱晓鹏的《王阳明与道家道教》,孔又专的《陈抟道教思想研究》,朱展炎的《王常月修道思想研究》等著作,都对道家道教思想与哲学有深入的研究。
(四)道教科仪与法术研究
20世纪90年代前的道教研究,偏重于历史文献和哲学,随着道教研究的深入,关于道教制度、仪式和方术等领域也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关于道教仪式的研究,前期只有闵智亭的《道教全真科仪》,张泽洪的《道教斋醮科仪研究》等少量著作。21世纪初,这方面的研究大量增加,先后有闵智亭的《道教仪范》,陈耀庭的《道教礼仪》,任宗权的《道教科仪概览》,吕鹏志的《唐前道教仪式史纲》,卢国龙和汪桂平《道教科仪研究》等著作出版;在符咒法术方面,也有专门的研究,如王育成的《道教法印令牌探奥》,刘仲宇的《道教法术》,李远国的《神霄雷法》,张振国的《道教符咒选讲》等,都有一定的研究深度;关于道教戒律制度等,也出现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伍成泉的《汉末魏晋南北朝道教戒律规范研究》,唐怡的《道教戒律研究》,刘绍云的《宗教律法与社会秩序——以道教戒律为例的研究》等。
(五)道教内丹与医学养生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道教内丹与养生就一直是研究热门领域,进入21世纪,该领域依然热度不减,出现了不少相关著作。如张广保的《唐宋内丹道教》,戈国龙的《道教内丹学探微》,盖建民的《道教医学》,杨立华的《匿名的拼接:内丹观念下道教长生技术的开展》,张兴发的《道教内丹修炼》,戈国龙的《道教内丹学溯源》,谢正强的《傅金铨内丹思想研究》,杨玉辉的《道教养生学》,程雅君的《金元四大医家与道家道教》,黄永锋的《道教饮食养生指要》《道教服食技术研究》,詹石窗的《道教与中国养生智慧》,陈兵的《问道:道教修炼养生学》,胡孚琛的《道教与丹道》《丹道法诀十二讲》,霍克功的《内丹解码:李西月西派内丹学研究》,蔡林波的《神药之殇:道教丹术转型的文化阐释》等。
(六)道教与文学艺术研究
道教文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历来受到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关注,成果较多。21世纪初,道教文学艺术研究进一步深化,成果大量涌现,主要有:詹石窗的《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杨建波的《道教文学史论稿》,张松辉的《元明清道教与文学》《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孙昌武的《道教与唐代文学》《诗苑仙踪:诗歌与神仙信仰》,李生龙的《道家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吴光正等主编的《想象力的世界》,赵益的《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蒋振华的《汉魏六朝道教文学思想研究》,曹静芬的《唐传奇的道教文化观照》,吴光正的《八仙故事系统考论:内丹道宗教神话的建构及其流变》,李艳的《明清道教与戏剧研究》,黄勇的《道教笔记小说研究》,刘敏的《天道与人心:道教文化与中国小说传统》,霍明琨的《唐人的神仙世界——〈太平广记〉唐五代神仙小说的文化研究》,王汉民的《道教神仙戏曲研究》,左洪涛的《金元时期道教文学研究》,田晓膺的《隋唐五代道教诗歌的审美管窥》,苟波的《仙境·仙人·仙梦——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道教理想主义》,蒋振华的《唐宋道教文学思想史》,童翊汉的《中国道教与戏曲》,李小荣的《敦煌道教文学研究》等。
道教音乐的研究,也有不少新成果出现。如蒲亨强的《神圣礼乐:正统道教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刘红的《道乐论:道教仪式的“信仰、行为、音声”三元理论结构研究》,傅利民的《斋醮科仪天师神韵:龙虎山天师道科仪音乐研究》,蒲亨强的《道乐通论》,史新民的《道教音乐》,朱瑞云的《扬州道教音乐考》,刘红主编的《天府天籁——成都道教音乐研究》。
在道教美术、图像学方面,有王育成的《明代彩绘全真宗祖图研究》,胡文和的《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上、下册),肖海明的《真武图像研究》,赵伟的《道教壁画五岳神祇图像谱系研究》,胡知凡的《形神俱妙——道教造像艺术探索》,张明学的《道教与明清文人画研究》,许宜兰的《道经图像研究》等。
(七)道教外丹与其他科学技术研究
道教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道家思想中蕴含有丰富的科学思想,古代道士在炼制外丹的过程中,留下了众多涉及化学、物理、医学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总结,开展道教与科技关系的研究,也一直是学术界持续不断的关注课题。进入21世纪初,在道教外丹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新成果。如金正耀的《道教与炼丹术论》,容志毅的《道藏炼丹要辑研究·南北朝卷》,张觉人的《中国炼丹术与丹药》,韩吉绍的《知识断裂与技术转移——炼丹术对古代科技的影响》等,对道教炼丹术的经典和理论有所研究;关于道教与科技的关系,有詹石窗的《道教科技与文化养生》,盖建民的《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贺圣迪的《古树新枝:道教与中国科技文明》,姜生等主编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两晋卷》《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等著作出版,有力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
(八)道教与当代社会的探讨
新时期的道教研究,除了继续深化对道教历史、文献、思想等传统领域的研究外,人们开始关注道教与当代社会的关系,关注现实中的道教,并于现实生活中运用道教文化资源,因而对当代道教的研究大大加强。这与道教界本身的文化自觉,以及积极与学术界的合作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学术界本身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以及与国际交流的扩展有关。关于当代道教的研究,早在1993年,李养正就撰有《当代中国道教》一书;2000年,李养正的《当代道教》出版,可被视为关注和研究当代道教的代表作。
关于道教与当代社会的关系,既探讨道教文化的当代价值,也是本阶段道教研究的新动向。2002年,叶至明主编的《道教与人生》一书出版,收录了在庐山召开的两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探讨的主题是道教与现代文明、生活道教,反映了道教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道教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研究路向。
从2002年到2008年,中国道教协会连续举办了四届“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研讨会,从不同的角度和专题,学术界和道教界共同探讨新时期道教思想与当代社会如何适应的问题,并对道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005年,宫哲兵、陈明性主编的《当代道家与道教》出版,收录了海峡两岸当代道家研讨会论文61篇,主要围绕道家和道教学说在当代的发展和传承问题展开了研讨;2007年,卿希泰的《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研究》一书出版,该书着重探索了道教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及发展方向。总之,对于道教文化资源和现代价值的肯定和挖掘,是此阶段学术界研究道教的新路向。
五 道教研究的创新与转型(2010—2019)
进入改革开放后的第四个10年,也就是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道教研究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面对新时代的需求,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变化,主要表现为研究领域的深度拓展,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研究范式的逐步转型。近10年来,道教学研究在研究平台、人才培养、课题申报和刊物创办上,都有所创新和发展,为道教学术的繁荣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首先是道教研究机构、研究中心和学会的不断创立,为道教研究搭建了学术交流的平台和人才培养的基地。如2010年,四川大学成立老子研究院,创办《老子学刊》;西南大学于2010年成立宗教音乐研究所,2012年开始招收宗教学博士研究生;2016年,华夏老子学研究联合会和中央民族大学道教与术数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同年,山东师范大学成立全真道研究中心,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武当研究院更名为“武当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2018年,中国宗教学会道教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同年,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道家与中国思想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成立;2019年,四川大学成立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道教断代史研究中心、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研究中心等五个中心,西南交通大学成立西南交通大学中国宗教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道教学术研究的繁荣。
另外,各种学术刊物在此期间不断创办,为道教研究提供了发表和交流的平台。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科研机构相继创办了一些学术集刊,以刊登道教研究的最新成果。如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于2010年创办了《老子学刊》,每年出版一辑,自2017年改为半年刊,主要刊登道家道教思想和传统国学类文章;山东师范大学全真道研究中心于2010年创办了学术辑刊《全真道研究》,每年出版一辑,自2017年开始,每年出版两辑;华东师范大学明道道教研究所于2012年创办了学术集刊《正一道教研究》,每年出版一辑;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创办了学术集刊《中国本土宗教研究》,每年出版一辑;中国人民大学道教研究中心于2018年创办了学术集刊《道教学刊》,每年出版两辑。总之,这些学术集刊的持续出版,极大地推动了道教学术的发展。
从2010年至2019年的十年,道教研究成果突出,数量庞大。据初步统计,此期间共出版道家道教类著述400 余种,平均每年新增40余种;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的道教学术论文在2000 篇以上,平均每年在200篇左右。从成果的数量和研究的深度来说,应该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以下将主要以出版的学术著作为线索,从八个方面初步梳理最近十年间的道教研究状况。
(一)道教历史研究
道教历史研究是百年来道教研究永恒不变的主题和重点,在此期间的热点主要集中于道教区域史的研究,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先后出版了樊光春的《西北道教史》,黎志添等的《香港道教:历史源流及其现代转型》,赖保荣的《罗浮道教史略》,孔令宏等的《江西道教史》《浙江道教史》,林正秋的《杭州道教史》,吴国富的《庐山道教史》,朱封鳌的《天台山道教史》,佟洵主编的《北京道教史》,赵芃的《山东道教史》,刘庆文等的《河北道教史》,刘固盛等的《湖北道教史》等。
区域道教史还应包括域外道教的研究,近年来亦有不少研究著作出版,如孙亦平的《东亚道教研究》《道教在日本》《道教在韩国》,宇汝松的《道教南传越南研究》等,都是有分量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著作都体现了新时期学者们学术视野的扩大和研究的深化。
除了区域道教的研究之外,在道教通史、断代史、教派史方面也出版了不少成果。断代史方面,有刘屹的《神格与地域: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向仲敏的《两宋道教与政治关系研究》,姜守诚的《出土文献与早期道教》,姜生的《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寇凤凯的《明代道教文化与社会生活》,田茂泉的《清代道教“龙门中兴”研究——以秦陇鄂蜀及东北为中心的考察》,刘康乐的《明代道官制度与社会生活》,张方的《明代全真道的衰而复兴——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白照杰的《整合及制度化:唐前期道教研究》等。
教派史方面,有吴亚魁的《江南全真道教》,赵卫东的《金元全真道教史论》,李志鸿的《道教天心正法研究》,晏安宁的《道教全真派宫观、造像与祖师》,程越的《金元时期全真道宫观研究》,盖建民的《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论》(上、下册),汪桂平的《东北全真道研究》,尹志华的《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丁培仁的《元前道派研究》,张广保的《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刘莉的《道教天心派北极驱邪院研究》,曹群勇的《明代天师道研究》,李大华的《香港全真教研究》等。应该说,关于全真道的研究,是此阶段的热点,成果较多。除了上述专著外,山东师范大学赵卫东教授,于2010年与香港青松观合作,创办了学术集刊《全真道研究》,至今已出版七辑,刊载了大量关于全真道研究的最新学术论文。
与此同时,正一道、净明道的研究,也受到较多的关注,并出版了不少成果。华东师范大学明道道教文化研究所,与上海城隍庙合作,编辑出版了学术集刊《正一道教研究》,自2012年至2018年,已出版六辑,刊载了大量关于正一道研究的论文;而净明道方面,亦有不少成果,如许蔚的《断裂与建构——净明道的历史与文献》,许蔚校注的《净明忠孝全书》等。
(二)道教文献整理、典籍研究
道教文献整理与研究也是道教学永恒的主题和持续的热点。这十年来,学术界在道教文献整理方面更上一层楼,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明《正统道藏》作为唯一现存的《道藏》,是从事道教学术研究最基本、最必备的资料,中华民国上海涵芬楼曾对明《道藏》进行了缩版影印,发行数百部,有力地推动了道教研究。此后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推进,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台湾、日本和中国大陆又相继对涵芬楼影印版进行了重新影印,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资料需求。到了21世纪初年,关于明《道藏》的点校整理本《中华道藏》出版。21世纪10年代,对于明《道藏》的影印出版又掀起热潮——2015年,九州出版社以涵芬楼本为底本,重新影印了明《道藏》,名《涵芬楼本正统道藏》(全60册);2017年,何建明主编的《道藏集成·第一辑》(全108册)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该辑影印的明《道藏》,其文字部分以涵芬楼本为底本,而插图部分则扫描了国家图书馆藏的明版《道藏》,是更为清晰、更为完整的《道藏》影印本。
作为道教的基本经典《老子》,历代注释家众多,传世版本不可胜数,2011年,熊铁基主编的大型道教文化丛书《老子集成》(全15卷)出版,收录自战国至1949年关于《老子》的传本和注疏本,共265种,全部加以标点、校勘,重新整理,形成规范的、便于现代人使用的文本,是新时期道家道教文献整理工作的重大成果。另外,2018年,方勇主编大型丛书《子藏·道家部·老子卷》(全120册)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共收录《老子》白文本、节选本、稿抄本、批校本及研究著作共457 种,影印出版,集《老子》各种版本及研究资料之大成。
除此之外,此阶段在道教碑刻资料的挖掘整理上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学者们下功夫对地方道教碑刻进行持续的整理,并陆续发表了大量的成果。如赵卫东主持的山东道教碑刻的搜集整理,现已出版三辑,包括赵卫东主编的《山东道教碑刻集·青州昌乐卷》《山东道教碑刻集·临朐卷》《山东道教碑刻集·博山卷》等;又有樊光春主持的西北道教碑刻调查项目,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如《山西道教碑刻》已出版四册,包括阳泉卷二册、晋中卷一册、长治卷一册。此外,其他地区的道教碑刻也在陆续整理和出版,如萧霁虹的《云南道教碑刻辑录》,黎志添等的《广州府道教庙宇碑刻集释》,潘明权等的《上海道教碑刻资料集》等。其他省份如甘肃省、湖北省、河北省、东北三省等的道教碑刻,亦有学者在搜集整理,有的已经立项为各级课题,有的正在出版中。
关于藏外文献的整理研究,碑刻是近年来最大的热点,除此之外,在地方志、档案、出土文献等方面,也受到关注和挖掘,如何建明主编的《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全1200册)分寺观卷、人物卷和诗文碑刻卷三大系列,分类搜集了全国各地历代六千余种地方志中的佛道教资料。
关于道教典籍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特别是对重要道教经典的点校整理和研究,不断推出新成果。如武峰的《葛洪〈抱朴子外篇〉研究》,刘永海的《元代道教史籍研究》,刘屹的《经典与历史:敦煌道经研究论集》《敦煌道经与中古道教》,王卡主编的《中华大典·宗教典·道教分典》,汪桂平等点校的《齐云山志(附二种)》,陈文龙的《王契真〈上清灵宝大法〉研究》,周作明点校的《无上秘要》,王岗点校的《茅山志》,王皓月的《析经求真:陆修静与灵宝经关系新探》,夏先忠的《六朝上清经用韵研究》,刘祖国的《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研究》,张阳的《〈道枢〉研究》等。
(三)道教思想与哲学研究
关于道家与道教思想、哲学的研究,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版,不断有新的理论构建。关于《老子》及道家思想的诠释研究,旧有的成果不断再版,而不少新成果也相继出现,如刘晗的《〈老子〉文本与道儒关系演变研究》,许抗生的《老子与道家》(上、下卷)等;陈鼓应的《老子注译及评介》也有多个版本,2015年再次出版,其《庄子今注今译》于2016年又出版了最新版;詹石窗的《道德经通解》亦于2017年出版最新版。
此外,乐爱国的《中国道教伦理思想史稿》,何立芳的《道教社会伦理思想之研究》,罗中枢的《重玄之思:成玄英的重玄方法与认识论研究》,程乐松的《即神即心:真人之诰与陶弘景的信仰世界》,岑孝清的《李道纯中和思想及其丹道阐真》,隋思喜的《三教关系视野中的陈景元思想研究》,伍成泉的《道教的道德教化研究》,黄新华的《四海无波——道教的和平思想》,王闯的《清代老学研究》,陈霞的《道家哲学引论》,程乐松的《中古道教类书与道教思想》,吴根友的《道家思想及其现代诠释》,陈明的《全真道道德修养论研究》,杨普春的《汉魏南北朝道教身体哲学思想研究》,魏胜敏的《道藏传统生命观研究》,吴晓华的《章太炎道家思想研究》等,亦是道教思想研究的重要成果。2019年1月,王卡先生的遗著《道家与道教思想简史》出版,该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专业严谨的文风,勾勒出了从先秦道家到近现代约两千年的道家思想通史,是道教思想研究的最新重要成果。
(四)道教科仪与法术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道教制度、仪式和法术等领域,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和关注,研究成果也不断增多。最近十年来,主要研究著述有:张泽洪的《道教礼仪学》,李远国的《道教法印秘藏》,刘仲宇的《符箓平话》,吴羽的《唐宋道教与世俗礼仪互动研究》,任宗权的《道教手印研究》,刘仲宇的《道教授箓制度研究》,张振国等的《道教符咒大观》,姜守诚的《中国近世道教送瘟仪式研究》,王承文的《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高丽杨的《全真教制初探》等。另外,劳格文(John Lagerwey)、吕鹏志合作主编的《道教仪式丛书》计划首批出版15种,从2014年起陆续问世,目前已经推出的有:戴礼辉口述,蓝松炎、吕鹏志的《江西省铜鼓县棋坪镇显应雷坛道教科仪》;吕永升、李新吾的《师道合一:湘中梅山杨源张坛的科仪与传承》;叶明生的《闽西南永福闾山教传度仪式研究》。
(五)道教内丹养生与道教医学研究
道教内丹与医学养生研究,仍然是持续不断的热点,如胡孚琛的《丹道法诀十二讲》自2009年出版后,2013年、2018年又多次重印。此外,还有多本内丹养生学著作出版,如于德润的《长生久视:中华传统内丹学的现代转化》,杨玉辉的《中华养生学》,陈禾源的《武当丹道修炼》(上、下册),张义尚的《丹道薪传》,戈国龙的《道教内丹学溯源》,张钦的《仙道贵生:道教与养生》,丁常春的《道教性命学概论》,孔德的《道家内丹丹法要义》,陈兵的《道教修炼养生学》,霍克功的《道教内丹学》,徐刚的《生命哲学视域下的道教服食研究》,魏燕利的《道教导引术研究·东晋南北朝隋唐卷》等。
在道教医学方面,有盖建民的《道教医学精义》,何振中的《内丹医学思想研究》,崔仙任的《〈东医宝鉴〉道教医学思想研究》,张其成主编的《〈道藏〉医方研究》,金权的《中医运气学说与道教关系研究》等。
(六)道教与文学艺术研究
道教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进入21世纪,有更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参与道教文学艺术的研究,热度不减,成果众多,如张成权的《道家、道教与中国文学》,苟波的《道教与明清文学》,张泽洪的《道教唱道情与中国民间文化研究》,倪彩霞的《道教仪式与戏剧表演形态研究》,陈国学的《〈红楼梦〉的多重意蕴与佛道教关系探析》,申喜萍等的《玄风道韵:道教与文学》,孙昌武的《道教文学十讲》,雷文学的《老庄与中国现代文学》,陈耀庭的《全真道诗欣赏:全真道士的思想、生活和艺术》,张振谦的《道教文化与宋代诗歌》,成娟阳的《三界津梁:道教科仪文献的文学研究》,刘彦彦的《〈封神演义〉道教文化与文学阐释》,王志军的《南岳道教文学思想概论》,何江涛的《唐代丹道文学简论》等。
关于道教图像艺术的研究,近年来也成为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日益丰富。2012年,北京大学李凇教授的《中国道教美术史》第一卷出版;王宜峨也推出了道教艺术研究的系列成果,包括《卧游仙云:中国历代绘画的神仙世界》《玉宇琼楼:道教宫观的规制与信仰内涵》《陶铸永恒:道教神像的塑造工艺与经典造像》《道像庄严:壁画水陆画版画的神仙世界》等。此外,李俊涛的《道教图像艺术的意象与思想研究》,朱尽晖的《西部道教造像艺术研究》,张鲁君的《〈道藏〉图像研究》,谢波的《画纸上的道境:黄公望和他的富春山居图》,阳志辉的《道教与书法关系研究》等,都是道教图像艺术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在道教音乐的研究方面,持续有一些新成果涌现,如黄剑敏的《明清以来江西道教与地方音乐文化研究:以宜春、南昌、鹰潭为中心》,蒲亨强的《道乐探奥》(上、下册)、《道书存见音乐资料研究》,蒋燮的《畲客共醮,乐以相通:赣南道教节日祈祥法事科仪音乐研究》,胡军主编的《道教音乐研究文集》等。
(七)道教外丹与科学技术研究
关于道教外丹与科学技术的研究,此阶段的成果相对较少,主要有谢清果的《道家科技思想范畴引论》,蒋朝君的《道教科技思想史料举要——以〈道藏〉为中心的考察》,张中平的《〈淮南子〉气象观的现代解读》,刘芳的《道教与唐代科技》,韩吉绍的《道教炼丹术与中外文化交流》等著作出版。
(八)道教与当代社会的探讨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当代道教的研究大大加强,关于道教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以及道教文化的现实状况,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于是人们加强了对道教现状的调查,加强了对道教当代价值的挖掘,出版了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
2008年,《中国宗教报告》(宗教蓝皮书)开始出版,此后每年一辑,到2017年已编纂出版十辑,每辑都有当年的各大宗教报告。其中每辑都至少有一篇道教报告,对当年的道教大事及热点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如李刚的《新生态、新问题、新挑战下道教文化的角色功能》,王卡的《道教发展的新气象和新机遇》,李志鸿的《2010年中国道教的发展与思考》,陈文龙的《现代社会中的道教及其未来》,詹石窗的《2012年道教发展与养生问题考察》,汪桂平的《2013年道教发展与走向世界》,王皓月的《2014年传统文化复兴背景下的道教发展》,盖建民的《2015年中国道教发展及道教医学养生文化报告》等,这些报告以其现实性、及时性和连续性,成为道教现状研究的最新前沿成果。
此外,还有不少专著或论文集也在探讨道教的现代价值和当代发展状况,如陈霞主编的《道教生态思想研究》一书,对道教与当代生态保护问题进行多方位探讨;黄永峰的《道教在当代中国的阐扬》,对道教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及其未来趋势进行了专题考察;袁志鸿的《凝眸云水:关于道教文化的思考与阐扬》,对于道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传承和适应现状进行了多方位思考;王卡、汪桂平的《洞经乐仪与神马图像》,是对云南腾冲地区道教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成果;李延丰、隋玉宝主编的《融合创新发展:2016 中国“温州”新媒体和道教文化发展高峰论坛论文集》,董中基主编的《道教教义建构与文化传扬——第六届长三角地区道教论坛文集》,均探讨了道教文化发展问题。
总之,道教与当代社会的研究是21世纪以来道教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范式的创新,并在未来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第二节 新时期道教研究的展望与思考
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道教研究,从缓慢发展到繁荣兴盛,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道教研究也进入全新的时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道教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支,在机构建置、人才培养、刊物创办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道教学科体系。
新时代的道教研究,必将在70年来积累的巨大基础之上继续前行,在传承中创新,在发展中转型。展望道教研究未来的发展走向,大致会在以下方面进行继承和创新。
一 道教历史、文献等领域继续深化
道教历史研究一直是百余年来道教研究的主要脉络和重要领域,也仍然是未来道教学术的主流,将在研究的深度、广度和方法上进一步深化、细化和创新。如断代道教史(特别是宋元以后的断代史)、区域道教史(包括海外道教)、教派史等仍然是重点研究领域。道教通史也将在吸纳新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新的视角进行重新构建,如卢国龙主持的大型课题正在组织学者撰写十卷本的《道教通史》,樊光春也在编写道教学院教材《中国道教史》。
道教文献也是传统深厚、历久弥新的一个重点领域,70年来出版的学术成果难以计数,未来仍然是道教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并且偏向于一些大型集体项目。如规模宏大的“中华续道藏”工程已经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之中,全国百余名专家学者参与其中,预计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另外,敦煌道教文献合集、东方道藏、道藏集成、中华道经精要、道医集成等大型项目也已启动。
二 道教仪式、修炼、戒律、法术等领域重点关注,有待突破
道教仪式、修炼、戒律、法术等领域属于道教内部的信仰要求和行为方式,以前学者们虽有关注和研究,但偏重于历史和现状描述,近年来一些中青年学者开始借用人类学、社会学、图像学、现代科学等视角和方法来研究,有望实现突破和深化。如吕鹏志与劳格文(John Lagerwey)合作主编的《道教仪式丛书》,计划首批出版15种。卢国龙正在主持的“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课题,其中在“道门威仪”“道法修持”子项目上,研究进路也有所创新。
三 道教交叉学科具有活力
道教医学、道教心理学、道教图像学、道教文学、道教语言学等交叉学科虽然一直有学者进行研究,但兼具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相对较少,研究深度和广度也远远不够。随着中青年学者的成长和不同学科的交流互动,该领域正充满活力,潜力无限。
四 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创新
新时期的道教研究,范式转型和方法创新是时代的必然需求。老一辈研究者多为历史学、哲学、文学等出身,偏向于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新一代研究者更为多元,兼具考古学、医学、心理学、艺术学、建筑学等学科背景,研究方法偏向于交叉学科,研究视野也更为开阔。在借用和吸收西方研究方法的同时,学者们提出要“构建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注]。因此,构建和完善中国道教学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应是未来的必然之势。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