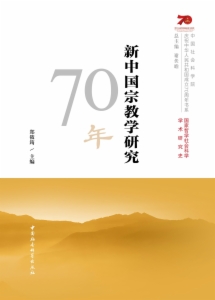一 佛教艺术领域
|
来 源
:
|
新中国宗教学研究70年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3 | ||
|
摘 要
:
|
石窟与佛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佛教美术研究进入全面开花阶段。另一方面,丝绸之路佛教艺术、西夏佛教艺术、佛教绘画等之前并未重视的研究领域得到了拓宽,特别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研究视野的开阔,如中印佛教艺术的交流,犍陀罗佛教艺术等出现在研究的视野之中。音乐、舞蹈与戏剧这一时期主要汉传佛教音乐研究成果有:田青的《中国佛教音乐研究的历史与未来》[※注] ,谢立新的《中国佛教音乐之初》 [ ※注] ,田青的《从“金瓶梅”看明代佛教音乐》 [ ※注] ,袁静芳的《中国佛教京音乐中堂曲研究》 [ ※注] 。 | ||||||
|
关键词
:
|
佛教艺术 藏传佛教 道教 艺术 佛教 佛教造像 音乐 雍和宫 石窟 中国佛教 造像 |
||||||
在线阅读
一 佛教艺术领域
字体:大中小
1.石窟与佛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佛教美术研究进入全面开花阶段。一方面,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寺依然是研究重点,大量学者致力于这些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丝绸之路佛教艺术、西夏佛教艺术、佛教绘画等之前并未重视的研究领域得到了拓宽,特别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研究视野的开阔,如中印佛教艺术的交流,犍陀罗佛教艺术等出现在研究的视野之中。在这一时间段重要的考古发现有,1990年发掘的宁夏贺兰宏佛塔天宫西夏文物、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新疆尉犁营盘汉晋墓地等,其中以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最为引人注目。这批造像数量达二百余尊,主要为北朝作品。像身多有贴金绘彩,其中有数件石像施以彩绘的卢舍那法界人中像,极为难得。此外,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原先重视不够的中小型石窟得到考察与研究,并出版了考古报告或精美画册。例如,江西赣州通天岩[※注]、陕西庆阳北石窟寺[※注]、河南新安西沃石窟[※注]、河北张家口下花园石窟[※注]、山东历城黄石崖[※注]等。其中西沃石窟的研究测绘,是因配合黄河工程而对石窟所做整体搬迁;下花园石窟则是对窟中积满的淤泥做了清理后,形成了考察简报。石窟摩崖刻经方面也有突出成绩:河北涉县中皇山北齐摩崖刻经洞[※注]、曲阳八会寺隋代刻经龛[※注]都有详细报道。关于山东摩崖刻经,还出版有《山东北朝摩崖刻经全集》[※注] 与《山东平阴三山北朝摩崖》[※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工具书是1997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我国学者不仅撰写了有关佛教艺术条目,还写出了东南、东北亚等各国的佛教的条目;季羡林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注] 也是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工具书。此外,重要图像资料《中国古建筑艺术大系》“佛教建筑卷”[※注] 公布了国内大量佛教建筑遗存;敦煌研究院主编的《敦煌石窟艺术》[※注],以单个重点洞窟介绍的方式公布窟内全部图像;北京大学考古系、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编著的《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注],详细披露了克孜尔石窟的结构、窟型、壁画等方面的内容。
在研究方面,金维诺、罗世平的《中国宗教美术史》[※注] 为第一部中国宗教美术通史,对历代宗教美术材料进行了系统梳理与研究。同时,敦煌、云冈、龙门等大型石窟依然是研究的重点。马德的《敦煌莫高窟史研究》[※注] 一书,系统梳理了莫高窟崖面窟龛的开凿情况和开凿历史;徐自强等主编的《龙门石窟研究》[※注],与龙门石窟研究所编的《龙门石窟研究论文选》[※注] 汇集了阎文儒、常青等学者的论文,从历史、宗教、艺术等方面,系统讨论了龙门石窟的佛教造像;温玉成的《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注] 一书,讨论了各大石窟的特点。此外,这一时期对于新疆、丝绸之路佛教艺术的研究逐渐兴起,如霍旭初的《龟兹艺术研究》[※注]《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注] 等,还有吴焯的《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注] 等专著。张广达、荣新江的《于阗史丛考》[※注] 一书中,有《于阗佛寺志》《敦煌瑞像、瑞像图及反映的于阗》等讨论丝绸之路南道佛教艺术的文章;姜伯勤的《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一书,对于新疆、敦煌的佛教艺术均有涉及。除大陆学者之外,中国港澳台学者对于佛教美术研究亦有突出贡献,如香港饶宗颐教授著有《敦煌白画》;台湾则有林保尧的《法华造像研究——嘉登博物馆藏东魏武定元年石造释迦像考》[※注],该书集中对东魏武定元年(543)造像进行了极为深入的研析;陈清香的《罗汉图像研究》[※注] 是第一部以中文写作讨论罗汉图像演变与发展的专著。建筑方面则对山西隰县千佛庵(小西天)大殿与彩塑进行探讨,学者得出了建于明、塑于清的确切年代的结论。[※注] 专题研究中有圣僧僧伽的造像及崇拜[※注];早期佛教初传时图像特征研讨也有深入[※注];密教美术方面,有吴立民、韩金科的《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注],该书详细地论述了供奉佛指舍利的法门寺地宫之设计、缘由及文化内涵,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
在蒙藏佛教方面,这一时期出版和发表的蒙藏佛教艺术研究著述逐渐增多,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视角更加广泛。学者们收集整理了大量相关材料,为我们研究蒙藏佛教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辅助作用。对于蒙藏佛教的重点寺院,出版了大量图书、画册,公布了寺院建筑、塑像、壁画、收藏品等珍贵信息。如波瓦·土登坚参主编的《雪域圣殿布达拉宫》[※注],该书是布达拉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际,布达拉宫管理处精心挑选了一批文物单独发表,并对这些文物的宗教、自性、历史、习俗、工艺理论等情况作了详细的研究。关于北京雍和宫就有《雍和宫志略》[※注]《雍和宫》(画册)[※注]、《走近雍和宫》[※注] 论文集等数本专门性成果。其他关于蒙藏佛教寺院的重要作品还有:杨时英、杨本芳的《外八庙大观》[※注],呼日勒沙的《蒙古族藏传佛教寺院大全——哲里木盟寺院》(蒙文版)[※注],嘎拉森的《蒙古族藏传佛教寺院大全二——昭乌达盟寺院》(蒙文版)[※注],阿日宾巴雅尔、曹纳木的《鄂托克寺庙》[※注] 等,以上研究成果主要梳理了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历史脉络,并通过调查与文献相结合为基础,阐释各寺院佛像的审美性与象征性,绘画的形式美与艺术美、绘画的题材特征以及文化特征,建筑的分布格局、选址特点与多元文化特点,并揭示了这一时期蒙藏佛教艺术的时代面貌。法国学者海瑟·噶尔美的《早期汉藏艺术》[※注] 一书,重点讨论了15世纪以前汉藏佛教的交流与融合。
2.单体造像
在这一阶段,由于1996年青州龙兴寺窖藏的发现,举办了大型展览,出版了画册类《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艺术》[※注] 等,使得南朝梁时期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来的新的佛教造像艺术为学者所重。虽然这一提法及传播路径还在讨论之中,但依然为时代学术现象。1991年,《东南文化》杂志发专刊登载此类“南传”系统的文章:阮荣春的《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续)》[※注]《“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概说》[※注],山田明尔、木田知生等的《“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概况及展望》[※注] 等文章,都对以青州造像为代表的“南传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梳理。区域性的研究有《论山西佛教彩塑》[※注] 一文,是金维诺先生为展览和随后所出画册而作,文章对山西境内、唐宋迄清各期彩塑,从题材、样式和内容等方面分别作了考察,为大家认识山西佛教彩塑这一艺术宝藏,了解整个佛教艺术的特色,提供了指南。还有《山东地区北朝佛教造像艺术》[※注] 一文,对山东地区的佛教造像进行了区域研究。在宗教仪轨和佛教造像的关系研究方面,有李翎的专著《佛教造像量度与仪轨》[※注],并尤以张总的《佛教造像与宗教仪轨的矛盾现象》[※注]成就最为突出。
这一时期对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刘宁、李玉玲主编的《佛教法像真言宝典》[※注],将原有的藏文、梵文译成英文、汉文,扼要说明了每尊佛的佛号、咒语、“种子字”,是研究佛教文化艺术的第一手资料;王家鹏的《藏传佛教金铜、佛像图典》[※注],是关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蒙藏佛教金铜佛像的代表性作品,作者在故宫博物院藏的藏传佛教造像、唐卡、法器等的基础上,汇集了国内外不同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图像近四百幅,并对其主题内容、艺术形式、地域特征、时代风格等进行了对比研究,论述精到,弥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中国台湾地区也举办了大型藏传佛教相关的展览,蔡玫芬的《皇权与佛法“藏传佛教法器特展图录”》[※注],共收录了123组文物,该书还阐述了清廷制作藏传佛教艺术品时对藏传佛教的态度、清廷制作藏传佛教艺术品的用途等情况,汉英文解图,是了解清代蒙藏佛教文化艺术的重要参考书。此外,还有《关于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展若干问题的讨论》[※注]《清代藏系造像艺术风格及其特征(续)》[※注] 等相关论文。
3.绘画与书法
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注] 涵盖了大量中国古代的佛教画家及其重要作品,是不可多得的工具书;徐建融的《佛教与民族绘画精神》[※注] 一书,从美学上讨论了中国佛教绘画的艺术特点;庞鸥的《试论元朝宗教状况与道释画之嬗变》[※注] 一文,讨论了元代流行的佛教绘画的特点、重要代表性画家;林树中的《李真真言七祖像及其他》[※注],讨论了唐代画家李真与其东传到日本的真言七祖像;法国学者乐愕玛的《揭钵图卷研究略述》[※注] 一文,梳理了关于中国古代的重要佛教绘画题材《揭钵图》的学术史。
在藏传佛教领域,费新碑的《藏传佛教绘画艺术》[※注] 一书,讨论了大量唐卡的题材、绘制技法;嘉木杨·图布丹主编的《雍和宫唐卡瑰宝》[※注],收入清代蒙藏佛地区活佛、高僧大德敬献给雍和宫的唐卡珍品63幅,该书图文并茂,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才让的《藏传佛教信仰与民俗》[※注] 一书,是利用唐卡等藏传佛教绘画进行宗教民俗研究的专著。
书法方面的代表性著作较少,田光烈在《佛法与书法》[※注] 中,谈到中国佛教书法艺术风采独特,包含写经与抄经、刻经、造像题记,有关佛事之碑铭、志、记,书法家手书之著述等几个类型。
4.音乐、舞蹈与戏剧
这一时期主要汉传佛教音乐研究成果有:田青的《中国佛教音乐研究的历史与未来》[※注],谢立新的《中国佛教音乐之初》[※注],田青的《从“金瓶梅”看明代佛教音乐》[※注],袁静芳的《中国佛教京音乐中堂曲研究》[※注],胡耀的《佛教与音乐艺术》[※注],周耘的《五祖禅寺佛教音乐述略》[※注],李宏如的《五台山佛教音乐现状》[※注],王日昌的《谈古代典籍中的佛教音乐》[※注],以上研究成果相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即学术研究队伍日渐扩大,研究对象呈现新颖、多样化的趋势,研究内容丰富化、研究视角开放化,尤其在以田青、袁静芳为首的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下,中国佛教音乐研究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
藏传佛教音乐、舞蹈的研究成果有:白翠英的《科尔沁的傩型戏剧〈米拉查玛〉》[※注],乌国政、李宝祥的《〈查玛〉探析》[※注],李军的《漠南蒙古“查玛”研究》[※注],莫德格玛的《蒙古舞与蒙古寺庙“查玛”》[※注],田联韬的《北京雍和宫“金刚驱魔神舞”音乐考察》[※注],乌兰杰的《清代蒙古族喇嘛教音乐》[※注],额尔德尼的《蒙古查玛》[※注],德勒格的《内蒙古喇嘛教史》[※注],郭净的《心灵的面具——藏密仪式表演的实地考察》[※注],罗斌的《“跳布扎”与“傩”——观雍和宫“打鬼”泛起的思绪》[※注] 等。在上述文献中,研究工作者从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对查玛乐舞的起源、角色种类、规模、内容与形式进行论述,其中田联韬的《北京雍和宫“金刚驱魔神舞”音乐考察》一文,作者以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查玛乐舞的音乐部分进行初步考察与分析,包括对查玛乐舞中的乐器类别、乐器形制、演奏方法、乐队组合形式、旋律进行、节拍节奏等诸多方面进行分析,弥补了查玛乐舞音乐研究部分,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
额尔德尼的《蒙古查玛》一书,是首部专题性研究查玛乐舞的著作,书中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查玛乐舞的形成与发展,种类、题材内容、服饰、面具、表演程序、乐器、乐队组合形式等,可以说是面面俱到,因此该书作为重要文献资料颇受学者们的青睐。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研究工作具有四个明显的倾向:第一,介绍查玛的起源、种类、规模、内容,其中查玛的历史来源问题,学术界尚存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查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羌姆”基本形态演变而来的密宗乐舞,认为无论是查玛的音译、历史渊源、服饰、面具、法器,还是表演程序等各方面都深深烙刻着佛教密宗乐舞的古老印记,这已是学界共识;另一种观点认为查玛来源于傩。第二,是对查玛的起源传说、查玛种类的划分持不同观点。第三,专题研究成果开始受到关注,说明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第四,研究方法呈现多学科交叉研究趋势。
蒙藏佛教诵经音乐研究是一门较新的研究领域,其研究起点较晚,只有部分学者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因此研究成果较少。主要成果有:乌兰杰的《清代蒙古族喇教音乐》[※注],呼和吉乐图的《内蒙古藏传佛教乐曲考》[※注]。其中呼和吉乐图在《内蒙古藏传佛教乐曲考》一文中,简要介绍了诵经音乐特点,并指出诵经曲可分为西藏风格、藏蒙合流风格和纯蒙古风格三大类,这也是在当时提出的比较新颖的内容,具有参考性价值。
在戏剧方面,周育德的《中国戏曲与中国宗教》[※注],日本学者田仲一成的《中国的宗族与戏剧》[※注] 等都从通史的角度梳理了佛教对戏剧的深入影响;余从等的《中国戏曲史略》[※注] 专门讨论了俗讲与变文对后世戏剧的影响;徐振贵的《佛教对戏曲艺术形式的影响》[※注]讨论了佛教与戏曲间的关系。佛教戏剧中的重要戏文“目连戏”在这一时期成为研究的重点,朱恒夫的《目连戏研究》[※注] 与刘祯的《中国民间目连文化》[※注] 这两本专著,以“目连救母”这一佛教故事为对象,进行了深入研究,讨论了目连戏的版本与流传。
显示更多